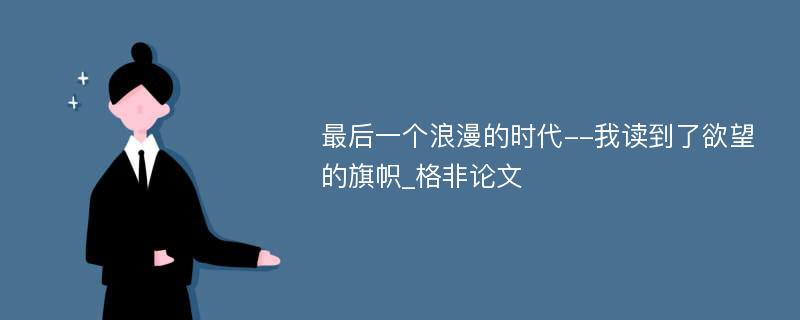
最后一个浪漫时代——我读《欲望的旗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旗帜论文,我读论文,欲望论文,浪漫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末世:思想的贫困
我不想把我们这个时代简单地描绘成一个贫困、衰退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在科学、艺术等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又确实难以掩饰其内在的贫乏本性。一个时代总是将它自己显现在它的宗教信仰里,社会形式里,最清晰的是,还显现在哲学与艺术里。沿着这条线索,就可以探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贫困本质:先是思想的贫困,再是情感的贫困,然后,经由艺术世界与外在生活将其传达出来。这条由里到外的线索在格非的长篇《欲望的旗帜》中得到了很准确的表现,并且,格非在这部小说中显露出了中国作家少有的勇气、高贵和对当下境遇的深刻怀疑。就这点来说,我非常喜欢《欲望的旗帜》里的孤寂品质,它将人存在的脆弱、矛盾和危机,人在他的世界里的陌生与恐惧,爱情的浪漫与诚实的丧失,人与人、人与自我隔绝后而有的孤独,以及在欲望这面最后的旗帜下,最后一点来之不易的爱与美的期待等,都表现得晓畅有力。作为一位严肃的思者,格非承担了一个作家与这个时代重要问题之间的冲突而有的心灵压力,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轻易和解这种冲突,而是将这种冲突继续在一些现代人身上(如曾山、子衿、张末,甚至贾兰坡、邹元标等人)。在面对人的困境这一问题上,格非显得温和而坚决,当贾兰坡自杀、子衿疯狂、张末站在车站上无所适从的结局渐渐显形时,我想,格非必须为挺住他的写作与生存而付出代价。小说的末了,张末在写给曾山的一封信中说,她差一点因着一朵玫瑰花就与这个乏味的世界达成了和解。我庆幸格非没有让她达成这种和解,这让我想起苏格拉底在死亡面前不妥协的坚决,我们时代是多么需要这种勇力和精神啊!
格非对我说,《欲望的旗帜》是他第一部写当代题材的小说。我也曾多次提出写作要“回到当代”,从这个立场出发,最能看出一个作家概括时代的洞察力与准确性。《欲望的旗帜》里,格非将爱情、理想、哲学、神学、宗教、艺术在末世(The end of the world)的经历与遭遇都陈明出来了,并且用小说的方式与之很好地相融,很不容易。格非笔下的世界,一如莎士比亚所说的是一个不透明的、密实的和非理性的世界;由于莎士比亚的思想十分接近中世纪的基督教,故这个世界在他那个时代只是一个预言,不可能存在,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已经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甚至格非在小说中重点写到的真实与幻觉,真实与谎言的界限的消弥,欲望对残存的爱情理想、单纯的感动的伤害,也像一个预言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逐渐应验。有一些东西正在越过理性与道德的界限,正在降低我们时代的存在质量,它是什么呢?
欲望。它几乎是贯穿《欲望的旗帜》的一个主词。欲望起源于情感的颓废,然而,在情感先颓废以前,思想已经先贫困了,这时欲望才乘虚而入,日益膨胀成为生成的主体。在这么一个浅薄且失去了永恒信念和神圣感的时代,现代人的信心已经腐朽,内心好像是一个欲望的加油站,无法再与真理达成和解,无法冲破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隔膜。没有人回到自己的内心,一切都越来越外在化了,这就是曾山与张末共同眷恋着爱情,却没有信心和能力来维持这种爱情的原因,它与张末眼中的音乐声、背带裤、一个男人带她回家的画面一样是一个梦想。同样的,子衿无法用正常的方式与人交流,(他是多么渴望交流!)贾兰坡教授在内心的冲突中被恐惧征服,都源于内在思想的贫困,贫困使人失去了力量。甚至严肃的哲学年会也落到了邹元标的游戏规则之中,它喻示着我们过去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已经瓦解。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可我们究竟要思想什么,我们的思想如何才能与我们的生活达成一致?
让我们一同来看一下思想贫困的内在秘密,以及思想如何决定和影响我们外在的生活。我相信,贾兰坡、子衿有私情、说谎等行为,在于他们的思想已经出问题了,他们分裂成了两个人: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这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就是所谓的自我冲突,而痛苦、绝望和疯狂都起源于这种冲突。在理解《欲望的旗帜》中围绕哲学年会而发生的种种现象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它与内在思想世界的关联。外在的现象是内心世界的产物,是随着内心世界而变化的;先有内在思想,然后才导致外在的现象,这是不变的法则。并且就道德而言,以内在为核心,如《圣经》所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这是从道德意义上说的。因为无论是原始人或文明而复杂的现代人,都是因为有内心思想才得以成人,并且每个人的内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现代的心理分析学也有同样的见解,学者们发现人和动物最大的差别,在于人对不存在的东西会产生恐惧——他们自己也对这种现象感到奇怪,因为他们不知这种恐惧从何而来。人头脑里的某种东西(不是外在的东西)使人类凸现出来,与其它生物不同。我们发现,人最大的特色是有思想的生命,这是内在的。人生活在自己脑海里的思想空间(并使用语言)中,这在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创世记》三章六节里,我们可以读到人类的堕落史:“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由此可知就道德问题而言,罪是由内在而起,然后便有外在的结果:“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显然堕落是由内而外的:人这一个体生命在他的思想世界中做了一个由始以来的第一次选择,便造成了对外在世界影响深远的事物——罪恶。诚如《圣经》上所描述的,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而创造的,先有内在思想的世界,然后才有外在行为的表现。我们的行为是由我们的思想而来,这虽然不是我们本质的延伸,但是却能彰显我们的本性。建筑师造的房子,虽然并非是建筑师本身的延伸,但是多多少少必能显示出他本质内的思想世界。因此,格非的写作,格非笔下的人物的言行,包括我在这里评论格非的小说,都寓有每个人的思想,不是随机促成的。杰格斯·蒙那德的机缘理论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这条由内而外的线索。
我说这些是为了确立一个与本源有关的思想背景,以回应格非在《欲望的旗帜》中大量涉及到的哲学、神学和宗教的深奥问题。在末世,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可真正对自己的生存负责的人又绕不过这个死结。贾兰坡教授将他的全部梦想都寄托在哲学上,这位斯宾诺莎的忠实信徒愤怒地对轻视哲学的夫人说:“倘若没有哲学,人与猪何异?况且猪也未必就不懂哲学。”哲学早已不能再给我们人生的正确答案。唐彼得、慧能院长等人进入神学与宗教领域,他们试图遗忘的那些疑问依然存在;子衿的困境在于无法活在真实中,他无法不说谎,是因为他没有信心辨认进入他眼中、头脑中的事实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幻觉,一如电影大师伯格曼所遭遇的难题;而曾山与张末则强行征用爱情,作为抵抗虚无、冷漠的最后一宗武器,可爱情却有一夜之间就消失的恶习。这些思想者,再也无法用强大的思想来达到想要达到的事,思想自身的矛盾、混乱和黑暗全都堆积在末世的思者身上了,我想起马克斯·舍勒尔的一句话: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谁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挣脱思想这一巨大的茧呢?
它的源流是这样的:以思想为主体的文化基础开始于希腊信仰,即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教导人的雅典城,它的方式是探查、追求、了解、分析、推敲。当年苏格拉底告诉人,真正的知识是从认识自己开始。如果认识自己是一切知识的根源,那么认识自己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到了柏拉图时代,他放弃了人类学,把研究重点放在唯心论上,他提到了“解脱”两个字,可我们怎样才能在有限的世界里得到解脱呢?到亚里士多德时代,他既放弃人类学,也放弃唯心论,注重现实世界、科学方法,这可能就是工具理性的哲学源头;到黑格尔、康德、笛卡尔等人所建筑起来的理性的统一性,则使人获得了强大的自信心。特别是达尔文进化思想的盛行,使人类获得了一种虚假的乐观;既然人已经从野兽的状态进化到了有道德的人性状态,那人类的明天一定会更伟大、更光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凡承受十九世纪黑格尔、孔德、达尔文、斯宾塞这些哲学家的思想,用理性或进化论来诠释历史的人,都没能逃脱这种乐观。可是,到郭尔凯戈尔、尼采、雅斯贝尔斯等人那里,共同产生了一种理性使人悲观失望,非理性给人带来快乐的思想。但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乐观,都成了他们思想的陷阱,神学家也不例外。本世纪初,新派神学家哈纳克、赫尔曼等人,就一面在神学课堂上教导人类是平等的,一面又在政治里赞成德国侵略别国。为什么?因为他们与哲学家一样不可能建立起一致性的系统理论和知识论,这当然也包括新正统派神学代表人物卡尔·巴特所持的“高等批判”——只要相信福音的意义,不相信福音的历史事实也可以——的错误思想在内。我还要提起神学家田立克在一战时期做军中牧师时写的一篇日记,他说:“我看见了瓦砾,我看见了断垣残壁;面前的废墟,在我看来并不是房屋倒下来,而是整个人类文化的解体,整个西方文明的倒塌,一切的乐观主义在这里结束了。”他看见乐观主义的虚无,也看见人为的神学是产生出来的,并不是世界真正的盼望,可就是这样一位田立克,临死前有人问他:“你祷告吗?”他却回答说:“不,我只冥想。”在冥想中死去的他也没有得到该有的慰藉,因为他和前面那些人一样,背后的思想基础错了。
我严肃地说,格非在《欲望的旗帜》里写到的生活的困顿、情感的颓废、哲学的苍白、交流的不可能、安慰者的缺席、宗教的虚空等,不是张末心中那个在午后庭院一个男人带她回家的梦想,或者子衿眼中的妹妹这些浪漫事物可以代偿的,它说出的不是个体的失败,不是历史性的失败,而是一个时代思想基础的失败,是神学性的失败。小说中写到的贾兰坡、唐彼得、慧能、曾山、张末、子衿等人的困境,以及由此滋生的惘然、冷漠、隔阂、放纵、绝望、自杀,都是因为他们置身于我上面所分析的错误的思想源流之中,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决定了他们必须遭遇历代思想者所遭遇到的困惑和苦楚。在末世这个关键时刻,哲学已失去了统一性,神学不再肯定神这一终极实在,宗教所出示的那套生存方法论又过于远离生活,甚至最高的艺术(音乐)所带给人的慰藉也已留在了过去的岁月里,那么,在人里面还有什么神圣事物能够救子衿脱离疯狂、张末脱离战栗,救老秦脱离欲望袭击他而有的痛苦呢?思想的贫困与失败必然导致生活与情感的失败。当人类失去了永恒信念这一故地之后,内心那个空洞一定是由像野草一样生长的欲望来填充了。
人与自我的分离
在具体分析欲望之前,我还要继续论到思想的贫困在人内心所造成的分离事件,即人与自我的分离、隔绝,这几乎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了。我前面说过,人的独特性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生命,或称魂生命。他有人格,能够思想、感觉和行动。但是那个人格是个独立的整体,虽然我可以因不同的方式把自己分为几部分:我可以把我自己分为身体和精神,或称生理与心灵两部分;我也可以很正确地把我自己分为心思、情感和意志等,因为这些都是由观察可见的。但我还是要强调人是独立的整体并非只是某些部分的组合这一前提,人不是一组分割零件的组合,也不仅仅是一道意识的源流,他应该是一个整体,有基本的所是和所需。
现在的困难是,这个完整的人在我们的视野里已经破碎了。首先是世界的图景在作家的眼中破碎,其次是人的完整性在作家眼中破碎,这类问题是涉及到人与这个世界、自我的疏离以及人在思想世界中与自己的关系。格非在《欲望的旗帜》中大量地写到了这种疏离与破碎的生存境遇。疏离带来孤独,破碎则使人失信,最终带来绝望或走向绝望的另一种形式——在欲海中浮沉。我先说张末,这位忧伤的浪漫主义者,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对未来爱情的憧憬与遐想,她想象中的一个画面是:午后时分,她坐在院廊下读书(或者什么也不做),她看见院门被推开了,一个男人向她走来,一声不吭地抓住了她的手,将她带回了家……没有沉思,没有犹豫,她只需要一种简单的打动。以后她的生活都是为了走向这个梦想,然而,她的梦想在音乐教师、药剂师、邹元标和曾山等人身上遭遇到了失败,她对城市的厌倦,以及内心不断增长的孤独感,使她成了一个冲突的人:她每次上街买梦想中的背带裤都空手而回,只是为了让愿望被反复提及;她深深地眷恋着对曾山的爱情,可又害怕见到曾山,只愿意在信上经历对爱情的缅怀;这位爱情的追寻者,到最后只能在曾山所讲述的淫秽不堪的故事中找到激情……
这种冲突与分离还发生在子衿、贾兰坡、唐彼得,甚至曾山的女儿身上。子衿这么一个冷漠的人,在欲望中却充满热情;他没有办法不说谎,控制不住自己,他无法让自我在真实与谎言、真实与幻觉之中作出选择;他听着妹妹与值班医生的对话,就好像是在听着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这是子衿与自我的分离,他无法活在自我的真实中,疯狂似乎成了他唯一的人生答案。贾兰坡一面是德高望重的大教授,一面却在桌子底下踩着女学生的脚;他带着资料员上电影院放纵欲望时,却为电影中奏响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而泪流满面;唐彼得身上兼具神学家与后解构主义大师这两种身份本身就是一个讽刺,而且现实中的他还与中国秘书、资料员开着下流的玩笑,并兴趣很高地阅读《贪欢报》。在他与贾兰坡身上不单看见人与自我分离了,不再具有内在的和谐性,还看见在这个时代,真理也和生活分离了,真理成了道理,不再有实际(有意思的是,在希腊文里,真理与实际是同一个词)。
分离在现代人身上已经显得非常普遍,最典型的例子是曾山与张末第一次约会时,他一边催促张末快点回宿舍,一边却极为笨拙地拉住了她,他的语言与随后出现的动作之间的巨大反差,连曾山自己都吃了一惊;而他那个年幼的女儿却喜欢躺在破旧的藤条箱里,喜欢躲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可见,人与自我疏离,人与别人疏离,与自然、世界疏离都已经内在到了现代人的灵魂中了。
分离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交流,人成了一个孤独的我,人甚至不能再与自己交流。交流的失去就是人的死亡。在过去,人的死亡只是指人的身体与灵魂分开,但在这个思想贫困、情感颓废、意志消沉的时代,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在许多方面与自己的身体隔绝。死亡固然会使人与身体融绝,但是与身体隔绝却不一定要等到死亡之后,人在此时此地就可能与自己、与自然隔绝。人不仅与自身的肉体疏离,也和自身的思想世界分离。自从入堕落以来,就未曾有真正身体健康的人,也未曾有真正心理平衡的人;人在现今的生活中与原有的人格产生分裂,造成对存在的整体性的伤害,这就是痛苦、绝望产生的真正原因。
怎么解释我与自己疏离后而有的痛苦呢?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关系到人存在的正确本质是什么,人一旦偏离了自己的存在本质,那这个本质就会起来审判人自己,这个审判便成了人的痛苦。我要脱离痛苦,就要回到人正确的存在本质上生活,可我是谁,我正确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由两个范畴来讨论人的问题。一是人存在的问题,这是所有人都面临的困境,人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也不管他信奉的人生哲学是什么,他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即使自杀也不能磨灭他曾存在这一事实,所以,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存在的问题;二是探讨人在其存在的领域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存在,神也存在,我与他之间的存在差异是什么?我存在,鸟兽虫鱼、山川树木也存在,我与它们的存在差异又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个无限大又具有位格(personality)的参考坐标,人就会产生作茧自缚的困境,误以为他必须安于自身的存在,不能走出自己这个巨大的茧,对世界也无法有所知,这正是所有实证主义者所面临的一种无望矛盾的情境,张末、曾山、子衿、贾兰坡都在这种矛盾之中。他们虽知陷于其中,却无法自拔,无法靠自己的理性脱离自身的限制。没有人能够这样过生活,因为在理性上人类不愿意划地自限,作茧自缚,可人类又确实生活在这种限制里面,这就决定人类直接地受理性的咒诅,不单是因为神说我们是罪人,而且因为人类自己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咒诅。神将人造成一个有理性、有道德的生命,人类想要破茧而出却又不能,于是造成人类生活方式与人类自身原有本质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可以从理性和道德这两方面来继续探讨。在理性方面,人类往往倾向于依赖纯神秘主义的跳跃来寻找存在的答案,即使对宇宙整体和人类存在目的的问题也不例外,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严重。人一方面说,存在何必要有理由呢?我们何不接受存在是一种非理性?另一方面心中却有所自责,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使人了解宇宙中必定有某种存在的一致性,所以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源于人内心里原有的理性对人的非理性生活的审判。格非所写的贾兰坡的自杀,虽然没写具体的答案,但其中就暗含了理性的咒诅给人带来的黑暗:贾兰坡在非理性的生活中时,他的理性仍然续要求一个基本的答案来达成生存的一致性,这使他进退维谷,造成他内心的崩溃。这位斯宾诺莎的信徒,必定意识到了理性的困境,因为斯宾诺莎这位荷兰的犹太作家是位泛神论者,他以万有为一无限的实体,而这实体既可称为神,也可称为自然,一切有限的人或属性都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的说明,这里斯宾诺莎强调了思想及其思想的广袤性,可贾兰坡的绝望在于发现了思想的力量非常有限,它甚至不能帮助他拒绝一个纺织女工在欲望上给他带来的诱惑。因此,人单靠自己的理性要去做些什么力量是不够的,他需要仰赖无限大的理性。我的重点就是说,在理性里,人往往有面对与自己分裂的危险。
在道德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情形。人无论摆脱内在是非判断的真正道德力量,所以,道德对人的审判照样使人痛苦。我相信贾兰坡的自杀还有道德的因素,因为造成他哲学信念瓦解的原因不单是他的学生曾山与他的争论,更是因为他不能抵挡欲望的袭击。他曾对曾山说:“没有对于永恒的确信,道德亦将不复存在。”然而,他的生活与他所说的是相距那么遥远,他的所谓的永恒信念,并不能保证他的道德。同样,道德感使得张末在欲望面前没有放弃抵抗,老秦也只好打消与妻子离婚的念头,但他们为此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人背叛神之后,与自己产生了疏离,便只能在冲突中接受原有本质(即神的形象这一本质)的审判了。
欲望的旗帜
人与自我的疏离不单造成人与自己、与别人都不能再正常交流,而且它还是一系列其它精神问题发生的根源。真正的交流是达到内心世界,深入到内在人格中的,譬如,真正的爱情不仅是外在身体的接触,更是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而张末与曾山之间缺的就是后者。由于思想与情感的贫困,使得他们的身体与自己的人格疏离,无法活出原来应有的生活。爱是一种完整的人格交流,完整的人格包括身体和灵魂,但我们在强调灵魂时,要小心不要落到精神主义(柏拉图主义)的观念中去,变得只讲情爱,我们强调的是情爱与性爱相结合的完整性。以外在身体的接触依据的性爱必须以内在人格出发的情爱为基础,并且以内在为核心,因为内在思想世界引发外在的表现:绘画、音乐、建筑,对人的爱恨,以及对神的敬虔或悖逆的种种爱情。这个内心世界不是奥秘的存在主义式的经验,也不是雅斯贝尔斯用宗教术语说的“最终经验”,更不是迷魂药所造成的空洞无实的感受,而是实际上能以理性来表达的思想。
人与自我疏离的问题就是内在思想世界不和谐而致。因着每个人在思想上都有程度不同的病症,表现在外在世界里,就有各种各样的精神难题,《欲望的旗帜》所表现的难题中,有几项是很值得我们继续探讨下去的。一是人的理性失败之后,人要怎样才能活在真实之中?这种真实的困境以小说家子衿的境遇为代表;二是在神的真实受到怀疑,自我的真实又得不到确认的时候,人除了走向欲望的真实之外又能怎样?其危机的本质与根源是什么?三是在一个只有欲望,没有理想,没有爱情,甚至连缅怀的心情都没有了,连自杀都失去了起码的庄严感的时代里,人如何才能尊严地活着?这可能就是张末所追求的。
先说真实的困境问题。我要再次提到子衿这个有意思的人物,格非在他身上表现出了一个现代人难以觉察的精神困境:无法活在真实中。与其说子衿成天都在说谎,不如说他根本就无法再分辨真实与幻觉的区别。诚如他自己所说:“在写作中,你的意识会不知不觉地被上帝或撒旦控制住。你分不清哪些事是真实,哪些是虚构出来的。”由子衿所叙述出来的关于贾兰坡的迟到,贾师母的偷情,他屁股上的烙斑,以及他与护士的艳遇等,我们根本无从分辨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不仅子衿面临无法指证真实的困境,张末在苏辛、邹元标面前,曾山在混乱的世界面前,也无从指证哪些事是真实的。有一次,张末还企图向曾山证明,幻觉与想象是真实的,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无用之物,就如空气一样;而子衿也在他妹妹到达上海时,急于向曾山证明他并没有说谎,可见,人渴望活在真实里。
然而,判断真实与否跟信心有关,信心又只能从正确的理性中来。子衿的痛苦在于他对世界,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这种丧失导致他与世界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子衿后来疯狂,就是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得不到和解的结果。如果没有了正确的理性,人就不可能有信心下判断,他只能相信自己的感觉,而感觉是多么的不可靠。理性的失败在于这种理性没有与无限大的理性(神)相联,人只好开始转向非理性。在非理性里面,感觉、欲望就可以在人的生存中取得合法的地位,从而取代理性与道德;在非理性里面,人被抛到了没有规范的环境中,无法分辨是非与客观的真实,整天只沉溺在幻想和荒诞之中。现代人为规避理性跃进非理性的境界(以欲望的生活为代表)以求好过,结果不单丧失了人性、道德规范和确定事物的能力,自己根本就生活在疑幻疑真的世界里。这也就是电影大师阿伦·雷乃、费里尼、英玛·伯格曼(格非在小说中一再提到伯格曼,且深受伯格曼影响)等人在电影中所表现的主题:如果人从自己出发,真正活在一个没有一位有位格的神说话的宇宙中,他始终都不能分辨自己究竟是活在现实中还是活在幻景中。
伯格曼曾在1963年执导的《沉默》一片的电影招待会上说,自己已获得了一个结论,就是神已经死了,现在宇宙间只有沉默。然而,宇宙可以沉默,人却似乎难以沉默,这时,人只能接受萨特的思想了:在理性的范围内,一切事物都是荒谬的,人只能借着意志支配的行动来“肯定自己”,在这个没有目的的世界里,人不应旁观,而应做行动者。如果伯格曼、萨特的思想是对的,那人唯一的出路就只能走向欲望了,因为神的真实、自我的真实被否认之后,人又要做一个行动者,他除了在欲望中行动外,还能做什么呢?人的尊严其实不在于帕斯卡尔所说的“思想”(因为思想可以不对道德负责任),乃是在于人的欲望受自身的理性与道德的约束,使他能够按着良心的要求活着。如今,神已经死了(?),就意味着永恒的信念和价值标准已经瓦解,而人又与自己疏离了,那么,人的良心、理性、道德就不再负责自己的行为,人为所欲为也可以不再受神、受自己的良心与道德的责备了,这时候的人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呢?
欲望的旗帜升起来了,这是一面破碎的旗帜,也是人类的信仰、理性、自我的道路上失败之后手中仅存的最后的旗帜了。如果不站在绝对的价值立场上,我们就不能指责贾兰坡、子衿、唐彼得等人拈花惹草的生活是不道德的。这个时代仿佛成了欲望的加油站,人那脆弱的生存在其中显得不堪一击,就像张末因为守住了贞操而遭受到女同学的嘲笑时,她不但没有力量痛斥这种堕落的思想,反而感到自己的自尊受到了伤害。同样,贾兰坡、唐彼得等人在追求高尚的哲学与神学时,却不能给他们带来力量,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因为哲学、神学都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满足。哲学、神学的困境在于一切都是从自我出发的,企图通过自我的猜想来达到神或者达到完美的存在,但是,因为哲学家与神学家的生活与真理发生了分离,以致于神在他们的眼中只是一个词而已。譬如,在唐彼得的生活中,许多时候神就不如他怀中的中国秘书、资料员实际。现在的问题是:在欲望的放纵中并不能使人为自己找到本质。人去失了一个更高的存在(神)作生存的基础后,人就成了独立的人,人的本质便只能由自己来决定,人一旦不能给自己一个本质,人就没有本质可言。然而,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人除了不断地给出欲望之外,还能给出什么呢?
没有本质的生存就不可能有满足,也不可能有尊严可言。因着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张末没有勇气,也没有信心回到上海、回到她过去的爱人(曾山)身边。她只能徘徊在车站这么一个尴尬的地方。就在这时候,“长期以来蛰伏在她体内的那头怪兽正用清晰有力的节奏敲打着她的腹部,并在她的耳边悄悄地提醒她,让她放弃挣扎,放弃抵抗……”张末要抵挡这种欲望的袭击,惟有依靠梦想的力量;梦想又遭遇到失败之后,便只剩下一些因缅怀梦想而有的忧伤心情了。这可能就是格非在《欲望的旗帜》中所能给出的最后一点温暖的感觉了:那些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在稻田上空低低飞过的一群鹭鸶,残破的院墙和天井都给张末的遐想带来浪漫的氛围;还有那条梦想中的背带裤,父亲的烟斗,曾山口中的烟草气息,被人遗落在路旁的那朵玫瑰花,以及旧磁带、小提琴手等浪漫事物,也不断地给张末的心灵提供来之不易的慰藉;而曾山的心则在幼儿园的琴声和小姑娘们丢手绢的游戏声中感到暖融融的;子衿却不厌其烦地向人描述他那个傻妹妹,以及他们在江边浪漫的对话,还有那条他妹妹帮他织的灰色围巾,这些似乎成了子衿心中唯一的理想。经过许多个苦难的日子以后,曾山、张末、子衿在现实中体会到的只有冷漠、孤独和欲望的冲动,仅有的安慰只能来自追忆中偶然闪现的浪漫情怀,并且那么容易消逝。
在这最后一个浪漫时代里,只要稍有精神追求的人,都活在与现实的冲突之中。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些大谈终极价值、佛学或神学的学者们,在有些方面却那样入世且充满肉体的趣味,就如伯格曼在大谈沉默、幻像时,自己却不是真正活在这种境况里,因此他的《沉默》一片是以巴赫的《郭德宝变奏曲》做背景音乐的。当有人问伯格曼对这影片的音乐怎样解释时,他说,片中人性仅有的神圣部分,就用音乐表达出来。他在家中一面写这剧本,一面听着这首音乐。可见宇宙并不是沉默的,人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是肯定的,有规范的,足以辨别虚幻,人之为人是可以理喻的,这是崇奉人文主义的现代人所缺乏的。
做有理性、有道德的人
至此,我忍不住想大声问道:我与自己疏离的问题,我如何才能在欲望的袭击中能尊严地活着的问题,究竟有没有答案?还是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格非在小说中没有给出答案,但我相信肯发问是找到答案的关键。这个问题与“作为一个人,我是谁?”这一根本性的质问是相连的。此类问题可以有许多答案,但“我是有理性,有道德的人”可能是末世最恰当的答案。我存在,特别是以有理性、有道德的方式存在,于是有了两方面的独特性:一方面,我与神不同,虽然他存在,我也存在,他有位格,我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的,但是他是无限的,我却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我也有别于动物、植物和机器的存在,因为它们没有人格,而我却有人格。所以,自问“我是谁?”是了解我今生的困境——我与自我疏离——的一个好方法。我有人格,有理性,有道德,就人格而言,我与神相像;但另一方面,我也像动植物和机器一样是有限的,同为受造之物,其中的差别在于我有人格而它们没有。我想,这幅存在的图景已经非常明朗了。
为什么会出现格非在《欲望的旗帜》中所表现的一系列的精神困境呢?原因就在于现代人偏离了理性与道德的存在轨道,妄想在神所规定的界限之外生活,不按照人原有的受造本质生活。理性的背面是非理性,道德的背面是欲望。贾兰坡的自杀、子衿的疯狂都在于他们无法活在正确的理性和道德里面,因为失去了永恒的依靠之后,一切都非理性化、欲望化了,这是作为一个有神形象的人所无法接受的,除非他泯灭良知。弗洛伊德对他未婚妻的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弗洛伊德并不相信爱——他认为性是一切事情的最终目的,但是他也需要真正的爱。在他给未婚妻的信中写道:“小公主,当你来到我身边时,请无理性地爱我吧!”对于弗洛伊德这样的人来说,我常想没有比写出这样的字眼更可悲的了,他那时内心的感觉大概可以用颤栗、恐惧来形容了,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成的,所以就受到情感上追求真爱的本质所咒诅。张末所遭遇的似乎恰恰相反,她想爱但没有信心,没有能力爱,她无法非理性地爱曾山,她的理性与道德要求她必须为爱找到一个理由和本质,可是她找不到,因为人的理性与道德不能单独存在,它必须依赖一位在理性上无限大、在道德上全然圣洁的神。
让我再举一个巴甫洛夫钟的例子。那是最先为了作机械性制约反应实验所用的钟,巴甫洛夫在喂狗之前会先敲一下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狗只要听到钟声,嘴里自然地分泌出唾液。对于狗来说,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因为神所创造的狗就这个样子的。但是如果人是这个样子就太可怕了。人是依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理性,有道德。我们的行为是有意识的,并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不可能轻易地让自己或别人归入制约反应中,然后就以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人还有更高的需求,会思索许多与神相关的问题,就如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康德,在年老的时候,把整个人生用四句话表达出来,就是:我要知道我是谁,我要知道我知道什么,我要知道我当做什么,我要知道我有什么盼望。尽管康德没有回答完这几个问题就去世了,但他所概括的四个问题是一个有存在感的人所普遍面临的。
康德在那个时代思索这些问题是正常的,但曾山、张末若在这个时代里沉浸在这些问题之中却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首先,这个时代的人在理性与道德上已不像康德时代那样坚强,其次,这个时代不再尊崇理性和道德,它只需要非理性和欲望。曾山、张末被错置在这个时代里,深深地体验到时代给予他们的伤害,所以,在我看来,他们不只是思想者,更多的还是见证人——是为他们的时代忍受时代本身拒绝承受是它自己内伤的见证人。正是在张末身上,见证了人的内里还可能存在的尊严和浪漫愿望,尽管脆弱,却还存在着,这就是意义之所在。
这个时代精神颓败的历史是这样的:因着人与神的疏离,导致人与自我也发生了疏离;失去了至大的依靠者后,人开始要为自己的存在负全部责任,如同笛卡尔经过怀疑一切而达到了唯一的确定性:他自己意识的存在——那著名的“我思故我在”。这时,人就被禁锢在他自己的我里,这个我起初还是一个非物质的实体,一个在思想的实体,紧接着,理性与道德的界限不断瓦解,这个我就成了一个非理性的实体,一个欲望的实体,渐渐以一个本质意义上的失败者的面目出现,就像叶芝在一首诗歌中所说,既然梯子撤了,我只好倒在放梯子的地方。这个梯子就是攀登最高实在(神)的道路,如今因着人远离神,时代远离神,它连同欲望一同腐朽了。显然,对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人的救治,必须回复到这些问题的源头——因为人与神疏离,才导致人与自我疏离,最终受欲望的辖制。
人的存在是一件十分奥秘的事,不但向外追求生存需要,也向内探索存在意义。内外建立完善(即使是自以为完善)人便幸福自在,否则就会失控而处于飘摇的状态,因此为自己的存在找一个位置、一个身份是很重要的事。人为什么要内外探索,建立起终极性的需要呢?答案非常清楚:因为人在神面前失落了。二十世纪这种现象在存在主义哲学里表现得很清楚。存在主义认为无限观念的我,应该脱离有限的自我,把自己的存在绝对化,否则“我”就不存在了。这样的解脱,表明人有一种对绝对性的渴望,盼望“我”的不朽。这些跃跃欲试的人本主义、自我中心式的挣扎,都试图借助可能的力量要从相对界进入绝对界,走上脱离相对界的过程,这是一条失败的路,因为过程只属于相对界的事,绝对本身不属于过程。相对的绝对不过是被绝对化的相对,不是绝对;同时,绝对永远无法被相对化。所以凡自称是绝对的,不一定是绝对,而绝对的却有权利自称是绝对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曾经自称绝对,其他的人不过教导了观念的绝对,这一位就是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稣基督。
我说这些是为了探查人类精神危机的最终根源是什么。是的,正是因为人不安于自己存在的本位,妄想跨入神存在的领域,才造成现代人内在的崩溃。在《欲望的旗帜》所出示的存在范畴里,因着神没有当有的地位,渐渐地,人也没有了该有的地位,完全沦落到了茫然失措之中,成了非理性的人。表面看来,他们的困境是因为爱情的瓦解,欲望的生长,理性的不可靠,从而带来了存在的虚空与无聊,实际上,其内在的原因乃是因为生存失去了正确的、无限大的参照物,从而从自己存在的本位上迷失了。此时,曾山、张末、子衿等人如果愿意应用自己的理性,他将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他可以用具有人格的受造者的身份,回到具有位格的造物主面前;或者他可以选择低于原有地位的身份。作第二种选择的人,不愿回到被造者原有的地位上来生活,他势必往下堕落,这是可悲的——我们几乎可以预见张末最终的结局必定如此。文艺复兴时期有一绘画作品,画着施洗约翰的手指指着天上,违抗神的人就像少了那根手指似的,他们宁可沦入与动植物和机器同等的层次,也不愿回到神面前,使得人在多方面都与自己的本质疏离。你可以再思想一次整个的过程——人在叛逆中与自己的理性、道德疏离,也与自己的思想、行动与感觉疏离。同时由于他希望成为神(这是每个不信者隐在的愿望),却困于自身的有限而不能如愿,这种道德上的罪使他与神隔绝,不但受到原有本质的咒诅,更因为他想以低于原有地位的身份活着(像动物一样放纵欲望)而不能如愿,故而再受到咒诅。不论他行为在怎样的境遇中,他受到这两方面的咒诅时,他整个生命仍然会从心底发出“我是人!我是人!”的内在呼喊,这就是对自身尊严的吁求。
可是,现代人可做超人,也可以以非人的面目出现,惟独无法成为一个有理性、有道德的正常的人。这是人否定了一位无限的、圣洁的有位格的神之后必然遭遇的大限:无法在超人或非人的身上建立起生存的盼望性。没有盼望,这几乎可以说是《欲望的旗帜》中所有人的困境。盼望什么,便是人的信仰。人年老的时候或不要到年老的时候,他知道一切都要过去,因此在有限的世界中开始因不可知的未来而感到恐慌,这个恐慌的思想就成了存在主义最重要的名词之一——焦虑(angst)。我这个“有”将变成“无有”,死是一件不能拒绝的事实,我这个“存有”要面对“无有”,而“无有”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一个永远不能解答的自我消灭问题,成了人存在的最大威胁。人要有更高一层的盼望产生,就是基于潜在的永恒性,这盼望的最终点就是冀求生命的永远存在,也就是永生。只有这个盼望,能够解决贾兰坡自杀、子衿疯狂、张末迷惘的一系列问题。可是,谁能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呢?我愿意将自己对《欲望的旗帜》的讨论终结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这也正是我抛开格非的其它小说,专注于《欲望的旗帜》这一重要作品的原因所在。我希望由此而激起文化界探查存在问题的持久热情。
1996年1月24日于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