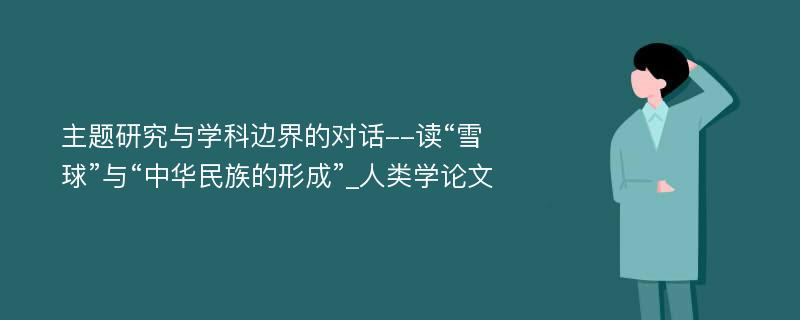
关于专题研究与学科界限的对话——读《雪球》、看《中国民族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雪球论文,中国论文,界限论文,专题研究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鸿保(以下简作胡):徐杰舜教授(以下敬称从略)在圈内人士眼里是汉民族研究的权威,辛勤笔耕经年不辍,迄今已有《汉民族发展史》等多部(篇)专著发表,影响很大(注:孟凡夏、徐杰舜:《汉民族研究是一座学术宝库——徐杰舜教授访谈录》,《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1)。)。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由他主编、 主笔的鸿篇巨著《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注: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他专门找到我,诚意听取批评,反而叫我十分为难,只得找你合作商谈。好在我平时已经嘱咐你看了一些关于汉民族的人类学研究著作,此情景中我俩讨论委实有不少便利,一来“童言无忌”比较自在,二来也可以让我那些已经成名的朋友得到一份“保持沉默”的轻松心情。
姜振华(以下简作姜):我读了《〈雪球〉出版座谈会发言纪要》(注:蒙本曼:《人类学本土化的示范之作——〈雪球〉出版座谈会纪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1)。), 了解到同行专家对这本书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比如,黄淑娉认为,《雪球》的选材很好,抓住了汉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的接触、融合犹如雪球滚动的重要特点;另外,它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分析、解读历史文献资料,对人类学的研究是一个贡献。乔健指出,《雪球》与传统人类学不同,它以12亿人口的汉族作为总的分析对象,是人类学本土化最好的一个示范。彭兆荣认为,《雪球》对中国传统历史学、文本学、文献学、资料等所作的解读是相当本土化的、中国特色的东西。
胡:这样的场合,当然不会有尖刻的话语,多半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其实“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含蓄的批评还是不难从中发现的。比如周大鸣说“我好佩服”,自己不敢做这么大的课题,不是也可以读解为:传统的人类学是做一个小社区的参与式田野研究、“雪球”这种做法有点出格了。刚才我说过,有的朋友想保持沉默,也是一种逃避喧嚣的处世哲学。所以我才邀请你出场相助。
姜:我注意到潘守永在他的博士论文里对西文sinologicalanthropology与作为其对译语的“汉学人类学”这个汉语术语有一番评论,他认为对“汉学”(sinology)与“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有必要加以区别。要而言之,两者在大、小传统的关注上自然分界。人类学的研究素材主要来自对“民间社会”或“民间文化”这些小传统的调查,人类学具有“边缘性”的特征,其研究内容民间文化相对于上层文化具有相对性,作为人类学田野地点的乡村也属于边缘地带。汉学则具有重视古典和文献研究的传统(注:潘守永:《重访抬头:中国基层社会文化变迁的田野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打印本,1999;同时参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
胡:《雪球》一书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把它定为出色的汉民族研究专著应说争议不大,但是否算得人类学研究则是有不同看法的。你在研读的萧凤霞的作品属于汉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大概在当前是不会有疑义的了。可见学人们也还是讲究直觉的,一时有一时的风气。
姜:萧凤霞的《华南的代理人和牺牲者》(注:萧凤霞( Siu,Helen):《华南的代理人和牺牲者》(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英文版, 耶鲁大学出版社,1989。)一书我阅读之后,初步的认识有以下几点:第一,该书是对乡村社区的田野研究的成果,属于传统人类学的范畴。它是萧凤霞在对广东新会县环城区作了十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以新中国建国前后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的变迁这一独特的视角,再现了国家意识如何向乡村渗透的过程。尽管人类学家对“小地方”能否反映“大社会”各执一词,但萧的这一著作却成为以小社区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成功典范,得到大多数人类学家的认可,享誉海内外。第二,该书注重对“乡村社会”小传统的调查研究。萧凤霞通过对乡村社区的长时间的田野作业,获得了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她更加注重通过农民的集体记忆去构建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关注农民的生活、生存处境以及对各种政治运动的感受等各个方面,使人们通过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对其经历的反思更加深刻而真实地去了解历史。第三,该书对历史文献作了恰当的处理和运用。人类学家要反映历史就必须借助于历史文献,但不能沉溺于对历史文献的简单堆砌。萧凤霞一方面以历史文献作为叙事的客观依据,另一方面在对历史文献的选择上力求作到恰当、精练,并能为其田野作业的访谈资料服务,既能勾勒历史的脉络,又为其田野调查资料提供背景。在对历史文献的运用、解读方面,萧凤霞应算得上是很成功的。
胡:是否可以这么说,当代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其主流是对小社区的田野研究。至于在方法论上讲它有没有可能折射大社会,也并非只有一种见解。比如张海洋在一篇文章里就争辩道,对小社区的人类学田野研究路数完全有可能有效透视大社会(注:张海洋:《马林诺斯基与中国人类学——〈科学的文化理论〉译序》(下),《民族艺术》(广西),1999(4),第171页。)。
姜:具体对于汉族研究而言,历史文献的运用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这是民族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的共识。近来内地比较成功的人类学学人庄孔韶、王铭铭有关福建汉族社会的作品都注意历史文献的释读(注:庄孔韶:《银翅:金翅的本土研究续篇——1920至1990年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一部社会人类学的文本撰述》,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6;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你和他们不是都有一些交往吗?
胡:我与两位都有学术上的“拟血缘关系”,自是有缘切磋,不过这样的人际关系也可能使得批评不够正规(注:参考王铭铭、纳日碧力戈、胡鸿保:《人类学的中国相关性》,《学术思想评论》,第4辑,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胡鸿保:《读解〈银翅〉》,《民族艺术》(广西),1999(4)。)。无论如何, 学术上的取长补短和正常的学术批评都是十分必要的,可是,“文人相轻”已然是不争的陋习,很难免俗。
姜:我看了曹树基的评论,王铭铭的文章里是有一些“硬伤”,曹批评王的著作中存在着对于历史的误读,出现了许多常识性的历史错误。例如,王铭铭认为土改中土地曾经收归国有,他还把集体化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认定为类似与“劳资关系”的东西。对于诸如此类的错误,曹树基以为王铭铭是对中国历史的曲解和信口开河(注:曹树基:《学术研究与学术著作的评审》,《文汇报》,1998年11月13日,8 版:曹树基:《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中国社会科学》,1999(1)。)。但批评者好象不太厚道?
胡:瑕不掩瑜,王铭铭的研究运用的无疑是人类学的手法,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而《雪球》这部作品之所以学科定位出现问题,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至少他和今天的人类学主流研究方法不一致,也没有同人类学学术史上研究汉族的已有成果相衔接。比如讲西南地区就没见他们提及施坚雅(W.Skinner),不论你是否赞同施氏的理论, 今天的同行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已经无法绕开或避而不谈前人的结论了。另外,有些新锐的研究也不容忽视,如濑川昌久的《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注: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日文版,1996]。),该书作者不但注重长期的田野工作,甚至对于包括徐杰舜等人合著在内的、与该论题有关的专著都没有轻易放过。近百年的学术积累已经迫使希望成为人类学圈内人的学者把阅读前人作品当成取得身份认同的“成丁仪式”。缺少了这一点,就难怪遭冷眼了。
姜:《雪球》开头是一个理论导引性的篇章,在“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的理论观照”一节里,作者力图对族群和民族的当代理论做提纲携领式的介绍, 为全书做铺垫。 不过看得出他还是持传统的原生说(primordialism, 或译为“根基论”)观点,而对于后起的、当前更为主流的边界论(theory of boundaries)和现代想象论(theory ofmodern-imagined communities )似乎关心不够(注:关于民族和族群理论,可以参考纳日碧力戈:《种族与民族观念的互渗与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秋季卷,1996,总第16期。)。
胡:你可是触及到更致命的方法论问题了。一般说来,“原生说”比较符合中国传统历史学家的思维定式。“边界论”、“想象论”等理论看来则有一种“后学”(Post-ism)的味道,试图站在边缘的位置去反省某种文化中心主义,并且好象采取一种立足今天、反观历史的视角。有位研究中国的洋专家阿里夫·德里克说:“民族主义一旦出现就超越时空,跨越这个民族所占据的疆域而消除一切差异,在时间上回溯到某一神秘的起源而抹掉过去不同瞬间的差异,这样,全部历史就变成了一部民族进化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特点成为民族的象征,而另一些与民族自我形象不一致的特点则作为外来的非法入侵而被扫地出门”(注:阿·德里克:《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载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8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这样的看法不少人都表示过,在当下情景里尽管不是讨论民族主义,而是在谈民族历史的书写,读来也不无启发。
《雪球》的作者们既想不落俗套、以稍微时髦的“族群理论”来突破我国旧有的“民族理论”框框,却又在潜意识里恪守“原生说”的陈规。这样一来又使自己处在相当被动和尴尬的位置。
姜:黄淑娉主编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注: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是以一个地区的族群为对象的综合性文化研究,大家都认为属于正规的人类学的研究。或许选择的研究地域范围的大小在这里对于评论家的判断也有一点影响吧?
胡:那倒也不一定。读《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自然让我联想到70多年前李济的人类学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一项人类学的考察》(注: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the Chinese People),张海洋、胡鸿保等译,载李光谟编撰:《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英文版,1928]。)。李济此文讨论的对象也很大,同样运用了许多历史文献,却被同行公认为中国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李济当年谈中国民族的形成, 主要着眼于所谓中国本部(ChinaProper)的18个省。 苏联民族学家伊茨的《东亚南部民族史》(注:P·ψ·伊茨:《东亚南部民族史》,冯思刚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俄文版,1972]。)从他的研究需要出发划定一个区域,把当代越南、泰国等的某些部分和中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看作为一个“历史民族区”,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从地区民族历史的角度看,打破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境线思考问题自有其合理性。后来费孝通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也有他自己的讨论范围,即以中国当代的国界为准(注: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4)。)。
拿《雪球》与《中国民族的形成》两者相比,一是时代不同了,且不说什么范式的转换,至少是主流风格发生了变化。你学过人类学史,应该记得早期的西方人类学大师如泰勒和弗雷泽也被后来者戏称为“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美国,大概还留有古典进化论的余绪吧,要说给人类学带来的田野革命的话,毕竟该记得1922年才是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功能学派代表作《西太平洋的探险队》和《安达曼岛人》发表的年代,而李济的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是1923年就拿到的。至于第二呢,李济是在异国他乡用英文讨论中国人,与徐杰舜等几位作者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大不一样。这种情况和刘绍铭先生谈论的比较文学研究在原则上是相通的。大陆中文作品如《红高梁》的英译漂洋过海在英文读者心目中产生的影响与它在本土的影响是不会相同的(注:刘绍铭:《旗鼓相当的搭配——葛浩文英译〈红高梁〉》,载刘绍铭:《文字岂是东西》,第126-128页,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姜:再说李济使用历史文献也有不同于一般国学考据的方法,例如谈张、陈、朱、胡等10个姓氏的来源、迁移和地望,就配置了78幅地图;研究城址衡量“我群”的规模并推测其迁移和各省的省龄,就应用了统计学的方法,也有数十张统计图。
胡:是的,李济开创的这些富有特色的研究法在后来的中国史学家、民族学家那里好象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也没有见到对于此类方法得失的评论。作为李先生大作的译者之一,我感到不无遗憾,作为中国的人类学士博士,有点惭愧了。
姜:《雪球》的总体编排架构把中国境内的汉族划成7 大区来做进一步分析,这样的安排有利于邀请熟悉各地区情况的专家通力合作。
胡:其实,把中国境内的汉族划成7大区来分析,利弊互见。 这样大区的基础是建立在当代理念上的。分定为几个区域之后如何说明彼此之间历代的互动是个难题。李济和费孝通都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各大区域之间人口的互动,然而区域的界线并不那么僵硬。李先生谈及“我群”由甘肃向东、向南等方向的移动,费先生在他的论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里提及汉族在中华民族凝聚过程中的网络作用,都是取一个宏观的视角。《雪球》的分篇格局就把弱点暴露出来了。例如“西南区”说的是当代行政区划上的云贵川藏,显然对讨论汉族滚雪球式地发展并非一个理想的框架,该篇内开头对此四省区的地理环境做了概述,但后文就无法对西藏汉族作与云贵川汉族等量齐观的描述。西南官话的方言分布也和行政区划上的西南很不一致(注:西南官话的地理分布范围除云贵川三省外还包括湖南的西北部以及湖北的大部分地方。)。本书大多数篇幅是考虑本区之内的历史人口贯时变化甚于对区域内外关系的论述。比如东北地区当代汉族的族源应该并非当地古代的肃慎等族,而是明清以还出关的山东等地汉族,研究追溯民族史需有“对他而自觉为我”(梁启超语)这种意识,想到这里的汉族是相对于满族、蒙古族、鄂伦春族等而言的。如果依李济曾经讲过的,“位于中国西北角的甘肃,肯定在很早以前就已将最早的层次[种族]输出殆尽”(注:参考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一项人类学的考察》,第324页。); 那么按同样的道理说,今天的东北汉族也无法在当地找到他直系的族群的底层。比较起来,西南篇还稍好些,作者厘清了历代由华中、西北等地一拨拨进入当地的汉族先民,并且声明,直到明代以降,汉族方成为当地的一个单一族群,而前此的移民都被“夷化”为当地民族。
姜:说到本土化,我想问:为什么“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来讲有所谓本土化的问题,而对于历史学和文学之类学科却只讲有地域或民族特点而无须本土化呢?
胡:这是可以多加推敲的。反正最近徐老师他们组织了会议专门讨论过本土化这个话题,许多同行发表了高见。我这儿要强调的是:论及一门学科的本土化是有隐含的前提的,那就是保持学科的规范,同行中间有种约定俗成的办事规则。做学问搞研究可以跨学科、持“问题取向”、当“脱缰的野马”(注:费孝通语,见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读书》1990(10)。),那与谈“学科建设”不是一回事。至于讲学科,则当然想有明确的边界,采取“广义”或“庸俗化”的手法都不足取。80年代中,学界就有过反对社会学“庸俗化”的呼唤。现在希望发展我们自己的人类学,我还是情愿从起步就严格要求,切忌一哄而起,“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民族历史悠久是事实,也可以引以为自豪,但如果西方的人类学被我们本土化为历史学,恐怕大家都会觉得不是滋味。一百年来从事本土化的学者愿意看到的是中国学科体系中多有一门新学科,而不是“化胡”。另外,也要认识到,经过百年的学术发展,尤其是解放后的多次运动的影响,当前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实际上已经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学理来作解释了。至少我看此语境中的民族学不等于人类学(注:详见胡鸿保:《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4)。)。
通篇而论,《雪球》引用的十八九是文史类的典籍和当今历史学家、文学家的作品。这固然反映作者作文史功底扎实,但似也隐含对现有人类学材料的隔膜。试挑两点小错:“导论”在谈汉族人口发展历史时引他人成果谓“两汉之时汉族形成的初期约有五千万人口,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到宋代时人口突破一亿大关;……”(注:徐杰舜转引滕泽元:《宋代人口突破一亿大关》,见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第43页。)。这里人口学者的统计恐怕是把今天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先民全都考虑在内、而不会单挑汉族的。这是《雪球》作者的考虑不周,造成纰漏。又如提到90年代面世的专门研究汉族族群的专著,汉文写的是霍尼各[Honig,Emily]的《中国人族群的创造:上海的苏北人》,而英文却写的是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分明是将霍著与冯客[Dikotter, Frank]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弄混了(注: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第19页;同时参见冯客(Dikotter,Frank):《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杨立华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英文版,1992];霍尼格( Honig,Emily):《中国人族群性的创造:上海的苏北人》(Creating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hai),英文版,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
姜:你把我们谈话的副标题定为“读《雪球》,看《中国民族的形成》”是否暗含有一种回溯学术历程的意向呢?
胡:正是。自李济的关于汉族的人类学研究以来已经有70多年了,形成一大批此专题的著作,使得我们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能对相关问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这是不能抹煞的。总之,《雪球》是汉族研究的一个突破、一种新探索,也可说一块里程碑。我以为它属于有人类学特色的历史学作品,值得人类学学者认真研读。此作同样使后来的研究汉族的学者不能随意绕开、视而不见、置之不评。
姜:这也正是老话说的“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呀,后学者们是会记得《雪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