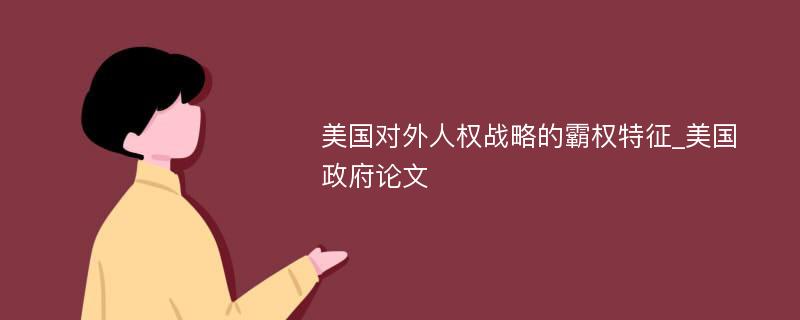
美国对外人权战略的霸权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美国论文,人权论文,特性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简要剖析美国政府对内对外的人权立场,可略窥美国对外人权战略的霸权特性和这种人权战略面临的困境。
人权战略是美国称雄世界和打击对手的工具
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内对外是双重标准,采取了轩轾不同的立场。在国内,不批准和不执行联合国的某些人权公约规定的人权要求,但在对外关系上,却借口人权,干涉他国内政。美国是单方面地,而非通过联合国或地区性人权机构来裁判他国的人权状况,美国对他国人权状况进行监视,并由国务院对每一国家的人权状况提出报告。而美国国务院对他国的人权状况的报告往往别有用心,危言耸听,乃至向壁虚构,悖离事实。这早已遭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抗辩反驳。而近几年世界人权大会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严厉谴责了美国借口人权,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美国是单方面地,即由美国一家来裁判另一国是否遵循美国的人权标准或遵循的程度,实际上是把美国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美国驻东欧的记者罗伯特·卡伦在美国《外交》双月刊1992/1993年冬季号发表的《人权的困惑》一文中直言不讳地披露了美国对外人权战略的目的:“坚定地主张清楚界定的人权会是一种强大的外交工具,即是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破坏美国的对手的工具。”“强大的和聪明的道德成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非此,则公众对外交卷入的支持会趋于迅速削弱。”诚然,克林顿谈论人权时,人们自然会嗅到“项庄舞剑”的气味了。
从历史上看,美国对于那些对美国具有军事价值和战略价值的国家,常常不计较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甚至对一些践踏人权的盟国给予援助。这早已是众人皆知的了。美国1980年《难民法》把难民界定为“有根据地惧怕因种族、宗教、民族、政治观点或社会地位不同,在返回他或她的国家”后而可能“受迫害的”人。但美国政府有选择地实施这一法律,优待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而不愿接受来自与美国结盟的国家的真正难民。美国是合众国,宣称美国建国思想之一是美国公民地位和政治权利不得以种族或宗教为基础。美国的某种铸币上刻有“合众为一”(即诸州联合组成合众国的国训铭文)。然而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美国却利用那里的种族的、宗教的分歧,分裂那里的国家,导致蛮力横行,祸乱不止,人不堪命。同样的,美国历来宣扬“自由贸易”是人权。但在美、日贸易摩擦加剧时,却又力图迫使日本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在《外交》双月刊1996年1、2月号刊登的《作为社会工作的外交政策》一文中批评了克林顿政府,指出,克林顿“政府把减少日本贸易顺差作为对其亚洲最重要盟国的政策之中心。……但是(克林顿)政府行事的方法具有不幸的副作用。这与自由贸易的原则相抵牾。而美国长期以来在全球主张自由贸易。……”这样,人们感悟到的是,与其说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是双重标准,毋宁说实行的是“霸道”标准,其原则是“说你不对就是不对,对也不对。”至今,日本还是美国的盟友。而美国对于不听命的国家,按克林顿政府曾提出的冷战后美国对外新战略,则是“力求从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上加以孤立。”真是霸权在握,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了。
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神圣性是美国国内人权理论的基础
美国在独立战争期间颁布的《独立宣言》宣布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其核心是宣示将资产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加以理论化的经济生活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合众国宪法》加强中央集权,以保护资产者及其财产权和与财产权有关的特权。《独立宣言》和《合众国宪法》肇始了美国人权政治的双重传统,首先是象征性的人权政治传统,抽象地侈谈自由平等;其次是实质性的人权政治传统,坚持阶级间、种族间和性别间的不平等,乃至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和文化教育上的不平等,美国自建国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一是信仰人性是自私的、个人主义的和竞争的;二是信仰私有财产神圣性。在19世纪后期,美国的赫伯特·斯宾塞提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广泛传播和扎根。斯宾塞依照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理论,重新解释自然法、自然权利和人权。他说,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过程中的最适者享有一些自然权利,赢得了特权。政府没有创造人权的权力。人权是自然法运作的产物。自然的和不可让与的权利只属于那些生存斗争中成功的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美国理论家是威廉·萨姆纳。他宣称,在经济上,在不断地“为生存而斗争上取得成功,并造成了最适者生存,这是善的,而其对立面,即不适于生存,是恶的。”他说,“自由对竞争来说是必要的,财产和不平等对于自由来说也是必要的,并且是自由的条件。”社会达尔文主义加强了美国的主流政治文化。以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神圣性为基础的美国主流政治文化是重竞争,重个人发展自己,挤垮对手,独占市场,谋取暴利;是歧视黑人、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歧视妇女,歧视穷人。这种主流文化指导下的对外政策就是扩张主义、霸权主义。
从历史上看,我们只须举荦荦大者,即可略窥美国国内人权之端倪。
第一,美国1776年独立,1920年妇女才有选举权。在这方面,美国用了144年。直至1965年,美国才取消了对黑人的有关选举的限制。在这方面,美国用了189年。时至1993年,《全国选民登记法》(1995年1月1日生效)才规定各州应允许人们通过邮政进行选民登记(只限于选举联邦公职),消除了选民登记中的程序性障碍。时至1984年,美国盲人和残疾人选举权才得到保障。时至1992年,《选举权语言协助法》才保障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填写选票,进行选举。
第二,长期以来美国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种族歧视借助文化而代代相传,沉淀在白人的深层文化结构和心理结构之中。种族隔离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从法律上取缔。但时至今日,仍存在有事实上的种族隔离。90年代,警察的种族主义暴行仍屡屡发生。1992年的黑人罗德尼·金事件曾引起全世界的注目。而近一两年来,拉美移民更是迭遭警察暴行。1990年以来,大约有100名墨西哥人惨死在美国警察和边境巡逻人员手中。1996年1~11月,美国共发生23起严重侵犯墨西哥移民人权的事件。
第三,美国土著印第安人长期以来是白人武力扩张领土的牺牲品。直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印第安人开展维护人权的斗争的震慑下,政府才允许印第安人在他们的保留地逐步实行了部分自治。但长期的掠夺政策使印第安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以及文化教育上比其他少数民族的地位更低。据1990年人口统计,30%印第安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91年,印第安人失业率为45%。
第四,美国政府历来强调政治上、思想上的一统,压制人民的不同政见,造成数次人权危机。在20世纪,第一次人权危机是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而发生的。反战者没有言论自由,遭到镇压,民选的议员因反战而被剥夺议员席位。1919年11月和1920年1月,司法部长帕尔默领导了两次大逮捕,警察未持搜捕状便逮捕了4000多人。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将11.2万守法的日裔美国人从西海岸押送到荒漠地区的集中营。二战后冷战初期,工会、学校和政府人员均要进行忠诚宣誓和接受安全检查,继后则扩大到教科书的审查。麦卡锡主义的盛行更加剧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这造成了“沉默的一代”。这是第二次人权危机。60年代,美国政府迫害抵制入伍者、反越战者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一些反越战的青年学生被警察和军队抢杀。这是第三次人权危机。
第五,美国政府允许人民行使一定的自由权利是以不威胁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为前提的。在美国,大资产阶级控制了生产资料,同样地垄断了大众媒体,诸如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美国政府虽没有新闻审查法,但媒体内部有新闻审查,以确保新闻报道符合官方和大企业的利益。持不同政见者和团体均受政府监视,难有言论自由。弗兰克·唐纳在1971年4月22日《纽约图书评论》上著文指出,在美国,至少有20个联邦机构(包括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和数百个州和地方警察机构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团体进行监视、渗透、设圈套诱人犯罪并进行镇压。1983年10月3日《纽约时报》载文指出,1975年,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披露,单单联邦机构就拥有858座资料库,内藏12.5亿份档案,多数是涉嫌持有非正统政治观点的人的资料。美国政府除依靠警察、军队和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和团体外,还利用精神病院,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心理控制,施行心理外科手术和强迫他们服用损坏思维的药物等。如今,种族歧视,压制不同政见乃象梦魇一样压在美国人民的心头。
美国对外人权战略迭遭各国抵制
中国和东方的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仁政”思想、“民贵君轻”思想等是具有民族导向的哲学思想和传统。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盛赞儒家“仁”的文化精神。在美国,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美国哲人爱默生面对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物欲横流和声色犬马,指出世界上有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称誉东方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佛家的“众生平等”思想。然而这种优秀遗产却被美国主流政治文化荡涤一空。仅就二战以后而言,美国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权思想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如枪杀、暴力犯罪、爱滋病、性骚扰、吸毒等。即使喻为“知识殿堂”的美国校园也被美国报纸比之为暴力和毒品的渊薮。
亚洲人民拒不接受美国的包括美国式人权在内的价值观。美国《外交》双月刊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对新加坡的李光耀进行了采访。李光耀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和西方的民主制和价值观不适用于东亚。他说,“不要不分皂白地把他们的制度强加于这种制度行不通的社会。”他指出,文化的差异使西方的关于民主和人权的概念不适合于东亚。他说,美国“作为总体制度,我感到它的一些部分,诸如持枪、吸毒、暴力犯罪、流浪和公共场合不合礼节的行为等,总之,市民社会的破裂,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个人的权利扩大到他自以为是地行动或错误地行动,损害了有秩序的社会。在东方,主要的目标是拥有良好秩序的社会,从而人人能充分享有其自由。这种自由只能存在于有秩序的状态,而非存在于争夺和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他举例说明,美国有恶性的吸毒问题。而在新加坡,法律规定,对行为可疑的人进行毒品尿检。如果是阳性,就强制对这些人进行戒毒治疗。而在美国,若这样做,就侵犯了个人权利,就会对簿公堂了。新加坡严厉制约个人的不良行为。即使美国公民迈克尔·费伊因在新加坡破坏公物,也遭杖笞。李光耀指出,西方人抛弃了社会的道德基础。离婚率高,妇女为家长的单亲家庭多,均为明证。李光耀强调,新加坡和东亚坚持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神。他指出,东亚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保持了传统的优秀价值观,而“这是美国人不能解决的。”这里,笔者不对新加坡的经验作全面评价,只愿指出,新加坡在经济长足发展的同时,有健全的法制,有国民对法的理解,尊师重教,民众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良好的礼貌操行和社会责任感,遵守社会纪律和社会公德。在新加坡,几乎没有吸毒,没有艾滋病,没有嫖娼,乃至刑事犯罪和自杀率接近于零。而在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如吸毒和暴力犯罪等与工业化成就形成极大的反差和对立。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已成为社会肌体上的痛疽,也使人性中的邪恶放肆恣张,表现为在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各领域的社会失范。
美国对外人权战略可以休矣
克林顿总统于1994年初夏把对华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受到中美两国人民的欢迎,受到美国企业家的欢迎,也受到美国两位前国务卿基辛格和万斯(他们都是美国大公司的顾问)的称赞。他们认为这种对华政策将会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和亚洲的和平和稳定。奉行同北京的更好的关系,不是美国施惠于中国,因为中美需要相互共同谋求地区安全。美国需要中国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合作,从朝鲜问题到先进武器技术的扩散对环境的威胁。因此他们称赞克林顿把人权问题置于“总体关系更广阔的背景中。”
前总统尼克松是美国一位重实际的政治家,首先对改善中美关系作出努力。他在逝世前完成的、并于1994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超越和平》指出,中国经济力量会使美国侈谈人权成为轻率之事。他反对美国把最惠国贸易地位与人权挂钩的政策,指出“在10年内,这将使它们(按指美国侈谈之人权)不相干;在20年内,这将使它们令人可笑。”尼克松认为,到时候,“中国会威胁不要美国的最惠国地位,除非我们改善底特律、哈勒姆和洛杉矶南部和中部的生活状况。”尼克松回顾1992年末邓小平已向美国新一届政府表示中国政府“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开展合作和不搞对抗。”尼克松针对美国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夙怨,批评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反应是“增加不信任,挑起麻烦,威胁不合作和激起对抗。”他指出,华盛顿应以一个大国应受的尊敬来对待中国。基辛格赞同尼克松的看法。他在1994年出版的题为《外交》一书中建议,美国不要“公开地限定条件”,即让中国屈辱地适应美国的价值观。他认为,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在全球战略,特别在亚洲战略上进行“心照不宣”的合作。他相信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在东亚,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发展与中国和日本的长期的良好关系。他把中、美、日看作是一种新的三角关系,而美国注定在中、日之间起平衡作用。并且他认为,在中、日中间,中国更具重要性。他写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美、日长期良好关系的前提,也是中、日良好关系的前提,”因为中国在未来数年中将表明“在大国中地位最大提高。”克林顿政府应该听一听美国有识之士的劝喻。
从世界格局看,冷战结束后,出现新的情况。全球经济的重心逐渐东移到环太平洋地区。在全球中,经济的重要性愈加突出。而中国具有广袤的腹地和丰富自然资源和众多劳动力以及占世界人口1/4的广阔市场。1994年夏末,美国商务部长布朗访问北京。美国报纸称这是“贸易外交”。中美贸易额已由1993年的300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600亿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美国第六位贸易伙伴。今后,克林顿政府不能不考虑美国大公司与中国做生意和在中国投资的意愿。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世界潮流。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新时期对中国和东方的“仁”的文化精神的发展应用。美国的有识之士也注意到这一世界潮流。美国的外交历来有两个支柱:一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二是输出美国价值观。美国是把中国看作合作者,还是看作潜在的对手呢?克林顿政府今后可能还会在这两极中间摆动。明乎此,对克林顿政府今后的举措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