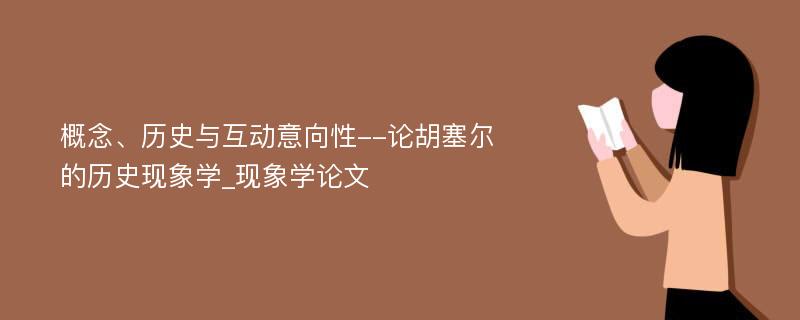
理念、历史与交互意向性——试论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向性论文,现象学论文,历史论文,试论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是历史性的存在者,甚至唯有人才能“有”历史。然而历史的本质究竟何在,却始终见仁见智。在这里,笔者试图从历史与理念(或意义)的关系角度切入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历史有无内在的意义或理念贯穿其中:它是单纯事实的集合,还是某种“事先”就存在的理念之实现历程?若是前者,它如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如何能称得上是历史?若是后者,这种“事先”就存在的理念本身又如何可能?它是否有其自身的起源?若历史真的只是“事先”就已存在的理念的实现过程,那岂不正如利科所说,历史就不再是“一种无法预料的冒险”,“恰恰会丧失它的历史性”(利科,第835页)?可见,如何理解历史与理念的关系,确是历史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以往的历史哲学在这个问题上往往陷入两难:若否认历史中有一以贯之的理念,则导致历史的统一性不可能,进而导致历史本身的不可能;若承认历史中有一以贯之的理念,则又解释不清此理念本身究竟如何可能,并且会导致历史性本身的丧失。与以往的历史哲学相比,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与理念之关系的新方案,从而使我们有可能走出上述两难困境。
一、历史的本质与历史现象学的基本任务
胡塞尔有关历史现象学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其后期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尤其是《几何学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篇手稿中。顾名思义,后者追问的就是几何学的起源这一历史问题。然而如所周知,像“起源”或“发生”这类历史问题,在胡塞尔前期现象学中恰恰是被排除在外的,① 因为那时的胡塞尔认为,历史并不能为哲学提供最终的奠基或论证(胡塞尔,1999年,第50页)。② 但既然如此,后期胡塞尔为何又要转向诸如几何学起源、甚至更为一般的历史可能性条件这样的历史问题?
现在以胡塞尔对几何学起源的考察为例,对此略作说明。在后期胡塞尔看来,几何学作为一种“意义成就”和“文化事态”,是凭借其“原初的意义”才持续有效的,同时也是凭借这种“原初的意义”才能“继续发展,并且在一切新的形态中仍然是‘这唯一的’几何学”。(Husserl,S.365;胡塞尔,2001年,第427页)③ 因而,如果要想真正理解几何学的意义,就必须对几何学的“起源”进行“回溯”,揭示出它的那种“原初的意义”。所以,“理解几何学以及一般预先给定的文化事态,就已经意味着意识到了它们的历史性”(Husserl,S.379;胡塞尔,2001年,第448页)。对胡塞尔来说,对几何学的意义进行“说明”或“使之明见(Evidentmachung)”, “不外都是历史的揭示”(ibid;同上,第448-449页),即对其原初意义的揭示。也正因此,胡塞尔在《起源》一开头就说:“我们不可将我们的目光仅仅集中到流传下来的现成的几何学上,以及集中到几何学的意义在伽利略的思想中所具有的存在方式上”:因为在伽利略以及“古老几何学智慧的所有后来的继承者的思想中”,几何学的存在方式都是“现成的”(ibid,S.365;同上,第427页),它的原初意义已被遗忘或掩盖了,人们不再能够生动地理解它。所以胡塞尔接着说:“宁可说,我们也应该,甚至首先就应该,回溯留传下来的几何学的原初的意义,……”(ibid;同上)。总之,“使几何学成为明见的,就是揭示它的历史传统,不管人们是否清楚这一点。”(ibid,S.380;同上,第449页)
然而,对几何学起源的回溯所具有的意义尚不仅如此。在胡塞尔看来,它还具有“一种范例的意义”:“我们的这些考察必然会引向最深刻的意义问题,科学的问题,和一般科学史的问题,最后甚至会引向一般的世界史的问题;因此我们的与伽利略的几何学有关的问题与说明就获得一种范例的意义。”(ibid,S.365;同上,第427页)换言之,不仅理解几何学必然要求我们回溯它的原初意义,而且理解一般科学史、一般世界史也要求我们追问其相应的原初意义。历史在本质上就是这种原初意义或内在意义结构之形成与传递的过程。用胡塞尔自己的话说即是:“历史从一开始不外就是原初的意义形成和意义积淀的共存与交织的生动运动。”(ibid,S.380;同上,第449页)
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历史概念。首先,依据这一概念,历史本质上是意义的历史、理念的历史。这就使它有别于把历史视为单纯事实之集合的实证主义历史观。其次,由于它认为历史必然具有内在的意义结构,而且这种意义结构甚至具有终极目的的品格,④ 这又使它也有别于狄尔泰式的历史主义,后者认为历史乃一系列没有内在统一性的精神形态的更替转化。最后,虽然这种历史观认为历史有本己的理念一以贯之,有似于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然而它又与后者有本质区别:在胡塞尔看来,作为历史之“主体”或“主词”的“意义”或“理念”,并不是在进入历史之前就已存在的某种神秘之物,好像历史只不过是它在时间中的实现过程,相反,这种意义或理念也有其发生、传递、积淀以及不断重新激活的过程。因此,一方面,正是理念才使得历史具有可能;但另一方面,理念自身也有其不可还原的历史性:历史性乃是其存在方式。在其历史性之外,理念一无所是。
若就理念(意义)与历史的关系看,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至少包含这样几重任务:
首先,对留传下来的历史事实进行本质直观或本质还原,以揭示出历史中的理念(历史的先天、意义结构)。其次,对理念进行谱系学的还原,揭示出理念的谱系或其发生的条件与过程。这里涉及的问题将与“观念对象性的历史性即它们的起源和传统”(Derrida,p.4)⑤ 有关。最后,考察理念如何从单个主体内在的意义构造物变为交互主体的、普遍的客观观念之物的过程,即理念的同一性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过程。这一方面将涉及语言、文字、历史等“肉身”因素对于观念对象性的构造作用,另一方面将涉及这种构造所以可能的超越论的主观条件究竟何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与否,最终将关系到历史的统一性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下面尝试对这几个问题分而论之。
二、历史中的理念与对历史的本质还原
历史本质上是意义史、理念史;历史中的意义、理念是历史中的先天和常项;正是这种先天和常项构成了历史事实的可能性条件。因此,就像世界中的任何事物都先天地处于其固有的本质区域中并以其为基础一样,人类的历史事实也是如此:
如同所有东西一样,每一种类型的事实性,包括那些在反对意见中起作用的类型的事实性,
都在人类的普遍东西的本质结构中,有其根源,……(Husserl,S.386;胡塞尔,2001年,第458页)
胡塞尔认为,如果关于事实的历史学要想具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就只能“奠定在普遍的、历史的先天之基础上”。(ibid;同上)反之,如果一种历史学仅仅关乎历史事实,即仅仅是“朴素地、直接地从事实出发进行推论,却从不将这种推论整个地以之为根据的一般的意义基础当作主题,也从不研究意义基础所固有的强有力的结构性的先天之物”,那么这样的历史学就是“令人费解的”(ibid,S.380;同上,第450页),因为可理解的只能是意义或理念。
所以,历史现象学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既有的历史事实出发,对历史进行本质还原,揭示出历史中的先天结构或意义基础,从而使历史传统变得可以理解。比如,对于留传下来的几何学传统,要想使其变得明见,就必须揭示出“具有其最丰富内涵的历史的普遍先天”,因为后者正是明见性所产生的东西(ibid;同上,第449页)。这样,通过对历史进行本质还原,历史现象学便使“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历史学成为可能”:
只有揭示出处于我们的现在之中,然后是处于某个过去或将来的历史的现在本身之中的本质一般的结构,并且整个说来,只有在对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们整个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具体的历史的时间的揭示中(从它的整个本质一般的结构加以揭示),只有这样一种揭示,才使真正有助于理解的历史学,有洞察力的历史学,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历史学,成为可能。(ibid;同上,第450页)
历史事实中的这种“本质一般结构”或“内在的意义结构”,构成了历史的超越论前提或条件。用德里达的话说,它们“制约着纯粹传统和纯粹历史即历史一般的模式的存在”,是“历史本身的显现的可能性”。(Derrida,p.56)只有揭示它们,历史才能对我们显现出其意义,才能成为可理解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历史现象学在为历史学进行奠基。当然,这里的历史现象学,还仅仅是作为对历史进行本质直观或本质还原的历史现象学。
既然对历史的本质还原如此重要,那么这种还原究竟该如何进行呢?“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获得历史世界的普遍的、与此同时又是确定的、始终忠实于起源的先天之物呢?”(Husserl,S.383;胡塞尔,2001年,第453-454页),胡塞尔如是问。与在其他场合一样,胡塞尔在此同样提出了想象变更的方法:
但是我们有能力,并且我们自己也知道有能力,完全自由地在思想中和想象中改变我们人的历史存在,以及改变在这里被解释为这种存在的生活世界的东西。正是在这种自由改变当中,在对生活世界的可以想象到的可能性的熟悉当中,以必真的明见性出现了一种贯穿于一切变体的本质普遍的存在。(Husserl,S.383;胡塞尔,2001年,第454页)
如此一来,我们就“消除了与作为事实而有效的历史世界的任何联系,而将这个世界本身只看作一种由思想上可能的东西构成的”。(ibid;同上)由于这种想象变更的自由,我们就可以不再把作为事实而有效的生活世界实证主义地看作一个不可还原的“事实”。相反,它现在暴露为只是超越论生活的一个可能的“事例”。我们的目光将从这个“事例”转向它所例示出来的“必真的不变项”,并将它“作为同一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原初自明的东西,……一再地表明出来”。(ibid;同上)
经过如此还原出来的意义结构、先天结构,一方面将涉及“历史的现在一般”、“历史的时间一般”这种整体的形式(ibid,S.380;同上,第450页),比如“活的当下”;另一方面,还将涉及人类的普遍的理性目的论:“这种意义必然进一步导致已经指出的理性的普遍目的论这种最高的问题”(ibid,S.386;同上,第458页)。但关于这一点,本文此处还无法展开。
现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通过本质还原得到的历史先天或理念又是从何而来?它也有其发生、起源吗?如果有,它的起源何在,谱系何在?要想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对历史进行一个不同于本质还原的发生学还原或谱系学还原。⑥
三、理念的谱系学还原——理念的“内在历史”或“深层历史”
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直到前期胡塞尔,其主流观点认为先天之物(观念对象或理念)没有历史。历史几乎总被当作经验的历史、事实的历史。由这种历史中获得的,自然只能是经验之物、相对之物,谈不上任何必然性与普遍性:既不能对后者进行论证,也无法对后者构成否证。一如胡塞尔所说:“从历史根据中只能产生出历史的结论。从事实出发来论证或反驳观念,这是背谬——用康德所引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从石中取水(expumice aquam)。”(胡塞尔,1999年,第50页)
但也正是胡塞尔本人的现象学的一系列革命性发现,又必然会推翻“观念对象没有起源、没有历史”这一唯理论的教条。因为首先,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任何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反过来,任何事物,包括观念对象或理念,也总是意识的意向相关项,因而是意识的构造成就。换言之,没有任何事物是独立于意识活动的自在之物。事物作为意向相关项,作为意向活动的构造成就,没有自性:它们都在某种相应的意向性活动中有其起源。其次,胡塞尔后期的发生现象学发现,作为执行意向构造活动的意识主体也并不是一个无时间、无历史的现成主体;相反,它也是自身构造、自身积淀的产物,因而也有其历史性。最后,观念对象本身的传递、积淀与重新激活,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这种历史性本身就是其存在方式。因而观念对象最终无法摆脱历史性。
这样一来,追问观念对象或理念的起源,揭示它的历史性,便成为历史现象学之不可回避的任务。一如倪梁康先生所说:“历史现象学所要讨论的课题,应当是观念对象性的本质构造的发生与历史。”(倪梁康,第44-45页)然而,这个意义上的历史还是被前期胡塞尔排除出现象学之外的作为事实集合的历史吗?显然不是。与作为事实集合的外在历史相比,胡塞尔将这种历史称为“内在历史”(Husserl,S.386;胡塞尔,2001年,第458页),或“内在的意义结构”的历史。在此意义上,历史现象学要走向的是“历史的纵向维度”(Derrida,p.15);沿着这一维度,它“将展示出一些通常的历史学完全不知道的深层问题”(Husserl,S.365;胡塞尔,2001年,第428页)。而这些“深层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就是观念对象或理念的起源问题。历史现象学将如何回溯理念的起源?下面仍以胡塞尔对几何学起源的追问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胡塞尔在《起源》中首先排除了两种对于追问几何学起源的误解:第一,“对于几何学的起源的探询”“不应被看作要查明那些实际上提出纯粹几何学命题、证明、理论的最早的几何学家们”;第二,也不应被看作是“查明他们发现的某些命题,如此等等”。(ibid,S.366;同上,第428页)在胡塞尔看来,这两种查明都是“文献学的-历史的探询”(ibid;同上)。这种“查明”即使是可能的,“即使它最终囊括了全部的历史事实……,我们仍然看不见这种奠基行为的意义本身”。(Derrida,p.19)那么,对于几何学起源的追问究竟要追溯什么呢?胡塞尔说:“与此相反,我们的兴趣应该是追溯那种最原初的意义,正是按照这种意义,几何学在过去生成,并且从那时起,在数千年间作为传统而存在……”。换言之,我们探询的是“几何学在历史上最初据以出现……的那种意义”。(Husserl,S.366;胡塞尔,2001年,第428页)然而,追溯到这种意义就完成了对几何学起源的追问了吗?否。因为最关键的是这种最原初的意义的起源。起源于何处?胡塞尔说:它“肯定也是从一种……最早的创造活动中生成的”(ibid,S.367;同上,第430页)。换言之,这种意义作为一种精神成就,“在成就的活动当中有其起源:首先是作为计划,然后是在成功的实行之中”。(ibid;同上,第430页)
所以在胡塞尔看来,几何学的起源最终并不是某种东西或状态,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一种特殊的有所成就的活动,一如有学者所说:“处于这个开端上的是所谓原创生(urstiftende)(的),也就是本源含义的构成活动。”(钱捷)因此,几何学的对象在作为观念对象被直观到之前,已经有一个在超越论的意向性活动中被构造、被创造的“前史”。
所以对几何学起源的追问,最终要回溯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创造几何学对象的原创造的活动。德里达也将这一回溯的过程称为“历史性的还原”:
历史性的还原(它也是运行在变更之上)将成为一种重新激活和意向活动。我们不再重复观念对象的业已构成的含义(这是本质还原要做的事——引注),相反,我们应该唤醒含义对开创性和奠基性行为的依赖,尽管这一行为被隐藏在第二性的被动性以及无限的沉淀过程之下;我们应该唤醒含义对原初行为的依赖,正是这一行为创造了对象,……(Derrida,p.32)
然而这究竟是怎样一种行为?在胡塞尔看来,这一创造几何学对象的行为乃是一种特殊的理念化活动:Idealisierung。这种“特殊的‘理念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创造理念的活动,它并不是一种直观活动:不仅不是感知或想像意义上的感性直观活动,甚至也不是“观念化”(Ideation)意义上的本质直观活动。胡塞尔认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纯粹思想’的理念实践”(Husserl,S.23;胡塞尔,2001年,第37页)。正是这种“纯粹思想”的“理念实践”,创造出了直观的生活世界中并不存在的“理念”。在此意义上,这种“理念化”与在直观世界中直接把握艾多斯(本质)的“观念化”有严格区别。用德里达的话说就是:它们“一个在创造中构造对象,另一个在直观中规定对象”。(Derrida,p.147)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理念化活动又如何可能?它能“凭空”发生吗?当然不能。在胡塞尔看来,这种理念化活动恰恰是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才获得可能。因此,理念的意义最终也要回溯到生活世界才能得到理解。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生活世界就是胡塞尔所追溯到的最终的根据、起源,因为通过现象学的超越论还原,胡塞尔表明生活世界乃是超越论生活的意义成就。
如此一来,理念的产生便有一个长长的谱系:首先,它直接的起源是理念化活动;其次,理念化活动是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发生的;最后,生活世界又是超越论生活的意义成就。所以,要追溯几何学的起源,乃至一般理念的起源,最终需要一种对于理念的谱系学还原,一种“理念谱系学”的研究。但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已在别处讨论,故此处不再展开。(参见朱刚,第47-53页)
理念被创造出来之后,它的“内在历史”或“深层历史”不仅没有结束,毋宁说才刚刚开始:它必然要经历一番积淀、传递的历程。然而这一历程同时也是它的历险:它随时有可能湮灭、埋葬。因此它也需要重新激活,需要后来者不断地从留传物出发进行超越论的回溯。但问题是,当理念不断被传递和激活时,如何能保证理念在这过程中仍保持为同一个理念?即如何能保证理念的客观同一性?如果无法保证这一点,历史的统一性又如何可能?最终,历史本身又如何可能?因为历史——如上所说——本质上是意义的历史、理念的历史。
四、理念的肉身化与交互主体性——理念的客观同一性何以可能?
历史是理念的历史,历史的统一性奠基于理念的客观同一性之中。然而如果理念像胡塞尔所说的,原本并非自在同一的客观之物,而是某个主体的意向性构造成就,那么这种原本是主观内在的构成物如何能够成为交互主体的客观同一之物?限于篇幅,这一过程的具体步骤在这里无法详述,笔者只强调使理念的客观同一性获得可能的两个条件:
首先,理念必须肉身化。先是肉身化为语言,这样才能传递给作为“同感共同体”和“语言共同体”的人类同伴,使得理念成为交互主体性的,这样“客观性就……初步地产生出来”(Husserl,S.371;胡塞尔,2001年,第436页)。之所以说是“初步地产生出来”,因为这时一旦人们不说话,那么理念就仍会停留于单个主体性内部。所以理念还要进一步肉身化为文字:文字“无需直接或间接的个人交谈,就使传达成为可能,它可以说是潜在化了的传达”(ibid;同上,第437页)。所以直到文字或书写,“理念构成物的客观性”才得以“完满地构成”(ibid;同上,第436页)。
其次,但是理念在文字中毕竟仍只是潜在地在场;只有读者把它重新激活,它才能重新变得明见,重新在场。不过问题是,后来的读者已不再是原作者,甚至即使是在当场的交谈中,听话者也已是一个他者。而既然听者或读者已经是他者,我们该如何确保听者或读者所接受或重新激活的意义一定是说者或原作者所构造的原初意义?
因此,要想保证理念构成物具有客观同一性,就还需要第二个条件:一种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或“同感共同体”的存在。只有这样一种交互主体性或同感共同体才能将理念构造为交互主体的,从而是普遍的、客观的,并进而构造出统一的历史、统一的真理:“惟有共同体的主体性才能创建真理的历史系统并总体上对此负责。”(Derrida,p.49)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交互主体性或同感共同体,在奠基的顺序上是第二性的、派生的,抑或是本原的、第一性的?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如何能保证一个个原本相互外在的主体能够真正地——至少是原则上可能地——走出各自的主观内在性而达到一致、相互认同?这种原则上的可能性靠什么来提供保证?靠共同的人性、理性?关键是,如果每个主体原本都封闭在其自己的、唯我的体验领域中,那么每个主体凭什么说自己所认为的“共同性”与别人所认为的“共同性”就真的是“同一个”“共同性”?这种共同性难道不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共同性”?如果主体性原本就是一个个相互外在的个别主体,那么它们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一致就并无先天的、必然的保证。很可能一切都是偶然的,很可能对一个普遍、客观的理念的认同只是一种假象。
所以,要想保证主体间的认同、一致是先天可能的,就必须承认交互主体性、同感共同体是先天可能的,而且是第一性的、本原性的。换言之,主体性原本就是交互主体性,“自我”原本就是“共我”、“大我”。诸多主体的相互外在只是假象,相互内在才是实情。而这也恰恰是胡塞尔本人的意思,至少是他在某些场合表达出来的意思。比如他在《危机》中谈到主体性与交互主体性之关系时曾说:“主体性只有在交互主体性之中才是它所是之物,即以构成的方式起作用的自我。”(Husserl,S.175;胡塞尔,2001年,第208页)如果说在这里胡塞尔还只是说明自我只有在交互主体性中才成其自身、因而离不开交互主体性的话,那么下面的这段话就表明,诸自我原本就是相互内在的,或者说,原本就是以交互主体的形式存在:
在真正理解着自己本身的普遍的悬搁中就显示出,对处于其固有本质之中的诸心灵来说,决不存在彼此外在性这样的分离。那种在悬搁之前的世界生活的自然的-人世的态度中是彼此外在的东西,……在悬搁中就转变成了纯粹的意向性的彼此内在的东西。 (ibid,S.259;同上,第305页)
这段话表明:诸心灵、诸主体只是“在悬搁之前的世界生活的自然的-人世的态度中”才是“彼此外在的东西”,而在悬搁之后就变成了“彼此内在的东西”:恰恰是这种“彼此内在”才是它们的“固有本质”。因此,“在朴素的实在性或客观性中是相互外在的关系,如果从内部来看,就是意向上彼此内在的关系”。(ibid,S.260;同上,第307页)所以,从超越论的层次上看,主体问的共同体或交互主体性才是第一性的、奠基性的;只是由于这种交互主体性沉湎在世界生活的自然的-人世的态度中,才把那作为超越论交互主体性之客观化的、一个个彼此外在的人的心灵视为自己的本来状态,然后再徒劳地去寻找彼此之间的一致,而忘记了它们原本就是相互内在的。
五、交互意向性:交互主体性与历史统一性的超越论条件
那么,这样一种本原的交互主体性又如何可能?它以何种方式存在?实际存在于物理时空中的只是一个个相互外在的个别主体,哪里有一个相互内在、相互包含的共同主体?欲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揭示出一种被普遍忽视的意向性:笔者把它称为“交互意向性”。这一意向性在胡塞尔那里已经被点出来了,只是好像还没有被如此命名。比如在前引这句话中:“那种在悬搁之前的世界生活的自然的-人世的态度中是彼此外在的东西,……在悬搁中就转变成了纯粹的意向性的彼此内在的东西。”在这里胡塞尔明确地说:诸主体的彼此内在是“纯粹意向性的”。换言之,如同意识活动对于意向相关项的包含是非实项的包含一样,诸主体的相互包含也不是实项的包含;它们的彼此内在也不是实项的内在,而是意向性的内在。所以胡塞尔在同一处又说:“在生动地流动着的意向性中(自我-主观的生命就在于这种意向性),预先已经以同感的方式和同感的地平线的方式意向地包含着每一个其他的自我了。”(ibid,S.259;同上,第305页)又说:“这些主体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摆脱意向性的关联,按照这种意向性的关联,他预先就包含在每一个其他主体的地平线之中。”(ibid;同上)这种每一个自我都不能从中抽身出来的意向性关联,即这种使得每一个自我预先就包含着任何一个其他自我、并且也被包含在其他自我之地平线中的意向性关联,笔者称之为“交互意向性”。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原本的、不可还原的交互意向性,所以虽然并没有一个实在的人格性的交互主体,但是当任何一个主体的意识生活进行的时候,即使这种意识生活并不是指向其他主体的,它也仍然同时已经生活在与其他主体的意向性关联之中了,或者说,就已经当场意向性地构造起交互主体性了。因此,交互主体性是以交互意向性的方式存在的,或者说,交互主体就存在于、而且也只能存在于意识活动的交互意向性之中。交互意向性乃交互主体性之所以可能的超越论条件。
同时要注意的是,这种交互意向性不仅存在于同代主体之间,而且也必然存在于不同代交互主体之间。换言之,每一个主体,都意向性地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并生活在这样一种意向性的世代关联之中。一如胡塞尔所说:“每一种科学都与一个由共同协作的工作者构成的开放的世代链条相联系,这些工作者……是为总的生动的科学贡献力量的主体性。”(Husserl,S.367;胡塞尔,2001年,第430页)或如德里达所说:“每一个研究者不仅感觉到他通过对象或使命的统一性而与所有其他的研究者联系在一起,而且他自身的主体性正是由那种总体主体性的理念或视域所构成——这种主体性在他之中并通过他为他的每一个行为担负责任。”(Derrida,pp.49-50)
如此看来,交互意向性以及作为其意向相关项的总体主体性或交互主体性,便构成了每一个主体的不可还原的本质要素。从发生的奠基顺序上来说,它们才是第一性的、本原的,它们作为单个主体性的地平线制约并构造着单个主体及其意向性。由此可见,不仅有作为对象意识之意向性的横的意向性和作为时间意识之意向性的纵的意向性,而且还有第三种意向性——朝向他人的交互意向性。正是这种交互意向性,构成了交互主体性的超越论条件,因而也构成了理念的客观同一性的超越论条件,最终构成了历史及其统一性的超越论条件。
注释:
① 利科甚至说,在胡塞尔思想中,“从一开始便……遭到抛弃的是一门历史哲学,这种哲学把历史理解为生成和发展”。(利科,第802页)
② 钱捷先生也认为:哲学史告诉我们,“历史”与“经验”一样是奠基性的否定因素。任何被认为是基础的东西,如果被证明是经验的或历史的,则它将永远地失去其作为基础的资格。(见钱捷)
③ 本文所引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的文字,主要来自王炳文先生的译文,但皆参照德文。有改动处不一一注明。
④ 关于历史目的论,胡塞尔曾明确地谈到过“一种贯穿于历史整体中的目的论的理性”(Husserl,S.386;胡塞尔,2001年,第458页),另外还可参见《危机》中译本第373-376页、第403-404页、第458页等处论述,亦可参见德里达的《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第十一章以及利科的《胡塞尔与历史的意义》一文。
⑤ 本文所引德里达的,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traduction et introduction(PUF,1962)的文字,同时参考了钱捷教授的繁体字译本(德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导引》,台北桂冠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和方向红教授的简体字译本(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并核对法文版,有改动处不一一注明。文中将只给出法文版页码,即中译本边码。
⑥ 德里达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中曾提到两种还原:一种是“静态现象学的还原”,另一种是“发掘出创建行为的独特本质”的还原,后者同时还“拯救出被打开的一般性历史的总体含义”。(Derrida,p.37)他这里说的第一种还原相当于本文所说的对于历史的本质还原,后一种还原相当于本文所说的发生学还原或谱系学还原。德里达本人在另一处也用到了“发生学的步骤”这样的说法:他在一条注释中引用了芬克的下述研究成果,即区分了重新激活的两个要素或两种类型:一是作为“逻辑解释”的重新激活,一是对“出现于正题性的含义构造中的内在的含义构成传统(Sinnbildungstradition)”的重新激活。“只有当第一个意义上的重新激活得到实现时,当它达到自己的目标时,作为向‘原创建’进行回问的重新激活才开始。”(引号中为芬克原文)在引了芬克的这一句后,德里达引申说:“因而这一说法确证并强调了对含义进行静态分析和规定的必然优先性,这种分析和规定必须统辖所有发生学的步骤。”(ibid,pp.41-42)这里所说的“发生学的步骤”,相当于本文所说的发生学还原或谱系学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