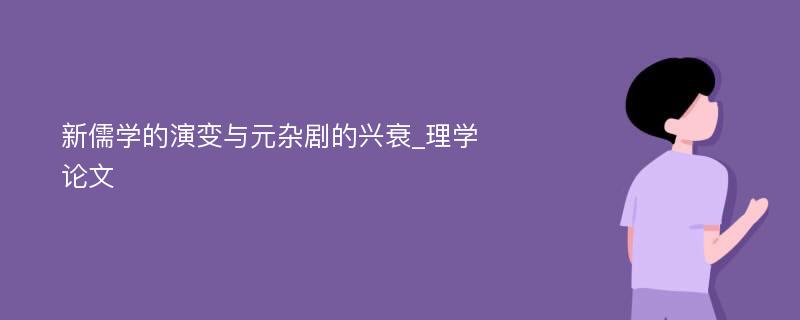
理学流变与元杂剧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衰论文,理学论文,元杂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来戏曲研究者们在探讨元杂剧缘何兴盛时,认为元代统治者对戏曲的特殊喜好,元代废止科举制度,元代“以曲取士”等是政治原因;论其经济原因,则指出元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为元杂剧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和群众基础;在考察其社会原因时,则以元代知识分子沦为“九儒”的社会地位和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及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为主要依据;至于分析其文学原因,则认为元代文化思想的放任政策,杂剧自身发展成熟的规律和剧作家、艺人的卓著贡献等都是重要条件。
诚然,上述种种观点都论之有据,自成一家之言,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对元杂剧兴盛原因的综合研究。而关于元杂剧衰落的原因,同样从思想控制的严密、士子地位的变化等政治方面和杂剧南移的社会原因以及内容蜕化、形式凝固、语言雕琢、唱腔僵化等进行探讨,自然也获得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成果。但是,就社会主导思想而言,宋元以来理学大兴,不能不对元杂剧的兴衰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对此,以上诸多研究论著中,虽偶有涉及,却未曾有较为系统的论述。本文试图从理学流变中探究元杂剧兴衰的原因,以期寻求一条新的线索。
一、宋代理学对杂剧的禁锢
宋代理学的核心观点,是将产生万事万物的本源归结为一个“理”。何谓“理”?朱熹解释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朱子语类》)“理”成为离开事物而独立的存在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因此,“理”就是“天”,就是“上帝”。朱熹说:“帝是理、是主”。从这一“理”本体论出发,理学家们对礼仪秩序加以阐释,曰:“礼者,理也,文也。理者,实也,本也;华也,末也”。①将“理”与“礼”的关系解释为本末关系,使“礼”完全归属于“理”的最高范畴,并在伦常系统中获得权威性和必然性的认识,从而达到构建封建礼治秩序的目的。由此,朱熹又把这种永恒的“理”引申到封建道德范畴中来,借以大肆宣扬封建的“三纲五常”。在这种礼治秩序中只承认人伦关系网络的存在,而根本否认个体的独立价值。为了强固礼治秩序,理学家们又提出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观念。二程说:“灭私欲,则天理明也”②,朱子说:“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③。这样一来,将伦常道德与人的感性自然要求完全对立起来,灭绝了个体的一切快乐、幸福和利益。从这种穷理灭欲的原则出发,又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④的律条,将个体的主体性、独立性完全消融于超越一切的“礼”之中了。这是理学的“经世致用”的一面,称为“外王”之学。另一面,朱熹又提出了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必然遵循“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与格物”⑤。所谓“格物”,是体验外在性的“天理”;所谓“致知”,是将外在的伦理规范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成为一种内心“自律”。这是理学中自我修炼的“内圣”之学。至此,在先验的绝对的“理”的统慑下,确冶了礼治秩序、等级名分,人伦道德和修身自律等十分严密完备的理论体系,非常适合封建统治者实行专制统治的需要。因此,宋理宗曾下诏书:“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颙、程颐,真知实践,深探圣学。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其令学官,列诸崇祀”⑥。从而,理学被钦定为官方哲学,各地兴起了书院讲学之风,作为传播理学的重要途径。
这里简述理学的基本内容在于说明,程朱理学与宋代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出现的市民思想形成了尖锐对立。北宋年间,京都开封城市人口密集,商业、手工业空前发达。南宋临安(杭州)更是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夜市喧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城市经济的繁荣培育了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市民思想的主要标志是摆脱封建礼治等级制度的束缚,满足个体自由发展的欲求。市民 们在劳作、招揽、竞争中,形成熙熙攘攘、风波丛生的都市生活节奏,因而他们无意欣赏典雅、空灵的诗情意境,而热衷于热闹、动作性强、满足感官刺激的故事情节。于是,话本、戏曲等娱乐性艺术形式应运而生。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开封府演出伎艺的瓦舍情形:“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文内栏50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纳数千人。”《武林旧事》记南宋杭州演出的伎艺有50多种,瓦子23处,其中北瓦内的勾栏就有23座,可见当时市民娱乐之兴旺。但这种市民艺术自然为理学所不容。中国历代哲学家重道轻文,不消说市民艺术,就是大学殿堂中的诗文,也为理学家们所鄙视。程、程颐曾反复宣扬“作文害道”的主张,把写诗看作无用的“闲言语”。朱熹更说:“至于文词,一小伎耳:以言乎迩,则不足以治己;以言乎远,则无以治人。”⑦在程朱理学家心目中诗文尚且如此,何况杂剧乎?朱熹于绍熙元年(1190年)知漳州州事时,曾直接禁止当地演戏。⑧可见,宋代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统治着整个社会思想,压抑、禁锢着新兴的市民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致使宋杂剧在理学思想的巨大网络笼罩下,终究未能登上大雅之堂,只能是市民的游艺娱乐而已。
二、官学沦为民学——离心思想情绪的勃发
南宋与金朝南北对峙,朱熹的学说在金朝统治下的北中国并没有广为流传,这就为北杂剧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时机,1234年蒙古灭金,北中国仍在游牧民族的统治下,理学尚未得到元朝君主的青睐。于是,北杂剧在市井社会中得到勃兴。但是,亡金儒士姚枢主动投降蒙古窝阔台汗,又随从蒙军出伐南宋,并俘获宋儒赵复。姚枢说服赵复,赵复答应北上,并献出了程朱的著作。1238年姚枢在窝阔台汗的大臣耶律楚材的支持下,在燕京建立了太极书院,请赵复为师,教授学生。从此,程朱理学在北中国传播开来。元代理学家许衡就是从姚枢那里见到程朱著作,读后受益颇深,并一一抄录,决心效法。他为了宣传理学之道,不仅首创元代的国子学,而且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他的倡导和鼓吹下,1287年,元廷正式建立国子监,教授生员达四、五百人。同时,在路州府县普遍设立了学校。到1290年,全国学校已超过二万所。与此同时,各地书院讲学活动也很盛行,据统计全国至少有四百多所书院。这又是程朱理学在元代传播的另一途径。可以说,理学在元代统治的广泛程度远远超过了视其为官方哲学的宋代。这就出现了一个极为反常的现象:一方面禁锢戏曲发展的理学得到了空前的张大,而另一方面与之对立的反映市民思想的元杂剧却又空前的繁荣和兴盛。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分析理学和杂剧这两个对立物同时在元代并兴的反常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有二:
第一,元代儒士重“内圣”,而无力“外王”。理学的建构本来完成于南宋偏安的社会环境里,随着元代统一南北中国,理学北上,对于身处蒙古铁骑下的北方儒士来说,酷似一剂摆脱精神困境的灵丹妙药。在广大儒士心目中所追求的儒家政治伦理理想,已经被蒙古铁骑踏得粉碎,他们顿觉失去了精神支柱,眼前一片迷茫,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而程朱理学所强调的“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从“格物致知”做起,通过“尽性”便可体味“天道”,达到“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这就意味着个人不必求助于外力,仅仅通过“正心诚意”的道德修炼,就可以强化儒家的道德责任心和社会使命感,进而实现儒家的政治伦理目标。诚如元代理学家吴澄所说:“夫道也者,天之所以与我,已所固有也,不待求诸外,有志而进焉。有见可得,可立而竣。”⑨可见元代儒士们热衷于内心的自我修炼,无暇也无力顾及和规范社会新崛起的市民思潮。在传统儒学中倡导“外王”与“内圣”两条经世路线中,“外王”之学即建立客观功业,“内圣”之学即修炼主体自觉。程朱理学强调“内圣”之学正与元代儒士们的客观处境和心理需要相合拍,更使他们完全转入“专用心于内”的学术路线,对于社会思想已经失去束缚力。因而市民思想得到空前的发展,为杂剧提供了比较自由的思想土壤,促进了杂剧的繁荣。
第二,更主要的是理学在元代沦为民间哲学,与释、道思想及市民思想并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既是一个异族政治统治非常残酷、民族等级划分十分森严的时代,也是一个整个社会思想失去重心和平衡的混沌时代。历代作为控制社会思想的儒学、理学失去了固有的威慑力量,因此,与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离心离德的思想情绪乘隙得以暂时抒发。于是,冲破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桎梏,窦娥敢于骂天骂地骂鬼神,否定“天道”,为争取“人道的呼喊”。其实,窦娥本是善良安分的弱女子,遵从封建礼教,守节尽孝,别无他求。但是,社会的危恶逼得她无辜受灾,含冤难诉,激起她迸发强烈的反抗意识,对封建社会观念中认为最公正无私的天地日月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这实际是对“理”对“天”对“上帝”的否定,也是对“礼者,理也”的否定。《西厢记》中张生和崔莺莺以离经叛道的反封建勇气,冲破“三纲五常”的樊篱,为追求爱情婚姻的自由和幸福而大胆结合。这对理学家宣扬的“非礼勿动”的律条是一种严峻的挑战。“愿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属”的婚姻理想,在《墙头马上》、《拜月亭》等剧中也得到了呼应。“有情”并非有“理”,而“情”是人性的真实反映,是人类进步的婚姻理解。对此,元代理学家胡祗遹不得不承认:“乐者与政通,而伎艺亦随时尚而变,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变而为杂剧。”⑩尽管他强调杂剧的“政治之得失”,“道德之厚薄”,却又不能否认杂剧“随时尚而变”,反映“闾里市井”、“九流百家”、“人情物理”的事实。但同时,胡祗遹也从杂剧中看到了排遣、稀释内心苦愁的作用,他说:“百物之中,莫灵贵于人,然莫愁于人,……于斯时也,不有解尘网,消世虑,熙熙皋皋,畅然怡然,少导欢适者一去其苦,则亦难乎其为人矣。此圣人所以作乐以宣其抑郁,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11)不难看出,历代被文人儒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不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所重视的市民戏曲技艺,元代的理学家们也给予肯定并阐明其社会作用。这一点,从理学的思想体系出发是难以解释的。然而,元代初期中期的理学,作为民间哲学面对当时杂剧兴盛的艺术现象,却不能不作出符合理学观点的解释来。
基于上述两点,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理学从宋代官方哲学流变为元代民间哲学,理学家们及其追随者从宋代的“外王”与“内圣”兼顾的伦理境界,流变为元代专注“内圣”的自我修炼以求摆脱精神困惑的处境,为元杂剧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自由的思想天地。当然,元杂剧的兴盛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本文开头已有陈述,这里只就理学流变对元杂剧的影响而言。
三、民学跃为官学——元杂剧内容的蜕化
到元代中晚期,理学的地位和影响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理学家们在改造儒学“经世”——“用世”路线的过程中,虽然特别注重讲求心性,但其“道德其本,世教其用”(12)的经世致用主张仍然是一贯坚持的。元代理学士们须臾都没有忘怀自己的道德自信心和社会使命感。元初理学家郝经明确地说:“士结发立志,挺身天地间,禀天地之正性……人之于世,治也有用,乱也有用……故天下无不可为之世,亦无不可为之时,至治之不兴,天下之恒于乱也,士之聪明睿智而达此者,必以天自处之,以生民为己任。”(13)出于这种思想,元代一部分理学士子们与蒙古统治者进行合作,郝经明确表示:“今主人(指忽必烈)开潜邸,以待天下之士……岁乙卯(1225年),下令来征,乃慨然启行。以为兵礼40多年,而敦能用士乎?今日能中国之士而不自用,则吾民将膏铁钺,粪士野,其无子遗矣。”(14)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着元代理学家投靠元蒙政权,企图用理学的伦理主张规范蒙古游牧式的统治方略。于是,许衡、郝经等理学之士屡屡向忽必烈进言,极力主张推行“汉法”。忽必烈也网罗大批理学儒士实行“汉制”。到延估年间,元任宗钦准中书省条陈、恢复科举考试,并以明经试士,汰去汉唐尚词赋取士之法,其“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释为主”,“非程朱不式于有司。”(15)从此,程朱理学遂一跃成为元代的官方哲学。这一转变给整个社会政治思想带来了重大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理学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在理学沦为民学时,想控制杂剧而无能为力,现在理学升为官学,自然要施展它应有的政治思想威力。然而此时,杂剧已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一种独立而成熟的艺术形式,想扼杀掉它已不可能。于是便利用它,将理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之类的律条注入杂剧艺术之中,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传播理学道统的工具。如元代后期杂剧作家鲍天佑的《尸谏灵公》宣扬愚忠思想,深得元统治者的赞赏和提倡。兰雪主人《元宫词》云:“尸谏灵公演传奇,一朝传到九重知,奉宣赍与中书省,各路都教唱此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期杂剧创作的倾向性。秦简夫的《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宜秋山赵礼让肥》、《晋陶母剪发待宾》等杂剧,基本上都是宣扬封建道德之作。这样元杂剧原来具有的人道意识、个体欲求及其生活气息和斗争精神被空洞无聊的道德说教所取代,杂剧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已经无法避免了。这种艺术内容的蜕变才是元杂剧衰亡的根本原因。因为任何艺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一旦成了封建礼教的传声筒,艺术就变成僵死的躯壳。所以,元代理学再由民间哲学变为官方哲学,理学家们由自我修炼的“内圣”中转向追求“外王”的功业,构成了元代杂剧由盛而衰的思想根源。
注释:
①程颐:《论语·八》“林放问礼之本”章。
②《二程遗书》卷24。
③《朱子语类》卷13。
④程颐:《四箴》。
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⑥《宋史》卷13。
⑦《晦庵先生朱文公大集》卷59《叔耕》。
⑧《漳州府志》卷38。
⑨《宋元学案》卷92。
⑩(11)《紫山先生大全集》卷8。
(12)《许文正公遗书》卷8《熊勿臾先生文集序》。
(13)《郝文忠公文集》卷19《历志》。
(14)《郝文史公文集》卷37。
(15)《通制条格》卷5《科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