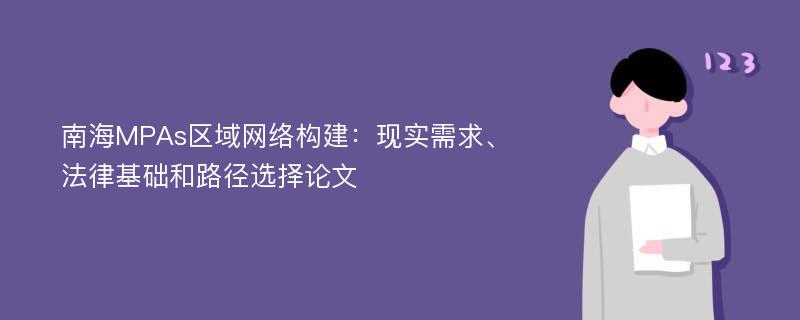
南海MPAs 区域网络构建:现实需求、法律基础和路径选择
胡 斌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400044)
[摘 要] 南海MPAs 区域网络构建是实现对南海大型海洋生态系统整体养护的必要手段。目前,一些全球性公约、现有南海区域环境合作以及南海各国国内有关MPAs 的立法和实践已经为南海MPAs区域网络的构建奠定了相应的法律基础。利用专门性国际公约中的划区管理工具、制定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定或通过沿海国国内MPAs 立法协同是南海MPAs 区域网络构建的三条潜在路径。其中,通过软法设定南海区域共同生态养护目标,并在这一目标下协调各国MPAs 行动来构建事实上的南海MPAs 区域网络是目前最为现实可行的选择。
[关键词] 南海;MPAs区域网络;大型海洋生态系统
海洋保护区(MPAs)被普遍视为实现海洋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养护的有效工具,但单一或少数不成体系的MPAs 往往无法完全满足开放海洋生态系统对大面积保护区的要求。因此,构建一个“由点及面”的系统化的MPAs 网络成为当前实现南海等大型海洋生态系统有效养护的重要手段。在南极、东北大西洋、地中海、波罗的海等大型海洋生态系统所在区域,通过区域合作建立大型MPAs 网络已经成为这些海域的沿海国共同维护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共同选择。近年来,为了缓和南海生物资源退化的趋势,南海各国多数已经在各自主权管辖海域内开展了MPAs实践,但这种“各自为政”、“碎片化”的MPAs 建设并未有效缓解这一趋势。通过开展南海区域合作,构建一个系统化MPAs 区域网络也因此成为当前南海区域环境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于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我海力算什么?面对这样的英雄丈夫,我海力什么也不算。除了对她表示崇高的敬意,我海力能对她做出丝毫的侵害吗?在海力公司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解雇马丽亚就是要告诫大家,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负起责任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南海MPAs 区域网络构建的现实需求
从MPAs到MPAs 区域网络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ecosystem-based)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总体发展趋势,也是实现南海大型海洋生态系统有效养护的现实需求。
入院后第二天凌晨患者突发意识丧失,实时心电监护提示室性心动过速(室速)、心室颤动(室颤),立即行胸外按压等急救措施,但均无效,宣告临床死亡。期间患者携带的24 h动态心电图完整记录了该患者发病至死亡的全部心电图变化(图1~图3)。
(一)从MPAs到MPAs网络
所谓MPAs,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MPAs 是指任何划定的海洋地理界限,为达到特定保护目的而指定并实行相应管制和管理的地区,通常也被称为划区管理工具(area-based management tools,ABMTs)。狭义上的MPAs,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定义,是指“一个通过法律程序或其他有效方式认可、划定和管理的、并得到清楚界定的空间,以此实现对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价值的长期养护。”① Nigel Dudley,Guidelines for Applying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EB/OL].[2019-03-27].https://cmsdata.iucn.org/downloads/uicn_categoriesamp_eng.pdf. MPAs网络是多个MPAs的集合,通过对协调不同空间范围内的MPAs 的设立和管理来实现单个MPA无法有效实现的更为综合的养护目标。① Canada-British Columbia Marine Protected Area Network Strategy[EB/OL].[2019-03-37].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farming-natural-resources-and-i ndustry/natural -resource-use/land-water-use/crown-land/land-use-plans-and-objectives/coastal-marine/canada_bc_marine_protected_area_network_strategy.pdf p.7 实践中,一个MPAs 网络往往包含若干个不同类型的MPAs,以此实现对不同海域生态环境的差异化养护和管理。例如,通过严格的海洋自然保护区保护珍稀物种的关键栖息地或生态系统,而用其他多功能管理区来承载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② Christie,P.,and A.T.White.Best Practices for Improved Governance of Coral Reef Marine Protected Areas.Coral Reefs,2007(26),pp.1047-1056. 此外,MPAs网络不仅是MPAs的网络化,同时也是MPAs 管理的网络化(networking to bureaucracy)。换言之,MPAs 网络不仅要求在特定海洋区域内形成一个“节点——廊道”型的MPAs网络,还要求不同MPAs 的管理者之间协调彼此的行动,从而形成一个高度协调的管理体系。目前,网络化MPAs 已经成为主要海洋国家单独或共同实现特定海域,尤其是大型海洋生态系统养护的主要手段。根据MPAs 网络空间尺度的不同,MPAs 网络既有完全处于一国管辖海域的域内MPAs网络,也有跨越国界的双边、区域和全球MPAs网络,即通常所说的“跨境MPAs网络”(Trans-Boundary MPAs Networks)。本文所讨论的南海MPAs 区域网络便属于后者,即一个涵盖整个南海大型海洋生态系统的MPAs网络,组成该网络的单个MPAs,部分分布于不同沿海国的主权管辖海域,部分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海洋边界,甚至可能建立在南海争议海域之中。从MPAs到MPAs网络的转变,是人类对海洋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也是人类海洋环境与资源管理水平提高的标志。
(二)构建MPAs 区域网络是南海生态系统整体养护的客观需求
首先,南海MPAs 区域网络可以有效克服单一MPA 保护范围过小与海洋及其生态系统开放性之间的矛盾。科研与实践均表明,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洋,在保护效果上,网络化的保护区都优越于单一随机建立的保护区。但相比较而言,一个系统化的MPAs 网络的构建对于多数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而言则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因为与陆域生态环境不同,在开放的海洋当中,无论是海洋生物还是其他物质和能量往往都会在大范围内进行交流和扩散,比如很多海洋迁徙类物种的幼体补充地、育幼地、栖息地、觅食地就往往分散在不同的海洋区域,甚至不同大洋。海洋及其生态系统的这种特点使得面积有限的单个或少数MPAs显得力不从心。正因为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学家主张,与其强调单一MPA 的选位优化,不如构建一个有交互作用的MPAs 网络来预防海洋生物进程中的变化和不确定性。③ 刘洪滨,刘康:《海洋保护区——概念与应用》,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2页。
其次,从环境风险预防的角度而言,与单一MPA相比,网络化的MPAs 可以更好地分散和消解剧烈环境变化或地区灾难给南海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压力,更有利于维持南海MPAs 附近海域的鱼类丰富程度,增强区域海洋生态系统面对环境灾难的韧性。事实上,在过度捕捞海域的“修复”工作当中,由于难以确定鱼类资源的源和汇,实践中管理者就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相互联系的MPAs 网络来解决不确定性问题。
最后,南海MPAs 区域网络是克服碎片化的国家海洋管理与大型海洋生态系统整体养护之间矛盾的必要手段。从海洋地理环境角度来看,南海地处东亚季风区,是季风-海洋动力过程生态响应的敏感海域。④ 李洁,经志友,张偲:《季风环流影响下的南海海洋细菌多样性特征初探》,《热带海洋学报》,2018年第6期,第2页。 在大气强迫、河流淡水输入、黑潮入侵、岛礁地形约束等众多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南海各区域的物质、能量和海洋生物会伴随季风环流而发生密切的交流与联系。夏季,在西南季风的影响下,暖湿气流从爪哇海出发,经卡里马塔海峡,经过南海中心区域后由台湾海峡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冬季则形成一个相反的环流,在东北季风影响下,冷流从台湾海峡出发,向西南流经中越沿海后,或者从卡里马塔海峡流出,或继续沿着婆罗洲和巴拉望海岸线流向南海北部。⑤ Aguliar,Shek O.South China Sea.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2001(12),pp.1236-1263. 因此,整个南海实际上会在季风影响下形成两个相对封闭的环流,在这个环流当中,不同海洋区域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多数的海洋生物也会在这一闭环当中迁徙、流动、扩散。这种海洋环境也因此使得南海周边各国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区域海洋环境共同体。例如,任何一国排放的陆源污染物都可能随着季风洋流扩散到其他国家的海岸;一国沿海红树林的砍伐可能破坏某经济鱼类的产卵地,进而导致其他南海国家渔业的减产;南海离岸珊瑚礁(offshore reefs)环境的退化会对整个南海地区的珊瑚礁以及“珊瑚大三角”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致命的影响。① Nguyen Chu Hoi,Vu Hai Dang.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Legal Obligation and Cooperation Drive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8(1),pp.23. 虽然近年来南海周边国家都开始重视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南海国家也都先后在各自管辖的南海区域开展了MPAs实践,然而,由于各国都只是从各自的海洋战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对MPAs进行管理,其养护效果也因为忽略了南海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而效果不彰,建立一个网络化的MPAs无疑是提升南海生物多样性整体养护水平的必要手段。
再次,从社会经济角度出发,根据南海整体生态特点和使用需求,通过全域统筹,构建由多类型MPAs所构成的南海MPAs网络,将有助于更好地平衡南海区域内海洋的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事实证明,与单个MPA相比,由数个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并相互连通的MPAs 组成的网络系统可以更好地满足多目标的海洋环境管理需求:不同类型、不同保护和利用水平的MPAs 在这一网络当中可以同时并存;不同海域可以因地制宜,针对不同海域采取不同的养护、管理措施。整个海域生态环境养护的成本也可以因此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公平地分担,总的社会成本也会因此降低。
二、南海MPAs 网络构建的法律基础
除了上述两个区域性合作机制外,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东盟+3”等在推动南海环境合作方面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也为南海MPAs 区域网络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合作经验。
(一)全球性公约基础
在众多全球性国际公约当中,素有海洋“宪法”之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为南海区域环境合作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国际法框架。在环境保护方面,公约第192条一般性地规定了国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第194条第5款特别强调各国应单独或联合采取一切符合公约的必要措施来保护和保全稀有或脆弱的生态系统,以及衰竭、受威胁或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和其他形式的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学者认为,此处所谓的“必要措施”,显然包括MPAs和MPAs 网络等在地养护措施。② Kristina M.Gjerde and Anna Rulska-Domino.Marine Protected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Some Practical Perspectives for Moving Ahead.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2012(27),pp.351-373. 除此以外,针对海洋内高度洄游和迁徙鱼类种群和其他海洋哺乳动物的养护,公约第61条、第63条、第66条和第67条也对南海各国在金枪鱼、海龟等物种的保护上设定了相应的国际合作义务。
(1)年龄≥18岁,<70岁;(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痔临床诊治指南》内痔诊断标准者;(3)符合2006版《肛瘘临床诊治指南》中低位单纯性肛瘘的诊断标准者;(4)无遗传性、传统性疾病者;(5)良好的依从性,签定知情同意书。
半闭海这一特殊的海洋地理条件还使得南海周边国家因此承担着特殊的海洋法公约义务。所谓半闭海首先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它们往往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所环绕,海洋区域空间的相对狭小和相对封闭,也因此沿海国无法依据《海洋法公约》的授权充分伸展本国的海洋权利。此外,相对封闭意味着此类海域的周边国家天然地形成了一个地缘海洋共同体。对于半闭海周边国家而言,共同的海洋将它们从环境、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天然地联系起来,并呈现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高度依赖关系。正因为如此,《海洋法公约》第123条特别规定了半闭海沿岸国在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区域海洋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义务。尽管由于采用了诸如“应合作”(“should cooperate”)、“应尽力”(“shall endeavor”)这样的劝导性措辞而削弱了这一合作义务的强制性,③ 撒切雅·南丹,沙卜泰·罗森主编,吕文正,毛彬译:《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注(第三卷)》,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页。 但第123条仍不失为南海各国开展MPAs 区域网络合作的重要国际法基础之一。
《海洋法公约》以外,《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及其缔约方大会(CBD/COP)有关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决议同样为南海MPAs 网络构建提供了相应的国际法基础。首先,CBD 本身包含大量与南海MPAs区域网络合作相关的法律规定。如第2条关于“保护区”、“生态系统”、“在地保护”、“易地保护”、“栖息地”、“可持续利用”等相关概念的界定,第5条关于具有“相互利益”缔约国之间开展生物多样性养护合作的规定,第8条关于保护区等在地养护措施的规定。其次,作为CBD 的治理机构,CBD/COP在审议CBD 执行情况以外,还出台了大量与生物多样性养护有关的战略目标和计划。如1995年的海洋与海岸生物多样性养护工作计划、2002年的生物多样性养护战略计划和植物养护全球战略、2004年保护区工作计划(The Programme of Work on Protected Areas)等。2010年,CBD/COP第10次大会审议通过了《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该计划提出了著名的“爱知目标”。在目标11中,缔约国承诺到2020年,要在至少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内建立起具有生态代表性的保护区系统。在上述诸多战略计划或行动当中,保护区和保护区网络在生物多样性养护和持续利用中的地位日渐凸显,保护区也逐渐从生物多样性养护的一个可选工具上升为生物多样性养护的主要手段之一。
作为南海最大的沿海国,中国较早便开始了MPAs实践。① 1994年国务院颁布《自然保护区条例》,为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1995年国家海洋局颁布《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就海洋自然保护区的选划、建设、管理和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1999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海环法》)正式将海洋自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纳入国家立法。2010年9月,国家海洋局进一步颁布《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技术规范》、《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工作规则》、《国家海洋公园评审标准》等配套技术性规范文件,为我国海洋保护区建设管理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指导和规范。 1989年,中国建立了首批五个MPAs,其中有三个位于南海地区。② 首批5个海洋保护区分别是:河北昌黎黄金海岸自然保护区、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海南大洲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海南三亚珊瑚礁自然保护区、浙江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 此后,中国陆续针对保护区、MPAs 进行了专门立法,并进一步在南海建立了若干MPAs。目前,在毗邻南海的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中国已经建立100多个国家和地方级MPAs。据统计,目前,广东省建立了97个MPAs。毗邻南海东海岸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仑河口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钦州茅尾海国家海洋公园、涠洲岛珊瑚礁国家海洋公园、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茅尾海红树林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等国家级MPAs,和若干地方性MPAs 来对海洋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物种进行保护。在南海最大岛屿——海南岛周边,海南省也已陆续划定了38个各类型的MPAs。③ 相关数据来源于《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二)区域环境合作基础
“东亚海洋环境与海岸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主要关注包括南海在内的东亚海洋和陆源污染的防治、海洋和海岸栖息地养护、海洋灾难的应对、数据收集、信息交流、国家能力建设等方面的事务。为实施这一计划,规划署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府间协调机制——东亚海洋协调机构(The Coordinating Body on the Seas of East Asia,COBSEA),由其具体负责出台阶段性战略规划,并负责协调成员间信息交换、协助成员进行能力建设、帮助成员识别并解决一些战略性海洋问题、新兴海洋问题、区域海洋空间规划、以及推动成员国开展更为紧密的区域合作等方面的具体事务。在其最新制定的行动战略中,COBSEA对《21世纪议程》第17部分做出了回应,提出在区域内推动包括MPAs和MPAs 网络在内的区域海洋空间规划,以实现区域生物多样性养护的目标。① COBSEA Strategic Directions2018-2022[EB/OL].[2019-03-27].http://www.cobsea.org/aboutcobsea/COBSEA%20Strategic%20Directions%202018-2022.pdf.
南海各国虽然至今尚未签订任何区域环保协定,但一些以项目为基础的区域环境合作仍为未来南海MPAs 区域网络的构建累积了相应的数据、技术基础和区域合作经验。这些项目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起的“东亚海洋环境与海岸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和“建设东亚海洋环境保护和管理伙伴关系”,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东盟+3”等机制下发起的区域环境合作。
前述专门性公约当中有关ABMTs 的规定为南海MPAs 区域网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选择。事实上,国内学者也已经提出过利用IMO框架内的“特殊海域”和“特别敏感海域”制度来推动南海区域环境合作的建议。⑦ 张辉:《南海环境保护引入特别区域制度研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37-40页。 当然,除IMO 下的专门机制以外,《国际捕鲸管制公约》框架下的“鲸鱼庇护区”、《东盟遗址公园宣言》(the ASEAN Declaration on Heritage Parks)下的遗址公园网络制度等同样可以为南海各国在专门领域开展区域MPAs 合作提供法律依据。
其中:Iα-1, 4和 Iα-1, 6分别代表淀粉分子中 α-1,4键(大约5.11×10-6)和α-1,6键(大约4.75×10-6)在核磁共振图谱中所代表峰的积分面积。
作为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PEMSEA 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建立区域一体化(integrated)海洋管理和伙伴关系,推动和支持东亚海岸和海洋环境保护,确保周边社区和经济的健康与活力。在过去20多年间,在PEMSEA 设定的区域海洋战略下,包括南海各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合作内容涵盖了识别和确立一体化海岸管理实施点、引入海洋污染热点地区和次区域风险管理评估制度等。② GEF/UNDP/IMO Regional Project for Marin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in East Asian Seas,Terminal Report1999:Sharing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in Marine Pollution Management( October1999),Doc.MPP-EAS/Info/99/209at4. 在2009年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马尼拉宣言》中,MPAs正式被PEMSEA 确定为实现区域综合海洋和海岸管理战略的优先手段。在东北亚、东南亚次区域层面,MPAs 网络合作也已逐步展开。2017年,在《迁徙野生动物养护公约》(《迁徙公约》)第12次缔约方大会上,菲律宾关于“推动东盟MPAs网络”的提案获得了大会通过。提案鼓励东盟各国在《迁徙公约》基础上,通过PEMSEA 构建一个有效的区域MPAs网络。然而,由于只有菲律宾加入了《迁徙公约》,而其他东盟国家和中国都未参与该公约,因此,菲律宾这一提案并未获得实质性响应。
虽然目前还没有可以直接作为构建南海MPAs 区域网络的法律依据,但一些全球性公约、现有南海区域环境合作以及南海各国国内有关MPAs 的立法和实践仍为南海MPAs 区域网络的构建奠定了相应的法律基础。
(三)国内法基础
如前所述,所谓南海MPAs区域网络,是从南海整体出发而构建的一个超越国家主权边界的网络,但究其实质,对于南海这样的半闭海而言,该网络中的多数MPAs 仍将主要由各国在本国主权管辖海域内设置。因此,南海各国国内MPAs 的立法与实践同样是南海MPAs 区域网络构建的重要法律基础。
此外,一些专门性国际公约也为南海MPAs 区域合作的实施提供了专业领域的合作指引。这些专门性国际公约主要包括《国际防止船舶污染海洋公约》及其修正案(MARPOL73/78)对船源污染的规制、《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对商业性捕鲸的规制、《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萨尔公约》)《关于重要湿地保护的规定》和《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迁徙物种公约》)等。这些公约,除从各自专业领域为缔约国设定了特定的环境保护义务以外,部分公约还引入了ABMTs制度,如MARPOL73/78下的“特别海域”和“特别敏感海域”制度,《国际捕鲸管制公约》下的“鲸鱼庇护区”制度,《拉姆萨尔公约》下的湿地保护区制度,以及《迁徙物种公约》下的全球跨境保护区网络等。这些专门性公约所提供的划区管理工具,一定程度上也为南海各国开展MPAs 区域网络建设提供了法律基础,或者说为南海各国MPAs合作提供了一种潜在选择。
作为一个群岛国家,菲律宾比中国更早开始现代意义上的MPAs实践。早在1874年,菲律宾便在其宿务省苏米龙岛建立了其第一个MPA。此后,根据菲律宾第7586号指令和菲律宾地方政府法典(The Local Government Code),菲律宾地方政府主导建设了大量MPAs。1995年,菲律宾建立了260个MPAs,到目前为止,这一数量更是剧增到了1557个,覆盖面积也达到10724平方公里,④ 邓颖颖:《菲律宾海洋保护区建设及其启示》,《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成为目前南海MPAs数量最多的国家。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同样在本国管辖的南海海域进行了MPAs实践。1997年,马来西亚在其兰卡央岛(Lankayan Island)建立起了第一个MPA。此后,根据《环境质量法》和《渔业法》,马来西亚又陆续在联盟和州两级层面上新建了若干MPAs。在众多MPAs当中,海洋公园是马来西亚MPAs中数量最多的类型。截止2012年,马来西亚已经建立了42个海洋公园。⑤ Vu Hai Dang.Marine Protected Areas Network in the South China Sea,charting a course for future cooperation.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pp.157-178. 被誉为“千岛之国”的印尼,其MPAs实践甚至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时期,当时的荷兰殖民者在印尼的帕劳建立了早期的海洋自然保留区(reserves)。上世纪70年代开始,印尼苏哈托政府建立了大量国家级MPAs 来维护印尼海洋生物多样性。苏哈托政府倒台后,印尼地方政府仍在继续MPAs建设。相对而言,位于南海东部的越南在MPAs 建设方面起步较晚,2002年,在丹麦国际开发署的支持下,越南才建立起首批三个试验性的MPAs。2010年,根据越南总理发布的742号令,越南进一步在其管辖的南海海域建立了16个MPAs,并将其视为越南沿海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⑥ 同上引。
三、南海MPAs 区域网络合作的具体路径选择
南海MPAs 区域网络合作存在三种路径:利用专门性国际公约中的ABMTs 制度建立南海MPAs网络、订立正式区域合作协定构建区域网络和通过沿海国国内立法协同构建区域网络。
3.2.1 由于电机顶部需加接口和开孔,初轧电机为对开电机罩壳,没拆卸开孔技术难题。但精轧电机中间段为不可拆卸整体结构,所以给顶部开口带来了难度,即壳体内是定转子,如氧乙炔割孔,则直接影响定转子。最后决定利用罩壳加强筋与电机筋板间四公分左右间隙铺设加湿石棉布,以遮挡氧乙炔割孔的火焰和废渣。这样,逐步铺挡、逐步切割,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利用专门性国际公约构建区域网络
另一个与南海MPAs 区域网络构建密切相关的区域机制是1994年UNEP主持建立的“东亚海洋环境管理合作伙伴”(Partnerships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or the Seas of East Asia,PEMSEA)。东亚11国均参与了该机制。在2009年东亚海洋会议第三次会议上,各国政府正式通过《认可PEMSEA 国际法人格的协定》,PEMSEA 的国际法人格者地位得以确立,这一项目导向的区域安排也正式转变为落实东亚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区域组织。
1.科技创新补贴。与单一科技创新补助金额相比,本文更加关注创新驱动政策实施后,相关地方区域性创新补贴的内在变动,扶持重点是否发生调整。因此本文在变量设计上选择了地方创新补助项目比重(Subsidy_local)、创新科技财政补助项目数量(Subsidy_item)、创新补助基准(Subsidy_item_mean)、集中度(Subsidy_item_sd)、创新科技补助金额(Subsidy_R and D)来刻画科技创新补贴的变动。
利用专门性国际公约中的ABMTs 制度构建南海MPAs 区域网络的优点是有现成的国际法依据,无需另外经历旷日持久的谈判。缺点在于,这些ABMTs 都只是从各自领域出发来思考和设计保护区,这种部门导向(sector-specific)的特点可能导致南海保护区建设的碎片化,反而不利于一个系统化的保护区网络的建构。当然,由于MPAs 网络并不要求将所有MPAs 均设计为严格保护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因此,这些专门公约机制下的ABMTs在南海MPAs 区域网络仍有用武之地。以波罗的海MPAs为例,在这一网络当中,除各国根据区域网络建设要求设立的MPAs以外,赫尔辛基环境委员会也鼓励沿海国在符合“特别敏感海域”或欧共体自然保护区网络(EC NATURE)要求的海域,可以遵照这些全球或区域要求,建立相应的MPAs,从而在一个统一的区域目标下(形成一个生态协调和有效管理的区域MPAs网络)形成了一个MPAs 的多轨构建路径。同样,在南海MPAs 区域网络构建当中,在符合区域整体养护目标的情况下,在符合“特别敏感海域”、“鲸鱼庇护区”或“遗址公园”设立条件的海域,相关南海缔约国同样可以遵照这些全球或区域ABMTs机制的要求,在相关南海区域建立起此类保护区。
每天和每周都会使用的高频率人数分别占26.32%和36.84%,也有26.32%的人表示几乎不用英语,看来航空从业人员并非人人都会用到英语。此外,他们中有71.05%的人表示最近一周在工作中使用过英语。调查结果显示,英语在工作中最主要的用途是阅读资料(42.31%),其次是与人交谈(36.54%),再是写工作邮件(13.46%),也有7.69%的人认为英语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人选择用来写作文章。通过将航务机务类人员与飞行类人员区分统计发现,对于该题,航务机务类人员英语更多用于阅读资料(47.62%),其次是与人交流(33.33%),而飞行类人员阅读资料和与人交流的需求是相等的(38.1%)。
(二)订立正式区域合作协定构建区域网络
当然,最理想的南海MPAs 区域网络应是建立正式的南海MPAs和MPAs 区域网络合作机制。在南海环境保护问题上,已经有很多学者主张借鉴地中海、波罗的海等半闭海地区的合作经验,在南海构建类似的区域合作机制。① 邓颖颖,蓝仕皇:《地中海行动计划对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启示》,《学术探索》2017年第2期,第23页。 就MPAs 区域网络而言,在一些区域一体化水平较高的闭海、半闭海地区,也的确已经出现了很多MPAs 区域网络合作机制。如东北大西洋MPAs网络、地中海MPAs 网络和波罗的海MPAs网络。构建此类有关MPAs或MPAs 网络的区域合作机制要求南海各国在海洋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养护方面达成更多共识和承诺。借鉴这些区域MPAs 网络合作的经验,一个正式的南海MPAs 区域网络合作机制,其基本要素应包括:制定一个区域环境保护框架协定,为南海MPAs 区域网络构建提供正式国际法基础;建立南海MPAs 区域网络合作专门机构,通过这一专门机构来统筹安排南海MPAs 区域网络合作,确保统一目标下各成员MPAs 实践的一致与协调;建立MPAs 实施监督机制,对成员国MPAs 的设立和管理情况进行定期审查,避免南海MPAs网络成为“纸面上的MPAs网络”。
形成正式的南海区域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固然是包括MPAs 区域网络在内的南海合作的努力方向和最终目标,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南海复杂地缘政治形势并未因为“南海仲裁案”的落幕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不仅阻碍南海区域合作的主权争议仍在,“后仲裁”时代,域外势力对南海的介入也愈发明显,这种情况下,要立刻实现南海区域环保合作的法制化和组织化显然有些不切实际。实际上,早在2008年,为落实“扭转南中国海和泰国湾环境退化”项目,中、菲、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七国就曾提出制定框架性区域环境协定的建议,最后甚至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草案文本,但最终还是因为各国政治意愿不强而作罢。② UNEP.Strategic Action Programme for the South China Sea,UNEP/GEF/SCS Technical Publication No.16,(Bangkok:UNEP,2008)[UNEP,SAP].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艰难谈判进程也充分证明了南海合作法制化的艰困。因此,尊重南海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客观现实,循序渐进、务实推进,仍是包括南海MPAs网络在内的区域合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正式制定完成之前,南海各国可尝试在COBSEA或PEMSEA 等次区域协调机制下展开MPAs 区域网络构建的前期合作。例如利用COBSEA和PEMSEA机制收集相关数据,并对一些海洋污染热点地区、海洋生态脆弱和敏感区域进行识别等。待“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正式通过后,再考虑在此框架协定基础上制定具体的MPAs 区域网络合作规则,实现机制化合作。
(三)通过沿海国国内立法协同构建区域网络
南海MPAs 区域网络合作的第三条路径是通过树立南海共同生态养护目标,并在此目标下协同沿海各国在各自主权管辖范围内MPAs 的建设和管理,进而实现南海MPAs 网络的构建。如前所述,目前的南海还不具备开展高度组织化和机制化合作的条件,因此,秉持务实合作,稳步推进南海合作的精神,在南海MPAs 区域网络构建上,南海各国可以在落实CBD“爱知目标”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东亚海洋环境保护项目等关于地区海洋环境和生态养护目标名义上,通过宣言、意向书等软法形式为南海各国设定一个共同的区域海洋生态养护目标,在此共同目标的协同下,由南海各国在本国管辖的南海海域内,依据本国法律建立和管理MPAs,从而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南海MPAs网络。这种貌似松散的合作模式有其现实的优势。首先,这种做法充分尊重了南海的客观地缘政治现实,在南海区域一体化水平发展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有利于打消各国对主权让渡的顾虑。其次,南海周边国家国内多数已经有了MPAs 实践和相关立法,也为这种事实上的区域MPAs 网络的构建奠定了现实基础。最后,可以合理预见的是,在这种过程导向型的务实合作模式下,通过持续的信息、技术和经验交流,这种事实上的网络合作也将不断深入,最终发展成为高度机制化和组织化的区域网络合作。
四、余 论
南海任何领域、任何层次的合作都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是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划界争议问题。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困扰今天多数南海合作议题推进的主要障碍,无论是南海“共同开发”还是“共同保护”,几乎都无法绕开“争议海域”的开发或保护的区域合作应如何安排的问题。对于争议海域,若双方或多方均承认对某一海域争议的存在,则“搁置争议”就有可能,问题也因此会变得相对简单,各方只需要思考如何公平、合理设计临时安排即可,此时,其更多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就南海MPAs 区域网络构建而言,在“各方均承认为有争议的海域”中的MPAs 的建设和管理,设计一种“共同建立、共同管理”的“临时安排”是完全可能的。真正困扰南海各种合作议题推进的是“争议被至少一方所否认的主张重叠海域”的处理问题,这一类海域的存在是多数南海合作的最大障碍所在。因为在各方无法就“争议”之存在达成共识之前,任何合作提议都可能被视为对己方主权立场的退让和对他方声索请求的间接承认。此类海域内MPAs 的设立和管理也必然成为南海MPAs 区域网络合作中的重难点。对于此类海域内潜在的MPAs 建设和管理需求,由南海各国各自依据本国国内法在此类海域设置“禁渔区”或“海洋保护公园”可能是目前最切实可行的做法。
Building the Regional Network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the South China Sea:Realistic Requirement,Legal Basis and Path Selection
HU Bin
(School of Law,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Abstract: Building a regional network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MPAs)is the necessary way to realize the overall maintenance of large marine ecosystem in the South China Sea.Currently,some global conventions,along with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established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area as well as some domestic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about MPAs made by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South China Sea,have laid relevant legal found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al network of MPA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pecifically,the area-based management tools in the specialize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formulating a cooperative agreement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collaboration through the domestic legalization about the MPAs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South China Sea,can be the potential paths to build the regional network of MPAs in the South China Sea.Among these,the most practical and feasible option at present is to set up a common aim for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a by means of soft law,under which the actions about MPA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an be coordinated to build the realistic regional network of MPA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Key words: the South China Sea;regional network of MPAs;large marine ecosystem
[中图分类号] D99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19)04-0009-07
[收稿日期] 2019-03-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CFX044);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海洋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海洋生态红线及生态补偿制度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 胡斌(1984-),男,湖南湘潭人,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海洋法研究。
[特约编辑:刘道远]
标签:南海论文; MPAs区域网络论文; 大型海洋生态系统论文; 重庆大学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