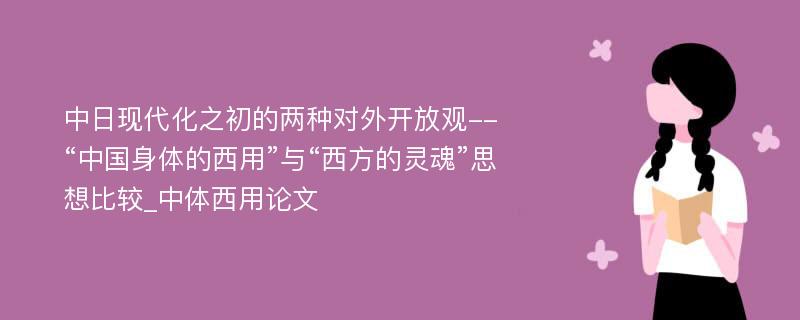
中日近代化之初的两种对外开放观——“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对外开放论文,之初论文,中日论文,中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化之初,以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为代表,曾提出过名噪一时的“中体西用”的口号,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无独有偶,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亦即日本近代化的起步阶段,也曾提出过“和魂洋才”这一颇有影响的口号。这两个口号极相类似,都反映了当时两国人们对待西方先进文明的基本态度,亦即反映了两国近代化之初的两种对外开放观。今天,我们研究两国近代史上的这两种对外开放观,对于加深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是不无裨益的。
两种对外开放观的形成
“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的形成,究其基本原因,是由于西洋文明对两国原有文明进行撞击的结果。就中国而言,作为一个闻名于世的文明古国,在西洋文明兴起之前,中国传统文明自成体系,独领风骚;就日本来说,在西洋文明尚未传入之际,一直向往的乃是中国古代文明,尤以隋唐典章制度为典范。西学东渐后,西洋文明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和日本。西洋文明属于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为物质基础的近代文明,与当时中国和日本以小生产自然经济为背景的封建传统文明相比,是一种更先进、更具活力的文明。他的传入,对中国和日本的传统文明产生了强大的撞击力,迫使人们正视现实,转变思想,抛弃旧嫌,接受西洋文明的熏陶,并进而提出学习西方的主张。“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口号的提出,就是这一过程的集中反映。这方面思想的出现,在中国是与洋务思潮的形成紧密相联的;在日本则是与幕末传统西洋观的转变分不开的。
(一)洋务思潮的形成与“中体西用”口号的提出
洋务思潮是与兴办洋务事业、发展近代经济事业等有关的思潮,它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因阶级矛盾激化而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冲击,以及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惨败,内忧外患,上下交困,正面临着“古今之奇变”。一批朝野志士仁人迫于局势变化,摒弃一向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陈习陋见,开始大谈洋务,主张学习西方,取长补短,富国强兵。如李鸿章即说:“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①,“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②,“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③。
但是,采习西学是否会将我国几千年积累的“中学”成果毁于一旦,甚至导致“以夷变夏”?人们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担心或忧虑,一些洋务思潮的反对者也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洋务运动。于是,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二者各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一问题便尖锐地摆到了洋务思潮代表者的面前。本来,洋务思潮的代表者大都是些清朝统治集团中的皇室贵族、达官权贵或地方官僚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对这些人来说,清朝基本政治制度是绝对不能改变的,封建统治的根基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必须以此为前提,或者勿宁说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根基。正是适应这一需要或在这一基本认识的指导下,“中体西用”口号应运而生,被一部分洋务思潮的代表者提了出来。
(二)传统西洋观的转变与“和魂洋才”思想的出现
日本在幕末开国前,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之中。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大致相同,当时的日本也存在着盲目骄傲,狂妄自大的思想。受中国古代有关“夷狄”思想的影响,当时的日本一般也称西洋诸国为“夷狄”,或称“戎狄”、“蛮人”、被作为信奉邪教,不知人伦,尚未开化的落后民族而予以蔑视;同时也被作为野心勃勃,欲据日本列岛为己有的侵略势力而予以敌视。蔑视和敌视,正反映了幕末开国前日本传统西洋观的基本特征。
江户中后期开始,尤其以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来航为契机,日本传统的西洋观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面对欧美军舰炮火的威胁,日本人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不得不正视当时事实上的确先进于古老东方文明的西方文明。为了抵制西洋列强的侵略,谋求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富强,人们开始认识到了解西方,研究西方以至吸取西方先进文明的必要性,于是西洋文明开始受到重视。如果说“蔑视”与“敌视”反映了幕末开国前日本传统西洋观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正视”与“重视”则可以概括为幕末开国之际及其以后已经发生变化的日本西洋观的基本特点。“和魂洋才”思想就是在这种西洋观的支配下逐渐形成的。
两种对外开放观的内容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最先对“中体西用”思想有所表述的是冯桂芬。他于1861年著《校邠庐抗议》,在其中的《采西学议》一篇中提出了采习西学,以求自强的主张。他指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这种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的论点,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表述。
之后,许多洋务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都述及这一思想,如左宗棠即说:“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逾。”④李鸿章也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⑤。“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⑥。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⑦薛福成说:“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⑧邵作舟说:“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迥然出万国之上”⑨,“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臣知纲纪法度之美,为泰西之所怀畏,而师资者必中国也。”⑩康有为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11)
除以上各说之外,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是孙家鼐。他于1896年在一个奏折中指出:“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12)
真正对“中体西用”思想作出理论概括和系统阐述的是洋务派后期首领张之洞。他于1898年著《劝学篇》,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他在《设学》一篇中说:“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他解释体用关系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心身,西学应世事”。(13)
从以上论述来看,“中体西用”思想主要包含如下一些内容:
1.中西二学相需并举,不可或缺。左宗棠强调了中西二学的并存性,认为二者虽有“虚”,“实”之分,但“各是其是,两不相逾”。李鸿章强调中西二学的互补性,认为中国既有远远高出西人之处,也有不及西人之处。康有为看到了中西二学的相互依存性和科学技术的普遍适应性,认为“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主张“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张之洞提出二者“不可偏废”。都强调了中西二学的不可缺少性。
2.中学为体,应置于根本的位置。“体”和“用”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对范畴。“体”指本体,是内在的、根本的;“用”指作用,是体的外在表现。洋务思潮的代表者大都强调“中学”应置于“体”的位置。他们所说的“中学”,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它不仅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等传统的纲常伦理道德,以及经学、史学、诸子学、典章文物等传统文化,而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所谓“文武制度”。他们认为这些中国固有的东西必须作为根本予以坚持。
3.西学为用,不能使之凌驾于中学之上。所谓西学或新学,既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成果“泰西之器”、科学技术“西艺”、自然科学“器数之学”等物质技术方面的内容,也包括“西法”、“西政”、“富强之术”等与政治、经济、军事有关的内容。在他们看来,这种西学只是“末”学,只能置于为“辅”的地位。
4.中西二学的功用与实质,从国家角度看,一在“郅治保邦”,“固其根柢”,即坚持中国原有的基本制度,巩固封建统治的基础;一在取长补短,革除弊端,以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成果、技艺方法、学术政教等来为巩固中国的封建统治服务。从个人角度讲,一在“治心身”即通过“内学”陶治人的情操,使其在立场观点、道德修养方面达到理想境界;一在“应世事”即通过“外学”培养人们适应时世、善于变通的能力,造就符合时代要求的一代新型洋务“通才”。
(二)“和魂洋才”思想的基本内容
“和魂洋才”口号的直接表述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这一命题的提出者是幕末著名思想家佐久间象山(1811-1864)。他这方面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1.肯定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强调了解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必要性。他说:“方今之世,仅知和汉之学识已断然不行,决难总括五大洲以适应大经济之发展。全世界之形势,哥伦布以穷理之力发现新世界,哥白尼发明地动之说,牛顿探明重力引力之理。三大发明以来,万般学术皆得其根基,毫无虚诞之情,悉成其实。故欧美各州面目遂改,以至有蒸气船、磁铁、电报等之创制,实夺造化之工,可愕可怖!”(14)
2.对比西洋诸国,分析本国差距,对当时日本的不足之处做出概括。他所概括的日本当时不及于西洋之处有四个方面:“其一,游民多,徒耗其财;其二,贸易、理财之道不如外蕃通达;其三,物产之学未精,山泽有遗材;其四,百工之职不知力学、器学,限于人力。”(15)这四个方面已涉及生产、流通、财政、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
3.主张知己知彼,“以夷之术防夷”。幕末不少思想家都以《孙子兵法》为依据,强调知己知彼的必要性。象山也如此,他说:“当今抵御外寇之急务,莫先于知彼;知彼之法,莫要于尽彼之术。”(16)基于这一认识,他进一步提出了“以夷之术防夷”的主张,他说:“愚意不外以夷之术以防夷。彼有大舰,我亦造大舰;彼有巨炮,我亦造巨炮。”(17)这里所强调的重点乃在军事方面,反映了近代日本学习西方的最初情形。
4.明确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象山曾赋汉诗一首,其中有“东洋道德西洋艺”(18)之句,这是他对“和魂洋才”思想所作的最简略的表述。除这一表述之外,他还对“和魂洋才”思想作过一个解释性的说明,叫做:“以汉土圣贤道德仁义之教为经,以西洋艺术诸科之学为纬。”(19)从这一说明来看,他所说的“东洋道德”指的就是汉土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亦即日本的所谓儒学。但是,他所理解的儒学,不是一种僵化守旧的陈腐之学,而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实学。他曾说过:“儒者之学以经世济民为务,学不足以经世济民,非儒也。”(20)所以,他所说的“东洋道德”,确切地说,不仅指的是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而且指的是带有日本特色亦即“日本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不仅是“日本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而且是适应当时经世致用需要亦即适应时代需要的儒家伦理道德。这是他所说的“东洋道德”的基本含义。至于所谓“西洋艺术”,从上已述及的他所肯定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具体内容,以及他所概括的日本不及于西洋的具体内容和他关于“以夷之术防夷”主张中所论及的“夷之术”的具体内容来看,这里的“艺术”应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所指的是以军事为重点,包括近代自然科学成果以及生产、流通、财政、科学技术等各方面内容在内的所有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以上可见,象山不仅明确提出了“和魂洋才”的观点,而且对其内容作了充分的表述。在当时的日本来说,具有典型的意义。
两种对外开放观的发展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
“中体西用”在中国近代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大致说来,19世纪60年代至1884年中法战争以前属于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洋务思想家们所面临的主要论敌是坚持守旧的封建顽固分子,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是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洋务思想家与封建顽固分子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顽固分子坚决反对学习西方,极力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伦纪圣道”。洋务思想家则对之予以驳斥,并反复强调“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极力表白自己无意改变中国固有的纲常名教和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亦即是在“中学为体”的前提下学习西学的。因而这一时期的“中体西用”思想既反映了洋务思想家与顽固分子的根本对立,又表明他们在这一问题上仍未与顽固分子彻底决裂。但在这一时期,“中体西用”思想总的说对顽固分子的传统保守思想是一大冲击,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1884年中法战争后,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体西用”思想发展到第二时期。这一时期,谈西学者不再被斥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因而这一时期,要不要学习西方已不再成为思想家们论争的焦点。这一时期,由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兴起并在思想领域中出现了洋务派与改良派的分野与对立,因而这一时期洋务思想家所面临的主要论敌已不是坚持守旧的顽固分子,而是主张变法维新的改良思想家。在这种情况下,“中体西用”思想已失去原有的积极意义,它的作用主要在于维护封建“圣道”,反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改革主张,对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起着抑制作用。
以上是就这一思想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的,实际上就个别人物来说,各人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的思想家对“中体西用”实际上是持批评态度的。如严复即明确反对将中、西二学分别以“体”、“用”相概括,认为事物的功用(“用”)与其存在(“体”)是一个完整和谐的统一体,中、西二学各有其体用。所说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21)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在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的问题上的不尽相同的看法,反映了中国近代化起步初期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二)“和魂洋才”思想的发展
“和魂洋才”思想虽形成于幕末,但却贯穿于日本近代化的全过程之中。除佐久间象山对之作过典型表述之外,还有一些思想家述及这一问题。
大体说来,幕末开国前后之际是“和魂洋才”思想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将“和魂”与“洋才”问题同时提出,并不片面强调哪一方面。这一时期以佐久间象山为主要代表。
明治初期大约10年左右时间,是思想家们着重强调“洋才”问题的时期。日本学者森鸥外将这一时期概括为“欧化主义”时期(22)。这一时期,明治政府大力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把革除旧弊,移入泰西文明定为国是。明治政府颁发的五条誓文中即有“破除旧来陋习”、“求知识于世界”之语(23)。于是,一时间西洋之风吹遍日本列岛,形成所谓“脱亚入欧”运动。日本近代著名文学家夏目漱石(1867-1916)在描述这一时期的特点时指出:“维新前的日本人只喜模仿支那,维新后的日本人又专一仿效西洋。”(24)
大约明治十年以后,转入批判片面强调“洋才”而忽视“和魂”的时期。森欧外概括为“对欧化主义的反对时期”(25)。这一时期不少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揭露欧化运动给明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如当时思想较为激进的幸德秋水(1871-1911)即于明治十三年(1880)发表《社会腐败的原因及其救治》一文,认为从道德上看,明治社会已“腐败堕落”(26)。另一思想家德富苏峰(1863-1957)的言词更为激烈,他于明治二十年(1887年)著《新日本之青年》,指出:“明治之世界,乃批评之世界,怀疑之世界,无信仰之世界。”他认为封建社会的道德虽“不完全”,“然社会之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尚着不完全之衣装”;而今日却“尽脱旧衣,未着新装”,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今我明治之社会,若从道德上观察,乃裸体之社会。”(27)像这样揭露当时社会问题的思想家,并不限于秋水和苏峰,据日本学者坂本多加雄说,当时思想家几乎大都具有这一“共通”特征。(28)。
以上也是就各时期思想家们在“和魂洋才”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或基本趋势而言的。实际上在各时期都或多或少有些不同观点存在。由于当时日本正处于近代化起步之初,各种问题都在探讨、摸索之中,所以在“和魂洋才”问题上必然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情形。
两种对外开放观的比较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思想,无论从其产生情况看,还是从其内容、实质与客观作用看,都既有大致相同或相似之处,又有十分明显的差异。
(一)从产生情况看:
其先,两者产生时间大致相同,但觉悟有先有后。从时间上看,两者均产生于19世纪中叶前后。具体来说,前者产生于两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刚刚兴起的19世纪60、70年代;后者产生于日本幕末开国前后(19世纪50年代)。因而从产生时间看,二者基本同时而后者略早。亦即当时的日本比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觉醒要略早一些。从绝对时间上看是如此,从相对时间上看更是如此。因为日本在幕末开国前后之际即已提出这方面的口号,亦即日本提出这方面口号与其国门的打开基本上同步的;而中国则是在国门被强行打开20余年之后才有这方面思想的出现,也就是说中国这方面思想的出现是相对滞后的。
其次,两者产生的背景大致相似,但“包袱”有重有轻。两者产生的历史背景,大致相似的表现主要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叩开两国国门,两国均负有抵制外来侵略的历史使命;两国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产生和发展,均处于近代化的起步阶段;西方科学技术、经济知识、学术思想等开始传入两国,两国原有文明受到西洋文明的猛烈撞击;两国志士仁人均在认真探讨落后挨打的原因,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与途径等。但由于两国国情不尽相同,因而两国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尤其在历史包袱方面,两国所存在的差异更大。
郭沫若曾从中日近代化失败与成功的角度,分析过两国存在的这种差异,认为两国文化传统负担不同是重要原因,即中国因前资本主义文化相当辉煌,故“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而“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日本接受西欧文化是成功了”(29)。梁启超也曾分析过中国与日本在接受外来文明上的差异,指出:“中国之受外学也,与日本异。日本小国也,且无其所固有之学。故有自他界之入者,则趋如鹜,其变如响,不转瞬而全国亦与之俱化矣。虽然,充其量不过能似人而已(实亦不能真似),终不能于所受者之外,而自有所增益,自有所创造。中国不然,中国大国也,而有数千年相传固有之学,壁垒严整,故他界之思想入之不易。虽入矣,而阅数十年百年,常不足以动其毫发。譬犹泼墨于水,其水而为经尺之孟,方丈之池也,则墨迹倏忽而遍矣;其在滔滔之江,泱泱之海,则宁易得而染之?”(29)郭沫若和梁启超在此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共同的看法,即认为两国历史包袱有重有轻,很不一样。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正是由于两国在历史包袱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而决定了两国在对西方国家的认识过程中表现出不太相同的特点。
(二)从内容上看: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都强调既要坚持本国原有传统又要学习西方,就这点而论,两者基本上是相同或相似的。同时,两者都将需要坚持的本国传统摆在优先或首要的位置,在这一点上,两者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两者在内容上也存在一些明显和重大的差异。
首先,洋务思想家所说的“中体”,如前所述,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亦即是中国封建之体。而幕末思想家所说的“和魂”,如前所述,指的则是符合经世致用需要并“日本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它所体现的内容主要在精神方面,亦即是日本民族之魂。二者一谓之“体”,一谓之“魂”,一在坚持封建性,一在强调民族性,其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洋务思想家所说的“西用”与幕末思想家所说的“洋才”,虽然所指的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但二者的侧重点却不尽相同。即前者所注重的是西方科学技术对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作用;而后者所注重的则是掌握、运用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才艺、才能。亦即一在于“用”,一在于“才”,二者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在“中西”或“和洋”关系的认识上,二者更是具有重大的差异。“中体西用”明显地将中学与西学分为“体”与“用”,亦即明显地有轻重本末之分;“和魂洋才”则只将二者分为“魂”与“才”,彼此并无厚薄轻重之别。
(三)从本质上看:
两者的根本目的大致相同,即都是为了改变本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富国强兵,实现本国国民经济近代化。两者反映的要求也大致相同,即都反映了本国朝野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与途径的心理与呼声。但在本质上,两者又有重大差异。
首先,两者的倡导者迥然有别。“中体西用”思想的倡导者主要是些洋务官僚及其代理人。这些人与清王朝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都以巩固封建统治为己任。“和魂洋才”思想的倡导者则主要是些主张改革的进步思想家和维新运动的启蒙思想家。如佐久间象山就是幕末著名进步思想家。这些人对日本旧有的封建制度持坚决批判态度,与从思想上对明治维新运动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其次,两者的出发点大不一样。“中体西用”的倡导者一开始就极力表白自己无意改变中国固有的纲常名教和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当变法维新运动掀起之后,他们又极力反对改良派的改革主张,他们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坚持封建的基本制度。“和魂洋才”的倡导者则自始自终都把革除封建弊端,实行文明开化作为基本出发点,他们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实际上强调的是制度创新、体制转轨。
因而,从本质上看,二者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一方保守性较强,消极因素较多;一方则开拓性较强,积极成分突出。
(四)从客观作用上看:
两者在两国均分别产生过重大影响,对一个历史时期和一代历史人物来说均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均在近代化之初发挥过积极功用,推进了本国近代化的展开或实现;均反映了学习西方过程中体现出的某些新的特点,即表达了学习西方思想认识的深化,促进了本国传统与西洋文明的融汇和整合等。但两者也有十分明显的差异。
首先,两者作用的范围不尽相同。“中体西用”思想的作用主要是在宏观经济领域方面,它所强调的是如何在不触动整个封建制度根基的前提下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问题。“和魂洋才”思想作用的范围,则不仅在于宏观经济领域方面,而且在于微观经济领域方面。因为它十分重视在具体的经营管理活动之中,如何做到既坚持本国原有传统又学习西方的问题,并在实践过程中提出了“土魂商才”这一适应企业经营管理需要的口号。
其次,两者作用的性质不尽相同。“中体西用”思想在批判顽固分子的守旧观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后来却愈来愈与变法维新思想相抵触,成为维新运动的障碍物。“和魂洋才”思想则在日本近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始终与维新活动相伴随,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总之,无论从哪方面看,“和魂洋才”似乎都比“中体西用”具有更多值得肯定和重视之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日本,其近代化已得到实现;在中国,其近代化则始终只停留在梦寐以求的阶段。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实用与否,其正确与实用的程度又如何,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从这一角度予以检讨,“中体西用”思想具有不及于“和魂洋才”之处,应该说是不难认知和理解的。
注释:
①《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附片》。《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9页。
②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刊本,第30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第10页。
④《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折)。《洋务运动》(五),第8页。
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第1页。
⑥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第35页。
⑦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洋务运动》(一),第49页。
⑧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戊戌变法》(一),第160页。
⑨邵作舟:《邵氏危言·译书》。《戊戌变法》(一),第183页。
⑩邵作舟:《邵氏危言·纲纪》。《戊戌变法》(一),第182页。
(11)康有为:《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4、295页。
(12)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戊戌变法》(二),第426页。
(13)此段引文除见于《劝学篇·设学》外,另见该书《循序》、《变法》。
(14)《象山全集》第5卷。参本庄荣治郎著:《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上卷),日本评论社1966年版,第232页。
(15)金子鹰之助解题:《高岛秋帆、佐久间象山集》。参藤井定义著:《幕末的经济思想》,大阪府立大学经济学部1963年版,第97-98页。
(16)《就兰日辞典出版事呈藩主建议书》,参植手通有著:《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岩波书店1974年版,第37页。
(17)《呈小寺常之助》。参同上书,第37页。
(18)参永田广志著:《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62页。
(19)《象山自笔》。参植手通有著:《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第55页。
(20)《送柽宇林先生》。参同上书,第36页。
(21)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外交报》第9期。
(22)参平川祐弘著:《和魂洋才的谱系》,河出书房新社1976年版,第24页。
(23)转引自本庄荣治郎著:《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上卷),第233页。
(24)夏目漱石:《片断》。参平川祐弘著:《和魂洋才的谱系》,第45页。
(25)参平川祐弘著:《和魂洋才的谱系》,第24页。
(26)大河内一男等编:《幸德秋水全集》,明治文献1968-1973年版,第2卷,第150页。
(27)植手通有编:《明治文学全集》第34卷《德富苏峰集》、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117、121页。
(28)坂本多加雄著:《市场、道德、秩序》,创文社1991年版,第145页。
(29)郭沫若:《中日文化的交流》。《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0、71、72页。
(30)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全集》第20册,中华书局1916年印行,第6-7页。
标签:中体西用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明治时代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西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