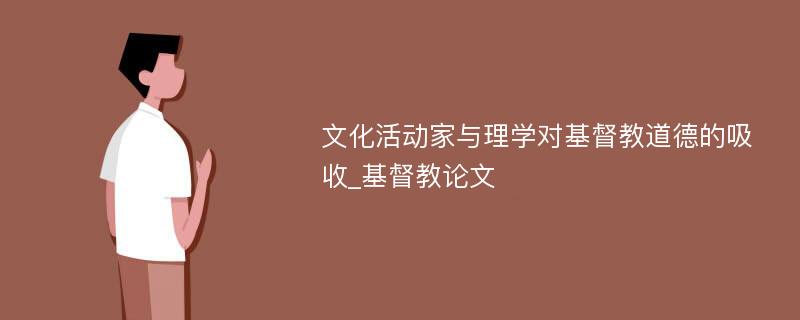
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新儒家对基督教道德的吸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基督教论文,激进论文,主义者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03-0157-08 19世纪后半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像曾国藩这样的正统士大夫的心目中,无疑产生了妖魔化基督教的作用。而20世纪头一年风起云涌的史上最大教案——义和团运动更以血腥的暴力,在国人头脑中深深地烙刻下了基督教作为“洋教”的负面形象。此后,在华基督教韬光养晦,反思自身,在风云中奋进,迎来了一段所谓黄金时期。当新青年在思想界崛起时,尽管基督教在中国仍未摆脱身上的洋教丑号,但它在新文化运动中,在中国知识界这个西方思潮多元竞起的试验场上,却成了一种供人审视乃至吸收的精神资源。 本文将选取文化思想激进派的代表人物陈独秀和稍后的现代新儒家贺麟作为分析对象,考察一下他们是如何将自己的心灵开放给基督教,并吸收基督教的伦理资源的。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说陈独秀(1879-1942)是老新青年,贺麟(1902-1992)则是新新青年,二者似有代沟。但由于贺麟在思想界出道甚早,其有关基督教的文字中最早者比陈独秀的相关篇章仅晚出4年①,可以说二者都是新文化运动运动之后不久的产物。因此,可以将二者置于同一时代语境之中,作比较分析,而不会有拉杂比附之嫌。 一、“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新文化中的伦理与基督教精神 在对新文化运动心存反感者的刻板印象中,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乃是一场鲁莽灭裂的思想文化革命,旨在颠覆中国固有的传统,以建构能满足时代需求、救亡图存的新文化。确实,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就曾多次使用“推倒”一词,以示其与传统决裂,在颠覆与觉悟中前行立新的决心。②新文化运动倡导的革命绝不只限于文学革命,还包括“伦理道德革命”。③这场革命必须首先“攻破”儒术孔道中“与近世文明决不相容者”,即“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④但这种伦理革命并非有破无立,其意欲攻破的对象是孔教,而其意欲建立者则是令其心仪的以西方近世的所谓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新国家、新社会。“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⑤ 所谓“彻底的觉悟”,即是陈独秀所说的“最后之觉悟”。稍早,陈独秀曾指出,中国众多问题的解决固然应当依赖于国人的政治觉悟,但“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⑥这里的所谓最后之觉悟,实际上是试图将西洋的独立、平等、自由等启蒙理念引入国人的精神生活之中。至此,宗教尚未被纳入到他试图建构的新文化蓝图之中。 此后,陈独秀虽然在反对国教请愿运动中出于对人类理性和科学进化的乐观信念,一度曾提出过“以科学代宗教”的说法⑦,但当他对自己极力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本身予以冷静的思考时,他对究竟什么是新文化运动、什么是新文化的具体内涵有了较为成熟的答案。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陈独秀指出:“文化的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够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很明显,宗教在此时是以积极的角色进入他的视野的。他甚至坦率承认:“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⑧从正面认宗教为人类生活活动的本源,并且为此前对这一本源的种种误解承认错误,这在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群体中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陈独秀对宗教的正面理解,虽然也带有浓厚的情感化和功能化色彩,但已深入到人性的层面。他说:“人类底行为动作……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所以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者都不应反对。”将宗教界定为发达的“人间性”的本质部分,自然便可以推导出它在新文化中的不可或缺性。因此,陈独秀断言:“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⑨ 可以看到,陈独秀的宗教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以为既然可以发现宗教的功能替代品,便可以取消宗教;稍后,他转而认为宗教乃是发达的人性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说,只要人的本能上的感情冲动一日尚存,则作为其利导者的宗教便一日不得消亡。因此,宗教不能被排除在新文化的架构之外。正是这种宗教观上的转变以及他对英雄伦理的探寻决定了陈独秀对基督教的理解和态度。 1921年,曾经主张以科学取代宗教的陈独秀发表了一篇题为《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文中力图发掘基督教中“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的“根本教义”。这是一篇很独特的文章,它在新青年中也许难以获得广泛认同,但却表达了一种对基督教伦理值得深思的态度。陈独秀究竟在基督教中发现了怎样的不可为科学家破坏的“根本教义”呢?陈独秀认为那就是“爱的教义”,是“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而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一个伟人耶稣身上。陈独秀疾呼道:“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在陈独秀对耶稣的人格化和情感化的理解中,耶稣显然只是一个历史性的伟人,是“穷人的朋友”,他的神性则从未被提及。因此,耶稣那深厚的情感便只是一种“我们更当看重”的“自然情感的冲动”和“先天的本能”。这种“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正是“中国底文化源泉里”所缺少的,中国“伦理的道义离开了情感,就是以表现情感为主的文学,也大部分离了情感,加上伦理的(尊圣、载道)、物质的(纪功、怨穷、诲淫)色彩。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在这种对耶稣的人格和情感的彰扬中,我们看到的是那种注重感性生命的现代性原则的凸显。当一些人在那里高唱什么“基督教救国论”时,陈独秀提醒道:“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底永远生命而来。”这生命自然是那摆脱了在他眼中僵化而又虚伪的伦理道义,生机勃发的、感性的、个体性的生命。在陈独秀的耶稣观里,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新青年在借他山之石来雕刻国人的性灵,塑造现代中国人的心性结构,而其中重要的底蕴便是挣脱礼教对国人的桎梏。 那么,具有启蒙情结的知识群体,如何才能将基督教教主耶稣那伟大的人格和深厚的情感,灌注到自己的血脉之中呢?陈独秀的答案与当代文化基督徒极为相似:“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仪,也不用借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他曾说:‘你求,便有人给你;你寻,便得着;你敲门,便有人为你开。’”⑩换言之,根本用不着借助于基督教的外在的宗教生活形式,只需直接去敲耶稣的门,“我们”便可以得着耶稣的人格和生命。这也许正是陈独秀极力主张区分基督教(即基督教教义)与基督教教会的原因,他认为,“博爱、牺牲自然是基督教教义中至可宝贵的成分”,至于基督教教义的其他缺点,新青年们不必“特别攻击”,矛头应该指向罪恶如山的基督教教会。(11)这也正是他在后来的非基督教和非宗教运动中警告学生不要运动群众反对一切宗教的原因之所在。(12) 陈独秀对基督教的态度,尤其是他对耶稣的理解,表明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在经过一番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性工作之后,已然切身地感受到了一种伦理的亏空,先前他们寻求到的宗教的功能替代品看来也并不令他们满意。于是,他们中的少数人便转而开始向那作为“人类活动的本源”的宗教来寻求填补这一亏空的资源。然而,陈独秀的做法一定会令基督教人士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一定会质问道:怎么能够把耶稣的人格、情感、伦理与他的信仰割裂开来?理查德·尼布尔写道:“若站在道德上而论,(耶稣的)这些神秘不可思议的英雄性的伟大人格……甚为明显地都根基于他与上帝之间独特的奉献和敬虔,及其信靠之诚挚。”(13)詹姆士·里德则说得更明确:“企图把基督的伦理与他的宗教分开是令人费解的……割断了耶稣的伦理教导同他的信仰的联系,就割断了耶稣的伦理教导并赋予他的伦理教导以意义的生命线,耶稣的目的、耶稣的服从、耶稣的力量全部都来自他对上帝的信仰。”(14)从这些教会人士的几乎异口同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坚执启蒙理念的新青年要想不触及宗教的本质部分——信仰,而试图从宗教中寻求伦理资源,其正当性一定会遭到质疑。因为在基督徒们看来,耶稣的伦理只是其对唯一至上神——上帝的信仰的果实,信仰才是其伦理与人格的根基,试图去其根而取其果,一定是本末倒置之举,无本之木与无源之水一定会萎顿枯竭。 陈独秀从人本主义伦理的角度对耶稣的人格、情感和伦理的吸取及其所赋予的意义,也许还需要做一些艰苦的理论奠基工作。换言之,他必须论证其对基督教取果去本或撷英咀华的伦理割取是合理正当的,而这在基督徒们看来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二、贺麟的新心学对基督教伦理的开放与吸收 如果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的领军人物(左翼),贺麟则是稍后开放的新儒家的一员(右翼)。尽管他是一位熔铸古今、会通中西的哲人,但他却是以新心学名家的。然而,基督教在其新心学中却具有结构性的地位,其思想倾向上的亲基督性是彰明较著的。 基督教精神被有机地纳入贺麟的新心学,在逻辑上首先借助的是他对文化问题的哲学思考。像20世纪上半叶所有反对浪言文化突破与创新、注重和珍视人类文化遗产(不论中西)的学者一样,贺麟也抱持着一种文化整体主义。(15)贺麟在借用19世纪以来大行其道的体用范畴时,通过赋予其新心学的含义而建构了一种文化哲学。在他看来,作为形而上的本体或本质的道或理,通过精神(心灵与真理的契合,或道、理活动于内心)的活动,实现或显现为文化。道是文化之本体,而精神则是文化之主体,在文化哲学中占有主要、主动、主宰的地位。文化乃是精神的产物,精神才是文化真正的体,文化是精神的显现。在贺麟新心学的文化哲学中,用为形而下之事物,体一用多。贺麟的整体主义文化哲学非常强调以下三项原则:体用不可分离割裂,体用不可颠倒,各部门文化皆有其有机统一性。同时,他还提出了从事文化批评与建设时应该遵循的三个指针:研究、介绍和采用任何部门的西洋文化,须得其体用之全;中学西学各有其整套体系,各有其体用,不可生吞活剥,割裂零售;以精神或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16) 正是在具体阐释和运用这些文化整体主义的原则和指针时,宗教问题或基督教精神,在贺麟的文化哲学体系中一再凸显其非同寻常的地位与意义。贺麟主张以上述原则和指针考察西洋文化时,多次强调作为一个部门文化的宗教(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曾游学于欧美的贺麟,在经验观察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断定,“基督教文明实为西方文明的骨干。其支配西洋人的精神生活,实深刻而周至……若非宗教精神为体,物质文明为用,绝对不会产生如此伟大灿烂的近代西洋文明”。(17)“宗教在西洋人生活中的地位,有时比科学、哲学、道德、艺术等都更重要,讨论宗教问题也可以说是讨论西洋文化的核心。”(18)在贺麟看来,基督教在西洋文化中的此种核心地位,不仅表现在它是西洋科学、民主及发达的工商业的精神支柱与终极资源,也表现在它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与陈独秀相似的是,贺麟主张将作为教会组织的基督教与基督精神区分开来,原因则在于,基督精神即为耶稣基督的人格所表现的精神,或耶教《圣经》中所包含的精义,与基督教会的组织之间实际上有极大的区别和冲突。这主要表现为,有时最能代表耶教真精神的人,反而不为耶教教会所承认,甚至遭到教会的压迫驱逐;而自命为正教的教会,以及教会中显赫的领袖,反而不能代表耶教的真精神。主张将基督教的精神与组织区分开来的贺麟认为,只有精神的耶教才是健动的创造力,它旨在追求一种神圣的、无限的、超越现实的价值。(19) 那么,在贺麟的文化哲学中,作为西方文化之骨干或核心的宗教或基督教精神,究竟所指为何?对基督教组织兴趣不大的贺麟给出的答案是:“耶教的精神可以说是一种热烈的、不妥协的对无限上帝或者超越事物的追求,借自我的根本改造以达到之。真正信仰耶教的人具有一种浪漫的仰慕态度,以追求宇宙原始之大力,而企求与上帝为一。”(20)此外,贺麟还多次谈到,基督精神即为耶稣基督的人格所表现的精神。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贺麟非常强调,耶教的精神(包括伦理)与教徒(真正信仰耶教的人)对上帝的信仰(企求与上帝为一)是不可分离的。 也许正是文化整体主义的原则,还有对西方与中国宗教的高下之分的认定,使得贺麟在建构其新心学体系时,一再严肃地提及基督教精神,并将其接纳为其新儒学的有机构成部分。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贺麟认定,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文化的危机。民族复兴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民族文化复兴的主要潮流、根本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思想是否有新开展、新前途,决定着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在无可回避的欧风美雨面前,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不能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的,而应该建立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21)在具体论及如何充实并发挥儒家思想,以求得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贺麟展示了以下途径:第一,必须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第二,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第三,须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挥儒家的诗教。换言之,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将遵循哲学化、宗教化、艺术化的途径迈进。(22) 为了不偏离本文主题,我们只对贺麟所说的第二条途径做些绍述与阐发。在贺麟看来,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和体。而其中用来磨炼意志、规范行为的礼教本来是富于宗教仪式与精神的,但失之“究竟以人伦道德为中心”。主张宗教为道德之本的贺麟认为,宗教(贺麟实际上参照的是基督教)可以为道德注以热情,鼓以勇气。宗教有精诚信仰、坚贞不二的精神,宗教有博爱慈悲、服务人类的精神,宗教有襟怀广大、超脱尘世的精神,而这一切都是基督教的精华。贺麟断定,中国人若不能接受基督教的这些精华而去其糟粕,是决不会有强有力的新儒家思想产生出来的。(23)基督教精神由此成为贺麟新儒学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贺麟发出的这种试图将基督教精神纳入当代新儒学思想中的倡导,并不只是泛泛而谈,他本人做过一些颇具跨文本诠释意义的阐发工作。例如,在谈及“仁”这个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时,贺麟认为,从宗教观点来看,仁即是救世济物、民胞物与的宗教热忱,而基督教圣经的《约翰福音》中有“上帝即是爱”之语,实际上说的就是上帝即是仁。儒家以仁为“天德”,耶教以至仁或无上的爱为上帝的本性。因此,儒家的仁是可以从宗教或基督教精神方面大加发挥的。贺麟对儒家的“诚”这一观念也作了类似的宗教化阐释。(24) 贺麟所做的以耶补儒的宗教化阐释,实际上意味着他隐晦委婉地承认了儒家在宗教维度上的不足,而这种不足之处也就是他提到过的基督教精神中的那种精诚信仰、坚贞不二、博爱慈悲、服务人类、襟怀广大、超脱尘世的精神。或许在贺麟看来,这些精神质素在儒家思想中不甚鲜明,因而需要借助于接纳基督教精神而予以发挥。贺麟的新儒学也因其力图将儒家缺少的基督教精神接纳为自身的精神质素,而对耶稣基督及其伦理表现出一种鲜明的亲和性和开放性。 科学与民主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精英追求的终极目标,作为新儒家的贺麟并不拒斥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普遍价值,他对基督教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亦给予了积极正面的阐释,并在这种阐释中彰显了他对一种很具现代性的政治伦理的探寻。他认为,基督教充满了民主精神。就历史事实而言,中古时期的基督教会固然是反民主的,但自宗教改革推翻教皇专政以来,基督教固有的民主精神就更得发展。这是因为,基督教本质上是一种没有国界的普世宗教,也不受旧家庭或家族观念的影响,主张人人皆兄弟;基督教更打破了贵族观念,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此种精神资源,大有裨益于中国人扫除其固有的封建思想,促进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基督教还有一种深厚的平民精神,主张到民间去,办学校,开医院,与平民接触,为平民服务,而这正是民主精神的精髓之表现。贺麟更认为,基督教的爱仇敌的观念,有助于培养一种宽容对方的伟大襟怀,训练公平竞争的民主政治家风度,从而大有裨益于民主政治的具体实施。因此,要了解和输入西方的民主政治,也必须了解基督教的精神。(25) 基督教的工作伦理也是贺麟甚为关切的论题。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精英就已认识到工业化对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基督教重视属灵的生活,是精神方面的,而工业化是物质方面的,基督教重精神而不重物质,故对工业化必有妨碍。贺麟自然不敢苟同于此种流俗的肤浅之说。他首先介绍了自己在美国的一些经验观察和思考: 我以前在美国,一次在一小城内登一座小山,发现两个特别触目的东西,一个是工厂的烟囱,一个就是教堂的塔尖,两者都高耸入云,挺立不移。这就给了我一个印象,觉得这两者之间,总必然有一种关系。而一个城市中如只有烟囱而没有教堂,总觉得是像缺了一面,是变态。烟囱是工业化的象征,教堂的塔尖是精神文明的象征,两者都高耸入云,代表着同一种向上的希天的精神的两方面。(26) 贺麟之所见所思,实际上即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谈到此一问题,人们自然会想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相关研究成果。韦伯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其结论可以概述为:加尔文宗的新教伦理认为,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世中唯一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诫,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的。因而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而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种荣耀上帝的特性,世俗的职业和勤奋的劳作由此获得了神圣化了的“天职”含义。此外,当加尔文宗的信徒以紧张的尘世的世俗劳作来消解内心的宗教焦虑的时候,禁欲主义与理性主义高度地结合在其内心,并且表现在其行为中,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兴起所最需要的精神质素。这是因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无非就是以对天职的责任感勤奋劳作、以和平和理性化的组织方式赚取利润。(27)换言之,在韦伯那里,新教伦理乃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因。贺麟是20世纪上半叶最早关注并输入韦伯的研究成果的学者之一,他对韦伯的绍述也相当简练和准确。(28)正是在对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贺麟得出了如下结论:宗教改革后基督教中的伦理观念,如勤劳、忠实、信用,实最适宜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社会,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基督教因其所倡导的工作伦理不是反工业化的,而是最适宜于工商业社会,并有助于工业化的,至少比佛教、道教更适宜于工业化的社会。(29)贺麟此论具有牢实的学理基础,因而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贺麟并未介绍韦伯有关儒教不适宜于资本主义产生的论述,这或许是其新儒家的立场使然。 贺麟甚至认为,基督教有助于培育国人认可的民族主义所需要的战斗与革命精神。一些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之达成,需要的是战斗的精神和革命的精神,而基督教传扬的却是谦卑的德行和奴隶式的服从,它本身就是一种与革命相对立的保守力量。对此,贺麟并不否认基督教在基督教国家因旨在保存价值、因循守旧而沦为保守的力量,但基督教传到中国这样一个文化社会境遇完全不同的国度后,实际上却成了一种生气勃勃的、进步的和革命的力量。贺麟此论可能主要是以孙中山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为历史依据的,但也有教义方面的基础,因为在贺麟心目中,耶稣基督乃是一位具有不妥协精神与生活的典范。他认为,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有助于中国的物质发展,有助于唤醒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有助于中国的改革者打破旧的习俗,鼓舞中国青年的战斗精神,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动力,它也鼓励了科学的研究和对技术的追求。贺麟甚至断言,“基督教的影响在中国的反映本质上是科学的、民主的和民族主义的”,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决不应该愚蠢地采取反基督教的敌意态度。他还乐观地预言,一旦中华民族的危机克服了,那么,基督教在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也会得到克服。(30) 三、比较与反思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界可谓百舸争流,中外各种思潮乃至宗教多元竞起。彼时的政治民主可能不尽如人意,甚至可以说令人失望,但思想市场却比较开放和自由。(31)而“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取得学术成就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开放社会与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道德与知识的基石”。(32)自由的思想市场之所以如此重要,还在于它是“偏狭与自负的最好的解毒药,有助于培育宽容开放的社会”。(33)人们也许会担心,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是否会产生劣币驱良币的效应。对此,颇为关注中国问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给出的解答是:“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也许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压抑思想市场只会招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能够培育宽容,这正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34)正是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市场中,20世纪上半叶文化思想中的激进派与守成主义(左右两翼)才可以竞相从基督教伦理中开掘他们认同的精神资源。换言之,只要有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可能,基督教的伦理资源就有彰显其价值的前景。 有趣的是,陈独秀与贺麟虽然文化立场大相径庭,但他们开掘基督教伦理资源的路径却多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主张将基督教的组织结构(教会)与精神区分开来,然后各取所需地阐释他们对基督教伦理精神的理解,并疾呼弘扬之。其原因在于,在他们看来,基督教的罪与罚都出自教会之手,背离了耶稣基督的教导。但有个问题却未进入他们的视域:如果忽视甚或灭除基督教的教会,基督教的精神将如何传承?教会外知识人的疾呼,真的能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将基督精神移植到国人的心性结构之中吗? 左翼的陈独秀与右翼的贺麟之所以能将自己的心灵开放给基督教,是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较为宏大且具有整体主义倾向的新文化蓝图或文化哲学。贺麟熔黑格尔哲学与陆王心学于一炉的新儒学,是集理学、礼教与诗教于一体的体系,其中的礼教必须包括宗教化的文化要素。换言之,贺麟对基督教伦理资源的吸收,可能是在比较视野中发现了儒家本身的缺欠(儒家伦理体系缺乏宗教的超验基础),而对儒家自身所作的补偏救弊。陈独秀早期曾主张以科学取代宗教,但随着其倡导的新文化蓝图越来越明晰和丰满成熟,宗教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其视野。而其新文化蓝图之纳入宗教这一重要因素,乃是基于他对“发达的人性”的深入洞察——宗教性是人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对基督教伦理资源的开放与吸收,可能是在经过一番破坏工作后,对由颠覆传统所造成的伦理亏空所作的补苴罅漏。饶有意味的是,1922年,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直接指导下,由尚未满周岁的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有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非基督教运动,在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35)当此之时,作为中共领导人的陈独秀却发表了《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该文虽然赞同非基督教运动,却又提出以下质疑:“从社会进化之历史观看来,自然有人类理智性日渐发展、宗教性尤其是宗教制度及宗教仪式日渐衰微的倾向。然在这进化过程中,我们若不积极的发展理智性,单是消极的扫荡宗教性,是不是有使吾人生活日趋枯燥的缺点?”(36)担心因无宗教而令生活日趋枯燥,的确略显可笑,却大有深意。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实际上是陈独秀在坚守着他早先对人性的洞察。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对刚刚创建的中共是有很大的话语权或领导权的,而当时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却对非基督教运动却发出了不和谐的质疑,这无论如何是值得深思的一段历史插曲。 此外,陈独秀与贺麟都肯定基督教服务平民、服务社会(积极办学校、开医院,对学生进行纪律与卫生训练)的平等精神。当代中国基督教或许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启发,即在可供其履行功能的领域显得相对逼窄的现状中,力所能及地履行服务社会、凝聚社会的正面功能。 当然,陈独秀与贺麟所吸收的基督教精神或伦理资源也略有不同,陈独秀从反对拘束人性的传统礼教、高扬个体感性生命的原则出发,赞美并弘扬耶稣的那种英雄式的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及其“爱的教义”“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而贺麟则更青睐于基督教精神中的那种精诚信仰、坚贞不二、博爱慈悲、服务人类、襟怀广大、超脱尘世的精神。但二者又都共同赞美耶稣基督的伟大宽恕精神。 需要注意的是,贺麟主张将基督教的精神(包括伦理)与其组织(教会)区分开来,但他坚守了基督教精神与基督徒信仰的合一整全性,认为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当然,关于他本人是否基督徒这个问题,还需要确切的有力证据才能立论。而陈独秀则置耶稣的信仰于不顾,试图舍本逐末地截取其英雄伦理,这在基督徒们看来一定是徒劳无益的。尽管社会科学家们在研究宗教时,可以标榜价值中立,因而不太顾及信徒们的感受,但陈独秀对耶稣的英雄伦理的倡导却不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所做的研究,他是在一个富矿中淘金寻宝,其割取的做法当然无法避免信徒们的质疑。 更重要的是,陈独秀与贺麟吸收基督教伦理资源的根本目标有所不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以建立一个西式的现代民主国家为归趣,而贺麟则意欲建立一个以新儒家为文化本位的现代工业化国家。 综上所述,尽管陈独秀和贺麟的文化立场迥然不同,但他们开掘基督教伦理资源的路径、所认同或赞美的基督教伦理与精神,可谓同多于异。这一现象或许表明,与其他几大世界宗教一样,基督教确实蕴藏着丰富的可供人类共享的精神资源。但是,对这些精神资源的开掘须有一前提条件,此即自由的思想市场之确立。 ①例如,贺麟的《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发表于其在清华求学期间的1925年,而陈独秀的《基督教与中国人》则发表于1921年。前者参见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46—148页;后者参见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23—528页。 ②③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④《非儒论》,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第46页。 ⑤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 ⑥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⑦陈独秀在《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一文中明确指出:“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 ⑧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⑩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 (11)陈独秀:《基督教与基督教会》,《独秀文存》,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年,659页。 (12)陈独秀:《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 (13)理查德·尼布尔:《基督与文化》,赖英泽、龚书森译,台南:东南亚神学院协会,1979年,第24页。 (14)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观》,蒋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0页。 (15)关于文化整体主义,参见本杰明·史华慈:《论五四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王跃,高力克选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4页。 (16)(18)宋志明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7—15页,第2、56页。 (17)(19)(20)贺麟:《文化与人生》,第8、129、132页。 (21)(22)(23)(24)(25)贺麟:《文化与人生》,第5—6、8—9、8—9、10—11、309页。 (26)(29)(30)贺麟:《文化与人生》,第309、310、158—161页。 (27)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66—67页、78—79页。 (28)参见贺麟所撰《物质建设与思想道德现代化》(发表于1938年)、《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两文中的相关论述,分别见贺麟:《文化与人生》,第40—42、309—310页。 (31)在科斯那里,所谓思想市场是由“演说、著述和行使宗教信仰等活动”所构成的,见R.H.Coase,“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in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64,No.2,May 1974,p.384.关于民主政治与自由思想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可参见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59—260页。 (32)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第265页。 (33)(34)科斯语,转引自冯兴元:《科斯的遗产》,《理论视野》2013年第10期。 (35)陶飞亚:《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36)陈独秀:《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标签:基督教论文; 儒家论文; 耶稣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上帝的教会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陈独秀论文; 宗教论文; 西洋论文; 新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