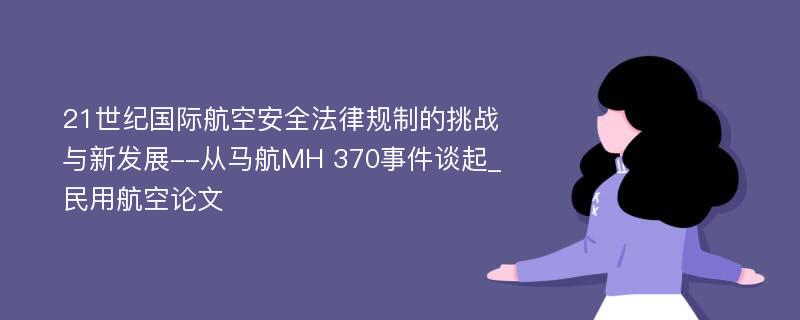
论21世纪航空安保国际法律规制面临的挑战和新发展——从马航MH370事件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保论文,新发展论文,规制论文,航空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415/j.cnki.fxpl.2014.04.015 2014年3月8日凌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200客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计划6:30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却在凌晨1:20失去联系。截至目前,仍无该飞机及机上人员的确切下落。3月24日22时,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客机在南太平洋飞行“终结”。①对于该航班失踪,至今尚无任何物理证据来证实事件的最终结果及其产生的原因。但结合“9·11”事件、埃塞俄比亚航空702航班劫机案②等国际航空实践及马来西亚政府公布的有关马航MH370事件的一些信息,我们不难发现,21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系列新兴航空犯罪,使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罪行的行为主体、手段及方式正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规制航空安保的现行国际法律规制呈现明显不足。 本文分析21世纪以来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新变化,研究现行航空安保国际法律规制及其应对新兴危害航空安全罪行存在的不足,最终为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航空安保国际法律规制的完善和发展提出建议。 一、21世纪国际航空安保面临的挑战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2006年7月第8版《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7《保安—保护国际民用航空免遭非法干扰行为》③的描述,航空安保就是指为保护民用航空免受非法干扰行为而采取的措施和使用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总和。④“非法干扰行为”是挑战国际航空安保的核心因素,制止与防范“非法干扰行为”是全球民航开展安全保卫工作的核心内容。 对于“非法干扰行为”的界定,尽管有人将非法干扰行为分为恐怖主义犯罪、可能危及飞行安全和扰乱安全飞行秩序的三大类行为。⑤也有人将非法干扰行为分为非法干扰的严重犯罪行为、严重违法或虽构成犯罪,但是一种轻微的犯罪行为、违犯机长的命令,扰乱机上秩序与纪律的行为。⑥实际上,非法干扰行为仅应指危害民用航空安全性质较严重的行为。⑦ “9·11”事件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也是一系列惨痛的航空空难事件。自“9·11”事件以来,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罪行呈现了诸多新的特征,使现行的航空安保手段、措施及法律制度面临严重的挑战。 (一)恐怖主义袭击成为了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重要手段 航空恐怖主义主要是指针对民用航空的机场、飞机、飞机上的人员和财产、航空导航设施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⑧从这个定义来看,大多数危害航空安全罪行都可以界定为恐怖主义袭击。 在“9·11”事件以前,航空恐怖主义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劫持航空器。从1930年秘鲁革命军劫获一架泛美邮运飞机并且强迫飞行员在首都利马的上空投放宣传单开始,国际社会发生了近千次的劫机既遂和未遂事件。最初的劫机主要是为了寻求公众的关注,或者将被劫持的航空器和乘客作为与政府谈判的筹码,或者仅仅是想籍以到达目的地。在这些情况下,劫机犯通常并不蓄意地伤害乘客和机组人员。但从21世纪70年代开始,劫机的动机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政治诉求劫持飞机的情况越来越多。根据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统计,仅在1977年,35.6%的劫机犯以个人利益为动机,而64.4%的行为人则出自于政治目的。⑨当然,也有寻求逃离政治迫害以及西方国家的庇护而劫持航空器的情况。如在20世纪50年代,东欧局势动荡,在1947年7月,三个罗马尼亚人劫持了一架正在飞行的Dc—3飞机到土耳其。其随后激发了14起既遂和2起未遂的劫机事件。⑩ 但这些劫持航空器的行为都有几个共同特征。首先,大多数劫持航空器的人或团伙并不期望导致航空事故,也很少蓄意伤害机组人员或乘客。劫持航空器仅仅是达成他们目的的一个手段,其目的并非是破坏航空器或伤害航空器上的人员和财产。其次,暴力或暴力相威胁是其主要行为特征。再次,大多数的劫持航空器行为发生在飞机内或使用中的飞机内,或在机场内。最后,行为主体主要是乘客或以乘客身份混入飞机内的暴力分子,几乎没有发生机组人员直接参与劫机等危害航空安全的情形。 “9·11”事件以后,航空恐怖主义行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飞机在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了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在使用,成为了民用航空安全一个重要的新威胁。(11)一方面,使用中的航空器开始成为恐怖主义的一种武器,成为了部分恐怖主义分子造成死亡、严重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害的一种工具。更有甚的是,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从事自杀式的航空恐怖活动。如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恐怖分子采用与航空器同毁的自杀式行为,航空器也同时成了其攻击美国主要建筑物的武器。 另一方面,航空恐怖主义行为并不一定表现为暴力或暴力威胁。实际上,当机组人员直接从事航空恐怖行为的时候,其手段当然不需要暴力或暴力威胁。当地面黑客通过程序直接入侵使用中的航空器系统来控制航空器的时候,其手段也不能定性为暴力或暴力相威胁。 (二)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行为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 从以往的国际民用航空实践来看,危害航空安全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机组人员以外的人。然后,北京时间2014年2月17日上午,一架原定由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往意大利罗马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班机ETH702在飞过苏丹时遭劫持,在瑞士日内瓦迫降。该航班劫机者为31岁飞机副驾驶员,并自称在趁机长上洗手间时,夺取了飞机的掌控权,他在航班降落以后,使用绳索从机窗逃出。这应该是民航史上第一起民航飞机的机长非法劫持飞机。2014年3月8日凌晨,马航MH370在从马来西亚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联。尽管尚无证据表明是机组人员劫持飞机,但是,马来西亚警方在2014年4月3日也明确排除了机上乘客参与劫机。这些新的事件不得不让我们再次审视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行为主体,包括机长在内的机组人员也有可能成为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行为主体。 此外,对于劫持航空器的极其严重的危害航空安全的行为,无论是机组人员还是乘客劫持飞机,行为主体大多是在使用中的飞机内。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脑黑客有可能侵入使用中的航空器信息系统,不知不觉中控制了飞行中的飞机从事危害航空安全活动。香港《文汇报》3月13日报道,有黑客曾在2013年示范利用智能手机遥控劫机,入侵飞机管理系统并发送虚假情报,成功改变飞机飞行路线。波音787“梦想”飞机是美国波音公司得意之作,自接受预订以来订单量不断刷新,但美国联邦航空局却对它亮起“红灯”,原因是机上电子娱乐系统存在漏洞,黑客可能通过这一系统侵入飞机控制系统,通过手中键盘操纵飞机。(12) 尽管在民航国际实践中尚未出现此类事件,但在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实践中,我们不能不考虑一种新的可能,劫持航空器的行为主体并不一定是航空器内的人员,也应该包括在航空器以外通过网络等方式控制或劫持航空器的人员。 (三)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手段呈现多样化 从国际民用航空实践及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的国际条约来看,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行为主要是劫持民用航空器,以及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中的五种行为,即对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人从事暴力行为,如该行为将会危及该航空器的安全;或破坏使用中的航空器或对该航空器造成损坏,使其不能飞行或将会危及其飞行安全;或用任何方法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放置或使别人放置一种将会破坏该航空器或对其造成损坏使其不能飞行或对其造成损坏而将会危及其飞行安全的装置或物质;或破坏或损坏航行设备或妨碍其工作,如任何此种行为将会危及飞行中航空器的安全;或传送他明知是虚假的情报,从而危及飞行中的航空器的安全。(13) 实际上,在国际民航实践中,以民用航空器作为攻击目标的地面犯罪行为也是危害航空安全的重要手段。1978年,韩国902航班在从法国巴黎飞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时,偏离航向飞往了前苏联北方舰队核动力战略导弹核潜艇的聚集之地,最后被前苏联空军苏-15战斗机拦截并击伤,最终迫降在摩尔曼斯克市郊并造成两名乘客遇难。1983年,一架从美国阿拉斯加起飞的大韩民航“波音”-747飞机,在飞往汉城途中又偏离航道飞向了堪察加半岛南部以及萨哈林岛,而这次“碰巧”又途经了苏联部署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弹道导弹基地。最终这架偏离正常航向的韩国客机被奉命起飞的苏-15战斗机击落,事后报道称,机上269名乘客全部罹难。(14)这显然是极其严重的危害航空安全行为,1983年9月15-16日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在蒙特利尔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谴责前苏联的决议。该决议宣称,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容许击落民用航空器。(15)1984年国际民航组织大会通过了对《芝加哥公约》第3条的修改:“任何国家均认知应避免对民用航空器使用武力;于空中拦截时亦应注意不危及机上人员之生命与航空器安全。”(16) “9·11”事件以后,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飞机有可能转换成为一种攻击性武器,攻击地面目标,导致大规模伤亡,如类似于“9·11”事件中的自杀式活动。此外,飞机也有可被恐怖主义分子控制用以作为喷洒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溶液的工具。也有可能恐怖主义分子将生化武器分拆后带入飞机,在飞机上合成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或爆炸性物质而直接危害国际航空安全。也有可能利用飞机运输(或)炸药、放射性材料、生化核武器以及原材料、特殊裂变材料以及辅助设备、材料等,该行为本身并不危害航空安全,但是其意图实施的犯罪却极大地威胁到人类安全。这些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罪行在21世纪的新发展直接影响国际航空安保措施与立法的发展。 二、有关航空安保的现行国际法律规制及其新发展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劫机虽时有发生但大多是零星的叛逃者所为。在60年代以后的近20年,在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了一股史无前例的政治劫机浪潮。面对越来越日益猖獗的劫机等危害航空安全的犯罪行为,国际社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加强了对劫机等危害航空安全行为的规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预防和惩治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罪的国际法律文件国际公约,并确立了相应的国际刑法原则、规则及制度。 (一)有关航空安保的现行国际法律规制 为了防范、惩治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犯罪,加强航空安全,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际民航组织先后组织召开了多次会议,订立了一系列预防、惩治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国际航空保安公约。这些公约包括1963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以下简称“《东京公约》”),(17)它第一次提出了非法劫持航空器的概念,并确认了航空器内犯罪行为的刑事管辖权;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以下简称“《海牙公约》”),(18)它专门针对劫机犯罪作了具体规定,确立了普遍管辖原则,并对劫机犯罪的追究实行“或引渡或起诉”的刑事追究原则;1971年的《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以下简称“《蒙特利尔公约》”),(19)它将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范围由“空中劫持”扩大到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既包括“飞行中”,又包括“使用中”的航空器;既包括针对航空器的非法行为,又包括针对航空设备的非法行为;1988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以下简称“《蒙特利尔议定书》”),(20)它重点打击针对国际机场的非法暴力行为;1991年的《关于注标塑性炸药以便探测的公约》,其目的在于通过责任方采取适当的方法确保这类塑性炸药的注标使其能被探测,有助于防止与塑性炸药的使用有关的非法行为。 上述国际公约对于防范和惩治危害国际航空安全行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解决了以下有关国际航空安保中的重点问题: 第一,根据《东京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及其补充议定书等国际公约的规定,危害航空安全罪一般包括非法劫持航空器罪、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以及危害民航机场安全罪三种。(21)对于“利用使用中的航空器造成死亡、严重人身伤害,或对财产或环境的严重破坏”,现行国际条约并没有明确其为国际罪行。 第二,《东京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及其补充议定书等逐步完善了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管辖问题。《东京公约》确立了航空器登记国管辖权原则,但其他国家仍可以根据国内法规定行使刑事管辖权,但只有犯罪在该国领土上具有后果,或犯罪人或受害人为该国国民或在该国有永久居所,或犯罪违反了该国有关航空器飞行或运转的现行规则或规章等情况下才可以行使管辖。(22)《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进一步明确了航空器登记国、航空器降落国、航空器承租人主营业所所在国或其永久居住国、犯罪发生国或犯罪分子所在国都具有管辖权。(23) 第三,通过《东京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及其补充议定书等确立了“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东京公约》在引渡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而是将这些问题留给有关的缔约国处理。《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都明确将劫机犯罪定为“可引渡的罪行”,确立“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并明确该原则不适用于政治犯的保护。(24) 尽管如此,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的现行有关航空安保法律制度的局限性还是比较明显。 首先,由于危害航空安全罪行行为方式的变化和发展,现行国际法律规制无法全部覆盖所有的新兴罪行或未来可能出现的犯罪形态。如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利用飞机作为武器攻击地面目标行为,以及可能出现的利用飞机喷洒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溶液,或使用生物、化学和物质对民用航空进行袭击等等,现行生效的国际条约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更为重要的是,针对自杀式的航空犯罪行为,现行国际规制对其的惩治已经不起作用,而对其组织者、资助者或支持者的惩治,现行国际规制显然不充分。 其次,现行国际航空安保法律规制确立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在国际合作实践中被弱化。尽管《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都明确确立“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并明确该原则不适用于政治犯的保护。但是,由于各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以及特定国际事件的国家利益纠葛共同影响了对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进一步导致了与“政治性目的”有关的国际劫机犯罪的司法协作困境重重。1978年的《波恩宣言》就是在此背景出台的。由于1973年国际民航组织对解决协调行动问题的失败,导致了几年以后一些国家寻求对另一种解决方法。为此,1978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七国首脑专门就劫机问题发表了宣言,目的就是惩治庇护劫机犯的国家。正是此类有关惩治航空犯罪的国际司法协助的实际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现行国际法律规制对危害航空安全行为的惩治。 最后,在国际民用航空实践中,大多危害航空安全罪行已经构成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如劫持航空器犯罪,劫持航空器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劫持人质等。在联合国框架下,通过了《制止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一方面加强了对恐怖主义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也确立了在打击恐怖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条款和保护基本人权等原则。显然,制止和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国际法律规制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法律规制应该进行关联,将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现行国际法律制度中的相关规则在制止严重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国际法律规制中予以体现。遗憾的是,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的制止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现行国际法律制度对此并没有直接规定。 (二)有关航空安保国际法律规制的新发展 为了有效制止和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罪行,国际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使现行有关航空安保的国际法律规制得到了不断完善和发展。 《东京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确立了打击劫持航空器犯罪的法律制度,但基于实践中有关劫机犯的引渡的国际司法协助的困难,1978年在七国首脑会议期间,七国首脑就劫机问题发表了《波恩宣言》,明确“在一国拒绝引渡或审判那些劫机犯或者不归还航空器的情况下,他们的政府将采取一切行动中止一切前往该国的全部航班,同时他们的政府也将采取行动中止一切来自该国的航班或者来自任何国家由有关国家航空公司排出的航班。”(25)《波恩宣言》对于促进打击劫持航空器犯罪的国际司法协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于1996年6月决定,将“国际民航界关注而现行航空公约未予涵盖的行为或行径”列入法律委员会的工作规划中,并于1997年6月成立研究小组,协助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局,强化此项工作。1999年3月研究小组建议国际民航组织针对现行航空保安公约未予涵盖的行为着手以下工作:制定法律指南或标准条款;修改附件17;修改1963年东京公约;制定一项全新的航空保安公约。 2001年9月的第33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加强了对航空安保的关注,会议通过了A33-1号《关于滥用民用航空器作为破坏性武器和涉及民用航空的其他恐怖主义行为的宣言》,宣布滥用民用航空器作为破坏性武器的行为和其他涉及民用航空或民用航空设施的恐怖行为构成违背国际法的严重犯罪,敦促所有缔约国要促使那些滥用民用航空器作为破坏性武器、包括负责计划和组织这种行为或帮助、支持或包庇凶手的人承担责任并得到严厉惩罚。次年2月在蒙特利尔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总部又召开了航空安全保卫高级别部长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288号文件发布了《乘客违规或滋扰行为法律处理指南》。该指南为进一步修订1963年《东京公约》等国际航空保安公约或者制定新的公约做了很好的准备。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7《安全保卫—国际民用航空防止非法干扰行为的安全保卫》颁布之后已经过十多次修订。特别是2010年的第十二次修改,第一次在“非法干扰行为”中增加了“毁坏使用中的航空器”和“利用使用中的航空器造成死亡、严重人身伤害,或对财产或环境的严重破坏”等内容,也第一次明确每一缔约国应制定措施,以便保护用于民用航空用途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免遭可能对民用航空和航空运输安全产生危害的干扰。(26)2014年2月26日,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在此通过对《安全保卫!国际民用航空防止非法干扰行为的安全保卫》的第14次修订,再次对应对网络威胁的安保建议进行修改。 在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无论是《关于滥用民用航空器作为破坏性武器和涉及民用航空的其他恐怖主义行为的宣言》、《乘客违规或滋扰行为法律处理指南》还是《安全保卫—国际民用航空防止非法干扰行为的安全保卫》,都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为此,为有效应对危害国际航空安保的新威胁,修改或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成为了国际民航组织近年来的重要任务。 2005年11月29日,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在其第176届会议第十二次会议上同意设立航空安保公约研究小组,协助秘书处拟定新的国际法律文件,使其涵盖对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民用航空安全罪行的惩治条款。研究小组于2006年和2007年举行了三次会议对现有公约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修订航空安保公约。201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国际民航组织在北京举行了航空安保外交会议,共有来自76个国家的代表和4个国际组织的观察员与会。大会通过了《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以下简称“《北京公约》”)和《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的补充议定书》(以下简称“《北京议定书》”)。 《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不但涵盖了《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及《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发展。 第一,《北京公约》增加了五种新兴危害航空安全的罪行,《北京议定书》及时修订了劫持航空器犯罪的定义。针对“9·11”事件后危害航空安全行为的新特征,《北京公约》将(1)以使用中的航空器为武器造成死亡、严重人身伤害、或对财产或环境的严重破坏;(2)从使用中的航空器内释放或者排放生化核武器或者其他危险物质造成或可能造成死亡、严重人身伤害、或对财产或环境的严重破坏;(3)对一使用中的航空器或在一使用中的航空器内使用生化核武器或者其他危险物质造成死亡、严重人身伤害、或对财产或环境的严重破坏;(4)在航空器上运输、导致运输或便利运输炸药、放射性材料、生化核武器以及原材料、特殊裂变材料以及辅助设备、材料等物品;(5)当情况显示做出的威胁可信时,行为人威胁实施公约规定的一种犯罪行为,或者非法和有意地造成任何人收到这种威胁等五种行为定性为危害航空安全的罪行。(27)《北京议定书》则针对网络技术可能控制使用中的飞机等新情况,将劫持航空器犯罪界定为“任何人如果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或以胁迫、或以任何其他恐吓方式,或以任何技术手段,非法地和故意地劫持或控制使用中的航空器,即构成犯罪。”(28) 第二,进一步加强对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惩治和管辖。《北京公约》首次将组织或指挥他人实施犯罪者,非法和有意协助他人逃避调查、起诉或惩罚者,以及与他人共谋实施国际航空犯罪,或者协助团伙实施犯罪等共同犯罪形式纳入了公约的制裁范围。同时,《北京公约》明确规定任何犯罪均不应当被视为政治罪,与政治罪有关的犯罪,或政治动机激发的犯罪,以排除相关国家以政治性理由对公约规定的犯罪拒绝引渡或司法互助请求。 此外,《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吸收了国际反恐怖主义公约的发展趋势,增加规定了一种强制性管辖理由和两种任择性管辖理由,为打击国际航空犯罪提供了更广泛的管辖权。(29) 第三,将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相关规则纳入了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法律制度中。《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分别增加了军事豁免权相关条款及保护基本人权等条款。(30) 尽管《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结合国际航空安保局势的新发展对《蒙特利尔公约》和《海牙公约》进行了发展,也确实有助于防止和惩治危害国际航空安保的新行为,但是,截止到2013年12月30日,《北京公约》只有8个成员国批准该条约,《北京议定书》只有7个成员国批准该条约。(31)而根据两条约的规定,两条约只有各自批准国家达到22个时才可以生效。 基于《东京公约》有关管辖权的规定在制止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的危害航空安全行为的局限性,2014年4月7日由国际民航组织100个成员国和9个国际组织和机构参加的外交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一项对1963年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的《东京公约》进行修订的议定书。(32)“此项《东京公约》的新的议定书可大幅提升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将对相关罪行的管辖权扩充至包括运营人所在国和降落地国的能力”,“同时,从此之后,该议定书明确地将法律承认和保护的范围扩充至包括机上安保员(IFSOs),这将有助于加强全球航空安保。”(33)当然,该议定书正供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签署和批准。 三、航空安保国际法律规制的完善及中国的对策 航空安保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制止和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罪行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任何单个国家都很难独自完成。因此,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的现行制止和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国际法律规制,加强国际司法协助,是确保航空安全的必要条件。 同时,中国是世界上的航空运输大国,也是航空犯罪的主要受害国之一。曾经在1993年就发生了十起劫持航空器事件。2012年6月29日,由新疆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GS7554航班被6名歹徒所劫持。这是继2008年成功挫败“3·7”机上纵火恐怖事件以来,我国发生的又一起航空安全事件。因此,在制止和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罪行中,中国应该从立法、执法及司法协助等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构建一个科学、完整的制止和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法律机制。 (一)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航空安保国际法律规制的完善 在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构建科学、有效的规制航空安保国际法律制度,架构顺畅、和谐的国际合作机制,是国际社会共同制止危害航空安全罪行,实现航空安全最为重要的基础。 首先,在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加强并推进相关国家签署和批准《北京公约》、《北京议定书》和《关于修订〈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的议定书》的进程,促成上述条约的早日生效。《北京公约》、《北京议定书》是基于“9·11”事件以后航空安保出现的新挑战,而即存的国际法律制度存在不足等背景而产生的。两条约对于“9·11”事件后出现的主要危害航空安全犯罪的新形态进行了明确的规制,加大了对相关航空犯罪的打击力度并相应扩大了对此类犯罪的管辖权。两公约应该是当前国际社会制止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维护航空安保的重要国际法基础。但两条约的批准国数量离两条约生效条件还有很大差距。(34)《关于修订〈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的议定书》则是基于《东京公约》对劫机犯罪等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管辖权的局限性而形成的,该议定书的生效将进一步便利对劫机罪等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管辖和惩治。 其次,进一步促进航空安保国际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即便是《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生效以后,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的航空安保法律制度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自身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新形态并没有完全覆盖,如航空货物运输及邮包运输中的危害航空安全罪行,从地面对民用航空器进行攻击等行为。此外,对于以航空器为武器对地面目标发动攻击等行为、劫持民用航空器进行自杀性的行为,这些航空犯罪本应界定为恐怖主义罪行,但两条约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发展新的有关航空安全的国际法律规范来解决上述问题。 最后,加强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制止和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的国际合作。当前危害航空安全的主要罪行是非法劫持航空器犯罪,而此类犯罪大多属于政治性劫机,因此,由于其政治因素,对此类危害航空安全嫌疑人的引渡大多被当事国以“政治犯不引渡”而被拒绝合作。在“政治犯不引渡”的借口下,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的国际合作面临严峻挑战。 事实上,将危害航空安全罪行排除在政治犯之外已成为国际趋势。1977年《关于制止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第1条规定:在各缔约国之间进行引渡,不得将下列任何罪行视为政治罪行或与政治罪行有关的罪行以及出于政治动机的罪行:(a)规定在1970年于海牙签订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的范围内的罪行;(b)规定在1971年于蒙特利尔签订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范围内的罪行……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在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加强对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惩治。 (二)中国的对策 中国的航空运输总周转量自2005年以来就一直在世界上排名第二位。(35)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航空运输大国。同时,中国也是危害航空安全罪行危害最大的国家之一。在打击危害航空安全的罪行中,中国一方面要就强国内航空安保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融入国际打击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国际合作中,推进国际航空安保法律规制的完善,促进国际司法合作。 作为世界上的航空运输大国,中国应积极推进国际航空安保法治体系建设。一方面,中国率先推进批准《北京公约》、《北京议定书》和《关于修订〈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的议定书》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应在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进一步推进国际社会关于制止和惩治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及邮包运输中的危害航空安全罪行、制止和惩治地面对民用航空器的攻击等新型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罪行的法律规制。 中国应加强有关规制航空安全的国内立法,以促进航空安保国际条约在国内的转化,加大对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打击力度。现行国际航空保安条约并没有对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犯罪罪名和刑罚作出规定,缔约国应当通过转化为国内法的方式来实施公约。(36)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吸收了上述规定,其第9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的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依据该项决定,对于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惩治还是应在国内刑法中予以明确。 从现行的刑法体系来看,在我国《刑法》第116、117条分别规定了破坏航空器和航空设施罪;在第121条“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直接规定了劫持航空器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刑法第123条规定了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的犯罪;刑法第125条有关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的规定;第151条有关走私武器、弹药罪与走私核材料罪等等。我国《民用航空法》第193条也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隐匿携带炸药、雷管或者其他危险品乘坐民用航空器,或者以非危险品品名托运危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但是,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与现行有关危害航空安保的国际公约的衔接是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对于打击新兴国际航空犯罪的规定也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如中国刑法第123条将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为“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但《蒙特利尔公约》规定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不仅适用于“飞行中的航空器”,还适用于“正在使用中的航空器”。我国刑法显然将《蒙特利尔公约》中的危害航空安全的对象缩小了。同时,我国刑法尚未将生化核武器有关的犯罪纳入刑法规范,因此,在我国刑法中,运输“任何对设计、制造或运载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有重大辅助作用的软件或相关技术”行为就不能被解释为制造生化核武器犯罪的预备行为,目前,这一行为在我国刑法中尚无相对应的规定。(37)此外,我国刑法对于通过地面电子干扰劫持航空器、地面攻击民用航空器、自杀式劫持民用航空器及以民用航空器为武器等新型航空犯罪的规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和发展。 注释: ①参见《背景:马航MH370航班事件回放》,available at http://world1.people.com.cn/n/2014/0325/c157278-24725477.html。 ②2014年2月17日,埃塞俄比亚航空702号班机于当地时间00:30由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起飞,原本定于当地时间04:40抵达意大利的罗马,在苏丹上空时发生了劫机事件,劫机者为该航班的副机师。最后飞机在当地时间06:00迫降于瑞士的日内瓦。参见《埃塞俄比亚航空702号班机劫机事件》,available at http://baike.baidu.com。 ③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附件是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根据《芝加哥公约》第54条所享有的职权,即“制定与航空安全、稳定性与效率相关的国际标准与建议措施及程序”而制定的国际文件,必须获得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同意,并无绝对拘束力。参见黄居正:《国际航空法的理论与实践》,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12-113页。 ④参见刁伟民:《论国际航空保安条约在中国的适用》,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⑤参见贺元骅、魏中许、许凌洁:《双流机场非法干扰行为调查分析》,载《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⑥参见李显臣:《试述非法干扰的概念和特点》,available at http:∥news.carnoc.com/list/126/126657.Html。 ⑦参见张君周:《民用航空“非法干扰行为”再探讨》,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⑧See Gerald Fitz Gerald,Aviation Terror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The Canad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87,p.221. ⑨转引自王新:《劫持航空器罪研究——以现象和概念为视野》,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1期。 ⑩See N.Aggarwala,Political Aspects of Hijacking,in N.Aggarwala,M.J.Fenello & G.F.FitzGerald,Air Hijacking: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71,pp.8-9. (11)See Doo Hwan Kim,Essays for th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Air and Space Law,Korea Studies Information Co.Ltd,2008,p.61. (12)参见《波音787 存黑客操纵隐患,网络入侵劫机更简单》,available at http://biz.xinmin.cn/chanjing/2008/01/10/1016413.html。 (13)参见《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第1条。 (14)参见《1983年苏联空军击落韩国民航747 客机内幕》,available at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902/0218_2664_1021452_1.shtml。 (15)参见陈致中编著:《国际法案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16)前注③,黄居正书,第111页。 (17)该公约于1969年12月4日生效,后于1979年2月12日对中国生效。 (18)1970年12月16日,国际民航组织在荷兰的海牙召开了国际航空法外交会议,讨论并签订了《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本公约于1971年10月14日生效。1980年9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美国政府交存了加入书,同时声明对本公约第12条第1款持有保留。 (19)1971年9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航空法外交会议上签订,1973年1月26日生效,中国于1980年9月10日加入。 (20)1988年2月24日订于蒙特利尔,1999年4月4日对中国生效。 (21)参见孙运梁:《危害航空安全犯罪的惩治及其立法完善》,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2)参见《东京公约》第3、4条。 (23)参见《海牙公约》第4条,《蒙特利尔公约》第5条。 (24)参见吴建端:《航空法学》,中国民航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7页。 (25)转引自前注瑐瑤,吴建端书,第47页。 (26)国际民航组织通过附件17—《保安》的第12次修订,available at http://www.caac.gov.cn/dev/ICAO/GZDT/201011/t20101122_36018.html。 (27)参见《北京公约》第1条。 (28)《北京议定书》第2条。 (29)参见《北京公约》第8条、《北京议定书》第7条。 (30)参见《北京公约》第11条、《北京议定书》第10条。 (31)Composite Table (Status of treaties and status of States vis-à-vis treaties),available at http://www.icao.int/Secretariat/Legal/Pages/TreatyCollection.aspx. (32)《关于修订〈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的议定书》(2014年于蒙特利尔)。 (33)国际民航组织新闻公报:《国际民航组织外交会议缔结新的处理扰乱性旅客的议定书》,available at http://www.icao.int/Meetings/AirLaw/Pages/default.aspx。 (34)根据《北京公约》第22条和《北京议定书》第23条,两公约均要求有22个缔约国的批准才能生效。 (35)参见国际在线专稿:《中国航空运输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available at http://gb.cri.cn/27824/2011/02/24/5311s3163246.htm。 (36)参见前注④,刁伟民文。 (37)参见张莉琼:《〈北京公约〉中的运输危险材料罪及其在中国的立法转化》,载《河北法学》2013年第11期。标签:民用航空论文; 中国航空论文; 北京航空论文; 马航事件论文; 法律论文; 国际法论文; mh370论文; 恐怖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