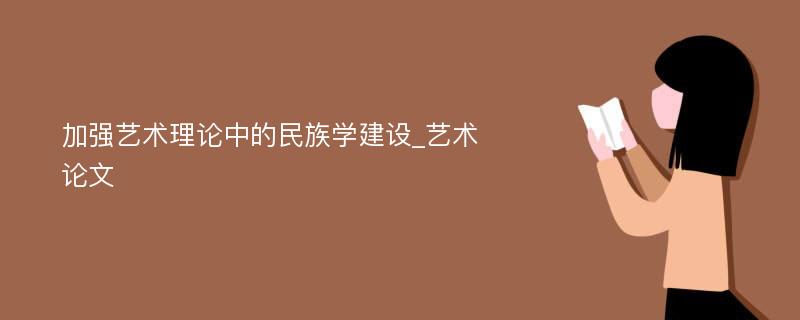
加强艺术学理论民族学理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文,民族论文,学理论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4)05-0068-04 作为一门年轻的人文理论学科,艺术学理论的建设任重道远,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来自学科内部和外部的种种挑战;既有学科自身的个性化问题,也有社会对艺术学科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人类文化发展的长效需求。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问题,就是如何加强自身民族学理的建设,从而使我国的艺术理论既能在世界艺术理论之林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能更好地服务于艺术实践和文化建设的需要。 我国很早就有从综合的文化的角度认识艺术活动的传统,它源自中国哲学的人生精神和中国文化的诗性思维。艺术、审美、生活、文化紧密相连,凸显了中国艺术理论以和谐理念、人间情怀、诗性品格等为基本特征的“大艺术”理论风貌。当前艺术学理论的建设,就亟需高度重视民族艺术理论的精神传统,在广纳中西滋养的基础上,重新打通民族审美与艺术精神的血脉,夯实艺术学理论的民族学理基石,推进建设既能与世界艺术理论对话又能切实解决自身问题的中国当代艺术理论话语和学理体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艺术学理论是一门年轻的现代学科。1906年,德国学者玛克斯·德索出版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一书,正式确立了“一般艺术学”的学科概念和研究对象,催产了一般艺术学剥离于美学的独立。1922年,俞寄凡翻译出版了日本艺术理论家黑天鹏信的《艺术学纲要》一书,书中的“艺术学”即德索所说的“一般艺术学”,由此在我国引入了“艺术学”的学科概念。20世纪20年代,宗白华撰写了《艺术学》和《艺术学(演讲)》两份讲稿,在东南大学首次开设该课程。20世纪30至40年代,张泽厚、马采的《艺术学大纲》、《从美学到一般艺术学》等论著相继问世。“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在我国初见雏形。[1-2]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我国学界积极吸纳国际艺术学独立运动的理论成果,开始了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基本的学科理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为艺术学理论在我国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建设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基础直接来自西方相关理论的输入,而不是从中国自身的艺术实践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也不是从中国艺术思想的实际中发展建构起来的。这样说,不等于否认中国艺术思想和理论资源所拥有的相关成果和特点。事实上,中国艺术思想和观念,一直以来就有广义的、综合的、文化的取向。但艺术学理论真正作为学科的自觉建设,是从1997年“艺术学”的名称正式列入国家的学科体制后才开始的。2011年,“艺术学”更名为“艺术学理论”,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因此,“艺术学理论”学科若从体制层面来说,还是一个刚刚落地不久的新生儿。当然,一门学科的建设与成长,绝不只是体制的问题,它更需要来自学科自身的长期不懈的自觉努力和科学、艰辛的理性探索。如果说,我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最初胚胎与营养来自西方,现在,我们就非常需要中西结合,获取我们自身的相关基因,打通我们自身的学理血脉,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新生儿在当下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健康地成长,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茁壮地成长。吸收一切优秀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养分,最终都要直面自己的现实,说自己的话,解决自己的问题。唯此,才能使我国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从嫁接到自生,对人类艺术实践与理论建设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艺术学理论学科在我国的孕生和确立,是20世纪中国几代艺术学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艺术学理论学科诞生的逻辑前提是现代学科界限的明晰化和独立性,但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理论方法却离不开综合与一般,离不开我国艺术实践和文化发展的实际情状。目前,我国艺术学整个学科门类大家庭中,集聚了艺术学理论以及美术学、设计学、音乐舞蹈学、戏剧影视学等五个一级学科。如果说,后四者是属于艺术学的分类研究,前者就是艺术学的一般研究、综合研究、基础研究。仲呈祥先生曾谈到,在艺术学升门过程中,学界曾有一些说法反对在中国建设一般艺术学,如“没有什么艺术学,只有具体的美术学、音乐学”,又如“外国没有艺术学”等等。他认为“一个民族统领全局的艺术学不能没有”,外国没有的中国也可以有;并指出中西艺术理论史上都有一般艺术学意义上的思想与文献[3]10。应该说,从中国艺术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实际来看,对于艺术的综合研究和一般研究源远流长,是一个比较明显和突出的特点。 从先秦始,中国艺术思想就与伦理、哲学、教育、文化等思想交揉在一起。中国艺术思想的源头,孔子、老庄的艺术思想,首先就是一种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如孔子谈的礼乐关系和美善关系,老庄谈的虚实关系和道技关系,都不仅仅是从艺术着眼,而首先是对宇宙、社会、自然、人伦问题的根本性思考。孔子十分重视艺术的道德化育功能,以仁释礼,以乐传礼。他的“乐”涵盖了诗、乐、舞等多个现代艺术样式,是一种综合性艺术活动。孔子将“乐”的审美功能、道德功能、文化功能相贯通,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有过于重视以善立美的某种偏颇,但他从美善相乐出发,强调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强调艺术的社会责任和文化功能,强调艺术审美和人性的内在关联,对于中国艺术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孔子是从个体的社会责任出发观照艺术,老庄则是从生命的自然规律出发观照艺术。与孔子从“礼”到“乐”不同,老庄是从“道”到“游”。“道”即本体,“道”在万物。“道”是有无的统一,体“道”乃是神味虚实之妙契和出入之自由。庄子赞美大美不言、得道遗技、虚静无为、心斋坐忘,追求素朴自然的逍遥至美。庄子并没有直接谈论艺术的问题,但无疑是中国艺术精神不可忽略的源头。孔庄学说构筑了中国哲学和艺术思想的根基,在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发展承续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孕育了中国艺术思想“大艺术”的独特文化品格和审美特性。孔庄之后,从汉魏经唐宋至明清,随着艺术实践的不断发展,艺术样式的日益丰富和独立,艺术思想和理论对艺术自身构成、内部要素的关注日益加强,乐论、画论、书论等各自独立,涌现了阮籍《乐论》、嵇康《声无哀乐论》等音乐理论论著,谢赫《古画品录》、石涛《画语录》等绘画理论论著,孙过庭《书谱》、张怀瓘《书断》等书法理论著作,以及计成的《园冶》、焦循的《剧说》等园林、戏曲理论论著。这些论著不仅有对音乐、绘画等世界各民族共同拥有的艺术样式的探讨,也有对书法、戏曲等极富中华民族特质的艺术样式的探讨。同时,它们在探讨艺术问题时,也大多延续了孔庄以降将艺术放在社会文化、自然宇宙的大视野中来观照的传统。如阮籍的《乐论》,就把音乐视为“天地之体,万物之性”[4]149,既讲乐有“常数”,也讲乐以“化人”,把音乐放在自然、个体、社会的大系统中。再如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提出了“意在笔前,然后作字”的创作原则,有学者认为这是“书法从单纯的文字符号”,“朝着‘人格化’方向所进行的初步转化”。[4]194中国哲学和文化强调主客、内外、出入的矛盾统一,重视自然、社会、个体的交融和谐,以生命之眼诗情之怀观照自然、宇宙、人生的生生化演,使得中国艺术理论涌现出“大音希声”、“澄怀味象”、“气韵生动”、“离形得似”等一批富有人生底蕴的理论命题和“神思”、“风骨”、“玄鉴”、“境界”、“机趣”等一批富有人生情致的理论范畴。这些命题和范畴,大都把人情、物理与艺术的形象、意趣相贯通,体现出艺术品鉴与人生品鉴相统一、真善美相贯通的大审美大艺术的理论旨趣。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谈到,“人生即是艺术”[5]20,“人人兼有艺术精神”[5]30,这是自孔庄以降中国文化和艺术的重要传统。这种传统,涵育了中国艺术与思想理论浓郁的人文情韵和文化气象,使得中国艺术理论的许多范畴和命题不是专泥于一种艺术样式,也不是仅仅局限于艺术自身。“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统”[5]82,由此,也成就了中国传统艺术和思想理论“大艺术”的重要视野与风貌。 中国艺术理论在各门类艺术间的贯通,及其艺术和人生的密切关联,都为以基础性、一般性、综合性研究为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厚实的文化根脉,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20世纪以来,我国艺术理论的建设,积极学习与引进西方,尤其是西方知识化、科学化、逻辑化的现代学术范式,但在本民族艺术理论及其精神传统的传承发展上,却一度着力不够,甚至不乏虚无失语之虞。今天,贯通中西资源,打通古今传统,在自觉的、科学的、逻辑的、系统的维度上推进学科化的艺术学理论民族学理的建设,既是我国艺术理论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下艺术学理论学科确立以后面临的迫切任务。 夯实艺术学理论的民族学理基石,推进艺术学理论的民族学理建设,是我国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面临的重大任务和现实课题。否则,学术推进、人才培养、实践引领都将无从谈起。 中国艺术理论的特点与中国文化的品格密切相联。中国文化孕育了中国艺术理论“大艺术”的气象、视野和方法,涵盖了中国艺术理论以和谐理念、人间情怀、诗性品格等为重要标识的民族元素和民族气质。 中国艺术理论具有突出的和谐理念。儒家文化追求的是人与社会的和谐,道家文化突出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和谐观也孕育了中国艺术的和谐论。如《国语》曾提出:“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4]194。和谐要求艺术在整体和部分、语言与形象、内容和形式等各种要素的组合上都能把握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4]22,这就是因为在文与质的关系上没有把握好对立统一的尺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较好地把握平衡了音乐情感不同质感表现的差别与和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艺术的和谐美并不是简单地把和谐理解为相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6]128。“和谐”是相灭相生、相反相成的辩证统一。“和谐”美揭示的是艺术中多种元素对立统一所达成的内外相谐、言意相称、形神相生、大小相应、有无相成、虚实相生的美境妙韵,是在矛盾、冲突、差异中升华的复杂美感,是艺术对事物内在规律与整体法则的深层体味。从儒道的孔庄,到现代的宗白华、丰子恺,中国艺术的和谐理想源远流长,一方面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核心理念,突出了中国艺术理论的重要旨趣;另一方面,“和谐”的理念在艺术的发展中,也面临着实践的挑战,需要解决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20世纪初,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都曾对中国艺术“悲剧”、“崇高”美感的缺失提出批评。实际上,包括“悲剧”、“崇高”、“怪诞”、“丑”等在内的现代艺术范畴,都对传统艺术“和谐”观的内涵和精神提出了发展深化的要求,需要理论工作者不断予以推进。周来祥曾针对“和谐观”的发展提出了古典素朴和谐美和现代辩证和谐美的概念,体现了理论上的一种积极探索与回应。今天,如何更好地发展提升极富民族特色的和谐美论,回应和引导艺术实践的需要,无疑是中国艺术理论应该去思考和解决的重要而现实的问题。 中国艺术理论具有温暖的人间情怀。“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5]1。中国文化的理想,既不是科学实证的,也不是宗教幻想的。中国哲人的安顿不在彼岸——天堂,而在富有艺术——审美品格的现实人生中。相对于宗教的超越,艺术的情味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中国艺术对于人生抱着温暖的情怀,能够在矛盾冲突中体味和谐,在虚寂静笃中体味生意。中国艺术活动的目的始终不是为了否弃人生,而是为了在自然、宇宙、个体、社会的审美观照中,更好地实现“生活的艺术化”和“人生的艺术化”。这就是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也是庄子“物我两忘”而“道通为一”的逍遥,是一种情感的深沉与超拔,是一种生命的温情与坚守,也是一种心灵的虚静与高逸。中国的艺术理论,谈着谈着,就会逸出艺术而潜入生命与生活,把人格情怀、生命情调、时空意识、宇宙精神都涵入了自己的观照中。观画、品字、赏乐,无一不着人不著情。中国艺术理论,有“小艺术”和“大艺术”之说,“美术家”和“美术人”之喻,前者更多是从艺术的技能角度着眼,后者则涵摄了审美化的生活和艺术化的人。把生活涵成“大艺术品”,这是中国艺术理想的最高境界,由此,在对艺术性、艺术精神、艺术美的理解上也体现出相应的旨趣,在生活、人生、艺术的实践中呈现出相应的态度。中国艺术理论的人间情怀,在根子上就是真善美相贯通的审美旨趣和人生情致。所以,中国的艺术理论不会拘泥于为美而美,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体现出生命的慧眼、开放的胸襟、人文的情韵。当然,这不等于把中国艺术理论视为玄学。中国历代的艺术理论,都不乏科学的理性的逻辑的元素,不乏对于艺术技巧技能的精到认知,不乏对于各门类艺术的精深研究。如战国时期的《乐记》,就从音乐的本质谈起,较为系统地论析了音乐的情感、形式、作用、教育诸方面的问题。更遑论《文心雕龙》、《艺概》等鸿篇。实际上,科学精神和人间情怀并不是也不应成为对立的因素,这也正是西方现代性发展中需要反思的重要问题。今天,我们应该将艺术理论的科学品格与人间情怀相贯通,吸纳中西艺术理论在思维方法、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各自优长,结合当下艺术实践与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予以发展推进。 中国艺术理论具有内在的诗性品格。“大艺术”的追求使得中国艺术理论非常关注艺术活动的诗性品格和超越精神,这种由艺术的具象通向精神的诗意的形上旨趣,可以追溯到老庄哲学以及儒家的有关学说。老子建构了“道”的最高哲学范畴。“道”是化生万物的本体,“道”又与万物同在。“道”是有,“道”是无,“道”是自然。体“道”乃美,既是对形下的体认,也是对形上的妙悟。可以说,老子的至美是有无虚实相生相成的美,体现出崇无尚虚的审美旨趣。庄子进一步发展丰富了老子的思想,他以大量生动的例证,精到地阐析了“唯道集虚”的哲学观和审美理念。“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万物之理和至美“道通为一”。除了老庄,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实际上也内蕴着形上之气质。儒家文化最核心的精神是生生的精神,也就是生命的精神。“道”也好,“生”也好,归根结底追问的都是人对宇宙的根源感。儒家由“生”到“仁”,强调生命之爱,追求“大生”与“广生”,从而由“器”达“道”,乐天知命。由物、器、道之间的关系,儒道两家都进而讨论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并不约而同地把意视为高于言和象的存在,主张言不尽意、立象尽意、大象无形、得意忘言,从而把审美的目光和旨趣导向了形上之维,并与实存的生活产生了亦实亦虚的诗性张力。中国艺术理论的诗性品格使其孕育了包括趣、境、韵、妙、气、品等在内的一系列即实即虚、富有延展性的民族化范畴。它们往往不是对艺术形象的某种具体技法的总结,而是对其整体性特征和诗意性情致的品鉴,并且往往由艺术而人生,把审美的目光和情怀引向更为超旷高远的天地,重视以艺术的美境高趣来引领人格的提升和人性的化育。在技与道、象与意、形与神等诸对关系中侧重后者,强调艺术创作者不是艺匠而是艺术家,重视他们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的引领意义。如宗白华的“意境”论,勾勒了艺术意境由直观感相到活跃生命到最高灵境,也即从情到气到格,从写实到传神到妙悟的美感路径,从而昭示了每一个具体的生命都可以通向最高的“天地诗心”和“宇宙诗心”的自由诗意。这不仅是对中国艺术诗性精神的深刻体悟,也是对诗意的艺术人格和诗性的艺术人生的形象标举。中国艺术理论的这种诗意取向,使得理论本身呈现出感性与理性统一、经验与超验融通的整体性特征,同时也突出了艺术对于生活的张力纬度和超拔意义。这种理论方法和价值取向,对于现代社会理性务实的文化特性具有突出的针对性,切入了个体生命存在的某种根基。中国艺术理论在这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资源和自己的优长,需要我们结合当代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予以梳理发展。 中国艺术理论的和谐理念、人间情怀、诗性品格,渊源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传统,构成了与西方艺术理论认识论方法、思辨性特征、科学化品格相区别的民族化标识,并以其“大艺术”的理论气象和方法视野,凸显了独特的理论品格和突出的人文意蕴。 20世纪以来,学术文化领域漫延盛行的唯西是瞻、以西观中的立场方法,给民族学术文化的传承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戕害。今天,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民族理论资源及其精神传统的梳理发掘和丰富推进。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先需各美其美,再则美美与共。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艺术理论学科建设,既不失现代的大气开放和国际视野,又不失自身的民族血脉与民族根基,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中实现与世界艺术理论的对话与共同发展,并能面对当下丰富多元快速发展的艺术现实予以切实而有针对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