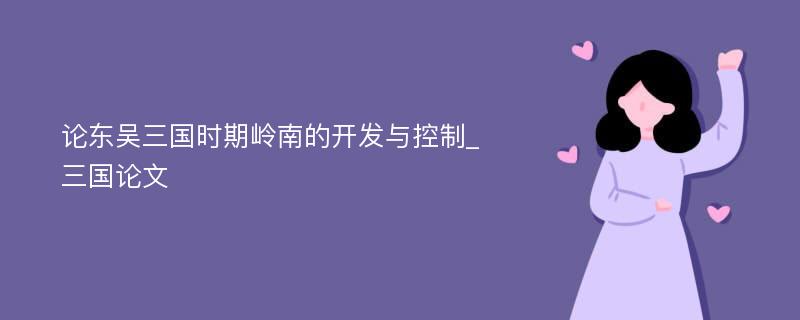
试论三国时期东吴对岭南的开发与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吴论文,岭南论文,试论论文,三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岭南(辖境相当于今五岭以南的两广、海南岛及越南北、中部地区)自古以来为我国百越族居住地。秦开五岭,岭南始被纳入中原统一王朝的版图。然而因其地僻居南方一隅,且有山林阻险,故长期以来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素有“蛮荒瘴疠”、“化外绝域”之称。经过秦汉王朝的大规模经营,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初见成效,但仍然明显落后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水平。三国鼎立,东吴割据江东,岭南位居大后方,对东吴政权的稳固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岭南辽阔的土地、丰富的物产,以及众多的人口(指土著和移民),又成为东吴统治者财赋和兵员的来源地。因此,东吴统治者重视对岭南的开发和治理。本文不揣固陋,拟就此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东吴治理与开发岭南的前提条件
汉末,中原大乱,岭南也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因此,东吴要治理与开发岭南,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其中东吴对岭南统治地位的确立(包括岭南归附后稳定局面的形成),汉末三国时期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等,是这一时期东吴治理与开发岭南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1)东吴在岭南统治地位的确立
东吴立国江东,据有江东的东吴政权,必须向西占领荆州,向南夺取交州(即岭南地区),才有可能站稳脚跟,长治江南。赤壁之战后,随着曹魏所属长江以南的荆州失地最终为孙吴所得,来自西面的忧虑基本解除,于是南下攻取交州,就成为东吴执政者的当务之急。
汉末,因中原丧乱,远离中原王朝的岭南地区逐渐摆脱东汉朝廷的统治割据自雄。当时,北方曹操、荆州刘表及江东孙权等都想为扩大地盘增强与对方抗衡的实力而争夺岭南。在岭南,恰逢交州刺史朱符因侵刻百姓过甚而为当地豪酋所杀,此事遂成为汉末各方军阀争夺岭南统治权的契机。出身岭南官宦世家的苍梧广信人士燮,利用“近水楼台”之便,抢先据有交州,并自署为交趾太守,同时表请诸弟分领合浦、九真和南海三郡太守。于是岭南很快成为士氏家族控制的地盘。然而,早已觊觎这块土地的曹、刘、孙三方并不肯罢休,其中最先将手掌伸进岭南的是曹操。他在朱符死后不久,即派亲信张津出任交州刺史,张津为部将所杀后,荆州牧刘表紧接着又派心腹赖恭和吴巨分领州刺史和苍梧太守。见此情形,曹操随即又假借朝廷名义,任命士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事,以便与刘表势力相抗衡。由于岭南对东吴江左政权的安危存在着极大的祸福关系,因此,东吴在战略上收服岭南更为迫切。因而就在曹、刘等势力先后插足岭南之际,东吴也于建安十五年(210 年)派大将步骘为交州刺史,率兵夺取交州。步骘到任,首先出奇不意袭杀吴巨,夺得苍梧郡,一时“威声大震”,称雄交州的士燮兄弟迫于形势,“相率供命”。接着,步骘又乘胜追歼了曹、刘等残余势力,“南土之宾,自此始”。(注:《三国志·吴书·步骘传》。)
岭南归附东吴后,汉末以来形成的士氏家族操纵当地局势的状况并无多大改变。史称士氏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佗)不足逾也。”(注:《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这种类似于汉初赵佗南越国的割据政权,东吴统治者显然不会容忍它长期存在下去。黄武五年(226年), 东吴趁士燮去世之际,派吕岱代士燮为交趾太守,而令士燮子士徽任九真太守,以此削弱和打击士氏家族的势力。在遭到士氏家兵的抵抗后,吕岱率所部绕道从海上突然发起进攻,士徽兄弟手足无措,连同余党全部被杀。这样,从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到吴黄武年间,东吴经过近20 年的苦心经营,至此终于全面控制了岭南。从而为东吴日后治理与开发岭南提供了一个较稳定的政治环境。
(2)汉末至三国时期北人的南迁及规模
封建社会中,人口数量往往是制约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岭南地广人稀,劳动力资源不足,加之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落后,是导致岭南经济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岭南归属于中央王朝之后,北方人口的南迁也随之开始,并由此揭开了岭南开发史的序幕。秦汉时期政府大规模移民活动前人多已论述,在此不赘。这里仅谈汉末三国时的情况。汉末,军阀混战,战乱迭起,继黄河流域之后,长江流域接着沦为战场。相形之下,岭南地区僻居南方一隅,且有南岭山脉为屏障,战乱波及较少;加之这里幅员广阔,人口稀少,又有不少荒田可供开垦,于是这里成为当时人们逃难、避役和谋生的好去处。故在汉末以来大批南渡避乱的北人中,有不少越岭或经海道南下到达岭南者。如汝南南顿人程秉、沛郡竹邑人薛综,就是在这时避乱交州的。(注:《三国志·吴书·程秉传》、《薛综传》。)另据《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记载:“是时(汉末)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时居桂阳)居者以百数。”又汉末雄居岭南诸郡的士燮兄弟,因“体器宽厚,谦虚下士”,故“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注:《三国志·吴书·士燮传》。)类似记载,不胜枚举。三国初,孙氏政权在江南统治尚未稳固,曹丕率十余万魏兵驻广陵(今扬州),临江观阵,有渡江之志。(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录》。)江东人心惶惶,其土著和侨民纷纷南下迁入岭南。如汝南人袁忠,沛郡人桓晔原已渡江定居会稽,因恐战乱及身,于是“浮海南投交趾”。(注:《后汉书·桓荣传后附桓晔传》、《袁安传附玄孙袁忠传》。)故吴初流入岭南的人口骤增,从而出现了汉末三国初第一次内地人民自发向岭南迁徙的高潮。
汉末至三国百余年间迁居岭南的人口总数,据有关学者统计,大致为778474人,约占东汉岭南人口总数的60%(注:参见刘希为、刘磐修:“六朝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 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除去当地诸蛮族人口自然增殖这一因素外,大体可看出这一时期北方人口的迁徙规模。
总之,汉末三国百余年间,由于中原及内地人民的不断南迁,不仅为岭南地区输入了大批劳动力,而且南迁人民为岭南带去了北方和内地先进的铁、犁等农耕器具和生产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这就为东吴治理与开发岭南做好了较充分的人力与物力上的准备。
二、东吴政权治理和开发岭南的措施
岭南归附于东吴后,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与东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为了加快岭南的治理和开发,以便维护和巩固东吴的统治秩序,东吴统治者对此采取了以下有效措施:
(1)地方行政机构——州郡县的增设与调整
在东吴收服岭南以前,岭南地方行政组织维持着东汉以来“一州七郡”的状态。然而随着汉末以来迄三国初岭北人民的大量迁入,岭南诸郡户口数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使得原有政区的设置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黄武五年(226年),吴大帝孙权遂将交州析分为交、广二州, 将交趾以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归交州管辖,合浦以北的郁林、苍梧、南海、高凉四郡归广州管辖。但因当时时机尚不够成熟,故增设广州一事不久即废。 (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到吴景帝孙休永安七年(264年),随着岭南政局的日趋稳定,于是全面恢复了黄武五年(226年)的建制。而且在增置广州期间,东吴还先后增设了临贺、桂林、始安、始兴、高凉、高兴、宁浦、珠崖等八郡。末帝孙皓时,又在交州新设新昌、武平、九德三郡。这样,终吴之世,广州领有苍梧、郁林、南海、高兴、宁浦、南凉、桂林等七郡;交州领有交趾、合浦、珠崖、九真、日南、新昌、九德、武平等八郡。从而结束了东汉以来“大交州七郡”状态;开创了“广州七郡”、“交州八郡”的新格局。这种新格局的开创,对于边远落后的岭南地区来说,意义尤为重大。这是因为,其一,两汉岭南东部地区本无州,郡县设置也比较稀疏,自东吴开始首置广州,并增置七郡,不仅使岭南地区的郡县分布更趋合理,而且为日后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二,州郡数量的迅速增加,不只是表明东吴统治势力较前代更深入岭南,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汉末至三国时期岭南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改变了昔日岭南“地旷人稀”的旧貌,密切了岭南与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所有以上这些,都将为岭南地区经济的开发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2)水陆交通的开辟 历史上岭南地区经济发展缓慢, 与五岭山区道路阻塞有直接关系。故开发岭南,疏通交通,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关键。先看陆路交通。早在秦汉时,曾对岭南交通有过几次大的开发,诸如灵渠的开凿,峤岭的开通(指零陵、桂阳峤道)、疏通六泷(今广东北部武水自坪石至乐昌一段)等。此后五岭中的越城岭、骑田岭和都庞岭相继凿通。(注:参见李绪柏:“两汉时期的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3期。 )东吴开发岭南山区的交通设施虽未见史书记载,但因东吴建都建业(今南京),自吴永安年间实行交、广分置后,广州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很快取代交趾成为岭南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于是位于五岭东端的大庚岭路逐渐成为连接都城建业和广州番禺的最近路程。从建业沿长江西上至江州,尔后逆赣水而上越过大庾岭至始兴城,再乘船浮水顺流南下至番禺,道路畅通无阻。于是大庾岭路遂成为东吴连接岭南最重要的交通纽带。另外,三国时荆州武昌,是东吴除都城建业外又一政治、经济中心。由于它与广州番禺政治经济交往密切,于是地处要冲的桂阳道骑田岭继秦汉之后,成为东吴时沟通荆、广区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注:参见刘希为、刘磐修:“六朝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水路交通。早在汉代,粤东沿海已初步得到开辟,但因秦汉王朝立足中原,海上优势难以发挥,故直到三国东吴统治时期,粤东海道航线才得到充分发展。如东吴对交州和广州的海上用兵,以及汉末北方避难民众多经此路到达岭南。粤东海道在汉代因种种原因未能成为商业航线,但进一步开辟此航线借以发展粤东经济,到东吴统治时已是当务之急。东吴增置广州,可视为这一举措的开端。另外,公元3世纪后, 由于林邑国日渐强盛,东吴所属的九真、交趾二郡相继遭受侵害,南海诸国往来船只多改道海南岛东岸抵达番禺。此后,随着广州的兴起,以及海上交通线的改变,最终促成粤东航线的进一步开辟。
(3)招抚诸夷,保境安民 三国时, 岭南境内居住着众多的百越系统的少数民族,如所谓“群蛮”、“七郡百蛮”、“交趾、九真夷”及“俚”、“僚”和“乌浒”等。他们大都栖居溪洞深谷,“负险不宾”,而且经常四处骚扰边郡。对此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岭南地区社会稳定与经济开发等大局。对此,东吴统治者在总结前代治理岭南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了以抚为主,镇抚并用的政策。其次是重视地方官的人选,凡为官贪暴者皆不得任用,由此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赤乌五年(242年),高凉渠帅仍弩等劫略百姓,残害吏民, 南海太守钟离牧奉命“越界扑讨”,“旬日降服”。(注:《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又延康元年(220年),吕岱任交州刺史时, 郁林郡所辖的桂阳、浈阳二县发生一起盗贼合众在南海郡界作乱之事,孙权诏吕岱率兵讨之。(注:《三国志·吴书·吕岱传》。)在对上述无端生事的蛮夷诉诸武力的同时,东吴统治者还注意用招抚、怀柔的办法招降纳叛,以便“绥和百越”,保境安民。如吕岱接任交州刺史时,有高凉贼帅钱博乞降,吕岱奉朝命,“以博为高凉西部都尉”(注:《三国志·吴书·吕岱传》。)。又比如,赤乌十一年(248),交趾、 九真夷攻陷附近城邑,引起“交州骚动”,孙权命陆胤为交州刺史兼安南校尉,前往招抚。陆胤抵州,对乱民“喻以恩信”,并“务崇招纳”,在他悉心安抚下,高凉渠帅黄吴等余党三千余家“皆出降”。接着,陆胤又引兵南下,“重宣至诚”,并“遗以财币”,于是“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注:《三国志·吴书·陆胤传》。)全都甘愿俯首听命。这种以招抚为主,结恩信于土人的做法,在当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史称陆胤治交州十余年间,“海隅肃清”、“商旅平行”、“交域清泰”(注:《三国志·吴书·陆胤传》。),就是很好的例证。
(4)编制户籍,安辑流亡 岭南入吴后, 为了维护和巩固已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同时也为了方便当地政府收取赋税和征兵,东吴在招抚诸夷、保境安民的同时,还对岭南境内大量避难和谋生的汉族流民进行招抚和安置。如赤乌年间,陆胤任交州刺史,曾“奉宣朝恩”、“招合遗散”。(注:《三国志·吴书·陆胤传》。)又吴初,全柔任桂阳太守时,其子全琮因对避乱南迁的中原流民竭力安抚,并且在生活上“倾家给济,与共有无”(注:《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而深得当时舆论的称赞。
东吴统治者招抚流亡的工作,对安定社会,以及组织人力从事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事业等无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不容否认,作为地主政权,东吴政府安置流民的目的,主要还在于将流亡人口重新编入户籍,以便为封建国家纳税和服兵役。为此,对于那些归降的诸蛮夷,也采取了同样办法。如东吴初置广州时,曾将受降的溪洞越人如高凉县钱博部、仍弩部、黄吴部及浈阳县王金部等数千户编入所在郡县户籍中(注:参见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注。)。又赤乌五年(242年),东吴攻下儋耳、珠崖二郡之后,随即恢复其建制,所得民户自不在少数。这些被编入政府户籍的诸蛮夷,固然使他们重新受到封建剥削与奴役,但因他们在入籍后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与汉人杂处,共同从事农业生产,这对于加快他们自身的封建化进程,促进民族融合,客观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劝课农桑,发展生产
岭南地区虽经秦汉时期大规模的开发,但直到东吴统治岭南之初,当地经济仍显得十分落后。为鼓励岭南各族人民从事农业生产,东吴政府采取了有别于江南腹地的赋税政策。所征赋税不以田租、而是以缴纳地方特产的形式充作租税。如岭南臣服东吴后,交趾太守士燮每年派贡使送给孙权的贡物主要是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翡翠、犀角、象牙等珍宝,还有香蕉、龙眼等异果。(注:《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这种不征田租而取土贡的收税办法,乃是从岭南地区特殊情况,如境内多山地丘陵,可耕地面积小等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有助于提高当地各族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东吴不收田租只取贡赋的政策,主要是在岭南初附时期,以及在那些越人居住较集中的边远山区,至于开发较早的平坝及三角洲,仍就按内地办法收取田租,只是赋税较轻而已。一些地方官在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时,也做了一些有益之事,如陆胤在任交州刺史期间,曾率领人民修筑蓄水池陂,“民得甘食”。不仅改善了当地人们的饮水条件,而且灌溉了农田。此外,他还以身作则,布德人民,因而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史称他“衔命在州(交州)十有余年”,“惠风横被”,“民无疾疫,田稼丰稔”。(注:《三国志·吴书·陆胤传》。)剔去浮辞,多少反映出当时岭南地区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的景象。
(6)城廓的修筑 封建社会,地方行政的治所州郡县城, 既为一方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也是某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开辟点,故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为治理与开发岭南,东吴在对岭南地方行政机构增设与调整的同时,还对各级地方行署所在地的城镇县邑加以兴建或扩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广州治所番禺城的兴建。史载,建安十五年(210 年),东吴将领步骘在攻取交州后,即挥师南下进驻番禺。经过对番禺故城一番“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的考察后,认为此城地处“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注:《水经注·泿水》。)于是派人平整了番山之北的土丘,并拆毁赵佗时所建“佗城”,另筑新城。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广州番禺城。步骘所筑番禺城的形制与规模,由于史料缺乏,难以窥见其全貌,只能从某些间接史料中得拾一鳞半爪。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步骘所修筑的广州番禺城,位置“在今县(番禺县)西南二里。”又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引《续南越志》也载:“其城(番禺城)周十里,尉佗筑,步骘修之,晚为黄巢所焚。”据此可知赵佗最初所建的佗城,城廓周长或面积为10里,步骘所筑城既然是在其故址上重建或扩建,其规模自当超过或相当于前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温水》中记载了与岭南地区自然条件相似、文化同源的林邑国城廓建筑情况,其中提到其城“周周八里一百步,……城内小域,周围三百二十步”。相比之下,番禺城若按方圆10里计算,规模不算小了。它能保存到唐末已相当不容易,从中可以想见番禺城在设计与建造水平之高超。除此而外,如上文所述,东吴治理岭南期间曾增设许多郡县,而每一郡县的设置,相应地要修建规模不等的城廓作为治所。这样终吴之世,随着郡县的不断增设,城廓建筑也在不断修建中。如始兴城(今广东韶关),东汉时在此设曲江县,因其地“控扼五岭”,且为“交、广之咽喉”,(注:《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韶州府》引宋余靖《州衙记》。)战略位置重要,故吴后主孙皓甘露元年(265年), 特意将它从桂阳郡分出,另设始兴郡,并随之修建了始兴城。此后经过历代的续建,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五岭山区一个中心城市。
三、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及影响
在秦汉开发岭南的基础上,东吴经过长达70年(210—280)的治理与开发,岭南社会经济较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变化及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的发展与进步
主要表现为水稻栽培技术与土地利用率的提高。水稻是我国南方主要粮食作物,其栽培历史之悠久,可追溯到公元前六、七千年以前。岭南百越族先民经过不断摸索和实践,到汉代,当地越民已培育出“一年二熟”的双季稻。(注:杨孚:《交州异物志》,清曾钊辑本,收入《岭南遗书》第五集。)到三国东吴统治时,岭南栽培技术又有了新突破,出现了“一岁三熟”的“三熟稻”。据《初学记》卷8《岭南道》引晋郭义恭《广志》记载,“南方地气暑热, 一岁田三熟”。“三熟稻”的出现,不仅大大提高了岭南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而且从一个方面弥补了长期以来岭南地区耕地面积狭小的缺憾,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岭南地区以山地丘陵为主,同中原及内地相比,农业垦殖数明显落后。故岭南农业开发只能从提高土地利用率与增加土地复种指数等方面考虑。(注:参见陈伟明:“古代广东农业发展的若干特点与启示”,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10期。)岭南气候特点诸如日照长、气温高、降雨多等恰好具备了复种作物的基本条件。因此,早在汉代,岭南交趾一带已出现了“冬夏又熟,农者一岁再种”(注:杨孚:《交州异物志》,清曾钊辑本,收入《岭南遗书》第五集。)的双季稻。东吴以后又出现了“三熟稻”。这种多熟复种,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岭南地区农业垦殖数较低的不足,保证了粮食生产的基本供给。除去以上这些因素,东吴统治时期岭南农业发展及耕地面积的扩大,主要是通过大批富有劳动生产经验和技能的北方人民的迁入,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的使用和推广,以及岭南诸蛮族人民为开发岭南所作出的贡献等诸因素而起作用。因为随着大批北方劳动生产者的涌入,以及当地诸蛮夷走出深山,出居平地,同汉人一起从事农耕,必将推动原有农垦区面积的扩大,而牛耕技术与铁农具的使用,又使岭南落后的粗放式“火耕农业”,为精耕细作的犁耕农业所取代。所有这些都将推动着这一时期岭南农业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
(2)多种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 岭南地处低纬, 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形成了丰富的植物资源。大量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得以在此栽培和生长。在东吴治理岭南的几十年间,岭南经济作物的品种有了较大的发展。据晋人稽含所著的《南方草木状》一书记载,当时,食用植物,如香蕉、桔、柑、荔枝、龙眼、杨梅、椰子、橄榄、甘蔗、桄榔、槟榔、千岁子、益智子等就有数十种,其中桄榔树不仅“其皮可作绠,得水则柔韧,胡人以此联木为舟”,而且此树,“皮中有屑如面”,“其大者一树出面百斛”,“夷人资以自给”。可见它具有多种经济价值。《南方草木状》中还记载了岭南人民利用水面种植蕹叶(即蕹菜,俗称空心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的情况,它的栽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岭南土地利用水平的提高。此外,书中还记载了当地所产沉香、密香、黄熟香、水松等香料植物。随着岭南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些域外花卉植物如耶悉茗花、末利花(茉莉花)等也相继移植岭南。“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注:稽含:《南方草木状》卷中,收入《丛书集成初编》。)按《南方草术状》一书撰于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 距东吴灭亡(280年)仅24年,可说是当时人记当代事。 故书中大部分内容所反映的应是东吴开发岭南的数十年间,各类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
岭南粮食作物的生产由于受自然条件的种种限制而发展缓慢,而众多经济作物的种植,却得天时、地利而茁壮成长。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为岭南开发创出了一条新路。
(3)手工业的进步
这一时期手工业的发展突出表现为造船业、 纺织业和丝织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先看造船业。岭南山多水盛,习于水性,善于用舟是岭南土著人民的传统习惯。岭南山区茂密的森林,优良的木材,为岭南人民伐木造船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其次,东吴立国于水乡泽国的江南,大量军事行动多动用水师。当时东吴出于军事用兵及对外贸易的需要,对船舶的需求量很大,岭南作为后方基地,特别是东吴主要造船基地之一,造船业由此迅速发展起来。这时期岭南造船业的发达,主要表现为所造船只数量多,规模大。据《三国志·吴书·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载:吴亡时,共有5000余艘船为西晋政府接管。按当时的条件这是个不小的数字。而其中相当一部分舟船系广州番禺、交趾龙编等岭南沿海码头所造。当时东吴所辖的建安侯官(今福建福州)、广州番禺(今广州市)都是规模巨大的造船基地。航海水手也大都从习水的闽、粤人中选出。(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西晋左思《吴都赋》中所言“槁工楫师,选自闽、 禺”是也。因两地造船业发达,东吴遂在东南沿海建立起一支相当规模的水师。水师出战,多用战舰,大的战舰据说已高达五层。(注:参见张承宗、田泽宾:《六朝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至于用于运载货物和进行海上商业贸易的船只主要是吨位大、且掌握了一定航海技术的大海船。据《太平御览》卷769 引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记载,当时东吴航行于南海上的贸易船舶,大的“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三四丈”,远望如“阁道”,可载“六七百人”,载物“万斛”。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已是一种设备较齐全、平稳舒适的大型远航货船。即使规模较小的海船,在当时也能载战马84匹(注:《三国志·孙权传》嘉禾二年注引《吴书》。)。至于三国时吴派卫温等率上万名甲士渡海攻取夷州(今台湾),所乘船虽不见史书记载,但从大陆横渡水势湍急的台湾海峡,必需是有风帆装置、体积不大却平稳、便于登陆和出击的战舰。所有这些均表明当时包括岭南在内的东吴江南造船业的发达和技术水平的高超。此外,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时,地处内陆的五岭山区,旬日间为起义军建造了“起四层,高十余丈”(注:《太平御览》卷70,《舟部》。)的巨舰达10余艘,说明岭南造船技术当时已达到相当高超的水平。东吴去东晋不甚远,所辖疆域又大体相似,东晋如此,东吴时岭南造船技术即使超不过东晋,也不会相差太远。
再看纺织业。纺织业是岭南手工业中颇具特色的行业。岭南地处热带、亚热带,独特的自然气候,使得岭南纺织品具有品种多、色泽鲜艳的特点。故自古便有“岛夷卉服”(注:《尚书·禹贡》。)之称。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岭南人民因地制宜,利用当地各种植物纤维,织出了多种多样的布品,计有葛布、竹布、蕉布、麻布和棉布等。其中棉布,当时习称为“古贝布”或“吉贝布”。据《后汉书·哀牢夷传》记载,早在东汉时,我国西南的哀牢夷人已开始种植棉花(木棉)。大致到东吴时棉花种植技术开始传入岭南。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中就记载了棉花从成熟到加工成棉布的过程。他说:“五色斑衣,以丝布、古贝布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毛,中有核如珠玑,细过丝棉,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织,任意小抽,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我国内地直到宋元时期才开始普遍用棉花织布,在此方面,岭南较内地领先了一大步。
岭南的丝织业水平虽比不上吴中,但其养蚕技术却颇为发达。据《水经注·温水》条记载,岭南一带桑蚕每年可产“八熟茧”。也即左思《吴都赋》中所说的“八蚕之绵”。“八熟茧”的出现,可说是当时全国桑蚕技术的最高峰,而这一纪录又是东吴时岭南人民所创造的。(注:参见刘希为、刘磐修:“六朝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 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除此而外, 东吴时岭南其他部门的手工业如矿冶业、煮盐业、食品加工业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发展。
(4)商业及海外贸易的发展 岭南沿海一带,既有鱼盐之利, 又便于通舟楫,故很早以来商业及对外贸易远较农业为发达。东吴时岭南商业在农业、手工业及海内外贸易的不断推动下,出现了较快发展的势头,并由此出现了一些闻名的商业都会。番禺,地处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上,且位于横贯岭南境内的三大水流(指东、西、北三江)的交汇处,为岭南内河与海上航运的交通枢纽,故水陆交通均很便利。早在汉代,这里已是国内有数的商业城市。史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番禺,其一都会也。”(注:《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东吴时在此设州治,这里遂成为广州地区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当时国内外商贾云集于此,各方珍宝堆积如山,番禺成为名副其实的岭南地区商业大都会。其次是徐闻与合浦。二者作为北部湾近海航线上的港口城市,早在汉代就因对外贸易繁荣而闻名。东吴时,由于广州的兴起,以及后来海上交通线的改道,两地靠转口业务而发达的商业贸易由此受到某些不利影响。但因两地均处近海,其中徐闻自身又与出产珠、贝和玳瑁的珠崖郡(今海南岛)隔海相望,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徐闻一地经商致富提供了便利条件。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欲拔贫,诣徐闻”(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志·阙卷逸文》卷3。 )的谚语,便是其商业发达的很好写照。邻近的合浦,素以盛产珍珠闻名天下。《晋书·陶璜传》中言及东吴末年,对合浦之珠“所调猥多,限每不充”,透露出东吴统治者对合浦珍珠需求之大。东吴统治者的奢侈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合浦珍珠市场的繁荣。再看始兴。其地位于五岭南侧及大庾岭路与桂阳道越岭后的交汇处,南面又有北江水路可通番禺,为内地与岭南交通的中转站,东吴末,统治者为加强对岭南内陆的开发,在此设郡筑城。此后岭南、岭北的货物在此集散,加之本地又以产银而著名,于是始兴商业由此兴起。此外,东吴时岭南一些开发较早的重要郡治如苍梧广信、交趾龙编等,也皆为一方之都会而闻名远近。
岭南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很早便与南海诸国发生了联系。但官方对外贸易的正式兴起则始于两汉。交趾地区是当时海外贸易的前沿阵地,地濒南海北部湾的龙编、徐闻、合浦等地皆为当时南海贸易的重要港口。三国时期,国土分治,岭南作为东吴疆域的一部分,既是后方基地,也是海外贸易的前沿。据史书记载,东吴孙权时,曾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使大秦、天竺等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注:《梁书·海南诸国传》。)此后,所到之国的商人有不少来到岭南的交趾等地做生意。其中有个名叫秦论的大秦(罗马)商人曾于孙权黄武五年(226年)取道交趾到达建业时受到孙权的礼待。 “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注:《梁书·海南诸国传》。)这些都足以说明东吴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其后随着岭南经济开发的不断深入,造船业的发达以及濒临南海的有利条件,岭南地区的海外贸易开始步入兴旺发达的时期。
(5)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 东吴时,由于岭南经济的开发, 影响到当地政权机构的变化。两汉时,因盛产珠宝香料的东南亚远航技术尚不够发达,近邻南海诸国的龙编(今越南河内)便成为珠宝贸易的最大市场和南海贸易的重要港口。交趾地区也由此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的重地,故统治者重视对交趾一地的经营,交州刺史常驻龙编。到三国东吴统治时期,岭南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是东吴重要的战略基地,而且也是它对外贸易的前沿阵地,所以统治者关注岭南特别是交趾以东地区的治理和开发,并采取有效措施,诸如首置广州,实行交、广分治等,从而大大推动了岭南东部区域经济的开发。其后,随着这一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及海外贸易的发展,以番禺为中心的广州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而交趾一地相对日渐冷清。此后伴随着北部湾近海交通线的变更,交广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就逐渐地由交趾龙编移到了广州番禺。这一变化,从此奠定了后世岭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其作用不可低估。
余论
以上通过对汉末三国时北方人口大量入居岭南、东吴对岭南统治权的确立、东吴政权治理与开发岭南所采取的措施、东吴统治时期岭南地区各经济门类发展状况等各方面的考察,不难看出,在东吴治理与开发岭南的数十年间,岭南经济发展正经历着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此以前,岭南被中原王朝视为化外之地,“长吏之设,虽有若无”。(注:《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在此以后,岭南作为全国一大经济区,区域性经济发展态势已崭露出头角。到宋元时期,以珠江流域为代表的岭南区域经济得以起飞,并快速赶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发展水平,这一切与东吴首创岭南经济发展新格局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