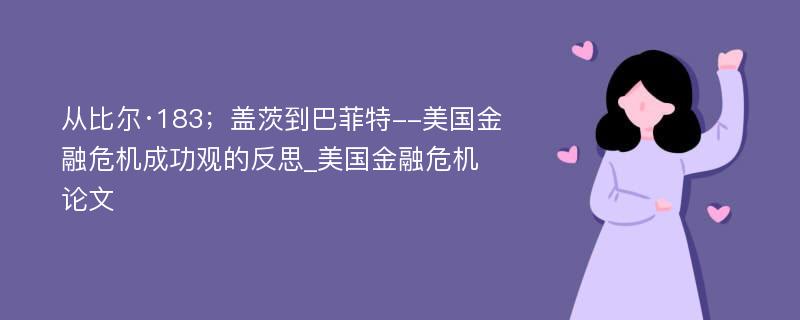
从比尔#183;盖茨到巴菲特——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功观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盖茨论文,美国论文,比尔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巴菲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0)02-0022-04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但同美国整个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息息相关,而且更与基于生息资本公式的成功观关联密切。这种成功观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流行,因此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一、“我要做巴菲特”
巴菲特被看作是投资股市、快速赚钱的成功典范。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想做巴菲特,想通过赚快钱发财致富。这种想通过钱来生更多钱的方式,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M—M',即从钱M直接生出更多的钱即M'来。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就同这一公式,同美国整个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有关。信贷经纪人、商业银行不需要任何首付就把钱放贷给购房者,然后再把这贷款出售给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由后者把它们打包成3A(即其安全性相当于美国国债)的证券卖给全世界的机构投资者,包括我们的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从经纪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到投机购房者,实践的就是这样一个M—M'公式。经纪人、银行赚取巨额费用,而投机购房者就等着房价上涨,“空手套白狼”,卖了房子赚大钱或者再用这房子作抵押继续贷款购房或者消费。
M—M'公式是货币公式或者说生息资本公式,但它是一个颠倒的或者说省略的资本公式。因为它抛开了其中的生产过程。按马克思的揭示,资本的总公式是:M—C—M',即货币—商品—增值的货币。货币作为资本只有回到生产中,通过剩余劳动,创造出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然后才能通过商品的出售,实现剩余价值。因此货币作为生息资本,它的公式应该是:M—M—C—M'—M',在这里出现两次的是,由投资者或银行(它是社会资本的管家)将第一个货币M作为资本贷给厂商作为生产资本即第二个货币M,在完成这个公式中间的M—C—M'即从货币到商品再到增值的货币的运动后,由厂商再将第一个M'即增值的货币连本带利地还给银行即第二个M'。如果投资者是作为储户或股民,那么他与银行或证券公司分割的是剩余价值或利润中的利息部分,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但是如果省略了其中的M—C—M',以为钱能直接生钱,即从第一个M直接得出最后一个M',这就像童话故事中把钱种到地里,就能长出许多钱来一样,从M—M'的增值或者说生钱,就只能是虚幻的了。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实践的也就是这个省略的或者说虚幻的公式。
二、“我要做比尔·盖茨”
约十年前,有许多年轻人以比尔·盖茨为成功榜样。按我们国内那时的评价,比尔·盖茨是英雄,知识经济时代的英雄。尽管当时许多人称比尔·盖茨为“英雄”,着眼的是“微软帝国”及其巨大的财富,但从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看,比尔·盖茨实践的还是M—C—M'公式,他致力于的还是将他的知识和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从事的是实际的剩余价值创造。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代表了两类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可以说,他们是这两种资本的人格化的典型表现。一方面,由于信用,由于巴菲特这样的货币资本家、风险资本家,使得资本总公式中的第一个M,不再限于缓慢的资本积累,而是可以通过资本的集中来达到并且扩大了。如马克思所注意到的:“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情完成了。”这种“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1]。因此,货币资本家的作用不仅使得产业资本家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更广泛地组织劳动的物质动力,而且能够加快资本形态在各个阶段的变化,从而加快整个资本再生产过程。然而,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创造也正是由于产业资本家,由于比尔·盖茨,才使得巴菲特的钱,作为过去劳动产品价值的第一个M能够保存下来,或者说能够再生产出来。它之所以能够保存和再生产出来,是通过产业资本的中介,通过同活劳动接触的结果。而过去劳动的产品对于活的剩余劳动的支配权,也只是在存在着资本关系中并支配着活劳动的时期内才存在。所以,巴菲特的投资收益是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而对产业资本剩余价值的分割。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相对于货币资本家,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2]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所有的资本家都是巴菲特,那么谁来做比尔·盖茨呢?这就是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所依赖的颠倒的生息公式M—M'所发生的问题。
据统计,1981年美国信用市场占美国GDP的168%,到2007年升至350%。1980年美国金融资产是同年美国GDP的5倍,而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则是同年美国GDP的10倍。其中,美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利用的借贷比例从1997年占美国GDP的63.8%,上升到2007年的113.8%。尤其突出的是,几乎美国信用市场的一半债务都是美国金融机构利用的。[3]换言之,金融危机前,美国金融机构创造的57万亿信用债务中,其中一半是它们自己利用的。也就是说,这一半的钱并没有用到生产过程中,而是用在从M—M'中去了。由于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是能够创造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创造只能回到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生产资本才能做到,因此,这就使得借贷资本发生了与产业资本同样的问题。在产业资本的场合,所有的产业资本家都把他自己的工人当作工人,而把其他资本家的工人当作自己商品的尽可能大的消费者,因而致力于提高剩余劳动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尽可能多地限制他自己工人的工资,从而降低工人的消费能力。但是所有的剩余劳动很大程度上又要靠必要劳动、靠工资、靠消费能力来实现,因此就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就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来自剩余价值的提高与必要劳动的缩小成反比,剩余价值的实现又要依靠必要劳动这一矛盾的趋势中。同样,在信用资本即借贷资本的场合,所有的借贷资本也都把自己当作借贷资本即生息资本,而把其他资本当作生产资本即产业资本,因而致力于虚拟资本的无限度放大。而如果所有的货币资本都不再转化为产业资本,都作为借贷资本来生存,或者如美国经济所发生的那样,一半的借贷资本都作为巴菲特来生存的话,那就必然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谁来为巴菲特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当生息资本的这种无限度放大的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在它的劳动者即生产资本身上得不到满足时,就转而通过虚拟剩余价值的生产来直接满足庞大的借贷资本对利润的饥饿追求了。
这就是美国银行将其传统的“贷放—持有”模式改变为“贷放—分发”模式的原因所在。因为贷放需要有回流,才能持有,也才能维系作为借贷资本机构的银行的生存。而如果没有回流,没有足够的产业资本家替它们打工,所投放出去的借贷资本又如何能带着剩余价值回来呢?因此,正是由于“贷放—持有”模式的不能维系,才为造成次贷危机直接原因的“贷放—分发”模式打开了缺口。“贷放—分发”模式的通行,意味着银行、金融机构不再为托付它们的社会资本负责了,它们可以放肆地将费用留给自己,而将还贷责任转移给其他人。也因此我们看到了,在巨额费用的刺激下,商业银行与保险机构、评估机构和投资银行一起,构造了一条住房抵押借款证券化生产线,或者说金融衍生品制造工厂,将住房抵押借款作为金融衍生品的原料,通过经纪人、贷款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证券化打包,源源不断且一路畅通无阻地销售给全世界。也就是说,银行和金融机构取消和取代了比尔·盖茨环节,直接采取了M—M'公式,甚至不是M—M',而是B—B'(Bills of exchange)即票据(股票、债券等定期支付的凭证)生票据的方式,也就是用虚拟的货币资本票据直接生产出票据的方式,来满足庞大的巴菲特及其追随者的钱生钱的需要,特别是作为社会资本管家的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管理人自己谋取巨额佣金报酬的需要。据纽约WMC住房抵押贷款地区一位信贷经纪人后来坦白说,他只要完成一笔CDO业务,就可获得一百万美元的佣金。由于风险愈大贷款利息愈高,他专向三无(“无收入、无工作和无资产”)家庭,有时称作“ninjna”(即“no income,no job and no assets”)的借款人兜售住房抵押贷款,华尔街的投行也因同样的理由,大肆购买混合更多这类贷款的住房抵押贷款。由于银行和投行从每份售出的房贷中获利丰厚,因此他们不断地催促信贷经纪人推销更多这类抵押贷款,有的甚至挨家挨户向贫困的居户敲门推销。新泽西的一位咨询师这样评论说:看在一笔次贷可获得18,500美元的分上,他们也有18,000个理由伪造三无购房者的抵押贷款文件,从而硬把这些人塞进他们根本买不起的大房子里。[4]
由此来看,生息资本公式在美国次贷衍生品生产中得到了最虚幻和欺诈的表现。而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是日常生活中生息资本公式盛行及其在成功观上反映的原因,后者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过度金融化经济的不可持续性。正如纽约州审计官办公室发言人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所批评的,从抵押贷款经纪人到华尔街风险经理,想的就是巨额奖金,而不管公司的长期健康与否,他们根本不懂得投资是如何工作的[5]。
三、可持续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成功观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知道投资如何工作的、并被华尔街的天才们认为是成功典范的巴菲特,到晚年时,也并不认为自己是成功的。他是在其妻子苏茜去世后才明白这一点的。据他的传记作者说,他后来认为:“衡量成功的标准是真正爱你的人的数目。”[6]
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最后,敏锐地注意到,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新教伦理的支持了,“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的地方,如在美国,追求财富已经失去了宗教和伦理意义,相反正在日益与纯粹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从而实际上往往使它具有娱乐竞赛的特征”。他认为,“如果完成某种职业不能与最高尚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念直接相连,那么人们一般就不会做出任何努力,去为它寻找存在的根据”。同时他又认为,“现代经济秩序与机器生产的各种技术、经济条件结合在一起,以其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决定着今天所有生而处于这种机制之中的个人的生活”。新教伦理曾经以为经济力量只是一个可随时扔到一旁的轻裘,然而它所支持过的这个力量现在却已经成了铁笼。韦伯认为,“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牢笼之中”,或者在这场巨大发展告终时,是否会出现面貌一新的先知,出现旧观念旧理想的复兴,或者出现病态的自我陶醉的机械僵尸。[7]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企业家领袖组织考克斯圆桌会议(Caux Roundtable)执行董事斯蒂芬·杨(Stephen Young)继续韦伯的思考,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原因是美国资本主义脱离了伦理的支撑,人们考虑的仅仅是如何赚钱。
韦伯所说的现代经济秩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力量现在仍然是个“铁笼”。但是按马克思的观点来看,最大的铁笼是它自身,也即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文明化趋势,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马克思当时指出的限制,揭示的是资本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也就是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创造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这是与资本要无限度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这个矛盾,是资本所具有的这种文明化趋势与资本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表现之间的矛盾,文明化的趋势以资本家是否获得剩余价值为前提,从而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后的绝对的形式。不仅如此,从金融危机和生息资本公式的流行,我们更深入地看到了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的矛盾。也就是产业资本家不断地从产业领域退出来,表现为从比尔·盖茨退回到巴菲特,加上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作用,使得借贷资本量日益庞大使得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特征愈益明显。资本的劳动者与资本的资本家之间的这种矛盾,使得资本的劳动者愈益多地转为资本的资本家,反映了资本家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驱动力减弱了,它愈益趋向的是通过借贷资本,通过与产业资本的对立,对产业资本的分割,资本对资本的剥夺来生存和扩大,从而显示了列宁揭示过的寄生和没落的特征。可以认为,这是资本发展生产力的文明化趋势在它自己身上遇到的第二种限制。进一步分析还可看到,对真正懂投资的借贷资本家如巴菲特来说,需要他所说的“专注”,即抛开作为人的其他所有因素,包括对亲人的关爱,而专注于借贷资本的人格化角色。巴菲特晚年的后悔,一方面表明了人性不能完全为赚钱的冲动、为借贷资本的人格化角色所支配和泯灭,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以个人物质财富的满足为经济发展驱动力的有限性。尽管个人很难跳出韦伯所说的“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但是从韦伯上述敏锐的观察,从巴菲特的后悔,从斯蒂芬·杨的论断中,我们看到了传统的、古典的或者作为落伍的、要丢弃的精神东西的价值。我们究竟为了什么而赚钱,为了什么而生活,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
巴菲特的后悔说明,仅仅发财致富,是不能为可持续的经济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心理动力的。或者说,资本的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文明化趋势,是不能靠它的人格化或者“专注”得到支撑的,从而暴露了以机械为基石的资本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这也从反面启示我们,在利用资本的过程中,必须寻求经济发展的持续的精神动力。可持续经济不仅仅是物质的可持续、环境的可持续,更重要的是人生观、成功观上的可持续。因此,这不仅仅是经济伦理学范围内能回答的问题,而是人生观与道德理想的问题了。上海富大集团董事长和总裁袁立先生在这方面作了有价值的探索,他把个人和企业的成功理解为做好人、做好企业的信仰和责任意识,使他的企业和作为企业主的自己,得到了可持续的发展[8]。他的探索或许有助于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处在朝新经济形态过渡点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用韦伯的表述来说,最终究竟是靠出现新的先知、旧观念旧理想的复兴得到支撑,还是靠打碎病态的自我陶醉的机械僵尸得到解放,或者用笔者的话来说,可持续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成功观?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已经突出地将这问题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标签:美国金融危机论文; 金融论文; 银行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剩余价值规律论文; 货币论文; 产业资本论文; 银行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