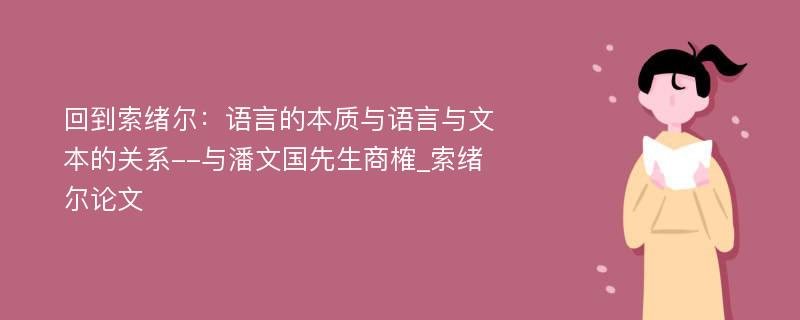
回到索绪尔:论语言的本质及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与潘文国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本质论文,语言论文,文字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的论题算不上什么新鲜话题,因为自从上个世纪初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以后,这个问题就已经获得了科学的解答。这本是语言学理论中最基础的部分,也是语言学界业已形成共识、成为语言学理论中的常识和基本原理的内容。为什么还要讨论这个话题呢?这是由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语言学研究出现了对汉语和汉字的特点进行重新认识、对以往的认识和研究进行反思,希冀能开辟出基于汉语汉字特点的语言学理论新天地来的自觉意识,也出现了一批这类研究论文和专著。应该说这是一种寻求理论创新和突破的良好契机。但是,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有些研究论文或专著中,往往在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或是理论基础上出现严重失误。其中就包括本文论题的内容。究其原因,除了刻意求“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的理论的误解和曲解,甚至以断章取义的方法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索绪尔的理论。由于事关语言学理论的科学基础、索绪尔语言学经典的正确解读和避免以讹传讹,为了中国语言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和健康发展,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予以揭示和讨论。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潘文国先生的专著《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中涉及语言的本质及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的有关论述;并以还原索绪尔的文本解读为旨归。
一、论潘文国先生对语言的“新定义”
潘先生在书中提出了对语言的新定义:“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1]83并说:
跟惯见的其他关于语言的定义相比较,这个定义不强调“音义结合”这一点,其目的就是为了容纳进文字。事实上文字是不是在“语言”的范围之内,是近几十年世界语言学界共同关心的课题。我们在考察语言定义发展的过程中发现,把文字语,乃至手势语包含在语言范围之内是90年代以来的趋势。著名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托尔在他编著的《剑桥语言百科全书》(Crytal 1997)里更提出了语言的三对媒介,在传统的“听”、“说”(口语),“读”、“写”(书面语)之外,还加上了“做”、“看”(手势语)。“认知和表述方式”的范围比“音义结合”要宽,它不但包括了“音义结合”,还包括了“形义结合”,如汉字,因为这是汉人“认知世界和表述”的方式。西方的文字是否包括在内?看你怎么理解。如果你认为它也是“认知和表述的方式”,那就是;如果认为只是对语音的记录和模仿,那就不是。聋哑人的手势语也可作同样分析。[1]83
按照潘先生对语言的“新定义”,那么,绘画、音乐、还有舞蹈等等其他艺术形式,算不算“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聋哑人的手势语能跟自然语言等量齐观吗?各种“形义结合”的符号如交通信号、各种标记、图案等等,难道都要成为语言和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了?逸出人类自然语言的范畴,还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普通语言学吗?我相信这该不会是潘先生给语言新定义的初衷吧?但这新定义的逻辑后果,就是这么令人不可思议。语言的媒介不等于语言自身;文字可以表现语言,但文字并不等于语言;就像一个人的照片并不等于这个人自身。试图把语言概念的外延扩大,只会导致模糊语言概念内涵的本质属性和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利于语言科学的进步。所以,我认为还是索绪尔对语言和语言本质的定义比较简明扼要准确:“语言是建立在听觉形象基础上的符号系统。”[2]78“与某一概念联系的听觉形象,是语言的本质。”[2]8
潘先生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定义“强调语言的自然属性”[1]81,并不准确。因为索绪尔说过:“一旦语言去掉了不属于它的一切,看来它就归入了人文事实一类。语言是建立在听觉形象基础上的符号系统。”[2]78至于语言的社会属性,更是不言而喻地贯穿在索绪尔的全部理论中。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观点。例如:“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但是有几个特点使它和政治、法律等其他制度不同。”“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3]37,“符号在本质上是社会的”[3]39;“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3]35“我们研究的具体对象是储存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产物,即语言。”[3]47
二、论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
潘先生把文字与语言混为一谈,称之为“文字语”,“不但包括了‘音义结合’,还包括了‘形义结合’,如汉字”。对“西方的文字是否包括在内”,潘先生的回答模棱两可、耐人寻味:“看你怎么理解。如果你认为它也是‘认知和表述的方式’,那就是;如果认为只是对语音的记录和模仿,那就不是。聋哑人的手势语也可作同样分析。”[1]83潘先生怎么认为呢?他未明确说。根据潘书的文本分析,可以推断潘认为“是”,因为根据潘的语言新定义“认知和表述的方式”,应包括西方语言无疑,故符合第一个“是”的条件;也可以推断潘认为“不是”,因为潘在后文中说:“表音文字……走的是曲线,是从概念经过语音的中介再到文字,也就是说,与概念直接联系的是词的读音,然后再用文字把读音记下来;……文字对语音负责,语音才直接跟概念发生关系,在这种文字体系里,语音是第一性的,文字只是‘符号的符号’。”[1]89按照潘的文本所作的理解和说法就是,这种文字只是记录语音的符号,故又符合第二个“不是”的条件。可见潘先生对西方的表音文字是不是“文字语”,前后是自相矛盾的。
把文字和语言混为一谈,还体现在潘先生将文字起源和语言的起源混为一谈。他把中国古代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说成是“汉语关于语言起源的传说和史实”[1]107;在将西方《圣经》中关于语言起源的两个传说跟中国古代仓颉造字的传说作对比后说:“中国古代关于语言起源的传说与西方关注读音者不同,是关注于文字的。”[1]107“如果说西方语言的产生是通过亚当的随口而呼的命名开始的,则汉语的产生是起源于对事物形象有意的摹仿。”[1]108
首先,潘先生立论的大前提就不能成立。“仓颉造字”的传说能等同于“汉语关于语言的起源的传说和史实”吗?究竟是先有语言还是先有文字?还是二者同时产生?无论从人类进化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看,还是从现存的世界上某些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社会群体看,都说明了人类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潘先生自己在书中也说:“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当然是先有语言,语言(狭义的语言,不包括蜜蜂跳舞那种‘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标志。有人甚至相信,人类历史有多久,语言历史就有多久,……而文字产生是相当晚近的事,以汉字为例,从半坡陶文至今也不过6000年左右。”[1]32既然如此,将汉字产生的传说说成是“汉语关于语言的起源的传说和史实”不是根本错误的吗?因而由此推论的下面两个观点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潘先生说“中国古代关于语言起源的传说与西方关注读音者不同,是关注于文字的”。语言起源既远远早于文字起源,怎么可能关注于文字呢?潘先生说:“如果说西方语言的产生是通过亚当的随口而呼的命名开始的,则汉语的产生是起源于对事物形象有意的摹仿。”把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等同于汉语也起源于“象形”,和上述把汉字起源说成汉语起源一样,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客观世界的事物形象,难道能转换成语言的音响形象?或者按潘先生的说法,汉语语言的音响形象能够“摹仿”客观世界的“事物形象”吗?就算拟声词、感叹词能摹仿自然的声音,而诸如“天地日月”、“红蓝黑白”、“美丑好坏”等事物和概念,如何用语言摹仿?
潘先生说,“(自源)文字直接与意义联系,语言通过语音间接跟意义联系,在开始时可说是各走各的路。但后来两者走上了结合的道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字越来越多地用来表示语言,凡不能表示语言的文字就逐渐丧失了生命力。”[1]170潘先生既将文字的起源等同于语言的起源,又说文字与语言开始时是互不相干,“各走各的路”,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说文字直接表意,语言反而间接表义,能说得通吗?脱离语言的“文字”还能算是文字吗?文字的独立性归根结底是语言赋予的。潘先生说:“随口而呼是任意(arbitrary)的、无理据的;有意描摹则是有理据的,可分析的(‘说’文‘解’字本身说明了其可分析性)。汉语与西方语言在产生之初所走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途径(‘语音一任意性’vs.‘文字—理据性’),对于普通语言学研究有很大的意义。”[1]108把汉字造字的“理据性”迁移到汉语语素的音义结合上来并从而否认其“任意性”,这一点潘先生和徐通锵先生如出一辙,只是潘比徐更直白无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更容易、更清楚地看出这种理论错误的症结和根源所在。
潘先生还批评“人们囿于索绪尔等狭隘的语言定义,只把音义结合的看成语言,把文字只看成‘符号的符号’,更不承认形义结合也是产生语言的一条途径。”[1]108请问潘先生:“形义结合”的“形”,是指视觉的还是听觉的?还是兼而有之?如指视觉,“形义结合”无非就是书面语言的文字(识读时也免不了要跟语言的语音语义相联系)表达的概念,与听觉语言虽是两码事,但表现的或者说依附的却是听觉语言;如指听觉,即语言的音响形象的心理印记,那就是音义结合,即口耳相传的语言;如兼指二者,那无非就是上述的两种状态;难道还有什么只有“形义结合”而不含语言的音义结合的人类自然语言吗?
潘先生认为造成像汉字这样的表意文字和用拼音字母的表音文字这样两种不同文字体系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人类认知世界和进行表述的方式不同。”他说:
在文字问题上,两大体系的不同其实就是认知和表述方式的不同。人类认识世界,形成概念,再通过语言表述出来,可以有不同的途径。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正体现了两条不同的途径。一条走的是曲线,是从概念经过语音的中介再到文字,也就是说,与概念直接联系的是词的读音,然后再用文字把读音记下来;另一条走的是直线,从概念直接到文字,或者说,是用文字直接表示概念,语音只是在这过程中的附加物,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附加物,否则就不成其为文字。在前一条途径里,文字对语音负责,语音才直接跟概念发生关系,在这种文字体系里,语音是第一性的,文字只是“符号的符号”,……而在后一条途径里,文字直接表示概念,语音是同时的附加物,这就使文字取得了至少跟语音相同、如果不是更重要的地位。文字就绝不只是“符号的符号”,相反,它是如同索绪尔所说,它就是汉人的第二语言,它在汉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同样起着语言的作用,而千百年来汉人对汉字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看作语言学的研究。[1]90
首先,人类认知世界是否因文字的不同而不同,我对此表示怀疑。从认识论看,应该具有共性。洪堡特(W· V·Humboldt)一方面强调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天然联系,另一方面也认为,语言差异并不表示各人的客观认识一定相去甚远,因为“人类最主要的精神力量的表达是互相支持、共同作用的”[4]。语言差异如此,作为表现语言的文字的差异亦当作如是观。
所谓“表音文字”、“表义文字”之说,是从文字表现语言的角度而言的。汉字因为形、音、义一体,既表语音,也表语义,当然还有承载语音语义的字形,这就具备了语素的性质、功能,所以汉字一般被认为是“语素文字”;而拼音字母文字,其单个字母通常只表语音(而且是不完整的语音,因为音位字母在拼音时只代表一个音素)而不表语义。两相对比就取二者的差异,把汉字说成“表义文字”(其实同时也必是“表音”的);把字母文字说成“表音文字”。如果把出发点对调一下,即以语言为本位(最小单位是语素)去看文字,那么无论是汉字或是英文(代表拼音文字),只要是书写正确的、代表该语言符号的文字,就都是具备形音义的、既表语音又表语义的文字了。
文字体系不同归根结底是由语言的语素音位系统和语素音位结构的关系决定的,阐明其原理需作深入研究和专文论述,在此不作展开。主要就语言与文字关系问题略作讨论。
无论是表音文字的“曲线”说还是表意文字的“直线”说,可以看出,潘先生都是把语言所包含的概念与语音分离开来和文字相联系。把语音当成“中介”或者“附加物”。殊不知语言单位的音义结合如同一张纸的正反面,是不可分离的。只要是跟语言的最小音义结合体语素相联系,无论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都必然是表意(概念)的同时也必表音。谈不上语音或概念谁先谁后、谁是“附加物”。把表意文字说成“是用文字直接表示概念”,请问,如果你不先通过学习、认识这些文字,不把这些文字跟语言相联系即经过语言认知,它能向你“提供思想的符号”吗?[1]90而一旦和语言相联系,能脱离语音和语义吗?正如杨亦鸣先生根据神经语言学的有关测试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所说:
我们认为,音与义的结合是第一性的,语言首先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形的介入最早也必须是在完整地掌握语言之后的学龄期开始的,所以,从理论上说,形与音、义的关系是平行的,不应存在形与义联系紧密,而与音联系脆弱的现象,这是东西方语言大脑词库的共性。但在形一义通道内,由于汉字某些表意的特点,可能使用汉字的失读症患者由形激活义更容易些,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在这方面要困难一些。但不能说在整个大脑词库中汉语形与义结合紧密,音与义或形与音结合不紧密。……由于汉字与拼音文字存在巨大的差异,往往使人不自觉地误认为汉语与其他语言也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忽略了语言普遍性的原则,在潜意识中总是希望在语言的本质上寻找出汉语与其他语言特别是印欧系语言的不同之处。实际上恰恰相反,语言在一般原则上应体现出共性,在具体问题上存在着个性。[5]
跟徐通锵先生的“两种编码机制”说一样(注:参见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潘先生的“直线”、“曲线”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根源,同样也是以文字而不是语言为出发点所造成的错觉;在语言“编码”单位上,不是以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语素为本位,而是以通常大于语素的“词”为拼音文字语言的本位,又以小于语素的“音素”作为拼音文字语言的编码单位,[1]99从而导致语音语义不同步的二元编码机制现象,因而有了徐先生的“约定性编码机制”说和潘先生的“曲线”说。而如果是以语言为出发点,以语素(最小音义结合体)为“编码”单位,就不会出现这种语音语义不同步的现象。因为人类语言的分节始终都是以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为单位的,这就是马丁内(A.Martinet)的“双重分节”理论中的“第一分节”原理(注:参见顾兆禄:《再论语素本位原理——兼与潘文国先生商榷》,《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对于表现语言的文字的识读,自然也是以这种音义结合体为单位的。并非像徐、潘二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逐个字母拼成音节再跟语义相联系(所谓“语音的中介”)。这是从拼音文字的字母出发去看语言所造成的错觉。正如索绪尔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忘记,通过习惯的力量,书写的词最终要变成表义符号,这种词具有整体的价值,(独立于它所构成的字母)。我们用两种方法读:拼读出不熟悉的词和读出一见就认识的词。”[2]71所以语言编码机制并不会因语言不同而不同。正如索绪尔所说:“通过把语言作为中心和出发点,我们就有了论及语言其他成分的讲台。如果我们把语言同其他成分混为一谈,不可能对语言中的东西进行分类。”[2]79
潘先生认为造成两种不同文字体系的第二个原因是“文字发生学上的差异”。[1]90潘先生说“凡自源文字都是表意的(不论是形义文字、意音文字、表词文字),凡他源文字都是表音的。这一发现有重要的意义。”并据此说明“任意性可以适用于拼音文字语言,却不适合于汉语。”[1]91
潘先生的这两个“凡是”恐怕站不住脚。仅拿日语来说,使用的是他源文字无疑,却离不开表意文字的日语汉字,也是事实。所以潘先生的“这一发现”并不符合事实。这也就使他下面的那些推论失去了依据。而且,潘先生上面所说的这两个原因之间也存在矛盾。既然自源文字都是表意的,而表意文字“认知世界和进行表述的方式”走的是“直线”;而表音文字,我们知道,都是由表意文字演变发展而来的(无论“自源”或“他源”),那是否意味着,同为自源文字的语言的传承者,其前后认知世界的方式也由“直线”改为“曲线”了呢?其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也由“理据性”变为“任意性”了?这能说得通吗?
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以前讨论过(注:参见顾兆禄:《回到索绪尔:论语素本位原理——兼与徐通锵先生讨论“字”与“语素”及“两种编码机制”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不再赘述。
三、论潘文国先生对索绪尔理论的误解和曲解
潘先生说:“声音是语言的符号,而文字则是符号的符号,这观点是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号称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提出来的(参见索绪尔1916:47-48),被认为是语言学的一条基本原理。”[1]30潘先生这里没有引用索绪尔的原话,从他提供的页码看,索绪尔的原话是: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按:应译为“分离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按:应译为“结合”)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按:应译为“以至要篡夺主要的角色”);人们终于把声音(按:应译为“口语的”)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按:应译为“口语的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3]47(按:对照Roy Harris的英译本[6]24,笔者在括号内略做修改。)
这段引文关键的最后一句话的英文是:As much or even more importance is given to this representation of the vocal sign as to the vocal sign itself.这里索绪尔说的“声音符号”(vocal sign itself,口语符号)是指语言(“口说的词”,spoken word),“声音符号的代表”(representation of the vocal sign,口语符号的代表)是指语言的代表,即文字表现的词(“书写的词”,written word)。哪里有什么“声音是语言的符号”的意思呢?索绪尔明明说:“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但是在日常使用上,这个术语一般只指音响形象,例如指词(arbor等等)。人们容易忘记,之所以被称为符号,只是因为它带有‘树’的概念,结果让感觉部分的观念包含了整体的观念。”[3]102可见,在索绪尔的理论体系里,单独用“音响形象”时,其内涵是包括了概念的。决不能把它等同于单纯的“声音”。所以,潘先生说“声音是语言的符号”是索绪尔提出来的,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理论根据,是对索绪尔理论的误解和曲解。读遍迄今行世的两种不同版本的索绪尔的《教程》,里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思,更没有这样的表述。恰恰相反,我们倒是看到这样的文字,索绪尔说:“语言的本质跟语言符号的声音性质没有什么关系。”[3]27所以,把“语音中心主义”的帽子扣到索绪尔头上,是没有根据的。[1]34实际上,从索绪尔对语言本质的定义看,也不可能做这样的表述。索绪尔说:“概念和声音符号的结合就足以构成整个语言”,“与某一概念联系的听觉形象,是语言的本质”。[2]8“它的唯一本质特征,是声音和表达某一概念的听觉形象的结合(听觉形象是留给我们的印象,潜在于大脑中的印象)。我们无须认为它 (语言)一定是无时不说的。”[2]9
很明显,索绪尔从未将概念(意义)与听觉形象(语音)分离开来谈论语言符号问题。因而,认为“在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里,文字只是记录语音的工具”[1]83是不符合索绪尔理论的实际的,是对索绪尔理论的误解和曲解。潘先生以此理解为前提的“符号的符号”说,其内涵也就跟索绪尔所说的“符号的符号”说不是一回事了。
至于说“文字是(语言)符号的符号”,索绪尔这样说并没有错。关于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索绪尔在《第三度教程》中有与上面引文内涵相同、更加简明的表述:“语言和文字是两种符号系统,一种具有表现另一种的唯一功能。看来它们各自相互的价值不会冒着被人误解的危险:一个系统只为另一个系统服务,或是另一个系统的形象。”[2]46
潘先生为了把汉字与语言混为一谈,还断章取义、曲解索绪尔的观点,他说:
“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告诉我们: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索绪尔1916:51)大师明明已经告诉我们,汉人有两种语言,一种是口说的语言,一种是用汉字书写的语言。这在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说明汉人研究语言学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果充分加以利用,汉人应该能够对世界语言理论的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1]47
索绪尔说这话的原文是:
书写的词在我们的心目中有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这两种文字的体系(按:指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来说,情况都是这样,但是在头一种体系里,这倾向更为强烈。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是这种代替因为可能是绝对(按:应译为“完整”)的,所以不致像在我们的文字里那样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汉语各个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3]51
难道索绪尔当真认为汉字是第二语言吗?当然不是。索绪尔强调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在两种文字体系里都一样,而在表意体系里更强烈。他揭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为了科学地认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并不是认为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和拼音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有什么根本不同,更不是为了肯定“文字就是第二语言”,而是一种形容强烈程度的譬况说法。索绪尔说的是“对汉人来说”、“在他们看来”,而不是表示自己肯定这种看法。索绪尔只是说汉人“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作为区别同音字或用方言无法通话时临时的相互沟通的手段。这是由于汉语同音语素多、方言分歧大导致的汉字与语音联系的地域性差异 (即索绪尔所说的“而这个符号却与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的原因)以及汉字的语素功能(表意)等特点造成的,绝非将文字等同于语言。实际上从索绪尔的理论体系里也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在英译本里看得更清楚:“He treats writing as a second language,and when in conversation two words are identicallv pro nounced,he sometimes refers to the written form in order to explain which he means.”[6]27这头一句用的是“He treats writing as a second language”(“他〈汉人〉把文字当作第二语言”)。在《第三度教程》里则根本就不再提“第二语言”,行文也更简明扼要:“书写词优先于口语词的倾向,对于这些不同的系统来说是否具有共性?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在表意系统中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在中国各个省都使用同一种符号,尽管这种符号的发音不同。”[2]48
一般讲,口说的语言和文字书写的语言本质上并无不同,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么只要是有成熟的文字的语言,都会有口头的语言和文字书写的语言这样两种形式,那么汉人的所谓两种语言就谈不上“在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潘先生据此认为“这两种体系在语言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1]88既不符合索绪尔的原意,也不符合语言文字的实际,是站不住脚的。
顺带还要提及的是,为潘先生的这本书作序的徐通锵先生在《序》中虽然在最后提及该书的“缺点和弱点”时说“把汉字看成汉人的‘第二语言’,其理论基础也还需要深入推敲;”但在文中却对“第二语言”说持与潘先生相同的理解,并且还进一步提出:
补充一点意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别字”。印欧系语言的文字体系只有错字,没有别字。别字,这是一个“富有中国特点”的概念。字的形、音、义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的实质就是用形义结合的理据衬托和凸显“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释名·序》)的音义结合的理据;别字抽掉了这种理据,使形、音、义三位分离,破坏了汉字作为“第二语言”的身份,……但“别字”作为汉人视汉字为“第二语言”的一种见证,我想是不容置疑的。
认为汉字的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实质是用形义结合的理据衬托和凸显音义结合的理据,其谬误在上文和以前讨论过,此不赘。不过这里徐先生提出的“别字”现象倒是反证了他说的“音义结合的理据”的不能成立。我们知道,所谓别字,就是误用音同而形义不同的字;这种现象同时也说明,同样的语音,可以与不同的语义相结合,可见音义结合具有任意性,是没有理据的。说“别字抽掉了这种理据”也不准确,因为别字所表示的本义字的形音义三位一体并未分离,也不可能分离,只是张冠李戴,用错了地方而已。“别字”的实质是汉语同音语素的误用,或者说是语素形位的错误,(注:形位是语素的区别性特征,汉语汉字和拼音文字语言皆然。关于语素形位原理,需专文讨论,这里不作展开。)不能成为汉字是“第二语言”的证据。实际上,古汉语里的“通假字”,有许多其实就是古代人使用的“别字”,习非成是,而“合法化”了。
要说语言的文字形、音、义三位一体,中外都一样。正如索绪尔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忘记,通过习惯的力量,书写的词最终要变成表义符号,这种词具有整体的价值,(独立于它所构成的字母)。我们用两种方法读:拼读出不熟悉的词和读出一见就认识的词。”[2]71为什么“一见就认识”呢?还不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缘故吗?像英语、法语这样的印欧语系语言中,也有音同而形、义不同的词或语素,只是数量上不如汉语汉字那么多,因而误用的概率要比汉语汉字小得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以上讨论,不当之处,尚祈潘文国先生及学界方家指正。
标签:索绪尔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汉字演变论文; 语义分析论文; 认知语言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汉字发展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书写系统论文; 听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