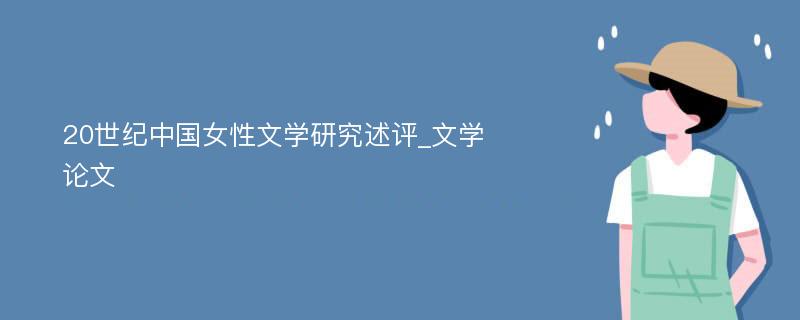
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当代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文革后”的文学视野里,女性文学无疑已是一种触目皆在的“物质”景观。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女性的“缺席”与“缄默”已成历史陈迹。女性作家的群体涌现以及性别意识在文学文本中的贯彻和张扬,构成了对男性文学以及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学传统的现实而强大的消解之势。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文学)理论的译介,以及中国知识女性在国家/社会权力结构中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的不断调整,使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研究第一次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定位。这种“定位”的划时代意义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包括文学在内的历史性的文化确证,并已经对当下的文学与文学批评造成了深刻影响。相当一批的女性学者——有的甚至调整或转换了自己原有的学术视角——表现出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积极关注与热情投入,并与为数已众的女性作家一起,携手成为在整个思想与实践领域反对将女性“他者化”(other)的先锋力量。这些学者的探索在短短的几年里便已硕果累累,她们以自己卓越的研究实绩改变着当下文学批评的话语格局。
但是,在肯定当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探索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性意义的同时,还必须指出这种探索在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偏狭与盲误,指出这种偏狭与盲误的理论根源以及对批评已经造成的和可能带来的消极、负面的影响。这非常必要,否则,就会导致女性文学主体性建构的视野障碍与方法上的重重困难。这也是写作本文的意义与任务。
性别与政治:两个文本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作为女性主义重要的文化标记并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于六十年代。但作为背景而起的女权运动则是一个具有宏大历史跨度的政治运动,它最起码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以英国妇女获得完全选举权为标志)。随着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与反越战运动的历史波澜,女性主义运动从最初的响应形式发展到最终成为一面夺目的反主流文化的时代旗帜。相应而起的女性主义理论便是对女性主义历史经验的文化反思,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则是其中重要的、必然的分蘖。
Feminism一词,在中国先后有两种译法,即“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海外有关的华人学者认为,这两种译法都存在偏颇、片面与局限性。“女性主义”太求政治色彩,容易掩去其他,而“女性主义”则性别意味过浓,无法传达“Feminism”在发展中日益加重的政治涵义。权宜之计,“女性主义”成了眼下与国际“接轨”后的通用术语。实际上,“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在译法上出现的分歧,体现的正是女性主义在批评策略上的“性别/政治”的双重设置。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主义就是一种以性别为“形构”(formation)的政治话语。六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最大的特点,可以用当时颇为流行的一句口号来概括,即“个人问题是政治问题”。这句口号提醒妇女,即使在私人生活中也存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从而引导那些一向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的广大妇女对社会、对政治加以关注。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婚姻即政治,因为婚姻就意味着统治与被统治。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女性主义就是对权力分配不平衡状态的反抗。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化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责无旁贷地将政治作为批评的第一向度。它一方面要揭示文学作为权力话语在政治上的疑点,同时也要使批评本身成为面对政治的批判话语。从这个意义引伸开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域应该兼容女性文学与男性文学,并且对文本中有无女性的存在不作追问。
女性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止的系统,相反,缺乏系统性正是它的存在方式。系统性的缺乏既导致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也导致了它的开放性。随着后现代背景的降临,解构兴趣的普遍兴起,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诸种理论在姿态开放的女性主义理论内部兼容,通过对“局限性”的解构,使女性主义呈现为多种以“差异”为前导的理论形态。这其中最引人注目,并且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最具认识与实践价值的,便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Third World Feminism)理论。
经典的西方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论(Gender Theory)为其理论起点,强调两性的社会性别(Gender)差异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根源。社会性别体制是一种不平等的二元化的社会体制,体现着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它又是一种促成或限制人的基于自己的生理范畴作出生活选择的强大的意识形态。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则对“女性”这一概念的本体性与普遍性意味表示怀疑,认为“女性”是一个意义不断被“延宕”的概念,源自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立场的西方女性主义唯本论的“女性”概念无法传达来自不同立场的妇女在经历上的深刻差异。由此,她们进一步认为,男女不平等及妇女受压迫、歧视的根源问题应该放在当今世界的权力结构中来分析。分析表明,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秩序中所处的被统治地位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是妇女受压迫和歧视的根源。社会性别体制作为一种不平等的分化人群的权力结构,虽有其独立性,但又是与其他的社会权力分配结构如阶级、民族、种族等是相互联系、浑然一体的。第三世界妇女必须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同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等多种反对压迫性社会关系的斗争联系、结合在一起。相应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任务便是研究分析第三世界妇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阶级压迫、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多种斗争的历史及其相互关联,而不仅仅是性别差异。
就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而言(半封建半殖民地,“三座大山”),中国的妇女解放就是一种多重的“解构”努力。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书写一旦进入到这样一种话语运作中,就必然会在两个基本向度上展开书写的文本形态:一是以延安时期的丁玲(与她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及萧红(与她的《呼兰河传》)为代表的对反抗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文学书写。由于是对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讲述,我将这种书写文本称为“政治文本”。二是以庐隐、冰心、凌叔华、苏青、张爱玲为代表的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话语的文学书写。因其显在的性别表征,姑可称之为“性别文本”。(丁玲是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她是两个文本的横跨者,并在两个文本中独领风骚。)这两种书写/文本,既分立又“互文”,构成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整体性景观。
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时期”,剥削阶级从权力结构中撤去,大多数的中国妇女在新的权力结构中找到了多样化的“主体位置”。但是,一种植根于家庭的父权制度仍然是妇女走向完美与自由的有形无形的枷锁。“五四”的反封建传统被割裂,国家浮躁地“跃进”了对资本主义这个虚设对手的声讨中。国家文化政策的失误,使始于“五四”的女性文学传统遭到严重破坏,女性文学部分地丧失了话语权力,最直接的后果是“性别文本”的基本缺失。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新组合的国际秩序中遭到了蛮横的打击和排挤(朝鲜战争、苏联的“围剿”、麦克马洪线之争、核威慑、冷战),就使是菡子对朝鲜战争的书写,刘真、茹志鹃对战争记忆的讲述,以及她们对社会主义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的讴歌,都具有女性意义上(不完全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合理性。“十七年”普遍地被认为是女性文学的低潮期,但在作历史清算时,不应归咎于女性作家对“政治文本”书写方式的选择。是“性别文本”的缺失造成了女性文学整体性上的“黑洞”。
“文革后”的中国女性文学书写仍然是两个文本的分流与整合。这一时期的日新月异的中国,让妇女命运也日呈斑驳的底色。一方面,城市知识女性在日渐宽松的权力秩序中开始了对“同一地平线”即平等的追逐(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主体意识空前饱满(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边缘写作也得到了权力话语的“合法化”认可。另一方面,更多的乡村妇女则仍在父权的象征秩序里“轻轻地呼吸”(蒲宁语),在相对贫乏的物质环境里无暇于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垂询;大批的女工在没有工会保护的三资企业里遭受跨国资本主义及其买办的欺辱与剥削。妇女解放的命题在中国仍然是极具差异性、层次性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仰赖于两个策略性的前提:1.缩小城乡差别;2.国家有足够的能量去解构现存的不平等的国际权力秩序。这两个前提归结起来就会指向“改革”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这说明,这个时期中国妇女面对压迫所作的解构努力,可以并且应该与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达成共识,并与之签署新的“文化协议”(protocol)。这一时期许多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一起,汇入到了“民族寓言”的写作中去。象张洁,在《方舟》中讲述不幸、受难和自我拯救这样的性别(女性)话语主题的同时,又在《沉重的翅膀》里进行“改革题材”的书写。可见,“政治文本”与作为边缘写作的“性别文本”,再次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双刃剑。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书写较之以往有什么差异的话,那便是丁玲式的双重书写已不再是个别现象。这意味着当代的女性作家对性别(女性)意识的认知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刻度,并由此迈向成熟与完满。
既分立又“互文”的双文本现象,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女性书写)的主体性内容。作为必然要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有对这一现象施以“双重关注”的义务,这才是正确的批评视野。然而,正是在对两个文本的批评姿态与价值取向上,当今的(一些?不少?许多?)女性文学研究/批评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淖。这些研究/批评一方面对性别文本在历史上总是被权力话语拆除或改写的命运进行了批判,使性别文本恢复合法性面目,另一方面,却以矫枉过正式的“报复”手段将政治文本逐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野,使政治文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暴力的清洗。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它反映了这背后的价值尺度的紊乱,反映了学术态度中非科学非历史动机的干扰,并且更为重要地反映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确定批评的主体位置和对女性意识再认识上的新的迷误。这种迷误对文学与批评自身的负面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理论的误植与批评的倾斜
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的“引言”中这样写道:
30年代以来,民族救亡与大众文学的呼声日益高涨,女作家有的走向战场有的走向乡土走向大众,笔下出现了战争硝烟,出现了“大众”这样的复合形象。在一些滞留都市的女作家那里,则艰难地保留着一份属于自己的女性体验女性话语,如白薇、沉樱、谢冰莹、赵清阁、林徽因、萧红、关露、梅娘、张秀娅等。写过《梦珂》、《莎菲女士日记》的丁玲,尽管在《莎菲日记第二部》(未完)中全盘否定了“莎菲”时期的自己,可她毕竟又在40年代初延安文艺整风前夕写出了《我在霞村的时候》、《风雨中忆萧红》、《“三八节”有感》这样的作品,仍旧成就了她那份独特的女性的敏锐和犀利。这差不多可以解释后来何以唯独在上海沦陷区才出现了《风絮》(杨绛)、《结婚十年》(苏青)、《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这样成熟的女性文学作品……[①]
这段论述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1.“女性话语”是与后方与都市与小资产阶级女性这样一个语域相关联的“娜拉”言说,因此,“走向战场走向乡土走向大众”的女性书写就应逐出“女性话语”。譬如,《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就是应该而且必须打入冷宫的,以维护和保证“女性话语”的纯洁性。2.延安特别是“整风”后的延安,是女性文学传统与发展之流的剪径者,一个冷面杀手。这样,救亡或启蒙就都是相对于妇女解放的强大的异化力量。民族沦亡于我何碍,国破山河在,不是还有租界吗?在主导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控制相对空疏的“沦陷区”、租界,书写真正“成熟的女性文学作品”,间或还可与汉奸谈婚论娶,亲演“倾城之恋”,以资题材资源的枯竭。
另一位在女性文学研究中已颇见成绩的批评者王绯,则直截了当地对“妇女意识为主导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政治意识、阶级意识)所统摄的女国民化的文学书写”,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与尖刻的贬抑。可以想见的是,“超越主导意识形态的”、“纯然女性化的文学书写”则顺理成章地被奉上了“具有普泛意义的和永恒价值的”经典性座标。(这里且不论“纯然女性化”这个模糊概念里浸渍了多少唯本的甚至是“纯然”性学的观念。)她在批判“女国民化的文学书写”时,批评丁玲在国家/政治意识的统驭下“直接书写革命者的就义和大众对革命的理解和向往”,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进一步为民族/国家意识所统驭,写出了……宣传抗日思想的作品”,“就是这样冷淡并放弃了以往创作中鲜明的女性意识和特征,消解了女性主义立场上批判的锋芒”。[②]
不仅仅是刘思谦和王绯,在批评界,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两个文本书写的倾斜性褒贬也几成共识,并且通过批评有意地强化了两个文本的对峙,拉大了它们的距离。这种倾斜性的价值取向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意,偏离了我们的批评所立足的中国立场,是必须予以阐明并进行再思考再认识的。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群体写作,大致始于二十年代。作为知识女性,她们大多出身“世家”,受过高等教育,并有留洋背景。当是时,在欧洲,女权主义运动正处在第一个高潮,国内,易卜生的《娜拉》正演得如火如荼。在这样一种中西交锲的时代语境下,女性作家很快地从娜拉那儿得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印证,并很自然地对娜拉进行了自我认同。在她们的文本中,“出走”是与一种基本欲望相一致的、针对男权秩序的解构性话语。但是,当“娜拉”们在文本空间里不断“出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祥林嫂和“芦柴棒”则因为走投无路而终至抛尸荒野。鲁迅在小说《祝福》中对祥林嫂,夏衍在报告文学《包身工》中对上海日本纱厂的女工的现实命运的揭示说明,“娜拉”只是一个限定性的指涉,因此,“娜拉”的解放(假如真能解放)并不等于妇女解放。尽管从“娜拉”立场出发的女性意识有其历史合理性与相对的独立性,但从更宽泛更现实的立场看,“女性话语”还应当兼容诸如“民族”、“阶级”、“革命”、“起义”、“战争”、“大众”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以弥补在进行批判言说时不时露出的话语“黑洞”。所以,中国现代女性书写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大革命失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的建立、阶级矛盾的激化与民族危机的爆发)就会出现分流,形成既互相区别又可互相参照的多样化的书写样式和文本形态。这当中,考察和分析丁玲文学书写的转型是很有意味,并且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莎菲”时期的丁玲的性别/主体意识较之同侪女性作家,其强烈与自觉程度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的主体/个性意识在其一生的创作中都是极为鲜明夺目的,并成为丁玲的魅力所在。很难想象,象她这样的作家会突然地、不假思索地放弃自己的个性立场,完全被动地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通道。实际上,当她进入“政治文本”书写时,正是对女性意识更为宽泛也更为完整的领域的进入。考察丁玲延安时期的作品可以发现,在丁玲那里,政治文本(《水》、《田家冲》)与性别文本(《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交替出现的,并间或在同一作品中“互文”(《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可见,对丁玲的“女性主义批判锋芒消失”的诘难是缺乏分析的,由此延伸开来的对“政治文本”的贬抑也是片面的、缺乏历史洞察的。对于丁玲及“类丁玲”的女性作家来说,书写“政治文本”,绝不是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技术性的“修辞”策略,而实在的是一种批判策略。当我们面对一些一望可知的悖谬观念和方法粗疏但易于吐纳的论述的攻击时,“保卫丁玲”就成了发自于女性主义立场的内在的、必需的口号。
在追寻造成“倾斜性”批评的理论根源时,我注意到,许多批评者公开说明自己的理论依据与理论立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这恐怕也是一段时间前唯一的理论来源。借鉴是一种普通的学术手段,无可指摘;问题的实质在于,当一些批评者获得一个批评视角后,在面对中国文学的观照中做出了削足适履的蠢举,即从西方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出发,对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出了基于性别差异的价值判断。这种片面性的判断抹煞了中国女性文学诱导因素的丰富性,使我们的批评实践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怪圈。这里特别应该考虑到的是,一些批评者由于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发展)的历史脉络缺乏必要的了解,以致于无法认清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时效性与相对于今天的历史局限性。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是被批判和扬弃的真理的原料,而不是真理本身。
这里顺便想提及的是刘慧英的新著《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在这部专著中,刘慧英通过对“女性文学批评”的概念界定而再次将丁玲及其文本作出了流放的裁决。她认为,一些男性作家对妇女生存状态的勾勒,“与出自女性手笔的《寄小读者》、《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相比显然更直接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我所划定和描述的女性文学批评的区域相对约定俗成的‘女性文学’概念既更严密(排除了女作家非妇女问题的写作)又更具松散性(接纳了男性作家或其它主题和题材的作品中有关女性问题的思考以及与此有关的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③]假定有一个文学裁判所,按这样的戒律,又不知有多少女性作家与她们的作品(除了丁玲,还有比如象池莉和《烦恼人生》、刘索拉和《你别无选择》)将因为是“非妇女问题的写作”而被判以刑期。与此同时,一些男性作家则或莫名其妙或喜出望外地直奔“女性文学”的羊圈。指出刘的理论迷误和观念荒谬尚在其次,重要的是从中发现当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概念理解与使用上存在的混乱状况。这种混乱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处在某种程度的无序的、自言自语的状态,使批评与交流时时可能出现障碍与错位。
批评的批评
由以上论述引发了下面的关于“方法”的论旨。
严格地说,任何一个文学文本,只要进入女性主义的批评视域,它就不会是“非妇女问题的”。这一方面提醒我们注意女性主义批评视域的宽度,另一方面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女性主义批评远不是开列女性作家名单和书目的“拟考古学”,即它在本质上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
雅各布斯(Mary Jacobus)指出,如果女性主义批评只针对女性作为对象的文本,可能会陷入理论上的矛盾,因为它所关注的不仅是简单的性别差异,而是“性别写作”问题。[④]文本中有无女性的存在是无须追问的。也就是说,丁玲/张爱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红玫瑰与白玫瑰》,“政治文本”/“性别文本”,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在本质上它们指的是“女性写作”。从这个层面上讲,“保卫丁玲”也是富于意义的。福科认为,批评就是要通过阅读文学文本了解分析作者置身的所在,即作者作为“陈述主体”的位置(place)以及使之获得这个位置的种种关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批评——就是要“复制”或重构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时代意识形态内容,寻找作者在种种权力结构或秩序中作为“陈述主体”的位置,倾听女性在文本中的“声音”和“语调”,以调整女性主义批评/批判的锋芒指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判断“政治文本”与“性别文本”的优劣则是毫无意义的。试想,假如“政治文本”一旦真的被逐出“女性话语”,并被从我们的批评视域中拭去(相同的情况也可以假定于“性别文本”),那么,当我们站在今天这个特定时期对中国女性文学作世纪回眸时,除了一言难尽的语言废墟以及密密麻麻的话语漏洞,还有多少“女性文学传统”可供我们去梳理、去分享和追逐呢?
同时,男性文学应该纳入(并且毫无疑问地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对象范畴,以标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域的宽度。一方面,这符合在终极意义上的“双性和谐”的文化要求。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民族寓言”的写作中男女作家所结成的精神同盟。另一方面,这有利于清楚而深刻地揭露文学的话语权力的分配秩序,揭露男权话语霸权意图及其在文本中的侵犯策略。比如,不少男性作家总是借“性”而谈“人性”(如《伏羲伏羲》、《妻妾成群》),在这个泛性的“人性论”里,最后踩着血迹获得“人性”解放的却总是男性自身。在话语的或隐或显处,女性的意义最终沦丧为“色情的能指”。遗憾的是,我们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似乎本能地、下意识地拒斥男性文学,以至于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完形填空”的工作要做。
性别/政治的双重设置是女性主义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批评策略。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其中的政治涵义也不断加重(而不是象一些批评者误以为的那样正在减弱)。但是,一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却对政治讳莫如深,有的则坦白地表露出对“政治色彩”的厌恶(这包括许多从事这方面批评的青年女学者)。这从批评者对“女权主义”(政治色彩较重的)和“女性主义”(政治色彩淡化的)的概念运用的转换上也可窥见一斑。对政治的规避,一方面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政治文本”的拒斥,另一方面,它本身作为政治话语的批判锋芒被严重挫伤。实际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是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而更主要的是作为“重写”的文本,与女性文学文本一起汇入到对从文学到文化的权力话语的解构洪流中去,并在“重写”与解构中确立批评自身的主体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认真检讨我们的批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基于自然性别区分的女性文学批评,又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女性主义立场,从而发现我们的批评成果与实际应该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尚为遥远的距离。
政治性的弱化,使得女性主义批评对女性作家的“边缘写作”持一种畸形的赞赏姿态。我将这种“边缘写作”称为“小品写作”。因为,在这种赞赏性姿态的后面,就意味着女性作家一旦涉入“重大题材”或“中心题材”的写作,就会遭到“女性主义立场消失”的责难和诘驳。换句话说,“重大题材”或“中心题材”的写作被一般性地认为是男性写作。由题材而划定写作的性别形态,其荒谬性不言自明,并已有批判在先。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西方女性作家在争取写作权利的时候,也曾遭到过男性作家基于男优女劣的性二元论而投射过来的怀疑与歧视的眼光,即使女性作家已经争得写作权并获得可观成果时,也仍然被认为只能从事较低级的文体和题材的写作。美国学者白露(Tani E.Barlow)在对“五四”文学话语作分析时尖锐地指出:“女性”是受西方男性统治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文学话语中的一个比喻,在将它引进中国话语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也巩固了这个词在达尔文进化论和蔼理斯(Havelock Ellis)性学中固有的贬义,如“女性”的被动、柔弱、智力上的无能、生理上的低能,等等。[⑤]对女性的这些歧视观念,通过男权话语被女性“内化”,并进一步衍为女性文学的审美特征,制约了女性作家对题材的自由选择。我对于“边缘写作”不持贬义,我只是警惕,源于这“边缘”的边缘的,来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内部的,对于腐朽的性二元论的男优女劣观念的无形的支持。
因此,发展一种“女性写作理论”成为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需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意识形态批评之外,同时还应该是一种美学批评,通过一种界定而凸现女性文学区别于男性文学的写作基础与美学形态。在这方面,英美特别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对我们是很有启发与借鉴意义的。比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运用精神分析与解构理论创立的被称为“描写身体”的“女性写作”理论,在肯定了拉康关于欲望与语言的依存关系的研究后,从身体快感(jouissance)的生理节奏的不同,区分了女性欲望的语言与男性欲望的语言的不同:男性的语言是“理性的、逻辑性的、等级和直线型的”,而女性的语言“是不重理性的(如果不是不理性的)、反逻辑的(如果不是不逻辑的)、反等级和回旋式的”。女性作家便运用这样的“身体语言”进行自我渲泻,或对男性的二元思维模式进行破坏。此外,吉尔伯特和库芭在《阁楼里的疯女人》里对英国十九、二十世纪女性文学中女性作家“认同和修正父权文化加之于她们的自我定义”的双重策略的梳理,也是富于启迪的。
我注意到,一些批评者已经着手于这样一件细致而扎实的工作。王绯在最近发表的《世纪之交的女性小说》中对女性小说的“意义召唤模式”的发掘和梳理,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在研究的出发点上缺乏对照(这便是将男性文学摒弃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域之外的恶果),使得这些“召唤模式”缺乏“异质性”,也就是说,这些“召唤模式”同样也适用于对男性文学的分析。
九十年代以降,女性文学在形态上更呈斑斓之色。有以陈染的《私人生活》和林白的《守望空心岁月》为代表的、与男性“代言体”相区别的“私小说”,有以徐小斌的《蜂后》《蓝毗尼城》和陈染的《纸片儿》为代表的、区别于男性写实风格的虚构性的“拟聊斋体”,有以池莉、方方为代表的跨性别外视点与女性内视点的“联网”……。所有这些都表明,刚刚翻开新土的“女性写作理论”尚有丰富的课题,以及攻克它们的任重道远的背景。
结语:补充与说明
1.关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理论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不是最近才从西方城市中产阶级那里进口来的,而是有其独立发展历史。从19世纪以来,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就作为一种重要力量,常常参加到民族的、爱国的工人农民运动中去,而不是通过组织单独的妇女组织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它认识到两性间存在着植根于家庭制度中的不平等,同时又强调妇女由于所属的种族、阶级的不同,本国殖民历史以及目前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不同而经历不同。”[⑥]归纳起来:a.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有自己的“妇女运动”背景;b.运动形式是独特的、与西方女权运动相区别的。
就中国而言,情况正是这样。
2.中国的许多女性作家如王安忆、刘索拉、张洁等,皆多次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者。我的看法,a.这些作家对待“女性主义”的认识上考虑到了自己的中国立场,而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是由于对“女性主义”的无知(王蒙),或是对女性主义心存“曲解”。b.这些作家所立足的女性立场与批评者所认可的女性立场存在很大差异。实际上,女性作家在对女性主义认知的深度上,超过了操持“女性主义”武器的批评者。这再一次提示我们,在运用西方视点观照中国(文学)的时候,切不可削足适履,终至丧失自己的立场。
3.除特别说明,本文中“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同义。为与班昭、蔡琰、李清照的“女性文学”相区别,故前缀“二十世纪”的限定词。
本文中“女性文学研究/批评”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批评”同义。时至今日,单纯基于自然性别而作的“女性文学”的区分与研究,不仅不可能,而且毫无价值,于学术无补。
4.本文不避讳极“左”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二十世纪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女性文学的程度不一的扭曲,尤其是在美学上造成的损失。当然,这只能是我另文论述的题旨。
注释:
[①] 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路历程》,第18、1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王绯:《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划时期流变》,载《钟山》杂志,1996年第1期。
[③]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第12、13页。三联书店,1995年4月版。另:从刘在此书中的具体批评运作看,她所界定的“女性文学批评”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没有区别。
[④] Mary Jacobus,“Is There a Woman in This Text?”参见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第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
[⑤] Tani Barlow,“Theorizing Woman:Funu,Guojia,Jiating in Genders”参见王政:《美国女性主义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角度》,载《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第267页。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
[⑥] 仉乃华:《妇女与发展:理论、实践与问题》,同上书,第226页。
标签:文学论文; 女性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丁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