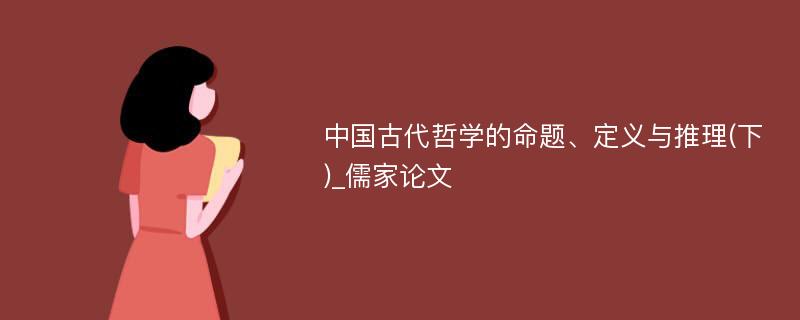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命题、定义和推理(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命题论文,哲学论文,定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中国古代推理的基础:分类
本文上篇第三节的讨论已经表明,中国古代的先哲们能够确切地理解命题,并且能够很清晰地给出命题。但他们是如何对命题进行判断的呢?进一步,他们是如何从一个命题合理地到达另一个命题的呢?显然,对于命题判断的合理性,以及由一个命题到达另一个命题的思维路径的合理性,是可以辩论的,但庄子认为,这样的辩论没有意义:
既使我与若辩矣,……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庄子·齐物论》)
庄子的这段论述与他的“齐物”的思想是一致的,或者说与他的“出世”的思想是一致的。庄子没有顾及老子的“不可名”只是认识问题的出发点这个基本理念,而把老子的“不可名”这个说法推到了极致,于是,庄子就否定了人世间一切事物的是非判断。中国人是崇古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尧是善的代表而桀是恶的代表,可是《庄子·大宗师》中却认为,与其赞誉尧而非难桀,还不如把这两个人的善恶忘却,从而归化于道。
不过,庄子的这段论述也对推理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推理的原则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强调了两条:一条是不证自明的出发点,另一条是推理过程的三段论,后来三段论就构成了演绎推理的核心。所谓的三段论是一种推理的模式,包括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著名形式是:凡人都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有死。其中,“凡人都有死”是一个清晰的出发点;“苏格拉底是人”是一个明确的命题;于是结论的成立是显然的。本文上篇第二节曾讨论过,古代中国建立了认识问题的出发点,但这些出发点并不清晰;第三节曾指出,古代中国建立了明确的定义和命题,但强调的是定义和命题的相对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推理模式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的先哲们为推理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准备工作,那就是对事物进行分类。人世间的事物是错综复杂的,要对这些错综复杂的事物进行判断和推理,一个有效的方法是把这些事物按照某种准则进行分类。如果分类清楚了,那么就可以对于一个类的事物给出判断的准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一个大范围内说不清楚的东西,在一个小的、具有某种共性的范围内就可能说清楚。我想,《墨经·小取》中的“明同异之处”和“以类取,以类予”,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①
虽然可以用各种方法对事物进行分类,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必须给出类的特性,这种特性要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共相”的功能;还要尽量做到:对于一个具体给定的事物,能够通过特性清晰地判定这个事物是否属于这个类。《墨经·经下》说:
牛与马偎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曰牛之与马不类,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
很显然,有角的动物未必就是牛,因此不能用有角的动物来定义牛,但用是否有角来区别牛和马却是恰到好处,这便是把握住了分类的特性。在这个例子中也能看到名实之争的影子:先哲们在进行名实之争、在强调“共相”或者“殊相”的时候,更底层思维的基础可能就是分类。因此,在中国古代之所以引发名实之争,很可能与分类有关,正如《墨经·经上》说:
名,达、类、私。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名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
这样,先哲们在“命名”的时候就顾及到了“类”。这与西方认识论是有所区别的,因为西方哲学强调的是具体与一般的关系,比如从马出发讨论动物,那么马就是具体,动物就是一般,由马以及其他各种具体的特性来分析动物的共性。中国哲学则更强调类与类之间的关系,从马出发讨论动物,那么马是一类动物,牛也是一类动物,可以不顾及所有动物的共性,而分析马与牛的特性之间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西方哲学重视的是共性,中国哲学重视的是差异。下面通过三个大的事情来进一步阐述这个区别:关于宗教,西方推崇的是一神教,并且希望这个理念能够得到全人类的共识;中国则可以让各类的神相安无事,并且根据特征给他们分派工作,各行其是。关于价值观,西方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并且希望得到全球的认可;中国则信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有各的活法,不可强求。关于管理,西方关注工商、行政、教育等各个行业内部的共性,即行业内部规律性的东西;中国则更关注行业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给出诸如级别这样的尺度来构建行业之间的桥梁。因此,西方更重视一般和特殊之间的关系,中国则更重视类与类之间的关系。
这种分类的思想是源远流长的,至少可以追寻到商末周初,因为学者们普遍认为《易经》从那个时代就开始已经有了。就思想方法而言,《易经》的本质是对世间的事物进行分类,共分64个类,称其为卦;每一个卦又分6种情况,称其为爻。它对于不同的类用不同的符号表示,用连线表示阳,用短线表示阴,阴阳6次组合正好形成64个不同的符号。“易”是变的意思,因此《易经》强调的是变化之道。阳也代表男性、积极、强势;阴也代表女性、消极、弱势。阴阳之说认为强势不可能永远强,发展到一定程度要逐渐变弱;同样,弱也可能逐渐由弱变强。太极图就表现了阴阳之间或强弱之间的变化,变化的结果就产生了万物。这样,针对某一个具体事物,根据烧甲骨出现的裂纹或者抽得草茎的奇偶数,把这个事物分派到某一类中去,然后依据《易经》中对这类事物的论述,给出这一个具体事物的解释或者预测。事实上,《周易·系辞》开宗明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说的可能就是这个道理。
中医的治疗理论可以很好地体现中国古代的思想方法。我想,中医治疗理论的核心就是分类。中医治疗有一句行话叫做“辨证施治”。就是说,中医不是根据“病”来施治,而是根据“证”来施治。证就是由一些病所组成的类。首先,中医把病的症状分类,称之为症候,并且依据五脏来命名,比如胃热、肝热等等。胃热并不是说“胃”热了,胃热是一类大概与胃有关系的症候的名,症状大体是:口臭口干、口腔糜烂、牙周肿痛;肝热也并不是说“肝”热了,而是指另一类症候,表现为:烦闷口苦、发热便黄、狂躁不安。然后,根据这些分了类的外在表现,再根据望、闻、问、切这四诊,辨别出证型,这样治疗的方略就基本定型了。最后,参照季节、地域、患者身体状况,决定治疗办法。很显然,其中的关键是确定证型,而“证型”就是从一些具有某种关联的病的共性中抽象出来的类。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情况下中医的方法应当比西医的方法更好一些,因为许多疾病往往是由许多原因引起的,而中医“辨证施治”强调的就是综合治疗,这显然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科学得多。当然,前提是分类必须准确。
中国古代是如此地重视分类,甚至把类还分出了等级。《墨经·经上》说:
同,重、体、合、类。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
这表明,针对共相本身,中国古代先哲的分析要比古希腊学者的分析更加精细。事实上,这种精细正是为了分类的需要,希望分类更加准确。
分类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强调“同”,也是为了分辨“异”。为了更好地讨论中国哲学中的分类,需要创造一个新的哲学名词“异相”,这是指分辨两个类不同的最明显的特性,比如前面引用《墨经》中所谈到的用“有角”来分辨马和牛,其中“有角”就是异相。本节开始曾引述了庄子关于“辩无胜”的说法,可是,如果讨论的是一个命题,即一个关于是非的判断,那么必然有一方是胜的,正如《墨经·经下》所说:“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这样,墨子不仅很清晰地解释了命题的实质,也说出了形式逻辑中三个基本定律之一的矛盾律的核心:一个命题的“是”与“非”不能同时成立。
对于“同”和“异”之间的关系,墨子还有更为明确的论述:“同异交得放有无。”(《墨经·经上》)。在《墨经·经上》中还对“异”划分了等级:“异:二、不体、不合、不类。二必异,二也;不连属,不体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类也。”
这与上文中所阐述的“同”是对应的。具体地说,例如:精神与物质是完全对立的,为“二”;不同国籍的人无隶属关系,为“不体”;甲和乙不在一个公司上班,为“不合”;人与岩石无共性,为“不类”。
这样,先哲们从同和异、彼和此的关系,把分类阐述得清清楚楚。那么,分类所依赖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什么呢?进一步,在分类的基础上如何进行推理呢?
五、分类的思维基础:归纳和类比
首先描述一下通常所说的归纳,也就是在上篇前言中引用的爱因斯坦的那段话中所提到的、西方文艺复兴以后所倡导的归纳:如果发现一个类的内部的个别元素具有某个性质,于是推测这个类中的所有元素都具有这个性质。
这里所说的归纳必须首先存在一个类,然后在这个类的基础上使用归纳的方法。事实上,这种归纳方法对于处理“物与物”之间的事物是合适的,但对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就不充分了,因为对于人世间的许多错综复杂的事物,分类本身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要在一个已经确定了的类中进行判断和推理。因此,对于人世间的许多事物,在构建类的过程中就可能要用到归纳;也就是说,这时的归纳并不局限于分类以后,也可以使用于分类的过程中。这可能就是《墨经·小取》中所说的“效”或“效法”。这种包括在构建类的过程中使用的归纳在内的归纳方法,可以称为广义归纳。② 换言之,西方所说的归纳的核心是:把一些具体的特性推广到更大的范围,甚至推广到一般,其中所说的更大的范围是确定的;我这里所说的广义归纳不仅如此,它还包括这样一种思维过程:凭借经验和直观,先得到一个大概的类,然后在这个大概的类中寻找“同”,最后根据“同”进行更准确的分类,很可能这个“类”最终也是不确定的。我想,扩大归纳方法的外延对于分析中国的方法论是必要的,因为,西方所说的归纳方法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强调的是从类中归纳出性质,从而得到命题,比如一些猜想;而中国所说的归纳方法主要是针对人文科学,因为问题错综复杂,所以要强调借助性质归纳出类,从而得到这个类与其他类之间的区别。
现在进一步分析先哲们的思考。为了阐述的连贯,这里把《墨经·经下》中分开的三段话连在一起表述:
分类的难点在于判断类的大小。比如讨论四条腿的动物,可以涉及牲畜,可以涉及到鸟,还可以涉及到物以及其他,有的类就大了,有的类就小了。
不同的类是不能比的,因为量纲不同。比如,如何比较木头与黑夜哪一个更长?
认为仁和义有内外之分是不对的,因为这违背了分类的原则。仁是爱人,义是利入。无论是爱人还是利人都是“内”,只有获爱者和获利者才是“外”。因此,爱人与利人之间无内外,获爱者和获利者之间也无内外。③
从上面的表述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先哲们在进行分类的过程中用到了归纳的方法,也就是我所说的广义归纳;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对于人世间问题的分类是需要特别仔细的。
最有说服力的还是中医理论。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可分析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伤寒论》这部书不仅为诊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也为中医临床提供了辨证施治的原则,被后世医家奉为经典。《伤寒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把病症由浅入深归纳为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六种,事实上就是病证的六个大类;还把疾病属性归纳为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以六经为统领,与患者的症候所属的类组合,就可以进行辨证、进而施治。据说张仲景曾经苦读《黄帝内经》,“伤寒”一词可能出于《素问》:“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这样就可以推断《伤寒论》的渊源是战国时期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而《黄帝内经》又相传是始于黄帝时期的治病和养生的方法,从而《伤寒论》的医疗理论和397法、113种处方至少是基于一千年以上中医临床经验的结果。更有说服力的是,《伤寒论》中提到的经穴、针灸是中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治疗方法:针灸必须针对经穴;可是至今人们仍然找不到一种可视性的测量工具或解剖方法来解释什么是经穴,甚至解释不清楚经穴是如何存在的,因此可以推断,在那个时代只能凭借经验判定经穴,然后用归纳的方法把经穴归类,用于治疗。
从古代开始,先是阴阳、然后是阴阳五行之说就在中国广为流行,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在做事的时候,往往都把阴阳五行中的说法作为准则,进行“是非判断”或者“是否判定”。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阴阳家是邹衍,而他分析问题的方法就是归纳,因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他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据说,邹衍曾把这种方法用于推演王朝的更迭:土德王的黄帝被木德王的夏“克”,后者被金德王的商“克”,再后者又被火德王的周“克”,而后者将被水德王的朝代所“克”,周而复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为了对应这个原则,秦始皇曾将黄河改名为“德水”。到了汉代以后,阴阳五行的学说更是流行,甚至影响到今天。这里不想更多地讨论阴阳五行的问题,我只是想说明,就思想方法而言,邹衍讨论问题的方法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所倡导的归纳方法是一致的,当然邹衍并没有对这种思想方法本身进行归纳。
还有一种与归纳关系非常密切的、也是建立在类的基础之上的思维过程叫做类比。先描述通常所说的西方文艺复兴以后所倡导的类比:对于甲、乙两个类,乙类中的事物与甲类中的事物有一些共性,因而如果发现甲类中的事物具有某种性质,就可以推测乙类中的事物也具有这种性质。③ 比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要调查研究,他在许多场合强调要学会解剖麻雀,因为“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参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8页)他的意思是说,如果甲乙两地情况差不多,那么在甲地发现的规律性的东西,可以用来推测在乙地或者更广的范围内也可能成立。毛泽东的这个思维模式就是类比。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国古代是广为采纳的,比如《老子》第八章用“上善若水”来解释“善”: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不争,故无尤。
与归纳类似,中国古代所使用的类比与上面所描述的类比也是有所区别的。西方所倡导的类比首先要求两个类是存在的,并且对其中一个类的特性是清楚的,然后推测另一个类也具有这个特性。而中国古代则也把类比用于分类的过程,也就是说最初大概知道有两个类,而在这两个类的比较过程中逐渐归纳出特性,甚至不进行比较就表述不清楚这些特性。当然,这也是为了描述人文科学的需要,这可能就是《墨经·小取》中所说的“援”,或者说“援引”。现在分析老子关于“上善若水”的解释。首先,老子建立了一个命题:水最接近于道。前文曾经说过,道是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因此最接近于道就是好的。也就是说,像水那样就是好的。如果遵循通常所说的类比思路,应当先讨论水的特性,然后类比于人。可是在上述引文中,老子所说的特性完全是“上善之人”所应当具备的特性,当然,从中我们能够感悟到水也具备这些特性。这样,老子就在类比的过程中把两个类的共同的特性归纳出来了。如果仔细分析中国古代的文献,可以发现许多论述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必须强调的是,通常所说的那种类比方法在中国古代也是广为使用的,这种思维的方法被《墨经·经下》描述为:“从一个类的已知可以扩展到两个类的已知,关键在于比较。……在描述事物时,应当用已知来推测未知,而不能用未知来猜测已知,这就好比用已知的尺来度量未知的长度。”④
进一步,《墨经》利用这种思维方式建立了动态的分类过程:“在进行分类时,可以把事物归为一个大类,也可以分为若干小类,关键是依据统一的共性,还是依据各自的特性。比如计算牛和马的数量,如果关注统一的共性,那么牛和马可以归为一类,称之为四条腿的动物,统一计数;如果关注各自的特性,那么牛和马就是两类,分别计数”。⑤
这样,凭借经验和直观,中国古代已经娴熟地掌握了分类的方法。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先哲们在分类的过程中使用了归纳的方法和类比的方法,并且是动态地使用这些方法。而恰恰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方法,针对个人修养或者人文科学的许多问题,分类之后判断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比如,如果认为某一个人的作为可以归于“仁”的类,那么这个人本身就已经得到了肯定。因此我想,《墨经·小取》中的“以类取,以类与”所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
六、基于分类的论理准则:正名和中庸
众所周之,儒学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那么,这个思维方式是什么呢?前面已经讨论,先哲们思维的习惯是把错综复杂的问题归类,然后从出发点开始分类研究;这个出发点是道,也可能是仁。如果这个立论是成立的,那么现在需要讨论基于分类的思维方法,或者说基于分类的论理准则。这个论理准则首先是:正名。
在《论语·子路》中记载,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君请先生治理国家,先生首先做什么?孔子回答得非常简洁:正名。然后说出了下面一段几乎是人人皆知的理由: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那么,孔子所说的“正名”是什么意思呢?本文上篇第三节曾讨论过,在中国古代,“名”是指定义中的谓词,也就是共相。按照一般的逻辑规范,“名”是从“物”中抽象出来的。也就是说,共相是从许多殊相中抽象出来的具有共性的东西,因此,必然是先有物或者殊相。但是,在中国古代并不是这样的,而是遵循着一个几乎相反的逻辑思路:先给出一个出发点,继而根据分类指出这个出发点在这个类中的名是什么,然后“正名”:要求这个类的元素都达到名的述说;如果达不到,就可以被划入“另类”。我想强调的是,这个思维过程对于人文科学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比如,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在这个命题中,出发点是“道”,讨论的“类”是关于制作礼乐和发动战争的权利,“名”是权利出自天子。那么,孔子的“正名”就是要求凡是涉及“制作礼乐和发动战争的权利”的事情,必须按照名的述说“出自天子”,否则就是没有正名,就是无道。因此,孔子的“正名”是要求实符合名,也就是不能有名无实。可以看到,在《论语》中基本采用的是这样的论理方法。再比如“仁”是孔子的出发点,虽然孔子并没有给出仁的一般定义,但对于“个人作为”这个类中的仁,《论语·学而》中以孔子的学生有子之口说: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或许,上面的论述就是中国古代的有些朝代“以孝治天下”的根基。其中,“孝”是指孝敬父母,“弟”是指尊敬兄长。这段文字是典型的“类”内部的推理,推理得到结论是孝弟是仁之本,但这个本只是针对“个人作为”这个类而言的。因为,颜回问孔子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这时所谈的仁是针对“众人作为”这个类而言的。进一步,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显然,这是孔子对“施政作为”这个类所说的仁。这样,作为出发点而模糊不清的“仁”,一旦成为具体类的“名”的时候,就可以表达清楚了。正因为“仁”是不需要述说、不需要争辩的出发点,就可以通过“正名”的方式来要求这个类中的“物”必须符合“名”。我想,这可能就是儒学论理的基本方式。
在“道”和“仁”的基础上,孟子又提出了“人性善”这个出发点。虽然孟子强调人性善,但他更强调保持这个善是需要教育的,其中重要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关于伦理,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解释到: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善在“人间伦理”这个类中的“名”,并且认为做到了就符合伦理,否则无伦理。因为,孟子认真地论述了把“善”作为出发点的理由,他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
人皆有不忍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孟子的论述是斩钉截铁的。孟子称其中的仁、义、礼、智为“四端”,到了汉代又被儒家后学加上信,成为“五常”,意味着这些是人应当具备的、不变的五种德性。但是,正如老子所说的,如果一个出发点是可以述说的,那么这个出发点就是具体的。(参见《老子今译》,第51页)显然,一个具体的出发点是可以争辩的。
同样作为儒学先哲的荀子提出的出发点是“人性恶”,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说法。现代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这个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类DNA所携带的信息本身可能就是“自私”的。(参见琼斯,第170-173页)事实上,无论孟子的论述还是荀子的论述,都是基于“道”和“仁”,因此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人必须经过努力才能达到仁、感悟道。他在《荀子·性恶》中说:
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
同孟子一样,荀子的出发点也是具体的,因此是可以争辩的。很显然,依据荀子“人性恶”的观点就更要强化“正名”的作用。荀子下面的一段话说出了“正名”的真谛:“圣王制名,是为了用名的定义来辨别事物,用名的道理来统一意志,……如今没有了圣王,人们懈怠了对名的遵守,于是奇谈出现、名实混淆、是非不辨,……如果有了新的圣王,一定会沿用旧名,制作新名。……所以明智的人为了分别事物,制定名来表示实,于是上可以明确贵贱,下可以辨别同异。明确了贵贱、辨别了同异,就不会因为话语不同而不能沟通,也不会因为表达不明而事不能成,这就是之所以要有名的理由。”⑦
总结孔子、孟子和荀子所说的名,可以知道他们所说的名是具体的名,是一类事物的名。虽然他们说这个名是圣王制定的,但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是他们凭借经验和直观⑧,归纳他们所认为的圣王的作为,为各类事物而制作的。因此,名这个共相是、但又不完全是从这个类中的殊相中抽象出来的。他们所说的名还同时起到了对于类中事物的“是否判断”和“是非评价”的作用。这样,先哲们所说的“正名”就是对类中事物的要求,这与前文所做的分析是一致的。
除了正名之外,先哲们基于分类进行的论理至少还有一个准则,这便是中庸。从字面解释,“中”就是恰到好处,“庸”就是普通平常。朱熹编撰的《四书集注》的《中庸章句》,前半部分主要论述中庸之道,记载了许多孔子的话,其中谈到: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朱熹,2004年,第23-24页)
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中庸之道的核心。从中可以知道,中庸是针对一类事物而言的,不同类事物有不同类事物的中庸标准,这正如朱熹在《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三中解释《中庸》时所说:事事物物上各有个自然道理,便是中庸。(参见同上,1986年,第1528页)因此,通过中庸在某一类事物中得到了位于中间的参照标准,这个标准就可以作为对这类事物是否或者是非的基本判断标准:超过了这个标准就是过分,低于这个标准就是不及。事实上,几乎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说法:“由此可以断言,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美德。……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亚里士多德,1106a-1107a)
这样,至少是儒学的先哲们就从出发点开始,通过正名和中庸,在类的基础上建立了判断准则,因而建立了推理准则。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几乎渗透到了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思考或者判断一件事物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想到类,想到这个类的名,想到这个名下的规范。虽然思维方式的运用是因人而异的,但人是社会的人,社会生活中无形的契约会迫使人遵循那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包括对事物的判断和推理。
可以看到,上述思维方式是非常人文的,对于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仅仅依赖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现代社会的许多事情必须逐渐走向确定性,因此,近代中国大量地吸收了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是,这两种思维方式是各有所长的,对任何一个都不应当武断地排斥,而是应当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作为文章的结尾,我想再谈一下分类的思想方法。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都遇到了新的难题,就是要处理大量的信息,人们称之为海量数据。因为海量数据的复杂性,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模型来进行刻画,于是人们就想到了利用特性对数据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因此,在未来的方法论中,分类的思想将可能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关心具体与一般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也要关心类与类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注释:
①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以类取,以类予”是两个重要的方法,相当于西方逻辑学中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冯友兰,第106页)这个说法有些牵强,大概是不确切的。
② 穆勒在《逻辑体系》中说:归纳法是从发生了某种现象的个别事例,推断与之类似的某类事物的所有事例也将发生这种现象。(转引自胡适,第126页)我所说的广义归纳与胡适所分析的中国古代的归纳法(参见胡适,第4章)有很大区别。
③ 原文为:“推类之难,说在大小。谓四足兽,与生、鸟;与物,尽与。大小也。”“异类不比,说在量。木与夜孰长?”“仁义之为外内也,罔。说在仵类。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内外。”
④ 几何学中的许多猜想都来源于类比,比如庞加莱猜想:因为把三维空间中球的表面上任意一个封闭的曲线逐渐收缩,最后能够归于一点,于是猜想,四维空间中的球也具有这个性质。因为就我们的感官而言,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四维空间,于是人们就模仿三维空间的情况,定义了四维空间的球。在2005年,人们证明了这个猜想。
⑤ 原文为:“闻所不知若所知,则两知之,说在告。……夫名,以所明正所不知,不以所不知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知长。”
⑥ 见《墨经·经下》,原文为:“区物:一、体也。说在俱一、惟是。俱一,若牛马四足。惟是,当牛、马。数牛、数马,则牛马二。数牛马,则牛马一。”
⑦ 原文为:“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
⑧ 《荀子·正名》中详细地说明:“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同其约名以相期也。”
标签:儒家论文; 中国古代哲学论文;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共性与个性论文; 推理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伤寒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