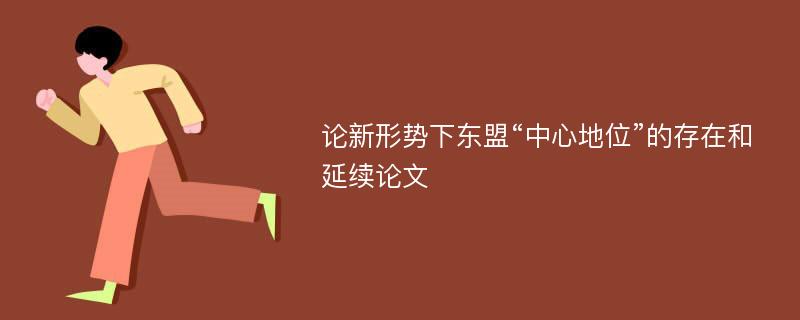
[东南亚研究]
论新形势下东盟“中心地位”的存在和延续
陈子恒
(暨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与区域合作进程中,东盟始终坚持并维护其“中心地位”,这既是东盟根据自身发展状况“量体裁衣”的结果,也是对其所处国际环境综合分析后的产物。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世界大势趋缓,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逆全球化”事件频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盟在谋求“东盟共同体”建设和区域一体化道路上的决心和意志;美国等域外大国加大介入东南亚地区的力道,东盟的团结也可能因为大国的分化变得岌岌可危;此外,东南亚内部矛盾也日益浮现,其中既有因内部差异和东盟决策机制衍生而来的内忧,又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民粹主义等外患,内忧外患相互交织,冲击了东盟进一步整合的进程。种种变化,既是摆在东盟追求独立性和自主权道路上的挑战,也为东盟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继续保有“中心地位”设置新障碍。
关键词: 东南亚;新形势;东盟“中心地位”
一、相关概念辨析
所谓东盟“中心地位”,指的是东盟为在东南亚乃至东亚区域一体化及合作进程当中维护其自主性和整体性,承担的“主导者”角色,这种角色不涉及绝对实力的高低,更多的是对东盟在区域合作里居中穿梭、主导议题、制定规则的功能的指代。这一地位的获得,既是东盟为了极大化自身利益刻意争取,也是由于区域内具备领导区域合作实力的国家,囿于合作观念的差异或相互关系的不确定,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关于东盟“中心地位”,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
第一,东盟所拥有的“中心地位”,和东盟的实力高低与规模大小并没有直接关联。 Marty Natalegawa认为,“东盟中心地位是通过其智力领导力、参与并充当平衡制定者的能力赢得的”[1]。国内学者也有相似的观点,“东盟所获得的主要是一种功能性中心地位,即东盟在东亚中发挥的主要是一个合作平台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一种功能性权利。”[2]第二,东盟“中心地位”不是东盟一厢情愿的“创作”。“比起东盟内部的团结和一致性,域外国家特别是中美等大国认可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获得助益更大。”[3]第三,东盟“中心地位”是对外的而非对内。指的是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对外交往及区域合作中发挥的作用,而非内部成员国要以东盟整体利益为中心,让渡、牺牲独立国家的部分权力。第四,东盟维持其“中心地位”的目的是保守而非主动的。与法德主导欧洲合作、美国主导北美一体化不同,东盟在本地区的合作进程中扮演的主导角色,更多的是为保障本身在区域合作进程中作为中小国家联盟的主体性、独立性与能见度,政治、经济的收益次之。[4]
二、东盟“中心地位”的形成
东盟的“中心地位”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长期的区域合作进程中,多方面原因形塑的结果。
就内部而言,东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累积了相当的实力,支撑起了东盟主导地区事务的目标。截至2017年,东盟已经发展成一个由10个成员国组成、拥有6.42亿人口、GDP总量排名世界第6的区域性国家联盟① 资料来源:东盟2018年统计年鉴:https://www.aseanstats.org/wpcontent/uploads/2018/12/asyb-2018.pdf 。除此之外,东盟还主导并创立了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10+3”、东盟“10+1”以及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会议和框架,涉及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领域,作为其影响力的拓展和补充。通过推进一体化进程,东盟促进了内部成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巩固了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2003年10月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之前,东盟的一体化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即通过自贸区的建立,推动了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的水平;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之后,发表的《东盟第二协约宣言》,宣布将于2020年建成以“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支柱的东盟共同体,表明东盟的一体化进入更高水平,这一目标在随后的2015年11月东盟第27次领导人会议上宣布提前达成,标志着东盟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好地发挥成员国的合力,在区域合作中施展拳脚。
没有坚强的实力作为基础,决定了东盟只有施行“大国平衡战略”,即在不排除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利用各大国的优势、它们间的矛盾及对权力的追求,主动与其发展政治、经济、安全等全方位关系;同时,防止任何大国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实现东南亚地区的势力均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12]才有办法在激烈的大国争斗中争取足够的生存空间,实现独立自主。
“让别人觉得舒服,是最好的修养。”这句话放在任何年代都不过时,生活中有许多人却总想靠踩别人去赢得自己的自尊。有位朋友的儿子进了外企,薪水不菲,每逢亲友聚会,他就会大谈如今物价高,月薪万儿八千的人活得生不如死。接着便掰着手指头,津津有味地计算他儿子扣除五险一金、所得税,还有多少多少。在座的月薪大多不过四五千,都在“生不如死”之列,当然越听越心烦。可那位老兄浑然不觉,依旧不停地“嘚嘚”,可想而知多招人厌。
总体来看,东盟实力的增强为其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扮演主导者角色提供动能,近20年因其“中心地位”而获得的实实在在的红利,也让东盟继续保有作为区域合作主导者的意愿。但是,东盟“中心地位”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东亚地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这也决定了东盟“中心地位”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和脆弱性。
(5) 模型单元选择。为使模型能够尽量反映实际结构的受荷特性,结合ABAQUS有限元软件中相应单元特点[14-15],在模型中主要涉及了两种单元:
三、东盟“中心地位”面临的挑战
东盟能够长期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维持“中心地位”,主要归结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存在事实,这是东盟“中心地位”的先决条件,二是东盟主导东南亚乃至亚太区域合作的意愿,以及东盟整体实力和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三是域外大国在认可东盟“中心地位”的前提下,参与到区域合作进程中,三者缺一不可。
按照检索的时间范围及内容范围,该文共获取42篇相关论文。按文章发表的时间,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对象进行分类统计后,得出以下结论:
不过,在次贷危机之后,亚太地区原本的权力结构日益松动,东南亚的安全格局进入新的整合和变动阶段,给东盟“中心地位”的维持带来了新的变数。首先,各方力量比对瞬息万变,排列组合的可能性各式各样,使得东南亚安全格局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骤升;其次,作为战略要冲,中美两国对东南亚都势在必得,并纷纷加大在本地区的干涉力道,东南亚各国被迫“选边站”,身陷“两大之间难为小”的窘境的同时,东盟的团结也备受挑战;最后,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威胁不断涌现,也让东南亚地区的形势雪上加霜。在外部环境恶化、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东盟能否继续保有“中心地位”仍是未知数。
(一)世界整体氛围的改变,冲击东盟稳步发展的进程。
东盟之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积极筹划区域一体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时的世界潮流。马哈蒂尔提出“东亚共同市场”构想时曾指出:“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经济集团,并利用它们的经济力量阻挠公平与自由的贸易。这本是一种不健康的趋势,而马来西亚向来也反对建立经济集团的做法,但大势所趋,马来西亚只好改变政策奉陪到底。”[5]如今世界趋势丕变,东盟稳步发展的进程必然也要遭受波及。“反全球化”的火苗越烧越旺,甚至延烧到东南亚。2016年6月份,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脱欧派”以微弱的优势取胜,重挫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尔后,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对全球化进行大肆抨击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成功当选,并在当选后兑现系列选举支票,包括立即签署行政命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此同时,随着这股“逆流”而来的民粹主义、反精英主义也愈发盛行,从2006年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的“街头对峙”,到2014年印尼佐科和2016年菲律宾杜特尔特两位草根总统当选总统,都是印证。而依靠民粹主义获得权力的政治人物为了巩固实力,势必会将更多精力集中到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内政治斗争,降低对“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兴趣、减少对东盟一体化建设的投入。[6]除此之外,国际安全形势更加严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在全球迅速蔓延,并逐渐向东南亚渗透。域内外恐怖势力交织、合流、共振和滋生出的新的恐怖活动,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最严重的安全威胁。[7]加之恐怖主义外溢性、隐蔽性和突发性等特点,对东盟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和区域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东盟迈向“政治与安全共同体”、实现更高程度一体化的一大考验。
(二)域外大国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干涉力道,冲击东盟的“中心地位”
曹云华认为:“美国的战略家们看来,东亚的团结,将会很大程度上损害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因此美国人最不乐见这种情况出现。”[8]美国在东亚一体化议题上一向戴着有色眼镜,在2004年8月,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 L.Powell)在谈到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时表示,美国不认为有此必要。他还警告说,虽然主权国家有这样做的自由,但它们的行动不应损害美国同亚洲朋友间的“良好而牢固的关系”① Colin L.Powell,“Roundtable with Japanese Journalists”,Washington,DC August 12, 2004,http://www.state.gov/secretary/former/powell/remarks/35204.htm,转引自吴心伯.美国与东亚一体化,http://www.tecn.cn/data/18243.html. 这一言论反映了美国对于东亚地区谋求地区一体化的警惕。此后,美国为了遏止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维持自己的霸权,加大了介入东南亚的力道。在2011年宣布“重返亚太”后,多管齐下,积极展开在东南亚的布局。外交上,美国在巩固与强化同日本、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关系的同时,也主动对印度、越南等国进行拉拢;安全上,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挑拨南海周边国家和中国的关系的同时,屡次在南海展开军事演习,并以“航行自由”为由,不断加强在东南亚、尤其是南海周边的军事部署。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大体上延续了奥巴马时期的对外战略,目的在于维持美国在亚太和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不同的是,特朗普的对外战略更注重实用主义,表现为不再扮演“义务警察”的角色,不再一昧为“ 自由和民主”价值情义相挺,更倾向通过鼓励其盟友在区域稳定中承担更大责任,降低美国负担的同时,维持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上台后一系列充满反复性和不确定性做法,也给东南亚未来局势埋下不稳定因素。
中国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后,累积了一定的实力,为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影响力,着力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寻求增强在本地区的话语权。为此,中国做了以下努力:第一,以经促政,通过加深经贸合作,稳步深化中国-东盟战略关系。随着中国产业升级的推进和世界产业链的转移,中国和东盟的经济互补性越来越强,两地的经贸合作大有前景。截至2017年,中国和东盟贸易额达5148.2亿美元,累计双向投资总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7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②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 第二,积极、全方位地参与东盟倡议的一系列区域组织和架构。中国积极参加包括10+(1东盟10个成员与单个大国的自由贸易谈判)、10+(3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和东亚峰会(目前也称10+6)在内的系列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通过切实参与、对等合作,彰显作为和平的地区大国的同时,努力消除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恐惧。第三,通过战略对接,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中国与东盟在谋求经济发展、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双方都致力于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达成谈判,同意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提出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共同的重点领域对接,并努力以互利共赢的方式,促进区域各互联互通战略的对接。虽然中国一向尊重且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并积极参与到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进程当中,但随着中国和东盟国家各方面合作的深入,使得东盟各国在执行政策时难免分心考虑“中国因素”,不自觉削弱东盟的整体性。
(3)学生实习教学必须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特点,紧密联系行业企业,与企业合作建设实训基地,共同开发实训课题,共同制定完善的与人才培养方案匹配的生产性实习课程标准,共同制定学生实习质量监控管理与评价办法,有效保障实习的质量。
(三)东盟内部的多样性,阻碍东盟进一步整合
新的形势下,东盟既遭逢联盟内部团结生变的风险,又濒临域外国家介入和分化的挑战,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东盟能否经受住考验,维持在区域合作进程当中的“中心地位”,看似前景黯淡,实则不然。
四、东盟维持“中心地位”的路径选择
在长期与大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东盟各国体认到,仅仅依靠单一国家的力量,很难在复杂多变的地区局势中站稳脚跟,只有深化团结与合作,树立“东盟中心”意识,建立以东盟为主导的地区协调机制,统一的发出“东盟声音”,才有可能摆脱现实主义下“操之不在我”的小国悲情。在中美对抗加剧的新形势下,东盟必须做出调整,弥补政治权力和整体规模上的不足,加固在区域合作进程当中的中心地位。
(一)深化和拓宽区域合作,巩固东盟“中心地位”
推动区域合作制度化和专业化。尽管东南亚地区的合作进程错综复杂、相互重叠,但东盟不应将政治、经济和安全的议题放置在一个单一论机制上进行讨论,相反,维护东盟在本地区面临的不同类型挑战时,使用更多元的区域架构疏解矛盾将更有利于东盟在新形势下维持“中心地位”。首先,专业化的区域合作制度解决了域外国家参与本地区事务的合法性问题,并且将纳入或排除某一国家参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决定权握在东盟手中;其次,区域机制的多元化,有利于分散大国为争夺本地区影响力和领导地位而给东盟国家带来的压力,缓和东南亚紧张局势;最后,高度专业化的区域组织架构意味着专业人员、学者在这些组织中的存在,而专业知识通常能为国际组织带来“专家式权威”(expert authority)[10],成为东盟权威的建构重要一环。
切实推动合作方式的变革。本地区既有合作现实的存在,有赖于以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通过非正式协商来达成全体一致和注重各方舒适度的“东盟方式”。在过去几十年中,“东盟方式”以区域合作而非区域治理来实现区域的利益聚合,以共识而非强制来推进合作进程,[11]帮助本地区各国在区域合作中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为东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进程的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果立下大功。但在新的形势下,原本的“东盟方式”因为照顾各方舒适度,很难有效应对新时期的危机和矛盾,切实推进区域合作方式的改革势在必行。一方面,需要重视“东盟方式”的约束力和执行力,强化东盟的权威。另一方面,既需重视区域合作的“过程”,也需拿出更实际的合作成果,改变外界过去对东盟主导的区域架构“清谈馆”的印象。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东盟已经初步建构起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作为东盟“中心地位”的制度性保障。在新的形势下,大国的倾轧和内部的矛盾让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继续保有“中心地位”陷入危机的同时,也为其进一步重构区域安全机制带来新的契机。
其他域外国家加强在东南亚的存在,使东南亚的局势更加复杂化。曹云华认为,东南亚地区正在发生的权力转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转移不是单纯地美国向中国转移,而是向多个地区大国包括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俄罗斯转移。[9]这种权力转移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但不会停止,还会加快。这一局面的出现,既是美国为防止中国在东南亚一家独大,刻意地促成的结果,也是各国在美国淡出东南亚地区、留下权力真空后,为追求经济或政治利益有意为之。
随着喹诺酮类药物在临床以及养殖畜牧业中的广泛使用,细菌对该类药物的耐药率逐年攀升[8-9]。本研究中,无论是ICU还是普通病房,大肠埃希菌对喹诺酮类抗生素均有较高的耐药率,与文献[10-11]报道相似。ICU中分离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呋喃妥因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均显著高于普通病房。因此临床应根据监测结果慎重选择抗菌药物,对于有ESBLs高危因素的患者或重症感染患者,应及时使用碳青霉烯类药物。
(二)继续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反哺东盟“中心地位”
就外部而言,东盟“中心地位”得以成立的另一条件之一,是域外大国承认东盟在区域合作框架中的“中心地位”,并在这一前提下,参与到这一合作进程中来。尽管东盟的整体实力上了一个台阶,但仍不足以独自主导区域合作框架的建立。因此,域外大国的认可就成了东盟“中心地位”的重要保障。就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而言,在本区域内最有资格担任领导的是中国和日本,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由中国或日本领导的区域合作并没有成局,在中日均难以凭一己之力主导东亚局势,又希望借着区域整合拉动本国发展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接受以东盟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区域合作机制。美国一向不乐见东亚进一步整合,并对此进行百般阻挠。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后,受欧洲和北美一体化影响,东亚各国为寻求更高效的发展,开始积极筹划东亚区域的整合,美国见这一进程无法扭转,只能转而支持对自己的霸权构不成威胁的东盟。
主动利用大国矛盾增进东盟利益。冷战后,东盟对待大国的策略实现了从被动依赖到主动平衡的转换,亚太地区几个大国间斗而不破的战略平衡,是这一转换的重要前提。作为一个弱小国家的联盟,却在多个地区合作机制中占据主导地位,美日对此颇有微词,提出双主席制的设想,即由东盟成员国和非东盟成员国共同主持论坛部长会议。[13]对于这一提议,东盟利用中国对美、日的不信任感提出反对,从而维护了东盟的主导权。通过在美、中、日等大国之间不断游走,不过分亲近某一方的“等距离外交”,东盟实现独立自主初衷的同时,凸显了在本地区的“驾驶员”作用,进而反哺了东盟的“中心地位”。
通过制度制衡域外国家。贺凯认为,制度制衡包括三种不同类型,分别是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间制衡。[14]东盟主导的亚太地区制度就综合运用了以上几种途径来达到制衡域外国家、进而维护“中心地位”的目的。所谓包容性的制度制衡,即将制衡的目标国纳进自身主导的多边机制,再借由该机制的规则来约束目标国,达到制衡的效果,举例来说,东盟通过将中国纳入东盟地区论坛,试图借此让中国接受本地区的规范,降低中国因快速崛起而对东南亚带来的压力,就是属于包容性的制度制衡;而排他性制度制衡,指的是从现有制度中将制衡目标国排除在外,进而达到制衡域外国家的目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10+3”机制就是亚洲国家对美国采取排他性制度制衡的一个案例[15];制度间制衡则是对上述两种制衡手段的综合运用,采取制度间制衡战略的国家不仅支持新制度的建立,还试图用这个新机制来替代既有的旧机制,即东盟通过制度间平衡的手段,保障自身“中心地位”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合作制度的新陈代谢。
(三)增强东盟整体实力,强化东盟“中心地位”
东盟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保持团结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有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东盟才能向其外部对话伙伴表明,它有能力主导本区域合作进程。东盟成员国应致力于更深入地融合,不仅要朝着一体化的目标迈进,而且不能满足于2015年完成的东盟共同体的建设。
夯实东盟一体化,提升东盟共同体水平。一方面,加强东盟团结的责任不应局限在政府层面,还要将自下而上的努力纳入其中,重视包括企业、智库和公民社会组织在内的民间交流,通过政府、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的交流,全面提升东盟各国对东盟的认同感,助推东盟“同一个愿景,同一个身份,同一个共同体”的实现。另一方面,在一体化巩固、深化基础上,加强东盟“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建设和跨支柱协调的水平,以此为依托强化东盟各国在区域合作中的协调能力,巩固东盟的“中心地位”。
开展务实合作,在合作中不断积累善意与互信。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已迈出了很大步伐。东盟内部关于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等传统矛盾短时间内难以调和,加之各国在制度、文化上存在的巨大差异,使得东盟的互信基础相对薄弱,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困难重重。此外,恐怖主义、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对本地区稳定的威胁不断增强,甚至超过传统安全的威胁,是摆在东盟各国面前亟需解决的议题。通过在具有共同利益且争议性较弱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东盟能在其中累积善意、培养默契,为今后更敏感、更深层次的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奠定基础。这一倾向在历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从2006到2017年共举办了12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发表了14份联合声明,其中涉及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条文达到了61条,约占总条文数量的三分之一
五、结语
首先,东盟各国之间存在各种各样利益冲突,团结随时可能被打破。从成立至今,东盟并非总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其来有自。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既存在领土和领海等传统安全方面的争端,也有渔业纠纷、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方面的矛盾,围绕这些以上的争端与矛盾,爆发过不少冲突;第二,就综合实力而言,东盟十国都是清一色的中小型国家,不存在一个实力卓绝群伦的力量来主导联盟的事务,这也使得主导权争夺而引发的相互掣肘破坏了东盟各国之间的信任;第三,东盟各国间的差异甚大,互信基础薄弱。和欧盟不同,对成员国宽松的入盟要求,也导致了东盟内各个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在东盟国家中,既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也有实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未开发国家。国家状况的不同,也决定了各国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同质性不高,某些部分甚至相互抵触;第四,东盟体制产生的问题。东盟内部各个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不甚相同,而东盟奉行以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追求各方舒适度为核心的“东盟方式”来产生决策,两者间的矛盾使得决策过程往往是一场各方博弈、僵持不下以及效率不彰的“马拉松”,最终出台的决策是照顾各国对需要、折衷后的产物,很难准确地应对东盟面临的困境。综合以上几点不难看出,虽然东盟在2015年宣布已经提前建成了“东盟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的质量和一体化程度偏低,更像是一具空洞的骨架,这也是东盟维护其“中心地位”过程中必须克服的第一个难关。
第一,东盟的成立和发展本身就是一部克服不利环境、逆流而上的发展史,历史的经验有助于东盟稳住其“中心地位”。一方面,东盟作为以中小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从成立起,就时刻处在域外大国的虎视眈眈之中,长期周旋在大国间的经验,有助于东盟因应新的区域局势;另一方面,长期以主导者身份参与东亚的区域合作,也为东盟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东盟在以“主导者”角色参与区域合作过程中,增强了其存在感,摆脱了中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边缘人”的既有历史定位。东盟体认到,只有坚持“中心地位”,才能继续在区域合作中掌握主导权,避免被边缘化,摆脱受制于人的命运。
7.3问卷调查创建工作提高了患者及家属依从性,对疾病相关知识、按时服药、合理膳食、生活护理、康复锻炼、自我效能等。并对2014年和2016年糖尿病病人的平均住院天数进行了对比,2016年8.9天比2014年住院天数平均下降10%—20%。提升了母乳喂养率,2014年产科分娩产妇2998人,母乳喂养率85%,2016年产科分娩产妇3810人,母乳喂养率提高了10﹪达到95%.
第二,冷战结束至今,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垄断了国际社会的主导权,但全球性问题的涌现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国际社会对现有以西方大国为主导的国际交往原则怨声四起,反倒使得“灵活变通”“协商一致”和“非强制性”的“东盟方式”备受期待,成了对现有国际交往模式的可替代方案。东盟大可以“重塑国际秩序”为契机,以中立的角色提供更加公平的区域合作机制,借此将区域内各国更紧密联系到一切,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支持,壮大东盟“中心地位”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民意基础”,进而巩固东盟“中心地位”。在东盟自身的努力和新兴国家的支持下,东盟继续发挥“中心作用”迎来柳暗花明也未可知。
第三,中美博弈进入深水区,并选择以东南亚地区作为前沿,限缩了东盟在本区域事务上自主权和主导权。但短时间内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不会发生改变,东盟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的“中心地位”也没有转瞬即逝的风险,这种稳定不仅是本地区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中美“斗而不破”博弈状态的投射。但是,只要中美间的矛盾没能完全消弭,东南亚安全格局就难言稳定,东盟“中心地位”走出风雨飘摇也就遥遥无期,也是东盟未来能否继续保有“中心地位”的最大变数。
如今,每当心中那抹乡愁涌起,父母就拿起手机与家人视频通话,聊亲人的近况,聊家乡的变化,咫尺之间,乡愁尽情抒发。
冷战结束后,东盟秉持“中心地位”展开对外交往和区域合作,并据此建立了一系列合作机制和框架,这既要归功于东盟自身努力,也得益于世界经济
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东风。在内外交迫的新形势下,东盟要想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继续保有“中心地位”,一方面需要努力弭平联盟内部矛盾,凝聚东盟各国,在此基础上提高东盟一体化程度和“东盟共同体”的建设水平,以更好的体质投身未来更加激烈的国际政治博弈;另一方面,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态度,也将直接影响东盟在区域事务中拥有多大程度的主导权,这种“操之不在我”的无力感,也是东盟各国在现实主义下无法摆脱的悲情。
乾灵真火带着灼热气流朝·天南星妖扑去。那妖物定是知道这真火之厉害,面露惧色,一把扯过墨颜掷向熊熊燃烧的橘色火焰。
参考文献:
[1] Natalegawa.Aggressively waging peace : ASEAN and the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view: The Indonesian Journal of Leadership[M]. Policy and World Affairs,2011(2):40-46.
[2] 王玉主.RCEP倡议与东盟“中心地位”[J].国际问题研究, 2013(5).
[3] Acharya Amitav.“The Myth of ASEAN Centrality?”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ffairs,2017(2).
[4] Leifer.ASEAN’s Search for Regional Order. Singapore: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87.
[5] 曹云华.东亚共同市场的理想与现实[N].(香港)经济导报,1991-5-20.
[6] 王忠宇.民粹思潮对东南亚的影响[J].世界知识,2017(16).
[7] 卢光盛,周洪旭.东南亚恐怖主义新态势及其影响与中国的应对[J].国际安全研究,2018(5).
[8] 曹云华.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权问题[J].东南亚研究,2004(4).
[9] 曹云华.东盟准备好了吗:纪念东盟成立五十周年[J].东南亚纵横,2017(6).
[10] 迈克尔·巴尼特, 玛莎·芬尼莫尔.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
[11] 张蕴岭.东盟50年:在行进中探索和进步[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7).
[12] 王森,杨光海.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J].当代亚太, 2014(1).
[13] 王子昌.东盟外交共同体主体及表现[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
[14] 贺凯.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与竞争性多边主义[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12).
[15] Mark Beeson.ASEAN Plus Three and the Rise of Reactionary Regionalism[M].“ASEAN Plus Three: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2003:25.
(责任编辑:郭丽冰)
On Existence and Continuity of ASEAN "Central Position"under the New Situation
CHEN Ziheng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 In the long-term diplomatic practice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process, ASEAN has always adhered to and maintained the "ASEAN Centrality" , which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ASEAN's judgment based on its own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product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the situation in Southeast Asia changed greatly. The world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s slowing down.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reverse globalization" such as Britain's "Brexit" and Trump's election,has weakened ASEAN's determination and will on the road of seeking ASEAN Community’s 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foreign powers step up their involvement in Southeast Asia, the unity of ASEAN may also become precarious because of the division of the great powers. In addition, contradictions are emerging in Southeast Asia, with internal concerns arising from internal differences and ASEAN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as well as outsiders such as extremism, terrorism and populism, the interweaving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cerns has impinged on the process of ASEAN's further integration. The challenges are not only a challenge to ASEAN's pursuit of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but also a new obstacle to ASEAN's continued preservation of "Centrality"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Keywords: ASEAN; New situ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SEAN“Centrality”
中图分类号: D81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931X(2019)02-0028-06
收稿日期 :2019-04-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南亚安全格局对我实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影响研究”(16ZDA091)
作者简介: 陈子恒(1994-),男,福建漳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亚太国际关系。
标签:东南亚论文; 新形势论文; 东盟“中心地位”论文;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 华侨华人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