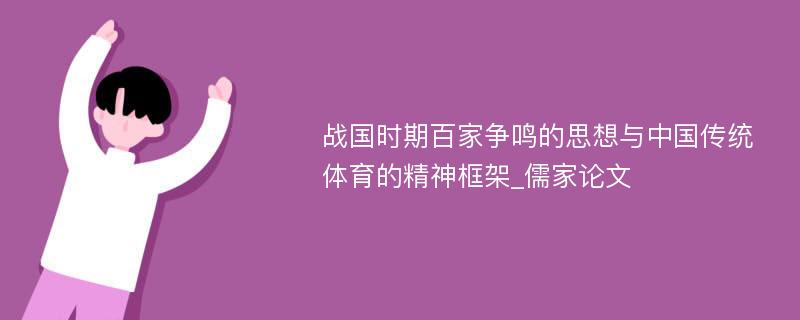
战国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百家争鸣论文,构架论文,中华论文,战国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9)06-0008-04
由于我国古代没有“体育”这一概念,我们现在对于体育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个从传统的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剥离和凸显的过程。早在上世纪初,郭绍虞先生在他的《中国体育史》中就曾明确指出,中国数千年之学术,儒家、道家二者而已,儒家重礼义,道家尚无为,“此则学术足以阻体育之发达者也。”[1]把思想观念与体育活动结合起来透视中国体育发展史,郭先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融合的第一个高峰,“通过稷下,先秦诸子之学得到了综合、批判,孕育产生出了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2]这一过程打造并构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体育发展中的“尚中贵和”、重心轻体、重静轻动、重道德轻竞技思想观念的理论框架,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构架起来的。
1 “和”: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的基本核心
战国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环境是以齐文化为基础文化背景的,齐文化的沃土对诸子百家的思想形成不可避免的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关于齐文化精神问题,学术界历来多以包容、务实、开放、变革等特点概之[3],而事实上,齐文化的精神则可以用一个“和”字作以概括[4]。“和”的基本元素实际上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思想史上通常把中国历史上“和”的人文精神的发明权归之于孔子儒学的创立,这不符合实际。孔子创立儒学是春秋末期的事情,而且仅处在思想理论阶段,到战国时期才成为“显学”(《韩非子·显学》),汉武帝时期上升为国家统治的思想理论工具。而在齐国,姜太公在封邦建国之初推行“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桓公任用管仲首霸春秋的时候提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管子·牧民》),齐国在这两个显赫的时代都已经清醒地提出并实践了“和”的思想理念。在《管子·宙合》篇中甚至有了“和”的哲学解释:“五音不同声而能调,此言君之所出令无妄也,……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无妄也。”这与春秋末期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哲学意义上几乎没有区别。管仲要比孔子早一百多年,更不用说姜太公了。而与孔子同时的齐国晏婴也对“和而不同”问题作出过清晰的阐释(《左传·昭公二十年》)。随后,战国时期齐国兴办稷下学宫,能够容纳诸子百家众多不同学派的学者在这里“著书立说”、“不治而议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本身也体现了一种“和”的文化境界。可见齐文化中“和”的思想理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要比孔子创立早期儒学时丰厚得多,不仅有理论,而且实践也比较丰富。应当说,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及其以后,“和”的人文精神的发展,在齐国既有继承、包容、革新的成分,也有儒学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原因。齐鲁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深度融合以后而凝练成的“和”的人文精神,相对于稷下学宫而言,儒学拘于政治伦理与齐文化重视现实功利,在这里形成了有效的互补,从而实现了“和”的人文精神的高度升华。
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家庭本位和家国本位是一体的,构架家庭、家国和谐稳定的基本措施,儒家靠伦理,道家靠“道德”,墨家靠“尚同”、“兼爱”,这些观点在百家争鸣过程中都曾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种以“和”为基本理念的人文精神的提出和升华,既为参与战国百家争鸣的诸子思想体系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同时也为传统体育精神的构架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材料。后来的社会发展中,儒家的尚中贵和、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墨家的“兼爱”等等,都包含有丰富的“和”的成分。齐文化中的这种“和”的文化精神,从根本上看,是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中的尚和、中庸、贵仁等泛道德观念的基本源头,从后世发展的基本状况看,则是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基本核心。
2 诸子思想: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基本材料
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是以诸子思想为基本原材料构架而成的。战国百家争鸣过程中,对传统体育精神影响较大的诸子学派最为主要的是儒学、道学和阴阳五行等学派。
春秋末期孔子创立儒学过程中就把他的儒学思想传到了齐国,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发展过程中,儒学大师孟子、荀子都是重量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这里充分的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体育思想。但由于儒学本身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他们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体育思想过程中,以素质教育、个人修养为基本出发点,形成了以“‘仁’学体育思想”[5]为基本特征的体育观念。在这一过程中,孔子是以号召天下“克己复礼”而行“仁政”为己任的[6],追求“成人”教育[7]。由于孔子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出现明确的文武分途,社会需要的还是文武兼备的人才,因而孔子的体育思想突出强调的内容,多半是个人人生修养的内容。孟子所处的时代与孔子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他并没有把孔子“克己复礼”的“未竟事业”传续下来,他的体育思想虽然同样也是建立在个人修养基础之上,但由于他的政治观念已经升华到了鲜明的“王道”水准,因而他的体育思想当中也就出现了所谓的“与民同乐”的全民运动观念,主张“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上》)这里所谓的“乐”,寓意非常广泛,既包含与民同心同德的意思,也包含体育娱乐活动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中的“钟鼓之声,管龠之音”。这一观点,既是孟子“王道”思想的衍生,也是他的民本思想能够成为先秦高峰的具体体现[8],同时更是对从军事活动中分化出来的体育娱乐活动的人文精神的有益丰富和补充。荀子也是从个人修养的角度阐述他的体育思想的,但有两点远超乎前人。首先,荀子从军事活动的条件论出发,明确提出了运动与健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荀子·修身》中提出“动静和节”的同时,在《荀子·天论》中又强调“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使之兵”、“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认为只要具备衣食等生活条件及经常进行肢体运动,人的身体就会强健,反之,如果生活条件欠缺,又不运动,就不能有身体的康宁。他把部队物质装备条件和军士身体状况看作是能否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明确地指出了运动与健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他对先秦体育思想上的杰出贡献。其次,荀子关于乐舞对人的心智陶冶作用同样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荀子·乐论》中指出了娱乐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荀子认为乐舞一方面可以陶冶人们的性情,“志意得广”;另一面可以使人的形体健全生长,“容貌得庄。”同时,还可以通过乐舞增强人们的组织、纪律性,“行列得正,进退得齐。”荀子甚至把乐舞的作用提高到了移风易俗的高度。
应当说,儒学从人生修养的角度阐述的体育思想,有着很强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道德色彩,从孔子强调“成人”,到孟子的“与民同乐”和荀子的“动静和节”、“人不能无乐”,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一进步,既充分的继承了儒学对体育活动中强烈的道德要求,同时又把体育活动从个人修养的范围扩大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必要工具,并且在充分吸纳齐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把“和”的文化精神升华成为以“尚中贵和”为基本特征的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看到,这一过程中是在从修身到治国再到平天下的积极进取理念支撑下完成的。
儒家的政治理念强调“大公”“无私”,而从老子的开始,道家则强调“贵己”、“重生”、“道法自然”。稷下黄老学派是道家学派的重要发展阶段,郭沫若在《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一文中曾经明确指出,稷下黄老学派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9]稷下黄老之学中的体育思想直接承继《老子》之学,这在现存的《素问》、《八十一难经》、《帛书四种》等文献中多可寻到轨迹。由于稷下黄老之学本于老子之学,因而,《帛书》中《称》篇有“毋先天成,勿非时而荣。”《十六经》中《姓争》篇有“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中,甚至把善养生的“古人”和不善养生的“今人”放在同一平台上作以对比,认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忠其天年,度百年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亡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素问·宣明五气》中说:“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这就是说,养生必须在生活上要有节制,要讲究规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又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告诫人们要根据不同季节的自然变化来注意身体保护。由此也就形成了人的疾病重在预防的思想:“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这类思想,历来多在古代中医理论当中应用,对日常的身体保健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所谓“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的理论本源与老子之学的“道法自然”是血脉相传的。此外,在《黄帝内经·灵枢·经水》中还出现了许多人体解剖的记载。如果我们把这些医学解剖理论与“顺应自然”、“适于阴阳”的保健理论结合起来看,其保健养生学说则显明的形成了对于生命在“未病”和“已病”两个阶段所采取的两种不同保健措施[10],这不仅在中国古代医学发展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在体育思想发展史上也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稷下黄老之学以自然之道为根本,以“静”为养生保健的基本要领,不管是治“未病”的“养生”,还是“治已病”的医疗,对于生命现象的认识是深刻的。但少有了儒学的那种积极的社会参与性,因而重心轻体、重静轻动的体育观念在黄老之学这里则更为突出,成为与儒学壁立的体育观念。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稷下黄老之学只是道家学派的一个发展环节,它们的体育思想是以修身养生为主体的,所有的道家学者在论及到修身养生问题的时候,都有着不可隐讳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
阴阳与五行的思想观念源远流长。战国时代齐国的邹衍把阴阳五行结合起来,形成了阴阳五行学说,在稷下学宫里边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阴阳五行学派。由于史料有阙,我们很难剥离阴阳五行学说中的体育娱乐思想,但是,这里有两点必须要特别重视的。其一,阴阳五行学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管子》书中的战国部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稷下黄老学说,以及随后出现的《吕氏春秋》中都可以见到这一学说的印痕。虽然邹衍的学说到汉代多为政治统治理论所采纳,但他对于阴阳学说的总结和升华,相对于与体育思想联系比较紧密的养生学、医学来说,无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传承作用。其二,《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说,燕昭王即位以后,“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在这种情况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以至于“士争趋燕。”秦灭六国以后,邹衍的学说引起了秦始皇的兴趣,于是也就引来了宋毋忌等众多依附于鬼神而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的齐、燕方仙道之徒。事实上,邹衍以五行学说“显于诸侯”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原因是其理论注重的了生命价值的珍贵,对于强身健体有所理论指导,但这些方仙道之徒非但没有弄明白邹衍的学说,反而把邹衍的“经文”念歪了,走上了欲通鬼神之邪路。邹衍创立的阴阳五行学说虽然没有得以系统的传续下来,但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养生之术对后来的长生不老之术影响是巨大的。
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从有限的文献记载来看,在黄老之学、儒学,甚至于其他学派那里都有或多或少的应用。对体育的影响,主要是与养生理论和医学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强身健体的理论指导。说明这一学说已经在探求某种生命保健运动的规律了,比如来自于日本的“五行”健身汤,实际上就是阴阳五行理论的延伸。战国以后,这一学说在汉代进入到了政治学领域,在民间则被方仙道所利用,成为长生不老术的理论主导。阴阳五行学说不管是在养生理论,还是在长生不老之术上的应用,都是要寻找事物发展过程中关键要素之间的平衡点,这使这一理论本身具有了一定的辩证科学成分,但由于受到了若干“术士”的鼓吹,最后有一部分也就进入了“迷信”的泥潭。因而,古代体育思想史领域对它的利用是有限度的。
3 “心性”: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突出特征
古代思想家们对体育精神的思考是以体育活动为基础的。在战国百家争鸣如火如荼的同时,体育活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就春秋至战国时期的体育发展而言,体育活动的确已经相当繁荣,在先秦典籍的记载中已经琳琅满目。在齐国,临淄城中以至于“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战国策·齐策》),甚至出现了以“千金”作赌注的赛马活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其中的“踏鞠”又作“蹴鞠”,现在已经被确认为世界最早的足球运动[11]。“且数百千”的学者们会聚稷下学宫参与“不治而议论”的百家争鸣,前后长达150余年,齐国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自然而然的为他们提供了思考的丰富材料。儒家的积极入世、道家的消极避世、阴阳学的规律性探索、墨家的科学追求,无不以人的内心世界作为调理的基本对象,从而也就几乎把所有的体育娱乐活动都看成了是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尤以儒学为甚,由此而与西方单纯的行为体育形成了显明的区分。
与此同时,“士”阶层的出现和分化,对传统体育精神的框架构建也进行了积极地实践。春秋时代的“士”大多都是有土地和农奴的,属于低级的贵族阶层。春秋末战国初期开始,已经出现了无田无土的“士”,所谓“士无田不祭”[12]、“士无土则不君”[13]正是这一现象的暗示,形成了“无田”、“无土”,“不祭”、“不君”的士阶层。士阶层的出现非常可怕,对社会潜在着巨大的威胁,诚如《荀子·非十二子》所说:“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惟权势之嗜者也。”情致如此,社会统治者也就不得不对日益增多的“士”严加约束[14]。但生活的压力、社会地位的日沉和对自身现实的不甘心,加速了士阶层的分化,那些肯于降志屈身者,转化成了诸侯的低级行政官吏或军队干部,或者甘心情愿的做了豪门贵族的门下客。不肯降志屈身者,大多走上了自我奋斗之路,孔子创办私学,就是士阶层分化的这样一条重要途径,但他们像孔乙己一样,是无论如何不愿脱掉身上的长袍的[15];也有的走上了“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史记·货殖列传》)的流浪之路,成为了纯粹的流浪无产者,他们既是发达城市的重要分子,又是后来所谓“慷慨悲壮之士”、“任侠之士”的祖辈。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士集团已经略具雏形”[16]。不管士阶层的分化方向如何,他们虽然也是始终处在苦苦挣扎的游戏场上,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奴隶和农奴仍然不同,他们无时无刻都以自己的行为实践正在远离他们的贵族阶层所制定的游戏规则,而不肯去忍受机器般的被操纵。但无论如何主动地“适应”和少有的“叛逆”成为士阶层在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在士阶层的分化过程中游离出来的所谓武士所表现出来的体育精神,首先也是以“心性”锻炼为第一要素的,诸如战国四公子的门客、刺杀秦始皇的荆轲,等等,侠肝义胆,视死如归,都是其平日“心性”砥砺的结果。
4 结语
近年来,关于儒学对传统体育的影响不断有学贤作出探讨[17]。直到上世纪末,还有学者指出:“传统体育观念与现代体育观念的冲突,传统体育体制与现代体育管理体制的碰撞,仍然是当代中国体育的主要矛盾。”[18]正如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一样,笼统地说,中华传统体育精神同样也需要两面来看,既有积极的元素,也有消极的成分。纵向来看,由于战国百家争鸣成就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传统的体育精神的基本框架也就随之而酝酿出来了。就传统体育精神在这一时期的剖面情状看,“和”是基本的思想内核,至于积极的身心修养观,或崇“道”,或重“仁”,或痴于阴阳五行变化,无不都在寻找身心运动的制衡点,因而“心性”体育又构成了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特征。这一特征并非像西方传统体育精神那样从体育活动中升华而来,而是来自于思想家们的对社会现实的思索,是对人生与社会关系思索的衍生,因而有着更为直接的以“和”为突兀点的东方文化特征。简而言之,“和”是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基本核心,伴随着儒学社会地位的不断攀升,后来也就发展成了的基本的主干。儒学强调的道德色彩,道学强调的顺应自然观念,阴阳学强调的平衡理论,事实上都是以静制动、平和心态、进而达到积极的健体目的,追求的终极目标始终没有离开人与社会、自然、肌体内部器官互动过程中的和谐。
这一点可谓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根本之所在。由于儒学的积极出世观推崇的“成人”体育思想、道学的消极避世观推崇的极端个人主义重生贵己思想,千百年来影响尤其至深,因而对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构架从根本上就形成了有别于西方传统体育精神的“心性”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传统文化,没有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也就没有特色鲜明的中华传统体育精神。
投稿日期:2008-04-07
标签:儒家论文; 孔子论文; 体育精神论文; 百家争鸣论文; 战国论文; 国学论文; 荀子论文; 邹衍论文; 齐国论文; 阴阳五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