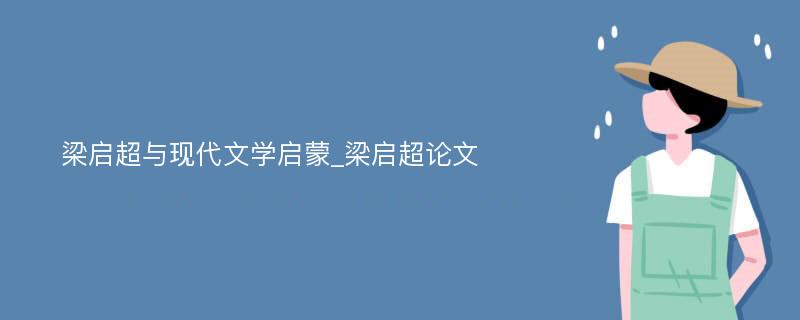
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文学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这是1927年初夏,饱经沧桑而潜心于教书著述的梁启超,以清华研究院导师的身份,对研究院中莘莘学子语重心长的告诫。此时的梁启超,已将数年前“舆论界骄子”、“新思想界勇士”所特有的踔厉风发、咄咄逼人的气势敛藏收起,而丰富的社会阅历与教书著述之余的闲暇,使他对于“做人”与“为学”的思考,变得更加通达从容。“造成不逐时流的新人”、“造成适应新潮的国学”,这既是步入夕阳之年的梁启超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待,又是他晚年学术追求生活心境的写照。一年多后,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文化巨匠,在北平溘然长逝。盖棺举悼之时,国内知名学者与文化名流,追忆他襄助变法,维新蒙难、海外流亡,倒袁讨张,历经成败之风雨,“日在彷徨求索”(注:《清代学术概论》。以下梁启超著述中的有关引文,均据《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中的一生,最为青睐最为推崇的是梁氏以书生救国,以文学新民的功绩。梁启超政见多变,但其“维新吾国,维新吾民”(注:《新民丛报章程》。)的宗旨始终如一;梁启超为学博杂,但其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注:《清代学术概论》。以下梁启超著述中的有关引文,均据《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尽国民责任于万一”(注:《三十自述》。)的志向始终如一。梁启超以他特有的敏感、热情、勤奋以及充满自信、轻灵锐利、富有情感的文笔,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数十年间,掀起了梁启超式的思想风暴,创造出“震动一世,鼓动群伦”,甚且至于“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注:黄遵宪:《致新民师函丈书》。)的辉煌。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将,更是近代文学启蒙思想的陶铸者。在促进近代文学启蒙与近代思想启蒙紧密结合,以文学启蒙推动思想变革方面,梁启超有过积极的努力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梁启超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中国近代思想的进化分为环环相扣,步步联接的三期。其进化过程像蚕变蛾、蛇脱壳一样,经历种种艰难苦痛而又渐入新境。咸同年间,是中国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的第一期,舍己从人,便有了制械练兵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至民国六七年间,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的第二期,变革政体,便有了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五四前后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的第三期,改良道德,便有了新文化运动。作为亲历者与参与者,梁启超的概括是十分真切而富有历史感的。正是这种环环相扣,级级嬗进的历史演化,构成了梁启超政治与文化选择的思想氛围和时代背景。
作为“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展运动”(注:《五十年进化概论》。)的风云人物与“急先锋”,梁启超是极富有进取精神与生命激情者。这两者使其行为与情感方式带有明显的个性特征而有别于其他维新思想家。梁启超曾生动地将思想进化比喻作危崖转石,又以为“自己的人生观”,是以“责任心”和“兴味”(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作基础的。责任心促使梁启超时时不忘救国新民重任,不间断地追求新知,融汇西学,并以“烈山泽以辟新局”的气度,将其介绍输入于闭塞委靡的中国思想界,企望以不倦的努力,逐步引导国民从自在的愚昧中觉醒,走向自主,携手创造民族复兴、与世界文明同步的未来。“兴味”则使梁启超不满足于己有,不拘囿于成见,不恂恂然守一师之说,时时保持拒旧而迎新的心态,且“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当康有为自诩“吾学三十岁已成,以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时,梁启超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注:《清代学术概论》。)。在维新思想家中,梁启超不愿以“富于成见”之稳健取信于人,而更乐于以“徇物而夺其守”,“移时而抛故”的善变赢得读者。不变的“责任心”与善变的“兴味”,皆以对民族、对真理热爱的情感作为依托。
梁启超自称:“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注:《清代学术概论》。)富有感情而又不肯压抑这种感情的梁启超,把启发国民蒙昧、洗礼民族精神的新民救国运动看作是包蕴着无限崇高感、神圣感的事业。这一事业赋予他拯救者的激情,也赋予他诗人般的灵感和情思。他比其他维新思想家更慧眼独具地意识到:输入新理,介绍新知,启发蒙昧,不但应作用于国民的理智,还应作用于国民的情感;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也应包括更新国民的情感世界。而影响作用于国民情感最有效的媒介是文学。新民救国,不可不借重于文学的力量;思想启蒙,不可无有文学启蒙的鼎力相助。在促进文学与思想启蒙、政治革命牢牢结盟,使之成为新民救国旗帜下的重要生力军的过程中,梁启超比其他维新思想家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也取得了更多的成功。
当然,梁启超对文学情有独钟,除了个人的爱好气质使之然外,主要是由于他个人也并不掩饰的功利性原因。当梁启超不厌其烦地讲述“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的道理时,当梁启超煞有介事地编造着海外文学救国的神话时,当梁启超极力倡导“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的政治小说时,无不自然而然地把文学与政治革命、思想启蒙的目的联结起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一语破的地指出:新学家治学的总根源在于“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以学问为手段、为工具,达到政治变革、救亡图存的目的,这在瓜分之声喧嚣四起,国内思想界闭塞委靡的时代,是新学家十分合乎逻辑的策略性选择,康有为所鼓吹的托古改制是如此,梁启超所策动的文学启蒙、文学革新也是如此。
梁启超与文学启蒙的缘份,可以说是与他的文学生涯、政治生涯同时开始的。而在梁启超参与维新、海外流亡与京居的不同生活阶段,文学启蒙也包蕴着不尽相同的内涵与特质。
1890年,18岁的梁启超入京会试后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注:《三十自述》。)。此年,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决意舍去训诂词章之旧学,而为陆王心学及史学、西学。梁启超的学术活动由此起步。自此年起至1898年百日维新的数年间,梁启超与师友砥砺气节,探求学问,参与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主办《时务报》,兴办时务学堂,共同寻求自强之路,鼓荡变法风潮。由一介儒生蓦然置身于政治浪潮的中心,梁启超既充满着救世的豪情与渴望,又带有年轻者所特有的浪漫与激进。梁启超晚年回忆1894年与麦孟华、夏曾佑在京读书的情况道:
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是“浪漫”的可惊……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思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思想。我们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元素混合构成。(注:《亡友夏穗卿先生》。)
正是这种虽不免粗糙浮泛但蕴含着极大思想活力的“新学”,构成了梁启超主办《时务报》时著书立说的根柢。梁启超是借助在《时务报》上所发表的文字而名声噪起的。读者接受梁启超,并非因为他有至深至妙的学理高论,而是因为他善于以报章文体的形式,以充满激情而流畅明白的笔触,把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著作中过于经院化、过于艰涩深奥的学说转换为平易通俗的语言,把亡国灭种之惨祸,清廷腐朽之秕政,“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变法道理一一条分缕析给读者,从而取得了“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新会梁氏者”(注: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的轰动效应。
出道的成功,坚定了梁启超以文字之功,导愚觉世、开通民智的人生价值取向。从甲午中国战败的教训中,梁启超意识到:“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士人之学。”(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中国“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优胜劣败的世界环境中,民智不开,对西方士人之学、立国之本,懵懂不知,则必然造成“今吾中国之于大地万国也,譬犹亿万石之木舰,与群铁舰争胜于沦海也。而舵工榜人,皆盲人瞽者,黑夜无火,昧昧然而操柁于烟雾中”(注:《变法通议》。)的重重险象,开通民智(包括官智、绅智),于士人,要多译西书,介绍学理,涤其旧习,莹其新见;于百姓,则应提供言文合一、宜于妇人孺子、日用饮食的文字。无论士人百姓,都可倚重俚歌说部,施之于教而劝之于学:
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官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哉!(注:《变法通议》。)
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于游戏小说者尤伙,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他国且然,况我支那之民不识字者十人而六,其仅识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注:《蒙学报演义报台叙》。)
以启发蒙昧作为己任,为民族自强谋求方策,梁启超此时所写的“愿替生民病,稽首礼维摩”(注:《自励》。)的诗句,正表达了这种心志。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梁氏辩白心迹道:“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韧此报(时务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扬光大之故。”为椎轮,为土阶,为陈胜吴广,以俟继起者,此正是启蒙思想家的气度风范。维新思想家为谋求民族自强选择了政体变革之路,而政体变革的成败,又以全民族思想觉悟为基础。在维新思想家的观念中,文学正是作为施教劝学、开通民智的手段之一,作为移风易俗、思想启蒙的方式之一,与政体变革、民族自强的总目标连为一体的。立言以求觉世,导愚而至妇孺,则不可不讲求言文合一而有宜于日用饮食,不可不讲求寓教于乐而借重于俚歌说部。民族自强、政体变革在赋予文学以使命感的同时,又规定制约着文学在作为启蒙思想的载体时,其从众向俗的基本发展方向。它将排斥孤芳自赏式的清高,而追求左右人心的社会效应。鉴于此,梁启超别出心裁地把文分为传世与觉世两种:
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沈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注:《清议报叙例》。)
传世之文,宜于通人博士、专门之家;而报有为椎轮、为土阶、为陈胜吴广之志的梁启超,其所着意揣摩、心向往之的自然是“条理细备、词笔锐达”的“觉世之文”。稍后,其自序《饮冰室文集》又谓:“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注:《三十自述》。)诸说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梁氏为文的基本取向。
维新时期,新学家的智慧与精力多集中在政体变革方面。“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思路,使梁启超对文学启蒙仅引其绪而未畅其意。戊戌政变后,维新派自上而下利用政治行政职能进行政治变革的希望流于破产。昨日尚为新政至贵的康梁,转眼之间成为“飘然一声如转蓬”的海外流亡者。待收拾起复巢而无宗卵的伤感、君恩友仇未报的悲慨、昨功今罪壮志未酬的失落之后,梁启超继续着读书著述的事业。其在《夏威夷游记》中自言初至日本发奋读书的情况道:“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逃亡日本的当年,梁启超就在横滨创办了以“维护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注:《清议报叙例》。)为宗旨的《清议报》。1902年,复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在海外重整旗鼓,以“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肯为百世师”(注:《自厉》。)自励的梁启超,掀起了一场持续数年、影响颇大的新民救国风暴。
新民救国的实质是全民性的思想维新。梁启超认为:在世界各国以民族主义精神立国的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中国言变法数十年而无成效者,皆因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中国要抵御列强以杜外患,拯救危亡以求自强,不可不更新国民精神。新民之道有二: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即发扬光大本民族已有的思想精蕴、优秀品格;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注:《新民说》。),即吸取他民族之优长以补我之所未及。围绕新民救国的宗旨,梁启超一方面以“梁启超式”的输入,向国人连篇累牍地介绍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培根、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等人的学说。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国民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指导,建立利群、自尊、自信、冒险、竞争、进取、尚武的国民道德,养成刚毅、坚忍、百折不挠、凛然不可犯的民族品格,携手共创“波澜倜傥,五光十色,必更有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注:《自由书》。)的20世纪少年之中国。
与维新时期主要通过国民教育开通民智的作法相比,新民救国具有更宏大的气势,更丰富的内涵,更深广的启蒙意义。它不再拘泥于政体变革之外在形质,而着眼于文野强弱之内在精神,它不再看重一时一事之成败,而更关心民族未来之命运。它鼓励国民从自在的愚昧中觉醒,自觉地参与民族精神的改造与重建工程,自下而上地促进中国政治的渐进和社会的文明之化。
像一位辛勤的拓荒者,流亡之中的梁启超如饥似渴地在所能接触到的著译之作中,为国人采集着思想的薪火,积蓄着除旧布新的希望。被破坏的快意、创造的激情和民族未来的辉煌所鼓舞,梁氏的笔端,洋溢着浓烈的进取精神和爱国情感,充满着叱咤风云的气势和惊心动魄的魔力。梁启超以他特有的真诚与热情赢得了读者,《清议报》、《新民丛报》因此在海内外不胫而走。
梁启超在构筑他新民救国的理想时,充分意识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民救国既然是一场更新国民精神、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启蒙运动,文学作为国民精神的重要表征,无疑是“新民”所不可忽视的内容;而文学自身所具有的转移情感,左右人心的特性,又是“新民”最有效的手段。从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需要自新;从促进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又担负着他新的责任。对文学,梁启超抱有“自新”与“他新”的双重期待。
一切都像是十分偶然。梁启超在逃亡日本的海船中,得一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记》而读之,触发了译印政治小说的想法。次年在去夏威夷的途中,得日本记者德富苏峰之文而读之,产生了文界革命及诗界革命的冲动。这些看似一时得之的思想,实际上都是蓄志已久的,民族自新的事业需要号角与鼙鼓。
且看梁启超为国人所编造的域外文学救国的神话:
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注:《饮冰室诗话》。)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注:《译印政治小说序》。)
梁氏希望这种神话也出现于中国,他热情地呼唤以文学浸润国民之思想、陶铸国民之灵魂的造福者、启蒙者:
呜呼!吾安所得如施耐庵其人者,日夕促膝对坐,相与指天画地,雌黄今古,吐纳欧亚,出其胸中所怀破磊磅礴,错综复杂者,而一一熔铸之,以质于天下健者哉!(注:《自由书》。)
亦不必自出新说,而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势力,亦复有伟大而不可思议者。如法国之福禄尔、日本之福泽渝吉、俄国之托尔斯泰诸贤是也。(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以清高之思,美妙之文,雌黄古今,输入文明,左右世界,造福同胞,在梁启超看来,是一项穆高如山,浩长似水,值得馨香而祝之,溯洄而从之的事业。文学新民救国,梁启超不仅仅是倡导者,更是力行者。梁启超发表于《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的“新文体”,无不以“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作为宗旨。梁启超于诗,主张“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其在《清议报》上开辟《诗文辞随录》,又在《新民丛报》上连载《饮冰室诗话》,提倡用诗“改造国民之品质”。梁启超推小说为文字之最上乘,以熏浸刺提概括小说支配人道之力。其所创办《新小说》,标榜“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为目的。又在写作《新中国未来记》中特意注明:“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梁启超以戏曲为文学中的“大国”,韵文中的“巨擘”。其所作《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意在“借雕虫之小技,寓遒铎之微言”,又开“捉紫髯碧眼儿,被以优孟衣冠”的先例。
如果说,学问饥荒与政治昏昧的时代,造就了作为舆论界骄子、思想界陈涉的梁启超,而思想维新、新民救国工程的实施,则造就了作为文学启蒙、文学革新领袖的梁启超。梁启超的鼓动诗界、文界、小说戏曲界革命时,始终围绕着新民救国的宗旨。正是从民族自新思想中,梁启超获得了文学创造的激情和灵感。也正是附着于民族自新之上,近代文学启蒙、文学革新才拥有超乎自身影响之外的意义与辉煌。
1912年11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京居的十数年间,他涉足政界,复又退出。曾经拥袁,旋又倒袁,辛亥革命后政党纷争、百无建树的局面,使他大失所望。目睹“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政,其结果乃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注:《大中华发刊辞》。)的现实,梁氏深感痛心。为何“凡东西各国一切良法美意,一入吾国,无不为万弊之丛”?(注:《伤心之百》。)梁氏认为:新学新政固有其粗率浅薄之处,但“平心而论,中国近年风气之坏,坏于佻浅不完之新学说者,不过什之二三,坏于积重难返之旧空气者,实什而七八。”(注:《复古思潮平议》。)此外,数年来,“举国聪明才智才士,悉辏于政治”。“政治以外之凡百国民事业悉颓废摧坏”。“政治一有阙失,而社会更无力支柱”(注:《大中华发刊辞》。)。故欲除辛亥革命死气沉沉之气象,仍须从“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处做起,从可以资养支柱政治的国民事业做起,以思想文化的进步补救政治革命的不足。
自称“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注:《外交欤?内政欤?》。)的梁启超,在其晚年,最终选择了执教著述的学者生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提出“学者的人格”问题,他认为:“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壹,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此说既是梁启超对新学家早年“以学问为手段”作法的修正,又是其脱离政治的喧嚣,走入书斋的宁静之后,以学术报国心志的表述。
在新的文化运动中,梁启超对文学复兴的期望最为殷切。他认为:
夫国之存亡,非谓夫社稷宗庙之兴废也,非谓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盖有所谓国民性者……国民性何物?一国之人,千数百年来,受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觉其卓然别成一合同化之团体,以示异于他国民者是已。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而传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者,殆非夸也。(注:《丽韩十家文钞序》。)
文学既是国民精神的传薪、民族凝聚的纽带,其自当引起策动国民文化运动者的注意。梁启超晚年论及清代学术,常将其比之于欧洲文艺复兴:“前清一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类甚多。其最相异之一点,则美术文学不发达也”(注:《丽韩十家文钞序》。)。但梁氏断言,此种不发达之中,正蕴藏着复兴发展的生机:
我国文学美术,根柢极深厚、气象皆雄伟,特以其为“平原文明”所产育,故变化较少,然其中徐徐进化之迹,历然可寻。且每与外来宗派接触,恒能吸收以自广。清代第一流人物,精力不用诸此方面,故一时若甚衰落,然反动之徵已见。今后西洋之文学美术,行将尽量输入。我国民于最近之将来,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采纳之而傅益以已之遗产,创成新派,与其他之学术相联络呼应,为趣味极丰富之民众的文化运动。(注:《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的这段文字,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1920年。步入生命晚年的梁启超,不再充任立于潮头的人物。尤其是欧游归来,目睹了西方科学主义的破产和精神危机之后,他更关心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责任,更关心中国学术对于人类精神发展的贡献,更关心中国文学对国民运动的资养及融汇中西之后的复兴发展。1923年,梁启超在《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中告白:“启超确信我国文学美术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价值,与泰西作品接触后当发生异彩,今日则蜕变猛进之机运渐将成熟。”在此预言中,充满着对民族文学前景的乐观自信,也包含着曾是耕耘者其期待收获的急切。
标签:梁启超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清代学术概论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新民丛报论文; 清议报论文; 时务报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