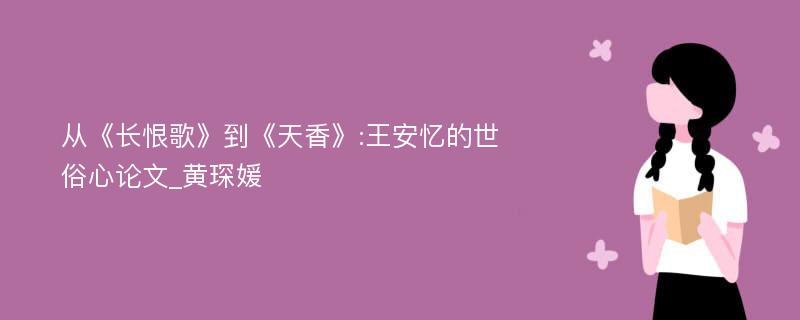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世俗生活是女性创作精神的物质力量根基,自现代女性作家发声以来,对于俗常生活的青睐和书写始终绵绵延延不曾断绝。到了王安忆,贯穿其三十余年创作生涯的即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和临摹,对此的坚守也成就了她鲜明的个人风格。然而,沉溺于世俗书写同样成为阻遏她另有突破的路障之一。本文通过《长恨歌》与《天香》的对比,意在说明这种世俗书写对王安忆的创作起着的双刃剑效果。
关键词:世俗生活;世俗书写;长恨歌;天香
一、对“世俗书写”的坚守
女性仿佛天生就具备维系生活的天赋与能力,相比男性永远旺盛的仕途欲望与对远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她们往往倾向于对日常器物进行亲切的体认,用自己的灵与慧赋予其意义,平常与琐碎的世俗生活也成为她们创作精神的物质力量根基。这种选择有其无可奈何的历史渊源,封建制度下的女性自由天地狭窄逼仄,笼统地说她们的生活范围不过是从闺阁到花园这一方小小的空间。在女性浮出历史地表之前,我们已无法清晰地听到她们对自身历史的言说,但以己度人地设想,她们也曾是丰沛而鲜活的个体,当自身欲望被拘囿于有限场所时,她们只有对已有的生活体验倍感珍惜。她们几乎调动了所有的情感力量和智力因素去认真而诚恳地体味生活本体的温凉,从亲历的物质生活中采集精神力量以填补对广阔世界无缘会面的空虚与失落。而这也就成为女性选择世俗书写的隐性基因,在一代代女性作家作出选择时发挥着影响作用。
粗略梳理现代女性作家的发展脉络,从凌叔华到苏青再到张爱玲,大多从世俗生活入手,写自己熟悉的婚姻家庭,写烟火气十足的尘世生活,写你来我往的俗世智慧,写食物写服饰写器物,写一切小而巧的东西。尽管选取这些例子不免带有主题先行的嫌疑,但笔者想借此声明的是,对于世俗书写的青睐与实践,从女性作家开始发声以来,始终绵绵延延不曾断绝。到了王安忆,不难看出张爱玲和《红楼梦》的影子,从《长恨歌》到《天香》跨度近三十年的创作,依然清晰可感的是她对世俗写作的坚守。
作家们钟爱写自己最熟悉的地方。精神上的原乡仿佛具有充沛的生命力,永远托举着作家的想象力去探讨人性的奥秘,同时原乡又具有宽厚的包容空间,所有故事都能在这片狭小空间中契合地生长。如苏童的香椿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贾平凹的商州,以及王安忆的上海。究其原因,是因为作家对原乡的深刻体认,它的精神气质,它的独特气息在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中浸润了作家的所有感官。所以,在叙述这片精神故里时作家用的不仅是视觉。还有听觉、嗅觉、触觉,一同构建一个活色生香的现实世界。
在这一方面,王安忆的确是个中规中矩的作家,她用近乎考证的态度在小说中去构建和还原一个世俗世界。她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她的小说观“这个心灵世界和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材料和建筑的关系。这个写实的世界,即我们现在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实际上是为我们这个心灵世界提供材料的。” 她坚信,只有在周密、严谨、平衡的世俗书写之上,才会有精神之光的显现。
时常在阅读中感受到,有时候单纯地写高而远的精神世界是取巧的,写灵魂的震颤与矛盾是易得的,因为只需截取人性共通经验的一瞬加以反复描摹渲染,往往就能达成直击心灵的效果。形而上的纯粹有时候给了作家更多的缝隙和填补空间,可以自成一家,可以自圆其说。而追求世俗书写却是相对艰难的,因其常见、琐碎、真实、可感,少有差池就会失去读者的信任。因此,对在《长恨歌》和《天香》中发现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尊重和倚靠的时候,已然被这种尝试的努力所感动。
在王安忆眼中,不管是史前上海还是旧日上海,这座城市都是一座无根基的浮萍之城。它没有北京帝王之都的厚重底蕴,也没有西安的古朴壮丽,甚至连南京的深重历史感都不具备。上海是座精致而包容的城市,但也正因如此它的面目显得驳杂,透露着四不像的无奈。而只有将其落脚到世俗生活里,这座城市才有了精神上依傍,显得不那么空虚和浅薄。诚然历史厚重庄严,但是世俗生活是上至君王下至百姓的都拥有和面对的,纵使上不了台面,在历经时日的积累后却也熬成一派自成风格的市民精神。而在王安忆看来,上海就是这种精神的集大成者。
所以她笔下的人物总是和细碎的日常生活过招,好比王琦瑶一干人等如何用一只小小酒精锅在有限的食物资源里变出花样来过日子,又是如何对一件旧衣物进行设计和裁剪;天香绣园里的女性是如何对绣进行钻研和琢磨,如何宴请宾客,如何布置自家园林,如何吃茶品美食的。世俗书写里头透出的是一种认真过日子的劲头,是全力以赴每日吃穿住行的用心,是一种坚韧而踏实的生活态度,是一座城的内蕴精神所在,也是一座城独特之处的外化。《长恨歌》中,“上海女儿”王琦瑶的一言一行都是这种老上海世俗精神的代言人,而这种温和安定的世俗力量吸引着老派和新派的过客,不管是李主任也好,康明逊也罢,或是最后出现的老克腊,对于王琦瑶的迷恋其实都是沉迷在烟火气息所带来的安心感中。而最后长脚将王琦瑶杀害也隐喻着现代生活对于这种精神的彻底毁灭和遗弃。这也正是王安忆感慨和悲哀,这种可称为老上海气质的东西,在一代代更迭中逐渐消逝颓败。在《长恨歌》里,薇薇一代对流行的盲目跟风与追逐丧失了思考和钻研的耐心和能力,失去了从容矜持的优雅,看似繁华热闹实则处处敷衍,形成了浮躁的表征。而这种浮躁也意味着失去了对生活美学的阐释能力。上海这座城市由漂浮到生根再到再度走向空虚,精神内核不断萎缩退化。
二、对“世俗书写”的沉溺
从《长恨歌》到《天香》,可以窥见王安忆一点蓬勃的野心。如果说《长恨歌》洋洋洒洒几十万字最终落到实处的不过是一个女性的一生,那么到了《天香》,同样的篇幅铺陈的却是申府几代人及其外延枝枝蔓蔓人物的起落变迁。在创作三十年的节点上,她推出了《天香》,或许并非如她所自白的那样“我既没有写《红楼梦》的野心,也没有为上海著史的野心,我不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我只是小说家......小说(指《天香》)还是一个关于女性生活的故事。” 从《天香》来看,王安忆绝非只想讲述一个关于女性生活的故事。园林、石墨、绣史、服饰、纺织在书中都能侃侃而谈,晚明时期上海的政治、经济、地貌、风土她都有所涉略,结构出一幅明末清初的上海风情画卷。正如前面提及的,这是一种谨慎而规矩的写法,史料知识的堆叠为背景的创设提供了基本的养料作用,初读之下,《天香》确实具有云览天下的广阔视野和气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个人和一方天地,而是力图以小见大囊括整个社会的风气与面貌,从述说一个人的“史”到一座城的“史”。
这次尝试可以看做作者创作三十年的一次厚积薄发,是作家积累的一次倾情展现。然而作家笔力的 丰盈还是枯瘦,是可以从字里行间触摸到的。这种笔力的充沛与否有时候无关乎字句的磅礴,无关乎背景的纵深与宏大,只在乎作者自身的情感气韵是否灌注于小说之中。叶圣陶在谈及苏州园林时曾说到,苏州园林的深刻繁复意境产生原因“全在乎设计者和匠师们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 创作皆相通,“胸中有丘壑”与否同样是文学创作是否有感召力的秘诀所在。《长恨歌》中的现代上海,是王安忆长大的上海,是她可感知可触摸的上海,形成了自成一派的亲切与贴合,所以我们感知到《长恨歌》的上海叙述是理直气壮的,说了哪些不说哪些,选了什么不选什么,因了作者的切身体会显得底气十足。这是因为王安忆心中已有一座清晰的城。而在《天香》中,就少了这种“胸中有丘壑”的底气与自信,又多了囊括万象的企图,所以生出了力不从心之感。纵使王安忆用了考据的认真与细致力求还原历史本真,却还是露了怯,而为了补足这点怯,技巧的东西用得就多了,对世俗书写的依赖就愈发明显,叙述就显出刻意的游刃有余来。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不知不觉中就把这种想象中的“文人中庸品性”、“工匠精神”营造得略微矫揉造作,反倒损害了人物的本真天性。
《天香》流露出的对《红楼梦》的致敬意味是显而易见的:精雕细琢的词句,环境氛围的营造,盛极而衰的故事走向等等都透露出对《红楼梦》的追随意味。但《红楼梦》是以曹雪芹刻骨铭心的人生阅历为基底熬出来的一曲悲歌,《天香》的致命缺点就在于缺少了感情上的悲悯力量。如果没有了这种力量的支撑,没有对生活的认知和解读,那么再精彩的世俗生活描写也仅仅只是一种写作练习而已。阅读《天香》不难发现,或许王安忆对上海“顾绣”的发展史做到心有丘壑,但却没有对其产生一种深度的热情或者说是情感上的联系,在创作过程中,作者的笔力又时常游移。对于整个社会面面俱到叙述的追求分散了她对“顾绣”的投入,原本应该成为主线贯穿整部小说的“顾绣”发展史虎头蛇尾,声势浩大的开始,不明所以的结束。
谢有顺在评价张爱玲的时候,高度赞赏其的一个原因在于张爱玲的写作保留了上海的原始风貌。张爱玲也写衣着服饰、写器物首饰但最为深刻的还是因为她记录下了当时人的精神状态。许多个体面貌汇集起来就成为一段历史时期的基本底色。而《天香》中最为遗憾的就是几乎所有人物都面目模糊。尽管出场人物繁多,还提及了董其昌、徐光启等历史上确凿存在过的人物,但是并没有留下深刻的痕迹,只是走马观花般路过一场,最后都沦为物质的陪衬。例如在写到希昭这个人物时,着墨虽多却都放在“闲笔”上,本末倒置。
希昭玩耍什么呢?穿珠子!母亲携她到高银巷珠子市场买珠子穿珠花。路两边全是珠子铺,琉璃珠子盛在扁桶里,颜色形制各异。赤、橙、红、绿、青、蓝紫、杂色、合色、无色;长、方、扁、正圆、椭圆、圆鼓、腰鼓、契形、锥形、水滴形、莲花形;金银片、云母片、琥珀片、翡翠片、螺片、贝片、牙片……希昭的眼睛都开不及看。
有一回,一领轿正停在希昭身边,只觉一股茉莉花香袭来,接着便看见一只手伸过来,拈起一颗珠子。这只手,有些像男人的,硕而长,颜色确是玉白。食指与拇指拈着珠子,对了光慢慢转动,珠子一闪一闪,转到了孔眼,便有一束针似的光穿透出来,没有缺损,也没有死眼。就这么挑着,一颗接着一颗。那小二捧着珠盆,一动不敢动。待挑齐了,再要比较大小颜色匀不匀,略有差池便拣出来,重新再挑……希昭从没见过如此明丽大胆又洒脱的女人,也像个男人,而且是见过世面的男人,部又看呆了。女人笑得更高兴了,从袖笼里摸出一个单耳坠子,也是珠子穿的,小红豆珠子纠成一球,吊一滴透明珠,就像果子上的露水。希昭木呆着,忘了伸手接,女人一低头,将耳坠子挂在希昭颈项上的盘花纽上,接过店主裹好的珠子,偏身重又上了轿,走了。
结合后文来看,这段话仅仅只作为描写希昭小女儿情态的一个侧面存在,对于希昭和风尘女子的短暂相遇也并没有什么伏笔深意,仅仅只是作为将希昭的女性特征进一步彰显的一个引子而已,但是作者却在此长篇铺陈,对于珠子首饰的描写洋洋洒洒挥洒了上百字。尽管小说中这类“闲笔”的存在,能使小说张弛有度,显出一种从容沉稳的气度来。但是对于闲笔的过多沉溺会分散了对主线的关注,削弱了故事本身的张力,减缓了戏剧冲突,造成不必要的耽搁。小说中这种耽于闲笔的地方有许多,虽然其中不乏有精妙的认识,譬如希昭对茶道的认识。小绸对佛道的解读,众人对武林、石墨、书画刺绣甚至是治水的见解,但是这些精彩的见解并没有起到烘托人物的效果,反倒是人物的存在似乎只见解的传声筒而已。
归根到底,《天香》缺乏的是一个高度凝聚的内核,原本应该为主线服务的、只是作为精神的寄托者的世俗书写却成为作者炫技的重点,从而形成了小说局部流光溢彩而整体上貌合神离。世俗书写构架出来的历史背景始终与人物隔离,脱离了它们,人物依然可以生存,这是一种拼贴式的阅读体验,折损了小说整体的流畅与圆融。
三、“世俗书写”的反世俗倾向
对于《天香》,学者王德威曾给予高度评价。据他的分析,王安忆创作《天香》是对前三十年创作风格的一次告别,是对一种新的创作风格的尝试与摸索。他认为这种尝试体现在《天香》中是一种暗藏的矛盾冲突,笔者试图将其归纳为“世俗书写”的反世俗倾向。
无疑,《长恨歌》中的“唯物”现实主义写法仍脱离不开“缘情”的最终目的,无论世俗书写多么繁盛细致最终还是要抒发作者内心对旧日上海气韵消失颓败的感伤。而到了《天香》,依据王德威先生的说法,王安忆之所以刻意以一种矜持而抽离的态度,冷静地叙述申家四代人的更迭,没有大悲痛,没有情感的跌宕起伏是因为言说对象已经发生了置换,也就是说,世俗书写已从背景成为言说对象,一贯居于主题地位的情感因素变为“情感外壳”,被用以辅佐叙述物的变化。王德威之所以盛赞《天香》是因为他看到《天香》反《红楼梦》以降世情小说的路数,当世俗书写不再与情感勾连,当传奇不再奇之时,就是一种返璞归真的极致,是极度绚烂之后的朴素清平。这种对世俗书写的白描手法是对个人和群体社会互动进行反思。
顺沿这种观点再读《天香》或许能解释王安忆沉溺“世俗书写”的心态和书中显露出的两难状态,这种主题的置换书写要抵抗来自以往书写经验的侵扰。一方面作者难以摆脱以往世情小说唯物缘情的影响,在世俗书写中沿物质方向却向着精神道路前进。“顾绣”的发展史总是被解读为几代绣女的人生经验的感性世界,难以控制笔下物质世界背后的精神价值的涌现。而另一方面,将物质作为言说对象的过程中也必须借助“人情外壳”来例证物的发展也同样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在读者尚未适应这种转变时,就形成了沉溺“世俗书写”或者说“物质书写”的阅读印象,这也侧面说明了将“世俗书写”本身作为言说对象的两难境地:既要避免成为纯粹的“唯物史”,又要时刻警惕精神情感因素突袭成为主题的可能。
至于王安忆的意图是否如此,由于缺乏明确的个人阐述资料,笔者也无法得出确切的推断,更何况在她的自述中,“《天香》还是一个关于女性生活的故事” ,似乎并没有将其看做是与过去创作的一次割裂。尽管王安忆擅长写物,但是本质上她还是一个小说家,写人和人与城的故事才是其作为小说家的诉求。而从《长恨歌》到《天香》的转变,与其说是一种从写人到写物的转变,不如说是王安忆不愿拘泥于只在女性幽微心理中进行塑造,而将笔端延伸至更宏大的社会境域中其构建自己心目中的上海。然而如果在事实和生活经验的层面上缺乏了一个更广阔的意蕴世界的存在,让读者无法进行一次精神的跋涉,那么这样的世俗书写注定只是一次自娱的书写。
不过,在创作过程中思维的流动并不是按部就班的,时常有发生突变的可能性,也许最后呈现的结果距离初衷已经是南辕北辙。这种突变的辨析恐怕需要更多的细读才能有进一步的阐述了。如果对一部厚重作品的阅读机会只有一次,那么为了避免浮光掠影的感想式评述,能做的就是捕捉浮上眼前的最明晰的感受来谈一谈,对笔者而言就是王安忆的世俗心及其笔下的世俗世界了。
参考文献
[1]王安忆:《心灵世界: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12页。
[2]石剑锋.:《500年前,上海的市井社会兴起男人退场,女人们光辉了》,《东方早报》2011年2月24。
[3]《百科知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9年,第237页。
[4]王安忆:《天香》,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第134页。
[5]石剑锋.:《500年前,上海的市井社会兴起男人退场,女人们光辉了》,《东方早报》2011年2月24。
论文作者:黄琛媛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10月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8/10/15
标签:世俗论文; 长恨歌论文; 天香论文; 上海论文; 王安忆论文; 精神论文; 珠子论文; 《知识-力量》2018年10月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