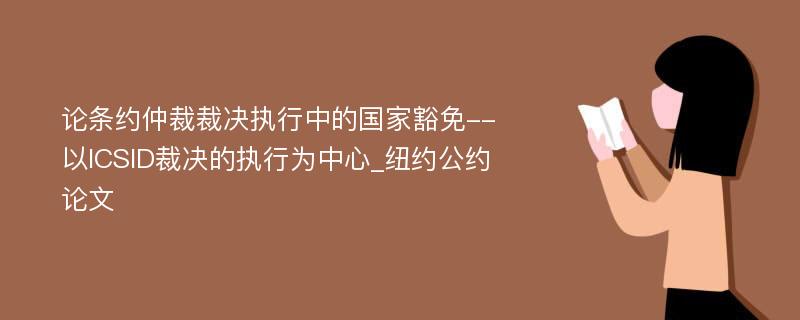
论条约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以ICSID裁决执行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约论文,仲裁裁决论文,国家论文,中心论文,ICSID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4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以下简称“ICSID”)接受了一起仲裁案件登记——申请人为马来西亚公司,被申请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①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作为ICSID仲裁被申请人的案件,此案的登记立即引起海内外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第7条“投资争议解决条款”向ICSID提出仲裁。1982年,我国开始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以下简称BITs),1998年与巴巴多斯签订的BIT出现“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之间任何投资争议”的仲裁条款。此后绝大多数的BITs均赋予了投资者可依条约进行仲裁的条款。但实践中,基于条约仲裁条款解决中国政府与投资者争议的案件非常少见。
所谓基于条约的仲裁,是指提起仲裁的依据为主权国家间条约中的仲裁条款,它区别于以合同中仲裁协议为仲裁依据的方式。②基于条约的仲裁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实践,国家与私主体间争议日益增多的产物。基于条约的仲裁,主要表现为BITs和与投资有关的多边公约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前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的第9条;后者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章和《能源宪章协定》第26条。在条约仲裁的机制中,以ICSID仲裁机制运用的最为广泛,影响力最大。ICSID根据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的公约》(以下称《华盛顿公约》)设立,在它成立的前20年里,案件之少让它的起草者都怀疑它存在的必要性。20世纪末以来,ICSID接受登记的案件数量激增。与此同时,对于ICSID仲裁机制的质疑也越来越多。③其中,影响ICSID功能发挥的两大挑战均来自于ICSID裁决本身:一是ICSID裁决的上诉机制,它会削弱仲裁裁决的终局性;二是ICSID裁决执行时,主权国家国家豁免的主张会影响仲裁裁决的执行力。④在这两大挑战中,国家豁免已成为所有仲裁裁决执行的一大难题,而不仅仅是条约仲裁所独有。但是,由于条约仲裁本身的特殊性,条约仲裁中主权国家主张国家豁免的情况也与传统国际商事仲裁中国家豁免的主张有所不同。
本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即为主权国家在条约仲裁中享有多大程度的豁免?围绕此问题,相关思考还包括条约仲裁与传统国际商事仲裁在裁决执行中国家豁免的适用有何不同?有关条约仲裁国家豁免立法与实践如何?中国在参与条约仲裁的实践中,应如何利用国家豁免规则保护国家财产利益?等等。
一、条约仲裁的自足性与国家豁免问题的特殊性
在主权国家参与的争议解决实践中,基于合同和基于条约的仲裁均能为私主体提供东道国以外的“中立”救济。但是,从争议解决基础到争议解决目标,条约仲裁均表现出独立于传统国际商事仲裁的自足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仲裁庭管辖权获得的依据不同。合同仲裁中仲裁庭获得管辖权的基础来源于仲裁协议,它表现为国家与私主体之间的合意。而条约仲裁中,仲裁管辖权获得的基础是条约本身,而条约主体是国家,私主体并非条约当事人。私主体与国家没有合同关系,条约只是赋予私主体可依条约仲裁条款提交仲裁的资格。这种非基于主权国家和私主体合意的条约仲裁,也被称为“无默契的仲裁”。⑤
其二,仲裁程序的透明度要求不同。合同仲裁出于仲裁保密的要求,从仲裁程序开始到仲裁裁决作出均不公开。因此,鲜见有涉及主权国家的仲裁案件的报道,除非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而条约仲裁对仲裁程序有“透明度”的要求,即要求仲裁当事人公开仲裁的程序和实体问题。例如ICSID仲裁就设有专门的网站,从案件登记到程序进行到仲裁裁决的结果均公开。
其三,可仲裁性事项的范围不同。合同仲裁可仲裁性事项范围很广,《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可仲裁性事项几乎没有作出限制。但条约仲裁中,可仲裁性事项受条约内容和目的约束。如《华盛顿公约》规定只有与“投资有关的法律争议”才可以提交ICSID仲裁。在某些BITs中,可仲裁性事项范围更为狭窄,并非所有与投资有关的事项均可提交仲裁。
除此之外,条约仲裁在裁决执行方面的自治性和自足性独树一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仲裁裁决执行的依据。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得以全球执行的基础是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条约仲裁裁决的执行主要依赖条约本身的执行机制,如《华盛顿公约》第54条规定缔约国应当承认与执行ICSID裁决,如同该国法院的终审判决一样。虽然某些条约仲裁裁决的执行也可依《纽约公约》来执行,但这需要BITs或国内法的授权规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不适用《纽约公约》。⑥
第二,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司法审查。通常,裁决的国籍国和执行地国法院均可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司法审查除了适用《纽约公约》外,还要适用法院地法可仲裁性和公共政策的规定。另外,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结果通常为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条约仲裁的司法审查被严格限定于条约本身。如《华盛顿公约》第53条规定,“裁决不得进行任何上诉或采取除本公约规定外的任何其他补救办法。除依照本公约有关规定予以停止执行的情况外,每方应遵守和履行裁决的规定。”而《华盛顿公约》规定的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方式包括解释、修改或撤销裁决。
上述条约仲裁的自足性将影响国家豁免规则的主张和适用。这些主张和适用方面的特殊性主要表现有:
首先,条约仲裁的自足性排除了主权国家可能主张的管辖豁免。一般认为,签订仲裁协议,意味着在与仲裁程序有关的法院程序中主权国家不享有管辖豁免。根据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以下简称《联合国豁免公约》)第17条的规定,与仲裁程序有关的法院程序包括:(1)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和解释;(2)仲裁程序的进行,包括指定仲裁员程序、仲裁员的异议和替换、仲裁管辖权的确定以及注册仲裁裁决等;(3)仲裁裁决的撤销和承认。条约仲裁中,仲裁协议表现为“无合意”的条约仲裁条款。《华盛顿公约》第41条规定,仲裁庭有权决定其是否具有管辖权。仲裁协议及仲裁程序的进行无需内国法院的协助。因此,条约仲裁从仲裁协议到仲裁程序进行的自足性排除了主权国家在传统国际商事仲裁中可能主张的管辖豁免。
其次,国家豁免规则构成了条约仲裁裁决自足性的唯一例外。《纽约公约》没有规定公约和国家豁免规则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中国家是否享有豁免由承认与执行地国法规定。承认与执行条约仲裁裁决依赖条约本身规定。一方面,《华盛顿公约》第53条和第54条建立了ICSID裁决自动简单化的承认与执行机制,规定ICSID裁决具有终局性,缔约国有执行ICSID裁决的条约义务;另一方面《华盛顿公约》第55条规定缔约国承认与执行ICSID裁决的义务不影响缔约国现行的国家豁免法。即,执行地国法院可以依据其本国法来确定主权国家的特定财产能否被实际执行。这样,缔约国的国家豁免规则实际上成为ICSID裁决自足性的唯一例外。
二、条约仲裁裁决执行与国家豁免的特殊问题
(一)条约仲裁条款与国家豁免的放弃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主权国家签订仲裁协议视为国家在与仲裁有关的程序中放弃管辖豁免。这已被《联合国豁免公约》以及相关国内立法所确认。但是,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是两个独立的问题。相对于管辖豁免,执行豁免的例外范围要窄很多。⑦在条约仲裁中,主权国家以条约仲裁条款约定将争议提交ICSID仲裁,是否意味着放弃包括执行豁免在内的国家豁免?有学者认为,主权国家参与ICSID仲裁本身不能视为对执行豁免的默示放弃。因为根据《华盛顿公约》的规定,ICSID裁决的执行并非自动的,而且ICSID裁决的执行机制不能解释为对执行地国国家豁免规则的减损。⑧也有学者认为《华盛顿公约》第55条实际上已经明确规定主权国家没有放弃豁免。⑨我国有学者认为,主权国家以国家豁免的理由来拒绝执行仲裁裁决从而避免履行其条约义务,这明显与条约的目的相冲突。⑩从条约仲裁的实践来看,签订条约仲裁条款视为放弃豁免,包括对财产执行的豁免仍远未实现。(11)
实际上,为了减少诉讼中国家豁免规则适用的困难,《华盛顿公约》的起草者曾建议拟定公约条款,让主权国家放弃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但是,也有起草者担心,“如果要求主权国家在公约条款中放弃执行豁免,会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而且影响公约的批准和生效。”(12)最终,《华盛顿公约》第55条是将国家豁免的问题留给各个缔约国。笔者认为,公约第55条没有赋予主权国家享有国家豁免或明确国家没有放弃豁免,而仅指出承认与执行地国的国家豁免规则享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在国内法中,主权国家签订条约仲裁条款是否构成执行豁免的放弃,各国做法不一。以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为例,签订仲裁协议可视为主权国家在执行仲裁协议和执行仲裁裁决的诉讼中放弃豁免。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主权国家同意在美国仲裁,美国法院将认为国家默示地放弃了豁免。如果主权国家约定在其他国家仲裁,美国法院将不会认为主权国家放弃了豁免。
(二)“承认”与“执行”条约仲裁裁决与国家豁免规则
作为一种条约义务,ICSID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由《华盛顿公约》第53条至55条规定。ICSID裁决一旦作出,除了条约本身所规定的内部复审程序外,排除了国内法院在承认与执行阶段对裁决进行司法复审的任何机会。根据《华盛顿公约》第54条第1款的规定,所有缔约国均有承认ICSID裁决的义务。而且所有《华盛顿公约》缔约国均是ICSID裁决承认与执行的义务国,而不管该国是否为仲裁裁决约束的一方当事人。对于承认与执行国而言,其条约义务仅仅被限制为“审查ICSID裁决的真实性”,不包括对ICSID仲裁庭管辖权、仲裁程序的公正性以及仲裁案件实体问题的审查,甚至也不审查仲裁裁决是否违反执行地的“公共政策。”
ICSID裁决有“承认”与“执行”两个阶段。“承认”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确认仲裁裁决具有“既判力”;另一方面,它是“执行”仲裁裁决的必经阶段。但是,“承认”并不必然带来“执行”后果,例如无实际金钱履行义务的裁决则无执行程序。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阶段,国家豁免规则均有可能适用。承认阶段主要涉及管辖豁免,执行阶段主要涉及执行豁免。根据《华盛顿公约》第55条的规定,国家豁免规则仅适用于裁决的“执行”阶段而不适用于“承认”阶段,国家豁免规则也不影响裁决的“既判力”。前文已提及,《华盛顿公约》第55条只适用于执行豁免,而不适用于管辖豁免。对于仲裁事项的管辖权,根据《华盛顿公约》第25条和第41条的规定,由仲裁庭来决定。而且根据《华盛顿公约》第54条第1款的规定,缔约国执行ICSID裁决的义务仅限于金钱义务。因此,在ICSID裁决执行的具体实践中,国家豁免规则仅适用于有财产执行对象的情形。
(三)国家豁免规则适用后条约仲裁裁决的救济
主权国家在ICSID裁决执行阶段成功主张国家豁免,将主要带来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主权国家的财产免于强制执行,二是主权国家仍构成对《华盛顿公约》义务——遵守和履行仲裁裁决义务——的违反。国家豁免规则仅是为主权国家提供了一种程序上免于执行的措施,它没有免除主权国家在《华盛顿公约》第53条项下的义务。国家豁免规则的适用仍构成对条约义务的违反,会导致《华盛顿公约》第27条第1款的适用,即私主体可以寻求其母国的外交保护。因此,主权国家成功主张国家豁免,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国际投资纠纷的解决又回到政治化解决的轨道。
主权国家成功主张国家豁免,不履行ICSID裁决的另一可能性后果是带来多边体制下的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是国际社会经常用于促使主权国家履行其国际义务的一种方法。经济制裁有可能是由单个国家作出的,例如美国《1961年外国援助法》及其1994年修正案规定,如果“某个国家针对美国国民实行了国有化或征收的措施”且“没有依据国际法进行充分有效的赔偿”,美国将不会对该国进行援助。国际组织也经常是经济制裁的实施者。与ICSID直接相关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其总顾问直到2008年也是ICSID的总秘书长。世界银行可以通过与不履行仲裁裁决的主权国家进行官方沟通,提醒其“遵守他们同意履行仲裁裁决的国际义务”。(13)
三、条约仲裁裁决执行的国家豁免立法与实践
(一)条约仲裁裁决执行的国家豁免立法
在国际条约层面,有关国家豁免最重要的两个条约是2004年《联合国豁免公约》和1972年《欧洲国家豁免公约》。《联合国豁免公约》第17条规定,如果一个国家签订仲裁协议,那么该国在涉及与仲裁有关的法院事项时,不得主张管辖豁免。《联合国豁免公约》这一条的精神在实质上与1972年《欧洲国家豁免公约》第12条一脉相承,都规定与仲裁有关的法院诉讼中,国家不享有管辖豁免。但执行豁免的判断标准独立于管辖豁免之外。(14)由于《联合国豁免公约》至今仍未生效,《欧洲国家豁免公约》的缔约国有限,在条约仲裁裁决执行的实践中,两大公约的实际影响力非常有限。
在国内法层面,国家豁免立法在英美法系的英国、美国等国表现为成文立法,而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均没有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需要从案例中梳理该国的国家豁免规则。在国内立法中,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和英国《1978年国家豁免法》有关仲裁与国家豁免的规定最为全面。
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1988年修正案规定,如果仲裁约定在美国境内进行或者美国有承认与执行一项仲裁裁决的条约义务时(如《纽约公约》和《华盛顿公约》),那么与该仲裁有关的事项包括仲裁裁决的执行不享有豁免。这一条规则仍与该法中的其他规则相互呼应。首先,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的只是“对事管辖权”,美国法院对某一涉主权国家案件的“对人管辖权”要独立判断;其次,仲裁裁决约束的主权国家仍要受到行为性质判断,即只有主权国家从事的是“商业行为”时,仲裁裁决才不享有执行豁免;最后,在财产实际执行中,还要考虑被执行财产本身的性质是否享有豁免。
作为一般规则,英国《1978年国家豁免法》规定国家财产不得作为仲裁裁决强制执行的标的。但有以下例外:(1)国家书面同意放弃执行豁免的。国家仅表示接受法院管辖的条款,不认为是对执行豁免的放弃;(2)如果国家财产正用于或拟用于商业目的,则可以采取程序上的措施;(3)如果是针对《欧洲国家豁免公约》成员国的财产,则为执行仲裁裁决而开始的程序不享有豁免。
(二)条约仲裁裁决执行的国家豁免实践
实践证明,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愿意主动履行仲裁裁决,特别是由ICSID作出的仲裁裁决。(15)由于ICSID裁决执行体制的自足性,因此挑战ICSID裁决执行的司法判决非常有限。从主要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涉及ICSID裁决执行国家豁免的案例主要有四个:两个法国案件分别是Benvenuti & Bonfant v.Congo和SOABI v.Senegal;美国案件是LETCO v.Liberia以及英国案件AIG Capital Partners v.Kazakhstan。
法国法院在Benvenuti & Bonfant v.Congo案(16)对ICSID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做出区分并认为法院职权被限制在前一个阶段。意大利公司Benvenuti & Bonfant在法国寻求对其有利的ICSID裁决执行。巴黎初审法院承认ICSID裁决的同时作了下列保留:根据仲裁裁决,没有法院事先授权,不得对位于法国境内的财产采取任何强制执行或保全措施。Benvenuti & Bonfant上诉认为,法官只需要去判断和承认裁决的真实性,原审法官不需要对执行问题作出判断,因为这涉及主权国家的执行豁免问题。因此,Benvenuti & Bonfant认为此项保留实际上使得执行无法进行,于是上诉请求删除此项保留。巴黎上诉法院认为,《华盛顿公约》第54条的目的是为了简化承认与执行ICSID裁决的程序,缔约国法院的功能被严格限制在确认裁决的真实性。对第55条的解释,上诉法院认为,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不构成实际执行措施,而仅仅是实际执行之前的前提。因此,根据《华盛顿公约》第55条,法官不应超出其权限去解决涉及主权国家豁免的第二个步骤。于是,上诉法院判决删除上述保留。
法国最高法院在SOABI v.Senegal案(17)认为国家提交仲裁表明其接受对裁决的“执行令”,但“执行令”本身不构成对国家豁免权的挑战。ICSID裁决Senegal赔偿SOABI因其单方违约产生的损失。巴黎初审法院作出承认该仲裁裁决并发出“执行令”。Senegal上诉,巴黎上诉法院推翻原审判决,认为提交ICSID仲裁并不构成对仲裁裁决执行时国家豁免的放弃,因此根据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502条的规定,对ICSID裁决的执行将会与法国的国际公共政策相违背。上诉法院同时认为,国家豁免规则保护Senegal的国家财产,除非SOABI证明Senegal可供执行的财产具有商业性质。SOABI上诉至法国最高法院,法国最高法院撤销上诉法院的判决并认为,根据《华盛顿公约》第53条和第54条的规定,法国国内法上有关国际公共政策规定不应适用,主权国家提交仲裁表明国家接受针对裁决作出的“执行令”,而“执行令”本身不构成一项具体的执行措施,其也不构成对外国主权国家豁免权的挑战。
LETCO v.Liberia案(18)表明申请执行人对主权国家财产的执行困难重重。LETCO在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ICSID裁决,法院作出承认与执行ICSID裁决的裁定。基于这项裁定,法院针对Liberia位于美国境内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随后,在Liberia的请求下,法院认为这些财产具有主权性质而非商业性质,因此享有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下的财产豁免,于是撤销了对财产的执行。基于同一仲裁裁决,LETCO又在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请求对位于华盛顿Liberia大使馆的银行账户采取保全措施,但遭到法院拒绝。法院对“商业活动”的范围进行严格解释,确认大使馆的银行账户受到《维也纳外交关系条约》和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的保护,享有外交豁免。
英国法院有关ICSID裁决执行适用国家豁免规则的案例是AIG Capital Partners v.Kazakhstan案。(19)申请人获得一项对其有利的ICSID裁决并根据《1966英国仲裁(国际投资争议)法》第1条在英国高等法院注册裁决并请求执行。申请人获得一项临时决定,允许执行位于伦敦的Kazakhstan中央银行的现金和债券。Kazakhstan中央银行参与诉讼并主张,根据英国《1978年国家豁免法》第13条第2款第2项和第14条第4款,Kazakhstan中央银行的财产享有豁免,因此请求解除执行命令。英国法院认为,位于伦敦的财产使用均是根据。Kazakhstan中央银行行使主权的行为,因此这些财产享有英国法的豁免。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实践中,对执行申请人而言,执行主权国家财产的实际难度和障碍并非国家豁免“主张”本身,而是在于“寻找”和“确认”性质上可供执行的国家财产。通常,针对主权国家财产执行的举证责任在于执行人,而非主权国家。(20)对于执行申请人而言,获得对国家财产的执行有三个途径:其一,执行人可证明主权国家放弃了财产的执行豁免;其二,执行人可证明主权国家有专门用于执行特定仲裁裁决的财产;其三,如果没有放弃豁免和划拨财产的情形,执行人必须确认国家财产的商业性质。当然,有些国家还规定了其他限制性条件,比如美国《1976年外主国权豁免法》规定财产必须“用于位于美国境内的商业活动”。(21)上述案件表明虽然执行申请人努力寻求对国家财产的执行,但除了增加的诉讼费用之外,执行结果不尽人意。
第二,从各国法院态度看,与其他涉主权国家的案件执行一样,法院对条约仲裁裁决的财产执行显得非常谨慎。首先,在解释国家参与仲裁与放弃豁免时,法院通常不认为国家放弃执行豁免。其次,各国法院具体执行ICSID裁决的程序客观上增加了执行国家财产的难度。在法国法院,ICSID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分为三个步骤:承认(recognition)、执行(enforcement)和实际执行(execution)。依据《华盛顿公约》的条约义务,法国法院通常会承认ICSID裁决并作出“执行令”(exequatur),并且认为国家豁免问题在这两个阶段并不会出现。美国法院同样如此,即使到了实际执行阶段,也会根据本国法对特定财产的豁免规则进行区分
四、代结语:中国可能面临的困境与解困
截至2011年12月,我国与101个国家签订有效的BITs数量达到100个。在这些BITs中,采用仲裁方式解决投资者与缔约方的争议,大体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仅规定缔约方之间的争议解决,排除投资者与缔约方的争议可以提交仲裁;第二种模式允许投资者与缔约方采用仲裁解决争议,但对仲裁事项做了明确限定,如仅限于“征收或国有化产生的补偿款额的争议”;第三种模式是对仲裁事项不做任何限定,可提交仲裁的事项为“有关投资的任何争议”。除了可仲裁事项,投资者与缔约方也可以在ICSID之外选择其他仲裁方式,比如选择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总体上,我国对外签订条约仲裁条款表现为越来越多元化,赋予投资者更多选择的趋势。
虽然条约仲裁条款早已存在,但据公开报道与我国有关的条约仲裁案件仅三个:谢叶琛诉秘鲁案、(22)黑龙江国际技术合作公司等诉蒙古案(23)和Ekran Berhad诉中国案。这三个案件均处于仲裁程序之中,因此我国尚无条约仲裁裁决执行的实践。(24)即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对未来条约仲裁裁决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不予考虑。对于条约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我国可能面临的问题有二:一是我国作为ICSID裁决的被执行国时,在执行地法院主张国家豁免;二是我国法院在受理一方为主权国家的ICSID裁决执行时,适用什么样的国家豁免规则。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由于ICSID机制是一个相对自足的体系,从争议的可仲裁性、仲裁庭管辖权的确定、仲裁程序的进行到仲裁裁决的复审,《华盛顿公约》都提供了明确的规则。如果要挑战仲裁程序和仲裁裁决,主权国家可先在公约范围内用尽救济,不必等到仲裁裁决执行之时。如果仲裁裁决进入执行程序,那么主权国家只能在执行地国法院主张国家豁免。执行地国法院只适用本国的国家豁免规则,因此在限制豁免论的国家法院主张绝对豁免将是徒劳。从主要国家的国家豁免规则来看,虽然在管辖、程序方面无法主张豁免,但仍可以在执行(实际执行)阶段主张国家豁免。因此,充分利用法院地国在豁免主体的区分和对特定财产的保护规则,积极地主张豁免将是保护国家财产的最后途径。
对于第二个问题,由于我国至今没有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目前只能从相关立场来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从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以及外交部在刚果(金)案三次致函香港特区政府政制与内地事务局的观点看,绝对豁免论仍是我国政府的核心立场。现阶段,我国法院不会受理以主权国家为对象的仲裁裁决执行请求。笔者认为,未来仅依绝对豁免论立场来解决司法实践问题是不合适的。首先,绝对豁免论只能保护在我国境内的主权国家财产,包括在我国境内的我国国家财产和他国国家财产。对于在他国境内的我国国家财产,则适用执行地国法——即广泛采用的限制豁免规则。因此,国家豁免规则适用的不对等,客观上对保护我国国家财产不利。其次,随着我国参与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实践日益丰富,国家财产在他国的分布越来越广,财产使用目的也越来越复杂。针对我国国家财产提起的执行之诉可能会越来越多。完善我国国家豁免立法是应对外国法院诉讼的最佳武器。最后,我国签署了以限制豁免论为基础的《联合国豁免公约》。虽然公约尚未生效,但在不超出公约义务范围内尽快制订我国的国家豁免法仍为上策。(25)
综上所述,条约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是所有签订条约仲裁条款的国家不可回避的问题。充分利用《华盛顿公约》提供的程序条款,积极研究他国国家豁免规则,尽快完善我国国家豁免立法,才能更好地保护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我国国家财产和利益。
注释:
①Ekran Berhad v.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CSID Case No.ARB/11/15),http://icsid.worldbank.org/ICSID/Index.jsp.
②关于条约仲裁形态的更多解释,可见石慧:《投资条约仲裁机制的批判与重构》,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18页。
③参见余劲松:《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权益保护平衡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郭玉军:《论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的正当性缺失及其矫正》,载《法学家》2011年第3期;蔡从燕:《国际投资仲裁的商事化与“去商事化”》,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1期;刘笋:《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不一致性问题及其解决》,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6期;刘笋:《论国际投资仲裁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兼评美国的应对之策及其启示》,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3期。
④See David R.Sedlak,ICSID's Resurgenc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Cart the Momentum Hold?,Penn Stat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Summer,2004,p.150.
⑤See Jan Paulsson,Arbitration without Privity,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Vol.10,No.2,1995,p.232.另参见杨彩霞、秦泉:《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无默契仲裁初探》,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3期。
⑥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法(经)发(1987)5号。
⑦See Sun Jin,The Linkage Requirement in Enforcememnt Immuniy,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Dec.,2010,p.700.
⑧See A.F.M.Maniruzzaman,State Enterprise Arbitration and Soveign Immunity Issues:a Look at Recent Trends,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2005,p.80.
⑨See Andrea K.Bjorklund,State Immunity and the Enforcement of Investor-State Arbitral Awards,in Christina Binder,Ursula Kriebaum,August Reinisch,and Stephan Wittich(eds.),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for the 21st Century:Essays in Honour of Christoph Schreu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5.
⑩参见易理胜:《投资者—东道国仲裁及中国投资者》,http://ielaw.uibe.edu.cn/html/wenku/zhongcaifa/20101014/15062.html。
(11)See Andrea K.Bjorklund,Arbitration and National Courts:Conflict and Cooperation:Soverign Immunity as a Barrier to the Enforcement of Investor-State Arbitral Awards:the Re-politic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The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2010,p.211.
(12)See Aron Broches,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Recueil Des Cours,1972,p.403.
(13)See Jan Paulsson,ICSID'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Vol.6,1991,p.386.
(14)See Jeremy Ostrander,The Last Bastion of Sovereign Immunity:A Comparative Look at Immunity from Execution of Judegments,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4,p.549.
(15)See Alexis Blane,Sovereign Immunity as a Bar to the Execution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Vol.41:453,pp.464-465.
(16)S.A.R.L.Benvenuti & Bonfant v.People's Republic of the Congo.ICSID Case No.ARB/77/2,Award rendered on August 8,1980.Reported in United Nations Judicial Yearbook,1981,pp.176-177.
(17)Société Ouest-Africaine des Bétons Industriels(SOABI) v.The Republic of Senegal,ICSID Case No.ARB/82/1,Award rendered on February 25,1988.11 Juin 1991,Cour de Cassation(1re Chambre Civile).Reported by Revue de l'Arbitrage,Volume 1991 Issue 4(1991),pp.636-637.
(18)Liberian Eastern Timber Corporation(LETCO) v.Republic of Liberia,ICSID Case No.ARB/83/2,Award rendered on March 31,1986.Liber.E.Timber Corp.v,Liberia(LETCO),650 F.Supp.73,77(S.D.N.Y.1986),Liber.E.Timber Corp.v.Liberia ( LETCO II),659 F.Supp.606,610.
(19)AIG Capital Partners Inc & Anor.v.Kazakhstan,ICSID Case No.ARB/01/6,Award rendered on October 7,2003.AIG Capital Partners Inc v.Kazakhstan,Commercial Court,[2005] EWHC2239,October 20,2005.
(20)See Andrea K.Bjorklund,Arbitration and National Courts:Conflict and Cooperation:Soverign Immunity as a Barrier to the Enforcement of Investor-State Arbitral Awards:the Re-politic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The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2010,pp.230-231.
(21)See George K.Foster,Collecting from Sovereigns: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d for Enforcing Arbitral Awards and Court Judgement Against States and Their Instrumentalities and Some Proposals for its Reform,Arizona Journal of Inte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Vol.25,No.3,2008,p.681.
(22)Tza Yap Shum v.Republic of Peru,ICSID Case No.ARB/07/6(China/Peru BIT),http://icsid.worldbank.org/ICSID/FrontServlet.
(23)China Heilongiiang International & Technical Cooperative Corp,Qinhuangdaoshi Qinlo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and Beijing Shougang Mining Investment v.Republic of Mongolia,UNCITRAL(China/Mongolia BIT).See http://italaw.com/chronological_list_if_content.htm.
(24)据报道,我国法院曾以“被申请人不存在”为由拒绝了当事人申请执行ICSID裁决。参见万鄂湘、夏晓红:《中国法院不予承认与执行某些外国仲裁裁决的原因》,载《武大国际法评论》(第13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25)参见张英:《论国家豁免原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载《暨南学报》2012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