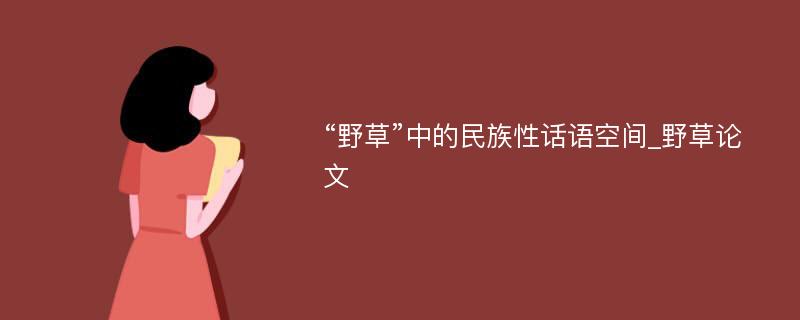
《野草》中的国民性话语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性论文,野草论文,话语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而言,大家耳熟能详的国民性(劣根性)话语更多呈现在鲁迅的小说(如《阿Q正传》的高度代表性)和杂文书写(如其点点滴滴犀利敏锐的多层次、多角度批判)中①,在相对个人化且高度诗化的《野草》中似乎较为少见。但实际上,作为富含了鲁迅各种哲学的《野草》同样也未放过这个鲁迅毕生关注的主题思想之一。整体而无处不在的犀利批判自不必说,甚至在貌似无关的篇章中也有精彩呈现,如《狗的驳诘》并非简单的一篇借狗讽人的寓言,也不是单纯结合现实影射对手或叭儿狗的批判。在我看来,它是对奴化和物质化丑恶文明的双重反讽,其中一重指向了制度反讽,而另一重则是对自我的解剖。其中,“我”的身份的犹疑性和作为“中间物”的劣根性也是一种值得警醒的存在。 本文并不想泛泛而论,借此凸显国民性如何点缀《野草》其间。反过来,本文毋宁更关注鲁迅在单篇散文诗书写中的交叉连缀或集中处理策略及其后果,这样既可保证单篇书写的宏阔性和完整性,同时又可以呈现其可能的繁复性和诗性实践。在我看来,《野草》中有关国民性的代表性篇章主要有:《失掉的好地狱》《秋夜》《墓碣文》《淡淡的血痕中》等。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在《野草》中对国民性话语的反思都和“空间”密切相关——比如作为高度隐喻的“地狱”、个体死亡后的墓穴、现实人间和自然环境“秋夜”等。 一、《失掉的好地狱》:国民性解/构 在我看来,《失掉的好地狱》有另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涉就是:解/构“国民性”,既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消解,同时又暗暗地进行了建构,至少是改革的努力和趋势。主要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对于有关制度的解构,另一个则是对国民性的反思与建构。 1925年3月31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中犀利的写道,“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②表面上看,《失掉的好地狱》貌似和国民性反思没有大关系,其实不然。毕竟,魔鬼和鬼魂们的对立面就是人类——他们更阴险狡诈、无所不用其极,将地狱的凄惨和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自我省思。 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首先是指向了人类(自我)。 1.与魔鬼的对照。地狱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专制黑暗的(实存)时空,也是一种神似的奴役制度、机制和思想逻辑。如果要详细区别文本中魔鬼和人类的统治差别,那么我们可以说人类显得更变本加厉、无耻之极。借用鲁迅的话说,人类治下的地狱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魔鬼时期则是想做稳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人所论,《失掉的好地狱》“则以象征的方式进行了更精炼和形象的表达:魔鬼统治的时代和人类统治的时代,统治者虽然更替,地狱依然是地狱。只是残暴专横的程度有一些差异而已;人类统治之时类似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魔鬼统治之时类似于没做稳奴隶的时代。当然有一些微小的差异。比如魔鬼统治时比人类统治时好,而没做稳奴隶的时代似乎不如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人类统治时更有秩序,更太平,更稳定,但自由空间更小,更残酷。所以,做稳了奴隶的时候也未必就比没做稳奴隶的时候好。”③ 耐人寻味的是,文本中的有关魔鬼角色的解读中却有不少误读,有些论者将之解读为西方殖民者,论者指出,鲁迅安排“魔鬼”作为“失掉的好地狱”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与评价者,又安满腹猜疑的“我”作为听众,这富有戏剧性的安排的深意,也许就是提醒人们要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及其文化这个“魔鬼”保持足够的警醒。更为发人深省的是,鲁迅认为肩负着“启蒙”重任的知识分子往往不是站在“鬼魂们”一边,而是“人类”之一员,甚至于他自己也可能是“人类”之一员。④在我看来,这样的解读其中问题也不少,可以追问的是:鲁迅未必把启蒙者划入人类行列,因为那是比魔鬼更暴戾和专制的生物,他们汲汲于统治的技艺,在奴化和专制层面可谓登峰造极;反倒是魔鬼,固然有其劣根性,但亦有可取之处。 同样值得推敲的还有文末一句,魔鬼对“我”说,“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胡尹强将之解读为,“魔鬼似乎窥伺到诗人陷入婚外恋的进退维谷,试图挑拨、消解诗人的启蒙主义信念。然而没有成功……诗人尽管有‘失掉的好地狱’的叹息,却依然以自己是‘人’而不是不可救药的奴隶而自豪。魔鬼只能去寻野兽和恶鬼。”⑤可以思考的是,如果所论中的“人”和《失掉的好地狱》中的人类叠合的话,那么这里的“人”其实也并非真正的“人”,而只是奴隶主,他们不过是居于主-奴结构的一端,身上同样亦有奴性。而魔鬼去追寻“野兽和恶鬼”,是进行身份的区隔,并非赞扬人类,而言外之意是——和人类相比,魔鬼和野兽才更是他的同类,远比“人”好。 2.奴役的进化拆解。鲁迅某些思想层面的深刻性其实亦有其发展过程,回到文本中来,比如一个多月前在创作《杂语》时,鲁迅关注的还是神-魔角度,二者本质上差别不大,而到了《失去的好地狱》时,人类角度介入,就可以看出鲁迅的复杂褒贬取向——人类才是真正的恶魔和狠角色,如人所论,“作《杂语》时,可能还未构思出‘人类’的角色,但神与魔都不是好东西。《失掉的好地狱》文中出现‘人类’,顿使寓言增添了历史预见,具有令人战栗的深度。”⑥ 结合现实,即使到了1930年代,看到人间地狱——监狱对人(无数个案)的迫害、摧残与压迫以后,鲁迅在《写在深夜里》一文中忍不住写道,“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这是一种怎样深化了的绝望与感慨啊。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部分消解和颠覆《失掉的好地狱》中的角色区分。所谓天神、魔鬼、人类其实原本都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非人、假人,尽管不断变换旗号,无论打着怎样美妙、先进与冠冕堂皇的旗子与口号,这才是鲁迅先生敏锐而深刻的地方,“他不仅坚持了早期的‘立人’思想,同时更提出了一种警惕,即警惕那些在‘立人’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奴相,警惕那些具有新的伪装的似‘人’非‘人’的假‘人’和非‘人’。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可能就在新文化阵营的内部。可以说,这是鲁迅对于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新现象的一种非常直接严厉的批判。”⑦ (二)理性勇敢倾注。 不容忽略的是,鲁迅既是国民劣根性的强有力批判者,同时又是新国民性的建设者和实践者,《失掉的好地狱》中同样有此关怀。 1.勇于反抗。鬼魂们的反抗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反抗魔鬼,在人类的助力下顺利推翻魔鬼的统治,“人类便应声而起,仗义执言,与魔鬼战斗。战声遍满三界,远过雷霆。终于运大谋略,布大罗网,使魔鬼并且不得不从地狱出走。最后的胜利,是地狱门上也竖了人类的旌旗!”另一次则是反抗暴虐的统治者——人类,“当鬼魂们又发出一声反狱的绝叫时,即已成为人类的叛徒,得到永久沉沦的罚,迁入剑树林的中央。”从言辞中我们不难读出鲁迅对人类伪善的反讽,同时又可感受到鲁迅先生对鬼魂们反抗失败的惋惜和同情。 更进一步,鲁迅借助梦和寓言,其实将地狱抽象成所有不合理、专制黑暗的结构存在,结合现实,他其实也在鼓励人们反抗不合理与暴虐,“统治者用来利用、麻痹和恐吓民众的地狱思想,在鲁迅笔下却成为锐利的武器,他以地狱来比类人间,以地狱‘鬼魂’来比类众生,并将这痛苦示诸笔端,希冀有一天打破这地狱,求得人的解放,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⑧ 我们不妨结合鲁迅同日所作的《杂忆》加以分析,鲁迅特别指出,在反抗的过程中,勇气、理性是在愤怒之后必须更长远坚守的原则,这其实就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有效的反抗,鲁迅写道,“然而我们在‘毋友不如己者’的世上,除了激发自己的国民,使他们发些火花,聊以应景之外,又有什么良法呢。可是我根据上述的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需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确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⑨ 2.理性睿智。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对同一主题的剖析,鲁迅往往既可苦口婆心,又可以花样翻新。在《“碰壁”之后》他曾经写道,“我平日常常对我的年青的同学们说:古人所谓‘穷愁著书’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那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正当苦痛,即说不出苦痛来,佛说极苦地狱中的鬼魂,也反而并无叫唤!”“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我装作无所闻见模样,以图欺骗自己,总算已从地狱中出离。”⑩其中,明明对鬼魂相当执着,却又说已从中“出离”,而同时“境由心造”一词却又提醒我们:我们固然可以从现实背景及鲁迅的位置体验考察其文字,但同时亦该有超越性,不可过分坐实和拘泥于现实比附。 从此视角解读,《失掉的好地狱》其实亦有鲁迅的心灵构造:天神、魔鬼、人类何尝不可以理解为有代表性的人类理念(如制度更换或重大事件等)的巨大冲击和可能的撕裂,政治制度当然可以是一种维度,故乡其实亦可以是一种可能性。当然更大的理解(精神层面)维度也可以是一种宇宙观(如“天地作蜂蜜色”),或急剧变化的现代性理念(时间演进)都可能是一种解说,如人所论,“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失掉的好地狱》又昭示出鲁迅的‘世界观’,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或时空交错,对于自我都构成了某种侵夺和压迫,因此本质上呈现于鲁迅观念中的宇宙秩序又是一个分裂着的世界,显现着个人与历史运动和现实秩序的某种紧张关系……自近代化以后,身处困境的现代人即已敏感于世界的分裂,因此而陷入无可挽回的紧张感撕扯感之中。鲁迅更是敏感于此,虽然鲁迅所在的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后进的封闭的社会秩序,但是分裂了的世界感觉已然被其捕捉到。”(11) 二、《墓碣文》重审劣根性 《墓碣文》写于1925年6月17日。值得一提的是,这恰恰也是震惊中外的五卅事件发生后的拉锯或滞后期内。身居上海的鲁迅对此事势必感触良深,而实际上他对此也有密集的文章抒发,如《忽然想到(十)》(6月11日)、《杂忆》(6月16日)、《忽然想到(十一)》(6月18日)、《补白(一)》(6月23日)等等,都是同一月份发表的相关主题文章,可以看出鲁迅的情绪、思考和态度。 在这组文章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鲁迅先生批判的独特视角,他既批评了肇事殖民者的残暴,但更着力于批判国民劣根性,无论是个体,还是民族国家的集体,“自家相杀和为异族所杀当然有些不同。譬如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忿。但一个人而至于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难免为别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实还没有消除。”(12) (一)从审己到审群。 张洁宇指出,“鲁迅所提醒的是,声讨与反抗帝国主义当然是必要和重要的,但与此同时还要借此机会从本国本民族的自身进行必要的反省和反思。——这可以说是鲁迅的一种思维惯式。对于他人和自我、他国与本国,他都是采取的这样一种辩证的、自省的态度的。”(13)其实,写于1925年6月的《墓碣文》亦有此倾向,也即,从审己到审群。 毋庸讳言,《墓碣文》中不乏鲁迅对自我的苛刻解剖与书写上的精心雕琢,可谓是自我的解剖和记录,如人所论,“《墓碣文》是探索自我的作品。内心冲突引发了对自我的探索,而自我探索却走向绝境,原本不言而喻的自我变得模糊不定,甚至无法看见,——这是个‘提灯寻影,灯到影灭’的追寻过程,注定失败。不仅如此,这种探索带出了更广更深的困惑,在无边的泥沼中,鲁迅越陷越深。”(14)但同时,细查这份记录,我们也不难从个与群的对抗中发现他对群的审查与省思。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上述文字固然呈现出主体选择的清醒与痛苦,但同时却又反衬出群体的喧嚣浮躁、幻想虚假、茫然空洞、绝望死寂。某种意义上说,“我”既是个体,一个无意闯入的旅人,但又可以是群体,一群好热闹或相对无知的看客。如人所论,“本篇通过对孤坟、死尸和墓碣语文句的描述,采用梦境的方式和象征的手法,来表达鲁迅对于腐朽、颓败的旧文化以及由这种文化模式所塑造的国民灵魂的一种独特认识。在这一认识中,包含了鲁迅对民族现状及未来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体现了他对于民族命运和作为启蒙者个体人生道路的迷茫心态,从中也流露着鲁迅这时一定的虚无与绝望的潜意识心理。”(15) 从群体的“我”的角度看,“诈尸”事件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审判过程,死尸“口唇不动”,居然可以发出颇有自信心、预见性和杀伤力的话语,而后果是,“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我”的迅疾逃走,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惊恐,另一面则很可能担心它的传染,其实更是审视与灵魂逼问。而耐人寻味的是,诈尸事件其实是鲁迅特别设计的追加式审视,因为墓碣的阴阳面已经高傲或善意的提醒观者“离开”了,但在“我”准备离开时,它却依旧“诈尸”断喝,这是多么威武独特而又寂寥、意味深长的追问与表述。 (二)如何重审? 引人深思的是,同样是对国民劣根性加以审视和批判,《墓碣文》采取了相当不同的策略。或许是限于超短的篇幅,或许是鲁迅企图以更凝练的方式表达自我内心,鲁迅先生对劣根性的批判更多呈现出对有关功能、意义和姿态的强调,而非内容侧重或缕述。毋庸讳言,此文本中,他以旁敲侧击的方式也批评了群体劣根性的内容,但是相对晦涩而凝练。 相较而言,他更多是以个体示范的方式进行深切解剖,虽然未曾缕述劣根性具体表现,结局也未必完美,但毫无疑问是一种丰富而有意味的实践,借此他更强调自省的功能与意义,正是因了自己的孤独自省,借别人的火,煮自己的肉,同时继续生发点燃,传递火种,并期冀其可能的星火燎原,有论者指出,“鲁迅已决心把旧我的灵魂和躯壳永远埋葬。他以自己的经验清醒地认识到,黑暗和消极虚无只会使人绝望、自弃和痛苦,死尸的‘微笑’意味着自己的彻底毁灭,因此必须义无反顾地疾走。这里,已不是告别,而是埋葬,使黑暗与虚无的阴影和烟尘永远不能追随;也不仅是无私地与黑暗一道沉没,而是更崇高地经过自我批判而求得彻底解脱。”(16) 同时,鲁迅却又深知这种重审的吊诡与限度,其中包含着失败与成功、新生与毁灭的相辅相成的复杂辩证:一般而言,彷徨和困惑自然也是重审和探索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使并不确认未来与前途,但挣扎着,努力着,本身也是一种希望,或至少是找寻希望的有益实践。 毋庸讳言,丧葬话语在鲁迅的各种文体中似乎都有所呈现,比如散文、小说等等,而在鲁迅的小说中丧葬话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其运行轨迹亦有其复杂之处,它不仅仅可以呈现出其作为常规打压角色对个体/群体真情的压制,而且也可以呈现出其相对积极的一面,对丧葬礼仪的反抗与僭越同样也可以映照出相关人士的性格乃至劣根性。同样,丧葬也可以架构小说情节、充当核心事件以及作为重要的场景进行细描,颇具意义。(17)实际上在《墓碣文》中鲁迅也巧妙借助了此类话语。 毫无疑问,丧葬礼仪制度在中国文化史上源远流长。即使缩小范围,棺材的发展史也可谓博杂繁复,比如,其中涉及不同权力阶层和身份的规定,使用怎样的材料和规格,以及棺椁上的不同雕饰等等都耐人寻味。(18)而在《墓碣文》中,我们不难发现,“那墓碣似是沙石所制,剥落很多,又有苔藓丛生”。这些描述说明了,墓碣的主人是相当孤寂的(有可能是特立独行的),墓碣根本缺乏必要的祭奠、打理也说明了他的非主流,在民众中毫无市场,从微妙的意义上说,恰恰可能反衬出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对立而非对话关系。 而在儒家的丧葬观念中,“入土为安”理念蕴含着不同时代的先人们对于身体/灵魂死后安放的一种认知,如《礼记·祭仪》中所言,“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而《礼记·郊特牲》中亦言,“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否则,尸体很可能出来祸害别人,为此,更进一步,“入土为安”还要考虑到墓地的选择,比如强调自然和人文的风水,同时,甚至也会非常重视对葬日的确认,最好是吉日良辰。(19) 反观《墓碣文》,“即从大阙口中,窥见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状,但蒙蒙如烟然。”鲁迅先生不仅让死尸暴露,还要让它“诈尸”,不难看出,借助此种对既有的丧葬礼俗的恶作剧式的粗暴批判,鲁迅先生在渲染着反抗的、同归于尽式的快意与无奈。不必多说,这也是对国民劣根性生成机制和传统的有意反戈一击。鲁迅先生固然更强调自我批判的姿态,而且不仅仅是让自我全面、痛苦而艰辛的实践,同时又对旁观者加以棒喝和提醒,“诈尸”的方式相当奇异而有效,甚至不只是批判陈旧的礼仪制度,又是对“我”、读者的棒喝和启发。 为此,墓碣下面的主体所企图解决的不只是个人孤绝问题,而更是对懵懂看客的独特启蒙,也是对劣根性生成机制的攻击。而结尾时的成尘时的微笑其实也是对自我牺牲的欣慰告白。无独有偶,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先生也有类似的表达,“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其间自然也有为卖钱而作的。这回就都混在一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三、批判及其可能出路 《野草》集子的暧昧、晦涩乃至歧义性,背后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其中隐藏了难以说尽的哲学意蕴,而涉及国民性话语时,其中的批判意味显而易见,但发人深省的是,鲁迅并非只会批判,同样他也探寻可能的出路。 (一)《秋夜》:点评国民性。 正如李欧梵所言,“这是现实和幻想相争。《秋夜》之奇不仅来自诗意的想象,同时也来自鲁迅对主观境界着意的处理。”(20)而耐人寻味的是,《秋夜》中貌似和国民性这种宏大叙述关系不大,其实不然。仔细考察一下,便可发现鲁迅先生从两大层面展开其国民性批判策略。 1.批评其生成机制。这尤其是以夜的天空和其帮凶为代表。夜空本身故作神秘,这本身就是专制统治的常用伎俩,同时以其虚伪高深以及“几十个星星的眼”众星拱月般神化自我。与此同时,在假笑(貌似镇定自若、真理在握、以德服人)的外表下却又欺压野花草,以此卑劣手段呈现出其统治的威严和强权。 除此以外,他还有帮凶月亮。虽然月亮也抗不过枣树的坚韧直刺,但至少在统治策略上可以呈现出一种群体效果,可以对付意志不坚定、头脑不清醒的“乌合之众”。(21)当然,夜空也有威逼利诱的其他蛊惑方式,如眨着各式各样的“许多蛊惑的眼睛”。不难看出,国民性,尤其是劣根性的生成和相关统治机制与传统延续密切相关。 2.劣根性种种。毫无疑问,国民劣根性在《秋夜》中也时有展现,如前述的瞒和骗传统其实对个体不无影响、相互作用、恶性循环。而其中也不乏助纣为虐者,这些指涉与批判可谓一目了然。 相对隐藏的是一种中性角色,如粉红小花的懦弱、爱做梦而缺乏反抗精神,其缺陷如果深入发展就可能变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变成了自欺欺人。同样还有小青虫,虽有匹夫之勇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如冯雪峰认为,作者“对于为了追求亮火而死于灯火的小青虫也表示了尊敬、肯定的态度”(22),但更多是不清醒的乱撞,缺乏真正的韧性战斗和有的放矢、运筹帷幄的策略与能力。当然,鲁迅对国民性的直面和批判其实也和烘托出反抗绝望、确立刚韧思想密切相关,“正视并揭露黑暗,赋予鲁迅的理性以现实的战斗的品格。勇敢、执着正是理性精神在现实的战斗中的表现。他独特的韧的战斗风格即是以对黑暗的深刻的理性认识为基础的。韧战把他锻炼成独立支撑的大树,《秋夜》中的‘枣树’便是它的象征。”(23) (二)新国民?! 虽然涉及篇幅不多,但鲁迅在精神关切上其实主要的指向之一就是国民性的出路问题。其中可能是最优先的出路就是国人要自强。这在《淡淡的血痕中》有不多但相对清晰的思考。 1.改造国民性。有论者指出,“在大家都竞言希望的时候,鲁迅常常是黑暗绝望和孤独的;但是当大家都受到沉重的打击而沉默的时候,鲁迅却是最坚持的……这一篇《淡淡的血痕中》就是‘三一八’惨案之后的一次起身,虽然他自己的灵魂也是伤痕累累。”(24)这的确是看到了鲁迅先生的韧性、洞察力以及貌似慢别人半拍实则引领未来的先锋性。 纵览文本,我们不难看到“人类中的怯弱者”的诸多劣根性,他们不仅怯弱,而且自欺自奴、坐以待毙,缺乏应有的勇气和反抗精神。当然其中也涉及了庸众中普及的庸俗中庸之道等,所以,鲁迅在文本中相当失望的写道,“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这样。”确实是对互相奴化的不满和愤怒。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其间的生者、将生者、未生者的新的可能性,而且人类中亦不乏微弱的异议者,他们是改造和革命的火种。 2.新国民的可能性。鲁迅写道,“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这其中就包含了最少两重内涵:一种是灭掉造物主的良民们,让旧有的劣根性乃至帮凶消失,可以实现代际替换,从头来过;另一种则是让人类苏醒,不再受欺诈、奴役,而变成真正的人类,而“猛士”就是这样的样板和示范。有论者指出了“猛士”与尼采“超人”的差别,“鲁迅则不仅立足大地,而且立足现实,将超人的价值进行转换,使其与青年学生和‘三一八’烈士的价值联在一起。这些地方,反映了作者在现实斗争的范围内,将超人改造、设计成提高人的灵魂的模式的企图。这样,超人意识便转换成反抗现实的战士的巨大的人格精神。”(25) 尽管没有指明具体的方向和可能性,鲁迅先生在文末还是提供了一点亮色,“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无论如何,这当然也是新国民、新世界的开始。《淡淡的血痕中》自然有其指向现实批判与反省“三一八”惨案的意义维度,但同时亦有超越现实的指涉。在我看来,它具有破解奴役的双重策略:一方面是揭示出造物主的统治技艺、拆解其间的奴役机制与角色对话;另一方面,鲁迅在文本中也彰显了反抗与建构的维度:他亮出“猛士”的大旗,凸显出其洞察力和行动力,同时又寄望于改造国民劣根性之后的人类自强——新国民或新世界因此得以产生。 结语:《野草》表面上看和个人性、诗性密切关联,而实际上它也对作者毕生关注的国民性话语有着独特而精致的关注与反思,尤其是它从空间视角的切入显得犀利敏锐而又功力深厚。《失掉的好地狱》中包含了对国民性的解/构两个层面,既对制度、逻辑结构和个人劣根性进行反思,也提出了建构的精神层面;《墓碣文》中结合丧葬话语,鲁迅先生对劣根性的批判更多呈现出对有关功能、意义和姿态的强调,而非内容侧重或缕述;除此以外,《秋夜》中也有对国民性的点评,但难能可贵的是,借助《淡淡的血痕中》,鲁迅先生也提出了改造和革新国民性的可能性。 注释: ①有关著述如谭德晶著《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杨联芬《晚清与五四文学的国民性焦虑(三):鲁迅国民性话语的矛盾与超越》,《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2期等。 ②鲁迅:《致许广平》(1925年3月31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③范美忠:《民间野草》,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④季中扬:《地狱边的曼陀罗花——解析〈野草·失掉的好地狱〉中的隐喻形象》,《名作欣赏》2007年第6期,第44页。 ⑤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⑥黄继持:《鲁迅论天地鬼神》,《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8期,第17页。 ⑦(13)(24)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第216页,第310页。 ⑧钱光胜:《人间世·地狱·无常——鲁迅与地狱探述》,《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104页。 ⑨鲁迅:《杂忆》,《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262-263页。 ⑩鲁迅:《华盖集·“碰壁”之后》,《鲁迅全集》第3卷,第72页。 (11)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12)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14)富强:《提灯寻影灯到影灭——从〈墓碣文〉看〈野草〉》,《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第36页。 (15)季桂起:《国民灵魂的绝望写照——试说鲁迅〈墓碣文〉的主题》,《东岳论丛》2001年第6期,第128页。 (16)黄梓荣:《“具象化的心象”——简析鲁迅〈影的告别〉和〈墓碣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4期,第51页。 (17)具体可参拙文《鲁迅小说中的丧葬话语》,收入拙著《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实人生”的枭鸣》,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164页。 (18)(19)具体可参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283页,第106-107页。 (20)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21)相当经典的论述可参[法]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2)冯雪峰:《论〈野草〉》,见氏著《鲁迅的文学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 (23)闵抗生:《看夜的眼·听夜的耳·夜的史诗——〈野草·秋夜〉重读》,《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2期,第24页。 (25)刘彦荣:《奇谲的心灵图影——〈野草〉意识与无意识关系之探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