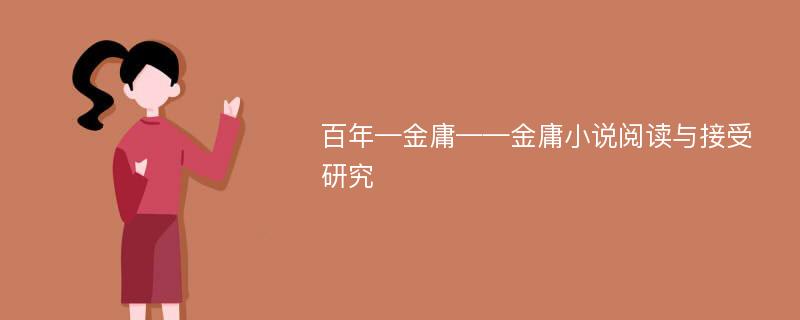
刁军[1]2003年在《百年—金庸》文中认为凡有华人处即有金庸小说在流传,阅读金庸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奇异的文学现象。金庸小说一方面满足了一般读者的浅层阅读快感,让读者在一个充满侠骨柔情的江湖世界中暂时得到精神缓解和感官享受;另一方面又用一个神奇的武侠世界来构成与现实世界的象征关系,借以抒发对现实人生的反思和慨叹,为现代读者提供了一个多层面的审美想象空间。金庸小说塑造了众多中华民族英雄人物的理想人格,读者被代入到英雄人物的事迹里,弥补了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足与遗憾,满足了读者对于张扬个性,追求自由的渴望和审美心理要求。金庸小说运用传统的小说表现手法,发挥了武侠文化的独特魅力,贯注了传统的精神文明和人生智慧,在通俗的基础上包含了丰富的高雅文化内容。“后金庸”时代,武侠小说既存在严峻的挑战,也存在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何菲[2]2007年在《金庸小说接受史研究》文中认为金庸小说迷有无数,而金庸小说给文学界、文化界、甚至历史界、社会界带来的谜也是无数的。金庸小说不但使得武侠小说登上大雅之堂,并且使得通俗小说的地位也大大地提高了,它雅俗共赏,建立了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的沟通桥梁,不仅是通俗文学接受史的一大奇迹,也是整个文学接受史上的一大奇迹。它使得通俗文学更加明白读者这个创作的第二作者的地位重要性,同时也使得严肃文学不得不反思自己在读者方面的缺陷。自金庸小说产生以来,无论是金庸小说自身价值通过港台大陆学者深入研究而得到的逐步呈现,还是金庸小说研究在“世纪末”及世纪之交所经历和折射的文化变迁,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金庸小说接受总的历史进程从最开始的人们争相传阅到后来的专家学者注意再到重视并研究评论它,金庸小说在这个接受历程中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这期间包括几次研究高潮,以及引发的强烈文坛论争,都是相当典型而且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在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发展史中,毫无疑问地,金庸是首屈一指的重要作家,其小说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武侠小说创作的巅峰。虽说倪匡称其小说“古今中外,空前绝后”未免有夸大之嫌,但是在金庸之前,的确找不出任何一位武侠小说作家和作品,曾经拥有过如此盛况不歇的赞许及实质上雅俗共赏的创作水准。那么金庸小说是否已经终结了武侠小说呢?学术界的看法是多种多样的。武侠小说到底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有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以及大陆新武侠小说家们的亲自实践成果如何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总之,金庸热已经成为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研究、探讨,它的这种“奇特的阅读现象”特别对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来说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本论文主要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运用其宏观接受理论即文学接受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来考察金庸小说。“金庸小说接受史研究”的完整过程包括两个基本环节:其一,文献学意义上接受史料的系统整理;其二,批评学意义上接受历程的现代理论阐释。那么,金庸小说接受史研究的思路和具体操作从哪些方面展开呢?一般说,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可区分为相互联系的叁个层面: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研究;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摹仿借用。与此相联系,我们从叁个方面来展开金庸小说的接受史研究: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批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小说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
何开丽[3]2005年在《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文中指出对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状况进行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其发展历程可分为叁个阶段:1980年至1993年为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阶段,1994年至1998年为文化颠覆与理论建构阶段,1999年至2004年为流行经典与反思深化阶段。其研究方法及表现特征主要有叁个方面:一是人文分析法与人文关怀特征,二是文学史方法与历时观照特征,叁是文化学方法与文化研究特征。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在两个方面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示:一是研究的学术规范,二是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眼界的提升。
宋雪冰[4]2014年在《论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创作技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诞生以降,金庸小说风靡世界之景观,历历在目。其势若龙门决口,千里奔泻,断不可遏。探本追源,究其所受欢迎之理,在在昭昭:衣冠儒生,慕其文采斐然;政客巨贾,聊以释闷消忧;红颜稚子,溺于绵绵情意;沧桑耆宿,感之世味幽深。金庸其人,少有奇志,矫矫不群,兼故里多文墨之士,耳濡目染之余,遂坚其慕学发奋之心。及其辗转天涯,一苇渡江,投身香江报业,每日执笔为文,其文艺创作之能方得一施展之地。《书剑恩仇录》横空出世,一经《大公报》连载,市井为之震动,学林为之侧目。其后一发而不可收,堪堪二十余载,十四部长篇巨制先后问世,引动全球华人一同瞩目。遍览金庸全集,佳作盈目,珠玉琳琅,而其中又尤以《天龙八部》一书最为世人所关注。其书篇幅宏大,人物众多,矛盾激烈,家国之恨充塞于历史之间,奇情怪恋翻腾于人性之内。更有甚者,作者将深湛佛学倾注其中,寓佛理于人生,悟人生于大法,创作思路之新奇,包涵思想之丰富,令人击节赞叹。至于创作技巧方面,为予关切尤甚之处。金庸饱读诗书,学贯中西,才究天人,妙笔生辉。作者于传统小说多有会心,于西洋小说技法亦了然于胸。《天龙八部》一书,技巧新奇,功力精湛,融中西于一炉,珠联璧合,妙手天成,置诸现当代文学版图之内,有如葱茏巨岭,巍然昭然。学界于此已有相关研究,前人所述,虽涉中西合璧之论,犹有未备也。予撰此文,共分章节有四:《天龙八部》结构之特点。本章着重于全书结构特点与叁大主人公之关联。《天龙八部》结构宏大而不失灵巧,叁大主人公鼎足成势,每位主人公与周围若干小人物构成单独"人物场","人物场"之间冲撞激荡,形成巨大矛盾漩涡,为此书技巧之一大特色。《天龙八部》之人物塑造。人物乃小说之魂,塑造人物形象之成败于小说之成败有莫大关联。金庸于塑造人物之处,多化用《水浒》《红楼》等传统之法,然于现代西洋小说之法亦未尝轻废。作者熔中铸西,妙合无垠,堪谓一大奇观。《天龙八部》之语言技巧。金庸容纳中国传统典雅白话与现代西洋文学语言于一体,华美而不流于俗艳,古雅而不失现代之风,为现当代文学语言之一大典范。《天龙八部》之叙事技巧。末尾单论叙事,以补前文之未至也。
郭峰[5]2013年在《试论莎士比亚悲剧对金庸小说创作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莎士比亚作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其戏剧以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对后世的戏剧、小说等多种文学体裁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金庸也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开创了中国武侠创作的新纪元。他的作品不断被搬上荧屏,成为了荧幕上的经典;他的作品飘洋过海,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关注。可以说,有武侠的地方就有金庸。“金庸热”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坛一种奇特的现象,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本文通过大量的实例对比,来分析金庸小说中呈现出的鲜明的莎士比亚悲剧风格,进而分析二者的影响与借鉴关系,从中总结金庸武侠小说获得成功的因素,为中国当代文坛提供一条可供借鉴的发展之路。本文主要采用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方法,全文共分为五大部分,引言部分主要描述莎士比亚和金庸的创作在文学中的巨大影响力,指出金庸武侠中存在的莎士比亚悲剧风格,指出本文所做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第二部分主要从悲剧主题的角度出发,从悲剧主题的多重性和体现主题的悲剧根源的复杂性两个方面来论述莎士比亚悲剧对金庸武侠创作的影响,即多种多样的悲剧主题和错综复杂的悲剧根源。第叁部分主要从叙事理论的角度出发,选取叙事要素中的情节和人物来分析二者的影响和借鉴关系,即情节设置方面的悲喜剧结合手法、人物塑造方面的角色非英雄化倾向和角色性格中心论。第四部分主要从审美追求的角度出发,分析二者的创作在这方面所呈现出的鲜明特征,即为了达到特定的审美追求、使文学消费最大化而呈现出的雅俗共赏的普适性特征,以及金庸小说呈现出的戏剧化倾向。最后一部分是在前文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升华,分析金庸武侠成功的因素,总结出借鉴、融合、传播这叁大文学创作成功的基本要素,然后从表现、原因方面来分析中国当代文学处于瓶颈阶段的现状,进而将两者对比,探索出一条中国当代文学从创作、传播到发展的可选之路,使中国当代文学能够更好地走向世界,更好地为传播中华文化而服务。
张璐[6]2015年在《论金庸小说中的疯癫形象》文中指出当代着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在1955年到1972年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他的每一部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中都深受欢迎,其作品之所以如此受读者喜爱,很大程度上在于作品中塑造的众多栩栩如生,脍炙人口,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在金庸小说中不仅有潇洒俊逸的英雄形象和为非作歹的坏人形象,还有众多个性鲜明、诙谐幽默、内涵丰富的疯癫形象,这些疯癫形象在金庸小说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们的文学史价值丝毫不逊于金庸小说中英雄和坏人形象的价值。本文以金庸在小说中塑造的疯癫形象为研究对象,结合疯癫人物的生存环境及过往经历,运用弗洛伊德、弗洛姆、阿德勒等人的心理学理论,以及相关社会学理论分析人物疯癫的原因,从而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深入探讨,在给予金庸武侠小说恰当评价的基础上,分析出金庸笔下疯癫形象的文学史地位和独特的文学史价值,进而挖掘出金庸在创作这些人物形象时复杂的内心世界。本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叁部分。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和金庸小说疯癫形象的研究现状。正文分为叁章:第一章,介绍了“疯癫”一词的传统意义和它在各个学科中的学理意义,进而总结出本文所说的“疯癫”一词的意义。通过对古往今来在文学史上出现的有代表意义的疯癫形象进行追溯和分析,去探究金庸小说疯癫形象对此前疯癫形象的继承与发展,总结出金庸小说疯癫形象和俗文学及雅文学中疯癫形象的不同之处,在此基础上阐述本文选择金庸小说疯癫形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第二章,根据人物疯癫成因把金庸小说中的疯癫形象分为因爱情失意而疯癫、因沉迷复仇而疯癫、因痴迷权名利而疯癫以及无法探究原因的疯癫四类,通过对这四类疯癫形象疯癫的原因进行分析,看到了金庸笔下疯癫人物的可怜可恨之处,看到了疯癫人物的身不由己,看到了疯癫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从而展示了通俗小说家金庸对人性深处的深入探究和对人物内心的深刻挖掘。第叁章,借各方学者对金庸小说的评价准确定位金庸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金庸小说中的疯癫形象与其他人物形象进行比较,总结出疯癫形象在金庸小说中的独特地位。最后在对金庸小说疯癫形象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指出疯癫形象在审美、认识、娱乐方面的文学史价值。结语部分总结全文,重申疯癫形象在金庸小说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指出金庸小说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张群芳[7]2004年在《金庸小说中女性角色的身份认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众多且性格各异,本文主要从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接受与批评来给其定位,认为这些女性角色既有表面上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又在深层次上成为男性形象存在的确证物。
李新祥[8]2013年在《数字时代我国国民阅读行为嬗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全面梳理了国内外数字时代读者阅读行为研究文献,描述了研究现状,讨论了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整合分析了我国历年全国国民阅读及相关调查的数据,对抽象的、理论化的“国民阅读行为嬗变”进行可操作化描述,提炼出一个包括阅读主体、阅读媒介、阅读环境叁个维度的指标体系。根据这一指标体系设计问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基于调查所得4256个样本数据,展开量化研究,描述我国国民阅读行为嬗变的具体表现。调查发现:(1)数字化时代作为阅读主体的读者,在数量上是不断扩大的,总体阅读率上升。但阅读主体的素质是参差不齐的,结构异常复杂。数字时代我国国民对阅读重要性进一步认可,对纸质阅读的前景不如网络出现前那么乐观,但依然有相当比重的读者对“数字阅读会取代纸质阅读”的观点不太认可。读者的阅读需求进一步多元化,知识需求依然是第一需求,但资讯需求提升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思想需求和审美需求没有随着数字化进程减弱,反而有提升的趋向。读者的阅读耐心减弱是数字时代我国国民阅读行为嬗变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点,而阅读能力、阅读目的、阅读积极性、阅读范围、阅读量等指标总体上呈现出积极的变化。个人阅读总体满意度提升不明显,尤其是女性读者的阅读满意度比会上网前还有所降低。读者阅读习惯发生改变的比例较高,但认为“改变程度有限”的比“改变很大”的还是要多,而且读者比较认可自己的阅读习惯。(2)从阅读媒介维度看,数字阅读媒介兴起,书报刊等传统纸质媒介的阅读率提升乏力。但远未到唱衰纸本阅读的时刻,纸本阅读依旧有其魅力,将在很长时期内与数字阅读并存。数字阅读的付费意愿有所增强,但仍然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3)阅读内容方面,功利阅读超越人文阅读,“浅阅读”、泛阅读的取向明显。流行阅读超越经典阅读,信息获取超越知识习得,新闻关注超越文学感受,娱乐追求超越理论探讨,但这并不表明经典、知识、文学、理论阅读的缺失。(4)阅读方式上,由过去单纯的读,变为现在的读、听、看叁种方式并存。随着多种媒体的兴起,尤其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快速浏览和扫读超越慢速凝视和审读,选择性阅读超越接受性阅读,跳跃性阅读超越连续性阅读,“F”式阅读超越“Z”式阅读。在传统纸质文献上深度阅读的频率和时长均有下降的趋向,但研究性阅读并没有受到轻视。(5)阅读环境方面,第一,在途阅读兴起,传统的图书馆、书店作为阅读场所其吸引力有所降低,去咖啡馆阅读的兴起说明读者对阅读环境的舒适度要求进一步提高;第二,读者对个人阅读环境改善的认可度高于对社会总体阅读环境改善的认可度,说明社会阅读环境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第叁,读者认可社会各界为改善和促进国民阅读做出积极努力,大多数读者个人也愿意为此付出努力。结合个人访谈和专家访谈,质化方法与量化方法相结合,多学科交叉探寻国民阅读行为嬗变的原因和影响。作者认为数字化技术引发的阅读媒介发生变化,是我国国民阅读行为嬗变的直接原因;现代市场化、产业化体制下发展的中国媒介的重合性和迭加性,是我国国民阅读行为嬗变的特殊原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制的变化,是国民阅读行为嬗变的环境因素;作为阅读主体的读者,在信息素养、生活形态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导致阅读需求的变化是国民阅读行为嬗变的基础原因。从个体读者而言,阅读行为嬗变的积极影响是阅读更自由便捷,相应的,读者的精神生活也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消极影响可以概括为数字阅读硬件设备存在的缺陷形成不良影响、阅读耐心的减弱、思想深度的缺失等。从社会性影响而言,积极的方面表现为阅读行为的嬗变会推动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的进程,消极的方面则表现为对政治权威的怀疑、对经济发展的迷茫、对文化发展的失望和对社会共同理想的消解。应对数字时代我国国民阅读行为嬗变的对策主要包括:(1)就国民个体而言,首先要树立能够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大阅读观”,要有“阅读是一种权利”、“阅读并非万能”的意识;其次要提升阅读素养;第叁要建构自己的意识框架。家庭组织可以在优化家庭阅读硬环境、塑造家庭阅读软环境两方面努力,特别注意要避免数字媒介成为孩子的“保姆”。(2)政府组织的对策包括:将促进国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并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加大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是促进阅读的根本之策,加强阅读的权利意识,政府在主导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要释放全社会的积极性,努力消除“阅读障碍”和“阅读歧视”,加强基层阅读服务组织建设,提高阅读推广活动的协同性和长效性,提升社会组织参与阅读推广的积极性等。(3)教育组织应该承担特殊重要的角色并发挥重要的功能。就基础教育组织而言,理念层面要明确“掌握知识和技能不是阅读教育的落脚点”,阅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独立精神、思想自由和敢于表达的公民。操作层面主要是建设专业的阅读指导教师队伍、推进分级阅读、迎接数字化等。高等教育组织应成为国民阅读的示范中心,要改善大学生的阅读结构,要发挥高校教师意见领袖的作用,大学生可成为推广国民阅读的志愿者,高校的阅读资源向社会开放,高校应为社会培养专业的阅读指导人才等。(4)媒介组织的对策:遵循扩大信息流量、追求阅读价值、追求易读指数、追求美学品格的原则,优化传播渠道,顺应媒介融合,生产与传播能满足和引导读者需求的阅读产品。(5)公共图书馆应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公共阅读资源,提高阅读服务水平;顺应阅读媒介形态的变动潮流,开展新型阅读服务。其他社会组织也应该为促进国民阅读贡献自己的力量。社会各界应该通力合作,构建更个性化、更快捷、更有效、更准确的交流信息、知识、情感、思想的阅读生态。
张秀丽[9]2019年在《烟台新华书店:文脉传承,打造优阅时代》文中认为悠扬的古琴声中,本土金庸小说研究者、高校文学教授、金庸武侠迷共济一堂,共话各自心目中的“金大侠”;炎炎夏日,非遗文化展区内的小读者们凝视着传承人手中的剪刀、刻刀和绳结,零距离体验“非遗”魅力……这些都是烟台新华书店举办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中的画面。近年来,烟台新华书店
参考文献:
[1]. 百年—金庸[D]. 刁军. 辽宁师范大学. 2003
[2]. 金庸小说接受史研究[D]. 何菲. 四川大学. 2007
[3]. 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D]. 何开丽. 西南师范大学. 2005
[4]. 论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创作技巧[J]. 宋雪冰. 作家. 2014
[5]. 试论莎士比亚悲剧对金庸小说创作的影响[D]. 郭峰. 山西大学. 2013
[6]. 论金庸小说中的疯癫形象[D]. 张璐. 河南大学. 2015
[7]. 金庸小说中女性角色的身份认同[J]. 张群芳. 安康师专学报. 2004
[8]. 数字时代我国国民阅读行为嬗变及对策研究[D]. 李新祥. 武汉大学. 2013
[9]. 烟台新华书店:文脉传承,打造优阅时代[J]. 张秀丽. 走向世界. 2019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金庸论文; 金庸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武侠小说作者列表论文; 读书论文; 人物分析论文; 天龙八部论文; 疯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