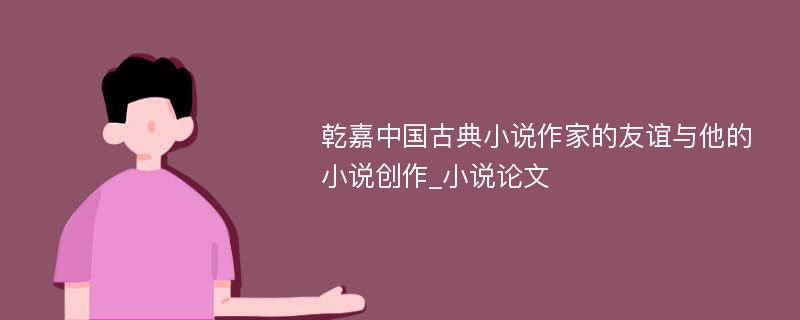
乾嘉文言小说作者的交游与其小说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作者论文,嘉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3)04-0092-06
鲁迅先生认为小说起源于休息时人们彼此谈论故事,“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1](pp.302~303)。谈论故事不仅促成了小说这一文体的形成,在古典小说己臻于成熟的乾嘉时期,它仍然是文言小说最主要的故事来源渠道。唐人有征奇话异之风,唐传奇中的不少名篇如《任氏传》、《庐江冯媪传》、《李娃传》等均是文人将在闲暇或旅行时借以消遣的故事记录下来的产物。宋代这种风气有盛无衰,从宋人留存下来的大量笔记中即可窥见一斑。王明清生动地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夜漏既深,互谈所睹,皆侧耳耸听,使妇辈敛足,稚子不敢左顾,童仆颜变于外,则坐客愈忻忻,怡怡忘倦,神躍色扬,不待投辖,自然肯留,……”[2]苏东坡强人说鬼的轶事更是为后代文人津津乐道,他们或仿效,或拈出这个故事证明这是博通如坡公者尚不能免的雅好。如蒲松龄说自己“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3],纪昀亦自称“说鬼似东坡”[4](p.567)。乾嘉文言小说作家多有喜人说鬼谈异的爱好,征奇话异之风不减唐宋文人,朋友聚会、公余闲暇以此消遣为常事,而所说的故事往往便成为其作品中的素材,并形成了一些写作小圈子,促进了文言小说创作在此期的全面繁荣。
一、谈异之风与小说写作小圈子
和邦额《夜谭随录》“自序”中说:“于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尝遇怪,而每喜与二三友朋,于酒觞茶榻间灭烛谭鬼,坐月说狐,稍涉匪夷,辄为记载,日久成帙,聊以自娱。昔坡公强人说鬼,岂日用广见闻,抑曰谭虚无胜于言时事也。故人不妨妄言,己亦不妨妄听。夫可妄言也,可妄听也,而独不可妄录哉?”[5]卷四《杂记〈五则〉》乃作者与同学聚会时谈狐说鬼之记录:“中秋夜,聚饮于南楼下。……相与说狐”,作者“择尤者五则记之”。[5](p.102)卷十一《市煤人》开篇云:“癸巳仲夏,过访宗室双丰将军,立谈廊下。见一人……怪而询诸将军,将军曰:……乃煮酒设馔,为予详述之。”[5](p.317)为述奇闻而煮酒设馔,亦可见作者及其友人嗜谈异闻之好。袁枚《新齐谐·序》中称其生平寡嗜好,“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6]。曾衍东《小豆棚·序》解释自己何以会写作本书,原因之一就是“平日好听人讲些闲话”[7]。乐钧在《耳食录·自序》中谓此书初编乃“追记所闻,亦妄言妄听耳”[8],初编付梓后,“诸君子竞来说鬼,随而记之,复得八卷”[8](p.165),又成二编。《阅微草堂笔记》成书与之相似,《滦阳消夏录》属草未定,遽为书肆窃刊,即有以新事续告者,于是作者又成《如是我闻》四卷。二书刊行后,友朋聚集,“多以异闻相告”[4](p.228),复成《槐西杂志》四卷。
其时有一位著名的画鬼与说鬼故事者,即画家罗聘。罗聘绘有《鬼趣图》八幅,此画名流题咏甚多。袁枚有《题两峰鬼趣图》三首,其一云:“我纂鬼怪书,号称《子不语》。见君画鬼图,方知鬼如许。得此趣者谁?其惟吾与汝!”[9](p.684)纪昀亦有《题罗两峰鬼趣图》,开篇云“文士例好奇,八极思旁骛”,结尾道:“儒生辨真妄,正色援章句。为谢皋比人,说鬼亦多趣。”[10](p.501)矛头不忘针对他所厌恶的讲学家。从袁枚与纪昀的诗中可见罗聘的鬼画颇受二人称赏,袁枚更将罗聘引为得鬼趣的知己。乐钧亦有《题罗两峰鬼趣图二首》[11](注:二诗其一云:聚窟神香那得焚,九幽甘露更无门。尺缣替写陈人照,摄入豪端便反魂。其二云:空山残月夜窗风,扇手叉头戏恼公。傥过南方逢赤郭,君魔齐避画图中。)。郭麐《樗园销夏录》中云:“罗两峰聘《鬼趣图》,一时名流长篇短咏,题句几满。牛腰之卷凡二。余到邗时止见其一。船山、兰士诸君皆各有作,旁行斜上而书。其令嗣介之属为赋之,乃以三、四、五、七言古今体八首应之。”下文他并详细描绘了《鬼趣图》八幅具体所画,并指出其“大率皆寓言也”。[12]罗聘不但以画鬼闻名,且逢人便说鬼。《新齐谐》卷十四《鬼怕冷淡》、《鬼避人如避烟》两篇均为罗两峰所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罗两峰目能视鬼”条、《履国丛话》卷十五《鬼神》目“净眼”条下均记罗公自言能见鬼物。各书所载其言鬼之情状基本相似,然故事各各不同。《耳食录》初编卷十《髑髅》所记最为详赡。作品开篇云:“余偕数君子看花丰台,饮于卖花翁。座中相与说鬼,罗两峰述一髑髅事,亦可乎(笔者按:疑为“发”之误)一噱。”[8](p.138)罗聘的《鬼趣图》成为当时的一个文化热点,他说的鬼故事亦闻名于世,为人收录于作品中,从这一现象中可见当时文人好奇谈异风气之一斑。
乾嘉时期文人征奇话异不仅仅限于口说耳听,还往往落实到笔头。其时写作小说类笔记和小说专集成风。友人之间以此为尚,互相影响,互相竞争,互相赠阅,形成了一些写作小圈子。如屠绅与其数友人均有志怪作品,他与金捧阊同时作志怪书,洪亮吉题金氏《客窗二笔》诗中一首云:“屋后回环西小湖,谈空时觅北街屠。(此句下原注:谓屠刺史绅时亦著《琐蛣杂记》等书)比邻各逞如椽笔,争作人间鬼董狐。”[13]乾隆六十年(1795年)屠绅自京还滇,其友徐书受送别诗中云:“各有文章堪志怪,莫嫌纸贵费抄胥。”下注:“时君以《琐蛣杂记》见贻,君亦索予所著《谈薮》。”[14](p.20)(注:据沈燮元《屠绅年谱》,此诗见徐书受《教经堂诗集》卷十三,我们所见两种版本《教经堂诗集》(一为梁溪杜氏刻本《教经堂诗集》,一为乾隆间刊本《教经堂全集》均为12卷,不知沈先生所据为何版本,姑录于此。徐所作《谈薮》今有《教经堂全集》本。)《谈薮》为杂俎集,记异闻、轶事、典故等,中有不少志怪短章。
据吴梅先生记载,沈起凤曾与吴翌凤、戴延年等九人结水村诗社,各有诗数十首[15],而吴、戴两人均有笔记传世,其中不乏足称小说者。吴翌凤做《东斋脞语》,载沈起凤与其夫人张灵韵事。(注:《沈薲渔四种曲·跋》中记云:“其夫人张氏名灵,字湘人,亦工词藻,闺中倡和有赵管风焉。薲渔尝泥其夫人以金钗作贽,拜为闺师,为谱北曲一套。其事绝韵,详载吴枚庵《东斋脞语》。”)吴暮年选编《怀旧集》,收录己故师友诗作,沈起凤诗亦被收入,沈名下吴翌凤有长注,其中提到《谐铎》:“司谕祁门时,著《谐译》一书,多所讥刺。余寄诗规之。有云:‘无憀漫续《齐谐记》,舌剑唇枪莫浪传。’盖为薲渔危之也。”由这些记载可知吴翌凤与沈起凤关系密切,吴作为沈的友人,对《谐铎》“多所讥刺”可能造成的后果颇为担心。《东斋脞语》今不见,从其所载沈张事推测当为轶闻类笔记。吴翌凤又有《逊志堂杂钞》十集,其中一些志人条目也颇有小说意味。戴延年著有《秋灯丛话》,为志怪类短章,杂以志人条目,虽文笔疏简,无甚文采,但亦有可称小说者。据杨复吉跋可知此书作于乾隆中后期,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已成书,(注:见《昭代丛书》续编卷二十三,杨复吉跋作于乾隆甲辰(1784年),其中云:“药砰别余十有二年矣。今夏自粤旋里,侨居松陵,空谷闻跫,且得快读别后等身著作,《丛话》亦其一也。”)时间早于《谐铎》。
乐钧与吴嵩梁为同乡、好友,均以诗闻名。《听松庐诗话》谓:“江西诗家,蒋苕生后当推乐莲裳、吴兰雪。两人同为江西人,同为孝廉,同为翁覃谿先生弟子,同以才名邀游王侯公卿间。”[17]乐钧《青芝山馆诗集》中多有与吴兰雪一同出游及一同访友的诗篇,而吴嵩梁《香苏山馆诗钞》中亦时时可见乐钧的名字。卷一《题乐莲裳莲隐图》诗云:“莲裳与我生同丙戌(1766)年,我居东乡之东君临川。两家相距不到六十里,西畴南陌隐隐相钩连。吾家伯兄与君早相识,一军初冠才调闻翩翩。己酉(1789)仲秋访我豫章馆,倾心半面遂结平生缘。……”[18]回忆了两人的同乡之谊和相识经过。在乐钧旅居京师创作《耳食录》期间,两人过从尤密。两人不仅是诗友,也称得上是小说和笔记写作的同好。《耳食录》初编有数篇得之于吴兰雪,如卷一《蕊宫仙史》篇末云:“此篇得于吴君兰雪,余绝爱之,并录于此。”[8](p.13)标明是抄录吴作,卷六《绣鞋》篇末云:“此篇得自吴兰雪。”[8](p.84)《异石》篇末云:“此篇亦吴兰雪笔记。”[8](p.85)可知二篇抄自吴之笔记。同卷《绀霞》开篇云:“吴仲子兰雪,少多诗梦,今记其一。”[8](p.85)作品素材由吴提供。吴兰雪所作笔记今不见传本,或是当时即未结集出版,或是今已散佚,但从乐钧《耳食录》中还可得见其一鳞半爪,就这仅存的三篇看,《绣鞋》与《异石》虽为志怪短章,但文笔生动,《蕊宫仙史》记一位早逝少女生前轶事,富于诗意。其写作风格与乐钧近似,而水平亦不相上下。与乐钧相似,冯梓华在《昔柳摭谈》中也收录了好友陆生西廨的作品;此书卷四《绿衣女郎》篇记柳生一见绿衣女郎而倾心,梦中与其相会事,作者云“曾见西廨杂记中有此传稿,……姑点窜以存之”[19],同卷《名花倾国》篇记陆生梦遇海棠仙之事,谓陆乃总角研友,善吟诗,喜卉木,故有此梦。
宋弼志人小说《州乘余闻》是在其好友纪昀嘉勉下整理成书的。书前小引谓:“己巳(1749)、庚午(1750)间葺州乘,网罗旧事,偶得一二,辄札记之。然志乘举要而已,余者顾弃之可惜,因更述所见闻,并刺取前人文字,都得百数十条,遂命曰《余闻》。草率写录,几不可辨。献县纪晓岚见之,漫谓似临川《世说》。遥遥千载,纵有一二相似,那可便唐突古人。念晓岚之意,聊复芟录。偶然披阅,亦觉神明奕奕,……”[20]纪昀为本书题词第一首云:“六朝小史艳缣缃,萧绮王嘉总擅场。独与临川传《世说》,可怜刘峻在齐梁。”此书写人记事确有几分《世说》的神韵,体例亦仿之,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共24门,但因体例、风格均着意模仿《世说新语》,无甚新意。不过从此书成书过程可看出友人的趣味与好评对于小说作者写作与整理作品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许桂林的《七嬉》与《春梦十三痕》(注:《七嬉》中《司花女子诵诗》篇后小沧评中提到他昔日曾读野客所著《春梦十三痕》,则此书之作先于《七嬉》。未见传本。从小沧评中知其为才学之作。)均是以小说见才学者。许桂林是李汝珍的姻亲、好友,二人不仅是学术上的同道(注:许桂林《李氏音鉴后序》中称李汝珍“方在朐时,与余契好尤笃。尝纵谈音理,上下其说,座客目瞪舌挢,而两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在小说写作上亦互相切磋。《七嬉》中《冰天谜虎》篇后松石道人(即李汝珍)评云:“予与冰天主人有旧,亦曾以谜虎粘其窗。余尚有谜虎甚多,世有与吴君同癖者,当于《镜花缘》内请教。”[21]《七嬉》中《洗炭桥》篇作者自称是受到《镜花缘》所写酒、色、财、气四关的启示而写出来的。而《镜花缘》初稿写成后,李汝珍曾请许桂林之兄许乔林斧正(注:据徐子方《李汝珍年谱》(见《文献》2000年第1期):嘉庆二十年(1815),李汝珍有致许乔林复书一封,称《镜花缘》“日前虽已完稿”,又称“刻下本已敷衍了卷,现在赶紧收拾,大约月初方能眷清。一俟抄完,当即专人送呈斧正”。)。许桂林亦曾见过付刻前的初稿(注:许桂林《七嬉》中《洗炭桥》篇中云;“顷见松石道人作《镜花缘演义》初稿已成,将付剞劂。”),以二人的交谊,他极有可能对李作提出过意见与建议。由此可见,李汝珍与许桂林志同道合、趣味相投,虽然用不同的语体进行小说创作,但在写作上互相影响,作品路数亦相近。
二、作者交游与故事的几种来源
从几种详细标出故事来源的作品看,乾嘉时期文言小说中故事提供者的范围极广。从与作者关系的亲疏看,既有作者的至交密友,亦有仅为一面之交、萍水相逢者。从社会地位来说,上自达官贵人,下至仆役婢媪。与作者关系密切、本人亦爱谈异话奇者是此期文言小说重要的故事提供者。如和邦额的友人恩茂先,《夜谭随录》卷一《梨花》、卷六《异犬》、卷十《秀姑》与《萤火》诸篇故事均得自此人。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此人有文人好奇之癖。如《梨花》篇中写他听完梨花男扮女装的奇事后“神驰者一晌”,并作《梨花》四绝。《秀姑》记太原布客田縠遇其姑与表妹秀姑鬼魂事,末段云:“恩茂先有田数顷,隶顺德,时往征租,与田氏子相交。……茂先下榻其家,因得子女之墓焉。其唱和之作,皆录归以示所亲,予因得以寓目。”[5](p.278)由这两则记载可知恩茂先颇好吟咏,好奇并形之于笔墨,自己虽无小说传世,但可以肯定他对于奇闻颇具文人浪漫气质的热情关注在他讲述故事时颇具感染力,对于刺激作者和邦额的文学想象有一定作用。有的得知作者正在撰写或已经撰有小说著作,主动前来告知异闻或谈狐说鬼。《咫闻录》多处提到友人见其有志怪之书而以异闻相告,如卷八《黑旋风》开篇云:“有朋自远方来,见予志怪,坐而言曰:……”卷九《顾友》开篇云:“未可园先生至,见余假传奇消闲,谈及苏友朱楚翘在天井鹾幕中时,……”[22]
袁枚与纪昀均是交游广、名气大的当世闻人,二人作品中所记故事亦多其时名流显宦所说,如阿桂(谥文成)、董邦达(谥文恪)、裘曰修(谥文达)、尹继善(谥文端)等。两人共同的朋友如蒋士铨、程晋芳等在书中多次出现。有学者认为纪昀书中的叙事者“不少是乾隆年间的显宦学者”,纪昀以此方式取得读者信任,这是“挟知名之士以踵华”[23](p.155)。这种说法似可商榷。因为我们看到,《阅微草堂笔记》的故事提供者中亦有不少在当时被认为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物,如婢仆、艺人、小贩、佃户等。略举数例:卷七记青县一民家厕中敝帚成精事,乃奴子王廷佑之母所言[4](p.142);同卷记一五十余老妇以一少年美妇诱一选人,而夜以身代赚夜合资,乃琴工钱生所言[4](pp.141~142);卷二记一丽妇托言为狐与邻家少年狎,为狐所骂,乃卖花妇所说[4](p.25);卷二十二记佃户刘破车妇云其邻人之女与月作人私会,为鬼所惊,并僵卧,其事遂泄[4](pp.520~521)。说故事的人物身份固然卑微,所说故事亦多鄙俗,但作者却能通过对故事的评点议论,使人从鄙俗的故事中看清世相或悟出某种人生哲理。可见《阅微草堂笔记》的魅力主要源于作者的学识与才力。以纪昀的身份,似不必要“挟知名之土以踵华”。只是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所交往者多为名流显宦,而这些人又多有好奇谈异之癖,因此故事的叙述者亦多名人。
不过,倒确实有一些人主动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作者,欲借名人之作留名或将所写故事传之更广。亦有作者将亲友、门生作品采入己作,如上述乐钧采录吴嵩梁作品。《阅微草堂笔记》中这两种情况也较多。据我们统计,该书所录他人作品主要如下:
1、卷十页208转录门人萧山汪辉祖《佐治药言》二卷中数条近事,作者认为“颇足以资法戒”。
2、卷十八页455摘王昆霞《雁宕游记》中一条,记其于雁宕遇仙事。
3、卷十八页465-466记济南火灾事,乃德州山长张庆源录以寄作者,作者点定字句,录入《姑妄听之》(四)。
4、卷十八页470-471录宝坻王泗和《书艾孝子事》一篇。
5、卷十九页486-487录孟鹭洲自记巡视台湾事。事前有乩仙预告未来,其语皆验,纪谓此“可使人知无关祸福之惊恐,与无心聚散之踪迹,皆非偶然,亦足消趋避之机械矣”。
6、卷二十页499录宗室敬亭先生《拙鹊亭记》。纪案云:“此记借鹊寓意,其事近在目前,定非虚构,是亦异闻也。先生之弟仓场侍郎宜公,刻先生集竟,余为校雠,因掇而录之,以资谈柄。”
7、卷二十二页529-530录门人吴钟侨《如愿小传》,纪公谓其寓言滑稽,以文为戏,而偶一为之,以资惩劝,亦未尝不可。
8、书末附长子纪汝佶所作杂记六则。汝佶所作杂记尚未成书,而“其间琐事,时或可采”。
从上述八种可知纪公采录他人作品入己作有一定的原则,或是所作符合其道德标准,可资法戒,如《佐治药言》、《书艾孝子事》等;或是故事奇幻、文笔飘逸,如《雁宕游记》;或是富于寓意与哲理,如《如愿小传》、《拙鹊亭记》。其他作家采录他人作品亦大体出于道德与文章两种考虑。
三、故事提供的一种流行类型:寓言
《阅微草堂笔记》是此期小说中将故事提供者标得最清楚、详细的一种。作者好友董元度(号曲江)、田中仪(字白岩)、程晋芳(字鱼门)、宋弼(号蒙泉)、申丹(字苍岭)、戴震(字东原)等人的字号在书中反复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这些友人已不满足于仅仅讲述奇闻异事,还要借谈异特别是谈狐鬼故事以讽刺世相、针砭世风、抒发人生感慨乃至表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思想观点。出于这种动机,他们不止是直达所见所闻或转述他人见闻之可异可叹者,还有意无意虚构一些故事,较之单纯满足好奇心的征奇话异有了更多的内涵。在纪昀与其友人形成的这个文化层次颇高的士人圈子里,借谈狐说鬼以寓意成为一种风气。
借狐鬼以讽刺世情,书中最为多见。作者好友田白岩颇善于此,卷八记田白岩僦居一宅,此宅传闻有狐,周兰坡学土曾居之,周去后,狐亦他徙,田居之数月,狐复归。田乃为文以祷,希望幽明异路,各守门庭,狐答以一帖,谓虽异类而好诗书,不愿与俗客为伍,闻其家学渊源,故望影来归,非期相扰。田并以此帖示人。作者谓有人猜测田白岩托迹微官,滑稽玩世,“故作此以寄诙嘲”,又谓此事与李庆子遇狐叟事大旨相类,“不应俗人雅魅,叠见一时,又同出于山左,或李因田事而附会,或田因李事而推演”,[4](p.152)总之此事真实性可疑。但田白岩说此故事的用意则是无疑的,那就是寄托不遇于时、得知音于异类的感慨,借狐之口讽刺惟知歌舞酒肉追欢逐乐的世风。卷十一记其所说真山民故事讽世之意更为明显。田曾与诸友扶乩,乩仙自称真山民,倡和方洽,外报某二客来,乩忽不动。他日复降,众问其故,原来此仙甚狷介,二客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仙拙于应对;一心思太密,礼数太明,仙不耐苛求,故避去。
纪昀的友人们还常借鬼神狐怪之口阐述其对于事理的看法,卷二十一程鱼门言某狐女论构精成胎之理,颇合传统医学阴阳之说,非通医理者不能出此言。卷七姜白岩言某士人行桐柏山中遇地神论鬼神之本始,驳斥宋儒之说。让鬼神现身说法,故篇末作者谓此乃白岩寓言,托之于神。
由于作者及其友人均是学识修养丰富深厚的学者,借狐鬼之口谈论学术问题、阐发某种学术观点亦很普遍。戴震是考据大师,他故事中的狐鬼亦长于此道。卷五记其所说一事,谓两生争《春秋》周正夏正,遭鬼揶揄,言下之意谓其缺乏基本历史常识,争论徒费口舌,不值通人一哂。在借狐鬼之口阐明学术观点的故事中,周永年所说叔姬托梦[4](pp.266~267)和游鹊华闻鬼论文[4](pp.329~330)故事,朱子颖所说泰山经香阁故事(pp.9~10)及何励庵先生所说书生遇狐翁论修仙与读书之道故事(pp.51~52)最具代表性。叔姬托梦故事意在驳斥元朝程端学《春秋解》之臆说,抨击宋学家擅解经文,不顾历史事实,悍戾狂谬。鹊华论文之鬼认为“质文递变,原不一途”,对于后世学者的门户派别之见不以为然。经香阁故事涉及到当时学术界的汉宋之争,有明显的右汉倾向。狐翁论修仙故事亦意在讽刺以圣贤自居的道学家。作者认为经香阁故事荒诞,“殆尊汉学者之寓言”,何励庵所说故事“殆先生之寓言”。周永年自言亲耳所闻的鹊华鬼论文事,作者亦不相信,谓其以平心之论托诸鬼神,周微愠曰其一生不能作妄语,以其人格担保所说为事实。于是此事之虚实似乎成了疑案。
上述数则纪昀友人所说故事,中有多则作者指为寓言。作者心知其为虚构,但“姑妄言之妄听之”,当他指出友人所说为“寓言”,则有像周永年那样坚不承认的,亦有如申苍岭那样以攻为守的。卷十一记申说某士人欲与好诗鬼接谈,此鬼因其衣饰华美,非同调,避不见。作者诘问曰:“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语既未亲闻,又旁无闻者,岂此士人为鬼揶揄,尚肯自述耶?”申则掀髯曰:“鉏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子乃独诘老夫也厂[4](p.149)申苍岭引《左传》典故为自己辩解,亦是间接承认自己所说故事为虚构。
纪昀将友人们所说的这种故事称为“寓言”,其语词渊源当出自《庄子》。《庄子》杂篇《寓言》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释文曰:“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24](p.947)友人们不直接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借鬼神狐怪之口说出,正是《庄子》所谓“寓言”之意。在狐鬼故事己盛行的时代,人们无须如《庄子》那样假造一些子虚乌有的人物,或假托现实名人,而是将故事托于信则真不信则假的狐鬼,省去了不少麻烦,也增加了更多灵活性。
友人们将自己的见解托于神怪狐鬼,纪昀则通过转述加评论的方式将友人们所说的故事转化成小说文本,巧妙地引导读者不执着于故事的真假,而重在体会叙述者及转述者通过故事所要表达的思想与观点,使作品富于理趣。其时一些作品如《谐铎》等也有同样的情况,如卷五《换形乞丐》,此故事乃西蜀李太史墨庄(鼎元)所言,故事叙述一乞丐一日乞于富贵家,归而痛哭不平,怨阎老不公,夜梦十王为其易富贵者之体,天晓则此丐不满于通常之饮食、衣服,并厌薄其妻,妻问知原故,讽刺他“满身都换却,只未换得石季伦富贵命”。作者曰:“此或太史一时游戏之谈,而世之不为疯丐者,鲜矣!”铎评又曰:“太史发此论,可以醒愚。”[25](p.70)卷六《森罗殿点鬼》(pp.79~80)为作者同乡名进士李堡所述故事。作者亦称此为李“游戏之谈”。这两个故事的类型正是纪昀所谓的“寓言”,但《谐铎》以及同时其他作品均未能像《阅微草堂笔记》那样大量转述这种类型的虚构故事,并拈出“寓言”一词以概括之。
从以上所述可知,乾嘉时期谈异之风颇盛,与文言小说特别是志怪题材小说写作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其时小说类笔记与小说专集写作成风,形成了一些创作小群体,在写作趣味与创作风格上互相影响。作者的亲友及各种交游是小说故事的重要提供者。在文化层次较高的圈子里,提供“寓言”类故事颇为流行。
收稿日期:2002-11-29
标签:小说论文; 阅微草堂笔记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寓言论文; 镜花缘论文; 耳食录论文; 鬼趣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