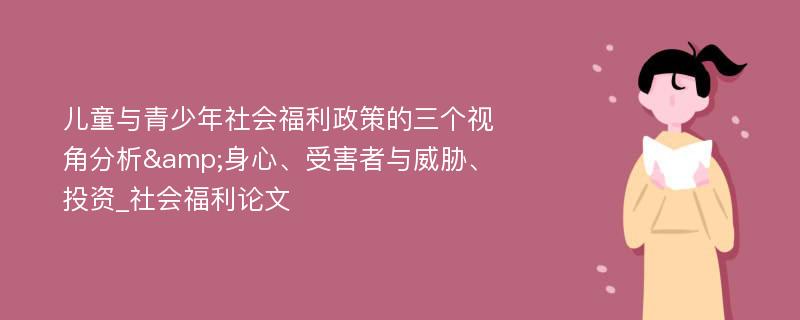
剖析儿童青少年社会福利政策的三个视角——身体与心灵,牺牲者与威胁者,投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牺牲者论文,社会福利论文,视角论文,青少年论文,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身体与心灵叙述:身体
关于身体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探讨的流行领域。那么,如何来看儿童/青少年福利史上对“身体”概念的使用呢?社会学家Bryan Turner(1984)认为,身体社会学是“对社会控制的讨论以及在父权制下男人对女人身体加以社会控制的一切讨论”。虽然在Turner的论述里并没有提到儿童和青少年,但他的这一关于身体社会学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对孩子身体的探讨。他所强调的“身体是愿望对欲望进行实践的场所”,深刻地反映了孩子与成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使成人把他们的“愿望”以不尊重孩子“欲望”的方式强加在孩子的身体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英国大多数儿童/青少年社会福利政策便是由成人“愿望”强加于孩子的身体来组成的,这种组成主要有四种基本方式:食物和喂养;儿童医疗检查;对行动中的身体和说话中的舌头的规范;将生理痛苦强加于初级和工业学校里、孤儿院里和无家可归的孩子的身体上。
当在考察某个时代孩子的身体时,必须记住这是在一个特殊的文化体系里“被经历和被表达的”,“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里,经历和表达都会随时间而变化”。身体并不能以永恒的实体存在,无论从它自身的角度还是从观察者的角度都是如此。与心灵(通常被界定为“愿望”、“自我”、“灵魂”等)相关联的身体“在不同的世纪、阶级、情形和文化里显然是不同的,人们常常持有对其意义的多元解释”。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孩子最初被关注便是通过观察他们在1870-1880年代引入义务教育以后的教室里的身体,这种通过身体而获得的对孩子的认识是短暂的、有阶级局限的。通过生理分级、肉体惩罚、医生检查和处理来对学校里孩子的身体进行规训,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学校午餐是与“身体乃万恶之源”的观点相一致的(Porper,1991:208-217)。
看待身体的一种特别有益的方法就是从“政治解剖学”的角度来看。福柯将人类身体界定为“通过解剖图将骨骼、肌肉、外表和血液置于其中的空间”,结果,该图表成为“诠释身体的一种手段”。对医学感兴趣的研究者最热衷于使用这种图表,医学的目的就是“分析和研究身体”。因此,到19世纪末,医学开始“虚构”儿童的身体,而这种“虚构”又通常以各种各样“道德和教育关怀”的形式出现,这意味着儿童的身体被纳入医学的话语而成为“病理学意义上各部分相互分离的客体”(Armstrong,1983:2-13)。
广义地说,在1870-1914年间,社会科学家、慈善家、医生、教育工作者和社会改革家在看孩子时所看到的都是孩子的身体,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是无家可归的被欺负的孩子,是被忽视的、遭到雇佣来的照顾者侵犯的孩子,是忍饥挨饿的孩子,是生病的孩子,是遭受精神和身体残障之苦的孩子,是被父母残酷虐待的孩子,是几乎被当作成人罪犯对待的犯罪青少年。即使当工人阶级的孩子在学校里时、教育体系也更多的是关注他们病态的、营养不良的、欠缺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心灵和情绪。①这一时期的英国儿童/青少年福利政策有以下重要文献资料来源和举措:Barnardo博士的专著《婴儿生命保护协会》(The Infant Life Protection Society)、针对盲人和聋哑人的教育改革、为学校里的孩子争取免费午餐和医疗检查的斗争、青少年法庭制度的建立等,所有这些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孩子的“身体”上。
这并不能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知识分子对心灵不感兴趣,或者认为心灵和身体分享着同样的功能。“他们更多的是从生理学角度进行思考:将构造精密的身体作为完美心灵的楷模”(Haley,1978:4)。首先,在19世纪学者的思考中,健康的身体占据着特殊的重要地位,随着生理学的发展,该学科力图去揭示“生命的法则”;其次,产生了生理心理学,该学科倡导身体与心灵之间的相互依赖;第三,人们相信体能教育是通向文明人的重要途径,强调个人得到全面培养的必要性。在这样的思考脉络下,“健康的人”受到以下形象的影响:Carlyle的“强健的英雄”、Spencer的“生理完美的人”、Newman的“绅士加基督徒”,特别是Kingsley的“强健的基督徒”。除了对心理—生理学感兴趣的医学专家以外,人们并不去探索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Steedman,1990:12,21,23-45)。
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存在着两种健康: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健康。两者均对心灵带来影响,但在身体是否优先于精神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场所是连在一起的,也许最完美的结合是在运动场上。改革后的英国公立学校在关注心灵道德健康的同时,尤为强调身体健康。对学校以及相信道义的人来说,运动场上蕴含着一系列道德规则,因为只有强健的人方可成为运动员,这样便出现了对运动员的界定:“强健的身体和健康的个性。”因此,维多利亚式的理想人便等同于“健康和刚毅”(Steedman,1990:141-160)。由于这一理想模式很少直接应用于工人阶级的孩子,因此,这些孩子经常被排斥在理想人之外。
二、身体与心灵叙述:心灵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和爱德华时代(1901-1910)强调孩子身体重要性的同时,不能否认在科学领域里对心灵的关注,尤其是在对婴儿的理解方面。至少从1880年代开始,儿童研究开始将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年幼孩子的心理特征以及如何识别“心理不健康”的学生等方面。然而,这时对心理的兴趣仍然基于发展的角度,即从进化的视角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这得到了“重演论”(the theory of recapitulation)②的支持,以表明人类特性中有多少是天生的,有多少是后天习得的。医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意味着在思考心灵时不能再完全将之与身体相脱离。可以说,认识孩子心灵方面的进步使得认识身体更趋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对儿童心灵的观念在19世纪末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有区别的。一方面,后期心理学家批判前期心理学家的著作,认为它们是“异质的”、“异化的”、“无系统的”,忽略了许多重要的因素,在方法论的变量方面也缺乏可比性;另一方面,19世纪主要关注的是心灵的进化层面,但20世纪初至两次大战期间则更多地关注情绪和对社区的个体适应,以及通过心理测试而进行的智商评估。在后一个时期,对心灵的控制和管理成了儿童/青少年福利的一大目标。
上述新的关注通过David Eder博士在Margaret McMillan心理诊所的实践获得进一步发展,在诊所里他注意到“隐藏在儿童病人身体里的神经性创伤”,战争年代里的孩子被描绘成“神经紧张”、“脆弱”、“不稳定”、“不适应环境”、“神经过度敏感”等。Eder的关注是19世纪末“神经官能症发明”的结果,神经官能症认为有些人的痛苦并不是因为发疯,而是源于“心理不稳定”。到1920年代,上述新认识发展成了“用医学方法处理心理问题”。这时,对孩子的心灵加以“观察和监督”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具有很大的变化潜力:“孩子们的不正常就如他们的正常一样尚未被型塑,而且他们通常能按照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去加以塑造。”(Steedman,1990:209)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儿童/青少年的“心理福利”研究产生了新的复杂分析框架。例如,1919年Hector Cameron在他的经典著作《神经紧张的孩子》(The nervous child)中,倡导从预防医学的视角去看待孩子,并敦促专业人士“深入到托儿所和学校里,在那儿去教授心理学、生理学、遗传学和卫生学”。这一视角努力将身体和心灵与社会和物质环境结合起来思考,儿童咨询诊所的数量迅速增加。Cameron认为,儿童的身体是“由其成长的环境来铸造和型塑的,纯净的空气、合理的饮食和自由的活动使孩子身体的每一部分变得强健和匀称”(Cameron,1919:V)。显然,这个时期从以前强调儿童的身体和生理健康逐渐转向强调儿童的心灵和情绪。
到1940年代,关于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医学和精神病学知识已经变成了心灵—身体与环境互动的认识,并强调家庭给孩子带来的深远影响,儿童的心灵得到了挖掘。20世纪初推行的医学检查和学校午餐政策,积累了来自医生、牙科医生和营养学家的经验,人们日益感受到儿童身体的存在和被监督,从而使撰写更为详尽的儿童个体和群体历史成为可能。除了战争年代儿童指导运动以外,人们不仅关注儿童身体的“成人疾病”表现,而更加关注专属于儿童的疾病表现。此时,儿童疾病已发展成为一门专科(Armstrong,1983:55)。
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近90万儿童和青少年出现大量难以预料的社会和心理问题,成千上万的孩子生活在肮脏的环境里,有很多孩子有各种各样的身体和心理疾病。在战争期间,约1.5万至2万撤离者被界定为喜怒无常的、有行为问题的“膳宿提供者”。在撤离阶段,许多人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身体和情绪问题,包括很多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但在立法条款里仍然没有一个条款旨在消除儿童/青少年遭受的身体或心理痛苦。撤离在很大程度上为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个戏剧性地说明儿童的身体和心灵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例子。除了撤离过程对社会的意义之外,它也是导致心理困惑和情绪混乱(这两方面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的依据,部分原因是孩子被迫与父母(尤其是母亲)分离,这影响到战后早期的儿童照顾政策。
英国在儿童照顾政策方面的第一个公共倡导是1946年的“柯蒂斯报告”(Curtis Report)。该报告首先指责地方政府和慈善机构的条件,接着对当时儿童照顾体系里的组织和员工提出批评,最后促成了一个重要立法的诞生,即1948年“儿童法案”(Children Act)。该法案提议创建一个集中的、连贯的儿童照顾组织,并配备受过专门训练的员工和当地政府官员。正如后来许多儿童照顾方面的官员所说,该法案开创了儿童社区照顾和保护的“新篇章”,因为法案强调儿童不仅是“国家的孩子”(在身体和心灵上均需获得照顾),而且是“家庭的孩子”,这样的观点不久在儿童照顾政策的所有方面成为支配的主题(Packman,1981;Heywood,1978)。
这一时期对儿童/青少年福利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重新批判性地将注意力关注在医学上,儿科医生日益把“正常儿童”看作创造“生病儿童”的源头。事实上,人们的兴趣逐渐地脱离“正常”和“非正常”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发展”观念。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Illingworth于1953年发表了《正常儿童》(The normal child)一书,该书力图论述身体和心理的正常状态,这种取向使儿童脱离孤立隔绝的状态,而将其身体和心灵都投入到社区中去。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病弱、神经紧张、孤独的孩子,现在被看成挨打、挨饿、遭忽视的孩子。到1950年代,儿科医生还发现了研究儿童心灵的重要性。1943年,一个叫BPA的委员会建议在儿童咨询诊所和儿童医院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为此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儿童心理分会(Child Psychology Sub-committee),该分会要求儿科医生必须掌握儿童心理学,强调在身体和心理残障之间不能划出严格的界限。因此,到194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在儿童的心灵和身体以及他们的社会认同三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Armstrong,1983:55-63)。
然而,到1960-1970年代,对“儿童时代”的重新发现再次强调身体的重要性,这次主要从身体和性的角度,将儿童看作特殊的牺牲者和一般意义上的弱能者,就性虐待而言更是如此。在提供道德堕落的身体依据方面,受虐儿童起到了隐喻性的作用。为什么1970年代到1980年代人们将兴趣重新投回到与心灵或心灵—身体结合相对的身体上来,其主要原因便是对受虐儿童投资所具有的重要政治意义。
通过以上对心灵—身体二元论的简单回顾,可知从1880年代到1940年代,在英国专业人士和社会福利改革者中,他们强调的重点从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身体(1880-1914)——主要是作为心理观察的客体,作为医学检查和治疗以及学校衣食的容器,作为学校纪律的对象——到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心灵(1914-1940)——日益感兴趣于儿童的神经症和他们的情绪不稳定,对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社会诠释以及心理测试在学校里的开展。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对身体(和心灵—身体相结合)的关注依然保留着,并继续存在于医学、社会、政治和训诫之中,尤其体现在大战期间对生活标准的辩论中,并以此来说明撤离者中的城市贫穷。然而,虽然心灵—身体二元论可有助于诠释这个时期英国儿童/青少年社会福利政策的不同意义,但这个二元论不能完全阐明这些政策,更彻底的剖析还必须导入另一组二元论,即牺牲者与威胁者二元论。
三、牺牲者与威胁者叙述
如果加以关注的话,不难发现孩子在什么阶段或什么场合成为牺牲者:被虐待、被忽视、饥饿、无家可归、战争、生病、没人关心等。英国许多早期的立法,从19世纪初的《工厂法》(Factory Act)到1889年的《防止虐待儿童法》(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Act)、1906-1907年的学校午餐和医疗检查立法、《1948年儿童法》(the Children Act)以及后来1989年的《儿童法案》(the Children Act),无不关心儿童免受广义上的忽视和被虐待的伤害。但在几乎所有早期的英国儿童立法里,充斥着诸如儿童是“无助无能的”、“遵命行事的”、“有某些破坏行为”等这样一些词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表面看来这些保护法案对儿童有许多有利因素,但作为牺牲者的儿童却很少因对他们所处环境的改善而获益,假如没有19世纪的慈善机构(如Barnardo博士的诊所等)和20世纪的国家保护,真不知儿童的生存和福利如何才能得到保障。儿童牺牲者差不多总是被另一种话语所掩盖:如道德谎言,性行为,忠于家庭,保存种族、法律和秩序,成为公民等。有一点对理解与儿童/青少年有关的社会福利政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在儿童保护立法中究竟有多少是将儿童的存在看成威胁者而不是遭受痛苦的牺牲者。通常的情况是,成人把孩子看作威胁者的想象决定着孩子成为牺牲者的现实。
在英国19世纪初的著作或更早时期的立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二元论,本文试举例来加以阐明。
第一个例子。19世纪的慈善行为大多体现在新教徒以及一些杰出人士对孩子的关心上,例如“周日学校”运动的创建者之一Hannah More、脱利党(英国保守党)社会改革家Shaftesbury勋爵等。新教徒在19世纪末发起了对社会行为和道德的改革,他们在欣赏儿童的重要性方面是最为突出的,并看到需要使儿童免受贫穷来保护社会,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才创建“周日学校”。Hannah More在回顾学校的成功时说道:
星期日我们总是能看到那些半裸的、贫穷的、被遗弃的、不幸的、被忽视的孩子在撒谎、赌博、滋事、流浪、满脸不屑地到处乱窜、对父母不敬、对国家诽谤、对上帝不尊、对魔鬼依附——他们现在都在哪儿呢?在学校,在祈祷,在教堂——在为上帝服务,在遵守他们的戒律。(Bradley,1976:50)
在以上这段话里,孩子的存在作为对社会、宗教或道德构成威胁的代表是显而易见的。毫不奇怪,根据新教徒认为孩子天生有原罪(Original Sin)的观点,他们毫无选择地认为孩子是需要规训和教育的,方法是提供必要的援助以保护孩子的心灵和基督教社会。
Shaftesbury勋爵是一位“把受奴役的孩子带往希望乐土”的人,他无疑是19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改革家。他积极地解救“小飞贼”、工厂里和矿井里的孩子,并把流浪街头的孩子(街童)送进简陋的校舍。因为街童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小野人”威胁到维多利亚文明的继续发展。对Shaftesbury来说,社会改革的重任即“解救”儿童并帮助他们免受工业主义和城市不公的伤害。他在日记里写道:“对人类而言只有虚假的希望,根本没有真实的希望,希望只在基督复临(the Second Advent)之中”。他认为“恶”比“善”更有力更持久:“‘恶’是自然的,‘善’是不自然的;‘恶’没有任何要求只要顺其自然即可,而‘善’则需要发现因上帝的荣耀而准备的土壤。”这便是奥古斯丁教义的世界观:末日审判,由降临(the Fall)所推动,由原罪所掌控。
第二个例子。包括有关幼儿福利、法定年龄、虐待儿童、学校用餐、学校医疗和治疗计划等一系列立法。众多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立法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维护英国的种族纯洁性、计算婴幼儿死亡率、保护大英帝国的完整性、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例如,立法反对虐待儿童的重要原因便是担心受虐儿童长大后也会成为施虐者和不合格的公民,人们坚信孩子在被虐过程中已埋下了威胁他们成为好公民的种子。对于挨饿和生病以及不适当抚育的孩子来说同样如此。著名的保守党社会改革者John Gorst在阐述其1906年的著作《国家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Nation)的目的时写道:“给因忽视物质条件而有危险感的英国人带来一个家。”在许多情况下,人道主义和合理的义愤无疑在推动改革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如果没有恐惧因素的话,这些改良法案未必能上升到律法的高度。③
第三个例子。从1861年《工业学校法案》(the 1861 Industrial Act)起,孩子可以因乞讨、流浪或与小偷经常一起鬼混而被送入工业学校。换句话说,孩子被送入这些学校的理由并不是因为犯罪,而是被认为可能给社会及他们自身造成危险。也有专门针对已经犯罪孩子的“少年管教所”(reformatories)。1913年的英国政府报告明确呼吁对这两类机构加以合并,因为两者的目的均在于防止孩子滑入所谓的“犯罪轨道”。在1927年的《青少年犯罪委员会报告》(the Report of the Young Offenders Committee)中,显然将“贫穷的孩子”(deprived child)与“堕落的孩子”(depraved child)联系在一起:“在被忽视的孩子与犯罪的孩子之间,在他们的特点和需要方面很少或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是否会因流浪或无人监控或犯有某些罪行而被送上法庭,常常只是出于意外而已。忽视容易导致犯罪,而犯罪通常是被忽视的直接结果”(Pearson,1983;May,1973)。这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战争期间人们对于社会稳定的愿望。
用“青少年犯罪委员会”的话来说,必须“保护和规训有犯罪倾向以及小团伙结帮倾向的青少年”,委员会还考虑到对那些“尚未犯罪但疏于父母控制、小团伙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保护和规训的孩子”提供服务。这些语言以及隐藏其后的思想把被忽视和遭虐待的孩子与有犯罪倾向的孩子放在一起,也就是把“堕落”(depravity)和“剥夺”(deprivation)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因此,“保护和规训”是经过小心选择的对这两种观念的结合,这样的精心设计目的是为了完成特殊的任务,那就是使受到威胁的牺牲者转化为自我保护的个人和社区市民。从此以后,保护这一概念就不只是简单地在其自身范围内存在,它常常在超出其边界以外的政策里发挥作用。这种建构的结果形成了《1933年儿童和青少年法案》(The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Act,1933),该法案取消了少教所和工业学校之间的区别,将之重新命名为“被核准的学校”(approved schools),强调被忽视的孩子有犯罪的可能性,而不去关注忽视的非犯罪结果(Bailey,1987:91-114)。这样,被忽视的孩子首先被看作威胁者,即法律破坏者,而不是法律被破坏以后的牺牲者。
第四个例子。对1940年代以后英国社会立法的简要回顾表明,英国的政治框架影响着这个二元论在某个时期的方向。二战后英国的儿童/青少年议题可归类为专业化的儿童照顾实务、“有问题家庭”的康复、回应青少年犯罪的上升、重视儿童/青少年身体和性虐待、完善应对问题的策略等。这种政治影响表现在几个阶段:1945-1951年劳动社会民主党、1951-1974年保守主义和多数派、1974-1979年社会民主党和持不同政见者、1979年新右派的兴起。
第一个阶段在儿童/青少年福利工作中表现出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liberal humanitarianism),并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重建家庭。就某种意义来说,不可否认在公共照顾里的儿童更多地被看作牺牲者而不是威胁者。另一方面,其社会和政治意义并非因其作为牺牲者,而是因为孩子本身与家庭之间的关系。John Bowlby在他那产生深远影响的“母爱剥夺”(maternal deprivation)理论中论述道:“离家在外的孩子很可能危险地成为情绪困扰者或犯罪青少年。”结果是,作为牺牲者的孩子重新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再次被作为公共体制(社会)的潜在威胁。发表了《英格尔贝报告》(Ingleby Report)及随后的《1969年儿童和青少年法案》(The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Act,1969)的立法机构便持这样的观点,这些法案通过“犯罪”和“忽视”概念将“剥夺”和“堕落”结合在一起,并将两者都视为有问题家庭的产物(Frost & Stein,1989:32-36)。
在1970年代,人们很少将孩子公然地视为威胁者,因为那正是共识消亡而反精神病学、偏差行为理论、马克思主义和福利右派实践兴起的时候。在那个“激进岁月”里,社会剥夺观点主宰着社会工作。然而,在有关家庭的政治辩论中,也很少有人把孩子作为牺牲者来看,阶级和种族议题支配着激进议程。新右派的兴起并没有影响到以上认识,取而代之的是,对儿童虐待的关注随着一个7岁女孩Maria Colwell遭其继父杀害而转变为“道德恐慌”(moral panic),这在《1975年儿童法案》的“反自然家庭”(anti-natural family)规定里达到顶点。左派对该法案提出批评,并不是因为它对孩子的态度,而是由于它没有提出向贫穷家庭提供经济和社会援助(Frost & Stein,1989:37-39)。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由于传统左翼关心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而使孩子作为牺牲者的处境遭到忽视。当然,应该说这两种地位状况是紧密相连的,但还是有所区别。
最为复杂、显而易见且令人烦恼的牺牲者类型是遭受故意虐待的孩子,包括身体虐待和性虐待。1987年全世界大约有1500万孩子死亡,有许多死于“可预见的、可预防的原因”,在英国有数百万孩子遭受贫穷的影响。为什么一个孩子的死(如1985年在Brent的Jasmine Beckford之死)会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呢?与孩子死亡本身相比,是否表达了公众对孩子作为牺牲者或作为符号(代表着更加麻烦的、普遍的现象)的关心呢?也许答案在一个缩写为MP的议员于1986年在英国国会下议院的质问里:教会是否在帮助拯救国家避免“所谓的许可社会(permissive society)”和因很少得到家庭支持和家规教育而导致的道德规范松懈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位议员回应道:他希望许可社会的预言者“现在必须认识到他们一直以来所鼓励的社会劫难”。显然,这些观点的意义在于把儿童虐待议题与以许可社会为符号的更宽泛的问题联系起来(Frost & Stein,1989:47-48),也正是通过这种讨论才能理解孩子作为牺牲者和威胁者的二元论。
四、身体和心灵与牺牲者和威胁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牺牲者和威胁者的孩子与作为身体和心灵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如下:
牺牲者:他们的身体是有病的、营养失调的、被虐待的;他们的心灵是受折磨的、被惊吓的、担忧的、有病的、被虐待的。
威胁者:他们的身体也是有病的、营养失调的、被虐待的;他们的心灵也是受折磨的、被惊吓的、担忧的、有病的、被虐待的。
换句话说,孩子的“客观”状况基本上是一样的,与他们是否被标签为牺牲者或威胁者无关。这是随标签过程而来的社会建构,该标签过程决定着究竟将他们界定为牺牲者还是威胁者。
现在转到身体和心灵与牺牲者和威胁者的关系:
牺牲者的身体:有病的、营养失调的、被虐待的;威胁者的身体:有病的、营养失调的、被虐待的。
牺牲者的心灵:受折磨的、被惊吓的、担忧的、有病的、被虐待的;威胁者的心灵:受折磨的、被惊吓的、担忧的、有病的、被虐待的。
同样,在牺牲者和威胁者之间身体和心灵的状况并没有什么不同。牺牲者和威胁者的“身体”有着同样的状况(只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有所不同),“心灵”也有着同样的状况。从这个角度说如何合并都没有什么不同,孩子的身体和心灵状况都不能决定其作为牺牲者或威胁者。然而,这两组二元论的存在以及对其意义的理解意味着孩子并不是根据其个人特点而被归类,而是由是否适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决定,也就是说,是被认定的归类。然而,在整个调查研究和立法过程中还是有重要的区别的。在早期的1870-1914年,不管把孩子看作牺牲者还是威胁者,在制定立法时更多依据的是孩子的身体而不是心灵,虽然在后期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对孩子的心灵和情绪越来越关注。
随着对心灵和情绪的日益了解,对心灵和情绪的关注成为一战期间儿童照顾的重要内容,这对儿童发展的认识变得更加复杂,人们开始重视身体与心灵之间的交互影响。这一新变化的结果是在牺牲者和威胁者之间开始产生差异。可能比较好的表述是前者受到了后者的包围,因为成为牺牲者的孩子造成了对公共健康、社会稳定、家庭整合和教育进步的多种威胁。同样,被看作威胁者的孩子因他们的牺牲地位而被关注,即他们的遭忽视或被虐待影响着他们的行为状况和行为方式,因此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威胁社会秩序。
五、投资
上述两组二元论为儿童/青少年福利政策和组织提供了分类依据,虽然这不是对孩子的唯一描述,但却是最主要的认同,或者说是当代人所使用的主要认同,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得以呈现。然而,二元论本身并没有结束,当它们完成了把孩子转化为投资的任务时,便成了一种有意义的政治存在。二元论向投资的转化并不总是很容易,也不总是很成功,更不会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展现,但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促进在种族、教育、家庭、医疗、社会或政治方面的投资,从而实现某种转化。正如Nikolas Rose所说:“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候,从社会的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在思想和实践中,孩子的健康、福利和抚育总是与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责任紧紧连在一起的”(Rose,1990:121)。
有许多英国儿童社会政策的目的既是一般意义上保护国家的未来(如幼儿福利运动等),又是倡导负责的亲职(如NSPCC的工作等)。同样,在惩罚乱伦立法和照顾“脆弱心灵”动机的背后,更加需要把种族和卫生学的思考结合起来,而不是只对儿童福利表示关注,就如同学校午餐服务和学校医疗检查与治疗既表达了对公共健康的承诺,同时也保障了对教育部门的回馈。这一点在1901年随着政治上的“民族效率”运动开展而变得特别重要。然而,最广泛的关注依然是英国民族的生计,因为“像英国这样的一个大帝国……尤其需要民族的强健、勤奋和勇猛”。用1902年布尔战争以后Bentley Gilbert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不健康的学童是所有社会的威胁,这既是社会的自私,也是非人道主义的,因此这样的孩子需要接受治疗”(Freeden,1978:227)。
1918-1945年期间对投资的兴趣非常多元,不太容易将之简单归类。一战时期有关营养和健康的辩论很少说到未来对孩子的投资,说的较多的是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时期儿童福利不太重要的方面,原因是那些营养不良的、有病的孩子没有太大的投资意义。然而,儿童咨询运动的扩展使保障未来变得十分普及,因为该运动旨在控制家庭、协调个人并提高民族的精神健康。在努力处理孩子情绪的过程中,诊所日益得到发展并日趋成熟,然而健康的成熟只有依靠完全适应的孩子才能达到,为了培育这样的孩子就必须理解他们的愿望和担忧。Emmanuel Miller博士在解释运动的意义时说道:“理解产生宽容,宽容给我们指导带来力量。”(Miller,1937:xii)
1945年以后的英国社会日益把家庭作为理想的教育和规范环境,英国皇家人口委员会警告说:“低出生率对英国的安全和影响力将会带来不良后果,并对西方价值观的扩展造成不利影响。”(Weeks,1981:232)对儿童虐待的解决方案显然是对社会和政治共识的投资,这种共识突出地体现在《1989年儿童法案》中。
总之,身体和心灵、牺牲和威胁以及投资,是始终贯穿英国儿童/青少年社会福利政策的三种视角,实质上是成人对儿童的话语建构。前两种视角以两组二元论的方式呈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第三种视角则抛开二元论的对立,将之归入投资的思考之中。
注释:
①关于对儿童身体本质的讨论,参见Sir John Gorst:The Children of the Nation,London:Methuen,1906.
②“重演论”是认为生物个体经过的发育阶段与其所属类群的各种系统发育阶段相似的理论。
③参见Deborah Gorham.(1978):The Maiden Tribute of Babylon,Re-examined:Child Prostitution and the Idea of Childhood in Late-Victorian England,Victorian Studies,21,2,1978,pp.353-379; George K.Behlmer(1982):Child Abuse and Moral Reform in England,1870-1908,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eborah Dwork(1987):War Is Good for Babies and Other Young Children:A History of the Infant and Child Welfare Movement in England,1898-1918,London:Tavistock; Bentley B.Gilbert.(1966):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Insurance in Great Britain:The Origins of the Welfare State,London:Michael Josep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