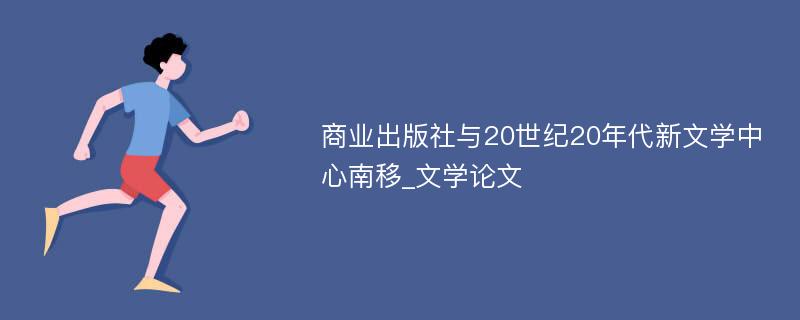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与二十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南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务印书馆论文,新文学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新文学发韧于北京,二十年代开始,中心南移。
所谓南移,是指与新文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新文学领导人、重要的刊物和主要的文学论争活动,都渐渐由北京南迁上海。1920年春,陈独秀绕道天津抵达上海,定居渔阳里二号,标志着新文学中心南移的开端。同年九月,《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从此北京再也没有象昔日《新青年》那样影响遍及全国的新文化刊物了。胡适二十年代开始,也心系上海。1920年夏,他借到南京高校讲学的机会,来到上海。1921年7月,胡适受商务书馆的邀请,又到上海进行了一个半月的工作访问。临别之际,写下了“多谢主人,我去了!两天之后,满身又是北京尘土了!”①的诗句,其对上海的留恋之情,溢予言表。鲁迅虽到1927年才定居上海,但那是经过北京、厦门、广州之行的比较之后才选定上海的。1929年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②鲁迅的到来,意味着中国新文学中心南移的格局,基本确立。
二十年代的上海,确有许多当时北京所不及的地方。象《小说月报》、《创造季刊》这样大型的新文学杂志,在当时国内真是绝无仅有。人员众多、声势浩大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也主要以上海为活动中心,但影响却在全国。在文学论争上,当时国内恐怕再也找不到有哪一场文学论争的规模、影响,可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论争相比拟。这场论战从1922年一直持续到1925年,为时三年,涉及到新文学发展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吸引了国内差不多所有新文学人士的注意,甚至连在北京的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都撰文参与,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少有的。上述情况,在我看来至少可以归结为如下结论:新文学在北京兴起之后,其中心地位逐渐为上海所取代,而这一过程,基本上是在二十年代进行的。③
那么,为什么从二十年代开始,新文学中心得以南迁上海呢?有许多研究表明,二十年代中国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变动和差异,使上海成为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枢纽,特别是南方革命政权的建立,北伐军顺利攻克沪宁,吸引了大批激进青年的南下。④这批激进的青年,都是新文化新文学的热情支持者和响应者,他们的南下,为新文学中心南移,提供了人员和群众基础。而北方的北洋政府对新文化人士的政治迫害及保守的文化政策,使得大批新文化领导人离京南下。如陈独秀、鲁迅的南迁,都与政治迫害有关。二十年代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变化及差异,为上海新文学的迅猛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我以为还必须指出的是,一个区域文化中心的形成,单靠几个人、几个文学社团和几家刊物,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借助于该地区某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组织力量的文化组织机构的作用,才能确立起该地区文化中心的形象。五四时期北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新文学诞生的摇篮,是与蔡元培主持下北京大学的文化地位及社会影响分不开的。二十年代,上海之所以能够逐渐取代北京而成为国内新文学的中心,同样是与当时上海拥有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上都远甚于北京大学的文化组织机构——商务印书馆分不开的,正是商务印书馆的文化组织作用,二十年代上海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新文学人士的注意,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学人士活动的重要区域。
一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929年,是上海一家民营的印刷出版企业。二十年代后,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继北京大学之后,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化组织机构,这首先与主持商务印书馆日常工作的张元济有关。张元济晚清翰林出身,曾参与戊戌变法,后变法失败,被革职,到南洋公学任职。他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应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之邀,到商务工作。1902年商务建立了集编辑、研究和出版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该所下辖英文、国文和理化三个部,另外还有九个杂志编辑部。从商务印书馆内部机构设制及决策人的指导思想来看,商务印书馆决不是一个单一以出版为目的的编辑机构,而是一个蓄纳文化人才,研究和传播新文化的文化组织机构。文化人才的吸纳,是商务印书馆着重考虑的问题,这不只是为了企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商务领导人张元济一直希望使商务印书馆成为南方的文化组织机构,因此,他保持与文化界人士的密切关系,凡在当时有影响的文化人,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均与之有关系。1916年7月,张元济拜访吴稚晖,明确表示商务印书馆“注意于培植人才,不专在谋利”。⑤1918年张元济又提出商务印书馆“永久之根本计划”三条,第一条便是“用人说”,主张“培植新来有用之人”。⑥1920年3月,商务印书馆决定“设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之,请其在京主持,每年约费三万元,试办一年。”⑦商务印书馆的开明作风,吸引了大批文化人。据在商务任编辑的叶圣陶、王伯祥回忆,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东南地区的文化汇集地,南来北往的文化人常与之交往,编译所编辑人员最多时达三百多人,汇聚了各方面的精英人才。⑧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文化组织机构,其最大的优势在于一有雄厚的资金,二具备强大的发行网络。这使得在文化事业上,商务有经济实力延聘文化人,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如二十年代泰戈尔访华,他在上海的活动经费均由商务资助。⑨其他如拟议中邀请法国哲学家伯格森到华讲学,商务印书馆也答应给予资助。⑩同时,商务能够及时将一些新的思想言论组织出版,通过遍布全国的发行网络,将书刊发往全国各地,真正形成全国性的文化影响。
那么,为什么商务印书馆在二十年代以前,不能象北京大学那样成为国内有影响的新文化组织机构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商务印书馆高层领导虽然思想开明,见识很广,但象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高凤池及王显华、鲍咸昌等人,都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思想也非常保守,基本上采取旧式手工业作坊的管理方式,故张元济与高凤池之间常常发生激烈的冲突。1916年9月6日在用人方针上,张元济力主非用新人不可,而高凤池则主张“宜用旧人,少更动”。(11)1917年1月19日,张元济荐举留学归国人员徐新六到商务任职,但高凤池以“留学生多靠不住”为由加以拒绝。(12)商务印书馆领导层的这种意见分歧,使得他们在用人政策上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在1920年之前,商务的杂志基本上掌握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人手里。虽然个别杂志也介绍国外的新思想新学说,但那也无非是做做姿态,实际上包括《学生杂志》、《教育杂志》主编朱元善在内的许多人,既不通外语,更不了解新学说的内容和意义了。(13)第二,商务印书馆在二十年代之前,企业本身也处在摆脱危机和加紧基本建设阶段。1910年因商务老板夏瑞芳陷于橡皮股票风潮,致使商务印书馆亏空巨大,濒临倒闭边缘。1912年张元济因教科书出版决策失误,而在竞争中为中华书局击败,教科书大量积压,资金无法收回。1914年总经理夏瑞芳遭刺生亡。(14)1916年商务因财政困难,被迫停印若干书稿。可以说,在1917年之前,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状况和资本积累并不很好,这就使得张元济等人不得不在摆脱经济困境,筹措资金,扩大企业规模上多下功夫,而对文化组织建设事业则一时难以顾及。第三,在二十年代之前,新文化运动虽已在北京出现,但其影响和社会地位还未最终确立。对于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民营企业来说,为保证经营,它们是不太愿意冒政治上的风险。所以,那些带有“过激”色彩的文章书刊,商务印书馆一概予以拒绝。如1919年3月,某俄国人请商务印书,张元济考虑政治上可能有麻烦,提出由俄领事馆出函证明此书无“过激”之处,才予接受。(15)
上述情况发展到二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了。这首先是张元济在与商务印书馆内部的教会派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开明派在商务决策层中形成绝对多数。在对外竞争中,商务印书馆最终击败中华书局,确立了自己在国内出版界的稳固地位。(16)在经济上,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也有了起色。从1918年开始,商务印书馆的存款出现剩余。1919年现款总计达一百万元,到1920年增资为三百万元,1922年又增至五百万元。(17)这样雄厚的资本,使得商务印书馆在二十年代有足够的经费资助新文化新文学书刊的出版。如《北京大学丛书》和《共学社丛书》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筹办出版。在商务印书馆摆脱企业自身的经营危机过程中,新文学运动本身的地位也得到确立。象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都已成为国内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新文学取代旧文学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1919年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列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和《妇女杂志》,加以严厉批评。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也严厉批评商务印书馆。(18)在这种情况下,商务印书馆方面积极延聘新文化人士,加强商务编译所的编辑力量。1920年10月,张元济,高梦旦亲赴北京,广泛结识新文化人士,并邀请胡适到商务编译所任所长。年底,任用沈雁冰改革《小说月报》。1921年又招聘王伯祥,杨贤江、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为商务印书馆编辑,聘陈独秀等为馆外名誉编辑。(19)商务印书馆适应时势所进行的文化改革措施,吸引了一大批新文化人士到商务工作,不仅商务印书馆在社会上的地位大大提高,而且真正起到了文化组织的作用,可以说,当时一些影响巨大的新文学文化书刊的出版,大都与商务印书馆有关,当时一些重大的文化组织活动都离不开商务印书馆的资助,当时的一些新文学人士也愿意与商务印书馆建立联系,商务印书馆确实承担起二十年代新文学发展的社会组织工作。
二
商务印书馆的内部改革之所以对二十年代中国新文学中心南移产生影响,这的确反映了商务印书馆在二十年代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地位和影响。
比较一下二十年代北京与上海的新文学发展情况,我们不难发现,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内并不缺乏新文学运动的领导人。象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始终在北京生活。北京的新文学社团,也不在少数。象语丝社、未名社、莽原社等等,不仅开展活动,而且还都拥有自己的刊物。但是,这些新文学社团活动,缺乏象商务印书馆那样一个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和强大发行网络的文化组织机构的支持。二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每年的资本都在三百万元以上,而1920年北京大学的预算为95万元,并且这些预算因受北洋政府财政影响,经常不能及时拨款,所以,二十年代开始,北京大学的教育经费极为拮据,1920年曾发生教师到教育部索要拖欠的教师工资事件。(20)教师的工资尚且不能及时分发,学校当局当然更拿不出充足的资金来资助新文学人士的聚会、组织活动和出版了。《新潮》开始发行时得到北大校方的经费资助,但二十年代经费拮据,校方无力资助,杂志便关闭。(21)《语丝》及其他一些新文学杂志,大都是北大教师和学生自己集资印刷、发行,这些杂志在文学史、文化史上虽然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实际上,这些杂志的发行量极其有限,影响范围当然也受到限制,它由学生自己销售,发行范围基本维持在学校范围内。对比之下,商务印书馆对新文学的支持显得十分有力,象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都被商务印书馆聘为馆外名誉编辑,给予优厚的聘金,其他象沈雁冰、郑振铎、谢文逸、顾撷刚、王伯祥、杨贤江等初出茅庐的文学新人,商务印书馆也以优厚的待遇,吸纳编译所工作。对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商务印书馆借助文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大型丛书,广泛宣传,扩大影响。如商务印书馆先后推出“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研作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在文学刊物出版方面,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小说月报》自1921年改革之后,始终是国内最大规模的新文学刊物。这份杂志尽管在改革初印数曾达一万册,但此后的销路却一直在下跌。(22)假若不是商务印书馆下决心支持和扶植新文学,那么,这份杂志根本不可能维持这样长久的出版,当然更不可能吸引全国的新文学人士,那样系统、充分地探讨文学问题。对比之下创造社出版的《创造季刊》等,就因为缺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机构的资助,而在短期内便停刊了。(23)
商务印书馆对新文学的扶持,不只是吸引人才,研究问题和出版、发行新文学书刊杂志、更重要的是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努力,中国的新文学第一次做到了真正面向社会。二十年代之前,新文学尽管在社会上造成一定影响,但影响范围基本还是在学校范围内,换句话说,许多文学社团、文学杂志和新文学的热烈响应者,均是学校范围内的一种文化实验。造成这种状况的很大原因,是与新文学在传播过程中缺乏强有力的宣传发行网络有关,新文学的传播最初主要是师生自筹经费印刷、出版刊物,由学生自己销售,这样,许多新文学作品以及新文学的研究成果无法直接传播到社会上,更无法在整个社会范围里,让人们普遍了解和接受新文学。自商务印书馆接手新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工作后,中国的新文学第一次有机会实现在全社会的普及。这应归功于商务印书馆强大而有效的发行网络。据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统计,到1918年为止,商务印书馆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馆34个,另外设香港分馆和新加坡分馆负责对海外发行,在北京和香港设有分厂,能够单独印刷,出版书刊。这三十六个分支机构,实际上使商务印书馆能够在全国各地推销它的出版物,并通过香港、新加坡这两个窗口,向海外扩大影响。(24)二十年代开始,商务印书馆大量印刷、出版新文学新文化书刊,据统计,1921年至1930年这十年间,商务印书馆单文学类书籍就出版815种,共计2269册,艺术类书出版263种,共计571册,在这些出版物中,应该说有许多书籍都与新文学新文化所倡导的内容有关。(25)1929年商务编印《万有文库》,都凡一千零十种,一亿一千五百万言,分装二千册,这套大型丛书几乎全是普及和宣传新文学新文化的思想,其中的国学基本丛书,也是抱着“整理国政”的新眼光,重新确立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位置。(26)这些书籍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分支机构散布到全国各地,使得新文学的发行范围从学校扩展到全社会,不仅造成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宣传运动,而且也为新文学提供了庞大的读者队伍和作者队伍。茅盾在回顾文学研究会时曾认为,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社团,并不存在,但作为一种共同的文学主张,文学研究会主要通过“文学研究会丛书”体现出来,(27)换句话说,是商务书馆的积极支持和组织,“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出版和发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从而赋予文学研究会这一社团的存在意义。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是商务印书馆所起的文化组织作用,促进并推进了二十年代新文学的发展。象《小说月报》改革初仅仅刊发一些成名作家的文学作品,到后来不断推出文学新人,如丁玲、巴金等人,说到底,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吸引了国内越来越多的文学新人的投稿。商务印书馆通过自己的出版物,有意识地组织及推进二十年代新文学的发展,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继北京大学之后,国内最具实力的新文学支持者和文化组织机构,也为三十年代上海成为中国新文学中心,奠定基础。
三
商务印书馆参与二十年代中国新文学中心南移活动,实际上也是参与铸造一种新型的文化产业的过程。在商务印书馆之前,近代中国没有企业参与文化建设的文化生产形式,许多手工印刷作坊出版书刊,仅仅为了追求商业利润,作坊老板在文化上并没有多少发展的眼光。后来象爱国书社等文化人士创办的一些学社书院,虽印发书刊,但这些印刷、出版机构的规模极其有限,差不多只是一个宣传部门。掌管这些部门的人,既不懂得管理,手里又缺乏足够的资金,故这些小型的出版机构往往维持不了多久,更自动倒闭。直到商务印书馆的出现,特别是1902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之后,文化规划与企业生产形式才得以有机地结合起来。商务印书馆的决策人士不仅要考虑企业的生产经营,同时还根据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制定出版计划,通过出版和发行新的文化读物,培养和刺激社会对新的文化内容及形式的需要,从而组织起新的文化秩序。茅盾在回顾商务印书馆改革《小说月报》的缘由时,认为商务印书馆痛下决心,改革《小说月报》,首先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即不让杂志在经济上亏本。(28)茅盾的观点反映了一种实情。一家民营出版企业,当然要追求商业利润的实现,至少在经营上必须做到收支平衡。但问题在于商务印书馆能够将企业生产经营方式与文化发展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加以考虑,它不只是追求商业利润,更重要的是文化上它有自己的建树,换句话说,商务印书馆是从文化发展的需要,来制定出版计划,而不是盲目依照读者的口味来出版读物。如果照当时上海一般市民的阅读趣味和需求,商务印书馆完全可以继续大量出版鸳鸯蝴蝶派的言情消闲之作,因为这方面的读者市场相当大,甚至比新文学的读者要多。1922年,鸳鸯蝴蝶派杂志《红杂志》创刊,不久销路便很好。茅盾在二十年代致周作人的信中也谈到,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比《小说月报》销路好。(29)商务印书馆在经济上不赔本的原则下,追求文化上的价值,这是商务印书馆所开创的文化产业的真意所在。当然,1922年王云五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期间,商务也出过以刊发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的《小说世界》,但这种出版物,从商务印书馆的整个出版计划看,并不构成影响,商务印书馆的总体出版规划,还是立足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整理,对新文学新文化大力扶植和支持。这既表现在商务印书馆的组织人事上,始终不渝地任用新文化人士。《小说月报》自1920年起,主编人选虽有过变动,但自始至终都是由新文学人士负责,刊物的宗旨一丝一毫不受影响。在文化出版规划上,商务也始终承担新文学新文化的组织、宣传和普及工作。规模巨大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及后来的“万有文库”,都是在二十年代进行的,这些出版物极大地普及和扩大了新文学新文化在社会上的影响。如果说,新文学新文化最初在杂志和报刊上进行宣传鼓动时,还仅仅是一种文学文化上的设想和尝试,但通过商务印书馆的文化生产形式,特别是商务印书馆组织各方面人士,大量刊印新文学新文化书籍,使得新文学新文化成为一种客观的文化事实存在下来,在大量新文学新文化书刊面前,谁也无法否认新文学新文化的存在价值了。
商务印书馆民营企业的独资形式,使得商务印书馆在出版和文化组织方式上,保持彻底的民间色彩。所谓彻底的民间色彩,是指商务印书馆的整个出版和发行,不受政府的控制。商务印书馆在本世纪初,曾吸收过日本人的投资,但到1914年,商务董事会完全收回日本股份,使企业真正保持民营性质。商务印书馆在经济上凭借自己的实力,不受政府牵制。在组织人事上,张元济等商务高层领导,虽与政府人士经常往来密切,但这种关系不属于政府部门上下级臣僚之间的关系,而是完全独立于此之外的一种个人之间的交往。如张元济与蔡元培、梁启超、严复的关系,便是友人关系,后来张元济与陈独秀、胡适的关系,也是建立在文化志趣相投的基础上。这种以文化志趣和个人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文化出版机构,带有浓郁的同人文化特色。这我们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中,就可以发现。改革之后的《小说月报》与其说是一份以文学研究会为依托的文学刊物,倒不如说是一份由茅盾、郑振铎等人编辑、出版的同人刊物。因为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在理论上主要倡导“为人生的文学”,在刊发的文章上也集中反映了办刊者个人的趣味与文学特长。茅盾和郑振铎主要是文学批评家,在他们主编《小说月报》时期,办得最有特色的也是与他们个人特长相关的文学批评及外国文艺思潮的翻译介绍。文学创作不是说不重要,但对他们来说,文学创作是证明其批评观点和文学主张合理性的一种具体材料。因此,在相当一个时期,这种批评家同人办刊的特色一直未变,直到叶圣陶接手编辑《小说月报》,文学创作栏目才真正体现出自己的特色,但批评和翻译栏目反倒不如茅盾、郑振铎执编时期。这些现象,实际上说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出版和文化组织形式,基本上是以同人关系进行联系,这种关系也反映在商务印书馆在对待新文学新文化的态度上,基本上是遵循文化自身的价值准则,而较少受政治的影响。商务印书馆对于那些明显有政治色彩的出版物,总是持审慎态度,甚至象孙中山的文集,也被张元济婉转拒退。(30)这不是说张元济对政治革命缺乏同情,而是他将政治同情与文化事业作了区分。一个庞大的文化出版机构,要长期合法地存在下去,就不能象那些刊发激进政治宣传品的地下印刷所那样,印一批宣传品散发一下便完事。文化出版机构要有自己立足之本,这个本就是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商务印书馆的决策者和编辑人员,确实都非常着重文化本身的精义所在。一些后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商务印书馆人员,他们在商务印书馆期间,并没有完全被党派的立场所左右,而筹划出版宣传小册子,相反,他们的注意力还是在出版文化读物。(31)正是这种民间出版家的身份和立场,商务印书馆在二十年代激进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不仅没有举步不进,相反,出版的天地更加开阔了。各家各派的著作,只要在文化上独树一帜,确有内容,不管作者的政治面目如何,商务印书馆统统予以出版。象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纲要》和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即《俄乡记程》),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倒不是商务印书馆对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有什么偏向,而是胡适和瞿秋白作为文化人,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当时文化的某种趋向,并且他们本人在哲学史和文学创造上确实具备了较高的修养和造诣,因而,商务印书馆正是从他们个人的文化成就上,接纳并出版他们的著作。
四
商务印书馆的这种民间独立地位,对于二十年代新文学的发展来说,具有健康的保证。作为正式出版物,商务印书馆必须保证文学刊物的文学特色,不管理论上人们对“文学性”作何种阐释,在二十年代激进的文化氛围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作品及文学刊物,始终坚守文学的纯正立场。虽然《小说月报》也发表“血与泪”的文学,但这种对现实的关注,与政治的关注有区别,它不是直接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和手段,而是作家本身对生活的一种经验,从这一意义上讲,三十年代新文学在上海能够蓬勃发展,使上海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中心,恰恰是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文化生活中崛起,通过商务印书馆的不懈努力,从经济、文化组织形式和文化自身的发展要求等诸多方面,为新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与二十年代中国新文学中心南移活动的密切关系。
1994年11月改定
注释:
①《胡适日记》上册P210页,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
②《鲁迅全集》第11卷P29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③茅盾二十年代末完成的长篇小说《虹》中,有一段描写,在五四初期,对话中作品人物明确说北京“那边是新文化中心”。而到了二十年代,主人公的对话中则说上海是“文化的中心”。参见茅盾《虹》P105,P276,开明书店1933年5月版。
④邓颖超曾回忆说,二十年代一些激进的组织活动,在北京是地下,在上海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半公开,在广东则是公开。参见《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记录》,收入《五四运动回忆录》续,P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⑤⑥(11)(12)(15)(30)参见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P128,P152,P129,P166,P176。商务印书馆1991年12月版。
⑦⑨⑩于冶《梁启超与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P504,P508,P507。商务印书馆1987年1月版。
⑧王湜华《王伯祥与商务印书馆》;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参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P276,P300~301。
(13)茅盾在回忆录中说,宋元善根本不懂日文,只能根据日文中的汉字来猜测文章的大至意思,有时译出来,发现与他猜测的意思毫无关系。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P12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4)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收入《商务印书馆九十年》P109。有关橡皮股票风波,参见陈诒先《上海橡皮风潮》,载《上海地方史资料》(三)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4年7月版。
(16)参见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陆指出,当时上海书业公会会员40余家,资本九百万元,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占资本五百万,中华书局二百万。载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P278,中华书局1957年5月版。
(17)(24)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收入《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P750,P249,商务印书馆1992年1月版。
(18)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P207,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
(19)参见《商务印书馆大事记》,商务印书馆1987年1月版。
(20)北京大学1919年和1920年的预算经费,分别为792459元和957579元。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上册)P76,明报出版社出版。关于北洋政府拖欠教师工资和教育经费的材料,参见吴惠龄主编《北洋高等教育史料》第一集P383,P392,P397,P39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版。
(21)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收入《五四运动回忆录》续。
(22)1921年10月12日,茅盾致周作人的信中提到“关于《小说月报》编辑一事,自向总编辑部辞职后,梦旦先生和我谈过,他对于改革很有决心,对于新很信,所以我也决意再来试一年。”茅盾1922年9月22日致信周作人,说《小说月报》“今年销数比去年减些。”同年10月2日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鸳鸯蝴蝶派小说在上海重新抬头。参见《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P113-114,P121-122,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
(23)郭沫若回忆《创造》月刊、季刊出版情况时,曾说泰东图书馆因资金缺乏、无力维持刊物,故《创造》办了一年便结束。参见《沫若文集》第七集P156-157,P167-168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8月版。
(25)《商务五十年》,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P775。
(26)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载《现代》第三卷第一号。
(2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P160。
(31)如,后来任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长的谢冠生,及后来任中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他们在商务时,都以编辑和出版文化书刊为己任,至于编许多宣传品,都是在商务印书馆之外进行的。
标签:文学论文; 商务印书馆论文; 文学研究会论文; 张元济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上海活动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1920年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茅盾论文; 胡适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上海论文; 新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