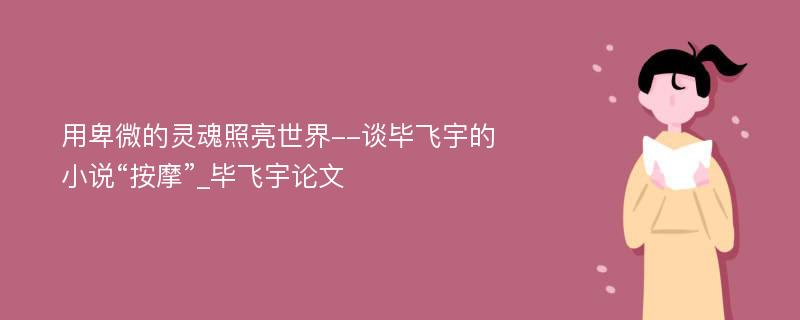
用卑微的心灵照亮世界——论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卑微论文,心灵论文,世界论文,毕飞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毕飞宇是一个极力推崇叙事力度的作家。他常常盘旋在那些世态人情的微妙之处,以极为敏捷的心智和眼光,捕捉和发掘各种难以言说的人性特质,并以内敛而又短促的叙述话语,迅猛地将之呈现出来,果断、冷静、强悍,且不留余地。因此,读毕飞宇的小说,我们总会在不经意中体会到某种猝不及防的震慑力——它既来自隐秘人性的自然呈现,又来自叙述本身的锐利和迅猛。像《青衣》里的筱燕秋对待自己的徒弟春来;《玉米》里的玉米敌视那些与父亲有瓜葛的乡村妇女的眼神,以及处理自己婚姻的决绝;《平原》里端方对待同伴红旗以及村支书吴蔓玲等等,都给人以强劲的内在力度和审美上的艺术震撼。
这一点,在他的长篇新作《推拿》中再一次展示得淋漓尽致。《推拿》以一群生活在现实边缘地带的隐秘人群——盲人推拿师们作为叙事对象,通过对他们敏感、繁复而又异常独特的内心世界的精妙叙述,既表达了他们置身于现实世界中的无助和无奈、伤痛和绝望,又展现了他们身处黑暗世界里的彼此体恤和相濡以沫,也折射了他们渴望用自己的心灵之光照亮现实世界的朴素意愿。
一
记得在《失明症漫忆》里,萨拉马戈曾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突然失明的世界——因为与失明者的对视,一群又一群人的眼前突然变成“一片浓浓的白色,仿佛睁着眼睛沉入了牛奶的海中”,于是一切现实秩序顿时失去了作用,饥饿、残忍、肮脏、阴谋,所有丑陋的人性开始泛滥,那些看似井井有条的现代文明瞬间瓦解,医院、超市、汽车……这些现代物质文明的产物,都变得不再有任何意义。显然,萨拉马戈是想通过一种寓言的方式,将曾经拥有光明的人群强制性地置于黑暗之中,以此来打开幽暗的人性风景,并对现代文明的存在价值提出尖锐的质疑。与《失明症漫忆》不同,毕飞宇的《推拿》则以写实化的手段,叙述了一群盲人的生活境遇,让他们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通过“推拿”这一特殊的谋生方式,与现实世界建立起各种微妙的联系。但在叙事的背后,同样也凸现了很多幽暗的人性,展示了这一特殊人群内心深处许多难以言说的疼痛。
这种疼痛,当然是源于盲人们自身的残疾。在《推拿》里,因为看不见,王大夫把“对不起父母”作为自己的原罪,还得忍受“对不起弟弟”的伦理煎熬;因为看不见,小孔的父母一定要她找一个能看得见的男朋友,她不敢告诉父母自己爱上了全盲的王大夫,谎言使她的幸福爱情变得难以坦然地面对一切;因为看不见,沙复明纵使拥有非同一般的雄心和能力,也进入不了健全人组成的主流社会;因为看不见,都红即使在音乐方面极有天赋,她的容貌即使美到极致,但她的自尊心还是一再受到伤害。因为突然失去了视力,年幼的小马居然果断地选择惨烈的自戕,成年后又拒绝一切与“公共”有关的事物,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因为失去了视力,张宗琪的生活似乎永远只有一件事——严防死守,过度的防范剥夺了他的爱;因为失去了视力,金嫣终日幻想着用一场漂亮、体面的婚礼,来弥补自己人生的缺憾,而泰来却无法满足她的这一愿望……他们的疼痛之处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源自他们自身无法疗救的残疾。因此,他们在作家的笔下,总是充满了某种绝望般的撕裂,甚至衍化成人物难以遏止的自虐行为,饱含着悲剧性的内在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与这种自身残疾所导致的疼痛相比,《推拿》中的盲人们所遭受的更为尖锐的疼痛,还是来自于光明世界里的人们,而且是与他们有着这样或那样亲缘关系的人群。譬如,王大夫的弟弟,既嫌哥哥出现在婚礼上给自己丢脸,又把自己闯祸后的难题硬生生地塞给哥哥;泰来的父母觉得两个瞎子结婚不体面,因而不愿给儿子操办婚礼,怕被人笑话;小孔在深圳做推拿时被“前台”反复欺凌;高唯和金大姐挑起的“羊肉之争”,让两个曾好得掏心窝子的盲人老板之间的关系迅速出现裂缝;向天纵为了和情敌竞赛而让十六岁的沙复明遭遇了两个多小时的“小爱情”,残酷至极……对于这些健全人来说,“他们永远会对残疾人说,你们要‘自食其力’,自我感觉好极了,就好像只有残疾人才需要‘自食其力’”。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所谓的“慈善演出”、“爱心行动”,“就是把残疾人拉出来让身体健康的人感动”。尽管毕飞宇并没有全力演绎这种健全人和盲人之间的尖锐对立,但是,他们之间所存在的这种“推拿”关系,已隐喻了一种异常吊诡的现实逻辑,用小说里的话说,就是“盲人的人生有点类似于因特网络里头的人生,在健全人需要的时候,一个点击,盲人具体起来了;健全人一关机,盲人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虚拟空间”。正是这种“边缘化”的生存地位,以及盲人所处的被“推拿”的地位,使得盲人们不仅要忍受自身残疾所引起的各种内心之痛,还要不断地承受健全世界带给他们的各种无法预测的内心疼痛。
这种来自于健全世界的疼痛,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欺凌和伤害,还包含了人们在身体与心理上的错位或对抗,也凸现了毕飞宇一向推崇的“伤害”母题书写。毕飞宇曾说:“在我的心中,第一重要的是‘人’,‘人’的舒展,‘人’的自由,‘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人’的欲望。”①为了突出这种具有丰富的精神向度的“人”,展示人在存在本质上的各种可能性,毕飞宇在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时,尤其注重具有那种锐利感的“伤害”。他曾毫不含糊地说:“我的所有的创作几乎都围绕在‘伤害’的周围。我为什么对伤害感兴趣?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你拿一张白纸放在马路上,那张纸一尘不染,光洁照人。你看吧,用不了一会儿一定会有人从那张白纸上踩过去,绕着道上去踩,直到那一张白纸被弄脏、弄皱,不堪入目。要不你换一只气球,随随便便放在那儿,它也许会被人偷走,要是偷不走呢?有人想方设法也要把它弄炸掉。炸掉了,他就安稳了。我不知道这样的基础心态有没有‘中国特色’。总而言之,我对我们的基础心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恨大于爱,冷漠大于关注,诅咒大于赞赏,我在一篇小说里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在恨面前,我们都是天才,而到了爱的跟前,我们是如此地平庸。”②毕飞宇的这种人性判断,有些类似于鲁迅所说的那句“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很有些决绝的意味,但是,它的确又击中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惯见的人性的顽劣和阴暗。事实上,《推拿》之所以具有一种尖锐的疼痛感,一种强劲的悲剧力量,关键就在于,在健全人的世界里,盲人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一种被“推拿”的对象。这里面所隐含的伤害关系,其实也反衬了健全人在心理上的“残疾”——如果我们审视一下王大夫的无赖弟弟、介绍都红表演的主持人、金大姐等人的言行,都可以明确地体会到此点。
但是,在叙述幽暗的人性所形成的各种“伤害”之外,《推拿》还更加突出了精神抚慰的力量。这也是这部小说最为丰实的内涵之所在。表面上看,毕飞宇是在通过“推拿”将盲人置于现实生活之中,而实质上,他是以盲人之间在心灵上的彼此“推拿”和抚慰,来传达那些卑微的人群试图用自身的心灵之光驱走黑暗的强烈意愿。由是,我们看到,在“沙宗棋盲人推拿中心”里,有着极为纯洁的爱情:王大夫通过与小孔的恋情体会到,恋爱无非就是一点——心疼对方,“有依有靠的感觉真好啊。多么地安全,多么地放心,多么地踏实。相依为命了”。金嫣辗转千里,以疯狂的方式爱着徐泰来,“因为恋爱,她一直是谦卑的,她谦卑的心等来的却是一颗更加卑微的心。谦卑、卑微,多么地不堪。可是,在爱情里头,谦卑与卑微是怎样地动人,它令人沉醉,温暖人心”。沙复明则“渴望把都红身上的疼一把拽出来,全部放在自己的嘴里,然后,咬碎了,咽下去”。小马暗恋上了嫂子小孔,这让张一光感到“小马通身洋溢的都是瓦斯的气息,没有一点气味。没有气味的气息才是最阴险的,稍不留神,瓦斯‘轰’的就是一下,一倒一大片的”。于是,他带着小马不断地去洗头房寻找安慰。小孔在感受到小马的这份心思之后,也在心里对他说:“嫂子欠着你一个拥抱。离别是多种多样的,怀抱里的离别到底不一样。这一头能实实在在,未来的那一头也一定能实实在在。”除了爱情,我们同样还看到许多温馨的友情,像小孔和金嫣谈起未来的婚姻,虽然各有各的烦恼,但她们在一人一句“我懂”后拥抱在一起,把各自的左手搭在对方的后背上,不停地摩挲。王大夫在沙复明痛苦的时候,总是不时地点拨他,希望他走出情感的泥淖。都红受伤后,向来把钱看得很重的盲人们纷纷慷慨解囊,纵使用错了方式,盲人们温暖的心灵依然让我们感慨。张宗琪在关键时刻更是不计前嫌,果断地在沙复明的手术单上签字——“张宗琪直接把签字笔送进嘴,咬碎了,取出笔芯,用他的牙齿拔出笔头,对着笔芯吹了一口气,笔芯里的墨油就淌出来了。张宗琪用右手的食指沾了一些墨油,伸出大拇指,捻了捻。匀和了,就把他的大拇指送到护士的面前。”……正是在这些情感深处的彼此“推拿”,使人们看到,在这个独特的人群里,有着远比健全社会里更为执著的爱、关怀、宽慰和理解,也有着比健全社会更丰富、更温暖的人性之光。因此,《推拿》虽然延续了毕飞宇一以贯之的“伤害”母题,但它同时又大大地强化了人性内在的体恤之情,从而使整个小说在审美格调上摆脱了对“灰色道德”的过度崇拜。
二
盲人的世界之所以特殊,不仅是因为他们无法以正常的方式实现人际间的自由交流和冲突,还在于无法以正常的言行直接彰显自身的生存感受。这无疑给作者在叙事推动上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事实上,在阅读《推拿》时,我们也一直在疑虑毕飞宇如何来确立故事的主线并推动整个叙事的发展,尤其是对人物内在个性的塑造上,如何丰富他们的精神镜像。但是,最终我们发现这种疑虑是多余的。毕飞宇不仅巧妙地通过人物的并列方式,以复调的结构将每个人物的人生历程和个性情感叙述得异常鲜活,还借助人物之间的内心碰撞,以及大量精确的心理活动,使他们在仄逼的空间里获得了多方位的拓展。这种复调结构与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非常接近。只不过,帕慕克靠的是一种真相探究式的悬念为线索,而毕飞宇则更多地利用了他对世态人情的熟稔。毕飞宇自己就认为:“对小说而言,世态人情是极为重要的,即使它不是最重要的,它起码也是最基础的,是一个基本的东西,这是小说的底子,小说的呼吸……我觉得世态人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拐杖。这根拐杖未必是铝合金的,未必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它就是一根树枝。有时候,就是这根不起眼的树枝,决定了我们的行走。”③这种对世态人情的透彻理解,使得毕飞宇非常轻松地摆脱了某些大众化的经验或抽象的思维,从而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借助对人物内在人性的扎实推衍,展示了盲人们既充满世俗意味又不同于世态常理的内心情状。
在《推拿》中,毕飞宇首先将世态人情的根基确立在一种“安全需要”之上。用马斯洛的心理学来说,这是人类生存的最低要求;而对于失去了现实竞争能力的盲人来说,这却是他们最为本质的生存需要。毕飞宇穿透了一些世俗生存的表象,让笔下的盲人们牢牢地附着在生存的安全感上,并由此演绎出许多丰富的人性面貌。像小孔就极度“抠门”,“钱一旦沾上她的手,她一定要掖在胳肢窝里,你用机关枪也别想嘟噜下来”。王大夫为了弟弟的债务,即使准备好了钱,但最终还是意外地给出了自己身上的血,因为“你们把钱叫作钱,我们把钱叫作命”,“没钱了,我们就没命了。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我们瞎子会死在哪里”。张宗琪虽是老板,但他照样上钟,因为“他只看重具体的利益。他永远也不会因为一个‘老板’的虚名而荒废了自己的两只手”。此外,像都红对沙复明情感的婉拒,金嫣对婚礼的不可遏止的狂想……所有这些,在本质上都折射了这些盲人对自我生存安全的强烈需要。即使是他们之间的彼此抚慰和以沫相濡,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是为了自我生存的“安全需要”,因为“盲人和健全人打交道始终是胆怯的,道理很简单,他们在明处,健全人却藏在暗处。这就是为什么盲人一般不和健全人打交道的根本缘由。在盲人的心目中,健全人是另外的一种动物,是更高一级的动物,是有眼睛的动物,是无所不知的动物,具有神灵的意味。他们对待健全人的态度完全等同于健全人对待鬼神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尽管毕飞宇并没有将这种“安全需要”放到叙事的表层,但是它已渗透在很多人物的潜意识之中,并且始终规约着他们的个性和言行,甚至成为毕飞宇推动叙事的一个核心筹码。这也反映了毕飞宇对世态人情的精确理解和把握。
《推拿》主要塑造了十位盲人形象,虽然他们绝大多数都被生存的“安全需求”所折磨,但是每个盲人又有自身一套独特的处世方式和个性气质。譬如,王大夫带着小孔回到南京之后,面对家庭的潜在冲突,急切地要去找工作。于是他决定给老同学沙复明打电话,他与沙复明的通话既含蓄又明了,既求人相助又不失尊严,而沙复明的回复也同样滴水不漏。沙复明虽然是推拿中心的老板,但他与张宗琪的内向完全不同,且热衷于日常管理,“沙复明是打工出身,知道打工生活里头的ABC,回过头来再做管理,他的手段肯定就不一样。他知道员工们的软肋在哪里。所谓管理,嗨,说白了就是抓软肋”。因为金大姐的“羊肉事件”,沙复明和张宗琪之间有了一些隔阂,但他们对待冲突始终以“权衡利弊”作为第一法则,退退进进,颇显“推拿”之道。张一光有些自私,而在关键的时候却不乏豪爽。纯情的小马,在绝望之中不得不把对嫂子小孔的情爱转移到妓女小蛮的身上,将他那赤子般无邪的“目光”也转移到了小蛮身上。还有纯净的都红,她的美貌让她收获了一份可能给她带来利益的爱情,但她坚定地拒绝了。当然,最令人动容的,可能还是在爱情面前特别渴望付出的金嫣,在亲情面前特别宽容的王大夫,在友情面前特别能包容的季婷婷。
金嫣是个特别愿意“爱”的女子。和“被爱”比较起来,她似乎更在意“爱”,也只在乎“爱”。为了“爱”,她执著,千里迢迢,从大连到上海,再到南京,只为寻找其貌不扬且与她并不般配的泰来;为了爱,她勇敢,在众目睽睽之下高调追求泰来,等泰来一起吃饭,从自己碗里给泰来夹菜;为了爱,她体谅、宽宥、无私。她是那么地希望泰来能亲口说出“我爱你”,但了解到泰来内心深处的自卑后,她便不再逼他,最终还是她自己说出了“我爱你”这句话。她对“爱”的理解是:“自己可以一丝不挂,却愿意把所有的羽毛毫无保留地强加到对方的身上。”她是个既大大咧咧又温婉细腻的女子,也是个饱含血性和母性的女子。她无数次地设想着自己和泰来的婚礼,因为“她就相信婚礼。有婚礼就足够了。有婚礼你就不再是一个人,你起码可以和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这是可信的。婚礼其实是一个魔术,使世界变成了家庭。很完整了”。这种对完整人生和家庭的渴望,使她的生命显得熠熠生辉。
王大夫对“家”则充满了复杂的意绪,既亲密,又疏远。他和自己的父母并不亲,父母把爱更多地倾注到了弟弟身上,但他却在“对得起”父母的世俗伦理中长大。为了父母,他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体面人”。他也嫉妒弟弟,这种一闪而过的邪念却让他对弟弟有种不能自拔的疼爱。弟弟结婚,他曾赌气汇款两万元,要和弟弟一刀两断,可他回家后,一秒钟之内就原谅了弟弟。弟弟欠了两万五的赌债,他也曾痛恨弟弟,想撒手不管,但他后来还是决定从股市上割肉(连结婚他都没有舍得这样做),并独自面对债主的威逼。王大夫是个特别宽容的男人,他把对亲人的恨替换成了爱。他的善良、责任感,使他始终包裹在一种世俗的伦理温情之中。
除了引言和尾声,《推拿》的其他各章都以人物的名字作为各自的标题,只有季婷婷没有被单独列出来,而是附着在都红的故事里,但同样没有减少这个人物的艺术魅力,恰恰相反,她的光芒正在于她甘于让都红遮住自己。季婷婷曾是都红的安慰:她热心地替刚到南京的都红张罗工作;她搂住找工作不顺利的都红,心疼她;她担心受挫的都红一大早不辞而别,整晚都不太敢睡。在最初的日子里,都红每天都和她厮守在一起。一两个月后,都红和高唯走到一起去了。季婷婷不满过,失落过,但她很快调整了自己,理解了都红。都红受伤,她非常自责,想死的心都有,于是留下来不声不响地照顾都红;而都红不想耽误她回家成亲,两个亲密的女人干坐了两三天,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血淋淋地给对方看。季婷婷的包容成就了“干坐”这样感人的场面,她是个真正懂得友情的人。
无论是出于爱情、亲情还是友情,《推拿》确实写活了一群生活在现实边缘的盲人。他们不仅为自己寻求安全,又处处替他人送上慰藉。他们用心灵照亮的,不仅是属于他们的黑暗世界,还有属于健全人的灰暗世界,因为在健全人的世界里,又有多少人愿意付出金嫣式的爱、王大夫式的责任、季婷婷式的宽慰?
三
借助于复调式结构,《推拿》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人物与人物、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自由转换,而且让整个作品在叙事节奏上也保持了“一推一拿”的从容状态,显示了毕飞宇对叙事张力的良好控制。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觉得《推拿》有着极为强劲的叙述力度,同样也在于毕飞宇在处理叙事时的准确和迅捷。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的细节之中,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动用“狠、准、冷”的手段,将人物的心理、行为、场景进行充分的展开、放大和延伸,使整个叙事既显得异常丰盈,又极具冲击力。譬如,小孔与王大夫独处时,因为害羞而显得慌乱。但是,“她的慌乱不是乱动,而是不动。一动不动。身体僵住了。上身绷得直直的。另一只手却捏成了拳头,大拇指被窝在拳心,握得死紧死紧的。盲人就是这点不好,因为自己看不见,无论有什么秘密,总是疑心别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点掩饰的余地都没有了”。又如,九岁的小马意识到自己的双眼无法复明时,开始了果断的自戕,“小马拿起瓷片就往脖子上捅,还割。没有人能够想到一个九岁的孩子会有如此骇人的举动。‘阿姨’吓傻了,想喊,她的嘴巴张得太大了,反而失去了声音。小马的血像弹片,飞出来了。他成功地引爆了,心情无比地轻快。血真烫啊,飞飞扬扬”。再如,一个剧组的导演对都红的美貌进行了一番高度的赞誉,这让沙复明的心顿时浮动起来,但是“美”究竟是什么?天生就是盲人的他却一无所知,于是他进入了近乎疯狂的想象……读这些细节,真正地让人体会到“小说小说,就是在小处多说说”的巨大魅力。它既附着在常识和经验之上,又不时地滑出常识和经验,在意外之中给人以迅猛的一击。
记得纳博科夫在谈及小说创作时,曾说过这样一段非常有意味的话:如果一个人冲进大火之中救出了邻居的小孩,我们应该向他脱帽致敬,而如果这个人还冒险花了五秒钟寻找并连同小孩一起救出了他心爱的玩具,那我们就要紧握他的手了。因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不仅应该密切关注救小孩的过程,还更应该关注“花五秒钟顺便救出小孩玩具”这一细节。正是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细节,却恰恰表明了一个优秀作家对生活本质的超验性关怀,“这种为琐物而疑虑的才能——置即将来临的危险于不顾,这些灵魂的低喁,这些生命书册的脚注,是意识最高尚的形式,而且正是在这种与常识及其逻辑大相径庭、孩子气十足的思辨状态中,我们才能预想世界的美妙”④。毕飞宇虽然并没有如此推崇这种超验性的细节表达,但他在处理小说中的那些潜在冲突时,的确赋予了这些冲突“与常识及其逻辑大相径庭”的艺术质色,并使叙述大大增强了内在的力度感。譬如,在《推拿》的第十六章里,面对弟弟的赌债,王大夫虽然筹好了钱,但是,当他回到家里,尤其是发现弟弟也在家等他来还债时,“王大夫的血当即就热了,有了沸腾的和不可遏制的迹象”。于是,他提起菜刀,在自己的胸脯上划了两刀,并在“规矩”的健全人面前振振有词。这里,毕飞宇一口气用了四十一个“王大夫说”,每一个“王大夫说”都是斩钉截铁,强悍霸道,不留余地,充满了血性的气息。它使一向通情达理的王大夫积淀已久的愤怒和绝望终于在瞬间爆发出来,也使王大夫的男儿血性展露无遗。这种细节的扩张和延展,显示出作家对盲人生活精细入微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也折射了作家对一些小说敏感部位的准确把握和再现。
当然,如果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这也体现了毕飞宇对叙事语言的高度自觉。毕飞宇非常善于使用一种干净利落的短句,冷静之中,还含有几分理性的警句意味。尤其是在叙述人物的内心冲突时,他总是能够让叙述完全沉入到人物的心境之中,以一种短促而又有爆发力的语言,迅速、准确地传达人物的即时状态,特别是那些肉眼看不到的心理活动状态。他自己也说:“这个世上从来没有单纯的语言、抽象的语言,它是你的洞穿能力。你只要逮住你想说的东西,逮住了,说出来,写下来,就成了语言,你的语言就会像海里的水一样,无风也有三尺浪。”⑤这里,毕飞宇试图将语言转向更为广阔的空间,视语言为洞察力的产物,但是就个性气质而言,毕飞宇仍然清晰地体现出他的表达方式:短促、坚硬、内敛,且具有警句般的审美特质。在此,我们不妨摘取两节:
就说沉默。在公众面前,盲人大多都沉默。可沉默有多种多样。在先天的盲人这一头,他们的沉默与生俱来,如此这般罢了。后天的盲人不一样了,他们经历过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链接处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也就是炼狱。并不是每一个后天的盲人都可以从炼狱当中穿越过去的。在炼狱的入口处,后天的盲人必须经历一次内心的大混乱、大崩溃。它是狂躁的、暴戾的、摧枯拉朽的和翻江倒海的,直至一片废墟。
——第三章
沙复明的食指神经质了。他的嘴巴始终是张着的,下巴都挂了下去。高唯注意到了,沙复明的食指在反反复复地摩挲,一直在摩挲最后的一行。他终于吸了一口气,叹出去了。最后,沙复明把都红的纸条丢在了沙发上,一个人站了起来。他走到了柜子的面前,摸到了锁。还有钥匙。他十分轻易地就把柜门打开了,空着手摸进去的。又空着手出来了。脸上是相信的表情。是最终被证实的表情。是伤心欲绝的表情。沙复明无声无息地走向了对面的推拿房。
——第十九章
这两段都是叙述人物内心的绝望感。前一节是叙述后天致盲的人所经历的内心绝望,包含了更多的理性思辨意味;后一节是写沙复明用食指“读”了都红留给他的盲文信之后的绝望,作者只是通过健全人高唯的眼光将这一切呈现出来,包括沙复明的每一个细微动作,并没有深入内心,但是却有一种“无风也有三尺浪”的审美效果。然而,无论是哪一种叙述方式,毕飞宇都不自觉地使用了一种短促有力的句式。应该说,这种句式的运用,既与毕飞宇一贯追求的准确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他一向推崇的强悍的叙事风格密不可分。读毕飞宇的小说,我们几乎无法绕开他那极富力度感的语言,它看似克制、内敛,却又欲隐弥彰,十分地耐人寻味。《推拿》的重要特点亦在于此。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浩波巨澜,然而在每一个盲人的内心深处,似乎都翻涌着各种炽烈的岩浆——为生存,为尊严,为爱。
毕飞宇曾说:“我喜欢的悲剧是发生在内心,不声不响,外人看不见的……当一个人遇到不幸时,承受痛苦都是安静的、沉静的、自我消化的。我希望我的小说在这一点上切合我们的生活、心理的写实,写肉眼看不到的悲剧。”⑥如果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种“内心悲剧观”无疑会凸显一种精神深处的震撼力,但是,倘若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要真正地呈现人物内心深处的悲剧潜流,显然需要超常的叙事能力。我们看到,太多的作家都喜欢经营一些人物的外在冲突和人生悲剧,但是,在真正的内心面前,却无力展示这种悲剧的力量。而毕飞宇却能以其特有的叙事耐力和洞察力,不动声色地呈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内心悲剧,包括这部《推拿》。当然,与作者以往的小说相比,《推拿》又明显地突出了那种发自人性深处的坚韧、友善和梦想。或许,这已显示了毕飞宇对美好人性的倾心关注?
注释:
①毕飞宇、汪政:《语言的宿命》,《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②毕飞宇、汪政:《语言的宿命》,《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③毕飞宇:《文学的拐杖》,《雨花》2007年第11期。
④〔美〕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第330页,申慧辉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⑤毕飞宇、姜广平:《“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毕飞宇访谈录》,《花城》2001年第4期。
⑥毕飞宇、周文慧:《内心的表情——毕飞宇访谈录》,《长江文艺》200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