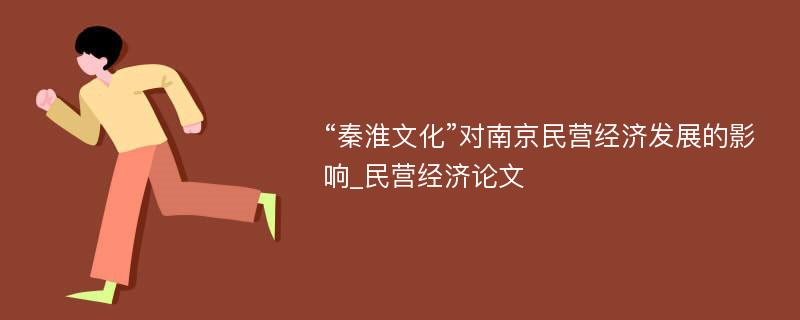
“秦淮文化”对南京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淮论文,南京论文,民营经济发展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06)04—0076—04
南京具有发展民营经济的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其一,南京滨江据淮(秦淮河),拥有水上运输的天然有利的地位。由南京溯江西上,可至安庆、九江、武汉、重庆各港;顺江而下,则可至镇江、南通、上海等地。南京下关东距长江口347 公里,江阔水深,经长江出海,通过海上运输向北可达大连、青岛、天津、秦皇岛,向南可达宁波、厦门、广州,通过海上运输线还可与世界各地相通。在历史上,秦淮河是一条重要的水上交通运输线,经胭脂河可与太湖流域相通,经石臼湖可至宣城、当涂、芜湖,对于沟通南京与皖、浙、赣等省的联系,集散物资,便利商旅起着很大的作用。其二,南京地处我国东部铁路大动脉津沪铁路与“黄金水道”长江的交汇点,控扼陆水交通,这种地处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使南京成为南北粮食和重要物资运输的必经之地,对南京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其三,南京山环水绕,气候温和,腹地广阔,历史上就是区域性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在东至海边,西抵巢湖盆地,南达太湖流域,北到淮河流域的纵横千里的广大城乡,每年有大量的货物通过发达的陆水交通运到南京。
然而,南京民营经济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根据历史资料,南京第一家近代民办企业是1894年兴建的胜利机器厂。1921年,南京最早的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大同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在下关三汊河创立。该公司是当时南京民营企业中资本最为雄厚的一家,也仅有资本100万元,职工185人,年产月兔牌面粉150万袋。而在无锡,从1895—1913年共建各类民营工厂12家,资金1422000元。[1](p65) 发展至1929年时,无锡民营经济已经涵盖棉纺、面粉、缫丝、机器翻纱等12个行业,拥有208家工厂,年产值近亿元。无锡“经十余年之惨淡经营,一跃而为苏省工商业中心”。[2] 在僻处江海一隅的南通,1895年筹建、1899年投产的大生纱厂,是南通第一个民营工业企业。至1913年,已发展到有工厂14家,总投资达到5483200元。[1] (p1069) 1923年,南通民营企业共有40余家,资金1200万元。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无锡、南通已经分别成为江苏大江南北两个近代民营工业最集中的城市,而南京难以望其项背。
南京拥有发展民营经济的区位优势,民营经济的发展理应既快又好,然而事实则不然。何以有如此反差?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且饶有兴味的问题。本文从区域文化角度对此略作探析。
一、“金陵帝王州”的政治文化难以提供有利于民营经济持续发展的投资环境
“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南京因其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赢得了“帝王州”的称誉。211年,孙权将政治中心迁至秣陵,次年改秣陵为建业,这是南京建都之始。此后,先后在南京建都者有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等政权。另外,在南京建都的还有南明等四五个政权。
不过,在南京建都的多为短命王朝,短暂的辉煌之后,往往伴随着血腥的屠戮和经济的巨大破坏,治乱循环,不绝如缕。早在六朝时期,建康已经相当繁华,“梁都之时,户二十八万,西至石头城(今清凉山),东至倪塘(今江宁方山北),南至石子岗(今雨花台),北过蒋山(即紫金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3] 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其繁荣可与长安、洛阳相比。然而动乱相寻,先有东晋时的桓玄篡位,乱京都,人相食;继有梁武帝时的侯景之乱,建康城化为焦土,幸存者仅两三千人,包括梁武帝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被活活饿死;再有隋灭南朝陈后对建康城邑、宫室的“平荡耕垦”。在这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后,曾经盛极一时的建康城“潮打空城寂寞回”,“万户千门成野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4]
五代十国时期,建都金陵的南唐是当时最为富庶的地区,“野无闲田,桑无空地”,[5]“制度壮丽,甚为繁荣”。[6] 然至赵宋大军平定南唐,类似陈亡以后的情形再度出现,南京经济又急剧衰落。
在近代,南京又先后两次遭受了惨重破坏。一次是1864年天京失陷,湘军破城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悉入于湘,南京惨遭洗劫。另一次是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南京有33万人死难。百年之内,南京遭两次“屠城”浩劫,元气丧失殆尽。
“金陵帝王州”的政治文化,客观上使南京经济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大起大落。对此,茅家琦先生有一段精彩之论:“南京有良好的政治地理形势:‘钟阜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统治集团钟情南京,在南京建都,自然会促进南京的经济繁荣。但是,另一方面,当新王朝兴起,打败在南京建都的旧王朝,并在其它城市建立新都的时候,新的统治集团必然会压低南京的政治地位,摧毁南京的经济力量,以清除旧王朝的影响和残余势力,消灭旧王朝卷土重来的隐患。”[7](P2) 历史上南京经济反复遭受人为的大破坏,正是这个政治因素在起作用。政治上的风云变幻,经济上的大起大落,使南京缺乏一个有利的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环境,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望而却步,因此投机一把就走的短期行为浓厚。反之,则往往血本无归。笔者调查得知,抗战前夕,苏北某富商曾在南京花牌楼投资创办了一家金店,不久南京沦陷,店主在万死中虽侥幸捡了一条性命,但巨额投资悉数东流,损失惨重。如此动荡不安的投资环境,焉能吸引投资?民间资本又岂敢长期投资?
二、超强的行政文化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健康成长
“行政权力支配社会”,[8](p693) 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极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在天子脚下、皇城根旁的南京,其所受到的行政控制更超乎一般。在强烈的行政控制下,历史上南京经济的繁荣主要是官营经济的繁荣,而民营经济往往遭受官府的强烈干预,其发展则步履维艰,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六朝时期,建康城设立了许多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如官营丝织业、官冶作坊、纸官署等。当时重要的手工业多为官府经营,为官府服务。官营手工业工匠被编为“百工户”,终身服役,身分世代相传。六朝时期,建康官商发达,不少世族、官吏竞相经商,他们利用免税特权,大量使用奴婢从事投机商业——邸店业、车船业及商品贩运。南朝梁临川王萧宏在建康有邸阁数十处,囤积了各种日用品。刘宋时,见于典籍的世族、官僚即有王玄谟、褚叔度、邓琬、孔道存、孔徽、吴喜等数十人。此外,政府还实行专卖政策,垄断经营盐、酒等高利润商品,又通过和籴对米谷等重要商品的价格进行调控,在稳定物价的同时,也获取高额利润。甚至皇室也设立宫市谋利。与官营工商业的主导地位相比,民营工商业显得无关紧要。
超强的行政干预对民间工商业的抑制,在明洪武年间的南京显得尤其突出。官府对民营经济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实行铺户当行制。南京时为京师重地,院、寺、司、府、县公堂林立,达官健吏日夜驰骛其间,所用物件不计其数,官府遂“建立街巷,百工货物买卖各有区肆”,[9] 将各铺行注籍于官府,以随时令他们应役买办。官府名义上是以官价向铺行收买,实际上是对民间工商业者的公开掠夺。正如有学者所说:“封建官府明文规定铺户为官府无偿服役,当行买办,将铺户纳入自己的消费轨道,这是封建社会任土作贡原则的补充,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徭役制,只是应役的主要是城市坐商和自产自销的小手工业者。”[10](p28) 二是在南京始行坊厢制。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将苏、浙移民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置于都城之内曰坊,近城曰厢,“有人丁而无田赋,止供勾摄而无征派”。[11] 附郭两县共编坊厢一百多,有富户三十万人,以“勾摄公事”,保证官府运转和官营手工业生产顺利进行。三是建立塌房,以政权干预私人商品贸易。为与牙侩争利,控制获利颇丰的转运贸易,朱元璋令工部建立塌房,让“商人至者俾悉贮货其中,既纳税从其自相贸易”,房“由各坊厢长看守”。[12] 发展至后来,“所司于贫民贾贩者,亦驱使投税”。[13] 四是建官营酒楼。朱元璋令官府在江东门、三山门、聚宝门及三山街等通商大道上建立了16座酒楼,“以接四方宾旅”,或“以为客旅游乐憩息之所”,或“所以处宫妓也”。[14] 官府对民间工商业的控制与干预由此可见一斑!经济掠夺之外,明朝政府还对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压迫,如不允许商贾之家穿绸纱,只许着绢布,压制以富商、士绅为首的市民势力,等等。
永乐十八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消失,行政控制有所减弱,特别是对强烈干预工商活动,限制市民流动的坊厢制和铺户制的改革和革除,大大减轻了南京坊厢和铺户人等的负担,免除了随时应值买办和备受抑勒之苦。由应役改为纳银雇募,由铺户当行制改为铺户买办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向,扩大了民间工商业者的自由活动空间,民间工商业者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了。在官营经济相对缩小的同时,南京的民营手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而尤以织造业、制扇业、酿酒业、印刷业、钢铁器皿业、木作业、染洗颜料业、金箔业发展更快。如在迁都以后,南京民营织造业异军突起,所产丝、纱、罗、绢,皆极精巧,品种繁多,花样翻新,色彩调配和谐,体现了很高的水平。民间刻印业也很快取代了官营印刷业。民营商业在官府控制有所松弛后也迅速发展。徽杭巨贾,扬州盐商,晋鲁丝客,龙游行侩纷纷以南京为据点,视之为利之渊薮。他们或东发两淮之盐,溯江而上,行销江西、湖广,又购载湖广之米、芜湖染布,顺流而下,贩运苏杭;或南载太湖地区丝织品,远走秦晋,又北运鲁、湘之棉,扬帆苏、松。明朝中后期,南京城西临江的上新河码头,木材、大米贸易盛极一时。为了更有利于贩运业的展开,众多的商人在南京广建质店、当铺,既为自身和其他商人提供大笔资金,又为一般小本工商业者提供生产、生活贷款,以获取双倍利润。
明朝官府对民营经济控制的由强变弱以及民营经济的由抑到扬生动地说明:行政控制越强,民营经济越弱;行政控制放松,民营经济则活。行政控制与民营经济大体呈反向运动。因此,历史时期南京作为政治中心所受到的超强的行政控制,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江南佳丽地”的享乐文化所导致的资本倒流限制了民营企业的扩大再生产
民间商业资本是最古老的自由资本存在的方式,是工业资本形成的重要前提。只有当大量的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时,民营经济才能迅速发展。然而,历史上南京大量的民间商业资本或用于购置土地,或用于放高利贷,或用于捐买官职,或用于营建豪华的住宅庭院,或用于挥霍性消费。总之,民间大量的商业资本处于封建化的状态。
明代,地租率超过五成,剥削极为沉重。高额地租吸引民间商业资本不是将货币转化为工业资本,而是不断将货币投向土地,疯狂购买和兼并“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财产,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地租。据万历《上元县志》卷12记载,明代,麕集在南京的豪商巨贾都在南京附近地区置买田产,成为所谓有田无役的寄庄户。嘉靖以后,贫民难以存活,纷纷变卖土地,寄庄户则更多。
高利贷资本的存在也强烈地吸引着民间商业资本。南朝梁武帝六弟萧宏在都城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券,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15] 明清时期,国家对高利贷率不加限制,许多高利贷者常常八折出借,滚算月利,商业资本加速转化为高利贷资本。
在封建国家的引导下,许多工商业者还将巨额财富用于追求政治地位上。在封建社会,社会地位不仅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且取决于功名禄位的高低。为改换门庭,提高身价,不少工商业者,特别是庶民出身的工商业者,不惜重金买官,这种情形早在南朝即已经司空见惯。他们还出资延聘名儒学者,教育子弟准备科举考试以获取功名。
为追求社会地位,许多富商大贾还将巨额财富用于炫耀性消费上。史称明代的南京:“风俗奢靡,园林亭榭之盛,勋戚世族肆其骄淫,以相夸耀。”[16] 在南京的徽商则把商业利润的很大一部分带至老家营建豪华的住宅庭园。如歙县商人许竹逸挟资经商吴越金陵十余年,积累起巨资,遂广建住宅,以贻后裔。时至今日,人们在皖南仍随处可见徽商营建的豪华民居。
将商业资本用于挥霍性消费者更是比比皆是。南朝刘宋时,建康的富商往往穿名贵的裘貂缇绣。明代的商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在南京经商的不少是徽商,据《虞初新志》记载:“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梨园以技鸣者,无论数十辈,而其最著者有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士与夫妖姬靓女,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文中新安贾即徽商之一支。又歙县《丰南志》记载:吴姓“北鹾于广陵,典于金陵,米布于运漕,致富百万。”其子吴天行,“姬百人,半为家乐,远致奇石无数。取‘春色先归十二楼’意,名其园曰十二楼。”至于其人之“后房丽姝”则“甚众”。南京商人的享乐之处主要集中在秦淮河两岸。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述明清时期秦淮河两岸盛况说:“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于工作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为满足豪商巨贾的挥霍性消费,朱元璋曾立富乐院于乾道桥和聚宝门外东街,让腰缠万贯者纵情声色。明代在武定桥和会同桥南等地,设有勾栏,以供商人消遣娱乐。
商人不将商业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挥霍,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顾虑赚钱太多而遭统治者所忌讳,甚至获罪丧生,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沈万山的例子即是有力的说明。沈万山是一位巨商,曾资助朱元璋兴筑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朱元璋犒军,沈万山欲代出犒银。朱元璋问道:“朕有百万军,汝能遍济之乎?”沈万山说可以给每位军士犒一两银子。沈万山筑城在前,犒军在后,对明朝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孰料朱元璋却因此而愤怒。《明史·高皇后传》记载:沈万山“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诛不祥。民富敌国,民有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结果将沈万山充军到了云南。若非皇后说情,沈万山性命难保。既然民富敌国为国之不祥而获罪,那么经商致富,也只能适可而止了。富了,享乐享乐,或购置土地,或兴建豪宅以遗子孙,反而是最为保险的选择。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经商发财并不必然意味着扩大再生产。显然,商业资本的封建化或倒流,是限制南京民营经济规模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四、重文轻工商的心态文化难以形成领袖群伦的企业家群体
作为十朝故都的南京,重文轻工商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南京古代人文荟萃,学术繁荣。各类古代的学校,上至太学、府学,下到县学、义学,在南京也很发达。……晚清之后,废科举,兴学堂,南京涌现出金陵大学、两江法政学堂、陆军讲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但是,南京缺少像徽商产生的那种土壤。皖南人民应对耕种土地少的不利条件的挑战,在儒家进取精神的引导下,形成了一种不畏困难,依靠血缘族群的作用,团结互助,讲究信誉,把经商、治学、做官联为一体的徽商精神,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兴盛了几百年。这虽非现代创业精神,但这当中的因素经批判继承后,仍可生长出新时代所需要的创业精神。但南京的地域文化中却缺少这些因素。南京缺少本土产生的大实业家,根源就是南京市民精神存在上述偏颇。”[17] 事实确实如此。如明代南京的大当铺,绝大多数为徽商所开,而尤以程北溪、黄季公、黄国宾、鲍秋等有名。当时的南京市场,外地商人云集,有所谓“贾婺、贾台、贾瓯、贾括、贾姑孰、贾淮海”,《续金陵琐事》“狱神显灵”条称这些外地商人“卜地利则与地迁,相时宜则与时逐,善心计操利权如持衡,居数十年累巨万”,在南京商界呼风唤雨。南京绅士顾起元对此愤愤不平,在《客座赘语》卷二《民利》中说:“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清代,在南京的外地商人更多,他们在南京纷纷建立会馆,至清中叶,安徽、山西、陕西、江西、江苏崇明和洞庭、浙江湖州、福建、山东、河南及两湖商人在南京建立的会馆多达30所,有“会馆之设,甲于各省”之称。其中,尤以安徽商人的会馆最多(有12所),势力最大,徽商中又以婺源木商为首。每年四月初旬都天会,徽州木商遍张徽州灯,其“旗帜、繖盖、人物、花卉、鲜花之属,五光十色,备极奇巧。阖城士庶往观,车马填闉”。[18] 发展至近代,南京周围的南通、无锡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的民营企业家,并带动了两地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南通,从1899年大生纱厂开工算起,至20世纪20年代初,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南通的工业化、城市化、近代化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与状元实业家张謇个人的主导作用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张謇,就没有近代化的“新新世界”——南通。在无锡,以荣氏家族成员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有力地推动了无锡经济的近代化,至抗日战争前夕,其生产总值仅次于上海、广州而在全国居第三位。在常州,在中国棉纺织工业十分萧条的背景下,大成纺织染公司却以50万元起家,在短短的7年中创造了辉煌的成就。7年中,股本红利及职工分红共支出100万元,纱锭从1万枚增加至9万枚,布机从260台增加至2000台。大成公司所以能创造出如此经营奇迹,是与总经理刘国钧的企业管理才能分不开的。[8](p4) 而反观南京,却没有或者说很少有如此杰出的企业家。
从来事业由人做。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营企业家的努力,而一个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更需要有知名的、能领袖群伦的企业家起推动作用。在南京,从历史上看,很少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企业家。历史上南京民营经济发展缓慢,与此不无关系。
以上我们考察了影响南京民营经济发展的地域文化因素。应当指出,在南京地域文化因素中,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有不少,如南京人很强的包容性有利于吸引外地企业家在南京创业和发展,当今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雨润集团总裁祝义才均是外地人,他们在南京的发展即得益于“秦淮文化”的滋润;同样是重文轻工商的心态文化,重文本身对于培养人才进而发展民营经济也是有很大助益的。只是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秦淮文化”对南京民营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因而“秦淮文化”对南京民营经济的正面影响未及展开,此一遗憾容今后另文探讨。
[收稿日期]2006—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