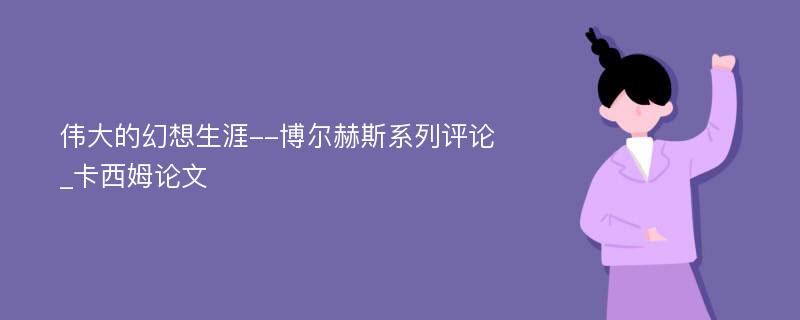
伟大的幻想事业——博尔赫斯系列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赫斯论文,博尔论文,事业论文,幻想论文,系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人们——欲望。
哈金——真理的使者。
《戴假面具的洗染工哈金·德·梅尔夫》讲述的是人如何样拯救自己的灵魂的故事。整个过程笼罩着阴谋的氛围而又令人感叹不已。
故事一开始描述了哈金早年的精神轨迹:他降生在悲哀的、令人厌恶的城市,酷烈的沙漠气候扼杀了幼年的心底的一切希望;他继承了上辈留传给他的洗染手艺,他意识到这种手艺是人在无可奈何的处境之下的权宜之计,是那些缺乏立刻赴死的胆量的“意志薄弱者”和“假冒者”的工作;洗染工用神奇的手艺抹去了善与恶、美与丑的世俗区分,用令人厌恶的颜色覆盖一切生灵,而这种该诅咒的职业却是通往真理的桥梁。他的职业终于让他的肉体从大地上消失了。到他再回来时,他已经成了一名真正的预言家、真理的使者。现在他要在欲望与理性、灵魂与肉体之间发起一场圣战,最后通过牺牲来将自己的灵魂救赎。他已经见过了上帝,窥破了天机,上帝授与了他在人间生存下去的面具,也授与了他拯救的权利——在不可获救中进行救赎努力的权利。哈金回到人间的时刻,正是那些人欲横流的贱民等待斋月(禁欲措施)降临的关头,上帝让他们在这样的关头同真理的使者相遇。贱民们渴望哈金来解救他们的灵魂,哈金则要通过他们来解救自己的灵魂,一切都像是一场阴谋。哈金要求人们进行圣战,通过付出牺牲来得救。战争进行了,哈金不断取得胜利,但胜利的果实不断被消解,结果只是将军的变换和城堡的放弃。邪恶的欲望以呼啸的利箭的形式显示着威力。但哈金领导的战争并不是要消灭欲望,也许却是要让欲望的烈焰烧得更旺。他的军事行动就是骑在棕红色的骆驼背上,用神能听见的男高音在战斗的中心不停地祷告。哈金究竟要干什么呢?他有着什么样的阴谋企图呢?谜底终于显现了。两极之间的战争到了白热化,哈金等待天使的援救,上帝作出了符合他心愿的安排。最后的安排是这样的:哈金被自己人扯下了面纱,人们看到了一张麻风病人的脸。感到受骗的人们于愤怒中用长矛刺穿了他,哈金终于通过自己的牺牲拯救了自己。也可以说他在理性的监视之下用欲望战胜理性的方式解救了自己。
故事从头至尾处在一场大骗局之中,这骗局是哈金代表上帝为人们所设下的。他让人们把麻风病人奉为自己的首领;他伪装有超人的德行,却让一百多名被他刺瞎了眼的女人承担满足他淫欲的义务。哈金并不想否认欺骗的事实,他只是想通过这种高超的欺骗告诉人:人不能看见真情,看见了就要瞎眼,只有自欺是唯一的活路,是人的命运。而他哈金,是唯一的知道自己自欺仍然戴着面具进行圣战的人。哈金的世界推崇至高无上的虚无,将这神秘的能折射出影子的虚无奉为上帝。对于我们居住的土地,他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认为人欲横流的大地是个错误,令人恶心;同时又认为这恶心是大地的基本美德,人可以通过禁欲或放纵来达到这种美德,并在有意识的禁欲和放纵中来救赎自己。哈金的地狱是难以想象的永远的煎熬的场所;哈金的天堂之幸福是告别、自我牺牲和自知睡着的特殊幸福,二者同样令人绝望。因此哈金从天堂下放到人间所担负的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使命,正如他在一开始就告诉人们的:他们等待的只是斋月的奇迹,而他要提供给他们的则是人的奇迹——终身受苦、死而后已的榜样。接着他就发动了阴谋的圣战,他在欲望的惊涛骇浪中驾御着理性的船,坚定不移地驶向彼岸,欲望既是他的动力,又把他推向牺牲的祭坛,而这正是他所追求的。早年的染工生涯让他学会了深入本质的技巧,后来同上帝的遭遇则让他获得了发展自身的秘密武器。哈金的“阴谋”就是创造性地运用这武器调动原始之力,来进行真正的内心的圣战,在放纵与牺牲的两极之间领略上帝的意志,让自己不断感受获救的幸福。
二
对于宗教,对于神,艺术家的态度总是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那蓬勃的生命力使他本能地排除或亵渎神道,在作品中由衷地赞美生命,展示人性中的一切,通过悲剧和喜剧的写作来进入人生的迷宫,在那里面遨游,追逐着生的奇迹。另一方面,经过漫长的生之探索之后,他往往发现他走过的每一段旅途都与宗教的追求暗合,那就像是异道同归似的。或者说,他的境界就在宗教的境界之中,而宗教的境界也渗透在他的境界之内。《阿凡罗斯的探求》中描写的,就是艺术家追求诗的境界的过程,这个过程步步离不开同宗教或神之间的瓜葛和恩恩怨怨,既排斥又统一,充满了迷惘困惑,也不乏刹那间的豁然开朗。
故事一开始,写作者阿凡罗斯正在通过写作抨击神道,弘扬人性。在他的写作境界里,充满勃勃生机的迷宫出现了,迷宫的一头是由潺潺的泉水滋养着的美不胜收的人生风景,另一头无限延伸,与永恒相连。但他的写作很快就遇到了障碍,一生都被幽闭在伊斯兰圈内的他在阐述亚里士多德学说时被两个陌生的词的含义难住了:悲剧和喜剧。他颓然搁笔。这时院子里传来一阵歌声,阿凡罗斯从阳台向下张望,看见几个孩子在表演宗教仪式,他们在表演时用俗话争吵,似乎是对宗教的反讽。但阿凡罗斯从他们的表演里受到了另外的启发:悲剧和喜剧不正是类似于孩子的表演吗?或者说宗教不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在艺术中的吗?这时他又想起了他的旅行家朋友阿布尔卡西姆的事。灵感涌出,他的写作顺利地进行下去。对神学一窍不通的阿布尔卡西姆将诗歌中的意境当做最高的信仰,他本能地忠实于这种信仰,但在神道面前,他是一个怯懦者,他不敢否定至高无上的神,却又由衷地赞美着人生。在这场神学家、旅行家和诗人的关于艺术、神和文字的讨论中,阿凡罗斯的立场其实是动摇的,他怀疑宗教能包罗万象,从心里虔信艺术的力量。他的观点遭到了来自神学家方面的反驳,他犹豫不决。这时诗歌的崇拜者阿布尔卡西姆给大家讲了一个奇异的故事。这个故事因为其中的意境无法言传而不为常人所理解,所以在座的神道维护者都不理解。阿布尔卡西姆的故事发生在生命之河的入海口,几乎是世界尽头的遥远地方。旅行家穿越茫茫的沙漠到达那里,一位穆斯林商人带领他去参观一幢木房,结构怪异的木房平台上,有十几个人在表演,这些人演的是囚犯,他们在音乐声中打斗,倒下死去又复活。阿布尔卡西姆说他们在表演历史,也就是说,在表演人类精神史。阿布尔卡西姆还认为他们是在演故事,而不是讲故事。为了更生动地说明他的观点,他又用另外一个故事来说明前面的故事。他说的是两个睡觉者的表演,睡觉者进了屋子,祈祷,睡觉,睡的时候睁着双眼,然后他们睡着生长,三百零九年之后幡然醒来,将一枚钱币交与商人,和一条狗在一起……神学家问阿布尔卡西姆表演者是否说话,阿布尔卡西姆便将表演者急躁的窘态描述了一下。表演者之所以急躁是由于词不达意,因为历史的本质无法言传。但神学家认为不论什么事都是可以说清楚的。阿凡罗斯之所以在写作中想起了阿布尔卡西姆的故事,是因为他所说的那种表演同院子里孩子们的表演性质上是一样的,阿凡罗斯在写作中才真正理解了那个故事的涵义。是的,悲剧和喜剧就是人性的演出,也就是把宗教变成表演,表演的场所在世界的尽头,同虚无接壤的地方。他们的讨论接下去又涉及到诗歌和语言。阿凡罗斯认为,没有一种语言是万能的,语言的表达总是局限的,词语和类比无论当时多么新鲜,总会过时。只有真正的诗歌可以使语言成为表达永恒的手段,这种表达同通常的类比无关,它凸现的是人生的本质,时间磨不掉它的魅力,只会使它越来越丰富地活在人们心中,每一代人都会在那些永恒的句子里加上新奇的想象。在这一点上,诗是最为接近表演的。阿凡罗斯谈到在蒙昧时代诗人们已经用沙漠的无限语言表述了一切。这令我们想到他所指的蒙昧时代的诗人类似于阿布尔卡西姆的囚犯表演者,也类似于当今每一位艺术追求者。那种沙漠的语言就是囚犯们发自内心的喊叫。从有表演那天起,人就有了自己的宗教。
阿凡罗斯在书写到最后时发现自己进入了虚无的境界——“仿佛被火化作了乌有”。他的探求的结论是:
“亚里士度(亚里士多德)把那些赞美的作品定名为悲剧,那些讥讽的作品定名为喜剧。《古兰经》的篇章和神庙的蒲团,充满了精美的悲剧与喜剧。”(注:《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第284页,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
阿凡罗斯从怀疑宗教出发,本想指出神道的局限,没料到得出的结论同他的初衷相反。他的探求似乎是一个失败的过程,然而这过程是多么的迷人啊。这就是艺术的方式,艺术使描写人性的悲喜剧充满了神性,使语言变成诗,宗教被表演,精神被张扬,人性的探索造就了人本身:
“我感到,我的故事象征着一个人,他就是过去的我。我一边写,一边觉得,为了写这个故事,我必得成为那个人;为了成为那个人,我必得写这个故事,相辅相成,直至永远……”(注:《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第285页。)
讲叙者“我”终于明白,艺术与宗教,均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源头,它们是精神长河中那万变中的不变,它们的存在从蒙昧时代开始,延续到永恒。
三
与《曲径分岔的花园》(一译《交叉小径的花园》)相对,《死于自己迷宫的阿本哈坎—艾尔—波哈里》是心灵故事的另一种讲法。前者突出的是人的勇敢无畏,拼死追求,后者描述的则是一个阴险的、心计异常深的、却又犹豫不决、最后则孤注一掷的人的形象。当然这个人同那名间谍同样忠实于理想,只不过在此处,人更显出其“一不做二不休”的横蛮勇气,而这种勇气又是在极度怯懦的性格外壳中爆发出来的。萨伊德大臣到底是怯懦还是勇敢?他对于像死神一样追逐自己的国王到底是害怕还是渴望?一切都是模棱两可的,又由这模棱两可展示出生命的真相。
仿佛是千年的地狱之火的锤炼,萨伊德集中了人类的全部的恶毒、怯懦和卑劣于一身,就是这样一个魔鬼现在要向死神挑战了。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样的残忍、猥亵、下作,令人作呕,可是他的气魄和非凡的想象力确实令人钦佩!作恶是人活在世上逃脱不了的命运,因为环境所逼,因为欲望高涨,也因为求生的本能。当人作恶时,死神就将自己那长长的阴影投在人前方的道路上,作为对人的不变的制约。萨伊德同国王所玩的,就是这样一场甩掉影子的游戏。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人已经变成了食腐肉的动物,那漆黑的灵魂再也不可能通过宗教来得救。人该怎么办呢?只好自己救自己,因为人不想死,人即使死到临头了也要向死神作最后的报复。萨伊德造迷宫就是出于这种顽固的报复心理。萨伊德出于贪婪杀了人,又出于害怕而潜逃,最后出于明白自己逃不脱自己的影子而异想天开造迷宫。他将他的绝望的处境向牧师描绘(当然隐瞒了重大情节),牧师便理解了他的牛头怪一般的行为,不再用教理来谴责他。因为宗教救不了他。萨伊德为了战胜死神而自己冒充死神,身后跟着“阳光般金光闪亮的猛兽”和“像夜晚一般黝黑的奴隶”,给人威风凛凛、法力无边的印象。他在海湾建造了显目的、大红色的迷宫,坐等真正的死神上门。也许是长久的担惊受怕快要耗尽他的精力,他才想出了这样一个绝招,这样一个胆大包天的、孤注一掷的诡计,以此来将他那噩梦般的生活告一段落。那位能够预测未来的数学家将它称之为“巴别国王”。因为他所造的迷宫类似通天塔。
萨伊德内心深处当然明白影子最终是甩不脱的,但他同样也明白自己在这场游戏中终究是要顽抗到底的。于是他在建造迷宫之时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将迷宫的内部弄得万分复杂,似乎真的要让死神找不到坐在中心的他,他对那人既憎恨又害怕;另一方面,他又把房子造在海岸的高地,外墙涂成大红色,让海上航行的水手们老远就能望见,并且将房子内的条条走廊修得通向瞭望塔,可以想见他天天去那塔上焦急地张望的情景。谜的答案永远只是一个——死,而活着是神奇的。萨伊德要用人工的方法活出一种超自然的状态来,要把最不合情理的怪事变为现实。因为迷醉于自己发明的游戏,他简直是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死神快快上门了。这个阴险怯懦的强者,终于如愿以偿地对死神开了个大玩笑,而自己悄悄溜走了。当然胜利只是象征性的,那影子仍然在身后紧追不舍,但只要想起自己曾经做过,或扮演过国王,那便是对他莫大的安慰了。
在这个故事里,人的形象是如此的阴暗、肮脏、下流、没有希望,与此对称的是,人为实现理想的卓绝的努力又是如此顽强、不屈不挠,并在努力中爆发出辉煌的想象力。死神说:“无论你到什么地方,我要抹掉你,正如你现在抹掉我的脸一样。”(注:《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第305页。 )人说:“我发誓要挫败他的恫吓……”萨伊德身后如阳光般金光闪亮的猛兽和像夜晚一般黝黑的奴隶就是人的形象的一分为二。这两个方面总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至于凶手梦中的蜘蛛网,那既是在暗示人已经恶贯满盈,也是在预示人将继续作恶,为圆梦而将已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数学家邓拉文就这样引导着诗人昂温一步步进入最后的逻辑性的突破和非理性的致命一跃,到达与我们凡人世界平行的另一片新天地。
要破译死亡之谜的人,最为切近的途径就是自己扮演死神。
四
《另一次死亡》描写的是艺术家那阴沉的、激情的内心和艺术被创造出来的过程。
堂佩德罗一生的经历是扑朔迷离的,对于他,人不可能获得完整连贯的印象,只有相互矛盾的片断瞬间,就如上校那反复无常的记忆。实际上,上校的记忆中记下的正是人性的真实模样。
初出茅庐的堂佩德罗很早就在马索列尔战役中同死神遭遇,并因贪生的本能而成了胆小鬼。这个故事开始的情节十分简单,不简单的是后面所发生的戏剧性的转折。堂佩德罗没有将那一次的耻辱逐渐忘怀,而是在离群索居之后便开始了另一项不可思议的努力:改变过去。但过去是不可改变的,人该怎么办?人可以使过去的事在幻想中重演(把过去变成一场梦),并在重演时修改或重塑自己的形象。这就是堂佩德罗在漫长孤寂的乡村生活中所做的事。
“《神学总论》里否认上帝能使过去的事没有发生,但只字不提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那种关系极其庞大隐秘,并且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取消一件遥远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取消目前。改变过去并不是改变一个事实,而是取消它有无穷倾向的后果。”(注:《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第266页。)
为了改变遥远的过去那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堂佩德罗取消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一头沉入自己的幻想,顽强地、按步就班地用艺术来篡改公认的现实,通过漫长的、隐蔽的积累,创造出了一部精神的历史,并在最终的意义上改写了世俗的历史。
堂佩德罗的形象很难固定,因为这是一个把生活改变成梦想和忏悔的人。在梦想中他的肉体消失,他成了影子,而尘世的生活仿佛是在玻璃的另一边隔得远远的。在众人眼中他的形象淡淡的,他的死就像水消失在水中,那么单纯、无声。这个模糊的形象内心却经历着腥风血雨的战役,完成了伟大的悲剧,他本人也以奥赛罗的面貌活在人们心中。故事涉及了艺术的根源问题,艺术不是来自于表面的社会生活,而是来自于内在的羞愧和激情,来自于要改写自我的冲动。堂佩德罗在死神面前悟出了人生的虚幻本质,也找到了使自己重新复活的秘密途径,那场外部的战争远不如他内心的战争来得深刻。
故事中的上校也是一个内心极为丰富的人。对于他来说,马索列尔战役同样是他灵魂里的一场战役,他对那场战役保留着鲜明生动而又充满虚幻的回忆。从他的叙述里你可以闻到战火中的硝烟,但你抓不住按常规解释的事实。那样的事实不存在。
“……他叙述的内战情况在我听来不像是两支军队的冲突,反像是一个逃亡者的梦魇。……他一件件事讲得如此生动,使我觉得这些事他讲过多次,他的话根本不需要回忆。”(注:《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第261页。)
他是从人生的本质来看待这场战事的,这便是他的记忆反复无常的原因。人必须及时“忘记”,才能更好地继续生活或改变生活。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很难对一件事作出定论。堂佩德罗到底是人们看到的胆小鬼还是具有非凡勇气的战士呢?应该说是二者的统一,必须承认没有多少人敢于像他那样将自己的一生置于腥风血雨之中。上校也是一个看透了人生的虚幻本质的人,所以他的记忆混乱而矛盾;因为他记下的是本质性的东西——迷宫中的绝望的行军,对城市的恐惧,梦魇似的逃亡,必死无疑的逼真感觉。在这种神秘的大氛围中,某个部下的具体表现实在无关紧要。
堂佩德罗用自己的一生构写了这个悲剧故事。结局到来前的几十年里,他因为不能满足只好一次又一次演习。他暗暗等待,想要的结果总是得不到,那个结果是命运留到他的最后时刻给他享用的,而他,一直在为奇迹的出现作准备。由于长年的激情耗掉了生命,他终于走到了最后一刻,梦寐以求的另一次死亡实现了,他获得了最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