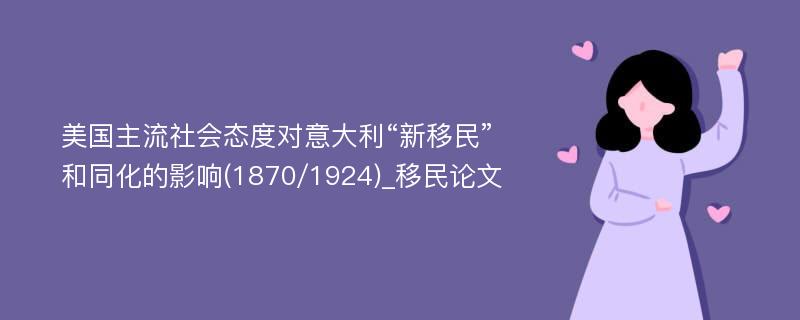
美国主流社会态度对意大利“新移民”、同化的影响(1870~192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大利论文,美国论文,新移民论文,态度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712.44;K712.51;K71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6)03-0076-11 同化(assimilation)①是移民社会走向同质化的必经之途。美国社会的变迁,也通常在其主流对移民同化态度上有所体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移民,作为美国“新移民”②的最大群体,其同化历程一波三折,与当时美国社会转型及一战桴鼓相应,因而颇受学者关注③。美国学界对意大利移民同化的研究呈现出对比鲜明的两极特征:一是关于美国意大利移民的宏观著述④,二是针对一城一镇乃至一人的细致研究⑤。前者固然能提供整个意大利移民的总体同化理路,却也无意间抹平了美国特殊时期意大利移民同化的起伏波澜;后者则常局限于一时一隅,在深化微观研究及个体经验的同时,美国变局与意大利移民同化之间的关联纠葛却被割裂。如此,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中观视野”,或许能为一战前后美国意大利移民同化历程提供某种新的认知,进而揭示移民同化的内在特性与规律。 一 意大利“新移民”的特征 19、20世纪之交的意大利移民堪称整个人类迁移史上的壮举。就其一般特征而言,鲜有与其类似者。恰如美国学者罗伯特·F.福里斯特所言,“这次意大利人口迁徙持续时间之长,在人类移民史上尚无先例”⑥。意大利移民大规模地持续往美,不仅是为了逃避本土政治压迫,寻求更好的物质生活,而且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人力资本配置的结果。意大利移民之所以在“新移民”中地位突出,所受美国排斥最甚,原因在于其所具备的显著特征⑦。 第一,意大利移民规模之大,在“新移民”中首屈一指。自美国有移民统计以来,累计超过500万意大利移民抵美,其中约400万人于1880~1920年间移民美国⑧。这种移民潮的出现并非突发事件,而是处于波浪式渐增状态。1861~1870年间,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为12206人,到1871~1880年间,这一数量增至55759人⑨。1880年,旧的意大利移民模式告一段落⑩,以南意大利移民为主体的移民模式兴起。此后,美国意大利移民急剧增长,并在1901~1907年间达到顶峰(11)。不难看出,直到1880年,意大利移民仍只贡献了美国外来移民的很少部分;到1896年之后,已经超越任何其他单个移民族群,成为最大的移民群体。1900~1910年,意大利移民占美国外来人口的比重,从不到5%上升至超过10%(12),足见移民规模之巨,增速之快。 第二,早期意大利移民多来自意大利北部,此时则以南意大利移民为主导。19世纪80年代初,第一波意大利“新移民”,仍多来自意大利北部的皮德蒙特(Piedmont)和利古里亚(Liguria)(13)。其后,意大利移民以南部为主导。从1876年到1900年,移民美国的772792人中,仅99023人来自北部,其余皆出自南意大利。19世纪的最后十年,超过80%的意大利移民来自南部,其中西西里占30%,纳普勒斯占27%(14)。到20世纪初这种移民特征更加突出,这从当时《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可见一斑:“在1914财政年度的前10个月……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共为220123人,北部移民为38397人。”(15)也就是说,这期间北部移民占整个意大利移民的比例不到15%。南部意大利移民对其故土有着深深的眷恋,在历史上虽经历过多次严酷内战仍不抛弃其故土而离去,而此时出现大规模移民浪潮,分析其原因,至少有四:其一,统一之后的意大利,北部对南部压迫尤甚,而人口剧增导致南部意大利人生存空间更受挤压;其二,美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也需要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工;其三,由于人口及环境的压力,当时的意大利政府史无前例地鼓励其国民移民海外;其四,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确立,要求人力资本实现全球优化配置。 第三,对照早期意大利移民的相对分散性,“新移民”聚居于美国东北部大城市。尽管意大利移民遍布全美,但在1900年,3/4集中于新英格兰和美国大西洋沿岸中部区域,如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以及新英格兰南部诸地。在全部意大利“新移民”中,有约75%~80%聚居于都市(16),超过当时美国人口城市化率的2倍。 第四,移民中持寄居心态者居多。“新移民”来源国的国民,在欧洲内部普遍有季节性移民的传统,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被认为是欧洲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意大利亚平宁山脉的村民,其大规模季节性迁移已为整个欧洲所共知(17)。但是,这种移民形式并非以在移居地扎根定居为目的,只是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暂别故土,而且这些移民所迁地离故乡较近,集中在德、法,漂洋到海外者屈指可数。这种传统也为美国的意大利“新移民”所保持。很多意大利人来到美国只为短期工作,一如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移民,来到美国的目的是“工作一段时间,赚得足够金钱,然后回老家享受”(18)。移民斯特凡纳·迈勒(Stefana Miele)就曾在他的回忆中坦诚:“我离开意大利去往美国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赚钱。”(19)迈勒的态度并非个案。这里有一数据颇能说明问题:意大利政府1901年规定,移民在申请护照时需要说明是暂时移居海外,还是永久定居异域。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3/4的人计划返回故土。1908~1916年间,有逾100万移民返回意大利,超过同期移民的半数。其中,北部意大利移民返回母国的比例为48%,南方则是56%(20)。 第五,不同于意大利早期几乎清一色男性移民的特征,在“新移民”潮中,越来越多的妇幼加入到了追逐命运的“豪赌”中。这由意大利“新移民”的模式决定。当时意大利移民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妇女和儿童自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数据显示,到1920年,绝大多数移民女性仍在族内通婚,每1000对夫妻中,有700~800对为族裔内结合。当移民男女不得不走出本族群寻求婚姻时,也会倾向于土生美国人,或与其族裔特性相近的族群。例如,爱尔兰人与苏格兰人、威尔士人或英格兰人结合,匈牙利人与奥地利人结合,波兰人与俄国人结合,等等(21)。一项关于马萨诸塞州移民小城劳伦斯(Lawrence)的研究证实了上述情况。该研究认为,移民的婚姻一般不外乎三种形式,同一族群内部通婚占77%,移民与土生美国人的婚姻占19%,跨族裔婚姻仅为4%(22)。意大利“新移民”的婚姻结构也大致如此。这种族群内婚姻,既是意大利移民未被完全同化的证据,也直接影响到移民二代的同化进程。 二 主流社会对意大利“新移民”的排斥逻辑 意大利“新移民”的诸多显著特征,使美国主流社会对其产生一种强烈的“非我族类”之感。社会群体的“我者”与“他者”归类,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以直接接触所感相似性和差异性为基础,以突发社会问题为刺激来强化之;另一方面,对某些预设分类的内化,如性别、国别、阶级、职业、宗教、文化或种族等。19、20世纪之交美国突出的社会问题,以及上述意大利“新移民”诸特征,使美国主流社会形成一种相对于意大利“新移民”自我优越的身份认知,并直接加剧其对“新移民”的他者意识、排斥理念与行为。据荷兰学者范·戴克研究,社会舆论符号再生产由精英支配,他们“控制了塑造公众意识的沟通条件,因而也就控制了族群共识”(23)。也就是说,美国白人精英通过其掌握的权力与话语资源,并利用公众的认知机制,使自己的种族主义观念与排外情绪成为主流思潮。如此,当时美国大众媒体、知识分子、有影响力政客的看法显得尤为重要。大众媒体能煽动民众的情绪;而知识分子在文化价值上有一定塑造能力,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引领着大众舆论与思想的发展;有影响力的政客则对民众有着极强的号召力,特殊时期能够左右社会舆论的发展。从一战前美国的总体舆情来看,意大利“新移民”面对着来自主流社会的敌意与歧视。 与此前排华情形如出一辙的是,大众媒体始终在意大利“新移民”排斥中扮演煽风点火的角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媒体中,强调意大利移民数量之巨及其对美国带来负面影响的报道屡见不鲜。例如,《纽约时报》1903年2月23日用两大版面,阐述过去几年“每年都有100万左右的移民来到这里”,其中意大利移民“超过任何其他单一国家”(24)。《华盛顿邮报》1904年12月5日报道:“在过去的一年,有812870名移民来到美国……其中193296人来自意大利。”尽管这一数据已很庞大,但仍不敌一年前的230622人(25)。1907年3月该报同样发文,表达了对大规模外来移民的恐惧,“在去年的移民大潮中,来自意大利的移民数为273000人”,并认为意大利移民是所有移民群体中最大的“潜在威胁”(26)。《华尔街杂志》对这一时期的移民也有持续的关注(27)。这些报道表面上看似一种基于事实的陈述,其实无形中激起了土生美国人对外来移民的恐惧,而作为“新移民”最大群体的意大利移民,自然是首当其冲。 随着南意大利移民人数的渐增,土生美国人遂将南意大利人视为意大利移民的典型,认为他们属野蛮人,是罪犯、污秽与贫困的代名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东南欧“新移民”的到来导致了美国人种退化,并指出当时意大利移民已超过爱尔兰人,但政府却仍无限制移民之策(28)。美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如作家威廉·霍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艾迪斯·瓦尔顿(Edith Wharton)同样为塑造南意大利移民的劣等形象添油加醋。霍威尔斯将南意大利移民视为半开化的人。詹姆斯将波士顿的意大利“新移民”视为粗俗、危险之人,认为应尽可能予以制止(29)。就连当时美国移民局局长秘书亨利·杰克逊(Henry J.Jackson),也发表了反对意大利移民的观点,认为意大利移民是美国“最不需要的移民”(30)。不仅美国主流社会将意大利“新移民”视为低劣的“有色人种”,曾一度饱受美国主流社会歧视的爱尔兰人也将意大利“新移民”与黑人相提并论(31)。就连北意大利人也不承认与南意大利人在种族、文化上的关联。在美国雇主们心里,北意大利人是稳重而可靠的工人,而将南意大利人视为野蛮狂暴之徒。由于种族主义社会学家以及马尔萨斯主义经济理论的误导,因此美国劳工领袖也认为意大利移民的大规模到来降低了美国人的工资待遇。很多进步主义者认为,移民是导致贫民窟扩张的罪魁祸首(32)。据《芝加哥每日论坛报》报道:“在纽约,已经有超过5000名无所事事的意大利移民,跟猪(hogs)一样拥挤于贫民窟的公寓内,……并与当地美国工人展开工作竞争”(33)。 每年意大利移民将在美国的所得汇回母国,也是导致土生美国人排斥意大利移民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笔汇款数目相当可观。《纽约时报》报道说,“1905年,邮局办理寄往意大利的汇款单为295221笔,总额达11092446美元,每单汇款的金额约37美元”,是所有外来移民中寄回母国资金最多的群体(34)。在主流社会的美国人看来,这些财富理应在美国内部循环,而不能流向国外,这是近代以来重商主义在当时美国的体现。他们只见美国资产表面上的流失,却没有意识到移民给美国社会创造的可见与潜在的巨大价值。这里仅举一例:19世纪末,意大利移民掌控着整个旧金山的卫生系统以及芝加哥99%的公路建设(35)。可以说,尽管他们大多没有技术,但凭借自己吃苦耐劳的坚韧精神,同样为美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意大利“新移民”中颇为流行的“契约工”制度,也为美国主流社会所责难。意大利“新移民”有的以“契约工”的形式来到美国。他们抵美后,需要为契约主工作数年,以偿还自己移民美国的各种费用。美国主流社会将之与奴隶制混淆,认为这些移民是美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事实上,这种“契约工”秉承自愿原则,与早期美国来自西北欧的“契约劳工”并无二致,而与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制则有云泥之别。当然,在意大利移民中还有一种“工头体制”(Padrone system)。一些意大利移民在到达美国后,由于无亲无靠,通常被所谓的“包工头”拐骗利用,被骗至矿区或铁路,从事异常繁重的劳动,即为带有强制色彩的“工头体制”(36)。在一般美国人看来,这种体制下的移民劳工,就是新时代的奴隶。这对于曾经饱受奴隶制之苦的美国来说,尤为敏感。不过,在这种“工头体制”下的工作者毕竟只是少数,不具代表性。 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同样表达了其对“新移民”排斥的观点。在20世纪初的美国移民大潮中,罗斯福愈发觉得,应通过严格移民法来限制移民,尤其是“那些不能迅速同化的种族”(37),同时“坚决拒斥所有种族的罪犯、弱智者、穷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移民美国”。他觉得包括意大利移民在内的南欧移民,改变传统旧习、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极为缓慢(68)。由于罗斯福在美国民众中的崇高威望,其观念自然也颇具影响力。罗斯福的态度在与美国主流观念的相互激荡之下,逐渐在全美范围形成一种排斥东南欧移民的氛围。 可见,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政治精英,都是基于美国种族主义的排斥“新移民”的观念。同时也能看出,种族主义并非天生,而是后天习得;人们通过公共话语的诸种形式来习得这些观念,而公共话语由精英控制。他们的“他者”所指,及其排斥话语,会同主流媒体在大众中广泛地传播族裔偏见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并使之成为“主流共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内的个体往往容易丧失自我而选择随波逐流。这也是意大利“新移民”在美国遭受普遍排斥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时期“我者”与“他者”的极化来自于人们对于极化了的规范的顺从,而规范的极化是主流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关系作用的结果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特别关注精英对意大利“新移民”排斥的话语支配,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大众种族主义及其对意大利“新移民”的排斥,也不意味着大众话语与种族主义不能自下而上地影响精英的社会认知与行动。精英话语与白人大众的互动催化,所构建的共识性意识形态,掀起的对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所有“新移民”排斥浪潮,其规模在美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美国主流对意大利“新移民”不易同化的指责,乃是对移民同化维度的片面解读,即过于强调种族、文化差异,以及对移民的同化之责,而忽视自身在移民同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事实上,主流社会对移民的接纳、尊重与包容,是移民同化的先决条件。美国主流社会一方面排斥意大利“新移民”,另一方面又指责其“不可同化”,实是颠倒了移民同化的内在逻辑,更有“欲加之罪”之嫌。 一旦这种对意大利移民排斥、歧视的话语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与支持,思想上的排斥就会转化为行动上的拒斥,且二者处于积极互动之中。其表现之一是意大利移民在入境美国过程中遭受一系列刁难。《纽约时报》1896年3月12日报道:“有900~1000人昨晚被拘留在爱丽丝岛接受检查,其中绝大多数为意大利移民。”(40)一如同时对华人的严苛审查一样,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减少意大利移民入境。19世纪90年代后,由于主流媒体、排外主义者对意大利移民危险性的渲染,致使意大利移民遭受了一系列恐怖的暴力袭击。其中,1891年3月14日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事件颇为典型。在该事件中,10名意大利移民被射杀,一名意大利移民被处以私刑。这一例子并非个案。1893年,9名意大利移民因涉嫌谋杀科罗拉多瓦楞斯格(Walensgurg)城的一名酒吧老板而被捕;两年后,其中6人被暴民处罚致死。1894年,在宾州的阿尔图纳(Altoona)有200名意大利移民被驱逐。1896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哈维尔(Hahnville)有3名意大利移民被私刑处决。3年之后,在密苏里州的塔卢拉(Talulah)有3名意大利移民遭受了同样的命运(41)。 面对美国这种歧视与排斥环境,很多意大利移民选择返回母国。在1887~1890年间,只有约10%的意大利移民返回故土,1900~1910年间为57%,到1911~1920年则高达82%(42)。然则,我们也不能将这种移民返程笼统地归为意大利移民在美国所遭受的歧视与排斥,在返回母国的意大利移民中,也并非都是在美国遇到了问题,而更可能是因为1908年意大利政府改变了政策(43)。当时,意大利向海外的移民被制止,并鼓励海外的意大利人带着积蓄和新技术回国效力,以实现意大利的崛起。但意大利移民所遭受的拒斥,无疑是其返回母国的直接推力。 三 一战前意大利“新移民”的同化困局 移民的文化适应过程,通常由移居美国时间长短来决定,但民族融合同化的程度,却因移居时间不同、所在地区和民族文化背景的相异,存在种种差别。移民同化入主流社会的比率,与移民自身的同化意愿、能力不能简单划等号。美国主流社会的接纳程度,可能在移民同化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尽管绝大多数1880年以前来自西北欧的“旧移民”,与土生美国人文化也不相同,但由于居住相对分散,且被美国社会接纳,因而较易同化入美国社会。相反,以意大利移民为代表的“新移民”,大量聚集于东北部城市的隔都区,似乎对其他地方的工作机会不感兴趣。而当时美国工业化的发展对大量普通劳工的需求,吸引了“新移民”来到诸如纽约等工商业中心。他们大多为实现家庭团聚而移民,有属于自己的社区。很明显,所谓“新”“旧”移民间的区别,并不仅仅关乎于其移民美国的时间与分布差异,更在于美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及两者所承载的文化差别。 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新移民”的同化进程相当缓慢。这是美国主流社会与意大利“新移民”拉锯的结果。与同期德裔移民不同,意大利“新移民”面对美国主流社会的严重排斥,对母国文化也缺乏自信,其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差异更为明显,因而缺乏安全感。一般而言,意大利“新移民”有积极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意愿,主流美国人则视其为低等人而加以排斥(44)。土生美国人通常误以为移民聚居在一起,目的是为了重建其在欧洲的生活环境;但事实上,移民在新世界的生活模式与旧世界相比可谓大异其趣。美国的城市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隔都”,外部世界的强大影响无处不在,这与移民在旧世界城镇间的隔绝状态迥然不同。意大利“新移民”互助组织,不是来自旧大陆的移植,而是缘于新世界需要的结果。在意大利南部,普通家庭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在他们移民美国之初,往往有手足无措之感,这样各种移民志愿组织就显得非常重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意大利人组织是1905年6月在纽约成立的“意大利之子社”(Order of the Sons of Italy)。该组织在短短几年内发展到拥有125000名成员,在全美有分支887个(45)。其成员每月需缴纳25~60美分的会费。如此,互助组织才有财力去帮助移民。其服务内容包括帮助移民立足,护卫其心灵,缓解其孤寂,照顾其病残,乃至移民死者的善后等。纽约市的“意大利外迁移民社团”(The Italian Society of Emigration)的目的也是为那些刚到且无助的意大利“新移民”提供寻找住所与合适工作的帮助。意大利移民社团建立,为保持传统化起了某种隔离墙的作用。这类组织在帮助“新移民”的同时,也延续了在美国的意大利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维系着移民对母国的情感(46)。意大利“新移民”群体内聚与吸引,既是在新社会的生存所需,更是对美国主流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移民排斥的反击。就理论而言,“群体凝聚力基本上是群体归属的表现而非起因”(47),但一旦与共同的社会认同直觉联系在一起时,就有可能成为群体形成的充分条件,更何况意大利移民有着共同的民族与文化基础,在母国并不相联系的地域间的人们,到美国反而有了共同的经历、认知和认同基础。 意大利文的报刊对意大利新闻事件的报道,给新来移民在美国最初时光以安慰与调整,使其在漂泊他乡的艰辛中感受到母语文化的温暖。美国最早一份意大利文报纸是1849年在纽约创建的周报《意大利回声报》(L' Eco d' Italia)。到1880年以后,随着“新移民”大规模的到来,在1880~1921年间,仅芝加哥一地就有至少二十种意大利文的报纸出现。此外,在美国还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激进报纸,纽约的《无产阶级报》(Proletaio)(1896~1920)便是一例;以及一些宗教组织出版的报纸,如《火炬报》(La Fiaccola)(48)。尽管意大利移民报纸秉承欧洲报刊的风格,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很快跟上了美国的潮流与风格。吊诡的是,在这些报纸自身跟上美国方式的同时,它们以意大利文对意大利以及意大利移民的关注报道,在维持意大利移民传统文化与认同中写下浓重一笔。 教育与同化的关系极其密切。但是,意大利移民却“不注重其后代的教育”(49)。尽管他们自己饱尝因文化水平低下,以及不通英语而难寻工作的艰辛,但仍积极尽早将其年幼的子女送入工厂。事实证明,有知识或中上层意大利移民更易于同化。当时美国《义务教育法》要求14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必须在校学习,南意大利移民的子女一般在到达14周岁后,无论成绩好坏、愿意学习与否,其父母都会将他们拉出校园,投入工作。这些孩子通过工作以补贴家用,缓解其父母经济困境压力。到一战前,意大利移民青少年中,虽有73%上过小学和初中,但继续高中学习者不足1/10。对于贫困的南意大利移民家庭来说,立竿见影的工作收益,远比长远的教育投资更具吸引力。教育水平的缺失,导致多数意大利移民家庭徘徊于美国社会的底层。 除教育外,意大利“新移民”家庭结构也延缓其同化进程。在意大利南部乡村,社会结构基于家庭而立,每个人最重要之事是维护家庭尊严,增进家族荣耀。父亲对家庭事务具有决定权;母亲尽管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在家事上也有一定发言权,常在父亲与孩子之间扮演协调人的角色;而孩子们在年幼时就需要担负起对家庭的责任,男孩尤其被视为家里经济的重要来源,其收入须上交父亲,所以儿子越多,经济收入往往也越丰厚。女儿一般不外出工作,而是待字闺中,以期佳偶②。孩子们在寻找配偶时一般倾向于听从父母之命。父母通常在本村为孩子寻觅配偶。在意大利“新移民”中,很多都是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迁徙。亲朋关联,既是当时意大利移民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也是维系其传统文化认同的重要粘合剂。迈克尔·卡莱菲(Michael Califi)1905年移民美国,源于其兄长与堂兄的先导作用。兄长帮他找到了一份搬砖工的工作。尽管卡莱菲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在几个月后就辞职离开,但这份工作无疑给他初来美国时扎稳脚跟以很大帮助(51)。马里奥·维纳(Mario Vina)全家能在1909年移民美国,也源于其父亲早先移民美国的多年积累(52)。局部封闭的意大利家庭生活模式也随着移民家庭而带至美国。这种亲朋纽带无疑有利于移民对原文化认同的维系。 意大利政府对美国意大利移民的立法保护也是维系传统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1901年,意大利政府通过保护海外移民的法律。无论是意大利政府或移民,都理所当然地将意大利移民视为意大利人。移民是意大利政府的特殊子民。移民到美国,只不过是时间或长或短地侨居在海外。有意大利官员甚至认为,海外的意大利移民应该在有关官员的监督下参与意大利国内的政治选举。即便是那些已经获得美国国籍的移民,如返回意大利,也该直接给予其意大利公民权(53)。母国对意大利移民的牵挂,使移民心中有一种进退有据的踏实感,对母国自然也更为认同。 四 一战期间主流态度转变与意大利“新移民”同化契机 在一战期间,美国社会将关注的焦点聚于德裔移民,非德裔移民基本平安地渡过了美国参战的两年余光阴。理论上,一战期间极端的移民族裔同化理论“百分之百美国主义”适用于包括德裔移民、意大利移民在内的所有外来移民,但是战争的后果往往超越一般的理论逻辑范围。美国社会对“带连字符族裔群体”(54)潜伏的仇恨变得公开化。这期间,在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发生了一起针对普通民众的袭击事件,要求将所有的外来移民教员清出校园(55)。不过,这在战时仅属个例,因为移民在美国已是无处不在,要将其清除出任何一个领域都难以想象。一战中,美国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美国社会对于移民团结与归同美国社会有着更加紧迫的需求;另一方面,非德裔移民的处境较一战前普遍有所改善,这时期的排外主义者很少对其进行侵扰。美国社会对德国移民的同化更为迫切,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给其他移民提供了一种宽松的环境。也正因此,不同移民族裔反而加速了对美国的认同感。当然,非欧洲移民排斥在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移民美国与美国的移民。战时的欧洲需要大量的人力,而移民要穿越大西洋需冒更大危险,移民美国的人数锐减。意大利去往美国的移民从1914年的283738人到1915年的49688人,急速下降到1918年的5250人,基本结束了对美劳工的输出(56)。由于1917年美国参战后对意大利移民态度的转变,以及军需生产对人力的大力需求,美国军队招募了30万名意大利移民,其中包括89662名未归化者(57)。美国劳工的短缺,给了意大利移民前所未有的高工资工作机会,主流社会对其排斥亦被一战的洪流所淹没。大众媒体对意大利移民的正面报道,也在这期间迅速增加。《纽约时报》1916年8月27日报道:“在整个纽约考试的前三甲中,其中一名是移民,一名是移民之子,另外一名则是第三代移民。”(58)该报道证明意大利孩子非常聪明,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意大利移民视为劣等人种的看法已有霄壤之别。对于意大利意军人在一战期间的表现,美国媒体也不乏溢美之词:“意大利飞行员在一战中的表现超乎一般水准。”(59)《华盛顿邮报》1918年4月25日也报道:“有一个很小的细节让人们不得不对意大利人刮目相看。很多意大利移民都积极踊跃地参加军队,并在战场上展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作为意大利移民,他们代表美国在法国作战,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60)意大利水手也被称为“杰出的水手”(61)。报纸对这种英雄事迹的赞扬,固然与战争时期鼓舞士气的宣传格调有关,更是美国人对意大利移民态度转变的有力证据。甚至包括战争结束后一段时间,意大利裔美国军人在一般美国人眼里也是正面形象:“据说有20万名意大利裔预备役军人即将重返美国。这会成为问题吗?他们将在农场工作,如果他们在城市从业亦会童叟无欺、合理要价。”(62)当时美国情报部门官员克莱尔(Creel)针对意大利政府对其移民在美国所遭受的敌对与歧视的宣传,认为可以将受伤的意大利裔士兵送到意大利去疗养,同时也是最有力的广告宣传(63)。其言下之意是,今日的美国意大利移民处境已非同往昔,已经获得了主流社会的认可、尊重与接纳。 面对主流社会态度的转变,意大利移民也积极地参与到美国事务与同化当中。据《纽约时报》转芝加哥4月21日消息,“有超过两万意大利移民冒雨游行”;市长认为“意大利移民很快选择成为美国公民”,“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个城市的所有意大利人成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64)。意大利移民之所以能在一战时期迅速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之中,并非其真正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同化,而是美国社会由以往的反感与排斥,因战时国家对内部同质性的特殊需求而以宽容与接纳取代之。《威尔士美国人》报纸甚至还出现了意大利移民联合英裔、法裔以及比利时裔移民写给总统威尔逊的信: 尊敬的总统先生: 德国代表要求美国禁止企业向协约国出售武器。但是,从美国的公民到政府都有向协约国出售军火的自由权利,该权利受国际法保护,且德国也是国际法的缔约国之一。这种法律非在和平时期不得更改(65)。 这一联合信件,是以美国人的身份发出的,同时也表达了意大利移民同化入美国社会的积极意愿。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意大利移民与英裔移民相提并论。 意大利移民中,参与美国军队对德作战者亦不在少数,这既是对以往美国社会排斥的一种回应,更是证明自己属于“百分之百美国人”的绝佳机会。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马力欧·维纳(Mario Vina)出生于1896年8月3日,13岁时移民美国,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时间不详。据他回忆,自己曾在一战时加入美军,在法国对德作战,并参与潘琼·维拉(Pancho Villa)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一只眼睛受伤失明(66)。这些经历,足以使维拉能够较为顺利地归化为美国公民。概而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某种程度上打断了意大利移民在美国所遭受的敌视与排斥,实现了其在美国同化历程中的一跃。这再次证明,美国主流社会的态度,在意大利移民同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意大利移民所经历的战时短暂包容仅是昙花一现,正因此,人们一般认为“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之下的所有族裔群体都处境艰难,这事实上抹平了“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下不同移民群体经历的跌宕起伏。无疑,一战使土生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注外来移民对美国的忠诚,试图使之彻底美国化,这事实上也给了以往被排斥的移民族群以同化之机。但是,一战结束后,由于“赤色恐慌”(67),以及对美国内部社会存在可能分裂的危机想象,使排斥外来移民的声浪迅速回升,美国社会掀起歇斯底里的反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风潮,很多美国人也将矛头再次转向意大利移民,认为其中多含激进主义者和罪犯。美国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很好地利用了这种移民排斥话语,从而为严格的移民限额制度提供理论支撑。美国国会适时地通过了一系列移民限制法律。到1921年,美国政府对东南欧移民实施限制。即便如此,《华盛顿邮报》1921年6月8日仍报道说,“来自意大利的移民超过了移民法的限额”,应当予以进一步限制(68)。到1924年美国颁布移民限额法,彻底颠覆了其以往对欧洲“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此后,意大利移民锐减,主流排斥态度死灰复燃,其同化历程也回归缓慢。 五 结论 自历史步入现代,不同群体相遇频繁,同化自然也不可避免。从生物学层面看,同化是一种营养补给过程,即将各种外来物质吸收到有机体的身体中,成为自身之一部分。但是,由于在这一过程中物质具有排他性,因而同化也需要一定强制力。就一般理解而言,所谓同化,是指具有不同种族和族群背景的人,在一个更大的社区生活中,摆脱原有文化的束缚,在相互交往中趋同的过程(69)。无论何时何处,只要具有不同种族和文化传统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不论他们是否构成数量上的少数)就会被逐渐同化。 同化既有单向同化也有相互融合。单向同化是指一个群体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行为方式而接受另一群体文化的过程;而相互融合是指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互动、交融,产生一种不同于任何原有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的过程,这种新文化可在同化过程中的不同水平上生长出来。戈登在他的著作中说明了整个同化过程的不同阶段,认为完全同化应包含下述七个方面的变化:文化模式朝着东道主社会文化模式的转变;在基层群体层面上,外族成员大量加入东道主社会的各种协会、社团和俱乐部等制度组织;大规模通婚;作为东道主社会族群成员的认同意识的发展;偏见的消失;歧视的消失;权利冲突和价值观念冲突的消失(70)。这个概念性框架,不仅对衡量同化本身,而且对确认同化进展到何种程度,都是颇有价值判别标准。完全同化,意味着人群中已不再有基于种族或族群观念而相互隔阂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这往往需要至少三代人的时间。意大利“新移民”模式则是一种非典型单向同化。美国主流社会排斥意大利“新移民”,虽未彻底关闭其同化入美国社会的大门,但同化速度迟缓。一战“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指导下的同化,极大地改变了意大利移民族裔的同化模式。意大利裔移民因被主流社会接纳也较快同化入美国社会中。这种特殊的同化模式,是一战极端局势下孕生的“同化怪胎”,它违背自然同化规律,效果也是转瞬即逝。 可见,移民族裔同化的制约因素,除了以往学界普遍关注的文化差异外,其自身的消极态度以及主流社会的排斥与抵触,更是移民不能融入美国社会的主要原因,后者更是同化受阻的关键所在。更何况,即便少数族裔完美地同化入美国主流社会,仍然很有可能面对歧视;而完全同化关键在于主流社会的接纳与包容。由于任何文化在不停的变化之中,我们在研究和理解一种文化价值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影响这一价值的其他人群。同样,认识美国主流文化的发展变迁,不能忽视移民族裔群体在同化过程中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改造。这也是研究美国移民同化的重要维度与意义之所在。 收稿日期 2015-08-10 注释: ①美国学术界对“同化”概念的研究聚于社会学领域,且经历了芝加哥学派、后芝加哥学派、新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兴起于20世纪初,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帕克与厄恩斯特·W.伯杰斯等。二人在合著的《社会学概论》一书中认为,同化是一种“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和团体获得了其他个体或群体的记忆、情感以及价值观,并通过分享他们的经历与历史而整合进入到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中。到1960年代,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戈登,在其代表作《美国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第一次将同化分为文化同化和结构同化,并将结构同化作为同化实现的关键。以戈登为代表的后芝加哥学派,最大贡献乃在于揭示了同化的多重性、多维性。查尔斯·阿尔巴(Richard Alba)与维克托·尼(Victor Nee)所著的《美国主流的重建:同化与当代移民》一书,是新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作。在该书中,作者对以往学界那种对同化简单化的处理提出了批评,指出非欧洲裔移民的同化进程要复杂得多。他们对新芝加哥学派的贡献在于从更微观的角度来审视少数族裔的同化,这也是对戈登同化理念的一大补充。这一学派一直持续到今天仍在不断发展完善中[分别参见罗伯特·E.帕克、厄恩斯特·伯杰斯:《社会学概论》(Robert E.Park and Ernest W.Burgess,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21年版,第735页;米尔顿·戈登:《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Milton Gorden,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17页;理查德·阿尔巴、维克托·尼:《美国主流的重建》(Richard Alba and Victor Nee,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Assimi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本文主要采纳弥尔顿·戈登对同化的理解,并受查尔斯·阿尔巴与维克托·尼著作的启发,认为意大利新移民比一般欧洲移民的同化进程更为复杂。Assimilation与Acculturation(涵化)不同,后者是指一个种族或部落或者社会族裔群体在与另一个种族和部落的接触中在文化和艺术上的接近,促使一个民族适应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同化一词尽管最初特指美国的情况,但对当前世界其他多民族、多种族国家也具有某种参考意义。 ②本文所说的“新移民”为1870~1924年间以东南欧移民为主的美国外来移民。当前提及的美国“新移民”,主要是1965年以来的以拉美人和亚洲人为主的移民潮。 ③国内学界对美国意大利移民同化问题的研究也有初步尝试。王寅教授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总体叙述了美国意大利移民的同化历程(王寅:《筚路蓝缕他乡路——意大利移民在美国的同化进程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76~82页)。对意大利移民同化问题稍有涉及的成果还有,李其荣:《整体性和多样性的混合——美国的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比较研究(1865~1965)》,《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7~15、6页;王寅:《美国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比较研究》,《世界历史》2。05年第4期,第48~56页。 ④主要成果有,亚历山大·德康特:《亦苦亦甜:意大利裔美国人历史探析》(Alexander DeConde,Half Bitter,Half Sweet:An Excursion into Italian-American History),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集团1971年版;理查德·甘比诺:《血统之血: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困境》(Richard Gambino,Blood of My Blood:The Dilemma of the Italian-Americans),加登城:双日与公司出版集团1974年版;帕特里克·J.加洛:《族裔疏离:意大利裔美国人》(Patrick J.Gallo,Ethnic Alienation:The Italian-Americans),拉瑟福德:菲尔里·迪克逊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南希·C.加内维尔:《新语言,新世界:美国的意大利移民(1890~1945)》(Nancy C.Carnevale,A New Language,A New World:Itali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890~1945),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代表著作包括,安德鲁·F.罗尔:《移民赞歌:意大利人的冒险与北美扩张中的殖民者》(Andrew F.Rolle,The Immigrant Upraised:Italian Adventures and Colonists in an Expanding America),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玛丽·霍尔·伊特斯:《罗萨:一个意大利移民的生活》(Marie Hall Ets,Rosa:The Life of an Italian Immigrant),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埃里克·安菲西亚特洛夫:《哥伦布的孩子:意大利人在新世界史话》(Erik Amfitheatrof,The Children of Columbus: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Italians in the New World),波士顿:布朗出版公司1973年版;玛塞拉·本希维尼:《意大利移民的激进文化:美国颠覆者的理想主义(1890~1940)》(Marcella Bencivenni,Italian Immigrant Radical Culture:The Idealism of the Sovversivi in the United States,1890~1940),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⑥罗伯特·F.福里斯特:《我们时代的意大利移民》(Robert F.Forester,The Italian Emigration of Our Times),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19年版,第3页。 ⑦关于意大利“新移民”特征,学界较少关注,笔者拟在此作相对全面的分析归纳;国内学者对意大利人移民美国的原因分析相对全面,笔者行文中仅略作补充,而不再赘述。关于意大利人移民美国的原因,参见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3~78页。 ⑧参见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数据:从殖民地时代到1957年》(U.S.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57),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0年版,第56~57页。文中数据为笔者根据美国人口统计数据计算所得。 ⑨数据为笔者根据美国历史数据计算所得(参见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数据:从殖民地时代到1957年》,第57页)。 ⑩1879年意大利移民美国的人数为5791人,1880年增至12354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跨越(参见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数据:从殖民地时代到1957年》,第57页)。 (11)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数据:从殖民地时代到1957年》,第56页。 (12)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数据:从殖民地时代到1957年》,第56页;罗伯特·F.福里斯特:《我们时代的意大利移民》,第372页。 (13)乔瓦尼·夏沃:《内战前美国的意大利人》(Giovanni Schiavo,The Italians in America before the Civil War),纽约:维戈出版社1934年版,第266页。 (14)托马斯·阿奇迪肯:《成为美国人:一部族裔史》(Thomas J.Archdeacon,Becoming American:An Ethnic History),纽约:自由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页。 (15)“不断增加的移民”("Immigrant Throng Grows"),《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1914年6月10日,第5页。 (16)乔瓦尼·夏沃:《内战前美国的意大利人》,第267、268页。也有报道称,只有“不到5%的意大利移民去了乡村”[“意大利移民的邪恶”("Evils of Italian Immigration"),《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1888年7月23日,第4页],但这一数据不确切。 (17)马克·怀曼:《往返美国:返回欧洲的移民》(Mark Wyman,Round-Trip to America:The Immigrants Return to Europe,1880~1930),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18)“意大利移民的邪恶”,《芝加哥每日论坛报》,1888年7月23日,第4页。 (19)汉尼拔·杰拉尔德·邓肯:《移民与同化》(Hannibal Gerald Duncan,Im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纽约:D.C.希斯公司1933年版,第561页。 (20)伦纳德·迪纳斯坦、罗杰·L.尼古拉斯、大卫·M.赖默斯:《本地人与陌生人:一部美国人的多元文化史》(Leonard Dinnerstein,Roger L.Nichols,and David M.Reimers,Natives and Strangers:A Multi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 (21)多丽丝·韦瑟福德:《外国女性:美国的移民女性(1840~1930)》(Doris Weatherford,Foreign and Female:Immigrant Women in America,1840~1930),纽约:肖肯书局1986年版,第210页。 (22)唐纳德·B.科尔:《移民之城:马萨诸塞州劳伦斯(1845~1921)》(Donald B.Cole,Immigrant city:Lawrence,Massachusetts,1845~1921),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04页。 (23)范·戴克著,齐月娜、陈强译:《精英话语与种族歧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24)“意大利移民工作”("Italian Immigrant Work"),《纽约时报》,1903年2月23日,第4页。 (25)“移民减少”("Fewer Aliens Coming"),《华盛顿邮报》,1904年12月5日,第4页。 (26)“作为公民的意大利人”("Italians as Citizens"),《华盛顿邮报》,1907年5月13日,第4页。 (27)“上一财政年度的移民”("Immigration Last Fiscal Year"),《华尔街杂志》(Wall Street Journal),1909年9月22日,第5页。 (28)唐纳·加巴希亚:《移民与美国的多样性:一部社会与文化史》(Donna R.Gabaccia,Immigration and American Diversity: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39页;又见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数据:从殖民地时代到1957年》,第56页。 (29)安德鲁·J.罗尔:《意大利裔美国人》(Andrew J.Rolle,The Italian Americans),纽约:自由出版社1980年版,第59页。 (30)“杰克逊再次见证:他认为意大利人是最糟糕的移民”("Jackson Again a Witness:Italians He Thinks the Worst Immigrants"),《纽约时报》,1903年4月10日,第8页。 (31)戴维·R.罗迪格:《通向白人之路:美国移民如何成为自人》(David R.Roediger,Working toward Whiteness:How America's Immigrants Became White),纽约:贝斯克书局2005年版,第87页。 (32)约翰·莫顿·布鲁姆:《伍德罗·威尔逊与道德政治》(John Morton Blum,Woodrow Wils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rality),波士顿:布朗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117页。 (33)“意大利移民的邪恶”,《芝加哥每日论坛报》,1888年7月23日,第4页。 (34)“现金流向欧洲:移民将数百万资金寄回母国”("Cash Returns to Europe:Immigrants Send Millions Back to Homes"),《纽约时报》,1906年2月18日,第13页。 (35)弗朗西斯科·保罗·塞拉斯:《从美国返回意大利:返回移民,保守还是革新?》(Francesco Paolo Cerase,From Italy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Back:Returned Migrants,Conservative or Innovative?)(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71年,第65页。转引自马克·怀曼:《往返美国:返回欧洲的移民》,第49页。 (36)“意大利奴隶贸易”("Italian Slave-Trade"),《每日人民报》(Daily People),1902年4月14日,第3页。 (37)(38)托马斯·G.戴尔:《西奥多·罗斯福的种族观》(Thomas G.Dyer,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页。 (39)约翰·特纳等著,杨宜音、王兵、林含章译:《自我归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页。 (40)“更多移民被扣:森纳博士认为来自意大利港口的人会越来越少”("More Immigrants Detained:Dr.Senner Thinks There Will Be Fewer from Italian Ports"),《纽约时报》,1896年3月12日,第9页。 (41)(43)乔瓦尼·夏沃:《内战前美国的意大利人》,第272页。 (42)安娜·玛丽亚·马特隆:“意大利移民定居与返回”(Anna Maria Martellone,"Italian Immigrant Settlement and Repatriation"),《美国意大利历史协会第十届年会记录》(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Italian Historial Association),1976年10月,第152页。 (44)安东尼奥·斯特拉:《美国意大利移民的几个方面》(Antonio Stella,Some Aspects of Italian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Statistical Data and General Considerations Based Chiefly upon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es and Other Official Publications),纽约:G.P.帕特南出版公司1924年版,第22页。 (45)(48)斯蒂芬·特恩斯特伦编:《哈佛美国族裔百科全书》,(Stephan Thernstrom,ed.,Haro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51、553,553页。 (46)汉尼拔·杰拉尔德·邓肯:《移民与同化》,第564页。 (47)约翰·特纳等:《自我归类论》,第121页。 (49)汉尼拔·杰拉尔德·邓肯:《移民与同化》,第746页。 (50)(52)彼得·莫顿·科恩:《埃利斯岛采访:移民讲述自己的故事》(Peter Morton Coan,Ellis Island Interviews:Immigrants Tell Their Stories in Their Own Words),纽约:福尔河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51)据卡莱菲本人回忆,他当时已基本花光身上所带的钱财,如没有这份工作,将不得不重返意大利。参见布鲁斯·M.斯特夫、约翰·F.萨瑟兰、奥尔多·萨勒诺:《从老国来:一部美国欧洲移民的口述史》,Bruce M.Stave,John F.Sutherland and Aldo Salerno,From th Old Country:An Oral History of European Migration to America),汉诺威: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页。 (53)乔治·M.斯蒂芬森:《美国移民史(1820~1924)》(George M.Stephenson,A Histor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1820~1924),纽约:拉塞尔出版社1926年版,第67页。 (54)这里所谓的“带连字符的族裔群体”是对移民群体在美国的后裔的统称,如"Italian-American"(意大利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华裔美国人)等等。 (55)约翰·海厄姆:《国土上的陌生人:美国本土主义的类型(1860~1925)》(John Higham,Strangers in the Land: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纽约:阿森姆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56)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数据:从殖民地时代到1957年》,第56页。 (57)亨伯特·S.内利:《从移民到族裔:意大利裔美国人》(Humbert S.Nelli,From Immigrants to Ethnics:The Italian American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 (58)(59)《全国劳工论坛报》(National Labor Tribune),1918年4月4日,第4页。 (60)“为意大利裔美国人骄傲”("Proud of Italian-Americans"),《华盛顿邮报》,1918年4月25日,第9页。 (61)《真相》(Truth),1916年9月23日,第6页。 (62)《全国劳工论坛报》,1919年5月15日,第2页。 (63)乔治·克里尔:《我们如何宣扬美国》(George Creel,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纽约:哈勃兄弟出版公司1920年版,第244页。 (64)“意大利裔美国人游行”("Italian Americans March"),《纽约时报》,1918年4月22日,第4页。 (65)“将这些寄给威尔逊总统”("Send This to President Wilson"),《威尔士裔美国人》(Welsh-American),1915年7月1日,第1页。 (66)彼得·莫顿·科恩:《埃利斯岛采访:移民讲述自己的故事》,第38页。 (67)在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1918~1920年与1947~1954年两次所谓的“赤色恐慌”。本文所指的是第一次赤色恐慌,即美国社会对政治激进主义以及工人与社会主义者革命的担忧与恐惧[参见罗伯特·K.默里:《赤色恐慌:一项关于全国癔症的研究(1919~1920)》(Robert K.Murray,Red Scare:A Study of National Hysteria,1919~1920),纽约:麦克格劳希尔公司1955年版]。 (68)“移民超过限额”("Immigrants Go Over Ouota"),《华盛顿邮报》,1921年6月8日,第6页。 (69)G.辛普森:《同化》,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种族与种族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8页。 (70)米尔顿·M.戈登:《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第71、70页。标签:移民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意大利经济论文; 意大利总统论文; 意大利生活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