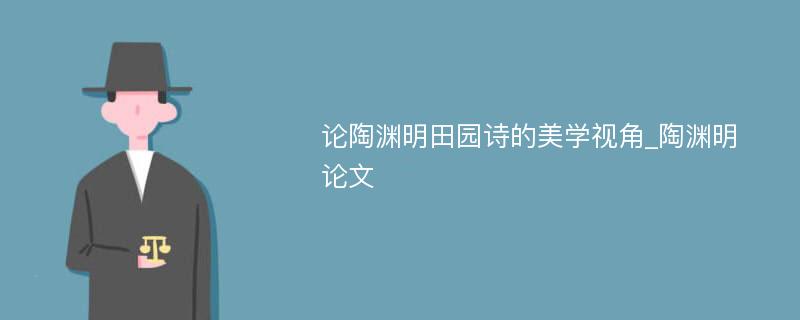
试论陶渊明田园诗的审美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园诗论文,视角论文,试论论文,陶渊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逃禄视角
陶渊明辞令归田后,在田园生活中之所以能以苦为乐,首先是因为他是从逃禄视角来审视田园生活之美的。中国古代的文士,大多以追求高官厚禄,建功立业,留名青史为人生理想,陶渊明青年时代也雄心勃勃,立志“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以一展自己人生的宏图,为何后来却反其道而行之,毅然辞令,逃禄归田,并且以田园为美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避祸患,二是离羁绊,三是远耻辱。
陶渊明避祸患,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陶渊明大半生遭逢晋宋更替的乱世,晋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乱,大混战,大篡弑的时代。在这种严酷而凶险的社会背景下,在陶渊明看来,与其呆在官场求取功绩名声还远不如归隐田园以保全性命。有了险象环生的官场的对比,能确保生命安全的田园自然就成了诗人所追求的理想之地,因为在这里,即使生活清苦,甚至忍饥挨冻,但对于生命来说,无论如何,它也是一方充满雨露阳光的足以使生命存活的美好乐园。
在陶渊明的心目中,官场除了是一个危及性命的险恶之地外,还是一个羁绊人性自由的污浊之地,这也是他以田园为乐园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中国古代的文士,大多心性清高,追求人性自由,不愿受制于人。因此,历代都有为摆脱官场的束缚而毅然辞官的,稽康因不愿为“七不堪”所累而归隐就是典型的一例。陶渊明辞令的直接原因是反感以繁文辱节迎拜上司,但这决不是事出偶然,而是他在居官期间心性和行为长期被束缚以至到了无法忍耐的地步的必然结果。还是在入仕早期,陶渊明就深感官场束缚的难以忍受,屡屡表示要挣脱官差的羁绊,回归田园去乐享人性自由的生活。
此外,在陶渊明的“田园美”里,还有一束来自“为官耻辱”的折光。供职官场,会使自己的人格受辱,这也是古代不少文人的共识,因此也是古代不少正直的封建文人决然辞官归田或终身隐居不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问题上,陶渊明也接受了前代文人的影响,他29岁初仕江州祭酒,30岁时就具有了这种观点,并且在诗中明确地表现了这种观点:“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虽无挥金乐,浊酒聊可恃。”(《饮酒二十首·其十九》)此诗实为诗人所表达的人生价值观,诗人认为,人可以贫,但应贫而不失“介然”之气节;贫而能坚守气节与人格,乃是人生价值之所在。
二、图存视角
对于陶渊明来说,要生存,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屈居官场,以违逆天性,牺牲人格尊严乃至性命为代价去求取俸禄,二是退隐田园自由自在、躬耕自资。官场的黑暗与险恶,是陶渊明看穿了,也厌弃透了的,因此陶渊明毅然作出了弃官归田的决断,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之所以视田园为乐园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田园能给他保全自己的人格独立、宝贵的生命和天性的自由提供生存所需,从而能使自己免受官场之患,羁性之累与人格之辱。
一是本农思想的影响。所谓本农思想,就是说农耕能为生民提供衣食等生存之需,因此它是生民生存之根本,又由于民为国之本,因此它又是立国兴邦之根本。在我国古代,本农思想渊源深远。陶明诗中的“舜既躬耕,禹亦稼穑”(《劝农》),“远若周典,八政始食”(《同上》),以及“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同上》),“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等诗句,都是上述本农思想的具体表现,也正是这种已上升为本体论的本农思想,给了陶渊明安于农耕,自力图存的永恒力量。
二是历代遁世者的影响。陶渊明力耕图存而不计有其苦,只求有其安,快然享其乐,其中亦多有来自遁世者人生实践的支持和鼓舞力量。历代遁世者,亦即历代隐士。他们基于“世于我而相违”的厌世弃世观,视官职俸禄为蔽履,隐居山林或田园,以耕钓图存,仅管生活清贫甚至窘迫,但却能以此为安乐。这些人往往被视为“洁身自高”的典范而为历代文士乃至官僚所崇拜或仿效。
三、适性视角
一是田园自然环境的适性乐。陶渊明出生于浔阳柴桑的农村,那里山水田园清丽的自然风光从陶渊明出生后就淘冶着他“性本爱丘山”的情性,并使之得以稳定地发展并进而成为影响他向往并深爱山野田园的重要精神力量。“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五首·其一》)这种归隐田园后如鱼得水、如鸟归林之感实是诗人“性本爱丘山”的本性升华的具体表现,同时从诗中亦可显见,这种升华的完成亦有来自避祸患、离羁绊的精神力量的巨大影响。有了这种精神定位,诗人对田园自然环境的深受便更具自觉性和自足感。
二是田家淳朴人情的适性乐。陶渊明以田园为乐园,还在于田家农友淳朴的情感与他真率的天性最为吻合。陶渊明是从官场上过来的人物,深知官场上的人情虚伪矫造,媚上欺下,甚至尔虞我诈,也深恨这种与自己真率的天性相左的人情恶习。陶渊明天性真率,其真率的程度真可谓空前绝后。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陶渊明视田园为适性宜心的天然乐园,实是他在对比了官场上人情之矫伪,田园里人情之善朴后出于适性需要而对田园的一种依恋。
其一是零距离交往之乐。“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其二》)“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归田园居五首·其五》)这种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任情随意毫无拘束的交谊是官场绝无,田园仅有的,其情之真,其性之朴,诚如老子所倡导的“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的修性反德于婴儿的朴真情性。
其二是歌诗谈叙之乐。“我唱尔得言,酒中适何多。”(《蜡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其一》)乐于赋诗吟唱,乐于赏析谈诗,诗人的这些性之好,也在田园中得到了满足。尽管这种满足是粗疏的,但却是真朴的,因而也是他所珍重的。
其三是商谈农事之乐。“时复墟里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话桑麻长。”(《归田园居五首·其二》)“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乐于同农人商谈农事,这是陶渊明“转志欲长勤”(同上)思想的升华:他不仅从身份上融入了乡民之中,而且从情感上,心志上融入了乡民之中,没有对村野民情纯真美的深爱,何能有如此的融入!
综上所述,陶渊明弃官归田后,之所以能把劳动艰苦,生活清贫的田园视为理想的归宿之地,就其社会和生性原因而言,是他在当时黑暗险恶的时势影响和自身天性的驱使下所形成的独具个性的审美视角的结果。但就其思想渊源而言,虽然也有道家的逍遥人生观和佛家的超脱现世苦的影响,但我以为最深邃、最强力的影响当是儒家的“安贫乐道”和历代先贤对他的感化作用。
陶诗中提及了不少古贤,这些古贤大多是安贫乐道的典范。陶渊明对他们不仅敬重有加,而且视他们为师范:“斯滥岂悠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乎,在昔多余师。”(《有会而作》)“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正是历代古贤的榜样作用,才使他永葆了贫而乐道,苦而无怨的精神风貌。
摘自《襄樊学院学报》,2005.1.7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