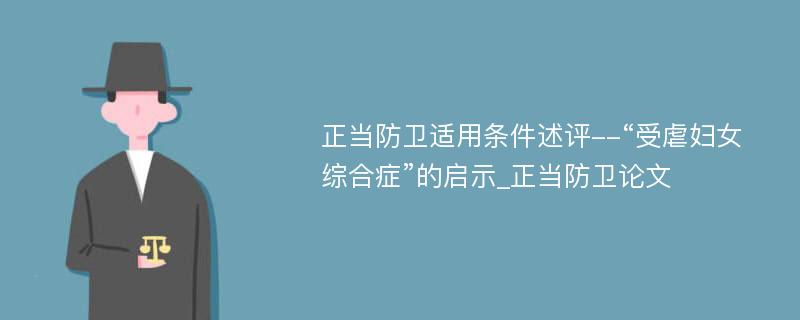
正当防卫的适用条件之检讨——来自“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当防卫论文,综合症论文,启示论文,受虐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12(2013)01-0012-09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且尚未结束时才能进行防卫。关于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一般应以不法侵害人着手实行不法侵害时为其开始。在不法侵害尚处于预备阶段或犯意表示阶段,对合法权益的威胁并未达到现实状态时,就实施所谓的防卫行为,属于防卫不适时[1]。这种传统见解是否无懈可击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件。
2004年9月7日晚,刘某冲向刚走进家中的丈夫黄某,对其连捅数刀,致其当场死亡。事后查明,17年前,刘某在帮黄某洗衣服时,被黄某强奸。由于刘某觉得丢人,只好勉强嫁给了黄某。婚后黄某经常对刘某施暴虐待。黄某爱酗酒,每次酒后都要对刘某施暴,甚至在刘某怀孕期间,黄某也没有停止对她施暴。刘某还称:黄某每次酒后都强行和她发生性关系,并进行性虐待,连月经期也不放过。前几年,刘某实在觉得无法再这样过下去,到厂里开离婚介绍信。黄某听说以后,到厂里大闹了一场,扬言谁要是给开介绍信,就和谁拼命。此后,刘某单位的人再也不敢管了。2004年8月的一天,黄某深夜回家,粗暴地打醒睡梦中的刘某,要和她发生性关系。之后,黄某说“今天不爽”,翻身从床头柜中拿出一把蒙古刀,对着刘某肚子就是一刀。刘某一直等黄某睡着了,才捂着肚子跑到医院,缝了12针。同年9月7日,刘某正在家养伤。晚9时许,她躺在床上听到黄某进屋的声音,并且闻到传来的酒气,想起又要遭受暴打,遂产生杀死黄某的念头,从厨房里拿出一把尖刀,冲向院子里的黄某,将其杀死[2]。
这是一个典型的受虐待妇女杀夫案,案例中的犯罪人长期受丈夫间断性的虐待,她完全有合理的理由预料,今后仍将受到同样甚至更严重的暴力虐待。更为无赖的是,她试图摆脱受虐待的努力失败了。在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的绝望处境下,她最终选择了杀死自己的丈夫。令人遗憾的是,对这种身处绝境中的弱者的自然反应,法律却将她们遗忘了。因为按照我国现行刑法及主流刑法理论,这个案例中被告人的行为不成立正当防卫,而是构成故意杀人罪。法律与现实的脱节表明,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制度存在缺陷,值得进一步反思。事实上,北美国家对受虐待妇女杀死丈夫的情况很早就有研究,一些学者进而提出了“受虐待妇女综合症”(Battered woman syndrome)理论。本文拟通过介绍“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理论,对传统正当防卫制度中的“紧迫性”条件的合理性、面临不法侵害时防卫人是否应履行躲避义务、防卫制度是否应考虑弱势群体等问题展开反思。
二、“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理论及其争论
“受虐待妇女综合症”原本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丈夫对妻子进行身体、性或精神虐待之后取得妻子的谅解,尔后又实施虐待。如此反复,使得妻子因为周期性的虐待而形成的一种习得性的无助感[3]。患有“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的妇女可能最终杀死其伴侣。受虐待妇女杀夫案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法律争议可被划分为三大类[4]:一是“面对面”杀人事件,这类事件是受虐待妇女在正遭受暴力虐待时杀死其伴侣。二是“间歇期”杀人事件,即受虐待妇女在其伴侣正在熟睡或在暴力行为已经暂时停止后杀死其伴侣。三是雇用他人杀人事件,即受虐待妇女雇用他人或强求他人杀死自己的伴侣。在“面对面”的受虐待妇女杀人案中,自卫的辩护通常被接受,因为杀人行为发生在正遭受虐待之时,所以有充分的理由使陪审团接受自卫辩护。而对于雇用第三人杀人的案件,所有法院都一致拒绝自卫辩护。有争议的是第二类受虐待妇女杀人案,因为受虐待妇女在实施“防卫行为”时尚未面临紧迫的不法侵害,不符合传统正当防卫的条件。由于对第一、第三两种类型没有争议,以下关于受虐待妇女杀夫案的讨论,都是以第二种类型为基点的,以下不再说明。
“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理论由美国学者雷诺尔·沃尔克(Lenore Walker)博士发展而来。沃尔克经研究发现,长期受家庭暴力虐待的女性通常会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心理和行为模式。这种心理和行为模式,以及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超过受害人的忍受极限,与受害人采取以暴制暴的行为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性。为解释受虐待妇女的这些特征,沃尔克假设了两个理论:习得无助论(Learned Helplessness)和暴力循环论(Cycle of Violence)。
根据社会一般观念,如果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无法忍受这种暴力,她可以离开这种被虐待关系。因此,受虐待妇女没有必要杀死她的丈夫,她的行为就不能按正当防卫处理。为了消除这种偏见,沃尔克博士提出了习得无助论。习得无助论源自心理学者马丁·塞利曼(Martin·Seligman)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做过的动物试验。塞利曼对被囚禁的狗进行随机的、间断的电击,当狗发现多次试图逃脱的努力最终都徒劳无功时,它们开始没有抵抗的屈从。既不能逃脱也无法抗拒的间断性电击,最终使狗感到“无助”。到后来,当为狗提供逃跑的机会时,它们也没有反应。更为惊奇的是,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狗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对其生存环境进行控制,许多狗是试验人员把它们从囚禁的笼子里拖出来的,很多狗不再知道逃脱[5]。受这个试验的启示,沃尔克认为,受虐待妇女对长期家庭暴力的反应与狗在铁笼子里受到电击的反应是相似的,于是她用这种现象来解释受虐待妇女的心理瘫痪状态。她认为,受虐待妇女经历了认为自己无法逃避、抗拒的长期暴力之后,变得被动、服从和无助,觉得不能对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施加任何影响[6]。习得无助论解释了受虐待妇女即使遭受了难以忍受的暴力伤害也不愿离开被虐待关系的原因,消除了人们对妇女保持受虐待关系是因为喜欢挨打的偏见,理解她们在有生命危险时为什么不是简单地逃跑而是选择以暴制暴。
根据传统正当防卫理论,只有对紧迫的不法侵害才能进行防卫。然而,不少受虐待妇女是在其丈夫熟睡或醉酒时杀死其丈夫的,按正当防卫的这一条件,受虐待妇女的杀夫行为不能按正当防卫论处。为了解释此问题,沃尔克博士提出了暴力循环论。暴力循环论反映了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循环特征。第一阶段为紧张情绪积蓄期。这一阶段开始于争吵及较轻的身体和情感虐待,并增强施虐者与受虐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二阶段为暴力殴打期。以施虐者无法控制的暴力暴发为特征,动辄不计后果地殴打受虐者。第三阶段是忏悔原谅后的和好期。在这一阶段双方重归于好,可谓雨过天晴[7]。因为家庭暴力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受虐待妇女长期过着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生活,不仅使陪审员(法官)相信家庭暴力受害人内心恐惧的叙述,也使受虐者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对她的伤害随时都可能发生。更言之,暴力循环论解释了受虐待妇女认为对自己的严重伤害即将来临(紧迫)的合理性,尽管施虐者当时很温顺甚至正在熟睡。
由于女权运动的努力和沃尔克提出的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法官相信,在审理受虐待妇女杀人案中,法律不能忽视存在两个受害者”[8]。已被杀死的施虐丈夫是受害者,实施杀人行为的妻子同样是受害者。受虐待妇女综合症以专家证言的形式作为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已经被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不少法院所采纳。
三、“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给我国的启示
法律的生命在于满足现实的需要,法律制度要根据现实不断调整姿态,才能永葆青春。传统正当防卫制度在受虐待妇女杀夫案中表现出尴尬后,催生了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理论。当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理论受到挑战与质疑后,西方有学者提出,应当对防卫制度的紧迫性要件进行宽松解释,将受虐待妇女的行为纳入正当防卫的范围,使其在法律上正当化[3]。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有就事论事之嫌。事实上,正当防卫制度要求在紧迫的不法侵害威胁下才能实施防卫行为导致的困惑,不仅是受虐待妇女防卫时遇到的难题,也是其他类型防卫面临的难题。更言之,在没有面临紧迫不法侵害的场合,并非所有受虐待妇女都有权使用暴力进行防卫,有权使用暴力进行防卫的人也并非都是受虐待妇女。因此,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使那些没有面临紧迫的不法侵害威胁,但有必要使用武力进行防卫的场合,可以进行防卫。因此,我们要跳出受虐待妇女综合症这个圈子,反思传统正当防卫制度本身的缺陷。
(一)用“必要性”条件代替“紧迫性”条件
一般而言,紧迫性与必要性密切相关,而且通常保持一致。当威胁不紧迫时,就没有必要诉诸暴力进行防卫。同样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使用暴力进行防卫具有必要性时,危险要么是迫在眉睫,要么就实际面临。当威胁只是潜在的,就没有必要使用武力防卫,因为有充足的时间寻找其他方法应对,如报警。不仅如此,当威胁的到来明显较远时,暴力威胁就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甚至可以说是假想的,自然难以主张用暴力反击是必要的。正因为如此,才用紧迫性这一条件替代必要性[9]。然而,这种替代是不完美的,反而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因为紧迫性与必要性在逻辑上是独立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有时是有差别的。所以,有学者认为,紧迫性条件的意义仅在于确定暴力防卫是否真的必要。换言之,紧迫性没有独立意义,仅仅是必要性的替代条件,目的在于限制必要性的范围[10]。因之,应将紧迫性这一条件废除,将正当防卫限定于有必要使用暴力进行防卫的场合。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紧迫性是不必要的僵硬条件。美国学者罗滨逊(Paul H.Robinson)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紧迫性这一条件的不妥之处。假如A绑架并且拘禁了D,A告诉D一周后将杀死他。D每天早上在A给他送食物时都有机会杀死A逃跑。在这个例子中,按照紧迫性的要求,D只有在第七天A持刀站在D面前时才能进行防卫。罗滨逊指出,但这一结论明显不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受害人即便等到最后一刻也不能通过其他方法避免侵害的发生,就应当允许他提前选择最有利的时机防卫[11]。由此可知,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不具备“紧迫性”,只要符合“必要性”,行为人也应有权进行正当防卫。当侵害处于一种周期性状态时,英国法院的态度是:既然侵害的发生是必然的,那么就应允许被害人在危险发生之前进行防卫。如被害妇女综合症,施虐者午睡时当然不可能对妇女进行侵害,但只要受虐待妇女有理由相信,施虐者醒来后会继续对自己实施虐待,就应允许受虐待妇女在施虐者午睡时进行防卫。否则,一旦施虐者再次实施暴力,处于弱势地位的受虐待妇女将无以应对。很显然,这一结局对受虐妇女是不公平的。
正当防卫的核心是避免对有必要进行自我保护的人适用刑罚,正当防卫的其他各种条件都是反映有必要使用暴力这一条件的。例如,成比例这一条件是确保防卫人不要超过必要限度,施加不必要的报复。再如,禁止挑起攻击的人自卫也是必要性的反映。又如,有些国家刑法要求受攻击者在面临威胁时有躲避的义务,也是必要性的自然演绎。
关于如何解释受虐待妇女的杀夫行为,特别是在施虐者并未对受虐者构成紧迫逼近的威胁时杀死施虐者的正当防卫问题,支持非功利主义的学者的理由是“权利丧失”理论。因为施虐者实施了应受谴责的严重暴力行为,自然丧失了生存的权利。这一观点在马丁(Harry C.Martin)法官就受虐待妇女杀夫案的发言中显而易见:“因为20年的粗野虐待,使自己的妻子,即被告人的生存状况极度悲惨,是他自己给妻子提供了杀死他的机会。陪审团也可以发现,被告人的行为是合理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本已很悲惨的生命。”[12]
其次,并非紧迫的威胁必然比不紧迫的威胁更危险。紧迫性这一条件起源于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缺乏紧迫性的威胁就是不必要的,只有紧迫的威胁,才有必要使用暴力防卫。因为如果威胁不是紧迫的,就假定行为人可以采取其他措施避免暴力防卫。然而,这种近乎直觉的判断是有缺陷的,上述绑架案例已经表明,即使不法侵害不是紧迫的,对他人的威胁也是很危险的。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理论也论证了,即使受虐待妇女没有面临紧迫的不法侵害,她也有必要使用致命暴力进行防卫。由于紧迫性不是确保行为人有必要使用暴力的完美替代,因而使用暴力进行防卫较好的限制条件应该是必要性。
倡导紧迫性这一条件的学者认为,允许在没有紧迫伤害威胁的情况下进行防卫意在鼓励谨慎。例如,没有紧迫性这一条件,行为人可能有充足的时间寻求警察的帮助,从而不使用暴力进行自卫,但这种认识是存在问题的[13]。第一,不少情况下行为人无法求得他人的帮助。例如受虐待妇女,由于其丈夫暂时没有实施暴力,警察也无法处理,或者说请求警察帮助也会徒劳无功。第二,如下所述,对不确定的侵害绝大多数法律都否定有躲避的义务。对确定无疑地将要发生的不法侵害,有什么理由要求行为人等到无法抗拒的不法侵害变成现实的那一刻才能防卫呢?特别是当施暴者与受暴者之间的力量特别悬殊时,如果一旦可能的暴力转变成了现实的威胁,法律赋予受暴者的自卫权就仅徒有虚名。这是对受暴者的苛求,也是自卫权的悲哀。由于社会日益关注受虐待妇女的处境,她们正是面临这种重复地、看起来无法避免的,但却不是紧迫的暴力威胁的受害人。根据罗逊(Richatd A.Rosen)教授的观点,因为紧迫性“只是发展了必要性原则,如果在紧迫性和必要性之间有冲突的话,必要性应当优先”[4]。
再次,严格要求紧迫性这一条件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结论。例如,小地痞甲经常无故严重地殴打乙。一天,在一间大仓库内甲再次明确地告诉乙要将他打成残废。当甲到停在仓库门口的车上取用于殴打的武器时,乙乘其不备将甲打成了重伤。在这一例子中,如果严格适用紧迫性这一条件,则乙属于防卫不适时。但是,如果等到甲取来工具实施暴力时,乙再进行防卫明显太晚了,甚至无法避免被打成残废的结局,显然对乙不公平。不难发现,在侵害能被确定无疑地预期时,不能适用紧迫性这一条件来限制自卫。可能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有人主张对紧迫性进行扩大解释,认为当后来不能再对一个不法侵害进行防卫,或者只能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防卫时,这种不法侵害就属于直接面临的状态,可以进行防卫。斯坦福·莫尔斯(Stephen Morse)教授建议,“如果在相对近的将来,死亡或者严重身体伤害是确定的话,而且等到将来的袭击紧迫时,已经无法足够的防卫,并且真的没有其他适当的选择的话,传统的自卫原则应当将预先的攻击行为视为是正当的”[14]。
依据传统普通法理论,当行为人有机会躲避时,就不能进行防卫。但现在美国多数州的刑法已经放弃了要求行为人履行躲避的义务。这种对传统普通法自卫原则的扩张,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真正的男人”有“天赋的权利”不撤退[15]。当面临威胁时,任何懦夫性的条件都与美国人的价值观相违背。为促进这些自治观念,通过放弃要求行为人履行躲避的义务,美国刑法扩大了自卫权的适用范围。与此相反,传统防卫法的“紧迫性”条件使受虐待妇女难以进行正当防卫,因为这一条件要求,即使防卫有必要性时,行为人也要等到威胁迫在眉睫时才能进行防卫。只有废除紧迫性这一条件,妇女才会与男人有同样的机会“不撤退”,防卫制度才可能更为平等[7]。
最后,允许使用暴力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担忧是可以避免的。一些人可能认为,由于没有可信赖的可行方式判断未来面临的不法侵害是必然的,如果对正当防卫不用紧迫性这一条件进行限制,这一权利可能被滥用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应该说,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以“9·11事件”以后美国对伊拉克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为例,由于美国主观上认定伊拉克正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不对伊拉克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等到伊拉克对美国发动袭击时再防卫就晚了。于是,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后来查明,伊拉克没有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的那种主观认识是错误的、不合理的,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个人防卫与国家防卫具有类似性,自卫权的滥用也可能导致不应有的伤亡。在笔者看来,这种担忧完全可以通过严格必要性的判断消除。
为消除废除紧迫性这一条件可能导致的风险,笔者认为,在符合以下条件的情况下,进行防卫才有必要性,才允许进行先发制人的防卫:第一,必要性的判断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根据行为人的经历或当时的实际情况,行为人必须诚实地相信对方将对其发起暴力攻击。第二,理性人在当时的处境下也会认为对方将向行为人发起暴力攻击。第三,对确定无疑将要到来的不法侵害,仅在难以躲避和无法求得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才能提前防卫。这里的躲避并不要求行为人不惜一切代价,如果能够安全躲避,就应履行躲避的义务。如果行为人诚实地、合理地认为不能安全躲避,就认定其履行了躲避义务。之所以对确定将要发生的不法侵害要求行为人履行躲避的义务,是因为未来的不法侵害毕竟不同于现实的不法侵害,从政策或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还是要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尽可能避免损害。以受虐待妇女为例,受虐待妇女必须诚实地相信,其伴侣将再次对其进行暴力虐待。并且,根据受虐待者以前受虐待的经历,理性人在受虐待妇女的处境下也会认为,受虐者的伴侣将会对其再次进行暴力虐待。只有行为人主观上诚实地、客观上合理地认为对方将再次施虐,才符合了第一个条件和第二个条件。再看第三个条件,如果她曾经多次试图逃离或请求离婚,但每次都被找回或不成功,并被施以更严重的虐待和威胁,就可以视为无法躲避。如果她没有尝试摆脱受虐待关系,或有理由相信她能安全躲避而没有躲避,就杀死了她的丈夫,则没有满足必要性条件,仍应承担刑事责任。
(二)躲避义务之思考
在进行必要性判断时,如果被攻击者能安全地跑开,从而避免攻击时,是否还有必要进行防卫呢?传统普通法规则要求,在使用致命性暴力进行防卫时,行为人必须履行躲避的义务,仅在退到绝路时才可以使用致命性暴力进行防卫。现在这一规则已被不少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所废止,不再要求行为人在防卫时履行躲避的义务。关于面临不法侵害的人是否应履行躲避义务,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反对行为人必须履行躲避义务的理由是:第一,假如人们在面临攻击时必须逃跑,那么那些小流氓和好打架的人就会用它来到驱赶和平的民众,只要他们想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统治。这将与法律要保护和平秩序的原则不相一致[16]。第二,要求一个人像“懦夫一样退缩”是错误的,至少是不现实的。对非法攻击理直气壮的反应是,用暴力进行反击,不用躲避,这是伸张正义的需要。第三,正确永远不必为错误让路,要求一个无辜的人躲避违反了这一原则。第四,呼吁人民躲避的规则可能最终使无辜者在没有退路时也试图寻找退路,因而增加无辜者死亡的风险[17]。赞成行为人必须履行躲避义务的理由是:其一,这一规则适当兼顾了生命价值的重要性,并且这一规则与仅在具有必要性时才能使用致命性暴力的一般规则一致。其二,如果受害人可以安全躲避就不能对侵害者使用致命性暴力,因为在可以安全躲避的情况下要求受害人躲避没有增加受害人的风险,同时减少了不必要的死伤结果的发生,符合保护生命的原则,体现了法律的文明。
关于防卫者是否应履行躲避义务这一问题,我国刑事立法没有具体规定,刑法理论也较少涉足。美国法院普遍认为,在行为人不负挑起侵害责任的情况下,如果使用非致命性暴力防卫,行为人没有躲避的义务,即便行为人完全可以安全地撤退而躲避侵害,仍然可以对不法侵害者实施防卫行为。但如果行为人面对的是致命性的不法侵害,而需要使用致命性暴力进行防卫,法院的态度存在较大的分歧。大多数法院认为行为人不必躲避,可以径直使用致命性暴力手段进行防卫。其根据是,正义不必屈从邪恶;面对生命危险进行必要的反抗是人之常情;倘若要求受害人逃跑,可能在逃跑的过程中被不法侵害人杀害。少数法院则主张,如果受害人可以安全躲避就不能对侵害者使用致命性暴力[3]。
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一般而言,对不法攻击不要求躲避,这是因为:根据惩罚性理论,使用武力对抗袭击者是被准许的,因为袭击者遭受的任何伤害都是自取的。根据个人主义理论,一个公民没有必要给那些侵犯其自由的家伙让路或作出任何妥协。从正当防卫的社会理论来看,对抗袭击作为保护法律和秩序的一种方式被视为是正当的,不撤退是伸张正义的需要。一般之外总会有特殊情况,防卫也是如此。在笔者看来,以下三种情况防卫人要履行撤退的义务:
第一,对来自无刑事责任能力者、减轻刑事责任能力者的攻击进行防卫,行为人要履行躲避的义务。在进行防卫时,要区分对来自无刑事责任能力者、减轻刑事责任能力者的攻击与有刑事责任能力者的攻击。罗克辛教授认为,对精神病人的攻击、无意醉酒的人的攻击、孩子的攻击、由于不可避免的认识错误而发动的攻击,防卫人要履行躲避的义务,只要这种躲避没有危险并且可能,同时应尽可能给攻击者造成较小的损害[16]。例如,人们允许把正在进行攻击的精神病人撞开,只要人们能够无危险地消除这种攻击,但将其击毙就不应当是“所要求的”。之所以对这类不法侵害进行防卫前要求防卫人履行躲避义务,是出于道义的考虑,因为在道义上对这类人应更宽容。在既不能消除攻击又不能取得帮助时,允许为了自身的安全,对无责任能力者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但是,在可能不会给自己造成重大危险的时候,人们就必须考虑到自己面对的是与恶意的攻击者不同的人。因此,在人们从使用拳头防卫向使用武器过渡时,自己就必须接受损害较小的风险(例如一些打击)。的确,对这种“有风险的爱护”的义务,有一些受限制的界限:任何人都不必让自己被一个精神病人或者被一些在刑法上不负责任的未成年人打成伤残。
第二,对尚未直接面临,但确定将要到来的不法侵害进行防卫,行为人应履行躲避的义务。如前所述,当不法侵害尚未直接面临,但行为人诚实地、合理地相信这种不法侵害必定要到时,行为人应履行躲避的义务,这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也是尽可能防止误伤的手段。
第三,因自己的过错引起的攻击,行为人应履行躲避的义务。一般而言,由被攻击者违法挑起的攻击,被攻击者有忍受的义务,不能进行防卫。但如果被攻击者只实施了轻微的过错行为,甚至是由于过失所致,而攻击者以与挑起事端者的过错行为极不协调的方式进行攻击,挑起事端者还是有防卫权。笔者认为,这种防卫权仍应受到限制,至少应履行躲避的义务。
(三)正当防卫制度应考虑受虐待妇女等弱势群体。
如前所述,传统正当防卫理论要求,仅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或者迫在眉睫的,而有合理的理由相信,除了以暴力反击的方式保护自己或他人免遭死亡或严重伤害外,才能进行防卫。这些传统认识和见解使得认定那些杀死施虐配偶的女性成立正当防卫非常困难,尤其是那些由于害怕自己或家庭将来遭受的致命暴力侵害而实施杀害施虐者的情形。因为根据上述要求,如要成功地提起正当防卫辩护,受虐待者必须证明她的行动是在特定情形下作出的合乎情理的反应,这就要求她所采用的反击手段是与所受到的人身威胁程度相适应的,且这种威胁是紧迫的。更言之,她除了给予致命性暴力反击外,别无选择。然而,对于一个长期受家庭暴力侵害而处于高度恐惧状态下的受虐待妇女而言,较之其伴侣,无论在体力还是在精神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她唯一合乎情理的选择只能是,当她感到安全时才采取行动,如当侵害者正熟睡时或醉酒后无力反抗之际。然而,由于陪审团或法官往往对受虐待妇女受到的伤害和经历缺乏切身的理解;更由于传统正当防卫理论以男性为基础而建立,对这种自然的、合乎情理的反应,在传统正当防卫框架内、在通常的司法群体中会将她的行为解释为长期怨恨积蓄下有预谋的行为,而不是在特定事件触发下的正当防卫反应。他们难以视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行为为合乎情理的,而往往将她使用凶器等器械对付毫无准备的施虐者视为是主动性的攻击行为。
尽管不少学者揭示了沃尔克有关受虐待妇女行为假设的不充分性和自相矛盾性,但抨击者承认,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对传统防卫法的一个重大改进,它承认妇女的经历并克服正当防卫中存在的偏见[6]。正当防卫的法律原则由男人发展而来,适用于男人间的争斗,并且对这一原则的争论经常由男人来解释。典型的情形是,假定冲突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他们力量相当且是陌生人。正当防卫因此被定义为,个人对其对手使用适当的武力,而且这个人有理由相信他正处于紧急的、非法的身体伤害危险之中,为防止遭受严重的身体伤害,适度使用暴力进行防卫是必要的。但这种高度主观化,且以男性为主的假设和处理,运用于男性与女性、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冲突时,就需要进行修改[18]。例如当一个瘦弱的妇女持刀对一个手无寸铁的拳击运动员进行防卫,其手段也应认为是适当的,因为拳击运动员的一拳一脚都可能对那个瘦弱的妇女构成致命的打击。就受虐待妇女而言,当其施虐的丈夫或伴侣还没有实施身体攻击时,她诉诸致命暴力的行为也应被认定为是正当防卫。因为和一个人遭遇陌生人的情况不同,她处于特殊的位置,从以往痛苦的经历可知,他的威胁是真实的并且即将实施。受虐待妇女从一个小小的暗示或者信号就能认识到殴打迫在眉睫。例如,男人说话音调和面部表情的微妙变化。同样的,在暴风雨前的平静期或者虐待达到巅峰之后,妻子对其伴侣发起的反击,也可以被认定为是正当防卫,因为她熟悉他的攻击形式[19]。
1987加拿大莱维莉(Lavallee)杀夫一案中,高等法院采纳了专家证言,支持了莱维莉提出的正当防卫辩护理由。莱维莉杀夫案的胜诉,突破了传统法律以男性视角对正当防卫所下的定义,正当防卫所要求的“紧迫性”和“使用防卫手段的相当性”不适用于受虐待妇女,因为其以男性的经历和反应经验作为衡量标准。加拿大最高法院也承认,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没有考虑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生理现象和社会经历,对女性来说这是不公平的。而缺乏性别视角,势必影响法官和陪审团对受虐待妇女杀夫的合理性作出准确的判断[20]。
我国司法实践没有采纳“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理论,没有认识到受虐待妇女杀夫是其摆脱家庭暴力的无力选择,对于受虐待妇女杀夫的行为不以正当防卫论处。家庭暴力的受虐待者与施虐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悬殊,受虐者在体力上远不是施虐者的对手,加上受虐者长期受家庭暴力侵害在心理上形成的无助感,使其觉得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在暴力行为正在进行时与施虐者抗衡,根本不可能成功地完成传统意义上的正当防卫[21]。如果以传统正当防卫理论来衡量这些人的行为,她们很难成立正当防卫。如果以弱势群体为视角,结合她们的生活经历重新审视她们的行为,不难发现,在普通男性看来是难以置信的行为,在弱势群体那里却是那么合理和自然。
女性主义的核心观念是,传统思想中存在一种根本性的男性偏见。传统理论主要是在男性至上社会中男性思考的产物,表现为男性不知不觉地把男性观点推定为普适的真理[22]。长期以来,男性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规则的制定和适用是以男性为主,防卫制度也是如此。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防卫制度是基于“合乎情理”的行为标准,对“合乎情理”的解释往往是以男性在特定情景下的合乎情理的反应的经验作为标准。如要成立正当防卫,就要证明存在一个紧迫的不法侵害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合乎情理”的反应,而“合乎情理”的认定标准是歧视女性的、有缺陷的,它是男性文化主导下的产物,它仅适合于男性行为,并不适合于女性的防卫行为,尤其不适合于那些长期遭受男性配偶在身体、心理及情感上虐待的女性的情形[23]。鉴于在立法与司法中“防卫”界定的种种缺陷,本人也赞同,正当防卫标准的制定与适用必须反映女性的特征和经历。推而广之,正当防卫制度的标准及其司法适用应反映弱势群体的经历和特点。
四、结语
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的研讨使我们认识到,传统正当防卫制度中的“紧迫性”这一条件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一条件将很多长期受虐待的妇女排除到了正当防卫制度之外,或者说正当防卫权的适用空间在她们那里被严重的压缩,导致了事实上的不公。“当一条规则或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只有服从正义的基本要求来补充法律安排的形式秩序,才能使这个法律制度免于全部或部分崩溃”[24]。因此,完全有理由用“必要性”条件代替“紧迫性”条件。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的深入研讨还启示我们,正当防卫制度中的躲避义务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尽管为了伸张正义,我们不能要求防卫人躲避,但在特定的情况下防卫人还是要履行躲避义务。
另外,加拿大和美国法院采纳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的出发点都是: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是以男性为标准制定的,它对受虐待妇女和受暴经历针对性不够,因此应当改革。[20]女权主义对传统正当防卫制度的挑战也告诫我们,防卫制度的制定及其适用要有性别的考量。推而广之,在制度设计时不仅不能以圣人的标准要求普通人,有时还要从弱势群体的角度检讨制度的合理性。一言以蔽之,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理论还启示我们,刑法中的各种制度值得时常从不同角度进行重新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