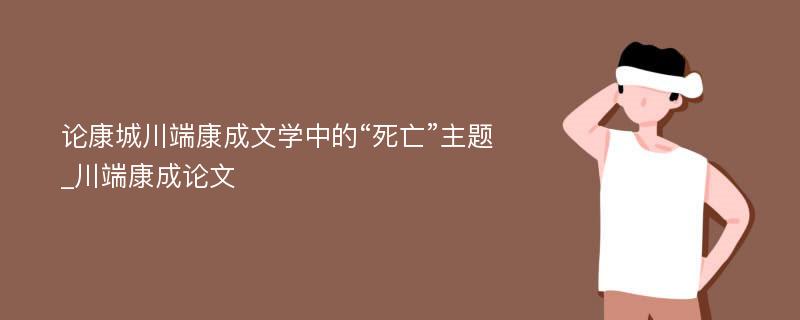
论川端康成文学的“死亡”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川端康成论文,主题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1)03-0065-03
1972年4月16日,日本文坛巨匠川端康成在其公寓口含煤气管自杀了。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川端康成无言的死,为世界留下了无限的话题。死亡和生存一样,都是人生的重大问题。许多哲学家认为,死亡是缠绕着人一生的极其深切的人生问题,追求死亡与追求幸福是一致的。一个人在暮年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他以往对待死亡观念的延伸。川端康成创作中不断出现的死亡主题,也反映着他的人生观和美学追求。
一
川端康成说:“优秀的艺术家在他的作品里预告死亡,这是常有的事。”[1]川端康成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对死亡有着切身的体验,他的审美情趣以及近三分之一多的作品是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川端的著作中,较之一般作家对死亡主题的追求更强烈,也更具个性色彩。川端康成对死亡的描写与海明威、波德莱尔等人不同,他笔下的死亡一方面笼罩着恐怖的气氛,渗透着深深的悲哀的情愫,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亦真亦幻、既悲且美的情调,以及人生无常、生死不灭的生死观。
(一)描写对死亡以及死亡临近的恐惧感,其间充满了伤感的情怀。在川端康成人生观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接触的死亡实在太多了,他自己深感每日都能嗅到死亡的气息。对死亡的恐惧感笼罩着他的身心。他说:“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死于肺结核。母亲受其感染,第二年也去世了。少年时期的我害怕自己也会因肺结核而早死,时常流露出少年的感伤。”[2]
川端康成早期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亲人的死亡给自己心灵带来的恐怖与痛苦。《十六岁的日记》描绘了少年和弥留之际的老人。老人痛苦的叫喊,不仅使少年的眼中充满了怜爱的泪水,而且也令少年对死亡的即将到来深感恐怖。为了让垂危的老人能起死回生,少年甚至去做连自己也觉得可笑的事,“我从仓库里取出一把剑,在祖父的床铺上空挥动了几下,然后塞进褥子底下。”少年这一迷信行为,似乎让我们感觉到整个房间都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在小说的后记中,作者又记载了祖父临死前的呻吟,“世上的人都会死的”,“可以不死的人就要死了”,以及祖父明知自己死之将至,却不拒绝请大夫的行为,反映了川端康成深感死之无常以及人对死的惧怕。同时,小说还表现了川端康成悲哀的心绪,“啊,我太不幸了,苍天大地将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短篇小说《意大利之歌》在描写主人公死前的情景时也同样充满了恐惧的气氛,“在昏暗的走廊里,死神一般的黑影肃然并立。产仔博士胸前的白色绷带却剧烈地起伏着。他呼哧呼哧地喘气,这是临近死亡的征兆”。
《山音》是一篇有关死亡的小说,其间对死亡逼近的预感,描写得比死亡本身更让人感到恐怖。主人公信吾面临衰老之境,十分颓伤,如记忆力不断衰退,忘记在自己家中工作半年的女佣的名字,甚至他连系领带的方法都弄不明白了。死亡的预感不断萦绕在他的脑海,他觉得妻子容貌的衰老也是老龄和死亡的影子,在每夜的梦境中,死者的影子不断出现。
《睡美人》与其说是描写江口老人对性的渴望,莫如说是他对死之将至的恐怖。江口、福良以及一些不知名的老人来到睡美人俱乐部,本身就证明了自己的衰老。因此,当他们“躺在睡着的年轻少女身边,碰到她的皮肤,从心底所产生出来的是靠近死亡的恐怖感,以及对失去青春的哀怨和对自己所做的不道德的悔恨。”小说写到隆冬将近之时,老人忍耐不住对生命即将消失所感到的恐怖,再一次拜访睡美人之家。他对女主人坦白地说:“像这么冷的晚上,能在少女的裸体旁死去是老人最快乐的死法。”当来拜访睡美人俱乐部的福良老人以及江口曾经拥抱过的黑皮肤姑娘猝死后,江口也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
(二)描写死之无常。川端康成深受佛教虚无思想的影响,“无常”的美学思想贯穿其创作的始终。在《川端康成的文学认识上的背景——关于“无常的美学”思想的周边》里有这样的议论:“死的存在始终威胁着活人以致使人感到人生无常,人总是孤独的。……生命追求美,而美又是虚幻的。虚幻又代表死,难道死就是美吗?当你号召及时行乐的时候,有个声音回答说:‘不要忘记死亡’,笼罩川端文学的地平线上、把一切归于虚无的一种对美的讽刺起源于他无常美学的思想。”[3]川端康成的《睡美人》让我们明白了生命的无常。在《睡美人》中如果说福良老人的猝死读者还能接受的话,那么,年轻的、强壮的、使江口慨叹“这就是生命”的黑皮肤姑娘的猝死,则给人生命虚幻和无常的哀感。《河边小镇的故事》也阐发了他的人生无常观。小说的女主人公房子的弟弟的死,深爱着房子的达吉的死,都是在一种偶然的状况下发生的。房子的弟弟平时体弱多病,只因身患流感,便离开人世。达吉舍身救助房子而受伤,假如他去看了医生,就可以避免破伤风的发生。其实,即使他不去看医生,也未必就一定要死亡,他的死纯属偶然,这不能不让人有人生无常之感。
(三)描写死亡的亦真亦幻、既悲且美。川端康成对死亡的过多的体验,使他觉得生是在死的包围中,死是生的延伸,“生来死去都是幻”。因此,它更加着力从幻觉、想象中追求“妖艳的美的生命”,“自己死了仿佛就是一种死灭的美”。川端康成十分欣赏自杀身死的日本画家古贺春江的一句口头禅:“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在他看来,生命从衰微到死亡,是一种“灭亡的美”,从这种“物”的死灭才更深地体会到“心”的深邃。《雪国》中叶子的死便是美的再现。小说中写道,在美丽银河的映衬下,在冲天的火苗中,“忽然出现一个女人的身体,接着便落了下来。她在空中是平躺着的,岛村顿时怔住了,但猝然之间,并没有感到危险和恐怖。简直像非现实世界里的幻影。僵直的身体从空中落下来,显得很柔软,但那姿势,像木偶一样没有挣扎,没有生命,无拘无束的,似乎超乎生死之外。……岛村压根儿没有想到死上去,只感到叶子的内在生命在变形,正处于一个转折。”[4]可见,作者把叶子看作是“非现实世界的幻影”,认为叶子的死亡并非彻底的死亡,而是内在生命的变形以及变形的过程。《抒情歌》描写了一个被人抛弃的女人,通过呼唤一个死去的男人来诉说自己的衷情。小说是由超现实主义架构而成的,而这种超现实主义是一种对超越虚无的肯定。或者说,它反映的是佛教轮回转生的思想。女人对死者的回忆似乎超越了阴阳两界,两人彼此呼应,产生了奇怪的“精神交流”和“心灵交感”,从而,使死亡变得亦真亦幻。正如作者所说:“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轮回转世的教诲交织出的童话故事般的梦境更丰富多彩了。这是人类的最美的爱的抒情诗。”[5]
二
川端康成如此热衷于写死亡的主题,是与他的生活经历、人生观、美学观以及他生活的时代分不开的。
(一)孤儿情结。川端康成从两岁到十六岁经历了五位直系血统的亲人的死别,因而过早地就开始了面对人生旅途中的“死亡”。在人们的眼里,他成了“参加葬礼的名人”。这种孤儿的身世,使他“害怕自己也会因结核而早死,时常流露出少年的伤感”,甚至他屡屡梦见祖父垂死在病床上的情景。他说:“我孑然一身,在世上无依无靠,过着寂寥的生活,有时也嗅到死亡的气息”[6]。生离死别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孤僻、伤感、自卑的性格,这一切对其人格的形成以及文学的资质都产生了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
(二)死亡的时代。川端康成不仅有一段悲哀和充满死亡的身世,他尤其处在一个悲哀和充满死亡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戮,令世人瞠目。他又目睹关东大地震和广岛、长崎原子弹灾害使几十万人丧生的惨状,悲哀的情绪笼罩着他。他说:“日本战败也略略加深了我的凄凉。我感到自己已经死去了,自己的骨头被日本故乡的愁雨浸湿,被日本故乡的落叶淹没,我感受到了古人悲凉的叹息”[7]。
(三)灭亡的美。从川端康成的生死观来看,不幸的经历,使他感到“对于死比生更加了解”,[1]“死后,虽说将那样石灰质的东西埋入先祖的遗址里,但人死一切皆空”,从而悟到“生即是死,死中有生”。其实川端康成对自杀一向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临终的眼》中他说:“一个人无论怎样厌世,自杀不是开悟的办法,不管德行多高,自杀的人想要达到圣境也是遥远的”[1]。尽管他一再表示反对“为死而死”的自杀方式,但却把死看作是一种“灭亡的美”,“所谓自然的美,是在我‘临终的眼’里映现出来的”。[1]这种对死的美学观,常常支配着他的创作,并成为他创作的主题之一。
(四)“无常”的美学思想。川端康成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他本人也说:“我是在强烈的佛教气氛下成长的,那古老的佛法的儿歌和我的心也是相同的”,“佛教的各种经文是无与伦比的可贵的抒情诗”。因此,他在审美意识上就非常重视佛教禅宗的“幽玄”的理念。他崇尚“无”,这里的“无”是最大的“有”,是生命的源泉。“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认为轮回转世,就是生死不灭,人死灵魂不灭,生即死,死即生,为了要否定死,就不能不肯定死;也就是把生和死总括起来感受。他认为生存与虚无都具有意义,他没有把死视作终点,而是把死视作起点。从审美角度来说,他以为死是最高的艺术,是美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艺术的极致就是死灭”[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