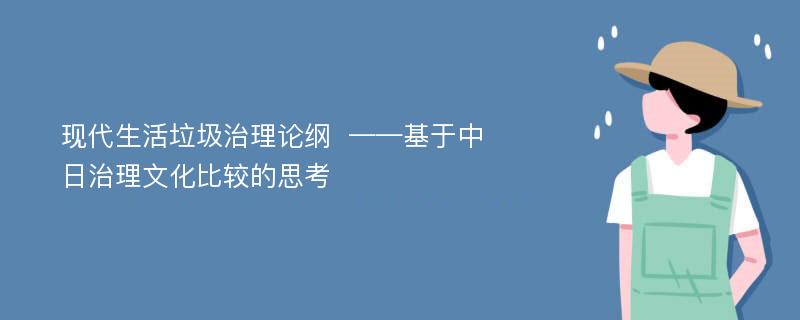
[摘 要]现代生活垃圾治理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时代难题。对人类来说,现代生活垃圾治理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或存在方式的生成和认同。从世界范围看,日本现代生活垃圾治理公认是成功的,值得中国学习。日本针对现代生活垃圾治理构建了一个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合力模式,在制度安排、技术创新与文化养成上实现了有机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对中国而言,目前积极推动有效的现代生活垃圾治理,需要从制度、技术和文化等三个向度及其关系入手,其中制度安排是保障,技术创新是支撑,文化养成是根本。现代生活垃圾治理已经发展成为全球问题,只有形成一个全球性现代生活垃圾治理文化,人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现代生活垃圾的控制、处置与治理。
[关键词]制度安排;技术创新;文化养成;现代生活垃圾;治理文化
一
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的生活,有人的生活就会产生生活垃圾。对人类来说,现代生活垃圾治理不仅是生活垃圾的处置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还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更是人类存在方式的重构和飞跃。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生活垃圾治理实质上是一种新文化的生成和认同。
(6)日常管理。每天坚持早、晚各巡塘一次,早上观察有无鱼类浮头现象。如浮头过久,应适时加注新水或开动增氧机。下午检查鱼类吃食情况,以确定次日投饲量。另外,酷热季节,天气突变时,应加强夜间巡塘,防止意外。
二
在人没有认识到生活垃圾的危害和生活垃圾还不足以引起人们注意的时候,生活垃圾就存在着,这时人与生活垃圾的关系处在一种自然的疏离状态,人既没有感觉到生活垃圾的用处或积极的成分,也容易忽视生活垃圾的危害及其消极的影响。而当人们明确认识到生活垃圾具有危害性,是一种公害,会对人的生存、生活和生产造成影响甚至是严重影响时,对生活垃圾的处置和治理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生活垃圾的存在也曾经因引发霍乱、鼠疫等危害人类生存的灾难事件而偶然引起人们的关注,此类事件在古希腊、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文本中都有记载。但当人类开始持续关注并思考如何处置和利用生活垃圾的时候,人类已经跨入现代社会。以16世纪为分界线,人类从传统社会、农业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工业社会,这不仅标志着以机器大生产为物化对象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发展,而且标志着人与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影响,具有现代征候的现代生活垃圾出现了并逐渐引起人类从个体到群体、从民间到政府、从区域到全球的重视,生活垃圾与人的关系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人类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人在生活中制造了生活垃圾,生活垃圾又对人的生活发生了诸多影响,如果不充分认识和科学化解这种影响,生活垃圾将会毁掉人的世界。而当人要努力去处置现代生活垃圾,解答这一社会问题时,首先就要回答什么是生活垃圾,现代生活垃圾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如何处置和利用生活垃圾,有哪些处置和利用的手段和方法,现代生活垃圾的治理与制度、技术、文化等的关系是什么,现代生活垃圾治理的归宿在哪里,也就是要从根本上厘清现代生活垃圾“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三
垃圾是什么?这是一个对人类来说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也是认识现代生活垃圾治理的一个本源问题。具有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本给“垃圾”下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垃圾就是“脏土或扔掉的破烂东西”(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43.。显然,这个释义是垃圾的基本词义。它表明了垃圾本质上的三个特征:第一是脏;第二是破烂;第三是要被人扔掉的。当然,脏不脏,破烂不破烂,要不要扔掉不仅是一种客观表象和行为,更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和选择,这意味着“垃圾”之所以为垃圾,其本身既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当某物被某人当垃圾扔掉时,其作为物的有用性对某人来说就已经终结了,就是被某人放弃了、扔掉了,在这个意义上,凡物都会变成垃圾,这是垃圾的绝对性。但对某人来说,某物成了垃圾,对他人来说未必就是垃圾,未必就没有用处,未必就会被扔掉。更何况判定脏不脏和破不破,往往因人而异,至于要不要扔掉更是会受主观选择甚至情感、爱好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垃圾是不是垃圾又具有相对性。垃圾具有绝对性表明,垃圾的存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处置和治理垃圾就要研究、寻找和尊重垃圾产生的规律和治理垃圾的规律,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能主观上随心所欲,轻视垃圾治理,以为喊喊口号垃圾及其危害就可以自动消失,要谨防现代生活垃圾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垃圾具有相对性表明,垃圾的治理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只有认真对待甚至是尊重垃圾,才能找到治理垃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垃圾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仅把垃圾当作垃圾,而不是把垃圾当成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存在物。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生活垃圾的构成日趋复杂且所含有害有毒物质日趋多样,已经不是脏和破烂所能直观概括的,现实中我们真能说清楚生活垃圾是什么吗?相关业务管理部门和单位进行生活垃圾治理时,在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置中出现的混乱情况以及居民丢垃圾时的茫然不知所措也许不是偶发的现象,需要我们从基本的认识论上入手去解决。重视宣传是必要的,但宣传是手段,宣传什么要明晰;进行治理也是必要的,但治理是目标,治理什么要精准,如此才能事半功倍。
四
现代生活垃圾的产生具有历史性,这种历史性不仅表现在它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亦步亦趋紧密相联,还表现在从生活垃圾到现代生活垃圾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无论是垃圾形态还是垃圾构成,现代生活垃圾都有着不同于传统社会生活垃圾的特点。一个基本的演化逻辑:首先,现代社会的出现引发了城市化的浪潮,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另一重要特征是工业化。现代工业和现代城市的出现与发展构成现代化图景上最具本质性的色彩,而描绘这一色彩的是具有现代性的人。无论是现代工业的发展需要还是现代城市构建的需要,都使得大量人口聚集到城市中,在城市里生存、生活、生产。城市化发展的总趋势是城市越来越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其次,随着人口的增多,生活垃圾的产生也呈上升势头。现代生活垃圾不但数量越来越多,而且种类越来越多、构成越来越复杂,且含有一定比例的有毒有害成分,对人类的影响和危害越来越大。所以,城市人口的数量与生活垃圾的数量以及生活垃圾产生危害的大小有一种正向关系,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生活垃圾治理的诉求也有一种正向关系。面对现代生活垃圾数量上的激增和危害上的不断扩大,治理生活垃圾已经是人类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刻不容缓的现实性任务。从生活垃圾产生的源头来说,如果不能减少城市人口的数量,人就只能想办法减少自己制造生活垃圾的数量。如果不能减少自己制造生活垃圾的数量,又不能控制人口增加的数量,人就只能想办法利用生活垃圾。这就构成当下两条治理现代生活垃圾的路径:一是控制现代生活垃圾产生的量,人要绝对减少制造垃圾;一是析出现代生活垃圾构成成分的质,人要充分利用垃圾,使垃圾成为暂时放进垃圾箱的资源。前者需要生活方式和意识观念上的革命,后者需要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治理生活垃圾不仅具有减少对人类危害的意义,还具有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不断满足和保障民生需要的功能和文化意义。
五
此前我们一直担忧处于高位的美股和大宗商品。对比今年A股和美股道指,2018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从最开始的同涨同跌,到二三季度的分道扬镳,再到四季度二者逐步脱钩,美股目前的风险已远远超过A股。而以原油为主的大宗商品2018年侍了回过山车后,在四季度破位暴跌,原油是全球经济的先行指标,其破位可能预示经济将迎来一轮向下周期。
六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互相影响。农业文明时期,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工业文明时期,中国颇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如果我们把中日两国推进现代生活垃圾治理的过程进行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两国在治理文化上既有同中之异,也有异中之同。第一,从治理所发生的文化背景上看,中日两国都是在现代文化建构时遭遇现代生活垃圾的,都是在现代工业化和现代城市化这样一个文化时空中面临治理现代生活垃圾的现实问题。不同之处是,日本进入现代化发达国家的时间节点比中国要早一百多年,现代生活垃圾的产生和灾害性影响的发生以及对现代生活垃圾治理的认识和行动也早。最近这几年中国现代生活垃圾治理时所常见的“垃圾无处填埋”“垃圾围城”“邻避效应”等都曾经是令日本社会和生活垃圾处置过程中头疼的事。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日本经济与社会发展在高速增长中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包括熊本县水俣病诉讼等在内的四大公害案,让日本举国对现代生活垃圾的认识及治理的诉求有了质的改变。对中国来说,日本的现代生活垃圾治理就是一面镜子或一个参照物。第二,从治理过程的方式方法的演变来看,中日两国在治理生活垃圾时所采用的主要都是填埋法和焚烧法。不同的是,中国早期使用填埋法比较多,并且在填埋的过程中因生活垃圾多为厨房垃圾含水分和有机物较多而采用堆肥法的综合利用;而日本由于国土面积小,填埋有占用耕地和污染土地、水源等弊端,大多采用焚烧法。早期的焚烧多为野外焚烧,由于在焚烧过程中产生较多的有害有毒气体,污染空气、伤害人身,从而转向使用专门的焚烧炉,焚烧炉技术大致经历了批次炉、机械化批次炉、准连续炉和全连续炉等四个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日本开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这意味着日本生活垃圾的治理从简单焚烧开始走向循环综合利用。2000年,日本制订实施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正是在推动生活垃圾循环利用的过程中,日本认识到现代生活垃圾治理必须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置,这引发了现代生活垃圾治理的革命性变革,亦即观念上的变革和技术上的创新使生活垃圾治理走向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良性有机状态。第三,从治理主体的构成和作用来看,中日两国都比较重视政府和公众的力量,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有着多元治理主体的存在。所不同的是,日本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扮演引导的角色,治理上通过市场激励并多依靠NPO和NGO来组织实施,公众参与多为区域自治。一个明显的特色是:日本在生活垃圾治理制度设计时,充分利用自身文化的约束力,亦即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羞耻感”:在日本人看来,“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志,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到偶然性的失误,都是耻辱”(2)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55.。日本对企业生产产品、商店销售商品甚至租房的合约都有明文规定的生活垃圾治理要求,这既是一种引导宣传手段,更是一种强制下的自律遵从。而中国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履行主导的责任,治理上多通过基层组织来实施,层层分解落实到位,公众参与多为志愿活动。第四,从治理对象的分类来看,中日两国都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所不同的是,日本的分类比中国的更细,不同地区和城市生活垃圾的种类往往划分为十几种甚至几十种,远远多于中国现在常见的四种分类法或六种分类法。总的来说,在现代生活垃圾治理中,日本把制度安排、技术创新与文化养成统一在一个机制里,形成一个有效的治理模式,值得我们学习。
2018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时提出一个具有纲领性的命题:“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垃圾综合处理需要全民参与,上海要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办好。”这个命题包含五层含义:一是新时代中国推进生活垃圾治理的主要抓手是垃圾分类工作,分类越具体,治理的针对性越强,效果就会越好,效率就会越高。当然,这个分类工作不仅仅是居民扔垃圾要分类投送,而是在垃圾投送-收集-运输-处置-利用的全过程都要分类;二是垃圾治理是新时尚,这揭示了生活垃圾治理的文化意义,学会垃圾分类就是学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生活垃圾治理就是一次革命;三是垃圾治理是一个系统综合工程,有一个治理发展的过程;四是垃圾治理需要全民参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生活垃圾治理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只有唤醒人民的参与意识,使人民群众真心投入到生活垃圾治理中,各项政策才能落实到位,治理效果才能显现出来;五是生活垃圾治理工作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既要抓紧又要抓实,不能弄虚作假、应付场面。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新时代中国做好现代生活垃圾治理具有指导性意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积极推动中国开展有效的现代生活垃圾治理,需要从制度、技术和文化等三个向度及其关系入手,构建一个治理现代生活垃圾的合力机制,其中制度安排是保障、技术创新是支撑、文化养成是根本。
七
通过建立符合企业实际要求的职能部门,对企业资金管理、财会纪要、货物流动等进行有效监督,严格落实责任人,加强监督,提升财务人员工作态度、积极性及责任感。
八
现代生活垃圾治理还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撑。这里的“技术”既是指生产工具类的硬实力,也包括管理方法和宣传手段等软实力。随着现代生活垃圾在量和质的演变,处理和利用生活垃圾就成了一个由技术水平决定的问题。技术水平高,处理和利用的效率和效果就好;技术水平低,处理和利用的效率和效果就差。正因为如此,现代生活垃圾治理中技术的不断创新格外重要,例如焚烧炉的更新换代,不仅可以提高焚烧量,还可以减少有害气体的产生,同时还可以产生更多的用来发电的热能,从而降低焚烧垃圾的成本。另一方面,管理水平和宣传手段的高低也是现代生活垃圾治理中的“技术活”。例如生活垃圾分类中源头减量控制非常关键,但如何调动制造生活垃圾的主体积极参与源头减量就是一个需要精心设计、广泛宣传和组织实施的技术活。积分卡奖励政策、在企业产品上标明垃圾属性、垃圾中的有用物质企业回购、把垃圾清洗晾干等都可以在源头上控制垃圾量。
对中国而言,现代化的起步较之西方先发国家大约滞后近五百年,及至我们开始思考现代生活垃圾处置和利用问题时,历史已经走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在改革开放推动下现代经济与现代社会的真正展开。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现代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也使中国的城市化步入了前所未有的扩张阶段。2018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有近90个城市人口超过100万,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已经是超过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58%。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扩大以及城市人口的剧增,生活垃圾的增长速度也是惊人的。以上海为例,1958年上海的生活垃圾仅为74.12万吨,1978年为108.13万吨,到了2018年已经达到900万吨左右,2018年上海的生活垃圾总量是1958年的12倍多,增长率约为1114%。2004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废弃物产生量最多的国家。悄然间,现代生活垃圾治理这个“小问题”成为政府和人民群众关心的大议题。2017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在全国46个重点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拉开了中国现代生活垃圾治理的帷幕。2019年夏天,积极推进“垃圾分类”治理的上海,坊间和社区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如何“倒垃圾”。实际上,早在二十多年前的1996年,上海市就开始试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当时把生活垃圾分为了有机垃圾、无机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三类,2019年则分成了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这里有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现代生活垃圾的治理不是小事,更不是简单的事情,不是发几个文件搞一个运动就可以“敲锣打鼓”胜利完成的,对城市的发展和民生的诉求来说,现代生活垃圾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某种层面上考验着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和政府现代治理能力,民众也有一个逐渐认识和习惯养成的过程。二是经过多年的治理试点,一个有效的治理模式尚未形成,原因何在?可以说,我国现代生活垃圾的治理仍然处在初级阶段,治理水平提升的空间极大,在现代生活垃圾治理的思想认识、方式方法、制度设计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需要向先进国家学习。日本既是我们的近邻,也是世界上公认的现代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最成功的国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有两种约束主体行为张力的形式:一是惯例,二是法律。无论是惯例还是法律其目的都是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失序,也就是说通过制度安排来保障人类主体有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减少因无序而产生的对人类的危害。在这个意义上,当人类意识到生活垃圾的存在影响了自身的生产、生活和生存时,就需要通过制度安排来化解影响。这种制度安排需要着力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法律法规既要有针对性,又要有可操作性;既要对个体义务作规定,更要对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管理主体和生产主体的义务作规定;既要有惩罚性的规定,也要有奖励性的政策;既要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前端作规定,也要对终端作规定等。二是要形成生活垃圾治理的惯例,也就是要在社会中——包括社区、学校、团体、组织、街道、邻里、家庭等——营造一种自觉自动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文化影响力和约束力,形成不参与治理可耻,参与治理光荣的氛围。诺斯认为,制度是人类的一种创造。这就意味着人类完全可能通过设计安排一种合理的制度来改进自己生存的状态,从而实现生存世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在现代生活垃圾治理中,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是保障。
对于个人叙事不能把它只看作是关于那一个人自己生活琐事的讲述,还要看到,由于在个人叙事中包含着人群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人情世故,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人间知识、技艺等,它是研究生活文化整体性存在的基本切入点。我多年前就指出村落是民俗文化的基本传承空间。[注]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但是进入村落后,研究者如果只是按照自己的提纲来进行调查,那么对民俗事象的了解就可能是零碎的、分散的、不完整的,但将民俗事象与活生生的当地人联系在一起时,就不难发现,每个村民都拥有一个民俗的整体,或说是整体的民俗。
文化养成是根本。无论是制度安排还是技术创新,要想切实发挥作用,就必须使制度和技术转化为文化。从本质上说,现代生活垃圾治理是以服务为逻辑前提,而通过制度和技术表现出来的管理常常是以惩罚为逻辑前提,例如有的地方利用征信系统来控制居民是否把垃圾分类投入垃圾桶;在垃圾桶附近安装摄像头等监控系统;对违规者进行罚款;等等。这种方式基本属于强制式的、非文化式的,但是效果是否好,特别是长效机制是否好?是否让人真正认识到垃圾分类的好处从而积极主动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我们认为,只有当人民群众把现代生活垃圾治理作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来接受时,才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对待生活垃圾的态度,才能遵守制度安排并把技术创新所具有的效用发挥出来。现代生活垃圾有着明显的外部性且对很多人有影响,是一个公共问题,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合力模式,需要我们把制度安排、技术创新和文化养成构成一个有机的治理机制。
九
现代生活垃圾治理已经发展成一个全球问题,需要所有国家共同面对。过去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生活垃圾时,常常利用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状态和亟需发展的技术诉求,把垃圾输出到发展中国家来处理,制造“洋垃圾”,给发展中国家造成极大的污染和伤害。随着全球化逐渐成为世界的基本趋向,时空的压缩或人类活动空间的延伸使得地球成了“地球村”,那种把垃圾从村东头扔到村西头的做法无疑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我们必须要学会全球性思考,从我们自身做到“第一是开始想到全球;第二是学会负责地生活”(3)欧文·拉兹洛.布达佩斯俱乐部全球问题最新报告——第三个1000年[M]. 王宏昌,王裕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60.。对现代生活垃圾治理来说,想到全球和负责地生活,就是要求我们形成一个全球性现代生活垃圾治理文化,如此人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现代生活垃圾的控制、处置与治理,才能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处在一个美好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时空中。
Outline of Modern Household Waste Management:A Reflection of Waste Management Culture in Japan and China
LI Wenqian,SHAN Juan
[Abstract] Management of modern household waste has become a worldwide problem that cannot be ignored.For human beings, the household waste management is substantially the gene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a new culture form or mode of existence.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waste management in Japan is recognized as successful and worth learning. By constructing a combined force involving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management mode in Japan has achieved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ulture formation with very good effect. In China, in order to actively promot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modern household waste, we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ystem,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among which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s the guarante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support, and culture formation is the key. 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culture is fundamental to solve this global issue, and facilitate the control, disposal and management of modern household waste.
[Keywords]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ulture formation; modern household waste; management culture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日语学习者反馈语习得研究”(项目编号:13YYD018)
[中图分类号]A811.6;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9)06-0098-8
DOI:10.3969/j.issn.1009-105x.2019.06.010
引用格式:李雯倩,单娟.现代生活垃圾治理论纲——基于中日治理文化比较的思考[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98-105.
Citation Format:LI Wenqian, SHAN Juan.Outline of Modern Household Waste Management: A Reflection of Waste Management Culture in Japan and China[J].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2019(6):98-105.
(作者单位:李雯倩,徐州医科大学;单 娟,常州交通技师学院)
(责任编辑:付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