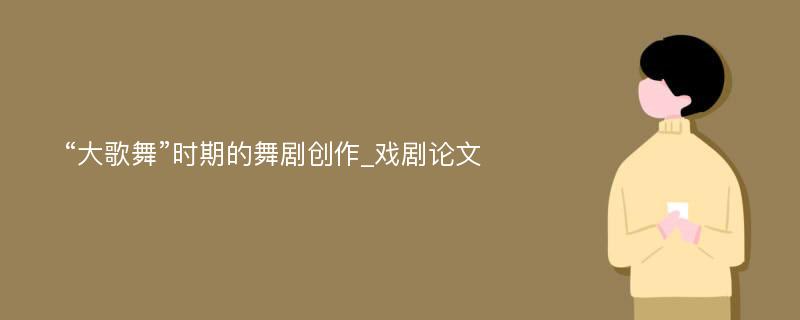
“大歌舞”时代的舞剧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舞剧论文,歌舞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对过去十几年的文艺舞台做一个概括,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大歌舞”的时代。十几年里,大型的歌舞晚会举目皆是,不论逢五逢十、过年过节,还是各种各样的开幕式和闭幕式;甚至连电视文艺这种走进家庭的传媒形式,也是在不断推出各种大型晚会的过程中,在无数“大歌舞”的辉煌场面中,走过这十几年。
“大歌舞”的创作,培养了一批属于当代风格习性的舞蹈编导。今天,几乎所有有成就的编导,多少都参与过这种“大歌舞”的制作过程。甚至有些著名的编导,作为大型晚会导演的声望,已经远远超过所创作的舞蹈作品。这也是“大歌舞”时代的一个特殊现象。
于是,当这些编导又一次汇聚在舞剧创作的舞台上,一种来自于大的时代环境的影响,自然就留在了他们的创作手段和舞剧形象中。
“场面”上的文章
去年的全国舞剧汇演,一路看过去尽是大规模、豪华型的舞台场面。在不一样的舞剧中,情形之相似、思路之雷同,常有惊人的一致。看得出来,只要有可能,大多数编导都不愿意放弃制造这种舞台大场面的机会。但是坐看舞剧的人,却总会被一种错觉打断,好像是在观看一场“大歌舞”的晚会。
编导如此得心应手于这种大场面、又热衷于这种大场面,既是沿袭了过去舞剧创作的一贯传统,也是在延用今天“大歌舞”晚会的某种创作方式。传统的舞剧,一向更重视舞段而不是复杂的戏剧情节和人物关系。舞蹈家常以舞蹈的特殊性解释其中的原因。只是当时条件所致,舞台上经常呈现出来的,是大片游离于人物情节的舞蹈段落,编导的功夫也主要集中在动作编排上。现在不同了,虽然那些与剧情关系不大的舞段依然如故,但是当代舞蹈编导的视野和想像力已经大为拓展,远非三四十年前老一辈所能相比;而“大歌舞”时代的舞台风尚,又让舞剧中的大场面,在舞台的空间和技术条件两方面有了更大的施展余地。看汇演中的舞剧若干部,台上的灯光烟雾经常是铺天盖地滚滚而来,让人眼花缭乱;各种推拉升降的手段也是堆砌陈列,甚至还要床上架屋、台上搭台。这样的舞台气魄之大,确实让耳目震撼,但人在其中之渺小,却往往是不堪一睹。服装化装也不示弱,大群演员动则铺满台面,服饰装束极尽艳丽奢华,犹如群起而斗富;或者奇异夸张,近似于舞蹈包装起来的某种时装发布会。如果再与前面所说各种舞台手段加起来,场面自然是热闹非常。但是这种场面于舞剧人物形象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又让人觉得似是而非。如此,缺少了经典舞剧所必要的严谨的艺术风格,倒更像一场综艺大晚会的娱乐场景。
以舞蹈编导的身份,下大功夫在这些场面上,创作所要思考的是什么?说白了,真是功夫在诗外,就是那些烂熟于心的大型晚会,在策划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点子”和“招数”;是那些大晚会为求瞬间的精彩,故意营造出来的豪华排场和手段。现在,这些造价昂贵的“手段”,正在让大晚会的舞台变得更大、更奢华;同时,也让晚会上的歌曲和舞蹈变得更加支离破碎、更加没有价值。假如在舞剧创作中,编导也如此热衷于这种“场面”上的文章,却找不到它与人物形象和戏剧情节的必然关系,甚至找不到与舞蹈动作构思的有机联系,舞剧的舞台,也会变得一样的浮华而空洞。
如果说“大歌舞”时代确实造就了一批舞蹈编导,而这些编导比起他们的前辈,在舞台手段上也更加左右逢源;那么轻视舞剧的人物性和戏剧性,或者在这方面依然创造乏术,让他们还是难以突破传统舞剧创作的历史局限性。同时,过分依靠视觉场面的效果,甚至离开舞蹈的动作形象,热衷于舞台场景、机关道具的设计,不仅会使舞剧在人物内容上,而且在舞蹈形式上也完全丧失经典意义。这正是“大歌舞”时代急功近利的舞台艺术经常会犯的通病。
其实,那些虚张声势的“大场面”和舞台上的机关“点子”,表面热闹而实际肤浅。大部分也只有一次性的欣赏效果,并不比变戏法的“绝招”更有审美价值。就是在“大歌舞”的台面上,这一点也已经被屡次证明过,对于舞蹈编导来说,在“眼花缭乱”的视野中,还来不及认识流行艺术与经典艺术的基本界限,以及二者之间必要的分工,是影响创作的更深层原因。
“戏剧性”与“经典舞段”
世界舞台上的经典舞剧,尤其是当代舞剧编导创作的经典作品,从来不乏宏大的场面和经典的舞蹈段落。但作为成功创造舞剧人物形象的手段,它们是戏剧逻辑发展的结果,不是单摆浮搁的台上展览。这是当代舞剧编导,在创作方法上与古典主义程式化的重要区别,也是当代舞剧的风格特质之一。可以说,今天的编导凭这一点,表现出了他们对舞剧发展历史的当代贡献。同样,凭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判断舞蹈编导到底是在创作一部舞剧,还是更合适去编排一场有故事情节串联的舞蹈晚会。
在过去的舞剧创作中,戏剧性一向就是个让人烦恼的话题。甚至在一些传统观点看来,总是强调舞剧的戏剧性,干脆就是不懂舞蹈的外行。而另一方面,几十年来上演的舞剧无数,尤其近二十年,自我称之为舞剧的大小作品至少也在百部以上;然数量虽蔚为大观,但是真正有名有姓、能让人想起来的舞剧人物,其实没有几个。就算这几个说得出来的形象,真是依靠人物性、戏剧性的成功表现让人印象深刻的,更少之又少。人们所以还记得,完全可能是因为其中一段纯粹的舞蹈。可见,没有戏剧性支持的所谓舞剧人物,和通常的舞蹈作品中的形象也差不多。但几十年来舞剧创作的传统,就是这样给我们以经验的。如此,舞蹈编导根本不必研究所谓戏剧性的问题,只要能创作一般形式的舞蹈作品,就可以照此方法,积累编排起更多的舞蹈场面,再加一个牵强附会的故事情节作串联,就算是在创作舞剧;而所谓的舞剧,也就轻而易举在我们手里变成了一场“有情节”的舞蹈晚会。
我们不用过多地旁征博引,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当代世界舞台上,看到那些在戏剧性的人物表现上,取得巨大成功的经典舞剧作品。这些舞剧,无论是人物内容所具有的人文历史价值,还是熟练运用自己艺术手段的经典性质,都可与同一题材的其他戏剧形式相媲美。其中经典的舞蹈段落,既是因为出神入化的动作技法让人赞赏,也因为细腻而独到的人物心理表现,让人为之感动。如此,那些称之为“技法”的肢体动作,才成为表达特殊含义的艺术语言;而舞剧的魅力,才会在与其他戏剧形式和戏剧人物的比较中,更显出独特的魅力。这显然是在戏剧范畴中对舞蹈地位的加强,而不是削弱。但前提在于舞蹈编导在戏剧性问题上,有足够的认识水平和实际解决问题的创作能力。这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过程,需要一种务实的积累。若单靠几个舞台“大动作”,就自信能成大型舞剧,甚至妄言能与世界接轨,是编导在自说自话。
在总结去年的舞剧汇演时,舆论似乎对现在舞剧创作在戏剧性方面的成绩赞赏有加。甚至在一番充分的自我肯定之后,又有人踌躇满志地说:“当然了,我们是舞蹈家,不可能搞了一辈子舞蹈,最后变成一个戏剧家。”这种轻松说法,让人听了更加不能乐观。想来在戏剧舞台上,多少人终其一生的努力,最后也未必能成为戏剧家;舞蹈编导绝不会因为偶然搞了一两部舞剧,就一不留神成了戏剧家。颐指气使、不求甚解的思维方式,也许是这个时代流行于各种艺术行当的普遍心态,但是对于半身已经埋在了“大歌舞”中的舞剧编导,这样的自信和从容,真的让人怀疑其是否明白自己所处的实际状况。看看我们周围同一时代的社会人文思潮和戏剧影视作品;再看看舞剧的舞台上,居然有那么多远离人世现实、根本无从感受其真实的所谓传说、神话,甚至明显就是人为编造出来的、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若就以这样的见识和作为,去证明戏剧性在舞剧中的价值,倒正好说明我们实在是有太长的路要走了。
戏剧性,本来就是一切戏剧范畴内的演艺形式,普遍具有的性质,舞剧并不例外。能不能成戏剧家,与形式手段无关,只是能力问题。
退一步而言,没有戏剧性作为依托的舞蹈段落,在今天的舞剧中也已经很难成为经典了。比如双人舞,当所有的爱情都变成一种差不多的情绪色彩,在不同的舞剧中,已经没有了戏剧人物特性的区别时,所有的双人舞在我们的眼前就变得如此雷同,都在拼命地搬弄技巧,让我们根本就记不住哪一段更精彩。
走出古典主义历史阶段的舞剧创作,在方法上,并不依靠纯粹程式化的舞蹈段落取得观众的青睐,而是要靠经典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戏剧结构设置与准确的动作语言风格,共同创造出属于当代的舞剧艺术形象。对于我们来说,在戏剧性上具有重大突破,乃至于有更加卓越的表现,仍然是这个时代舞剧创作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舞蹈诗”
根据以往的经验,想从理论上澄清一种舞蹈的名词概念,往往是十分困难的,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诸如“什么是舞蹈”、“什么是中国舞”、“什么是中国古典舞”、“什么是民族舞剧”之类的讨论,结果莫不是自生自灭、不了了之。而舞台上的万千气象,从来不会因此受影响,新的名词还会不断地应运而生。所以,我们也不必非要讨论什么才是“舞蹈诗”,以免还没找到所以然,它就已成昨日黄花,又被别的说辞取代了。
但是,为什么会有“舞蹈诗”的说法,并且为什么会在舞剧创作的前提背景中,在今天被提出来,却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在“舞蹈诗”出现之前,各种类似的说法就已经流行一段时间了。回忆起来,人们一定还记得像“情绪舞剧”、“情景舞剧”、“心理结构舞剧”、“交响舞剧”、“舞蹈诗剧”等等的概念名词;如果再加上“意识流”、“蒙太奇”、“多空间”、“异质同构”之类借鉴来的词汇,可以看到,舞蹈编导在解释舞剧的时候,竟然有过如此之多的说法。
我们都一致同意,舞蹈是一种非概念性的视觉艺术形式。为什么解释舞剧的创作,却需要这么多深奥的、甚至艰涩的名词概念?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这些看上去不一样的说法,其实都在竭力地绕过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完整的、连贯的、言之有物的戏剧情节。不想面对这个问题,而宁愿相信自己是因为与众不同的更高追求才故意放弃了戏剧性,舞剧的编导需要某种说法做根据。但无论如何,这些概念还是在舞剧的范畴里,还是不能摆脱戏剧性的“纠缠”。如果被问到舞剧之“剧”,在这里究竟还是不是指戏剧的时候,这些解释立刻会变得更加艰涩混乱、甚至自相矛盾。
这真是一个痛苦的挣扎过程,在舞蹈与戏剧性之间的艰难选择。是开始想要搞一部舞剧,最后却没有把握还能不能完成一个连贯的戏剧情节的舞蹈编导都可能有过的烦恼。
既然如此,又何必非要搞一部舞剧呢?也许编导所需要的,只是一种结构上的规模,是一个“大型”的作品而已。而今天,在一个“大歌舞”的时代里,追求“大型”已经是一种流行的时尚,甚至是一个“大编导”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其他的舞台艺术如此,舞蹈又何以能例外呢?看来,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概念,来满足这种时代的要求了。
也许就这样去解释“舞蹈诗”的来历,缺少了些艺术的庄严与神圣感。但即使是一种大的社会潮流,最初也可能产生于某些极其普遍的、实际的心理需要。我们当然没理由去否认“舞蹈诗”会有这样那样的美好前景,但是我们也不必现在就故意把它摆上“殿堂”,追根寻源为它创造理论根据,或者言过其实地把它理想化,宣布一个“舞蹈诗”的时代开始了。也许这样做的结果,会让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已经“超越戏剧”,又登上了一个更高境界;或者又发现创造出一种新的舞蹈形式。多年来,这种自我宣布成之为体系、流派、舞种、学科一类的制造活动,在舞蹈界也不是第一次了。
其实,一种成熟的、有高度创造力的艺术形式,原本不需要有这么多的说辞来解释自己。就像一个稳定而有效的市场环境,并不需要大呼小叫、每天变换商品的称呼一样。“大歌舞”时代的浮躁心理,不光表现在艺术手段中,也会表现在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上。与世界舞台上不断推出经典艺术作品相比,我们好像总是在不断地欢呼和呐喊声中:为一个“时代”的开始,为一个“里程碑”的出现,为一种体系的诞生,或者“一群人”的崛起。诸如此类的情形,是否就是一种繁荣的真实呢?
如果我们总是在迎来“某个时代的开始”,是不是我们始终还没有来得及站稳自己的脚跟;
如果我们总要面对某个“新舞种”,去为之欢呼,是不是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一种成熟有效的艺术方法,让自己不断地走向经典?
与这种喧闹相比,“大歌舞”时代的舞剧创作,需要安静而务实的态度,解决那些长久以来并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如此说来,除了那些华丽的包装、惊世骇俗的舞台“大举措”,以及精心设计的舆论攻势之外,“大歌舞”时代的舞蹈编导,是否真的做好了创作一部舞剧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