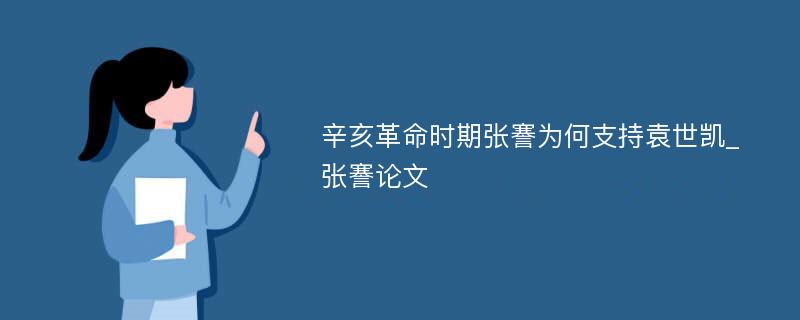
辛亥革命期间张謇为何支持袁世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张謇论文,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謇(1853——1926)是近代中国爱国的资产阶级事业家和社会改革家,袁世凯(1859——1916)则是窃夺辛亥革命果实、建立独裁卖国的北洋军阀统治的历史罪人,根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但是,在1881年到1915年的35年间,他们却有过几度带有传奇色彩的交往,尤其是辛亥革命期间,曾成为政治密友。辛亥革命期间,张謇为何支持袁世凯?他对孙中山和临时政府是持什么态度?后来又为什么要跟袁世凯分道扬镳?搞清这些问题,将在助于深化张謇研究和对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的进一步了解。
一
首先要从“复交信”和“洹上会晤”谈起。张謇与袁世凯的最初交往,是1881年于淮军将领吴长庆军幕中,有过师生兼同事的关系。1884年,因袁世凯乘吴长庆失势、病危,私自巴结李鸿章,张謇写信加以痛斥,导致中断关系达20年之久。1904年6月,张謇“以请立宪故,南皮(指张之洞——引者)再三属先商北洋(指袁世凯——引者),汤寿潜亦以为说。余自金州归后,与袁世凯不通问者二十年,至是始一与书。”[①]20年前写过断交信,现在又主动要求复交,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因袁世凯已今非昔比,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营务处管带副营,而是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政坛要员,张謇当时为运动立宪而奔走呼号,必须争取得到袁世凯的支持。虽然,1904年的复交信因“袁答尚须缓以俟时”而未直接达到目的,但20年的僵局终于打破了,恢复了书信联系,就为后来的“洹上会晤”创造了条件。
1911年6月,张謇为请立宪事由沪粤津汉四商会公推入京,对清政府“进最后之忠告”。途经河南漳德时,特地拜访袁世凯于洹上村,这是两人自1884年分手后的第一次会晤。两人交谈从午后5时至夜12时,据张謇《年谱》所载,称袁世凯“议论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论治淮,曰不自治人将以是为我罪;又曰此等事国家应做,不论有利无利,人民能安业,则国家之利。”[②]无疑给张謇留下了良好印象。离京后,张謇又到天津参观了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所建设的马路工、罪犯游民工厂、图书馆等社会设施,得出“袁为总督时,气象自不凡,张南皮(指张之洞——引者)外,无抗颜行者”[③]和“举世督抚,谁能及之”[④]的结论。洹上会晤和天津参观所获得的好感,多少改变了张謇原来对袁世凯的看法,也就为辛亥革命时的支持袁世凯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张謇与袁世凯的热交期,发生在辛亥革命期间。表现之一,函电交往频繁。在1911年11月到1913年9月的不到两年时间,仅见于《张謇存稿》的就有25次。其中,以1911年11月到1912年4月的半年内,张謇给袁世凯的函电就有12次,这还不包括托专人面交的密信和密陈,这段时间又正是政局最动荡、南北方斗争最激的时期。1912年9月9日到10月8日张謇在京的一个月间,见于《张謇日记》的“诣洹上(指袁世凯——引者)”就有6次。表现之二,从函电的内容看,主要是向袁世凯通报政治信息并为之出谋划策。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有:一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致通过”,让袁世凯及时掌握南方各派的政治动态,并鼓励道:“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⑤]二是1912年2月袁世凯被推为总统后,张謇针对中央政府留在北京还是南迁问题,南方革命派要求袁世凯南下的呼声甚高,而袁又不愿南下受制于革命党,为袁策划道:“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著手,一从北数省人民著手。飞箝捭阖,在少川心知其意而妙用之。若不著一毫痕迹,使不欲南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⑥]三是为袁世凯政府的人事作了周密安排,“一陆军宜段(指段祺瑞——引者)正而黄(指黄兴——引者)副。一财政必熊(指熊希龄——引者),熊有远略,有成绩。一实业周缉之亦可。一保皇党人若梁启超亦可择用”,并说“南方现已疏通。”[⑦]至于张謇当时所以没有答允出任总理组阁,他解释道:“惟审察时局,尚未至可以效力之期。自忖目前但可以一二事稍分公虑,幸勿处以国务地位,庶几彼此皆有余裕。”[⑧]张謇还进一步说明:“以生平所知拾遗补阙,自问尚有一日之长,若一处行政地位,侪于国务,则言论转难发挥,而与社会亦易隔阂。”[⑨]也就是说,以“在野”的身份,言行自由,更能发挥其联系社会各界的作用。当然,张謇也不能不考虑到当时正为汉冶萍事件的争执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职务而离开了孙中山,“今若忽焉而北,则浅见者必以为有轻重向背于其间,而无识者且可造为种种荒诞离奇之语。”[⑩]四是劝告袁世凯应注意斗争策略,如“凡公旧日信用之人,除军队外,愿公勿尽置左右,而拟以可遥为声援之地”[11];“政党以‘统一’较胜。少川已入,足以代公……公可勿入一切政党,以免障碍。党需要有基本金,謇拟合实业助之。”[12]
三
辛亥革命期间,张謇支持袁世凯是无庸置疑的,那么,他对孙中山是持什么态度呢?支持袁世凯是否就意味着反对孙中山?且让用张謇的有关材料来加以对比说明。张謇对袁世凯的基本看法,在1884年的断交信中已有了充分反映,1898年又在日记中写道:“闻袁世凯护北洋,是儿反侧能作贼,将祸天下,奈何?”[13]可视作对断交信观点的补充。如果说这只是对早期袁世凯的看法,那么,1916年,当袁世凯因复辟帝制而亡身后,张謇则称:“袁氏失德,亡也忽焉。彼其罪过,已随生命俱尽。可留与吾人以最真确之发明者,则权术不可以为国,专制必至于亡身。深愿吾党之士引为大鉴。”[14]这不仅仅是专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倒行逆施的批判,而应视作对袁世凯一生好玩弄权术、专横独裁品性的概括和总结。至于张在给袁的函电中也曾用过一些颂扬之词,如1906年在《为运动立宪致袁直督函》中所称:“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公之苦心毅力,如水之归壑,万折而必东。下走独心喻之,亿万年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繄公是赖。”[15]目的是为了动员袁世凯支持立宪;1912年1月28日的信中写道:“南北一致,趋向共和……不世之勋,惟诸公图之。谨以公民资格,遥致欢忱”[16]和“公膺众选,全国汴庆”[17],则是为了督促袁世凯赞同共和、早定统一大业的政治颂词,不能视为是对袁世凯的客观评价。人们还不难注意到,在张謇与其他友人的信函中,很难发现对袁世凯有过良好的评价,而这恰恰又是最能客观真实地反映自己的观点的。
张謇与孙中山的接触远没有与袁世凯的接触多,信函的交往也很少。他对孙中山的看法和评价,集中反映在追悼会的演说中,称得上是“盖棺定论。”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张謇率先在南通举行了追悼会。张在追悼会的发言中指出:“孙中山是手创中华民国之人,是国民党的领袖。既手创民国,则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谁不该敬佩他!谁不该纪念他!”“孙中山不畏难,不怕苦,不耻屡仆屡起,集合同志,谋举革命,千回百折,备尝艰苦,至辛亥年,事会凑合,卒告成功。”“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斯人不贪财聚畜,不自讳短处,亦确有可以矜式人民。”[18]明确承认孙中山是手创民国的元勋,是国民的领袖;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高度评价了孙中山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大公无私的优秀品德。拿此与对袁世凯的评价相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由于张謇与孙中山的接触,主要是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期间,因此,张謇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就格外引人注目。有人指出:1912年初张寒被推为实业总长,“始则要约以最短之任期,继则以争汉冶萍而辞职”[19],任职期间又并未真正至署办公,辞职后的第二年,又到北洋政府任农商总长。也有人认为,汉冶萍事件,只是张謇退出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种借口。言下之意,是想说明张謇是反对孙中山的,至少称得上是“疏远”。历史的现象是复杂的,许多事件靠直线推理很难反映当时的真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面对“金融困滞,兵革未定,益无可措手”的困状,张謇在致函孙中山时表过态:“顾临时政府方成,建设伊始,若人推诿,不独有负盛诣,抑无以尽匹夫之责。谨当竭所知能,以酬眄睐。”[20]并无敷衍之意。至于说任职期间没有完全到署办公,这是事实,但众所周知,当时临时政府的人员构成很复杂,除少数如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首领外,各部基本上是总长挂名、次长任实职,如副总统黎元洪就一直留在武汉未到任,关键是看有没有干实事。政府初成立,亟需筹集军政经费,虽然这本是财政总长的事,张謇却自任为筹,用自己经营的大生产业作抵,向日本三井洋行借了50万元,缓解了政府的燃眉之急。关于汉冶萍事件,张謇与孙中山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有过激烈的争论。事先,孙中山曾征求过张謇意见,张在给孙中山和黄兴的复函中指出:“汉冶萍之历史,鄙人知之最详。综合要之,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不可。”理由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鄙人尝持一说,谓我国铁业发达之日,即日本人降伏于我国旗之下之日”,“今盛宣怀因内地产业为民军所占,又乘民国初立,军需孔亟,巧出其平日老猾手段以相尝试。吾政府不加细察,一受其饵,则于国防于外交,皆为大失败……愿两公宏此远漠,勿存见小欲速之见,致堕宵小奸慝之谋。”最后说:“謇忝任实业,于此事负完全责任,既有所知,不敢不告。”[21]由于孙中山未听劝告,而张謇则认为这本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因而提出了辞职:“汉冶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与,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谨自动辞职,本日即归乡里。”[22]为此事件,1925年张謇在追悼孙中山的演说中,对所作挽联还特地解释道:“因将汉冶萍铁矿厂抵押于日本,鄙人持不可,而字已迳签,鄙人遂即辞去。”我们姑且不论当时对此事件的处理意见谁是谁非,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张謇的态度是严肃认真而且很坚决。正因为有过严重的分歧和争论,所以,过了13年后对此还耿耿于怀。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这只是张謇要脱离孙中山临时政府的一种借口,至多只能说是有点意气用事。
四
张謇在辛亥革命期间支持袁世凯,既非取决于孙中山和袁世凯两人的品格,又非出于个人感情的好恶,那就只能从政治斗争的需要上去寻求答案了。大家清楚,害怕战乱、力求安定,是张謇一大政治特点。1900年他积极参与“东南互保”活动,是害怕义和团运动扩展到南方来;“五四”前后不遗余力地哀吁和平,是出于对军阀割据混战的深恶痛绝;“五四”和“五卅”运动期间迁怒于“宣传最新学说者”,是认为他们鼓励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导致社会秩序不安宁;武昌起义后不久,能从立宪派向赞同共和的转变,也是害怕因立宪与共和之争导致全国分裂和引发外来武装干涉。张謇之所以特别害怕战乱和社会动荡,是由于他是个拥有庞大的大生实业集团的实业家,又致力于推行地方自治事业,一个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就成为他的全部社会事业生死攸关的首要条件。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统治已濒临瓦解,这时战机四伏,秩序混乱,还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忧,亟需有一强有力的人物来控制局势、统一国家。在张謇看来,孙中山虽然具有优秀的革命家品质,在革命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却缺乏政治实力可以直接左右清政府,又无经济实力来支撑危局;只有已控制了清政府,又拥有庞大的北洋军事实力并得到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袁世凯,才有可能承担此历史任务,因而就成为无可替代的人选。这就是当时张謇支持袁世凯的根本原因。
在今天看来,支持袁世凯就是支持反动,只有拥护孙中山,才是支持革命。可是,当时持张謇同样观点和态度的,并非少数人,而是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甚至连革命党的领袖人物也无例外。如革命党二号人物黄兴,1911年11月9日,就曾以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致书袁世凯,竭力颂扬袁的才能,并说只要他倒戈覆清,归附革命,“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23]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也曾致电袁世凯,表明自己只是“暂时担任”,并称“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24]如果说孙中山写这封信时是由于客观上有压力和为了争取袁世凯早日推翻清政府的话,那么,1912年2月13日,即清帝正式下诏退位、袁世凯通电声明赞成共和的当天,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称:“此次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其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25]特别是1912年秋,孙中山应邀到北京会晤袁世凯后回到上海时的演讲中称:“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推荐项城(指袁世凯——引者),并不谬误。”[26]确是反映了当时对袁世凯的认识。应该说,袁世凯之所以能顺利地取得政权,就是跟当时对他的这种“共识”分不开的。正如张謇所称:“辛亥之役,海内骚然,中外人士,咸以非洹上不能统一全国,故南中各省拥护不遗余力,凡可以巩固中央者,举不惜牺牲一切以徇之,苏鄂两省,尤为显著。癸丑之事,洹上得收迅速藏事之功,虽由北方将士之用命,亦全国人心信仰之效也。”[27]正是由于当时大家对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普遍缺乏认识,误把支持袁世凯当作支持革命事业,才导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这一历史悲剧的发生。
五
张謇支持袁世凯,是以袁世凯赞同共和为前提的。张謇曾是坚定的立宪派领袖人物。1911年6月他入京对清政府“进最后之忠告”,就为请求实行立宪以阻遏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武昌起义后一段时期内,为了采取补救措施,张謇的态度更为积极:10月15日到江宁,劝说清将军铁良援亟“鄂”,“奏请速颁决行宪法之谕”;第二天,商于江苏总督张人骏,未果;第三天又到苏州会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请速布宪法国会之议”,并连夜为之草拟奏稿;10月22日,“由咨议局迳电内阁,请宣布立宪开国会。”[28]可是,“曾未弥月,而响应已十二三省”,革命形势发展之快,是张謇始料所不及的。他既恨清政府不听忠告,“专己自逞,违拂民心,摧抑士论”,导致“人民希望之路绝,激烈之说得以乘之”的后果,同时也不得不面对革命形势已“猋举潮涌,不可复遏”的现实,与其让战祸绵延,“各省金融之闭塞,实业之拘困,父老之惊恐,子弟之死亡,妇孺之流徙”[29]的惨剧进一步扩大,最明智的选择,是顺潮流而动,努力争取实现共和。这无疑是张謇政治上一大进步。为此,他当时在给袁世凯的一系列函电中,都一再强调了实现共和主义的必要性:1911年11月8日的信中称:“旬日以来,采听东西南十余省之舆论,大数趋于共和……潮流所趋,莫可如何。公之明哲,瞻言百里,愿征广义,益宏远谟,为神州大陆洗四等国最近之大羞,毋为立宪、共和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30]11月13日的电文中称:“謇持立宪之说十年,上疑而下阻……其必趋于共和者,盖势使然矣。”[31]11月19日,为辞宣慰使和农工商大臣给袁世凯的电文中又指出:“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于共和主义之下。[32]在给其他友人的信函中,张謇也一再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并希望他们共同来做袁世凯的工作。如11月15日致张绍曾的信中说:“迩者鄂军事起,艰苦文明之举动,遂使各省响风……渴望共和之意,乃如危峰转石,不到地而不已……共和政体之成,已无可疑。惟望公与蓝、陈诸公赞助项城(指袁世凯——引者),早安大局。若多一日踌躇,则多一日糜烂,外人起而干涉,瓜分之祸,即在目前。”[33]正因为支持袁世凯是以其赞同共和、实现共和政体为政治前提的,故当袁世凯假共和的真面目逐步暴露,特别是1915年下半年复辟帝制的阴谋公开化后,道不合不能与谋,张謇坚决与之分道扬镳就势在必然。
注释:
① ② ③《张季子九录·专录》卷七,《年谱》卷下,癸卯年五月,辛亥年五月、辛亥年闰六月
④《张謇日记》辛亥年闰六月十四日
⑤《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劝告袁内阁速决大计电》
⑥ ⑨ ⑩ [11] [19]《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为时局致袁总统函》
⑦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致袁内阁电》
⑧《张謇存稿》页31,《致袁世凯电》(1912年3月9日)
[12]《张謇存稿》页31,《致袁世凯电》(1912年3月10日)
[13]《张謇日记》戊戌年八月十日
[14]《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促费克强返国函》
[15]《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为运动立宪致袁直督函》
[16]《张謇存稿》页29,《与汤寿潜致袁世凯函》(1912年1月28日)
[17]《张謇存稿》页30,《致袁世凯电》(1912年2月)
[18]《张季子九录·文录》卷十七,《追悼孙中山演说》
[20]《张謇存稿》页28,《致孙中山函》(1912年1月3日)
[21]《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为汉冶萍借款致孙总统黄部长函》
[22]《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辞实业部长电》
[23]《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见《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一期
[24]《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76
[25]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辛亥革命丛刊》册8,页136
[26]《总理全集·演讲丙》页3,《孙中山民国元年十月五日上海国民党欢迎会演讲》
[27]《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劝告袁氏退休致徐菊人函》
[28]《张季子九录·专录》卷七,《年谱》卷下,辛亥年八月
[29]《张謇存稿》页19,《拟赴省垣宣告江苏父老书》(1911年11月)
[30]《张謇存稿》页533,《致袁世凯电》(1911年11月8日)
[31]《张謇存稿》页20,《拟会程德全属杨廷楝进说袁世凯》(1911年11月13日)
[32]《张謇存稿》页22,《致袁世凯电》(1911年11月19日)
[33]《张謇存稿》页20—21,《致张绍曾函》(1911年11月15日)
标签:张謇论文; 孙中山论文; 袁世凯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共和元年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