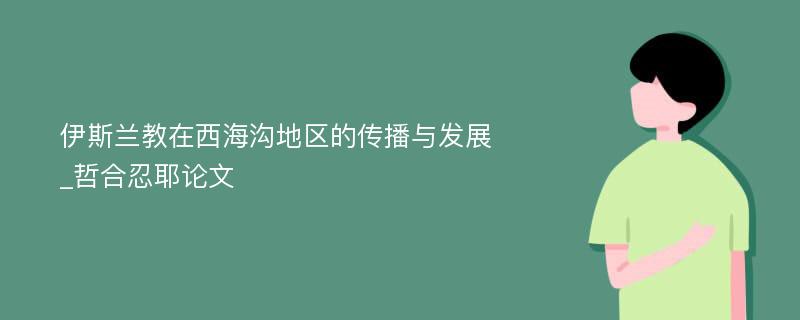
伊斯兰教在西海固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地区论文,西海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宁夏西海固地区位于我国黄土高原的西北边缘,地貌类型以黄土覆盖的丘陵为主,气候干旱,土地贫瘠(注:“西海固”一词是对原西吉、海原、固原三县的联称,始于1953年成立的西海固回族自治区。1954年,甘肃省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改为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后又改为固原回族自治州,1958年划扫宁夏回族自治区,设固原专区。本文所说的西海固主要包括今宁夏固原市六县和吴忠市的同心县。同心县虽然隶属于吴忠市,但从其历史渊源、地理环境和文化特征等方面来看,也应视为人文地理概念下西海固地区的一部分。)。以门宦制度为代表的本土化的伊斯兰文化居于主导地位,苏非神秘主义的宗教人文环境与干旱贫瘠的自然环境的相互映照,使这里成为一个独特的人文地理板块。西海固现有虎夫耶(al-Khufiyyah)、哲合忍耶(al-Jahriyyah)、嘎德忍耶(al-Qādiriyyah)三大门宦和格迪目、伊赫瓦尼(al-Ikhwān)、赛莱菲耶(al-Salafiyyah)三个教派,门宦内部支系繁多。信教群众人数约为107万,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2524座(注:信教群众人数统计来源于固原市民族宗教局和同心县民族宗教局提供的《宗教活动场所年检》等资料。),是一个多元教派并存、穆斯林人口集中分布的地区。西海固地区的人文格局经历过一个“相继占用”的演替过程。在明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大佛文化”在该地区居主导地位且几度繁荣,最终留下了以须弥山石窟为代表的佛教文化景观(注:薛正昌:《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276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从元、明到清代,伴随着政权更迭、民族迁徙和生态环境的交互变动,一种新的宗教文化在西海固地区逐渐传播和发展并成为该地区人文地理的象征,这种标志性文化就是以苏非门宦为特征的本土化伊斯兰教。
一、伊斯兰教在西海固地区的早期传播
(一)元、明时期西海固地区的伊斯兰教
西海固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与回族先民在元、明时期移入该地区相伴随。据考证,元朝初期的开城(今固原市原州区开城乡)等地已有清真寺,这说明伊斯兰教在元朝初期就已传入西海固地区。当时的穆斯林主要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和因成吉思汗西征而移入中国的其他各族人。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封其第三个儿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安西王在六盘山麓的开城一带设立王府,冬住长安,夏居凉爽的开城。忙哥剌信仰伊斯兰教,他有一个儿子叫阿难答,年幼时由一个穆斯林家庭抚养,这种双重影响使阿难答“皈依回教,信之颇笃”(注: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345页,中华书局,1962年。),成了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忙哥剌死后,阿难答袭任安西王,播布伊斯兰教于唐兀之地(其中包括今宁夏西海固大部分地区),并在自己的营地上建立清真寺。他统领的15万军队中的大部分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在西海固一带活动并最终留居的数量很少,此外,元代西海固地区也有西域传教士活动的踪迹。据嘎德忍耶门宦内部资料和民间传说,今原州区开城乡二十里铺拱北的墓主很可能就是元代的一位伊斯兰先贤,而且有可能就是跟随阿难答的军中传教士。元朝时期,西海固地区见于记载的清真寺很少。
回族定居西海固主要始于明代。元朝灭亡后,原来活动在陕西、甘肃等地的一部分蒙古人放弃北撤,归附明朝。其中有一些被安置在固原一带定居,史书上把他们称为“土达”。综合分析有关史料和研究可知,“土达”中有穆斯林,但数量不多。明代之际,也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因商业贸易、征战戍守等从异地迁入西海固。如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朝廷“徙甘州、凉州寄居回回于河南各卫,凡四百三十六户,千七百四十九口”(注:《明英宗实录》卷十八。),其中迁徙到陇右、陕西一带的最多。明代开国将领沐英(回族)由于征战西北有功,钦赐武延川(今西吉葫芦河)、撒都川草场6处,筑城沐家营,后留兰、马两姓18户居之。总之,经过一段时期的迁入、改宗、通婚、融合等,西海固穆斯林人口数量较元代有明显增加,并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坊”的独特社区形态(注:“坊”是若干个回族穆斯林住户以清真寺为中心组合起来的宗教杜区。唐宋时期的城市中有“市”、“坊”之分;“市”是商业区,“坊”是居民区。这种社区形态在回族社会中得以保留并延续至今。)。明朝时期西海固有史可考的清真寺有8座,其中有西吉的硝河清真寺、沐家营清真寺、新隆清真寺、单明清真寺,固原的黄铎堡清真寺,同心的韦州清真大寺、豫旺清真大寺。有些清真寺规模宏大,精雕细琢,说明穆斯林不仅已定居该地区,而且其经济社会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
元、明两代是回族先民移入并逐渐定居西海固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在本地区得以传播并有所发展,其主要标志就是清真寺的建立。伊斯兰教的传入,改变了西海固地区的人文生态结构,形成了以“大佛文化”为主导,佛、道、伊斯兰三教并存的局面。
(二)清朝时期西海固地区的伊斯兰教
清代是西海固伊斯兰教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教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成功实践,二是多元教派并存格局的出现。清朝初期,虽然在青海、甘肃等地区产生了毕家场、花寺、穆夫提等苏非派别,但它们的传播区域较为狭小,基本上是在距离其创始人家乡较近的周边地区,在西海固地区并没有传播。到了清乾隆九年,祖籍甘肃阶州的马明心结束了在阿拉伯也门地区和中亚一带长达十余年的求学生涯,回归故里并创立了哲合忍耶。马明心学识渊博,主张简朴的宗教生活,甘、青、宁等地区的好道之士纷纷慕名前来求学问道,“拜马明心为师的有名阿訇,先后就有百余人。”(注:马通:《中国伊斯兰救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43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有一位叫田伍的阿訇就是马明心的弟子。田伍是海原小山人,他不仅虔诚地信奉哲合忍耶,而且在海原及周边地区尽力传播哲合忍耶教义,甚至在官方严禁“新教”(注:清代官方文献称哲合忍耶派为“新教”,是相对于当时的花寺门宦等而言的。)后仍“私行传习”。田伍发动起义时“从者数千人”(注:《平定关陇纪略》卷二。),他还在“沿途纠合新教党羽”(注:《石峰堡纪略》卷二。)。这说明当时西海固地区已有比较多的人开始信奉哲合忍耶。
从清朝初期到同治前期,西海固地区的穆斯林人口没有明显增加,这一点可以从该地区修建清真寺的数量上得到证明。据统计,西海固地区所修的清真寺,“康熙朝仅有1座,乾隆朝有3座,嘉庆朝有6座,道光朝有16座,咸丰朝有11座,同治朝有29座”(注:佘贵孝:《固原回族研究》(内部出版物)第133页。)。同治末年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数万回民被安插到今西海固地区,这一地区的回族人口显著增长。光绪年间,西海固地区新建清真寺335座,清真寺的兴建和清真寺数量的增加一方面与人口的增长相关联;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在战乱中幸存下来的回族穆斯林经过二三十年的拓荒垦殖和家园重建,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已有所恢复。从教派构成看,这一时期的西海固地区以格迪目和哲合忍耶为主,其他门宦和教派要么传人极少,要么还没有产生。
二、伊斯兰教在西海固地区的发展
清朝时期,处在多种民族文化结合部的河州地区变成了一个“专为穷苦的黄土高原居民制造度世理论”的“学术思想的中心”(注:张承志:《在中国信仰》(回族题材散文选)第184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这一时期,西北地区不断有新的门宦和教派产生,这些教派和门宦大多创建于甘、青的河湟地区,然后再从这些地区向西海固扩展。从清朝初期到民国时代,西北地区相继产生了虎夫耶、哲合忍耶、嘎德忍耶、西道堂、伊赫瓦尼、赛莱菲耶、库布忍耶等门宦和教派,门宦内部支系繁多。除西道堂和库布忍耶外,其他门宦和教派在西海固地区都得到有效传播和发展,其中虎夫耶、哲合忍耶、嘎德忍耶三个门宦的一些主要支系还在西海固地区建立了传教中心,至今不衰。西海固也是伊赫瓦尼及后来赛莱菲耶教派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
(一)苏非派各门宦在西海固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前文已经提到,哲合忍耶自第一辈道祖马明心起,就在西海固地区有所传播,其中马化龙、马元章、马进西等人的传教活动都曾涉足西海固地区,但对西海固哲合忍耶传播和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当推第六辈教主马元章。在社会环境不利的情况下,马元章常常乔装成货郎,挑着货担往来于各地回民之中,他在西海固地区传播哲合忍耶时,着重向西吉一带发展。20世纪初,马元章令其弟马元超管理张家川宜化岗教务,他自己离开张家川,到西吉沙沟落脚,建立道堂(注:本书对西海固地区各门宦的传播和教权继承方面的叙述,主要以马通的《中国伊斯兰救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和勉雄霖的《宁夏伊斯兰救派概要》为依据。)。马元章聪慧有智,阅历较多,擅长交际。他除攻读经典圣训外,还博览诸子百家和史籍文物,是哲合忍耶历代教主中精通阿拉伯语和汉语并有著作的惟一人物。他写的文章均本《古兰》之精神,融以儒家的道德标准,劝勉自己,教诫后人。他还接受刘智等经学家的思想,强调用汉文宣传教义,用儒道之学解释伊斯兰教,又运用儒家忠义之道建立哲合忍耶门宦的教权制度,从而使哲合忍耶走上了继马明心和马化龙之后的第三次极盛时期(注:马通:《中国伊斯兰救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42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马元章继任教主后,吸取了前辈的经验教训,对哲合忍耶的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
第一,注重教派团结和民族团结。“和为贵”是马元章为人处世和传教立道的一贯主张。在民族内部,马元章主张教派之间互相尊重、各行其是,促进了各教派之间的团结和睦。在回汉团结方面,他主动结交了许多有声望的汉族士绅贤达,与他们互相往来、谈古论今。要求教民主动抛弃成见,和汉民多交往,化阻力为助力。马元章同情孤苦,常常帮助汉族群众解决困难。
第二,尽量融洽政教之间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马元章吸取了前辈的经验教训,认为传教者不能与当政者搞对立。因此,他在发展宗教的同时,十分注意政治影响及与政界官吏的交往。强调服从政府和官长,力做顺民。马元章在政治方面的态度和言行,不仅有助于缓和政教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而且为哲合忍耶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也提高了他个人的社会威望。马元章有一次赴兰州时,受到官方的出郊欢迎,待如上宾,这是哲合忍耶前辈教主从未经历过的。
第三,在传教过程中注重淡化“舍西德”(注:阿拉伯语,是对在圣战(jihad)中阵亡穆斯林的称谓。引申为“殉教”、“为教门牺牲”。)(shahid)思想,主张和平兴教。他常对那些想通过追求“舍西德”而进天堂的教民讲:伊斯俩目教门是为活人创立的,不是为死人立的。“舍西德”不是随意而为的,它是最后迫不得已的事情,自找的死不是“舍西德”。他这种调和适中的思想对塑造哲合忍耶穆斯林宗教生活的理性精神有一定的积极影响。马元章是一个教乘和道乘造诣很高的宗教家,他的办教、处世原则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虎夫耶源于中亚地区广泛流行的一个苏非主义派别——乃格什板顶耶教团。由于师承渊源的多样性,虎夫耶从一开始就有门户多样、互不隶属的特点。马通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一书中列举了19个虎夫耶的支派,这些派别传入时间不一,大部分规模较小,主要分布在河湟一带。传入西海固地区的虎夫耶主要有两个门宦,即洪门和鲜门。
嘎德忍耶是12世纪产生于波斯的一个苏非派教团,其创始人是阿卜杜·尕迪尔·吉拉尼。大约在康熙年间,有一位叫华者·阿布都·董拉西的谢赫从中亚撤马尔罕一带来到中国西北地区传教,早期主要传播于甘肃的临夏、兰州一带,形成了大拱北、沙门、阿门等支系,传入西海固地区的主要有九彩坪门宦和齐门门宦。九彩坪门宦的第一辈道祖叫安洪维,甘肃平凉人,是嘎德忍耶第六辈道祖的族孙。安氏早期以青海的后子河拱北为传教中心,后迁居宁夏海原的九彩坪进行传教活动。齐门门宦的名称来源于其第五辈教主马德明。马德明经名七什子,他当了老人家后,他的教下尊称其为“齐爷”,这个门宦则称为齐门。传说齐门创始于清末,其第二辈“老人家”归真后葬于同心的石塘岭并建有石塘岭拱北,说明该门宦早在第二辈时就已经传入西海固地区(注:勉维霖:《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第6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
(二)伊赫瓦尼教派在西海固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1892年,甘肃临夏地区一位名叫马万福的东乡族阿訇从沙特阿拉伯朝觐归来,因为他家住临夏东乡的果园村,故又被称为“果园哈知”。马万福在受教于麦加海里夕巴氏学堂期间,将中国当时的伊斯兰教尤其是盛行于西北地区的苏非门宦制度与当时沙特阿拉伯地区的“瓦哈比”学说进行了对比,有选择地带回了一些经典。根据这些经典,他提出“凭经行教”“遵经革俗”的主张,反对门宦信仰,并公开宣布退出北庄门宦,称自己的主张为“伊赫瓦尼”(注:“伊赫瓦尼”一词是阿拉伯语“兄弟”之意。)。
马万福有一个学生叫郭四高,是宁夏吴忠人,曾随马在西宁念经,“穿衣”毕业后受马指派到宁夏传教。郭四高是最早在宁夏传播伊赫瓦尼的阿訇。后来又有同心的大顾阿訇和伊依底力阿訇及固原三营的老四阿訇等在同心、固原、海原一带传播伊赫瓦尼,但遭到格迪目、哲合忍耶、虎夫耶等教派与门宦的激烈反对,甚至引发械斗事件。伊赫瓦尼在宁夏的初期活动没有获得明显成效,许多当地的伊赫瓦尼阿訇甚至一度停止了传教活动。面对这种情况,伊赫瓦尼中出现了一批“温和派”,他们总结了早期传教活动失败的教训,克服了某些极端主义倾向和偏激情绪,对格迪目和门宦作了一些妥协。这批“温和派”中在同心、海原、固原一带影响最大的当推虎嵩山阿訇。虎嵩山先后在同心、固原县城(今固原市原州区)、固原三营等地开学,培养了很多有学识的伊赫瓦尼中青年阿訇,对伊赫瓦尼在西海固乃至整个宁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注:冶正纲:《宁夏伊赫瓦尼著名经学家虎嵩山》,《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第290~30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三、对西海固伊斯兰教传播史的几点思考
(一)教派分化是宗教自身发展的一个规律性表现
教派分化是宗教自身发展的一个规律性表现,也是世界上一些主要宗教的共有现象。例如基督教先是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然后又从天主教中分化出基督教新教,目前仅基督教新教中就有10多个主要教派,如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公理宗、浸礼宗、卫斯理宗、公谊会、基督复临宗、五旬节派教会、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基督教科学派等。佛教在产生后不久即分化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系,此后经过300年的发展,到公元1世纪中叶,形成了很多独立的派别,已知的部派名称有40多个,佛史称这一段历史为部派时期(注:杜继文:《佛教史》第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1年。)。我国有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小乘佛教之分,其中汉地佛教内有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上宗、密宗等宗派;藏传佛教中有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葛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等,还有希解、觉域、郭扎、夏鲁、觉囊等5小派。葛举派又有4个支派,这4个支派中的帕竹葛举内部有8个小的分支。可见,不论哪种宗教都有教派之分,多元教派并存格局往往反映出宗教内部的革故鼎新和相互补充。衡量一个教派是否合理的基本尺度就是它与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适应程度。具体到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来说,就是要看这种宗教是否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否有利于教派间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是否有利于穆斯林群众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信教群众的身心健康,是否有利于穆斯林宗教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是否具有包容和谐的内在精神并能够为信教群众提供较大自主选择的空间。有了科学、合理的评价尺度,我们就可以作出准确判断,做好宗教事务管理工作,维护人民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二)教派分化过程中容易引发各种宗教矛盾
在西海固伊斯兰教史上,每当出现新的教派或从某一门宦中分化出新的支派,都会受到来自传统教派、门宦的抵制和压力,引发宗教矛盾。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一般来说是倾向于维护传统的,所以每当出现革新、反传统的事物时,就会受到传统力量的抵制,这样就形成了新旧事物之间的对立,通常表现为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矛盾。新教派产生时,其学说和主张一般都是针对原有某一教派或某几个教派的,既然是“革新”,就要与原有教派有所不同,甚至公开批判某一教派或某些教派的思想主张,否定原有教派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和相应的宗教仪式,这就有可能引起原有教派的不满而形成对抗。第二,新教派的产生会打破旧的利益关系格局,重新分配宗教资源,因此会遭到传统力量的排挤。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经济有着密切关系。伊斯兰教是“入世”的宗教,宗教上层和教职人员的宗教活动与社会经济相关联,主要表现为对教权、财富和社会声望的需求。宗教资源是指一个特定区域内的宗教人口、空间分布及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西海固地区宗教人口数量有限,土地贫瘠,人民群众生活贫困。也就是说,宗教资源稀缺。教派越多,这种资源就越稀缺,宗教资源追求者们之间的竞争也就越激烈。新教派或从某一原有教派中分化出来的支派的产生和传播,既有对宗教真理本身的追求,也有重新分配宗教资源、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要求,这种利益竞争容易引发矛盾和纠纷。历史上很多宗教纠纷和矛盾首先是在宗教上层之间出现的,产生这些宗教矛盾和纠纷的实质就是对宗教资源的争夺。
(三)门宦制度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产物
所谓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就是伊斯兰教义学说、宗教习俗和宗教组织等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一定程度的结合。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伊斯兰教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反映。从宗教与特定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角度看,伊斯兰教中国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伊斯兰教经典的汉语化和教义学说阐释过程中对儒释道某些“术语”及合理思想的适度借取和接近;二是穆斯林社会中某些习俗的中国化;三是组织结构的中国化。组织结构中国化的典型事例就是门宦制度的产生,所谓门宦制度,是指苏非导师及其追随者为了有效实现与宗教信仰相关的一系列特定价值目标而建立起来的结构比较严密的制度化群体,是由文本化的宗教思想、模式化的宗教仪式和层级化的教权组织等要素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体系。门宦制度是具有苏非思想的教团主义适应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经济形态和人文价值观念的产物。它的本土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苏非派在宗教话语、教义学说体系方面与中国本土宗教的融通。中国苏非派各门宦大多认同并推崇刘智、王岱舆、张中、马注等经学大师的汉文经著。这些经学大师都是“回而兼儒”的伊斯兰思想家,他们的经著具有浓郁的苏非主义色彩。这些经学家在翻译、研究和撰写伊斯兰教经典的过程中,不仅大胆借用了儒释道的某些宗教术语,还将伊斯兰教与儒释道诸教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对儒释道诸教中的合理思想进行了有选择的吸收与整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式的伊斯兰话语体系。这些宗教话语和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我国苏非派各门宦吸收、运用并加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之际兴起的“以儒诠经”思潮及其成果为中国苏非门宦的创建提供了思想条件。
2.门宦教权组织和继承系统的形成受到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门宦制度可以说是具有苏非思想的教派主义(Sufi-sectarianism)与传统中国世袭制的内涵,同时也结合了伊斯兰宗教神格化思想 (Islamic religious charisma)与中国家系制的结构。”(注:转引自张中复:《论研究中国伊斯兰门宦制度的民族学内涵与意义》,《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银川)第115页,内部资料,1998年。)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是宗法制,而宗法制的核心正是围绕家系制建立起来的世袭制。苏非门宦在教权继承方面,起初大多实行“师徒相继制”,即门宦创始人倾向于在他的优秀弟子中选择教权继承人,避免血缘继承。但回族穆斯林的价值观念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到后来,各门宦在教权继承上都转化为“父子世袭制”或“家族世袭制”。多年来,研究门宦制度的学者们对门宦的教权世袭制或多或少有些非议。我们认为,对宗教系统中的教权继承等问题没有必要用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准去加以衡量,也没有必要过多地去讨论它本身的是与非,因为宗教的发展、变迁往往落后于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也就是说,不能用现代价值标准去审视门宦制度。
3.苏非门宦的老人家都有修功办道的专门场所,这个场所一般被称为“道堂”。前一辈老人家去世后,下一辈要为其修建拱北。苏非门宦往往通过盛大的祭祀活动和宗教节日强化拱北、道堂在人们宗教生活中的重要性,使拱北、道堂成为教徒心目中神圣的令人向往的地方。这种对拱北的崇拜和对道堂的向往,在某种程度上受中国传统宗祠文化的影响。在门宦中,“穆勒师德”(Murshid)和“穆里德”(Murid)(注:“穆勒师德”一词系阿拉伯语,是“引领者”、“导师”的意思,官方文献称其为“教主”。在门宦内部,一般把在世的“穆勒师德”尊称为“老人家”(虎夫耶、嘎德忍耶)、“爷”(哲合忍耶)、“掌柜的”(嘎德忍耶)等,把已故的“穆勒师德”尊称为“遭祖”、“老太爷”等。“穆里德”一词是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寻道者”。)之间既是导师和弟子的关系,又是“巴提尼”(bātin)(注:“巴提尼”一词是阿拉伯语,意即“内在的”、“心灵深处(sirr)的”、“精神上的”。)的父子关系,这种关系的延伸给门宦赋予了“家”的意义。各门宦每一辈教主之所以重视对历代教主的纪念活动,就是要保持他所掌管的这个“精神家园”的凝聚力和持久性。
标签:哲合忍耶论文; 西海固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回族论文; 教主论文; 马元论文; 固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