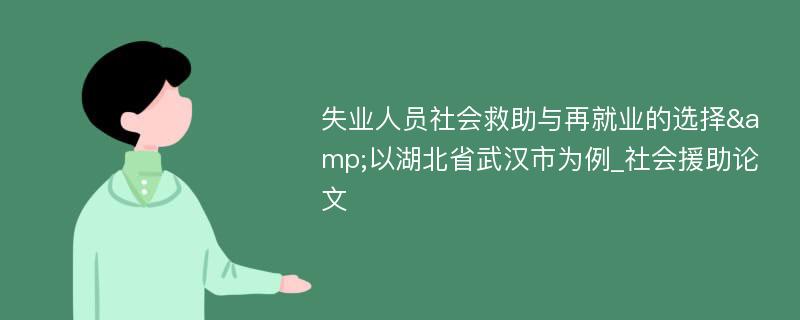
失业者社会援助与再就业的选择——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汉市论文,失业者论文,湖北省论文,为例论文,再就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于社会援助与就业的相互制约关系,社会援助会导致劳动惰性的想法由来已久,很多时候劳动者的懒惰不仅被认为是社会援助的后果也被认为是导致其接受社会援助的原因。作为最后一道安全网的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运行近十年,失业、下岗人员不仅构成现实受援助人口的主体,也是一个日益增加的庞大的潜在受援助人群。在面对人力资源的浪费,担心社会援助难以承担的同时,也使人们关注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否有受助者某种主动选择的影响?在失业者中是否存在着社会援助和再就业的权衡选择?社会援助是否削弱了失业人口再就业的主动性、从而影响了其再就业的实现?对以上问题的困惑,构成了本研究的中心内容。
湖北省武汉市作为中部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游,其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工人的下岗、失业及由此导致的生活水平下降,即贫困问题突出,再就业工程难度很大,对全国而言也具相当的代表性。基于此考虑,本研究以武汉市为个案,通过对失业者一定范围的问卷调查,尝试测度社会援助对失业者再就业的影响及其表现方式,以此作为今后社会援助制度调整和完善的参考。
一、失业者社会援助与再就业的比较分析
由于“失业”这一状态在国内使用上的多种表述方式,如登记失业人口、待业人口、下岗人员、内退人员等,为避免概念的交叉和混淆,本文取失业的初始定义,即失业者即为有劳动能力、没有工作但愿意工作并正在寻找工作者。只要符合这三个要件即为失业人口,而不考虑其登记失业人口、待业人口、下岗人员、内退人员等失业保险领取资格和企业劳动关系的界定等。社会援助是一个相对宽泛而不太统一的概念,一般是指保证居民最低生活水平的制度,在有些国家失业或生病时就可以接受援助。为研究的方便,在本文里社会援助包括失业者享有的最低生活保障、失业救济和下岗生活费。只要享有其中一项社会援助的,就被称为受助者。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03年对“楚天帮扶活动”中求职者的电话访问调查。2002年9月27日至2002年10月27日,《楚天都市报》专门开辟了楚天帮扶再就业专辑栏目,刊登打进热线的下岗职工求职信息,公布了1578位求职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特长和联系电话等资料。笔者以这些求职者为抽样框,随机等距抽取300个样本进行电话调查,遇到拒绝的则替换为邻近的上一位求职者,回收有效问卷253份,有效回收率为84.3%。因为是以2002年9月27日至2002年10月27日的就业状况界定的失业,不排斥在2003年调查时有些失业者已找到工作。
度量社会援助对失业者再就业的影响是一个很微妙的困难工作,涉及到个人层面的道德、社会责任等的价值评判,直接询问有伤害被调查者自尊和侵犯个人隐私的嫌疑,而且被调查者也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有选择的符合自我价值认同的回答。所以,在本调查研究中,设计了一系列相关的、侧面的、他人的问题进行测量。冀望通过比较社会援助的受助者和非受助者在再就业的实现、再就业和社会援助的价值观念、再就业的行为等方面的差异,考察和分析社会援助对失业者再就业的影响,进而推断和估测失业者在社会援助与再就业间的选择行为是否存在以及表现特点等。
(一)失业者社会援助与再就业的基本情况
在所调查的失业者中,领取过下岗生活费、失业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一种社会援助的人,占总样本的40.7%。经过一段时间的求职,到调查时有87人有工作,占总样本的34.4%。
1.失业者社会援助与再就业的实现
在调查中发现,受助者和非受助者实现再就业的比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非受助的失业者在调查时有40%找到了工作,而受助者仅有26.2%找到工作,低13个百分点。非受助者再就业实现的工资上下浮动区间较大,从最低的100元到最高的1200元;相比之下,受助者再就业的工资区间偏窄,从最低的200元到最高的900元,仅有700元的浮动空间。受助者的平均失业时间要短于非受助者的失业时间(见表1)。
表1 失业者社会援助与再就业实现
受助者非受助者
再就业的比率(%)
26.2 40.0
工资(元)
中位工资 500.00
500.00
最低工资
200
100
最高工资
900
1200
平均失业时间(年) 3.7
4.4
2.因社会援助而放弃就业的情况判断
在社会援助和再就业之间的选择,不仅是一个机会成本的经济决策,还涉及到个人层面的工作价值、生活意义、社会责任等的道德判断,因社会援助而放弃就业的行为也是被社会所谴责和不允许的。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政策解答中,民政部副部长范宝俊指出,受助者“要想生活富裕起来,就要积极参加再就业,不能因为有了国家救济就不想工作了”。各地在实施社会援助的同时,也对受助者参加再就业培训、积极实现再就业规定了相应的条款。故此,直接调查因社会援助而放弃再就业的情况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调查中,我们期望“你认识的人之中有没有因为领取社会救助而放弃了就业的机会”这个询问,能从侧面了解和判断因社会援助而放弃就业的情况。
调查结果是,30.0%的非受助者对“你认识的人之中有没有因为领取社会救助而放弃了就业的机会”这个询问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受助者有24.3%给予了肯定答复。也就是有接近1/3和1/4的非受助者、受助者认识的人中因为社会援助而放弃了就业,这个相对高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失业者社会援助和再就业的选择是一个被普遍认知的客观存在。
(二)社会援助对失业者再就业影响的比较分析
1.受助者与非受助者再就业培训参与及评价的比较分析
在过去一年里接受过再就业培训的非受助者为20.7%,受助者接受过再就业培训的为26.2%,受助者参与再就业培训的比例高于非受助者。
对再就业培训有否帮助的判断,非受助者比受助者更多取正面的评价,在认为再就业培训完全没有帮助的选项上,受助者的比例高于非受助者;认为有一点帮助、有帮助、有很大帮助的选项上,非受助者比例高于受助者。总体上看,认为再就业培训至少有一点帮助及以上的比例两者都不到一半,一半以上的人通过选择难讲、不回答等方式表达了对再就业培训的怀疑甚至否定的判断(见表2)。
表2 失业者社会援助与再就业培训的评价 %
受助者 非受助者
完全没有
24.3
18.0
有一点
16.5
20.0
有帮助
15.5
20.7
有很大帮助
4.9
2.0
难讲 11.7
12.0
没有回答
27.2
27.3
2.受助者与非受助者寻找工作方式的比较
调查显示,非受助者在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工作方面表现得比受助者更为积极。受助者和非受助者在通过何种方式寻找工作上的偏好基本一致,比如,依赖非正式的个人社会关系网——亲戚朋友同事的帮助寻找工作(45.6%、38.7%),对正式的就业社会支持——职业中介、再就业中心、街道居委会的倚重偏弱(低于30%)。但在具体分布上,受助者与非受助者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不同,受助者借重非正式渠道的比重高与非受助者,对正式渠道的依赖稍弱于非受助者。而且,对任何一种寻找工作方式的选择,受助者或非受助者都没有超过50%(见表3)。
表3 失业者社会援助与寻找工作方式比较 %
受助者
非受助者
正通过职业中介寻找工作 24.329.3
正通过再就业中心寻找工作
24.325.3
正通过亲戚朋友同事找工作
45.638.7
正通过街道居委会找工作
4.9 4.7
通过其他方式找工作
12.624.7
人均寻找工作的方式(人次) 1.121.23
注:失业者寻找工作方式的调查是一个多选题,失业者很有可能正在通过多种方式寻找工作,调查结果也显示人均寻找工作的方式超过了一种。
3.受助者与非受助者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比较
失业者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的起点都为月收入300元,但选择这一收入水平的非受助者高于受助者5个百分点;定位在600元及以上的比例受助者高于非受助者5个百分点;在400元和600元之间各收入层次的选择上受助者、非受助者的比例分别为32%、27.4%和26.2%、31.3%,呈交替上升趋势,没有明显的差异。总体上,在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低收入层次上非受助者比例较高,在高收入层次上受助者比例较高。
4.受助者与非受助者在工作条件差时的选择比较
在面临介绍的工作条件差、工资低时,55.3%受助者、44%的非受助者选择先干着再说,有12.6%的受助者和14%的非受助者表示会等等看,只有23.3%的受助者和24%的非受助者明确表示拒绝。总起来说,受助者比非受助者,更多地选择先干着再说,表示等等看、拒绝或不回答的比例都低于非受助者。
失业者无论其是否接受社会援助都表现出较强的工作意愿,在被询问如果找不到自己期望的某一职业、行业的工作,是否愿意改做其他的工作时,一半以上的失业者回答“愿意”,只有14%的人回答“不愿意”。受助者和非受助者回答愿意改做其他工作的各为55.3%和54%,表示不愿意的比例各为14.6%和14.7%,认为应视具体情况而定的为30.1%和31.3%,受助者和非受助者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
二、结论与分析
(一)社会援助对受助者再就业的影响
基于受助者与非受助者再就业的比较,社会援助对再就业影响的表现较为复杂,呈现离散的、相反的倾向。虽然社会援助的受助者再就业比例偏低、对再就业培训评价偏低、寻找工作不太积极等指标,预示着社会援助对失业者的再就业有着负面的、消极的影响,可以初步判断失业者社会援助与再就业的选择,以及社会援助对失业者再就业的负面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的。但同时也有一些指标表明,社会援助的接受与否对失业者的再就业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甚至社会援助的受助者再就业在有些指标上表现的更为积极主动等。各项指标对社会援助影响再就业的支持呈现离散、相反的倾向。
一方面社会援助对再就业有负面影响。首先,有近1/3的非受助者和1/4的受助者在被问到“你认识的人中有没有因为领取社会救助而放弃了就业的机会?”时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同时,接受社会援助的失业者其再就业实现的比例明显低于没有接受任何社会援助的失业者,非受助者接受的工资最低为100元,而受助者为200元。其次,虽然受助者参加再就业培训的比例略高于非受助者,但其对再就业培训有否帮助的判断,受助者比非受助者更多取负面的评价;受助者借重非正式渠道的比重高于非受助者,对正式渠道的依赖稍弱于非受助者。再次,失业者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的起点都为月收入300元,但选择这一收入水平的非受助者高于受助者。受助者人均寻找工作的方式为1.12人次,非受助者为1.23人次,非受助者在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工作方面表现得比受助者更为积极。
另一方面失业者无论其是否接受社会援助都表现出较强的工作意愿,在被询问如果找不到自己期望的某一职业、行业的工作,是否愿意改做其他的工作时,一半以上的失业者回答“愿意”,只有14%的人回答“不愿意”。受助者和非受助者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
另外,社会援助对再就业也有正面效应。受助者的平均失业时间为3.7年,要短于非受助者的失业时间4.4年;受助者比非受助者在面临介绍的工作条件差、工资低时,更多的选择先干着再说,表示等等看、拒绝或不回答的比例都低于非受助者;在过去一年里接受过再就业培训的非受助者为20.7%,受助者接受过再就业培训的为26.2%,受助者参与再就业培训的比例高于非受助者。
(二)社会援助对再就业影响表现形式的理解和认识
1.社会援助对再就业影响的双向表现形式是受助者主观选择与实际行为之间距离的体现
如何理解和认识社会援助对再就业影响的双向表现形式,我们发现:虽然社会援助对再就业影响的表现呈现离散、双向的特点,既有负面的效应,也有正面的影响。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负面的效应往往体现在实际所发生的行为上,表现为“你做了什么?”;正面的反映往往集中在受助者个人的主观意愿选择上,表现为“你认为应该怎么做?”二者有着很大的不同。社会援助对再就业正、负效应的双重表现,其实正是受助者社会援助民再就业的主观选择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的体现。从社会责任、工作价值以及政策约束出发受助者所做的主观意愿表达,体现了其社会人的一面;而其实际行为则可被看做是经济人的理性决策。
相关的研究分析也从不同侧面支持这一结论,如对欧洲七国的研究显示,其社会援助对低收入的替代率超过80%,救济累加等于或高于工作收入时,失业者重新就业的比例大大降低(M.Einerhand M,1999)。是从实际结果出发的研究结论。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则更多偏重主观愿望、寻找工作行为的表达和度量,如黄洪宇、蔡海伟(1998)的研究指出,综援人士均曾积极寻找工作。顾东辉(2001)对上海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服务和求职行为研究认为,如果让有劳动能力的援助对象在就业和救济之间选择,他们几乎都会选择前者,而且大多数人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正在为寻找工作而努力。
2.受助者社会援助与再就业主观选择受社会援助、工作等价值观的制约,是一种被“修正”过的意愿表达
接受社会援助对绝大多数受助者来说意味着必须承受一定的心理压力,在调查中有63.5%的受助者表示接受援助令他们经常有心理压力。受助者中也有相当比例认同工作的价值高于一切。调查显示,对“救助影响自食其力”观点表示同意和有些同意的受助者比例为46.6%、54.7%,表示不同意和反对的仅为28.2%;对“领低保者工资再低的工作也该干”观点表示同意和有些同意的受助者比例为38.9%,表示不同意和反对的为25.2%;对“领取救助意味着个人的无能”这个相当负面的问题,有17.4%的受助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不同意和反对这个观点的受助者为41.8%。总体上说,受助者相当认同“救助影响自食其力”、“享受低保者工资再低的工作也该干”等观点(见表4)。
表4 受助者社会援助与再就业的主观判断
同意 有些同意 不一定 不同意 反对 没有回答
救助影响自食其力
22.3 24.3
17.5 24.3 3.9 6.8
领取救助意味着个人无能8.7 8.7
34.0 35.0 6.8 6.8
领低保者工资再低的工 21.4 16.5
24.3 22.3 2.9 12.6
受社会援助、工作等价值观的制约,受助者在被询问其社会援助与再就业选择时,按照自己认为“应该”的口径来回答,是较为容易理解的。或言之,笔者认为受助者的再就业主观选择是在一种压力状况下做出的,是某种经过润色和“修正”的符合社会期望、规范和自我认同的表达。
3.社会援助政策、制度对受助者的再就业有所规定和约束,为了遵守或规避这些约束,受助者的再就业行为也做了相应地调整
社会援助制度和政策对受助者的再就业是有着确定的要求的。受助者在接受社会援助的同时也被要求必须参与再就业的培训,并积极努力实现再就业。政策约束的考量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受助者比非受助者对再就业培训更多取负面的评价,同时其参加再就业培训的比例反而比非受助者要高这一矛盾状况。因为受助者是“被要求”而非“自愿”的参加再就业培训的。
虽然受助者已被纳入政府应给予一定帮助的社会再就业网中,受助者还是更愿意倾向于通过非正式渠道寻找工作。除了非正式渠道可能更有效率之外,通过非正式渠道而实现的再就业及收入等信息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的难以获取性,可能也是非正式渠道更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借助非正式渠道的帮助,失业者可以实现“隐性就业”,从而逃避收入监督。
受助者的平均失业周期短于非受助者的失业周期,也可理解为失业周期较短、距今较近的失业者更易获取社会援助。因为下岗生活费、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起动及大范围推广的时间大致都在1997年之后,在这之前的失业者失业时还没有相应的社会援助,也就不可能享受社会援助。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满足理论,当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生存第一,为了求得生存,人们会不惜代价、不计手段。在这个层面上是很难要求人们重视道德的自我完善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古人云:“衣食足,然后知廉耻。”所以,虽然在道德和社会层面上,受助者树立了一定的工作价值观,但在实际选择中,如果工作与救济发生冲突,受助者基于生存、理性、经济的选择就会压倒其道德层面的犹豫而做出收益最大的决策,也即在工作的收益没有足够大的时候,为了获取或保有社会救济而放弃工作机会。故此,受助者主观选择和实际再就业选择的矛盾,也是受助者个人在协调社会承认和满足生存需要之间冲突的一个结果。
三、建议
社会援助对受助者再就业影响的分析结果,使我们在警惕受助者再就业条件抬升、动机不足的同时,也提醒我们看到社会救助对受助者个人自尊和社会承认的打击,关注受助者主观意愿与客观选择分离对社会政策的干扰。
如何协调社会援助与再就业的关系,在不产生依赖的同时保证社会援助的短期救济功能,中国未来的社会救助与再就业政策的完善既要建立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上,也要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社会救助的经验和教训。自有社会援助以来,各国政府的社会援助就一直摇摆在“终止贫困”还是“终止依赖”的两个政策目标中。早期的英国“济贫法”是“终止依赖”政策的极端形式,而美国里根时期“新联邦主义”所实行的迫使和鼓励受救济的穷人参加工作的改革,也是以终止依赖为目标的政策。遗憾的是,“济贫法”把穷人视做“罪犯”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其政策的失败;美国“终止依赖”的过度保守的反贫困政策,超过了社会价值和贫困文化所能承受的负荷,最终再度制造了大批新旧贫困人口。
以终止贫困为目标而建立的中国城市社会援助制度在建立之初就已注意到了防范依赖的问题,并进行了相关的制度建设,在以后的发展和完善中,终止依赖的政策目标将逐渐彰显。
基于中国的实际,对社会援助政策与再就业推进协调发展的适度政策设计,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个人尊严的回护。现代观念里,社会援助的国家的责任和公民的权利,社会援助的实施不应使受助者有耻辱感和压抑感。应努力通过再就业的实现帮助受助者重新找回和提升自己的尊严,达至主观意愿和实际再就业行为的统一。
第二,以再就业替代社会援助。以再就业替代社会援助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想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政府就曾以“以工代赈”的方式救助了城市大量的无业贫民,罗斯福的“新政”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基于失业者是社会援助主体的考虑,可以以提供工作岗位的方式发放社会救济。举例来说,可以把这部分救济金下放社区,由社区提供服务岗位给受助者(如清洁、保卫等很灵活的岗位),受助者通过工作而拿的工资,虽然在量上等同于领取的“救济”,但对于社会和个人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工作的完成是受助者的主动选择,而不再是为领取社会援助而必须要做的规定任务。以再就业替代社会援助,在个人实现了其工作的主观意愿,是以劳动换取报酬,无耻辱感和挫折感;在社会则鼓励了劳动,也得到了受助者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丧失劳动能力的受助者不在此计划内。
第三,引导经济理性的原则。受助者社会援助和再就业的实际选择往往基于经济的考虑,那么,社会援助和再就业的制度构建必须建立在经济合理性之上,体现“劳动者总比不劳动者收入要高”的基本原则。最低生活保障金、下岗生活费、失业救济的水平低于最低工资的幅度要足够大。建议对受助者的再就业给以所得税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