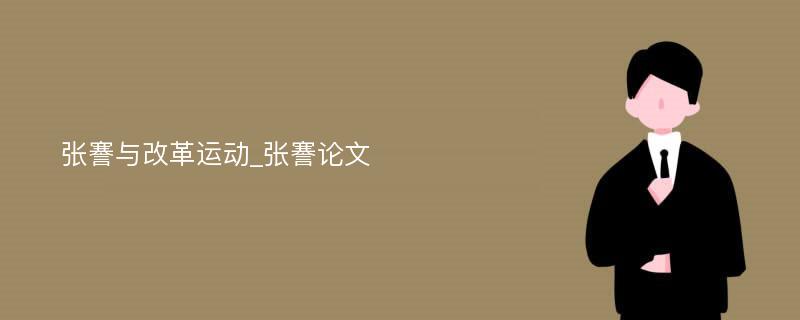
张謇与维新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新运动论文,张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K256.5
在19世纪末年,张謇是一位“状元实业家”,东南绅商界领袖人物;而维新运动则是一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严重的思想和政治斗争。探讨张謇与维新运动的关系,既有助于全面评价张謇,又有助于深刻认识维新运动。
一
关于张謇对1895—1898年间维新运动的态度,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他抱着冷淡、怀疑的态度,有的则断言他的态度是支持和赞助。揆诸史实,这两种说法既有其合理因素,又不无偏颇之处。他的真实态度,似乎可以用“若即若离”四个字加以概括。所谓“若即若离”就是既有联系,又有距离,请看下列史实。
1.营救康有为
维新运动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依靠帝党的支持而鼓动起来的。早在1889年张謇就与康有为相识并有往来。张孝若记其事说:
光绪十五年我父到京的时候,康也在京,其时相识,很有往来,康并且还做了好几首诗送给我父,表示他的钦迟。但是我父看了康的居处,见客排场很大,意气过嫌豪放,不大平正,心里很不赞成,所以他尽管送诗,我父都没有回答。(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137、84、136页。)
张謇对康有为尽管印象不佳,但在1894年仍然参与了营救他的活动。是年给事中余晋珊弹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鉴于康有为处于危难之中,“沈子培、盛伯熙、黄仲弢、文芸阁有电与徐学使琪营救,张季直(按指张謇)走请于常熟(按指翁同龠),曾仲伯亦奔走焉,皆卓如(按指梁启超)在京所为也”。(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4 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28—129页。)
2.列名强学会
1895年8月在家乡守制的张謇专程到南京拜访两江总督张之洞, “论下不可无学,学不可无会,若何实地进行”。(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第854、858、859、861、858页。)无独有偶,当时康有为也正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谋“合大群”、“开知识”、“开风气”,推动变法自强,“主之者内有常熟,外有南皮(按指张之洞),名士会者千计,集款亦数万”。(注:谭嗣同:《致欧阳中鹄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568页。)10月康有为赴南京拜访张之洞,并获得他的赞助,于11月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张之洞幕僚、张謇友人梁鼎芬电邀张謇共襄盛举:“现在中弢(按指黄绍箕)、长素(按指康有为)诸君子在沪开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南皮主之,刊布公启,必欲得大名共办此事,以雪国耻,望速复。”(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374—375页。)张謇赞成组织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以“雪国耻”,因而欣然同意列名发起,并且声称“中国之士大夫之昌言集会自此始”。(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 年版,第854、858、859、861、858页。)
3.介入《时务报》
1896年初,北京强学会被劾遭禁,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是年 8月,在上海强学会的基础上,创办《时务报》。《时务报》由张之洞亲信汪康年任经理,康有为高足梁启超任主笔,以传播西学、鼓吹“变法图存”为宗旨。(注:汪诒年:《汪康年年谱》,《戊戌变法》,第4 册,第204页。)“一时风靡海内外,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 梁启超“著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时务报的言论,两书可为其代表,前者为救时之政治主张,归结于变科举、兴学校,后者为救时之学术主张,归结于中西学并重”。《时务报》的经费张之洞“与有力,因时讲民权,张颇干涉之,致有冲突之时”。(注:杨复礼:《梁启超年谱》,《戊戌变法》,第4 册,第171—172页。)张謇对《时务报》既有赞誉,又有批评。1896—1897年间,张謇两次致函汪康年,谈及《时务报》问题。一则说:“别久甚相忆。读时务报,快如面谈,积怀为之一散,官民之情不通,天下事无可为者。”(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3页。)一则说:“如所议增董理监管报事,窃谓不便”,“下走所虑报馆之衰,在议论渐弱,不逮初时之精彩,宜设法振起而扩张之。如人人言宜伸民权,而海内名人,自南皮以下,尚言须保君权,以为此为下不信之义,走以为所恶于君权者,官毒害之也。欲保君权,须先去官毒,官毒不藉君权不横,而二事实不相关,可以此议透发一篇,请质之卓如以为如何?”(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4页。)由此可见,张謇关注《时务报》的动向,赏识通“官民之情”,反对“增董理监管报事”,担忧“议论渐弱”,主张“设法振起而扩张之”,在有关“保君权”与“伸民权”的争论中,则站在“保君权”一边,但与张之洞稍有不同,认为“欲保君权,须先去官毒”,“官毒不藉君权不横”。
4.匡赞上海女学堂
1897年夏,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会同梁启超、郑观应、康广仁等筹议并报请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培养维新人才,“以翼中国自强本计”(注:经元善:《中国女学堂缘起》,《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 对于这所女子学堂,张謇不仅是“在事集议者”(注:经元善:《中国女学堂缘起》,《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181页。),而且“允为局外竭力匡赞”(注:杨复礼:《梁启超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73页。)。
5.著文宣传变法应以“吏治民生是务”
1896—1897年间正当维新运动由北京、上海向全国各地扩展的时候,张謇相继撰写了《论农会议》、《论商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和《请兴农会奏》等论著,认为“农务、商务者,民生得丧之林,即吏治修坠之镜,日言变法,而不于吏治民生是务,未见其有益矣”。(注:张謇:《论商会议》,《张謇全集》,第2卷,第11页。 )他主张效法西方,在各行省设立农会、商会和工会,“实办”商务,“开导”工务,“振兴”农务,“听民自便,官为护持,则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器制造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也”。(注:张謇:《论商会议》,《张謇全集》,第2卷,第11页。 )张謇在这里不仅提出了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案,而且明确提出了整顿“吏治”乃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保证,而所谓整顿“吏治”,就是他所倡导的“去官毒”,以“保君权”。
6.为翁同龠出谋献计
翁同龠是光绪皇帝师傅,亲信重臣,时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甲午战后,倾向变法,断言“不断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注:翁同龠:《致子京》,《翁松禅墨迹》, 第3册,商务印书馆1917年影印本。)他鼓励引导光绪皇帝藉助维新派变法图强,因而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张謇既是“翁门六子”之一,又是以翁公为首的帝党中坚。1897年正在家乡守制的张謇在《致于恒斋函》中表示:“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藜州原民视水火之义,因常闻之而识之矣。凡夫可以鼓新气祓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事,无不坚牢矢愿奋然为之,以为是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也。即使入都,所欲效者不过如此。”(注:《张謇全集》,第4卷,第528页。)翌年四五月间,正当维新运动渐趋高涨之际,张謇毅然入都销假,意在做些“鼓新气祓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事”。他在京期间,多次拜访翁同龠,“无所不谈”(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为翁同龠出谋献计,现将已知内容列举如下:
其一,张謇向翁同龠提出变法所应遵循的原则。他说:“法刓则必变,有可变者,有竭天下贤智之力而不能变者矣。”(注:翁同龠:《致张謇》,《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上海有正书局1926年影印本。)所谓“可变者”系指“吏治民生”,“不能变者”显系封建纲常名教。对此翁同龠表示“雄论钦服”(注:翁同龠:《致张謇》,《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上海有正书局1926年影印本。)。
其二,张謇向翁同龠提出某些具体革新建议。诸如:请求停办间架税即按铺面大小额外征收的商业税,认为“间架税甚于昭信票之弊”;“上标本急策,曰‘商工农’”;“作留昭信票款于各省办农工商务奏,并请免宁属米粮捐”;“作‘农会议’、海门社仓滋事略”;“拟大学堂办法:宜分内外院。内院已仕。外院未仕。宜分初中上三等。宜有植物、动物苑。宜有博学院。宜分类设堂。宜参延东洋教习。宜定学生膏火。宜于盛大理允筹十万外,酌量宽备。宜就南苑择地。宜即用南苑工费。宜专派大臣,宜先画图。”(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408—410页。)翁同龠 看过张謇“各种说帖”之后,称赞张謇“的是霸才”、“毕竟奇材”(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其三,劝说翁同龠尽快离京返乡。6月10 日张謇亲眼看过翁同龠遵旨“所拟变法谕旨”(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410页。)。6月11日光绪皇帝将这份谕旨颁布天下, 史称“定国是诏”,以此为标志,百日维新正式揭幕。不料就在“定国是诏”颁布后第四天,翁同龠竟被开缺回籍。张謇在日记中写道:“见虞山(按指翁同龠)回籍之旨,补授文武一品及满汉侍郎,均具折谢皇太后之旨,亲选王公贝勒游历之旨。所系甚重,忧心京京,朝局自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是时城南士大夫人心皇皇。”“‘奉送松禅老人(按指翁同龠)归虞山’,引朱子答廖子晦语,劝公速行。”(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409页。)他用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的故事,劝说乃师及早退出政争漩涡返乡避祸。
7.一再劝说康梁“勿轻举”
张謇在自订年谱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至是张甚,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 第854、858、859、861、858页。)
张孝若解释说:我父“那时候在京,已经听说康等有不很审慎的变法,我父不赞同这种轻举,所以见面也曾经竭力劝过;既然劝过,自然不会预闻他们的策画,他们当然也不引我父为同志”。(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137、84、136页。)张謇父子笔下的所谓“轻举”,似指“用激烈雷霆式的手段来变法”。(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137 、84、136页 。)他们主张“在不流血、不纷争的状态范围以内,循序改进”,是一种“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137、84、136页。)
8.避居东南而关注变法
自从见到翁同龠开缺回籍谕旨以后,张謇预感到“朝局自是将大变”,因而“忧心京京”。他怀着怨愤与恐惧的心情,面对变幻莫测的政局,决意尽快离开京城,避祸自保。他在离京前夕,既“作学堂奏”,又“作辞寿州(按指孙家鼐)奏派大学堂教习启”(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411页。),这说明他仍然寄希望于锐意变法的光绪皇帝能在兴学育才方面有所作为,但却不愿出任大学堂教习而滞留政争漩涡。他返回南通之后,在艰难的筹办大生纱厂的同时,像翁同龠身“在江湖,心依魏阙”(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样,关注着北京政局和变法命运。在百日维新期间,张謇有几次活动值得注意。其一,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设商务局、商会,各省之有商务局、商会,始此”。刘坤一推荐张謇“总理商务局、商会”,张謇先辞后就。(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第854、858、859、861、858页。)其二,“唐侍郎景崇以经济特科荐”,(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第854、858、859、861、858页。)张謇未辞亦未就。其三,光绪皇帝谕令变通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之后,张謇在《经义徵学序》中写道:“罢科举而兴学校,置经义而事士农工商兵各专科之学,为中国今日计,圣人复起,无以易之。而朝廷功令废声病对偶之文,犹复慄唐宋试法之旧,则以纳约自牖,靖天下士子无耳目震扰之嫌,而非以经义为至善止也。”(注:《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215页。)其四,“闻南皮奏上《劝学篇》,意持新旧之平,而何启讦其骑墙,徐桐咎其助新,人尽危矣”。(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 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第854、858、859、861、858页。)
9.戊戌政变后的表现
戊戌政变后,翁同龠“益战慄罔知所措”,并表示“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不敢与往来,……阙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和乃师一样,张謇也竭力洗刷嫌疑。他在自订年谱中写道:“得彦升、眉孙讯,闻政府罗织党人,甘陵之祸将及,属远避。余与康梁是群非党,康梁计划举动,无一毫相干者,内省不疚,何忧何惧,谢之。”(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第854、858、859、861、858页。)他在得知戊戌六君子被害的噩耗后,竟然攻击说:“谭好奇论,居恒常愿剪发易服效日本之师泰西,不知波兰、印度未尝不剪发而无补于亡也。又常创杂种保种之说,谬妄已甚。林旭喜新竖子。杨故乙酉同年,平时修饬,见赏于南皮督部,不知何以并罹斯劫?”(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414页。)除了洗刷嫌疑,张謇还为刘坤一代拟《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大意请曲赦康梁,示宫廷之本无疑贰”(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 年版,第854、858、859、 861、858页。),既请保护光绪皇帝,又“请曲赦康梁”,说明张謇忠于光绪皇帝并同情康梁。鉴于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张謇深感失望,决意另谋出路,他致函汪康年说:“新政殆无大指望,欲合三数同志,从草堂下手,以海滨为基础,我侪所能为者止于如此,公以为何如?”(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5—1806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张謇对于维新运动,既有支持,又有反对;既有关联,又有距离。张謇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与翁同龠、张之洞、刘坤一对维新运动的态度极其相似,因而他们在维新运动中,彼此设法关照、沟通情报,甚至密谋对策。张謇的言行,不仅有时或多或少的带有张之洞、刘坤一,特别是翁同龠的某些思想印记,而且有时与翁同龠共进退,与张之洞、刘坤一配合默契。
二
张謇对维新运动的态度,所以“若即若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特定的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张謇的阶级地位、思想状况是内因,而外因则是以翁同龠为首的帝党、以张之洞、刘坤一为代表的洋务派和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制约。
张謇自称“家世业农”(注:张謇:《海通蚕桑兴衰事略复汪穰卿》,《张謇全集》,第3卷,第759页。),“窭人而兼腐儒,忽为实业公仆”(注: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提议书》,《张謇全集》,第3 卷,第91页。)。他原本是一位具有忠君爱国思想的封建士大夫,深谙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甲午鼎甲榜首,乙未虽然由于外来侵略的强烈刺激与西方文化的侵润潜移,而“弃官从商”,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但却“言商仍向儒”,始终未能摆脱绅士地位和儒学意识。韩愈说过:“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注:韩昌黎:《与干襄阳书》,《韩昌黎全书》,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7页。)张孝若认为乃父所以“能享大名显当世”,正是得益于“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的翁同龠与刘坤一的鼎力扶持。他说:“我父先前没有翁公,成名没得这样大;后来没有刘公,成事没得这样快;翁、刘二公着实是我父的真实知己了!”(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 137、84、136页。)。 张孝若的这种说法,虽然反映了某些历史真实,即没有翁同龠的奖掖,张謇难以大魁天下;没有刘坤一的提携,张謇难以推进实业;但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这就是张謇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转移到资本主义方向的驱动者,并非是翁公和刘公,而是被誉为洋务派殿军的张之洞。翁公所以奖掖张謇,是为了增强帝党的声势,刘公和张之洞所以提携张謇,旨在藉助张謇的绅士地位“贯通”“官商之气”(注:张之洞:《筹设商务局片》,《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册,第782页。),以便合官绅商之力,稳定秩序,振兴实业。当然,他们之间的这种“真实知己”的特殊关系,是有其相似的阶级和思想的根基的。他们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渡时代。他们适逢其会,成为“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注: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 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 页。)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他们,而他们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他们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具有改革精神,他们的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开拓和因循并存。他们对甲午战后兴起的变法浪潮,有着基本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其一,他们都认为中国非变法无以图强。翁同龠说:“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张之洞认为“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注: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75页。)“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也”。(注: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76页。)张孝若说乃父“看了当时宫廷的纷乱,亲贵的昏聩,内政处处腐败,外交断送权利,越看越痛心,也认为非改革变法不可”。(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137、84、136页。)其二,他们都坚持“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翁同龠对光绪说:“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写道:“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亡羊。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注: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44页。)正确的作法,是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的政艺之术。张謇认为张之洞的《劝学篇》“本旨专持新旧之平”,近似“骑墙”,而非“全是康说”的“助新”(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 卷,第433页。)之作,是值得称道的。张謇在1897 年撰写的《江生祖母七十寿序》中,论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说:“今外夷之所谓政治律例公法格致植物农商医化重电光气之学,其法駴荡耳目,而其意常与三代秦汉圣人贤豪之言,往往而合。謇尝欲得渊颖有志识之士数十辈,端本经训,而各颛其一二家之言,以待世变而应天下之所乏。生才而有志,比且从事彼族之学,规揽要领,以当于用,而明我三代秦汉圣人贤豪之言。”(注:《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342页。)其三,他们认为法“有可变者”,有“不可变得”。“可变者”系指“吏治民生”,重点在于振兴实业、发展教育之类。1895年张謇代张之洞拟定《条陈立国自强疏》,张之洞将全疏一分为二,并对文字稍加润色,而以《吁请修备储才折》和《致总署》的形式上奏。他们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反对“因循游移”,力主学习西方,设法补救,以期中国自强自立。他们提出“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等九条建议,“愿圣明决而行之”(注:《张謇全集》,第1 卷,第29—41页。)。这些建议大多并未超越甲午战前洋务新政范围,唯有“速讲商务”和“讲求工政”两条,反映了时代发展趋势,具有崭新社会内涵。他们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他们认为传统的“农本”思想无力扭转中国的贫弱现实,而只有大兴“工艺”,才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所谓大兴“工艺”,并非复兴传统的手工作坊式工业,而是开创全新的近代机器大工业,而以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生产,正是中世纪跨入近代社会的显著的物质标志。他们主张在各省设立工政局,加意讲求,“招商办厂”。他们虽然不赞成“以商立国”,但却十分重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主张效法日本,“专讲精造土货、自运外洋两端”,“商本亏累,则官助之”,在各省设商务局,“维护华商,渐收利权。”由此可见,他们把变法的重点放在“民生”方面,旨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富民强国”。他们所谓的“不能变者”,显然是指封建纲常名教而言。张之洞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注: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75页。)而其核心则是不能以民权取代君权,“保君权”,反对“伸民权”,可以说是张謇、翁同龠、张之洞、刘坤一的共同信条。其四,他们反对“激烈雷霆式”的变革,而主张“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他们之所以主张“渐变”而反对“骤变”,首先同他们的性格和地位有关。张謇直到中年才大魁天下,喜得骄子,因而自称“生平万事居人后”(注:张謇:《戊戌正月十八日儿子怡祖生志喜》,《张謇全集》,第5卷(下),第107页。)。世态炎凉的磨难,科举仕途的坎坷,创办实业的艰辛,使得张謇谨言慎行。翁、张、刘三人则由于位高权重、宦海沉浮、老于事故,因而处事稳健有余而势头不足,虽倾向变法,而实主持重。其次由于他们深知宫廷的内幕和变法的艰难。维新运动是一场帝党和后党、维新派和守旧派围绕着权力再分配和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问题而展开的殊死斗争。帝党和维新派所依靠的光绪皇帝,虽然年青有为、锐意变法,但是并无实权,而反对变法的后党和守旧派所拥戴的西太后,却老谋深算,大权在握。这显然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翁同龠对康有为说:“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巡数之者,故吾见客,盖有难言也。”(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2页。)张謇在《致吴彦复函》中对此作了更为透彻的剖析:“下走固言天下纷纷,当轴无人主张国是,其下建言者更苦矣。请上亲政为第一义,三尺童子知之矣。然上方在群顽固之掌中,如足下诸公所为,能使反掌而脱之乎?抑尚许天下人多其途以效策乎?五洲变法之速,无逾日本者。彼变法之人,皆有行法、立法之权者也,然尚二十年而小成,三十年而大效。其初变法之日,七局之首曰神祗,又有学习院、户山学校,何为者?足下与日本士大夫习,曷讨求当日之用意也?而□□也。”(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 43—44页。)张謇既深知光绪皇帝“方在群顽固之掌中”,实难有所作为;又鉴于日本“变法之人,皆有行法、立法之权者”,而变法尚且经过二三十年始有成效,因此断言中国变法只能“循序改进”,绝不应急于求成,“挟至锐之气,取一切之法而更张之”。
总而言之,张謇与张之洞、刘坤一,特别是翁同龠,既有着近似的阶级特性、密切的政治联系、深厚的个人交谊;又对维新运动有着基本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因而他们在维新运动中,彼此设法关照、沟通情报、密谋对策,张謇有时与翁同龠共进退,与张之洞、刘坤一配合默契,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与此相比,张謇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关系,就有着明显的不同。张謇曾说:“余与康梁是群非党”。所谓“是群非党”,可以说是张謇与康梁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他们原本都是封建士大夫,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不同的是,张謇起步较晚,仍然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康梁起步较早,业已立足于资本主义。封建色彩较浓的张謇隶属于以翁同龠为首的帝党阵营,并且依托于张之洞、刘坤一两位洋务派殿军。资本主义色彩较浓的康梁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首领,他们与帝党结盟,依靠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活动。正因为如此,张謇同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变法问题上,就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又存在着原则性分歧。他们之间相同或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其一,他们都认为变法是时势使然,中国非变法无以图存;其二,他们都认为变法旨在“富民强国”,因而必须改变“农本”思想,“以工立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农商业;其三,他们都认为变法之本在于培养人才,因而必须变通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其四,他们都认为变法事体重大,必须依靠皇权自上而下进行。他们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主要表现在:其一,张謇、翁同龠等认为“法刓必变,有可变者,有竭天下贤智之力而不能变者矣”。康有为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在听到光绪皇帝“今日诚非变法不可”的说法后,立即表示:“近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45页。)其二,张謇钟情于“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而康梁等则倾向于冲破“中体西用”防线,构筑起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理论模式,“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32 页。)其三,张謇反对“伸民权”,主张“去官毒”而“保君权”。康梁起初主张“伸民权”,而反对“保君权”。但当他们一经接近清朝中枢政权,就立即改换调门,正像梁启超所说的:“中国倡民权者”以康有为为首,“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旨在“以君主之权,行民权之意”(注: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第4册,第34页。)。 当然,康有为的这种转变,并非是放弃民权,而是以退为进的权宜之计,最终目标,依然是改变君权“乾纲独断”的局面,“立宪法,设议院”,实行“君民合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其四,张謇主张变法应该是“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而康梁等则“用激烈雷霆式的手段来变法”,主张“扫荡桎梏,冲决网罗”(注:谭嗣同:《致汪康年书》,《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3页。)。 康广仁也批评乃兄“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并说乃兄“亦非不知,以为死〔生〕由命,非所能避。”(注:康广仁:《致易一书》,《康幼博茂才遗稿》,第1页。)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决定了张謇对维新运动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有利于维新运动的开始兴起,却不利于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从而表明当时张謇尚未作为一名“志同道合”的同志而跻身于维新派的行列,还只是一位刚刚把人生道路转移到资本主义方向、在政治上属于以翁同龠为首的帝党阵营、在思想上倾向于张之洞、刘坤一两位洋务派殿军的进步人物。
标签:张謇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刘坤一论文; 劝学篇论文; 张之洞论文; 康有为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八国联军论文; 甲午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