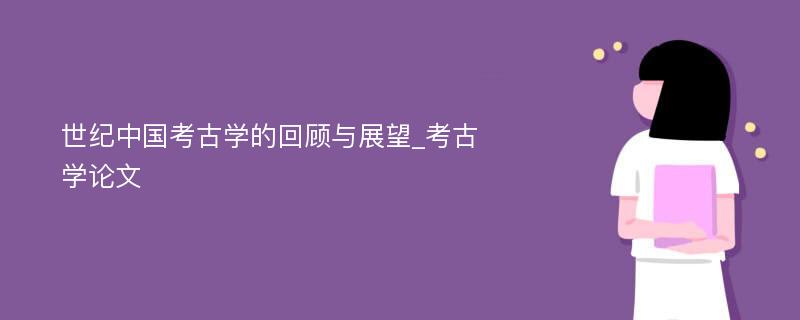
中国考古学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在热战和冷战中度过的。在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人们终于争来了能憧憬更美好未来的和平与发展的局面。在此世纪转换之际,我们这些从事考古学的人们,不时地出现了前瞻性思考,或禁不住要问:21世纪的考古学将会是怎样的?我们都不是预言家,未来的事情不好预测。不过,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深藏于对往昔的回顾和对今日现实的审察之中。因此,为了思考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还得从这个学科的昨天和今天谈起。限于篇幅,尤其限于个人能力,在检讨这一问题之前,我想作如下的说明:
这里将要讨论的中国考古学,不包括香港和台湾两地的中国考古学,也不含国外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是指中国大陆境内的中国考古学。这是一个界定。
同时,无论是作为大陆境内的中国考古学的援手学科,还是被大陆境内的中国考古学所渗透的学科,范围都十分广大,在一般情况下,本文均不涉及。这是第二个界定。
再次,大陆境内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早已进入宋元时期,而本文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基本上限于先秦,且只作些鸟瞰。这是第三个界定。
在此三个界定的前题下,对所拟题目,作些讨论。
一 以往走过的路
关于这一问题,我在《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提出过这样的认识:
“观察中国考古学产生以来至今的过程,可认为以下事件表述了中国考古学前进与发展的主流,它们是:
1.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发掘;
2.1931年,梁思永揭示的后冈三叠层;
3.1948年,苏秉琦发表的《瓦鬲的研究》(是1940年写成的《陕西宝鸡斗鸡台所得瓦鬲的研究》一文的摘要,刊《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4.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刊《考古》1959年第4期);
5.1975年,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学术讲演(《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6.1985年,苏秉琦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讲演(《辽海文物学刊》创刊号,1986年)。
这样,以往的中国考古学已走过了五个时期,今天正经历着它的第六个阶段。”〔1〕
中国考古学的过去与现在,学者选择研究方向的歧异,学者之间认识的歧见、研究的深浅、水平的高低以及学科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是恒见的现象。我的上述意见,没有涉及考古学史应该涉及的这些问题,讲的只是中国大陆考古学的主流对学科具有导向意义的重要实践,或对研究对象内在规律的理论揭示,而可作为考古学史分期标志的重大科学事件。这六个阶段,是中国大陆考古学对学科内在发展逻辑的揭示过程,是学科承前启后而具有质变阶段性意义的历史演变。我对中国大陆考古学以往走过的道路的这些认识,是在1993年提出来的。距今已过去了4年,在世纪之交的今天, 中国大陆考古学的发展仍未出现新的质的变化。我自认这些见解,尚合时宜。
在以往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我对这些作为考古学史分期标志的重大科学事件的作用与意义,进行过一些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从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的角度,来评估那些具有考古学史分期标志的重大科学事件的意义,故未言及包含揭示后冈三叠层的殷墟发掘和包含《瓦鬲的研究》的斗鸡台的发掘。这并非忽视这两项发掘工作的意义。在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一方针指导下,并由他策划的殷墟发掘,向世界展示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灿烂的商代后期文明,奠定了商史研究的基础,同时把中国考古学的发掘及研究水平推进到当时世界的先进行列,引起了世人的注目。斗鸡台的发掘,确立了西周和先周的考古学分期,揭开了先周文化研究的序幕,证实了周人和商人属于不同的文化谱系。无论是从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和对以后的学术传承产生的影响,还是从对当时史学研究的推进和确立考古学在整个史学中的作用及地位来看,这两项考古发掘工作,尤其是殷墟的发掘,冲破了时代的藩篱,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是仰韶村的发掘难以比拟的。
大家知道,中国考古学者一贯认为:中国考古学是广义的中国史学的一翼。那么,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形成与发展,在这广义的中国史学中起着什么作用?占怎样的地位?它对狭义史学有什么作用和意义?这是我想在这里讨论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不仅大,且是动态的,实不易说清楚。我这里只能讲点个人的认识,目的是引起讨论,祈求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国的传统史学,是通过文字资料研究历史的狭义史学。金石学只是这个史学的附庸。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之交,基于我国社会的变革和西方进步思想的传入,传统史学出现了近代化的趋势,随着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兴起,加快了变革传统史学的步伐,在20年代,当中国思想史上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奏演变为科玄论战的时候,中国古史领域涌现出了新的态势:一是疑古风潮的兴起;二是以仰韶村和周口店的发掘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前者侧重于“破”,后者侧重于“立”,同时对传统史学展开了勇猛的进攻,古史研究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疑古”廓清了经籍中的关于古代的荒谬传说,使三皇五帝的神圣地位失去了依据,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古史研究起了进步的作用,然而,却不能建设起一座真实的古史大厦。同时,“疑古”往往疑过了头,从疑经籍走到了疑人疑事,诚如杜正胜所说的“历史研究本来只能就少数留传下来的史料论证其史实,也就是据史料之‘有’而说‘有’的史事,不能因为史料不传而断定必无其事”〔2〕, 或如傅斯年所指出的“古史者,劫灰中之烬馀也。据此烬馀,若干轮廓有时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多矣。以不知为不有,以或然为必然,既违逻辑之戒律,又蔽事实之概观,诚不可以为术也。今日固当据可知者尽力推至逻辑所容许之极度,然若以或然为必然则自陷矣”〔3〕。 故史学随同“疑古”步入了“迷茫”。
而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则打破了以文献为研究对象和附以金石学的狭义历史学的治学传统,开拓了新的史学领域,导致广义史学的产生,并同“疑古”一道促进了史学的近代化。至迟到30年代,在广义的史学中,考古学已成了一相对独立的学科,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到30年代中期,考古学者已作了大量的田野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产生了一些新的学术认识,现摘要说明如下:
在铁器时代,对一些城址进行了调查与勘探,并发掘了燕下都,认识了东周城址的规模和某些城址的文化面貌。在青铜时代,除通过殷墟、辛村卫国墓地和斗鸡台的发掘,揭示出较为完整的灿烂的商代后期文明,奠定了商史研究基础,认识商周属于不同文化的谱系,并确立西周和先周的考古学文化分期外,还开始了商文化起源的探索,并认识到除商周青铜文明外,中国境内还存在诸如辛店、寺洼、沙井和鄂尔多斯青铜器以及被后来区分出来的夏家店下、上层文化这类青铜时代的遗存。于新石器时代及铜石并用时代,认识了仰韶、齐家、马厂、良渚、龙山和以昂昂溪为代表的这些相互区别的文化遗存,展开了仰韶与龙山文化相互关系以及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讨论。在旧石器时代,除发现在世界引起轰动的中国猿人及其遗存外,还在北京周口店和东北、内蒙古及甘肃见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墓葬及其他遗存,开始认识到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区别于欧洲,中国猿人的一些体质特征亲近于蒙古人种的事实。所有这些发现及研究成果,基本上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遗存年代序列,显示出中国古代文化与文明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与境外同时代的遗存相比,均具有自身特征,在某些方面又存在一些类似性,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的普遍注目,提出了“东西夷夏说”,并在30年代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论战中被广泛引证,从而使史学超出了“疑古”,走出了随“疑古”俱来的“迷茫”,依靠考古学,史学走上了重建古史的康庄大道。
二 走向未来的起点
中国考古学从未停滞在30年代。前进的路,尽管曲折、崎岖、险峻,但总有人攀登。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中国考古学者仍推进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从1949年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来,中国考古学无论在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方面,还是于学科的理论建设以及学者个人学术素养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见的进步,完成了重建古史的基本任务。现就个人的理解,作些提要式的说明:
(一) 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化。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智人化石,已具备了蒙古人种的基本特征,可称为原始蒙古人种。他们的某些体质特征,例如铲形门齿,上可追溯到猿人,下与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相联系。旧石器文化可分为南、北两大文化谱系,北方又可分为两个亚系统。在河北、湖南、江西及广西发现的几处超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从文化上还不能说明它们和旧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直接传承关系,但可推定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从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同时,据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的谱系差异来看,可以估定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转化或演进,无疑是多元的。
(二) 基本上搞清楚了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编年,探明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与辽河流域及燕山南北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谱系。它们的源头,均可追溯到公元前五~六千年。这些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至迟从公元前五千年起就存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交往愈益密切,以致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周秦实现政治统一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三) 关于生产技术与经济,考古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下面述及的一些认识。
其一,导致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化,是经济的发展。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实现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同时,发明了粟或稻作农业。据有关资料及稍晚的情况推知,这类农作物在当时人们的食物结构中,仍只占很小的比重;食物的基本来源,仍依靠渔猎和采集。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乃至辽河流域的较早甚或晚至公元前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尚过着渔猎生活。无疑,可推定他们的祖先是靠渔猎生活。无疑,可推定他们的祖先是靠渔猎经济的提升,实现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转化的。可见,种植农业的出现或农业革命,不是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转化的唯一前题,同时,即使在那些发明种植农业与旧石器转化为新石器时代发生联系的居民经济中,在很长时间内,种植农业也未处于重要地位。不过,应指出的是,如果种植农业发明的意义,在发明的当时不那么显著甚至还相当微小的话,那么,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则愈益显突出其重要地位了。
中国在世界少数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占了粟作和稻作两个。在公元前六千年居民的生活中,粟作农业已占据了相当的地位。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可追溯到公元前一万一两千年前,公元前四千年的稻作遗迹已被考古学家揭示出来。同时,在汉水上游及淮河流域的公元前第六千年的老官台文化及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稻壳痕迹或稻粒印痕和炭化稻谷及稻米,说明早在此时稻作农业已开始自南向北传播。
其二,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使人们认识了磨光、穿孔、制石及治玉工艺的演变过程。直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还普通地使用打击方法制作石器,但这时期的山顶洞人,却发明了磨光、穿孔的技术,不过,只限于加工石质饰品而已。直到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长江中游的蛤蟆洞中,与最早陶器伴存的仍是打制石器。可见,以磨制技术加工石质生产工具的出现,很可能晚于陶器的发明。至少长江中游是这样。换言之,使用打制石器而发明了陶器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一个类型。同时,被学术界列入新石器时代的河南许昌的灵井和陕西大荔的沙苑发现的既未见磨光石器,又无陶器的遗存,当属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另一种类型。看来,无论是陶器,还是磨光石器,都难以认作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的标志。
公元前第六千纪,出现的切割石材的技术,经过不断的改进,到公元前四千纪晚期,线割石材技术广泛流行,双面钻孔技术发展到了顶峰。此时,整体抛光、棱角清晰、刃口锋利及双面钻孔的石器广泛流行起来。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单面钻孔替代了双面钻孔的技术。至此,制石技术发展到了顶峰,此后,似乎再难见到如此时那样精致加工的石器了。
公元前四千纪晚期,基于社会需要和制石工艺提供的技术,治玉工艺发展起来,形成了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两个玉文化中心。这时期的治玉,已运用了切削、阴刻浮雕、杆钻钻孔以及旋转机械工具琢磨及抛光的技术。这样复杂的技术,导致从石匠中分化出了专门治玉的匠人。
其三,关于制陶技术的发明与演进。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是蛤蟆洞和仙人洞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经[14]C测定, 两地陶器的年代,均为公元前一万二三千年。蛤蟆洞的陶器的陶胎分层,内外表皮均作糙面,显然是以某种质地的编织物作模或范,以贴塑法制作成型的。自此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各地居民均以贴塑法制作陶器,到公元前六千年,长江及黄河流域出现了泥条盘筑技术,辽河流域及广大东北地区则发明了泥圈套接法制陶技术。至公元前五千年发明了陶轮,半坡文化居民在陶轮上用泥条盘筑法制作陶器,然后轮旋加工口沿,使之造型规整。公元前第四千纪中期偏早,即西阴文化泉护遗址三期的居民,已用陶轮制作小型陶器了。从此,轮制陶器技术逐步推广,到公元前三千年初期前后,轮制制陶技术已相当普及。顺便说一下,这时期还出现了城,发明了水井和用于建筑的土坯。应指出的是,自此包括整个公元前第三千纪,自伊洛河以下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诸文化的轮制制陶技术的普及程度及轮制技术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公元前二千纪初期前后,吴越及百粤地区出现了用高岭土制作的印纹硬陶,到商代前期,吴越地区发明的原始瓷器,已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流传开来。在轮制制陶技术普及的同时,很可能已出现了制陶的专业家族,至于从制陶匠人中分离出来的制瓷专业匠人的出现年代,显然较此晚得多,具体年代,尚待研究。
其四,冶金技术的出现及其发展。这种比治玉、制陶更复杂的工艺,已在公元前五千纪悄悄地出现了。到公元前第四千纪晚期的马家窑文化、义井文化和红山文化,都掌握了制铜技术,采用了冶炼、范铸和锻打及戗磨技术制作铜器。从这时始,中国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在这个时代,整体抛光、棱角清晰、刃口锋利及双面钻孔的石器流行起来,治玉工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红山及良渚两个玉文化中心,轮制制陶技术已相当普及了,发明了水井和用于建筑的土坯。同时,社会分工获得了纵深发展,出现了制石、制陶、治玉、冶铜等专业家族或专业匠人。聚落分化了,出现了城,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出现了贫富分化,巫师和掌握军权的王成了社会的显贵。总之,这是个继旧石器转化为新石器时代之后,伴随着技术革命飞跃发展而来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往后,历经龙山时代技术的进步,至夏代进入了青铜时代。尽管目前我们只知道齐家文化经历了由纯铜发展到青铜和四坝文化东灰山居民经历砷铜到制作青铜的过程,但从夏时期不同谱系的诸考古学文化的铜制品型制存在的差异来看,可以认为中国制铜工艺的起源及其初步发展,当是多元的。夏代诸考古学文化的制铜技术水平,存在着差别。二里头文化最为先进,其次为四坝文化的火烧沟居民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再次为齐家文化。四坝文化火烧沟居民的制铜业,在四坝文化乃至陕甘宁青地区,就其技术发展水平来说,是一孤岛。它的存在,很可能与中西文化交通有关。商文化的青铜工艺显然继承于二里头文化。青铜工艺经历了商代前期的发展,到商代后期达到了鼎盛。周人承袭了商人的青铜工艺,同时,到西周后期,掌握了制铁术。中国炼铁技术的出现,很可能缘于中西文化交流,但由于已掌握了冶炼青铜的高度发达的技艺,使这一新技术获得了较快的创造性的发展。至春秋晚期,开始用固体还原法生产块炼铁,几乎同时发明了铸铁,战国早期出现了生铁脱炭农具,战国时期已能制作被认为是近代科学技术产物的球状石墨可锻铸铁。铁农具的出现,使五口之家这样的个体家庭可能独立地经营农业,导致井田制之被破坏,为实行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秦汉帝国的出现提供了前题。
其五,家畜饲养与主营畜牧经济居民的出现问题。中国古代居民饲养家畜始于何时,目前仍未搞清楚。最早饲养的动物,可能是猪、狗两种,其次是鸡。至公元前三千纪初期前后,水牛、黄牛、山羊和绵羊,都成了饲养的动物。从目前见到的资料来看,到龙山时代甚或夏代早期,才开始养马。半坡文化时期,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居民的肉食的主要来源,仍然来自渔猎业。到公元前第四千纪,家畜饲养业获得了发展,此期的西阴文化居民肉食的重要来源,似乎已能依靠家畜饲养业了。在公元前三千纪初期前后,甘青及东北地区的养羊业,增加了其在家畜饲养业中的比重。经夏代及商代前期的长城地带的某些居民的饲养业乃至畜牧经济发展之后,到殷墟时期,沿着长城地带自东而西便出现了主营畜牧经济,同时兼营农业的一些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从这些考古文化谱系观之,可知其来源有二:一是自渔猎居民转化而来。他们分布于长城地带的东部;另一是自农业居民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分布在长城地带西部。从这时期起,黄河流域的农业居民和长城地带的畜牧居民,以及长城地带牧民之间,相互长期地展开了拼杀、战争和经济、文化交流。张家口至大同这一地区,似乎具有三岔口地带的战略地位,是长城地带东、西部牧民之间,以及他们和黄河流域农民之间相互争夺的要地,同时,也是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正是这些活动,才较广泛地沟通了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而东西文化经常性、大规模的交往,则是自西汉打通西域之后的事。
(四) 基于考古学最近十多年来对宗教遗存研究的重视,使我们对宗教有了些新的认识。
人类社会的宗教观念出现很早,山顶洞人安葬死者,在尸体上撒些赤铁矿石,便是出于宗教信仰的行为。近十余年来发现的重要宗教遗存是:濮阳西水坡伴着用蚌壳铺成动物形象的墓葬,大地湾F411及其地画表现的行巫场面,福临堡的陶祖及石祖,牛河梁的“坛、庙、冢”,凌家滩M4随葬的玉质卜卦器具,反山、瑶山的祭坛和桥村H4的羊肩胛卜骨,等等。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期以前,中国诸考古学文化居民的宗教信仰,均还存在着一些区别。例如大汶口文化及以凌家滩M4为代表的文化,使用龟卜,桥村H4为代表的文化则用羊肩胛骨进行骨卜,而良渚文化则以“黄琮礼地”,等等。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文化交流乃至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融合,经过人们的选择,这些相异的考古学文化的宗教,便会聚起来而成为融合后的新考古学文化居民的共同信仰。换句话讲,上述那些公元前三千年初期前后的宗教遗存所反映的宗教文化,便是以后中国宗教信仰的源头之一,为后来宗教信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宗教信仰是科学不发达的产物,凡是科学占领不到的领域,往往是宗教信仰的所在。在此前题下,宗教信仰是人类所在的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辐射。自然界不仅不和谐,而且是不平等的。灾异威胁植物、动物及人类的安全,动、植物界存在着食物链,存在着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反映和认识自然界这类关系的宗教信仰,便是个不平等的世界。所以,在平等的社会里产生的宗教信仰的世界中,就存在着不平等,创造了超人类自身及自然而受到人类崇拜和侍奉的神。随着人们的神观念的发展,导致神权的产生和对沟通人、神的半人半神的巫师的崇拜。前面提到的公元前五千年濮阳西水坡伴着蚌塑动物和殉人的巫师墓葬,表明在远离王权出现之前的母权制社会时期的宗教信仰的世界中,就已存在神权和对巫师的崇拜。这在客观上为以后王权的产生提供了思想环境。以后的历史发展说明,那些最初为实现权力统治的代表性人物,便是从传统思想中请出了神权,加以宣扬、扩充,演出政教合一和王权神授这类魔术,以实践他们的权力。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说过:“每个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4〕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道教出现前,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宗教。 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是有宗教的,这就是起源很早而流传颇久的以敬天祭祖为中心的泛神教。崇拜、神化祖先,祭祖,无疑是社会和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现象。母权制时代,产生了对女性祖先的崇拜。父权制时代的红山文化居民祀奉女神,说明其时尚未创造出与现实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男神的同时,也反映出处于母权制时代的红山文化先民已有了崇拜女祖的宗教信仰。前面述及的福临堡的陶、石祖,则是迄今见到的崇拜男性祖先的最早的宗教信仰实证。李大钊说:“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5 〕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延续了二千余年,所以,敬天祭祖为中心的泛神教长久不衰。
(五) 考古学的研究,提出了关于古代文明的新认识。苏秉琦于1985年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演讲,是他继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之后,指挥中国考古学这支乐队,演奏出以“古文化、古城、古国”、“古国、方国、帝国”为主题的又一出新的交响乐,启动了从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汉专制帝国道路的列车,使中国考古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进入了黄金时代。从此,关于古代文明的研究,成了热门话题,使那些怀有成见或持异见的人也卷了进来。这一课题的讨论,正在向纵深发展,迄今取得的成果是:
其一,明确了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不同含义,认识两者既存在区别,又有着联系。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时代的概括”,“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6〕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同义语的观点, 已基本上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学界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文明形成的标志的认识上。有的学者认定城市、文字、金属器和仪礼性建筑,并以这些要素的综合为文明形成的标志。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由于已被公认的几个原生的文明古国各自都不同时具备这些要素,所以难以依此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问题。另外一些学者据“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提出“当祀与戎复杂到需要专人从事这职业,发展到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并且已被从事这职业的人予以控制的时候,便进入到国家的阶段”〔7〕的认识,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 文明起源是文明形成之前诸文明要素的孕育过程,故需在前国家或文明形成之前的社会中,求索文明的起源。
其二,关于文明形成于何时的问题,已突破了形成于夏代说,有些学者认为形成于龙山时代,有些学者认为更早,指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的良渚文化和同期即半坡遗址四期的黄河流域及长江中游的其他诸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文明起源及形成的不均衡性和“满天星斗”说,已基本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
其三,苏秉琦探讨了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不同道路或模式,中国同中国以外的世界文明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可区分为“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认为面向海洋和欧亚大陆的“中国两半块和世界两半块”是相互衔接的〔8〕。这些认识,虽有待深入论证, 却是发人深思的。
其四,关于古代文明社会的性质与发展阶段的问题,除有人坚持奴隶制社会说外,还有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先秦未经历过奴隶制社会阶段,杜正胜和日知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城邦制〔9〕, 苏秉琦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发育于发达的古文化,而经过“古城”、“古国”、“方国”,进入到秦汉帝国,论证了从文化的多元一体到政治上多元一统的发展过程〔10〕,而我则认为:包括西周在内的以前的文明社会的“基本内涵是:父权家族、贵族、平民、农村公社(井田制)、神权、王权、宗法制、礼制和分封制。这些内涵的损益及其形成的结构,表现出这时期社会的阶段性变化”〔11〕,而将其区分为半坡四期文化及其稍后时期,龙山时期或其后段,夏商时期和西周的四个阶段。
以上仅从重建古史角度检讨了我国考古学,尤其是它最近25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据此可知,考古学在改变自身面貌的同时,也使三代及其以前的历史研究的状况为之一新。可以说我国考古学已成为三代及其以前的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支柱。
至于考古学渗透于自然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及科技参与考古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则说明考古学已成了研究我国古代的最重要的学科。关于这些以及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进步,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讨论了。
三 对未来的希望与预测
我们已检讨了这学科的历史与现状。这里,还应指出的是:中国考古学的层位学及类型学的实践与理论,处于世界最高的水平。为了对未来中国考古学提些希望,我们于此仍需对这学科本身的局限性作点讨论。
考古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存在着天生铸就的和受制于一定时代科学水平的局限性。考古学是揭示、研究古代遗存及其呈现的时、空矛盾,并据此探讨人们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历史学科。由于考古学遗存是物质的,就难以研究人们非物质的,需要以文字、语言所表述的那些活动,只能探讨人们于物质的及其能体现的精神方面的活动内容,同时,目前的学科手段也难以确切地了解遗存所在的时、空,不能准确地说明留下遗存的那些人们当时所处的自然及人文的环境。只有如实地承认考古学的局限性,并清楚地分辨出哪些是天生铸就的,哪些是受制于时代科学水平的局限,但能依靠科学的不断发展而突破的,我们才能避免把考古学研究当作艺术的自由创作,避免幻想,才能对未来的考古学提出切实的希望,科学地预测它的未来。
这里对今后一二十年中的中国考古学,提出如下几点希望:
(一) 填补空白,加强薄弱环节。中国考古学现状存在如下四个不平衡,即:地区不平衡;同一地区对不同年代或文化遗存的研究不平衡;同期或同文化的遗存类型的研究不平衡;同类型遗存的研究水平不平衡。当务之急,是解决这些不平衡状态,填补空白,加强薄弱环节,对此试作如下说明:
其一,地区不平衡问题。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仍以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先进,西南及新疆相对落后,其他地区处于两者之间。这是就大地区而言。这类地区的不平衡,还可以细分之,如西南诸省之间的考古学研究又存在不平衡,在一省之内还存在地区或河流之间的不平衡,即使在考古学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区,例如陕西省的考古工作就存在渭河流域、汉水流域和陕北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等等。
其二,同一地区的不同年代或文化遗存的研究的不平衡。后进地区不必说,即使先进地区也广泛存在这类不平衡,例如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研究不如大汶口文化,岳石文化的研究又不如龙山文化;从后冈发现以后,河南省境内的龙山时代的遗存已发现了66年,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说不清楚河南省境内有几种龙山时代的文化以及它们分布的范围如何?等等。
其三,最后,再谈谈同期或同文化的遗存类型研究和同类型遗存研究的水平的不平衡问题。住地和墓地是任何同期或同文化遗存的基本类型。在这方面,只有半坡文化的住地和墓地都同时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至于其他同期或同文化遗存,往往不是仅仅揭示或主要研究了墓地,就是只研究了住址。而红山文化在注重宗教遗存研究的同时,却又忽视了住址和普通墓地的研究。其结果是使我们难以全面把握同期或同一文化的内涵。同类型遗存的研究水平不平衡的状况,也是广泛存在的。如同一类型的墓地,有的不仅搞清了分期,还明白了它的布局,探讨了其时的社会制度,有的则不甚了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发掘的260 座东周墓葬,虽不能搞清楚这些墓葬所属的墓地,但苏秉琦却在对这些墓葬作了分型、分期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东周社会的变化。然而,后此发掘的同时期墓地或墓葬的研究,都未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科学发展无止境。在解决旧的不平衡的同时,又将出现新的不平衡。不平衡永远存在。如果我们以现今先进水平为标准,在今后20年左右时间内把以上提出的几个不平衡问题解决了,中国考古学将出现崭新的局面。
(二) 两步并成一步走。所谓两步,是指“区、系、类型研究”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研究”,或“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这两个课题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前者是苏秉琦于1975年提出来的,后者则是他在1985年提出来的课题。这两个课题的提出为何存在着先后,自然与其时考古学发展水平有关。然而,自这两个课题提出来以后至今仍未解决或未基本解决考古学文化序列或谱系的那些地区,对这两个课题的探讨,可不必机械地仍旧分作两步走,应两步并成一步走。这样才能赶超先进地区。
两步并成一步走,不仅是出于需要,而且是可以做到的。因为解决考古学文化序列、谱系这类问题的研究,只用打一、二条探沟,甚至沿遗址的断崖切出适当的剖面的小规模发掘,就可以达到目的。例如苏秉琦在50年代初用清理断崖的办法,就探明了分布于渭河流域的西阴文化、客省庄文化和西周文化的先后顺序。解决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则需对考古学遗址做大规模的发掘,甚至全面的揭露。由于两者所需工作规模不同,加之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必定分布在一定地区,而这地区内的某些小区域的文化分布及结构状况,往往是其所在地区文化分布及结构的缩影,这就使我们能在选择一探索文明起源或形成的遗址或墓地并进行全面揭露的同时,对这小区域内的遗存进行调查和试掘,以了解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谱系。这种将“区、系、类型”和“文明起源与形成”结合起来做田野考古工作的方法,也完全适合于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1958~1959年的配合黄河水库工程中,我们在大规模和全面揭示泉护村遗址及元君庙墓地的同时,对渭南、华县作了较仔细的调查与试掘,结果除了探明了元君庙墓地反映的社会制度,也基本上搞清楚了这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谱系。
(三) 开展聚落群的研究,探讨聚落与聚落群的变异。聚落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传统,80年代以来,聚落考古得到进一步发展,但聚落群的研究,似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揭示聚落同期诸单位的布局,是聚落考古的基本追求。这里所说的同期,最好不是依类型学确定的同一时期,而是据层位学断定的同一地面。聚落群的研究,则是在探明聚落的前题下,探讨同一文化的同时期聚落分布及聚落间的关系,并据此求索由住居于一定数量聚落中的共同体组成的社群的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情况。这是进行聚落群研究的目的。
认定聚落群共时,是搞好聚落群考古的关键。这对三代及其以前的考古学来讲,比起探明聚落内诸单位同期更难。确定聚落共时的最可靠的证据,是聚落间交往的物件和交通聚落间的道路。这类证据很难被保存下来,即使保存了下来,也不易被发现或难以做工作。目前主要是依据碳十四测年和类型学研究,以确认聚落的共时。前者机率过小,不易认定被研究的聚落是否真实共时;后者虽可靠一些,但在类型学确定的期别中,有的期别的年代较长,据此定为共时的聚落,有的实非共时。这是从事聚落群考古时必须注意的。搞清楚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和同一谱系的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聚落与聚落群,就明白了它们的空间变异和时序变迁。聚落形态、内涵、结构与布局和人们所在社会的经济、人际关系及意识形态乃至生态环境,均存在密切联系,故聚落与聚落群的研究,能从整体上把握一聚落居民社会经济、文化,人际及人与生态环境,同一文化同时期居民社群的关系以及同一文化或同谱系的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居民社会的历史变化,不同谱系的诸考古学文化的生态环境、社会现象及社会结构的异同及相互关系。聚落群研究的作用及意义如此重要,故对透物见人、研究历史为目标的中国考古学来说,当把它作为一极为重要的工作开展起来,并尽力做好。
(四) 跟上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步伐,积极利用当代自然科学与科技成果,使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获得更多的支撑和生长点。利用自然科学与技术成果加强考古学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良好传统。1949年以来将自然科学与技术成果用于考古学研究所经历的道路,虽有曲折,总的趋势是使这一传统得到了光大。至今已在碳十四测年、金属成分及工艺分析和栽培作物种属与进化以及人骨性别、年龄及种属的鉴定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摄取了相当系统的信息。同时,对陶瓷成分及烧成温度、石玉器材料、植物孢粉和野生及驯养动物种属的鉴定,航空摄影及物理勘探技术运用于考古调查,计算机技术及概率论运用于考古学研究以及开发科技成果用于文物保护等方面,也都获得了可喜的成绩。总之,运用自然科学与科技于考古学研究,提高了资料及文物保存水平,使考古学显示出更为丰富的内涵及旺盛的生命力,增进了考古学研究的能力。但同时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到目前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自然科学与科技运用于考古学能量的评估,确存在失实的倾向;其次是已做的工作大多缺乏系统性;再次,或许更重要的是,从当今自然科学与科技发展状况来看,自然科学与科技运用于考古学研究及文物保护,尚未能充分发挥其能量,还存在许多空白,如DNA检测及分析技术,碳、 氮同位素及微量元素分析,光盘技术,以及概率统计和弗晰数学原则,等等。为了推进新世纪的考古学工作,必须从中国考古学的实际需要出发,本着积极稳妥、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态度,跟上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前进步伐,加强文字、图纸及照相资料的保存,推进文物保护,以多角度、全方位地诠释考古现象,更全面地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
概言之,两步并成一步走,加强薄弱环节,做好以聚落为单位进而探索聚落群的考古学研究,积极利用当代自然科学与科技成果,搞好考古资料的保存、保护与考古研究,使文物保护与利用良性循环,形成可持续发展局面,是我们对迈向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希望。如果我们能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深化层位学和类型学研究,踏实工作,中国考古学定将于新世纪开拓出新局面。
注释:
〔1〕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 《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第47~4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6页,台北,1995年。
〔3〕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全集》第二册300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台北。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5〕 《李大钊文集》下卷17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北京。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6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北京。
〔7〕 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 《文物》1995年第5期。
〔8〕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29~13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香港。
〔9〕 杜正胜《周代的“封建城邦”》, 《古代社会与国家》449~478页,先晨文化,1992年,台北;日知《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北京。
〔10〕 同〔8〕,108~129页。
〔11〕 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 《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标签:考古学论文; 中国考古学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石器时代论文; 文物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