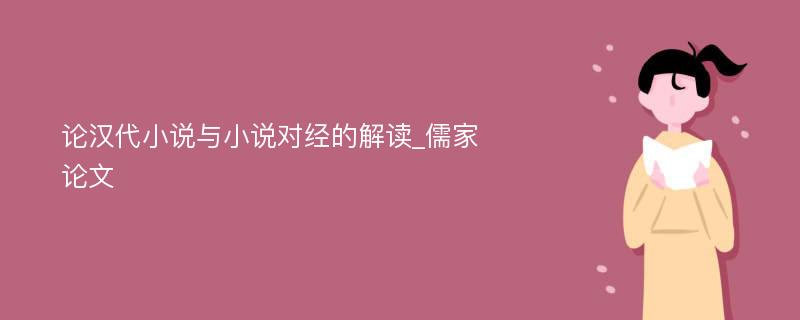
论汉代小说与以小说解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说与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2-0117-05
小说作为独立的文体虽形成于汉代,但却长期被斥为“小道”,处于非主流地位,难以与儒学相提并论。然而,汉代小说虽小,却又并非微不足道,《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记小说家与儒家同为九流十家,而所著录作品数量,“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小说家之文从数量上远多于儒家,“是则小说家者流,且侈然以六艺之附庸,而蔚为大国矣”[1]。小说之所以在汉代迅速发展,与汉儒对待小说的态度有关:汉儒学者在解经和阐述儒家思想时往往喜欢引用小说进行说理。正如王利器先生所言:“(以小说解经)皆旷古以来,解经之士之所不能言或不敢言者。今余为之擘肌见理,使之涣然冰释,岂非汉人之所谓礼失而求野者乎?”[1]
一、汉代小说的文体性征
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时间,一直是文学史上争议较大的论题之一。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就存有先秦说、战国说、汉代说、魏晋说、唐代说等五种代表性的说法。造成巨大分歧的关键原因,在于对小说文体发生标志性认识的差异,如果按照现代小说的要素标准去评价汉以前的作品,作为独立文体的小说特征显然是比较模糊的。就汉代小说来说,汉人辑录的小说多已散佚,我们能参考的只有《汉书·艺文志》录小说15家,且有目无文,为考证带来很大的困难,再加上其文体特征尚未定型,如何囿定汉代小说范围就成为主要的问题。不过,通过分析《艺文志》所列书目,我们可以约略看出汉代小说的一些总体特征。
观《艺文志》著录小说15家,其中《伊尹说》等8家以历史人物为题,《周考》等3家从题目看当以记录周代历史事件为主,班固《周考》注曰“考周事也”[2]。至于《百家》一书,刘向在《说苑序奏》中称自己“别集以为《百家》”,两者如为一书,参照《说苑》内容看当是刘向搜集的历史故事集;惟《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3篇较难确定内容,从题目看应与汉初流行的黄老思想有关,然史书记载武帝时的封禅、养生故事多依托于黄帝等黄老人物,则其内容也应与历史相关。由此可知,汉代小说多涉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正因为汉代小说多讲述历史,所以,后人往往把这些内容当成历史事件,从而混淆了历史与小说的区别。
但是,汉代小说虽然也讲历史人物和事件,却与《尚书》、《春秋》等王朝史官所记史书不同。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引余嘉锡《古书通例》“古书多造作故事”章说,古书喜欢“引古以证其言,或设喻以宣其奥”,但兴之所至,往往多有造作。这种造作主要有七个方面的原因:
一曰:托之古人,以自尊其道也。二曰:造为古事,以自饰其非也。三曰:因愤世嫉俗,乃谬引古事以致其讥也。四曰:心有爱憎,意有向背,则多溢美溢恶之言,叙事遂过其实也。五曰:诸子著书,词人作赋,义有奥衍,辞有往复,则设为故事以证其义,假为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也。六曰:古人引书,唯于经史特为谨严,至于诸子用事,正如诗人运典,苟有助于文章,固不问其真伪也。七曰:方士说鬼,文士好奇,无所用心,聊以快意,乃虚构异闻,造为小说也。[3](P220)
这些特点在《汉书·艺文志》所列小说中大多都已显现。也就是说,汉代小说多为造作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历史。王充《论衡》就指涉大量这样的历史故事,批评这些故事“殆虚言也”,并在《书虚篇》中说:“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4](P167)
班固所注小说家的叙述内容综合起来看,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依托。是后人借历史人物表达自己的观点,如《鬻子说》班固所注“后世所加”。二是迂诞。它们可能不完全是历史事实,具有虚构的因素,故班固说《黄帝说》“迂诞依托”。三是叙事性。班固注《青史子》曰“古史官记事也”,注《周考》曰“考周事也”,《臣寿周纪》似也记述周代历史。这些特点都说明,汉代小说已经具有了小说文体的基本性征——虚构性。而且,汉代小说是对历史的夸述,对历史的再阐释,加上“小说”概念的确立,故汉代小说已形成为独立的文学文体。或许因为小说是稗官记录的“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街谈巷语”,所以,它被刘向父子和班固贬称为“小说”,以区别于儒家之“大道”。
二、汉代传书小说的寄生形式
汉代儒家学者在奏议和著述中喜欢引用历史论证其观点,“以史为鉴”是汉代政论文的论证特色,如贾谊所言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但是,我们对儒者著述所引述的历史应辩证地认识,因为其中许多纪事并不见于史籍,许多言论颇似小说家言,很难视为史实。班固《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这句话说明,小说来自稗官。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出土的编号185竹简记曰:“取传书乡部稗官。其田及作务勿以论。”[5](P23)这里也提到了稗官,而且说“传书”出自稗官之手,则编辑“传书”应该是稗官的职责范围。既然“传书”和“小说”都是稗官所记,就说明小说与“传书”应该有相通之处。
“传书”一词在汉代子书中多处记载,《论衡》就经常引用“传书说”、“传语”、“儒书说”,仅“传书”一词在《论衡》中共出现44次,其中28次都是记载“传书”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带有神异的特征。出现最多的是感应故事,共有17则。《感虚篇》载:“传书曰:燕太子丹朝于秦,不得去……当此之时,天地佑之,日为再中,天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秦王以为圣,乃归之。”今传汉代小说《燕丹子》的开头部分即取此说,只是情节更丰富了。《感虚篇》中“师旷奏乐”的故事,据考也是一篇汉代小说[6]。这些“传书”所记载的都依附于历史,但却充斥着如此违背常理的怪异内容,显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诞欺怪迂之文”,故被王充作为虚妄的言论严厉驳斥。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传书”主要就是汉代的小说。如果确认这些“传书”多为汉代小说文本的话,那么我们还注意到,和其形式相似的故事在汉代儒者子书和纬书中也大量出现,像《孔丛子》、《孔子家语》、《韩诗外传》、《说苑》、《新序》、“七纬”等著作里都有很多历史事件与“传书”的故事相同或相似。刘向在《说苑序奏》中就称其《说苑》采录了小说,然后又另编了小说集《百家》。因此,儒者书中实际是包含大量来自“传书”小说内容的,今所见汉代小说虽然没有独立的文本传世,但却大量散见于其它汉代著作中,以独特的“寄生”形式被保存下来。
三、汉代儒书小说的经学阐释
虽然这些“闾里小知者”的言论不乏迂诞,但其所讲的道理“必有可观者”、尚有“一言可采”,因此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从而被经学所采用。
1.子书小说的解经内容
汉代儒者书中包括子书和纬书。子书中有很多小说形式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如《大雅·荡》载:“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韩诗外传》卷二则曰:
昔者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群臣皆相持而歌……伊尹知大命之将去,举觞造桀,曰:“君王不听臣言,大命去矣!亡无日矣!”桀相然而抃,盍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
再如《春秋》记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孔丛子·记问第五》就解释为是孔子预言“宗周将灭”的谶语。当然,与专门解释经典的“传”不同,这些儒书较少采用训诂式的释注,更多的是由经典申发,用艺术的形式诠释德、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常主题。因此,子书小说的内容多是对孔门家族人物的神化:孔子好学,子书小说则有孔子向老聃、师襄求学的故事;曾子守孝,子书小说则虚构了曾母扼腕而曾子痛的故事等,并塑造了儒家心目中理想道德模范的群像。如孔子曾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韩诗外传》卷十则举吴延陵季子见遗金而牧者不顾的故事为例。另外,子书小说还会依据宣传的需要对历史进行重新阐释。如周武王在历史上一直是兴干戈、尚武力的形象,但《韩诗外传》卷三则记录了武王偃武息兵,治文修德,把武王塑造成了以“仁”治国的典范。有些造伪甚至是非常明显的,像刘向作品中常见的一事多记现象就是很典型的仿作,如余嘉锡所说:“苟有助于文章,固不问其真伪也”。同时,汉代儒者之造作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讽谏。贾谊《新书》多为上汉文帝之书,其引“青史氏之记”即出自小说《青史子》。刘向采录小说的目的,班固说是为了“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2]《楚元王传第六》,明讽喻之义。讽谏是汉代文学的时代主题,汉儒喜谈小说,正是看准了小说可借渲染史事以炫视听、游说帝王,又打着历史的旗号来证明确凿有据,从而强化了说服的能力和效果。所以,成帝见刘向奏书后“嘉其言,常嗟叹之”,证明确实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2.纬书小说的解经内容
在汉代儒者著作中,小说出现最多的当数纬书。关于纬书的性质,学界颇有争议。然《易纬乾坤凿度》卷上郑康成注曰:“纬者,古本经,已后不知纬字何也。经之与纬是纵横之字。”刘熙《释名·释典艺》也云:“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苏舆《释名疏证补》进一步释曰:“纬之为书,比傅于经,辗转牵合,以成其谊,今所传《易纬》、《诗纬》诸书,可得其大概,故云反覆围绕以成经也。”这说明,在汉代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纬书与儒家经书相对应,是对经书的解释。
汉代儒家经典包括“五经”和《孝经》、《论语》,在汉代都有相对应的纬书,称为“七纬”。但是,纬书对经的解释也非对文本的注释,而是结合当时社会流行的谶说对经书加以引申发挥,内容也就多为符命、阴阳灾异之说,实际上是天人感应思想与儒家经学结合的产物。两汉儒学在先秦儒学基础上吸收了阴阳五行、黄老等学说之精华,使之成为社会实用的“新儒学”,以便“经世致用”,能运用于政治和社会实践。谶说由于其神秘性的特征,被多数经生儒士认同,并充分加以汲取以补充自己的思想体系,于是谶纬合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易》类录《易纬》称:“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渐杂以数术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所以,纬书是指专以谶术比附解释儒家经典的书。
纬书中所涉及的谶语多与社会政治相关,日本学者安居香山称之为“史事谶”。汉人在解释谶语时往往把隐语与具体的历史事件相联系,预言政治、人事的吉凶,体现儒家思想。但纬书所引述的历史事件一般带有极大的神异色彩,与《论衡》所引“传书”的内容相同。如帝王异相之说,《春秋·元命包》即载:“黄帝龙颜,得天庭阳。上法中宿,取象文昌。载天履阴,秉数制刚。”[7](P590)“尧眉八彩,是谓通明。历象日月,璇玑玉衡。”[7](P591)《孝经·援神契》载:“伏羲山准,禹虎鼻。”[7](P966)对此,王充一律把它们作为虚妄之说进行了驳斥。所以,这些历史故事带有较明显的小说色彩,小说的夸诞性使之成为纬书美化、神化儒家学说的主要手段。
纬书小说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主要集中在祥瑞与灾异,这些祥瑞与灾异的故事往往与政治是否清明有关。董仲舒说:“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8]《同类相动》班固也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2]《董仲舒传》如《春秋·考异邮》引“白孔六帖”曰:“龙门之下血如江。时人谣曰:王侯之斗”,宋均注曰:“龙门战在鲁桓十三年。”[7](P796)《春秋》载此事说:“十有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而《春秋纬》则引“春秋说”称:“龙门之战,民死伤者满沟。”[7](P907)有时,为了体现天命的神异,纬书会对历史事件赋予新的含义。如《春秋》哀公十二年曰:“冬十有二月,螽。”《左传》载,哀公就此事咨询于孔子,孔子从历法角度解释说:“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而《春秋纬》引“春秋说”认为:“陈氏纂齐三年,千人合葬,故螽虫冬踊。”[7](P906)“西狩获麟”事件在纬书中也有了新的解释,孔子成了为汉家创制大义、预言刘汉当兴的预言家。
除了这些对经典的直接阐释外,还有许多纬书小说则是从经典所记历史申发,如纬书中记载的圣人感生与受命的故事。《商颂·玄鸟》有“玄鸟生商”,《大雅·生民》有姜嫄“履帝武敏歆”,《诗·含神雾》则引“诗传”记述了两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同时纬书小说又把这样的感生故事附会于每一位圣人身上。《礼纬》:“禹母修已,吞薏苡而生禹。”[7](P531)《春秋·合诚图》:“尧母庆都,有名于世,盖大帝之女,生于斗维之野,常在三河之南。天大雷电,有血流润大石之中,生庆都。”[7](P764)圣人因为非凡人,所以一出生也就与众人不同。同样,受命故事也与每一位圣人有关,这样,就给君权神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如文王受命时,“赤雀衔丹书入丰鄗,止于昌户”[7](P411),《尚书·帝验期》载“西王母献舜白玉琯及益地图。”[7](P387)《尚书·帝命验》和《尚书·中候》等书都是专记应验故事的纬书。
因此,纬书小说在解释儒家经典时,由于和符命、天验等内容相结合而呈现出怪奇的色彩。但总起来看,纬书记载了很多生动丰富的故事,有的情节曲折变化,具有想象的色彩,甚至像神话故事,所以刘勰称赞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这些故事的神奇想象力和浪漫色彩与后世的志怪及神话小说无异,让这些著作具有了鲜明的文学色彩。
四、汉代经学小说的特色
汉儒学者在著述中贯穿了大量的小说,一是以之论证君权神授天赋的天然合理性,二是为了进一步抬高儒家经典的地位。这一特殊的目的就使得汉儒著述中的小说呈现出浓郁的说教味道,形成了独特的经学小说。这些小说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历史进行了重新阐释,呈现出许多独有的特色。
1.衍生性
汉儒著述中的很多小说在古书中本有其事,汉儒出于立言的目的对原来的故事进行了改写,衍生出不同的情节,内容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了新的主题。例如,孔子“西狩获麟”在儒书中传播最广,内容不断被丰富。《左传》据《春秋》解释说,“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仲尼观之曰“麟”,获麟故事开始和孔子发生关系。《孔子家语·辨物》与《公羊传》相似,在情节中加入了孔子见麟后叹曰“胡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但没有说明其叹泣的原因。《孔丛子·记问》则增加了细节描写,添加了孔子及冉有、高柴、言偃的对话,并解释“获麟”的含义:麟出而死预示“宗周将灭”,而孔子“吾道穷矣”,这里,已经表现出谶纬的影响。至《孝经·援神契》则对此故事进行了完全的改编,不仅人物发生了变化,结果也出人意料地变成了麟吐瑞书,言刘汉将兴,获麟在纬书中成了汉王朝君临天下的神示。再如,《论语》有孔子厄于陈蔡事,《孔子家语·在厄》则记述甚详,以很大的篇幅描述子贡怀疑颜回窃食,孔子竟借托梦问明缘由,证明颜回之可信。此故事在《吕氏春秋·任数》也有记载,不过是孔子亲见,佯为不知。大概是因为直接写孔子怀疑颜回,有损于孔子圣人形象,故而被汉儒嫁接于子贡,来称赞孔子的知贤不疑。
2.模拟性
汉儒作品喜欢对历史事件改头换面,来表达儒家的伦理观念。如《尚书·中候》记曰:“殷纣时十日,雨土于亳,纣竟国灭。”[7](P409)《淮南子》称“尧时十日并出”,《中候》则变成了“纣时十日”,证明商纣荒淫暴虐,必遭天谴的结局。汉儒在小说创作上的模仿常见于感生与受命故事,增强了圣王先贤的神异性、神秘性。《诗经》中有姜嫄“履帝武敏”感孕生后稷、契母吞玄鸟五色卵生商的故事,纬书便出现了大量与此相似的感生故事,几乎涉及每一位圣人贤王,如华胥感大迹生伏羲、安登感常羊生神农、附宝感大电生黄帝、女节感大星生少昊、女枢感摇光生颛顼、庆都感雷电生尧、握登感大虹生舜、颜征在感黑龙之精生仲尼等等。受命故事也与每位圣贤有关,而他们受命的形式同样如出一辙,都是借助河图洛书,只是在细节上略有差异而已。这种模拟甚至影响了当时的杂史,禹母吞薏苡生禹故事便为《吴越春秋》采用;《汉武帝内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景帝梦神妇捧日以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9](P140)刘向作品中的仿作故事也很多,《韩诗外传》有孙叔敖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劝谏楚庄王的故事;《说苑》中则把孙叔敖换成了少孺子,庄王故事则移植到了吴王身上;《复恩》中记述的介子推归隐和舟之侨归隐故事,与《杂言》第八、九、十三章分别记述的惠子、西闾过、甘戊落水被船夫救起并和船夫辩论故事情节相似,只是主人公发生了改变。
3.夸张和玄虚色彩
古代许多学说为了扩张其影响力,往往喜欢添加一些神秘元素,汉儒对汉朝和儒家学说的神化也让小说具有了玄虚的特征。王充引传书“杞梁氏之妻向城而哭,城为之崩”,此故事又见于刘向《列女传》,刘向引此故事的目的是赞扬杞梁妻“贞而知礼”,儒家的贞节观被刘向神化到了可以感动土石的地步。《新序·杂事》写丑女无盐嫁齐宣王事,无盐在和宣王说话时竟“忽然不见”,可见此事为虚构无疑。无盐随后指出齐国有“四殆”之害,批评齐王“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国家之治”,终使宣王顿悟。由刘向编纂《新序》的目的可知,刘向实际上是借无盐之口,行劝谏之实,也是借此体现儒家的重德轻貌思想。此故事在《列女传》中主角变成了“齐钟离春”,可见传书对历史故事往往加以夸张、神化,来宣扬自己的学说。
如果说,这些小说描述还可能是历史的加工的话;那么,一些神化孔圣人及其弟子的故事则应是儒者的创造。《论衡》引传书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太山,孔子东南望吴昌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昌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正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4](P170—172)孔子竟能看到千里外的吴国城门,可谓神异至极。再如《孝经·中契》讲述了孔子作孝经后天赐书题,麒麟口吐图文,书于鲁端门,文字化为赤乌翔于青云的故事。《孝经》在武帝时本未进入儒家经典之列,《钩命决》引郑康成注:《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7](P1014),《孝经》的书简仅为《春秋》一半,属于“短书”之列。但经过后来汉儒的推崇,也列入儒家经典。《孝经·中契》这段生动的文字显然是为神化《孝经》而专门创作的小说。
经过儒生的艺术加工,儒书中的小说故事不仅具有了神异性,情节也更加丰富,尤其开始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如《孔子家语·好生》记曰:
鲁人有独处室者,邻之嫠妇亦独处一室。夜暴风雨至,邻妇之室坏,趋而托焉。鲁人闭户而不纳。嫠妇自牖与之言:“何不仁而不纳我乎?”魯人曰:“吾闻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纳尔也。”妇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谓其乱。”鲁人曰:“柳下惠则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曰:“善哉!学柳下惠者,未有期于至善而不袭其为,可谓知乎!”
通过简洁的对话,作者寥寥数语刻画出一个固守儒家“男女授受不亲”古训的节义者的形象。儒者书中的孔子形象更是丰富多彩,有意识的虚构和非现实的描绘使得孔子形象由历史上的智者上升为儒者敬仰的玄圣素王。
从以上经学小说的内容可以看出,以小说解经增强了儒学的神异性、神秘性,从而把儒学抬高到了神学的地位,与此同时,完善了汉代的儒学思想体系,为汉代以经学治国、巩固立国之本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因此,小说在汉代得到了迅速传播,到东汉时,世人征引、造作小说已经成为一种风气,甚至影响了官学。《后汉书·蔡邕传》记灵帝开“鸿都门学”,其征辟的学者“喜陈方俗闾里小事”,世俗小说成为儒生立言造事的工具。因此,小说是汉代经学阐释的重要工具,对汉代儒学形成广泛的影响。
以小说解经不仅促进了儒学思想体系的完备,也形成了早期小说叙事的风格,并影响到以后小说发展的走向。首先,汉代儒书所载小说在六朝小说中仍有记载,如《论衡·感虚篇》引传书“武王伐纣平波”和“鲁襄公援戈麾日”仍见于张华《博物志·异闻》;“商汤身祷于桑林”见于《搜神记》卷八;“曾子之孝,与母同气”见于《搜神记》卷十一;《语增篇》“纣与三千人牛饮于酒池”见于殷芸《小说》卷二;《孝经·援神契》“孔子预言赤刘当起”见于《搜神记》卷八等等,这说明六朝小说仍然继承了汉代小说的特色。其次,六朝志怪小说的怪诞风格源于汉代小说的神异性,其自然异象、人兽同体、心梦感应等神异化手法广泛影响了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艺术。其三,汉代小说注重运用语言和行为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则影响了六朝的志人小说,只不过所表现的人物对象发生了变化:一个塑造了儒家的圣贤系列,另一个则塑造了以魏晋风度为代表的人物群像。其四,汉代小说的历史主题也被后世小说所继承,《世说新语》、《搜神记》、《小说》等六朝小说基本都是取材于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唐以后的小说其历史题材仍占了很大的部分,即使是虚构的言情小说也延续着讲历史的叙事手段。汉代小说对历史的虚构使之成为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
参考文献:
[1]王利器.试论以小说解经[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5).
[2]汉书[M].
[3]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三联书店,2004.
[4]王充.论衡[M].黄晖.北京:中华书局,1990.
[5]刘信方,梁柱.云梦龙岗秦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6]魏鸿雁.黄老养生思想与汉代散体大赋的形成[J].文学遗产,2012,(1).
[7][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8]董仲舒.春秋繁露[M].苏舆.北京:中华书局,1992.
[9]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春秋论文; 文化论文; 韩诗外传论文; 论衡论文; 说苑论文; 搜神记论文; 艺文志论文; 孝经论文; 孔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