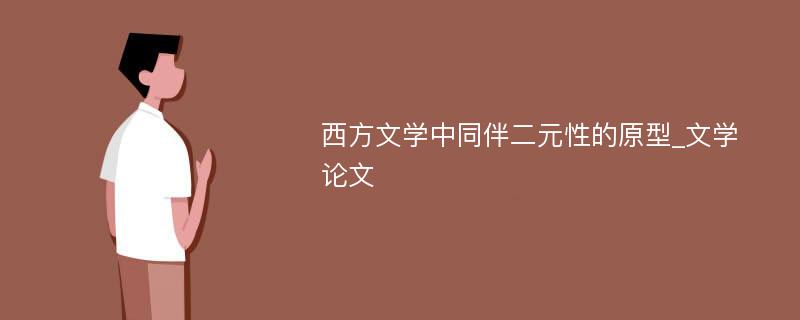
西方文学中的伴生对偶原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偶论文,原型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文学人物的画廊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成对的伴生人物,既有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这样如孙悟空与猪八戒在中国一样闻名西方的人物,也有像爱伦·坡小说《威廉·威尔逊》中孪生兄弟般相似的人物,这些相伴相生的人物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但又水火不容,迥然相异。在西方文学发展的长河中,类似的对照相偶人物生生不息,层出不穷,他们交相辉映,妙趣横生,互为依恃,像闪闪发亮的星星,显现出极为独特的神采。他们的历史源远流长,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并随着时代、民族艺术心理方面的异同呈现出不同的外在形象,但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具有典型的原型特征,本文正是想通过对西方文学中这一类形象的分析,追寻其古老的神话原型特征,并发掘其心理和哲学内蕴,从而探求它在文学发展中特有的艺术规律和审美价值。
一、西方文学中的伴生对偶形象
(一)来源于流浪汉小说中的主仆对照类型
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中主仆相随这一典型类型直到今天还可以在西方众多的文艺作品中找到。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很早就出现了,但第一部现存的流浪汉小说《托尔梅斯河上的盲人引路童》产生于16世纪中叶,以小拉撒路为主角,他与后来出现的流浪汉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都是出身微贱的市井游民,为人做仆,借浪游遭遇来贯穿杂凑的情节,充满了嘲讽和揶揄。在此类小说中主仆流浪这一模式经常出现,只不过最早往往是一仆多主,仆人的性格也就在与主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塑造完成。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拉伯雷正是借鉴了这种写法,描绘了妙趣横生的一对伴生对偶人物,庞大固埃与巴汝奇,庞大固埃具有英雄般的力量,巨人般的形象,是“理想人”的象征,而猥琐的巴汝奇,机智狡猾,市民气十足,捣鬼骗人,刁钻古怪。这一主一仆形影不离,相互对照,相映成趣。但这一类“主仆”流浪汉小说形式,在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笔下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伴生对偶形象。
《堂·吉诃德》这部作品,戏拟骑士传奇的铺陈写法,同时借用了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及主仆流浪的情节结构。主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伴生、对偶极其鲜明,没有桑丘·潘沙的陪伴,很难想象堂·吉诃德会有第二次游历,这两个人物作为一对对立互补人物,互为对照,主仆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一个骑着干瘦的“弩骍难得”,一个骑着肥肥的小毛驴;一个主观武断、一个实是求是;一个耽于幻想,一个只求温饱;一个夸夸其谈,充满书本知识和雄辩的言辞,一个满口俚语,充满民间的智慧和辛辣的谚语,这两相对照的形式,造成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效果。
许多海外研究《堂·吉诃德》的专家认为,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主仆二人互相影响,互相补充,堂·吉诃德渐变得像桑丘,桑丘渐变得像堂·吉诃德,而在译者杨绛看来,这一疯一傻的主仆又都有独特的个性,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是各趋极端的性格,但又相反相成,纯粹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固然绝无仅有,一身兼有两人特性的却很普遍。
流浪汉小说体的英国小说中一直是惹人注目的一类,其目的,显然是为讽刺的、幽默的或批评性的叙述提供许许多多的情境和形形色色的对象。这一类小说中伴生对偶形象出现的频度也是有清晰脉胳可寻的。从托马斯·纳什的《不幸的旅游者或杰克·威尔顿传》中的杰克和萨里,到约翰·班杨的《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和“忠诚”;从斯摩莱特的《罗德里克·兰顿历险记》(兰登传)中的罗德里克与斯特拉普,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中的项狄和托比叔叔,一直到狄更斯的作品《匹克·威克传》中的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忠仆山姆。这一类主仆型人物层出不穷。特别是此类人物在菲尔丁笔下更是活灵活现,他仿效《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风格写了成名作《约翰·安德鲁》,安德鲁和亚当斯这两个人物在随后的《汤姆·琼斯》中,又变成汤姆和帕特里奇的形象,两位类似于吉诃德和桑丘的人物。
莎士比亚也是《堂·吉诃德》的崇拜者,在他的《亨利四世》中塑造了一对可爱的伴生对偶人物——哈尔亲王和福斯塔夫,年老的胖爵士和瘦高的年青亲王同游,把卑贱与高贵,伦敦东市的市井生活和威斯敏斯特的景象联系起来。青年的哈尔,像条“鳝鱼皮”,“裁缝尺”,老福斯塔夫则是“一堆肉山”,哈尔称福斯塔夫是他的“恶魔”,“白胡子的老撒旦”,两人互相影响,互为映衬。
伴生对偶形象在美国文学中常常寓于赶路寻求式的发展小说中,是与“美国之梦”的追求分不开的。像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白人孩子哈克和黑奴、已成人的吉姆在密西西比河上的自由浪游,也是一对伴生对偶形象,有的美国评论家认为它恰恰说明了美国独有的白人的黑人情结和黑人的白人神话,两者的互补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形象。美国著名作家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汤姆·乔特和吉姆·凯西,象征了率领以色利人出埃及的摩西及其助手约书亚,因此这部小说被称为现代人的迦南之旅。在作家的另一部小说《人与鼠》中的流浪工人莱尼和乔治更具有鲜明的伴生对偶性。
(二)来源于忏悔得救故事的伴生对偶形象
伴生对偶形象的另一类分支来自忏悔得救的故事。上帝与魔鬼的对立,是基督教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观念在印度和东方故事中也有所反映。在中国的太极图中,阴与阳的能动性是对称的,但这种对称并不是静止的,这种合理的对称暗示着强有力的无休止的运动,在图中的圆点则象征着这样的思想,每当这两种力量之一达到自己的极端时,它早就孕育着自己对极的种子。这一思想在西方文学中则反映为上帝和魔鬼的较量,善与恶、灵与肉的冲突常通过伴生对偶式的人物形象反映出来。像浮士德和靡菲斯特这对伴生对偶的西方典型形象,最早的追溯可以从印度古代梵语叙事诗《玛哈帕腊达》和一些东方叙事故事中找到。而最直接的西方来源则取自包含宗教寓意的民间传说,在蒂尔索·摩利纳的《不信上帝而被打入地狱的人》中,隐士巴马洛,在魔鬼的导引下,走入地狱。浮士德这个形象较早的文学表现是在加尔德隆(1600—1681年)的戏剧《神奇的魔法师》中,西泼里亚诺与魔鬼订约,出卖灵魂。这一先驱直接导致了歌德的《浮士德》,这部书前后历经60年的酝酿,根据前人的作品和自16世纪以来浮士德在德国民间宗教故事中的流传,歌德塑造了浮士德和靡菲斯特这对伴生对偶形象。浮士德在靡鬼靡菲斯特的引诱下走出书斋,开始投入广大的世界,从一开始靡菲斯特就是作为一个否定的精灵与浮士德对应。在每一个有浮士德的地方,必有靡菲斯特,他对于浮士德是一个永恒的矛盾,对于浮士德的发展既是一个障碍,又是一个激发的力量,他与浮士德既矛盾对立,又息息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个人物几乎居于同等的地位,靡菲斯特滋长了浮士德性格中阴暗的一面,而实际上又是帮助浮士德完成了他的肯定的人生哲学。两个人是对偶中的两极,对立中趋向统一,是资产阶级人性中两种力量的冲突与合一。
(三)表现于现代文学中的伴生对偶形象
伴生对偶形象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中因文学观念的变化而呈现出新的特点。既有类似于原始类型意义的赶路寻求式,如美国“垮掉一代”代表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狄恩和索尔的伴生对偶形象,贝克特《等待戈多》中的波卓和幸运儿主仆;也有浮士德和靡菲斯特人格发展式小说,如陀斯陀耶夫斯基的《两重人格》,雅可夫·高略德金与和其一模一样的“相似者”小高略德金的伴生对偶,小高略德金一方面是同高略德金敌对的一种异己力量,同时他又是高略德金形象的补充,是他内心中“恶”的实体,这两个形象反映了现代心理学的成果,充分显示了心灵的内在分裂。
在新一代小说家手里,伴生对偶形象也有其新的发展,在詹姆斯·齐伊斯的巨著《尤利西斯》中,斯蒂芬与布鲁姆两形象的互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犹如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的对应,斯蒂芬代表幼年,理智本质,高雅的精神境界,艺术的象征;而布卢姆则是成年,情感本原,沉湎物质生活的象征。斯蒂芬和布鲁姆影射了《奥德修》中的父子,他们的追寻和团聚,象征了两者的合一。
二、伴生对偶形象的神话原型
西方文艺批评中的原型理论认为,艺术的巨大概括性既不来自于抽象的理论概括,也不来自于艺术思维自身的“正—反一合”过程,而是导源于原型本身的特点。原型是一种超现实、超个体的人类经验。它所包含的深意跨越了时空界限。因而,以原型作源泉的艺术具有极大的概括力、震撼力和魅力。原型论认为艺术的源泉是神话,而神话本身则具有多义性、模糊性与巨大的包容性,神话犹如晶体的轴系统,只能决定其基本结构,而不能决定其具体形状。
伴生对偶形象也有其神话原型,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在约瑟夫·L·汉德森的《古代神话与现代人》一文中,引用了1948年保罗·拉丹博士出版的《温内巴戈神话的英雄轮回周期》一书,在其中的孪生子周期中,描绘了太阳的孪生子,在最初母亲的子宫内,他们曾连为一体,在出生之际被迫分离。然而,他们却互相属于对方,逐渐趋向于结合为新的一体。他们有时表现为合而为一,有时又呈现为两个各自独立的形象。
类似于这种孪生子英雄的神话原型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可以找到。如澳大利亚的图腾人物,其中最著名者有二:“聪慧”与“愚顽”,即胞族始祖的“正”“反”两种变异。试以古南图纳人(属美拉尼亚人)神话中全然拟人化的胞族祖先托·卡比纳纳与托·卡尔乌乌为例,这两兄弟造地形地物,造种种动物和种族团群,首倡渔猎、培养作物等。然而两兄弟的创造截然相反,一切美的、有益的均出自托·卡比纳纳之手,一切有害者,则为托·卡尔乌乌所造,托·卡比纳纳是“善神”的化身,托·卡比乌乌则堪称“瘟神”,招致死亡、饥馑、争斗、乱伦,同时,与卡比纳纳相对,卡比乌乌还是愚拙和滑稽的化身,被看作一个十足的“傻瓜”,(譬如:他自内向外覆盖屋顶,结果让雨淋透),这与伴生对偶原型中的“聪明人”与“傻子”结伴而行的形象特别吻合。在非洲的神话叙事题材故事中,大多都有为数众多的胞族英雄兼作恶作剧者,其主要人物如尼日利亚西部的“半人”神幻人物莱格巴,他是神与人的中介,以娴于法术和恶作剧著称。
综观北美神话,有不少孪生英雄兼恶作剧式的人物形成一体。这些性喜作恶作剧的胞族祖先,不仅诉诸机巧,对英雄的相应业绩及神圣仪典予以揶揄,像巴汝奇一样习惯于佛头着粪的行为,成为其低俗、戏谑一面的变异。印弟安人有时将渡马氏等类似于既是始祖英雄又是恶作剧的神幻人物视为“同一称谓,两个形象”,如他们的家兔氏英雄的一个称谓“格卢斯卡帕——维萨卡”,意即“双面者”。诸如此类合二为一,一兼二用的双重性人物常常与北美神话中同样也存在的孪生英雄形象相吻合,这孪生两者或为仇作对,或友善相处,如北美印弟安人易洛魁人的信仰中就残留有胞族英雄即为相互对立的两兄弟合一的观念。
同样,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世人盗火种,并由于为人类谋福利而被宙斯严惩,被禁锢于高加索的山崖,日复一日备受鹰鹫啄食肝脏之苦。而普罗米修斯的孪生兄弟埃庇米修斯,却是做尽坏事的反面典型,他反普罗米修斯之道而行。相传,他使人类失去一切可资防护之物(皮毛、爪等),又不听劝告娶潘多拉为妻,好奇地打开了潘多拉的灾难和瘟疫之盒。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至高神奥丁和狡黯之神洛基两形象,可视为“孪生子—胞族英雄和神幻狡黯者”两者合一的体现,奥丁是始初第一位“术士”,众神之父,曾寻得圣蜜,与洛基共同完成造人之举,而洛基则是冥世众魔怪之父,招致死亡的罪魁祸首。他俩在一系列神话中协同合作,几乎彼此相合为一。
从古老的神话系统我们可以发现,孪生子胞族祖先这种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对立互补,相反相成的伴生对偶原型,不仅与神幻创世时期的孪生英雄相契合,而且是负载着神话传统的整个集体潜意识的积淀。神话中可以用隐喻和象征来表达的东西,在文学中往往用明喻的形式来表达,给人以意义联想。一方面,使神话朝着人的方向置换变形,另一方面又朝着理想化的方向使内容程式化。但要使它成为一个真实可信的、艺术上和谐、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故事,就受到不同程度的置换变形。N·佛莱把文学作品分为神话、传奇、高模仿、低模仿和讽刺五种。伴生对偶原型身上往往有一种发展寻求模式,但无论是在路上浪游,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追求,往往都带有一种反讽性,使整体的作品深深浸染一种悲喜杂糅的风格,这一点在人物身上比较突出,这也许正好对应了神话两英雄以失败或死亡告终的仪式献祭模式,在文学中伴生对偶原型大致是在讽刺性的作品中,常常带有滑稽模仿的特点,如《堂·吉诃德》对骑士小说的戏拟,《巨人传》对传奇圣怀追寻的反讽。不过,在众多的表现形态上由于民族、时代、心理的不同,伴生对偶原型也呈现出不同的差异。
三、伴生对偶原型的原型心理学分析
在《原型和集体潜意识》一书中,心理学家荣格详细讨论了一些原型,他着重从心理学而不是从人类学方面探讨,他对神话批评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也是运用心理学从事文学批评的先驱者。
荣格在心理学上的主要贡献,除了关于集体潜意识的理论外,还有与阴影、人格面具和阿妮玛这些原型相关的“个体化”理论。所谓“个体化”,是指心理上的“成熟”,即发现每个人自我的各方面的过程。一个人的成熟意味着,他必须有意识地认识自我中积极的和消极的各个方面,这对于一个人心理上的平衡是极为重要的。用荣格的话来说,“投射”是主体没意识到的内容转化客体的一种本能的作用;投射的结果使这种内容看来像是属于主体时,投射便停止了。通俗地说就是,我们平常很容易把自己没意识到的缺点或弱点投射到别人身上,而不容易把它们看作是我们自己的本性的一部分。“阴影”的观念,是由个体的意识心理投射出的暗影,蕴含着隐秘的、受到抑制的,以及负面的人格特征。但是,这种阴影绝不仅仅只是意识自我的简单颠倒。正如意识自我蕴含有种种令人不快的,具有破坏性的态度一样,阴影之中同样也蕴含着正面的特征——常态本能和创造性冲动,虽然意识自我与阴影的确相互独立,但是宛如思想和情感相互联系在一起一样,它们同样是无法分割地联为一体。它们可以说是古代孪生子神话的心理对应体,反映了胞族英雄身上自我与非我双方冲突对立而又同一的复杂人格。长久以来,人类依然尚未意识到人格阴暗或消极一面的存在,但从神话英雄身上,却很容易找到这种潜意识的对应心理反映,如:胞族英雄往往能够认识到“阴影”的存在,认识到他可以从这种“阴影”中汲取力量。在英雄与恶龙战斗的神话中,如果英雄想征服恶龙就必须屈从于“阴影”的毁灭性力量,变得凶狠可怕、残酷无情。神话中的孪生英雄恰恰隐喻性地说明了这一点。托·卡比乌乌和托·卡比纳纳从两极相反的方面共同创造了世界,奥丁和洛基分别是至圣和至恶两种势力。一明一暗,但他们只能共同完成造人之举。这对英雄从同一到独立,又从独立趋向合一的过程,体现了人类对自身潜在的全面认识过程。在伴生对偶原型中,其中一方所指的正是这种无意识的方面,是英雄的人格阴影一面的象征性“投射”,成为英雄人格中的互补性因素,是意识自我未知或知之甚微的特征。在文学中,阴影人物往往蕴含着富有价值的、生命的力量。在《可兰经》十八书中,描述了在沙漠中伴随摩西的黑德尔(“神的第一天使”)的故事,他们形影相随,一道漫行,黑德尔做了许多坏事,如沉没渔船,杀死一位英俊的青年,还修复了异教徒们的城墙,摩西感到无法容忍他的所作所为,让黑德尔离开。然而,临行之际,摩西才发现,沉船使渔民保住
了被海盗劫掠的命运,青年的死掩盖了他犯罪的企图,保全了父母的名声,城墙的修复则使废墟下的珠宝得以重见天日,挽救了两个虔信者的生命。单纯从故事来看,黑德尔是那位虔诚的、信守法理的摩西的阴影,他无法无天,反复无常、阴险邪恶。然而,事实上两者又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互补的统一关系,这在伴生对偶原型这类文学中,又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
四、伴生对偶原型的审美意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伴生对偶原型的基本特点,这对形象往往是相伴出现的,你长我短,不可或缺的。但其中必有一人为主,另一人为辅或伴生,角色的地位比主角低,但人物本身却不一定逊于主角,只不过小说主要是以主角做为中心人物罢了。他们两个人各有独特的个性,即不同的“性格核心”,决定着他们不同个体性格的基本方向、形态与面貌,他们的个性特征基本上是相干性和相向性结合。相干性,心理学上是指性格中相反相异的心理特征趋向;相向性是指性格中相近、相似的心理特征趋向。相向性的内容特质使他们走到一起,相伴相依;反之,相干性的心理特质又使他们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趋向,他们两人中间某种对立的相干两极比较突出,造成互相冲突,但其同一、迭合、交叉、包容的一面又使他们唇齿相依。可以说,这两个人物无论哪一个都是单纯与复杂的统一,只不过有的是单纯中见复杂,有的是复杂中见单纯。根据现代耗散结构理论,系统中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非线性(线性:是指简单并列、相加或单向、直接的因果关系)和相干性两个重要特点,如人的双眼的视敏度比单眼高至十倍,并能形成单眼所没有的立体感。也就是说,双眼协同的视觉功能大大超过两只单眼视觉功能简单线性相加之和,显示出非线性和相干性;在社会中,人与人的简单协作也能产生新的生产力(大于个人生产力的简单相加),这一点在伴生对偶原型中表现明显,二者的相反相成,盈缺互补在整部作品系统内形成一种高度统一、有序的、具有新质的内在动力。他们的两极互补因素互相对照,互相影响,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同一行为中既表现了彼,又表现了此,可以说是两极并举,效果鲜明,彼此映衬,相得益彰。
近代西方由黑格尔到马克思所传袭的永恒进步的辩证法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原则,而和谐化的辩证法认为,万物之存在皆由“对偶”而生,“对偶”同时具有相对、相反、互补、互生等性质,万物间之差异皆可解释为原理上的对偶,力量上的对偶和观点上的对偶,对偶生成了无限的“生命创造力”,如果我们善于描述各种对偶之间互生关系的架构,就找到了和谐的整体性。求同、求异的有机统一原则,是文学形式的基本原则,形式的审美结构的多样性统一功能是互相渗透的,在统一的基础上变化,才能丰富,在变化中统一才能集中。对照也是一种平衡,不过是性质相反的平衡,“遥遥相对,息息相通”,矛盾的双方是不平衡的,但它们又处于统一性的艺术结构之中。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它又分裂为两个相互联系、依赖又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部分。老子说过:“反者道之动”,认为世界上存在着的相反力量是运动的源泉。古代的哲学家认为,宇宙的变化是永远不会停息的,宇宙变化是由阴阳两种矛盾所构成的。在歌德的笔下,则反映为人类感性心理两极的共存,虽然,“美与丑从来就不肯协调”,却又“挽着手儿在芳草地上逍遥。”(注:《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第二辑,第501页。)浮士德和靡菲斯特两种力量互不相让,并相争高,首肯了人类感性心理的二元化,如交响乐中“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的对立展开,使得人的心灵在向十全十美的进军中,充满了痛苦的体验。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书简》中认为:“审美范畴往往是成对对立而又可以混合或互转的,例如与美对立的有丑,丑虽不是美,却仍是一个审美范畴。”对偶相映,二极互射,恰恰对应了人们在欣赏中的审美观照,正如黑格尔在《美的理念》中所说的,“美的对象各个部分虽协调成为观念性的统一体,而且把这统一显现出来,这种和谐一致必须显现成这样: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各部分还保留独立自由的形状。”
伴生对偶原型,仿佛琴瑟相异,而又共鸣中音,合奏成美,曲终而引人遐思,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所说,“噬啮嗑合”,“相反相成”是这对矛盾统一体的贴切而形象化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