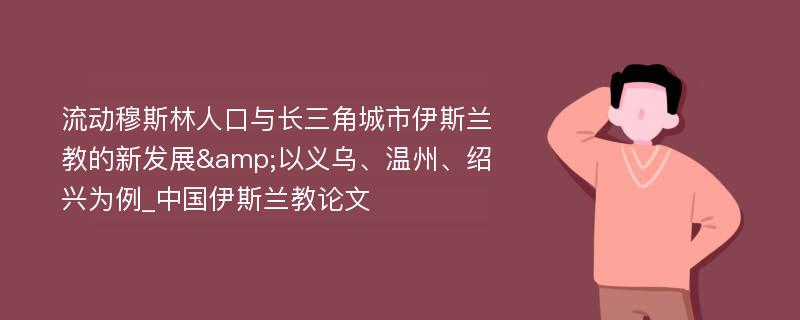
流动穆斯林人口与长三角城市伊斯兰教的新发展——以义乌、温州、绍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穆斯林论文,义乌论文,绍兴论文,温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5)02-0048-06 10.16023/j.cnki.cn64-1016/c.2015.02.008 长期以来,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和窗口,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舶来宗教都在此获得长足的传播、发展、互动、适融,对长三角社会影响深远,这里的宗教文化延续了较为发达的态势。从伊斯兰教来看,长三角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与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渊源至深。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包括穆斯林诸族群在内的内地人口大量涌入该地,他们或因务工、经商、供职留居此地者也不断增加。其中有一些阿拉伯国家在长三角成立商贸公司,前来参加华交会、义交会的外国商人中,阿拉伯国家商人数量可观,长三角伊斯兰教的外来穆斯林更多。 一、穆斯林人口移入是长三角城市伊斯兰教发展的基础 (一)历史上的穆斯林人口概况 唐宋之际,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商人就曾到过上海。751年(唐天宝十年),华亭县(今上海)青龙镇已经发展成为我国东南重要的通商重镇。其时,华亭县“富宝大家,蛮商舶贾,交错水陆之道,为东南一大县”[1]。宋朝初年,随着渔盐业的兴盛,华亭县从而成为“蕃商辐转,民物繁庶”。大批穆斯林来到上海始于元朝。南宋建立上海镇,元代上海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并设立市舶司。许多东南沿海港口留居了大量的蒙古、西域穆斯林官宦、商贾和前来的亚欧商人等。1227年,蒙古军大举进攻江南,穆斯林被带到江南者众多。“今回回均以中原居家,江南甚多。”[2]1259年,赛典赤·纳速拉丁受命任松江府达鲁花赤①,据说其部落氏族随之从浙江嘉兴迁居松江者几万人(亦说三万人)。1341-1367年,松江城西景家堰之北建有清真寺。其乃回回人人拜天方之地,过往松江之亚欧商人均前往叩拜之。寺旁建有当年达鲁花赤之墓地[3]。元代回回在浙江形成了聚居区,其中回回官员人数16—17人。在《金华府志》中记载了元代有回回官员17人,其中标明义乌籍回回官员则有16人[4]。之后,东南沿海的唐兀人、畏吾儿人有皈依伊斯兰者便渐渐融入回回当中。明清乃至民国年间义乌已无文件记载穆斯林的活动,故而无法对当时的伊斯兰教状况和回族人数加以考证。新中国建立后,据统计因工作、婚嫁、经商等来义乌定居的回族人数1953、1964、1982年分别为2人、11人、19人[5],1989年19人[6]。 (二)改革开放以来流动穆斯林人口现状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和城乡社会的巨大变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客观条件,流动穆斯林人口离开故地,找寻新的生计,致使东南沿海各地流动人口规模和数量迅速扩大和增加。故而,长三角地区不仅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而且也是流动人口最密集流入区域之一。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统计显示,义乌市常住人口91.27万人,其中有45万流动人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2.5万,全国有42个少数民族成员都在义乌留下了身影。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统计显示,义乌市常住人口123.4万人,其中市外流入人口为58.58万人,常驻外商1.3万人,48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到6万多人[7]。因没有具体的数字,笔者结合田野访谈数字估计流动穆斯林人口约占总数的50%。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成员不但是流动大军的一份子,而且其“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标记因他们在长三角诸城市的生存状态、群体行为等关涉族群关系、族群互动、文化传承等较抽象的深层问题,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如今留居长三角的流动穆斯林人口,其中经营西北(兰州)拉面的青海省化隆、民和、循化等县的回族、撒拉族从业者就有7万之众,开办餐馆5 000多家,其中义乌400多家,温州300家,绍兴100多家。同时,长三角也有数万维吾尔族从事干果(杏干、葡萄干)、烤羊肉串、切糕、烤馕等。此外,还有大量流动穆斯林在长三角外资、中外合资企业务工,一部分成为中东、中亚、东南亚地区派驻义乌、温州、绍兴等地的商务机构代表,从事商务代理和翻译工作。以“短工”“零工”“散工”和活动在大街小巷的“小摊贩”身份出现在长三角诸城市的流动穆斯林人口也为数不少。如此之众流动穆斯林涌入长三角,他们的从业情况复杂多变、流动性强、分散居住,他们在相异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因其宗教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和挑战,但大多数流动穆斯林人口都能恪守传统的文化信仰。 据统计,1998年长三角穆斯林人口约为3万余人,2013年底则高达20多万人。其留居地也从上海、南京、杭州等一线城市不断向温州、义乌、绍兴等二线城市延伸发展。参加穆斯林两大节日会礼的人数已高达15万之众。在温州、义乌、绍兴,每年参加穆斯林宗教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加。依据三地伊斯兰教协会提供的数据,1998年,每周聚礼人数不足100人。2003年,聚礼100—200人,会礼1 000人;2010年聚礼1 000人,会礼则达到5 000人。2013年,聚礼人数达3 000人,会礼人数20 000人。此外,每年参加各清真寺组织的圣纪、拜拉提夜、盖德尔夜等活动的穆斯林人数亦逐年增加。 二、长三角流动穆斯林人口的文化认同 长三角流动穆斯林诸族群主要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如西北、西南,当他们迈入高速运转的长三角城市现代化社会生活,其主要聚居地位于城乡结合部,那里生活条件较差、居住环境恶劣,身心长期处于蚊虫叮咬、高温的湿热环境中难以忍受。可是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人们能吃苦耐劳,大都能恪守伊斯兰教的信仰,虽然身处异乡但精神世界较为充实,久居自然会克服气候、环境等外在不适问题。然而,长三角流动穆斯林在文化适应方面最迫切、最突出的问题在于能否坚持信仰、族群语言的使用、饮食禁忌等文化特质。如此文化特质的不断适应,进一步增强族群认同、族际互动和吸引更多内地流动穆斯林前来谋生,故而,客观上为长三角伊斯兰教注入新的活力。 (一)流动穆斯林人口的族群语言差异和内部认同的增强 长三角流动穆斯林人口主要指的是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除回族(青海化隆部分回族使用藏语)外,其他流动穆斯林人口大都使用本民族语言,语言使用情况复杂。在长三角诸城市尽管大多数人在族际互动中使用汉语,但主要以西北方言为主,仍然存在着普通话和长三角方言如吴语、江淮官话、闽南语等难懂的困境。 从长三角流动穆斯林人口构成比例来看,回族占流动穆斯林流动人口总数的90%以上,虽然大多数人都使用汉语,然而他们普通话发音不标准,地方口音较重,从而与当地群体在交流时难免语言不畅。虽然他们有些人在学校学习过汉语但汉语发音受甘青口音、方言影响很大,而在民族聚居区人们主要使用族群语言,因此,普通话的运用能力较差。他们留居长三角诸城市后,不仅需要提高普通话表达能力,而且也要了解吴语、江淮官话、闽南语等。因此他们在与当地族群成员交流时,害怕表达错误或担心被人听不懂常常反复组织语言,进而感觉交流压力很大。田野表明,长三角流动穆斯林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掌握了吴语、江淮官话、闽南语的简单词语,在其日常生活、工作中仅能听懂个别口语,绝大多数人对以上方言无法熟通。 显而易见,长三角流动穆斯林人口的语言差异在其社会交往过程中产生诸多不便,从而使其交流、接触的范围有限,生活单一。工作之余的空闲时间,他们或者蜗居于出租房内,或者与本族群同胞相聚一场。在族群内部,他们才能找到相同的语言交流场景,通畅、自如地交流。语言的差异也导致不同的流动穆斯林族群留居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流动穆斯林族群内基于同一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乡土情结等因素而出现“抱团”聚集现象,这是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环境而增强自我保护和文化认同的必然选择。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流动穆斯林族群仅限于单一的族群内的互动和交流。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流动穆斯林族群因同一宗教信仰“似曾相识不相知,一声色兰变知己”。众所周知,在伊斯兰教活动中无论是回族,还是其他9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均操同一种语言——阿拉伯语与经堂语(波斯语),从而密切了他们之间的互动,频繁的交往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普通话和当地方言之不足,拓展了都市社会中流动穆斯林族群的文化交往和互动空间。 (二)从业结构单一和传统文化的恪守 绝大多数流动穆斯林人口主要来自农(牧)村,当迈入都市现代化社会环境时,因普通话表达有限,方言不通致使他们成为边缘群体,其从业结构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整体而言,流动穆斯林人口从业结构单一,可选择范围有限,基本以开办清真小餐馆、街头摆摊设点、流动小商贩、商业贸易为主而求生。 2000年以来,青海化隆、民和、循化、大通等地回族、撒拉族获得当地政府的培训和资助而陆续来到长三角开办了清真拉面馆。同时也有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穆斯林开办中高档饭店。兜售电话卡、发菜、买卖外汇的流动穆斯林人口比例也较大。此外,在义乌、温州、绍兴等地还有大量的阿拉伯国家、国外穆斯林团(个)体创办的贸易代办处,贸易公司数量亦可观,从而也吸引部分流动穆斯林从事阿拉伯语、英语的翻译工作,仅义乌就有2 000多人专职阿拉伯语、英语的翻译。另外,流动穆斯林人口在长三角各类企业集体务工的人数很少,也有部分流动穆斯林人口经所在地政府以扶贫渠道培训而在长三角进行劳务输出等等。 长三角内地流动穆斯林所从事行业局限于商业买卖和服务行业。其行业特点带有明显的穆斯林文化符号,尤其是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乃穆斯林最传统的职业。归根到底,来自流动穆斯林族群本身的文化约束,大多数流动穆斯林人口科学文化素质较低,适应高速运转的现代化城市生活的基本技能、知识较弱,加之普通话表达能力较差,方言交流有限等,因此,只有选择本族群最传统的、熟知的清真餐饮业才能立足于陌生的都市。 流动穆斯林人口因宗教信仰而产生高度的认同感,证实了文化信仰之价值所在。在长三角主流社会的认知中,流动穆斯林倾向于“抱团”存在,他们有自我的小世界,见面互道“赛俩目”如同旧识,侃侃而谈,亲近有加。偶遇困难,往往求助于亲戚、老乡,人际交往圈较为狭窄。田野表明,流动穆斯林人口在离开故土前,主要居住在农(牧)村,伊斯兰教信仰虔诚,来到长三角诸城市后,努力参加每周的聚礼便成为丰富其精神世界的归宿,故而,清真寺则成为其心灵世界的最佳安全港、停泊港。只有在清真寺,教友、老乡、朋友相见互道“赛俩目”,共同礼拜,彼此顾惜缘起于伊斯兰教信仰,认同强化,宗教凝聚力增强。 (三)清真餐饮的发展与流动穆斯林人口的壮大 一般来说,宗教信仰和实践是区分“我群”和“他群”的边界,穆斯林最根本的文化特征即是伊斯兰的文化特征。饮食问题通常是穆斯林恪守文化特质的重要原则,无论他身居何处,均要食用伊斯兰规定的合法(哈俩里)食物。流动穆斯林大多数有虔诚的信仰,自然在饮食上会按照宗教规定进食,非清真食物勿动、勿食,因而每到一地,查问是否有清真饭馆,饮食便利与否乃是决定其立足、留居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特别是2000年以来,随着长三角流动穆斯林人口的大量进入,内地许多清真餐饮业入驻长三角也促使长三角清真餐饮业的快速发展。 清真餐馆的大量出现,便利了穆斯林的生活,经营者收入颇丰,进而吸引更多的流动穆斯林从事清真餐饮服务,逐渐形成了“亲帮亲、邻帮邻”的规模化效应。其租赁30—50平米的房子作为店面,以家族式经营方式开张营业。清真餐馆消费群体不仅包括进城务工者、学生、城市白领,而且最主要的对象是进入长三角诸城市找寻生计、创业的流动穆斯林群体。十几年来,流动穆斯林人口资源在长三角诸城市的壮大的重要因素与清真餐馆的遍地开花密切相关。拉面餐馆的扩张随之带动了肉牛育肥、面粉加工、餐具消毒等生产、运输等相关清真餐饮产业链的发展,进而吸引更多的流动穆斯林人口从事相关行业。 如今,清真拉面馆逐渐融入长三角诸城市。通常,清真拉面馆选择店面都会以穆斯林的就餐需要为前提,且大多数都和汉族餐馆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满足穆斯林心理“就餐”的需要。同时,售卖干果(杏干、葡萄干)、烤馕、切糕、烤羊肉串的维吾尔族摊贩基本上是以拉面馆为同心圆散布在大街小巷。从而在空间分布上,以拉面馆为中心,维吾尔族商贩遍布四周的分布格局。虽然摊贩和拉面馆产生的交集不多,但为了满足在异乡生存的需要使二者形成稳定的生物链。最为重要的是,清真拉面馆在长三角诸城市的蓬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流动穆斯林人口的饮食问题。尽管流动穆斯林的“吃饭”问题解决了,但依然存在购买清真副食品、肉食品难的问题。随着流动穆斯林人口大量涌入长三角诸城市,随之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增加,故而一些穆斯林在当地也开办起清真超市以供应清真副食品、肉食品和穆斯林特殊产品。例如义乌五爱新村、桥东路、江东区等均有了供应清真副食品、肉食品的超市,丰富了流动穆斯林族群的生活需求。 总之,清真食品是所有穆斯林族群恪守的重要原则。在我国,穆斯林族群通常以饮食是否清真来作为文化信仰是否虔诚的底线。我国穆斯林长期以来因受饮食禁忌底线的约束,大多数都不愿离开故土步入城市。随着长三角清真餐馆的大量出现,供应清真副食品、肉食品的清真超市的诞生,清真食品供应能力增强,从而使长期以来困扰流动穆斯林人口的吃饭、饮食问题得以解决,维护了穆斯林族群的文化信仰的底线,城市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的保障,生活水平、质量随之有所提高,促使更多的流动穆斯林步入长三角,渐趋颇具群体规模,他们则成为穆斯林族群的中坚力量,有利于推动长三角伊斯兰教的新发展。 三、清真寺的建立和聚礼点、临时礼拜点的发展 如上所述,长三角流动穆斯林族群以信仰伊斯兰为基础产生的认同,使原来单一的族群界限被打破。在长三角流动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维吾尔族等族际互动中,文化信仰的纽带作用不可忽视。拜功是伊斯兰教的基石,穆斯林成哲玛提②(集体)礼拜被视为可嘉的行为,尤其是每周的聚礼和两大节日会礼尤为重要。不可否认,伊斯兰集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为一体,但更重要的其是乃一种生活方式。因此,长三角流动穆斯林族群坚持了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特征,基于此,自然形成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流动穆斯林族群的互动圈。其实族群文化中能够真正持久产生认同基质的因素乃宗教,其与族群意识密切勾连起来,是族群心理归属感的表达。长三角诸城市流动穆斯林有着浓厚的宗教意识,他们信仰虔诚,但因居住环境、语言交流等不适应,清真寺则被视为其丰富心灵世界的重要场域,他们在此聚集、礼拜,寻找精神归宿。 在流动穆斯林人口经济收入有保障、形成群体留居规模后,兴建清真寺的便提上日程。此外,流动穆斯林的宗教热情和实践也激发了原本信仰趋弱、很少入寺礼拜的世居回族的宗教情感,触发部分回族思想回归和流动穆斯林一道参加日常宗教活动,带动长三角伊斯兰教出现新的发展态势。 义乌、温州、绍兴世居穆斯林较少,随着回族人口的向外迁移或者汉化,部分原有清真寺被废弃或者消失。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城市逐渐成为流动穆斯林人口迁入和留居地。他们远离故土步入长三角诸城市后,因清真寺数量有限或居住地与清真寺距离太远给其生活带来诸多不适。对穆斯林而言,清真寺不但是宗教场所,而且也是其习学知识,开展社会互动的重要场域。对流动穆斯林人口来说,迈入陌生的都市环境,加之面临艰难和困苦之时,清真寺则是获取心理慰藉和寄托情感的港湾。因此,修建清真寺便成为穆斯林群(个)体的共同心愿和迫切要求,并促使大家行动起来解决问题。流动穆斯林来到长三角伊始大都在各自出租房屋内礼拜,因穆斯林较重视每周聚礼,有些热心的清真饭馆老板便在其饭馆内临时开辟一室为众穆斯林提供礼拜之便,这样临时拜所成为聚礼点。随着聚礼人数的增加,临时拜所毕竟因容纳量有限,乃出现大众集资租用固定房屋,聘请阿洪成立礼拜点之举。这样的礼拜点在长三角诸城市大量出现,当地政府也日益关注着流动人口的宗教需求,修建清真寺则逐渐被提上当地政府的日程。 (一)义乌伊斯兰的发展 长三角流动穆斯林的礼拜点最早是以清真餐厅为依托。创办于1995年的中国义乌小商品博览会从2002年开始升格为由国家商务部参与主办的国际性展会。此后,义乌吸引接踵而来的创业者、淘金者,善于经商的流动穆斯林在义乌市也积极活跃起来。20世纪90年代末,因来义乌的流动斯林增加,他们大都住在义乌市工人路的红楼宾馆,礼拜就在宾馆房间里。宾馆为了留住顾客专门腾出会议室和仓库供穆斯林礼拜。2001年,红楼宾馆获得义乌政府部门的认可从而成为义乌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伊斯兰活动场所,也标志着伊斯兰教在义乌的传播开始。2002年,义乌穆斯林人口达5 893人,红楼宾馆礼拜点根本无法满足穆斯林参加每周聚礼的需求。2004年4月,许多参加广交会的中东商人顺道涌入义乌寻找商机,当时参加聚礼的近3000人都跪在马路上,致使严重堵塞交通,引来围观。2004年9月经政府协调将位于江滨西路90号原义乌丝绸厂旧厂房改造成礼拜场所,面积2500平米,能容纳5000人同时礼拜。义乌作为中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商人,同样,也吸引着流动穆斯林来到义乌从事清真餐饮、商务代理、阿拉伯语的翻译工作。很多宾馆都逐渐地为流动穆斯林开辟礼拜场所。 温州、绍兴聚礼点、礼拜点的出现和发展大都和义乌类似。田野中,笔者了解到,从经营清真餐厅的老板的角度来看,在自己餐厅能开辟一室供流动穆斯林大众礼拜之需,使很多穆斯林聚集于该餐厅,不但给餐厅留下较好的口碑和声誉,而且还会招揽更多的穆斯林宾客满座,获利丰厚,此乃一举两得。在经营清真餐厅的老板获利后,常常愿意慷慨解囊资助礼拜点的日常开支,包括房租、水电费、卫生、垃圾处理费,有些大的礼拜点还要开支阿洪的工资等。温州、绍兴等地聚礼点、临时礼拜点基本按此模式发展起来。 (二)温州伊斯兰教的发展 1998年青海化隆回族妥生祥开了温州第一家拉面馆。据妥生祥介绍,当地户籍的回族基本上不礼拜。虽然温州有清真寺,但因历史原因,当地4户回族长期居住在清真寺,导致清真寺一直没有恢复。2004年开斋节,流动穆斯林在温州汽车西站的奥林匹克体育场集体参加会礼,结果引来城管等询问。2004年以后,拉面馆迅速在市区铺开。2005年初就有170多家。到2013年温州的清真餐馆有400家,每周参加聚礼的有200—300人,参加会礼的有3 000人左右,去何处礼拜成了众人面临的最大问题。 据说,温州穆斯林礼拜点起始于2001年,以后数度搬迁,更换地址。流动穆斯林频繁的搬迁礼拜点的活动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温州市政府最终在2006年协调将鹿城区粮食供应公司的办公室租为临时礼拜点。临时活动场所主要为参加聚礼的穆斯林提供方便。除了聚礼和斋月,其余的时间聚礼点基本都关门。每逢开斋节、古尔邦节的会礼场所均要另找。田野调查中,妥生祥介绍,2007年的开斋节会礼首次在温州隔岸路的羽毛球馆举行。他说:“我在温州汽车西站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参加过5年的会礼。会礼的人数,从20世纪末的300—500人逐年增加到2013年开斋节有3 000多人。”后经多方努力,2005年8月19日温州市民族宗教局下达温民宗(2005)66号文件,同意设立伊斯兰教临时活动场所,文件称之为“聚会点”。温州海区梧田街道鱼鳞夹金穗商贸城B幢二楼(207室)可续租作为穆斯林群众临时聚会点。据统计,到2013年底,温州有穆斯林人口2万人,建有1座清真寺,设立18个礼拜点且都聘请专职阿洪。 (三)绍兴伊斯兰教的发展 绍兴历史上原本无世居穆斯林,所以没有清真寺。现在绍兴的穆斯林主要来自流动穆斯林人口。目前,在绍兴学习、工作、生活、经商的穆斯林约有6 000人。2003年一些拉面馆老板共同出资在柯桥镇港越路租了一套100平米的民居作为临时聚礼点。2005年绍兴城区里租借当地天主教的教产作为礼拜点。据了解,每周都有200多穆斯林参加聚礼。在开斋节和古尔邦节,前来参加会礼的穆斯林达1 000多人,穆斯林大众便相约在柯桥公园礼拜。2008年以后,绍兴穆斯林先后租赁柯桥区五洲大酒店、天宇大酒店作为伊斯兰教临时宗教活动场所。其中五洲大酒店面积670平方米,平时礼拜人数50人左右,周五聚礼有600人,天宇大酒店租用房面积700平方米,平时礼拜100人左右,周五聚礼有800人。 随着来绍兴打工、经商的流动穆斯林增多,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成倍增长,给临时活动场所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开斋节、古尔邦节更是特别拥挤。据了解,这两个临时活动场所最多仅可容纳1 500人左右礼拜,但在绍兴流动穆斯林少则2 000人,多时甚至有5 000—6 000人,根本无法容纳。且这两个临时活动场所均设在酒店屋顶,使用简易材料搭建的临时建筑,不仅不能承重,而且消防通道不畅,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另外,五洲大酒店业主调整经营重新装修,不再出租,只在周五聚礼为穆斯林开放一天。天宇酒店也已在轻纺城西市场改造规划中被列入拆迁范围。绍兴伊斯兰教礼拜点存在的问题和新出现的情况,引起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未雨绸缪。经过政府和流动穆斯林大众的努力,2013年8月13日,租赁绍兴柯桥最繁华的笛扬路746号一商务大楼的5幢301室868平方米的场地,能同时容纳1 200多人礼拜。同时,绍兴亦成立伊斯兰教活动场所民主管理小组,其成员主要来自流动穆斯林人口。 毫无疑问,倡导修建清真寺、建立聚礼点、礼拜点者都是那些虔诚的流动穆斯林所为,其中,经营清真拉面的青海籍穆斯林贡献颇大。在论及此现象时,学者们也有提到留居的国外穆斯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国外穆斯林在我国的生活、工作、经商等活动,客观上也助长伊斯兰教在长三角的发展。义乌、温州、绍兴成为这些人的留居地,人口数量毕竟有限,他们是“匆匆过客”,又没有“公民”身份。根据中国的政策法规要求,国外穆斯林只有从经济上资助我国穆斯林修建清真寺,他们却无法获取修建清真寺的资格。因此,流动穆斯林诸族群才是真正推动兴建清真寺的建设者。客观上因穆斯林的流动人口进入长三角,逐渐形成留居的群体规模,主观上因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故此他们的主客观努力推动了长三角伊斯兰教的新发展。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长三角诸城市伊斯兰教的新发展,离不开宽松、开放的城市社会环境,政府的包容、开明的心态和理念。清真寺获得开放、修缮、重建、新建也离不了当地政府从政策、财政等方面的关心和支持。比如,义乌、温州、绍兴政府部门很重视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每逢开斋节给穆斯林放假一天。绍兴民宗局每逢两大节日会礼,都会帮助穆斯林联系室内体育馆等公共设施为穆斯林提供方便。 一般来说,移民带入的文化在移入地总是以多元化的方式生存,而移民与移入地的文化共存是一种常态。特殊情形则是在较为包容、开明的文化、社会环境中,原生形态的文化得以保持,同移入地主流文化一起形成多元文化社会。归根到底,多元现象的并存和移民群体数量的多少和规模大小密切相关。因具有相异的族群文化背景,长三角流动穆斯林诸族群和主流社会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有迥异的文化特质表现。客观地掌握和了解流动穆斯林的规模、数量和生产、生活状况、长三角伊斯兰教发展态势,不仅有利于长三角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对新时期局部地区的民族宗教工作的开展和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意义。 ①达鲁花赤,是蒙古语,原意为“掌印者”,是蒙古帝国历史上一种职官称谓,也就是督官。 ②哲玛提,阿拉伯语音译,意思是集体、群体。中国穆斯林在伊斯兰教功修中,特指礼拜时候的集体礼拜。标签: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穆斯林论文; 长三角论文; 绍兴论文; 回族风俗习惯论文; 中国温州论文; 清真饮食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义乌论文; 回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