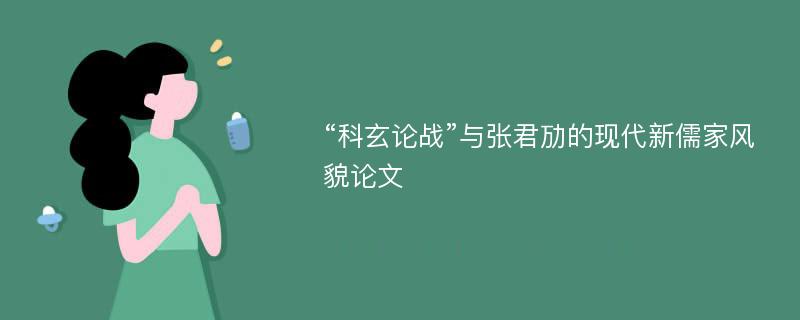
“科玄论战”与张君劢的现代新儒家风貌
陈寒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天津300380)
[摘 要] 一生游走于学术与政治的张君劢,是在1923年“科玄论战”中以“一造”之主角的身份跃登现代中国哲坛的。他一出场,便向世人呈露出一位现代新儒家的风貌。他当时所提出的“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观念,与此前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提主张完全一致,并都成为其后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立场,因而他与梁漱溟共同开启了现代新儒学形成发展的历史序幕。
[关键词] 五四新文化;“科玄论战”;张君劢;现代新儒家
一
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思潮和学术流派的现代新儒家(学)是在“五四”时期开始产生的。此前已有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国粹派”,倡言“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揭扬文化保守主义徽帜,而到“五四”时期,杜亚泉、钱智修相继主编的《东方杂志》和章士钊主编主撰的《甲寅》周刊继之而起,以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观念与《新青年》自由主义西化派相抗。尤其是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反孔教、反儒学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毅然以儒家圣贤的使命感起而为孔子出头说话。他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更以其十分鲜明的与“五四”启蒙者文化主张截然有别的观点揭开了现代新儒家(学)形成发展的历史序幕,故此书实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张君劢对东西文化问题也十分重视,有着他自己的看法,如其留德回国后不久在江苏中华教育改进社所作题为《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讲演中,就提出了很系统的思想,并且对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有所关注,他曾评析道:
梁任公先生告诉我,梁漱溟之孔学,乃阳明门下泰州一派,则自得者,孔子之一部而非全体也。譬如梁漱溟先生释孔子之“仁”字,引“予之不仁也”以证明此“仁”字乃感情温厚直觉敏锐之意。然而孔子答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答子张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言礼言祭言大宾,其郑重将事为如何?而非直觉二字之所能尽明矣。以吾看来,所谓“仁”所谓“义”,孟子说得最好,乃是不学而知,不虑而能之良知良能,既无所谓理智,亦无所谓直觉。梁先生书中乃强名此良知良能为直觉,则康德之实行理性,亦名为直觉派哲学可乎?①
虽然张君劢不是很赞同梁漱溟的孔学观,但他对梁氏的文化哲学之类于黑格尔的理论贡献还是予以肯定性评价:“梁先生此书,虽名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吾人观之,非关于三方面文化及哲学之研究,乃梁先生对于三方文化之特点,自己拟定一个方式而贯串之。所谓三方面文化之特点,西洋向前要求,中国为调和持中,印度为转身向后要求。此种说法,可谓为梁先生自身之文化哲学,与黑格尔以一人自由说明亚洲文化,以少数人之自由说明希腊罗马文化,以全体人之自由说明现代欧洲历史,有相似之处。梁先生之贡献在此,而不在三方面文化之研究。”②更重要的是,张君劢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从不同于梁侧重于文化哲学的视角,而是从人生观的角度,即以“科学与人生观”论战③中“一造”之主角的身份在客观上紧随梁氏之后拉启代新儒家(学)形成发展历史序幕的。④
张君劢年长于梁漱溟,很早就形成关于民族文化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本位意识、创造意识的思想,但他早年全身心地追随梁启超从事政治活动,并不很重视学术,加之又一赴日本、数至欧洲,多年游学在外,中国学术文化界对他并不十分了解。直到“科玄论战”骤起,他才以现代新儒家风貌跃登中国哲坛。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应吴文藻的邀请为一批即将赴美学习科学的清华大学生作了一场题为“人生观”的演讲。1921年11月,他在巴黎曾给中国留学生演讲《倭伊铿精神生活哲学大概》(演讲稿发表在《改造》第3卷第7号上)。而这一次,他则依据着倭伊铿《大思想家的人生观》(Die Leben-Sanschaungen der grossen Denker,1890)一书中阐论的科学并非万能的思想来讲述他对人生观问题的看法。大约考虑到听讲者是赴美学习科学的学生,故而他开篇即言:
诸君平日所学,皆科学也。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譬如二加二等于四,三角形中三角之度数之和等于两直角;此数学上之原理原则也。……诸君久读教科书,必以为天下事皆有公例,皆为因果律所支配。实则使诸君闭目一思,则知大多数之问题,必不若是之明确。而此类问题,并非哲学上高尚之原理,而即在于人生日用之中。甲一说,乙一说,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此何物欤?曰人生。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人之最不同一者,莫若人生观。⑤
接着,他进一步说明人生观没有公例可循道:“人生观之中心点,是曰我。与我对待者,则非我也。而此非我之中,有种种区别。就其生育我者言之,则为父母;就其与我为配偶者言之,则为夫妇;就我所属之团体言之,则为社会为国家;就财产支配之方法言之,则有私有财产制公有财产制;就重物质或轻物质言之,则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凡此问题,东西古今,意见极不一致,决不如数学或物理化学问题之有一定公式。”⑥他又指出,我与亲族、我与异姓、我与财产、我对社会制度之激渐态度、我的内在心灵与外在物质、我与所属之全体、我与他我、我对于世界之希望、我对于世界背后有无造物主之信仰,“凡此九项皆以我为中心,或关于我以外之物,或关于我以外之人,东西万国,上下古今,无一定之解决者,则以此类问题,皆关于人生,而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也。”⑦他由此进而将科学与人生观加以比较:第一,科学为客观的,而人生观则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学的,为方法论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相同之现象,而人生观则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就以上所言观之,则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⑧。”“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追求之于己,而决不能以他人之现成之人生观,作为我之人生观者也。人生观虽非制成之品,然有关人生观之问题,可为诸君告者,有以下各项:曰精神与物质,曰男女之爱,曰个人与社会,曰国家与世界。”⑨他最后强调自己本次演讲的主旨道:“方今国中竞言新文化,而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西洋之有益者如何采之,有害者如何革除之;凡此取舍之间,皆决之于观点。观点定,而后精神上之思潮,物质上之制度,乃可按图而索。此则人生观之关系于文化者所以若是其大也。诸君学于中国,不久即至美洲,将来沟通文化之责即在诸君双肩上。所以敢望诸君对此问题时时放在心头,不可于一场演说后便尔了事也。”⑩由此不难看出,张君劢发表这样一篇演讲,其目的显然是要对那些即将赴美留学而又会以科学为职业的中国学生进行一次“人生观”教育,试图使他们认识到科学不是世界上的一切,亦非万能;西方文明绝不是人类文明的唯一标准,中国文化自有其价值;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依靠科学而要依靠人自己,并且,人生观问题说到底是个文化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化,数字经济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数字经济规模加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积极拥抱数字化,加速转型升级,重塑竞争优势。自2017年首次向中国市场推出ABB AbilityTM,ABB已为油气石化、汽车、机械、钢铁、交通等行业的数十家企业提供了行业领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支持用户实现安全、高效的数据集成和分析,为用户提高绩效和生产效率提供帮助。
张君劢的这篇演讲稿登载在《清华周刊》第二七二期上。胡适读到后大为不快;丁文江亦勃然大怒而与之面辩良久,为了“玄学的鬼附在张君劢身上”⑪,更为了“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在身上的青年学生”⑫,先后在《努力周刊》上发表了《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和《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两篇长文,着重指出:“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凡是真的概念推论,科学都可以研究,都要求研究。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⑬“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伦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知道生活的乐趣。”⑭这实际将张君劢演讲中提出的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能否在科学方法之外寻求人生观的是非真伪问题,转换成为科学的知识论及其分类原则如何处理人生观与科学以及精神科学与物质科学之关系的问题。
要想提高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和动力,那么教师就需要创造有趣的教学情境来调动学生的兴趣,从而使学生主动参加到课堂教学中来,而使用微课就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在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活动中,利用微课模拟真实的数学应用情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课堂教学引入教学内容主题中。它可以提高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的兴趣和动机,帮助建立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充分感受到数学知识改进、进步的过程以及成就感,同时提高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对此,张君劢在1923年4月29日和5月6日出版的《努力》周刊第50、51期上发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进一步系统阐述他的思想;该文又为《晨报副刊》连载,引起更大反响。在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中,他批评其朋友丁文江“中了迷信科学之毒”,并旁征博引地申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强调支配人生观的不是理智,而是情感和意志。他认为包括人生观在内的精神科学与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物质科学是不同的;物质科学是经过观察、比较与试验之后得出的一定的自然公例,这些自然公例一经成立便不可动摇,而一言及精神科学如政治与生计之类就根本没有什么公例可求,因为精神科学的客观规律只限于已经过去的事情,对于未来则是不可能进行推演的,故依严格的科学定义来说,精神科学已不可认为是科学,当然,属于精神科学范畴的人生观自然也不是科学。他说:
由图5可以看出,虽然锚固长度和锚杆承受载荷等级大小不同,锚固剂-围岩界面的剪应力均在端口出现剪应力集中,且随着锚固深度的增大,界面剪应力逐渐变小。分析可知,轴向载荷作用下,锚固剂在锚固段外端口最容易出现界面滑移脱黏或锚固剂剪切破碎。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性破坏,使西方不少人士对其身处的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1918年出版的斯宾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就反映了这种心态。对此身历其境地进行过考察的梁启超,归国后即出版《欧游心影录》,很形象地描述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充满怀疑与失望之情道:“一百年的物质进步,比之从前三千年所得还要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象沙漠中失落的旅人,远远望见一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随同梁氏赴欧考察战后状况并居德游学的张君劢,不仅对“一战”后西方社会心理有深切体察,而且还曾从文化角度颇为深刻地评析过造成“一战”的原因,说:
㊴[61]《新儒家思想史》第601页,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7年版。
在君知之乎!当此人欲横流之际,号为服国民之公职者,不复知有主义,不复知有廉耻,不多知有出处进退之准则。其以事务为生者,相率于放弃责任;其以政治为生者,朝秦慕楚,苟图饱暖,甚且为一己之私,牺牲国家之命脉而不惜。若此人心风俗,……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所谓实际上之必要者此也。㉒
他又针对丁文江引管仲所谓“衣食足而后知礼节,仓廪实而后知荣辱”来论证其说而言曰:“若夫国事鼎沸纲纪凌夷之日,则治乱之真理,应将管子之言而颠倒之,曰:‘知礼节而后衣食足,知荣辱而后仓廪实。'吾之所以欲提倡宋学者,其微意在此。”㉓张君劢的这些表述说明他反对科学支配人生观,提倡“玄学”或“新宋学”,旨在为人类社会和世界文化,尤其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寻找新的出路。唯其如此,他才会说:“若固守科学的教育而不变,其最好之结果,则发明耳,工商致富耳;再进也,则为阶级斗争,为社会革命。此皆欧洲己往之覆辙,吾何苦循之而不变乎?”㉔并说:“物质文明之内容定矣,吾乃发问曰:苟今后吾国以西方文明四大特色为标准,从而步趋之,则其利害当如何?以言乎思想上之唯心唯物与夫目的机械之争,今日欧美之迷信科学者,已不如十九世纪初年之甚,故欲以机械主义支配中国之思想界,此必不可得者矣。若夫深信富国强兵之政策者如国中尚不乏人,而国家前途最大之危险亦即在此。”㉕
稍后,张君劢在中国大学所发表的题为《科学之评价》的演讲中,再次阐述科学的目的在求一定之因果关系,此方法最成功的地方无过于物理界,而对于不受因果支配的心理学、生物学特别是社会、历史领域,如“文学之创作,思想之途径,乃至个人之意志与社会进化之关系,谓其可以一一测定,这是科学家的梦语了”㉖;“科学家但说因果,但论官觉之所及,至于官觉之所不及”如“伦理学上善恶是非之标准,以及人类之美德如忠考笃敬之类”“则科学家所不管”㉗;“若谓论理的推理由于习惯而来(经验派哲学之言),道德为环境所支配,这是科学欲以有形解释无形之故,乃将人类精神之独立一笔抹杀了”㉘。他指出科学能给人类带来物质文明,却不能带来精神文明。因此,不可太重视科学而忽视人生观问题。人生在世,存在着形上、审美、意志、理智、身体五大方面的问题,科学主义注重于身体和理智,却忽略了形上和情意(审美、意志),故而科学绝不是万能的。“人生原不能离开物质,然一国之文明,致令人以物质文明目之,则是有极大原因在。而其原因之可数者,利用科学之智识,专为营利之计,国家大政策,以拓地致富为目的,故人目之为物质文明”㉙;科学在欧洲造就出了巨大的物质文明,这“是科学上最大的成绩”,但“专求向外发展,不求内部的安适,这种文明是绝对不能持久的”㉚。所以,他告诫“诸君认清今后发展之途径,不可蹈前人覆辙。什么国家主义、军阀主义、工商主义,都成过去;乃至思想方面,若专恃有益于实用之科学知识,而忘却形上方面,忘却精神方面,忘却艺术方面,是决非国家前途之福”㉛,并据之而提出要正确处理好欧洲以往思潮与吾人今日思潮之关系:“若以欧洲以往之思潮为官觉主义,而以吾人之思潮作为超官觉主义,则其利害得失当如下表:第一,官觉主义之结果:实验科学发达,侧重理智,工商立国,国家主义。第二,超官觉主义之结果之预测:重精神(或内生活)之修养,侧重情意,物质生活外发达艺术,国际主义。今后吾国将何去何从,是文化发端之始的极大问题,望诸君再三注意。”㉜
后来,张君劢回忆并评论道: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
回想当年“人生观”之论战,起于我一篇“人生观”演讲。吴君之藻、为清华大学生时,约我演讲。时我方自欧洲返国,受柏格森与倭伊铿之影响,鼓吹“人类有思想有自由意志”之学说。此乃哲学层与玄学层上之立言,胡适之读之大为不快,某日晚在宴会席告我——“我们将对你宣战”。及驳论印出,乃出于丁在君起稿,于是论战交锋达一、二年之久。我自身坦然处之,不以为意,因我内心乃知此为哲学上之悬案,无两造胜败是非定论之可言。
今日试将此一论战为之评价。我以为此乃吾国思想幼稚迷信科学万能之表现。欧洲各国受科学洗礼之后,亦同有此现象。法国拉曼脱里(Lamettrie,1709—1751)著《人生机器》一书,费尔巴哈(Feuerbach,1804—1872)主张唯物主义,命定论与无神论。德国唯物主义思想较后于法国,至十九世纪乃始开展。其代表之者为伏格脱(Vogt,1817—1895)、蒲 许 纳 (Buchner,1824—1899)、海 克 尔(Haeckel,1834—1919)等。此三人均主张世界构成之基本要素为物质,力与能,由物质生力,由力生热与运动。其实一也。此等学者之论调,以之与吴稚辉黑漆一团之宇宙观相比较,可谓为一鼻出气。丁在君有一枪打死后,人之精神安在之责同,其基本信仰与吴氏正同。我无以名之,名之曰唯物主义之先驱而已。此种唯物主义与中共之唯物辩证法大有异同,然其否认人类之精神与知识与伦理观念之起于彼此、黑白、是非之心灵作用,则异流而起于同源。试问宇宙之现象,有物质有生物人类,可谓复杂万端,岂“物质”一种元素所能解释?奈简单头脑风靡一时,致陷全国于疯狂状态,吾人惟有努力于今后之澄清,而往事之谁负其责?置之不问可矣。㉝
这场由其《人生观》演讲而引发的“科玄论战”,是以“玄学鬼”被人唾骂,广大知识青年同情、支持、理解和接受科学派的思想而告终的。“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更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需要,更符合向往未来、追求进步的人们的要求。承认身、心、社会、国家、历史均有可确定可预测的决定论和因果律,从而可以用以反省过去,预想未来,这种科学主义的精神、态度、方法,更符合于当时中国年轻人的选择。不愿再‘返求诸己'回到修心养性的‘宋学',也不能漫无把握不着边际地空喊‘意志自由'、‘直觉综合';处在个体命运与社会前途休戚攸关的危机时代,倾向于信仰一种有规律可循、有因果可导从而可以具体指导自己行动的宇宙—历史—人生观,是容易理解的事。”㉞徐复观尝忆其“年少时在沪购一书曰《人生观之论战》,于京沪车中总读一过,内容多不甚了了,唯知有一派人士斥君劢、东荪两位先生为‘玄学鬼'。玄学鬼即系反科学、反民主,罪在不赦。自此,‘玄学鬼'三字,深入脑际,有人提及二张之姓名者,辄生不快之感”㉟;杨允元也有类似的经历和感受:“中学时代读到‘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时候已在论战后好几年),才知道张君劢之名。大概当时一般青年像作者一样,都是充分赞同当日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和地质学家丁文江所倡导的‘科学的人生观',尤其是为胡适所特别称道的吴稚老的嬉笑怒骂的文章所激动。对于张君劢呢,只知道他是讲什么莫测高深的倭伊铿柏格森的哲学的,我们好像觉得丁文江骂他为‘玄学鬼',似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㊱即使“内心对于张君劢先生以及梁任公确有一些同情”的当年“还是一个中学生”的劳幹,虽接受“自然科学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的社会问题自是事实”,却仍坚信“科学方法也是正确的方法,而且张君劢先生以生机主义来反对自然科学也并不能打动人的心眩。就当时中国的客观需要言,当国家受列强重重压制之下,科学确实是一个翻身的工具,讨论科学的弊害已落在第二义。科玄之争的胜负,已超过了理智的问题而落在一般青年人情感问题之上”。㊲
正因充分注意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后“科学终于上升为包罗宇宙和社会人生的因果大法,上升为绝对永恒的真理,从而也成一种真正超验的玄学体系。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科学这个‘词'固然赢得了更广泛的公众,但却也失落了科学最本质的东西——自由批判的精神”,“走到这一步,科学主义的思想体系就不仅取消了对人本身的关注,甚至有了一种为所欲为的霸道,成为一种无视科学的真正学阀”㊳,此亦即他所说的“简单头脑风靡一时,致陷全国于疯狂状态”,所以,1934年和1963年,张君劢又两次发表《人生观论战之回顾》;1940年还发表了《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在全面批判胡适思想的同时,对他自己的人生观及其哲学理论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还批评“极端地提倡科学研究”的胡适道:“中国经书以及某种范围的史书,表现了形成中国传统一部分的道德原理和价值判断。胡适认为经史只是发见事实的资料,而忽视其中的道德价值,并且还引起中国的怀疑主义精神,从这两方面看,他确是……在中国造成精神真空的人。”㊴由此可见其对于主要是胡适、丁文江、吴稚辉和他本人参加的“着重于道德价值和自由意志的人生观论战”㊵以及他在这论战中提出的思想观念的看重;“科玄论战”确乎成为他毕生挥之不去的一个“情意结”。他虽坦承自己当年对于“人生自由”的提倡“不免过于充满了热与力”,但他仍郑重指出到现在“仍丝毫没有变更”。对于启蒙现代性和科学之流弊的反思、对于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探求以及对于儒家想想特别是儒家义理心性之学的重视,成为贯穿张君劢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
二
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开创的儒学本是“学做人”的学问,它大体上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培养德性,二是学习知识;此即《中庸》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道问学指的是以经典学习为主要内容的知识性活动,尊德性则特指道德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培育;两者之间虽以培养德性更为重要,但这两者又是内在统一、交相发明,不可偏废的。但自南宋朱熹与陆九渊论辩以来,“至于尊德性、道问学为两途,或沦于空虚,或溺于训诂,卒无以得真是之归”㊶,以至“中世以来,学者动以象山藉口,置尊德性不论,而汲汲乎道问学,亦不知古之所谓问学之道者何?或事文艺而流于杂,或专训诂而入于陋,曰我之道问学如此,孰知紫阳文公之所谓道问学者哉?”㊷到明代前中期,大体与王阳明同时的程敏政认为,“所谓尊德性者,知吾身之所得皆出于天,则无毫发食息之不当谨,若《中庸》之‘戒慎'、‘五藻'、‘九容'是也;所谓道问学者,知天下无一事而非分内,则无一事而非学,则如《大学》之‘格致'、《论语》之‘博约'是也。……大抵尊德性、道问学,只是一事。如尊德性者,制外养中,而道问学则求其制外养中之详;尊德性者,由中应外,而道问学则求其由中应外之节。即《大学》所谓求至其极者,实非两种也。”㊸所以,他指出,尊德性、道问学皆“入道之方”,应统一为一体,而不应将之对立。他申论道:“……盖尊德性者,居敬之事;道问学者,穷理之功。交养而互发,缺一不可也。”如果“尊德性而不以道问学辅之,则空虚之谈;道问学而不以尊德性主之,则口耳之习。兹二者皆非也”。㊹他以这种本于《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而又有所发展的思想来考察朱、陆之学,辨析二者异同,既认为朱子和陆子在“尊德性”“道问学”相统一上“殊途同归”,又指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体认“朱子之为学,泛观约取,知行并进,故能集大成而宪来世如此”㊺。应该说,程敏政此论不仅符合朱、陆思想实际,而且更对由所谓“尊德性”“道问学”问题上的歧见而引发的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朱、陆之辨”㊻做了总结。
说到青铜文化,各种著述无不自豪地描述古代的青铜文化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但是这种表述只说到了史实的一个层面,青铜文化另一个层面的意义,就像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告诉我们的那样,还有无数矿工千辛万苦的劳作,用血与汗擦亮了青铜器的幽冥绿光,用无数条鲜活而屈辱的生命,幻化成了我们灿烂的青铜文化!
如果说古人所谓“尊德性”类于今人讲的人生观,“道问学”类于今人讲的科学或科学知识,那末,历史上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就大体可相当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曾联系到儒学史上的朱陆之分与汉宋之争,他说:“……然吾确认三重网罗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而尤觉内生活修养之说不可不竭力提倡,于是汉学宋学得失问题以起。”“汉学宋学两家,苟名认定范围,曰甲之所研究在考据,在训诂名物;乙之所研究在义理,在心性。则各行其是而不至有壤地相接之争也。惟其不然,甲曰卫道,乙亦曰卫道;甲曰吾之学为圣学,乙亦曰吾之学为圣学;甲曰经学即理学,乙曰天下无心外之理,亦无心外之物。两家各认其研究对象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其方法不同。甲曰穷理即在读书中,乙曰读书不过穷理之辅佐,其甚者则曰六经皆吾注脚。因是之故,甲尊汉儒,乙宗明理学,同为理学之中,而又有朱子陆王之分。窃尝考之学术史上之公案,其与此相类者,莫若欧洲哲学史上经验派理性派,或曰唯心派唯物派之争。”㊼道德与知识的关系问题确实是“科玄论战”的焦点所在。
当然,20世纪20年代所进行的“科玄论战”绝不是历史上这种由“朱、陆之辨”引发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的简单重复,而是在20世纪时代背景下所展开的内涵极其深刻的思想论辩,“它是唯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交锋中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被凸现了出来。此后,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明确区分为两大阵营、两条路线,一方走的是科学的、实证的道路,另一方则走的是人本的、形而上学的道路。”㊽严搏非曾评论道:“1923年的科玄大论战,就其所涉及的哲学内涵甚或现代化的文化精神而言,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各次论争中最深刻,也最具现代意义的。它在论战初期所涉及的精神—物质、主—客体、自由—理性、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等问题,甚至到今天也还是当代哲学思考的焦点。它所争论的东西方文化问题,也一直是中国及亚洲许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时面临的巨大困难和基本问题。”㊾这显然是历史上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所无法比拟的。
历史上“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中,很有些儒家学者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不可对置而有着内在有机联系,程敏政这方面的观点已如上引,后于敏政的徐阶亦著《学则》,力言“尊德性、道问学原为一事”,又撰《学则辨》认为:“夫君子由学以入圣,犹人由门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问学为两门矣。然而圣之所以为圣,践形尽性之外,无他事也,尊德性、道问学,室一而已,门亦一而已,安得有异入乎?”㊿如此等等,难以尽举,亦不用一一引述。但是,在1923年的科玄大论战中,张君劢“把科学与人生观对立起来,否定社会科学的确实性、否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否定人的意志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宣扬意志万能、意志决定一切的主观唯心主义”[51],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他后来反思忆述道:
当时……自己要说的话,就是人生(Human Life)与自然界不同之上何在?我说了好几点……我当时脑子内所有“科学”二字,实在是指自然科学,不是指令部科学,因为自然界才能同人生对立起来说。假定有人来问我对此问题,现在意见如何,我可以明白答复,“人生观”(Lebensanschauung)之名,本于倭伊铿所著之“大思想家之人生观”,是指哲学史中各家对于人生与宇宙问题之答案,其为主观的,毫无疑义,我的老师重视大思想家之创造力,我是的确受他这方面的影响。然以人生观与科学对比,倭氏本无此说,我当时自己想出来的。我现在想想,人生观是思想家对于人生之答案,科学是科学家关于宇宙现象研究之结果,这两样虽可拿来对比,而对象上之不同不甚明显,故这样的题目,现在我自己也不赞成了。……话虽如此说,在大根本上人事界与自然界两方之不同,我现在仍丝毫没有变更。[52]
而另一方面,“如果纯从学术角度看,玄学派所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某些(只是某些)基本论断,例如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有根本区别,心理、生物特别是历史、社会领域与无机世界的因果领域有性质的不同,以及对非理性因素的重视和强调等等,比起科学派虽乐观却简单的决定论的论点论证要远为深刻,它更符合于二十世纪的思潮”[53]。所以,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提出的那些思想观念又自有其学术价值和思想史意义。并且,张君劢特别强调人生观的意义乃是针对着“吾国今日人心,以为科学乃一成不变之真理,颇有迷信科学万能者”,而“劝人不相信科学,不重视科学”则绝非其本意;事实上,在他看来,“欧洲之科学方法与社会运动足以补救吾国旧文明之弊,此信仰维持一文化之输入早一日,若此信仰而失坠,不独吾国文明无复兴之机,而东西洋之接触更因此阻迟”。[54]换言之,他自“科玄论战”以来,始终认为“科学的发展要受道德的限制”,尤其是当“知识的发展与人类的生存不能并立时,知识应受道德的限制”[55]。
三
人生者,变也,活动也,自由也,创造也。惟如是,忽君主,忽民主,试问论理学上之三公例(曰同一,曰矛盾,曰排中),何者能证其合不合乎?论理学上之两大方法(曰内纳,曰外绎),何者能推定其前后之相生乎?忽而资本主义忽而社会主义,试问论理学上之三公例,何者能证其合不合乎?论理学上之两大方法,何者能推定其前后之相生乎?⑮
欧美百年来文化之方针,所谓个人主义,或曰自由主义。凡个人才力,在自由竞争之下以国际贸易尽量发挥,于是见于政策者,则为工商立国,凡可以发达富力者则奖励之。吸收他国脂膏,借国外投资为灭人家国之具。而国与国之间,计势力之均衡,则相率于军备扩张,以工商之富,维持军备;更以军备之力,推广工商。于是终日计较强弱等差,和战迟速,乃有亟思乘时遂志若德意志者,遂首先发难,而演成欧洲之大战。今胜败虽分,荣辱各异,然其为人类之惨剧则一而已。于是追念往事者,悟昔日之非,谓此乃工商立国之结果也,此乃武装和平之结果也。一言以蔽之,则富国强兵之结果也。[56]
他对斯宾格勒所著书亦很有了解,谓“斯宾格勒(Spengler)的《欧洲的衰亡》(Untergangdes Abendiandes),此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轰动一时,后来有英译本,名曰《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因其书名引人注意,而且把欧洲人所崇拜的西方文化的没落,用预言家的态度说出,更使人们为之触目惊心。在德国国内,此书出版后引起各方面之评论,单单做批评的,也大大小小出过一本本书籍。这书所以引起如此的注意,在于它内容之丰富,立论之新奇,引征之广博。无论你不赞同亦好,但在他丰富材料下的立论,你是不能不吃惊的”[57]。
不过,诚如林安梧所说,由丁文江和张君劢对垒展开的“科玄论战”,“可视为当代新儒家的方向起源”。[58]从现代新儒学思潮史的角度看,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的《人生观》演讲,绝非简单地沿着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思路,基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反省“一战”教训,揭示欧洲文化危机,告诫人们科学并不万能,不能包办一切、代替一切,尤其不能用它来支配人生观,而是犹如稍早前粱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实质上是对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战的深化”[59]。尽管进路有所不同,但张君劢在《人生观》中明言:“方今中国竞言新文化,而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思潮之变迁,即人生观之变迁也。”又说:“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于己,而决不能以他人之现成之人生观,作为我之人生观者也。”其所提倡的“返求于己”正是儒家的基本精神;这与粱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断言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中国的人生态度的复兴,从这里动才是真动完全一致,都是在明确为儒家的人生观张目;“而张君劢所倡导的反求诸己的人生观无疑是接着粱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话题讲的。”[60]并且,梁、张二氏都将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与他们所自觉体认的儒学传统有机结合,认为这不仅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且是根治西方社会和文化危机的不二法门。他们就这样通过强调人之“理性”弘扬民族文化意识,以强烈的理想高擎起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巨帜,从而形塑了其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理路。这也就使得“科玄论战”中的双方,无论在主观意识上或者还是在客观事实上,都将这场论战视为其时广义的东西文化论战的一个重要部分。
唯其如此,他才会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说:
我国立国之方策,在静不在动;在精神上自足,不在物质上逸乐;在自给之农业,不在谋利之工商;在德化之大同,不在种族之分工。……以农立国,既乏工商之智识,又无物质之需求,故立国虽久,尚可勉达寡而均,贫而安之一境而已。今而后则何如乎?……此其强弱优劣至为明显,故多而不均,富而不安,殆为今后必至之势矣。
这里的理路和基本思想主张,无疑与粱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文化精神和文化生命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这样的理路和思想是张氏始终坚持着的,如其后来不仅坚称:“道德原则、习惯和信念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的主要部分。很显明的,这些东西是不能形成为科学定律的。”[61]而且还以比较哲学视野更宏阔地说:“哲学为讨论人生之应如何及人生所处之宇宙为何如之学问。其在欧洲,自亚里斯多德以来分为三部:第一曰逻辑,第二曰物理,第三曰伦理。在希腊时代,论理学方开始成为科学,绝无如现代以为研究象征逻辑便为尽哲学之能事者。亦未有以为物理世界之研究为哲学重心之所在者。至于伦理为研究人生之应如何,在希腊哲学家中之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氏均注重人生问题。苏氏、柏氏之哲学著作,与东方极多相似之处。惟亚氏著作中多分科之学之研究,则与东方异。然伦理之与政治合一为亚氏学说中重要部分,乃其同于东方之处也。至于现代欧洲哲学以认识为主题,此认识论之主题,即知识之可靠性(Validity)何在,由于科学知识之昌明,乃有认识论之出现。然认识论中之两派,一曰理性派,二曰经验派。此两派一以理性为主,与孟子所谓‘人心之同然'同;一以五官感觉为主,与荀子所谓五官当簿之言相近。自此方面言之,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固分途发展,然两者在根本上初不甚相远也。至欧洲哲学之其他派别如唯物主义,以物质世界之本质,推论人生问题,或和逻辑实证主义派以可证明者为哲学范围以内之事,其不可证者视为不在哲学范围以内之事。此两派忽视人生,否定价值,虽在西方视之为哲学,然与东方哲学相去远矣。”[62]又说欧洲学派中又“有物理学之机械主义有生物学之进化论。吾国自近半世纪以来,颇有持其说而鼓吹之者。进化论传入中国最早,以赫胥黎之天演论为第一书,由严复氏首先翻译;其后有达尔文氏物种源论,由马君武译出。此派学说证明万物之必变,其变由动植物起,自然为厌故喜新者所欢迎。机械主义说明宇宙变化由于物力之运动,否定精神力量,换言之,一切心理现象同于物理化学元素之化分化合。此说由吴稚辉之《一个黑漆一团的宇宙观》代表之。……吴氏之说显然为唯物主义,犹之英、法、德三国思想史在科学发达时代所必经之阶段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入中国,马氏持生产关系决定思想之说,恩格斯氏与列宁氏更以相反、对立与统一之说,推广为一切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之规律,是为辩证唯物主义,为共产党钦定学说。……吾于此所以提出机械主义进化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者,所以明此种偏激学说,既不能以之概括宇宙中之物、心二种现象,更不能为社会一切问题谋解决之法,因此引起中国思想界之反感,增进吾人对于儒家哲学复兴之勇气”[63]。至于在他率先发起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中,更竭力批评以科学实证论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认为传统乃为历史过程中所累积之人类心灵的客观化,具有生命、精神,并不是无血无肉的死物,不能“非人格地”“无感情地”去研究它。因此,“张君劢的演讲以及他后来的论战文章,从某种意义来讲,形塑了现代新儒学的致思方向,张君劢本人也因此而成了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之一。”[64]
从文化观角度看,张君劢继粱漱溟之后,在“科玄论战”中提出的那些思想确实型塑了其后现代新儒家不同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发展方向和基本主张。自由主义西化派热情讴歌先进的西方近现代文化,充分揭示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落后因素。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自有其价值。但西化派全力否定传统,倡导西化,亦因其所存在着的内在弊端,因而无法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其一,传统绝非博物馆中陈列的历史故物,同现实社会生活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了无关涉。传统犹如时时刻刻流动于人体内的血液,渗透到现实社会生活之中。无论承认与否,它都必然要对现实社会和现实人发生深刻影响。即使是力反传统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事实上也无法摆脱这种影响。胡适曾严厉批判儒教传统,但同时又相当尊崇孔子、孟轲,“对十二世纪‘新儒家'的开山宗师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65]。因孔子曾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二千余年“专制政治之灵魂”而愤然抨击之的李大钊,也承认:“以孔子为吾国过去一伟人而敬之,吾人亦不让尊崇孔教之诸公。即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值,吾人亦绝不敢蔑视。”[66]尤为耐人寻味的是陈序经,他以明确倡导“全盘西化”而名震一时,但其一生生活方式、待人接物等都始终是中国式的,实际仍存留着很浓郁的中国文化传统。因此,仅凭着摧枯拉朽式的批判、否定、革命,并不能够真正与传统“告别”。其二,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其模式应是多元而绝非单一的。即使是在西方,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现代化也各有样式,都是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具体国情来选择自己的现代化发展之路的。至于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在谋求其现代化过程中,固然应以开放的心智向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西方学习,但不能照抄照搬别的国家或地区的模式。“全盘西化”,显然是没有出路的。诚如S.N.艾森斯塔在谈到“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非西方国家中发展出来的现代性的具体文化形式和组织形式,也能发展出具有一切现代性特征的社会来。”[67]因此,尽管近代以来,西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实际上的主潮,但其毕竟没有能够在神州大地上真正建成现代化大厦。其三,传统虽未必会自发地开启出现代化,但其也并非一定就本质地与现代化相对立。现代化过程中,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不仅可以提供多方面的资源,而且更能成为现代化赖以存在发展的沃土。如依西化派求国新必弃国故的思维全面否定传统,则必然会使现代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如何切实协调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68]。对于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思想的这些弊端,文化保守主义者均有所省察,故其在指出西化派全面否定传统必会导致“民族生命无处安立,民族生命彻底丧失”的同时,又中肯地告诫国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第二,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又不把自己传统文化的精神断绝或斩伐了。换言之,即是如何既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又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第二问题若不解决,则中国国家民族虽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仍将失其存在了。”[69]这实际将使中国国家民族丧失精神命脉。显然,相对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思想,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这种认识无疑有救弊补偏的积极意义。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提出的那些思想及其与胡适、丁文江等“科学派”进行的激烈论争,实际是对后者思想的救弊补偏。正是为此,他后来仍然还要对胡适思想进行全面清算和批判。
站在一边目睹了全程的小青发出一阵爆笑,如芸坐在那儿运气,发誓以后再也不跟他打招呼了。小青则乐不可支地跟每个人宣扬如芸被无视的遭遇,大家纷纷取笑她:“原来美女也是这样的待遇,这下我们可平衡了。”
总之,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在现代新儒学思潮形成和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科学主义思潮,其特征是过分夸大科学的功能,鼓吹‘科学是没有界限的',‘科学方法万能'。在‘科学派'看来,科学不仅能提供无所不包的自然系统的知识,而且也能解决社会和人生观问题。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则认为:‘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这也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立场。”[70]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大体上沿着两条道路:一条是科学的、实证哲学的道路,一条是玄学的、道德形上学的道路。现代新儒家哲学显然是沿着后一条道路发展的。
注释:
① 《文化与反思·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中西印哲学文集》上册,第222-223页,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
② 《明日之中国文化》第31页,岳麓书社2012年版。
③ 1923年展开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论战或人生观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著名的重要论战之一。
④ 唯其如此,论者多喜梁、张并举,将他们归为一派,称之为现代新儒学的倡行者或基于文化保守主义而对现代化的批评者。梁漱溟与张君劢二氏的比较研究亦因之而成为极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他们二人的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共同处,但如美国学者艾恺所说:“他的文化理论不像梁漱溟的、是比较粗略的;却因而比梁氏的理论,就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文化哲学言,更有其代表性。”(《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张君劢》,引见郑大华编《两栖奇才》第289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To 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the author applied AntConc to work out a wordlist of FC.The top 10 frequently spoken words are:“I”,“you”,“it”,“the”,“s”,“and”,“to”,“a”,“oh”and“t”.applying Brown as the reference corpus,the author got the keyword list of FC.
2018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节点。20年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化肥流通体制改革决定》,我国化肥产业得以持续快速发展,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重要了贡献,成为农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依靠力量;40年前,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60年前,毛泽东主席提出我国要设立自己的化学肥料厂,发展自己的化肥工业。从无到有,由弱至强,中国氮肥工业走过了60年大发展的光辉历程,取得了足以令全世界为之瞩目的巨大成就。
那狗终于来到我的身边。它依然要汪汪地叫上几声。它的叫声在这个时候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救命的呐喊。我知道自己有救了。
㊼ 张君劢、丁文江编:《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 33、33、34-35、38、39、40、41、42、53、53-54、80、102、100、118、112、112-113、113、113、119、108、110、223、224、224、225、225、225-226、226-227、113-114 页。
㉝ 《文化与反思·我之哲学思想》,《中西印哲学文集》上册,第38-39页,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
㉞ 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59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水稻育秧主要采取软盘细土育秧与双膜细土育秧这两种方式。以软盘育秧为例,通过软盘细土进行水稻育秧必须保证各个育秧操作环节的标准化,其中,播种的质量好坏将对秧苗的质量和水稻机插秧的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在育秧和插秧的实际操作中,要根据具体的水稻品种准确计算好播种的数量和质量,无论是人工育秧还是机械育秧,都需要尽可能的做到播种均匀。
㉟ 引见《张君劢传记资料(五)》第140-141页,台湾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
㊺ 《篁墩文集》卷五十四《复司马道伯宪副书》,第二册,第278-2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㊲ 劳幹:《记张君劢先生并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影响》,引见郑大华编《两栖奇才》第64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㊳ 严搏非:《论新文化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引见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第211页,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据此,他断言科学上之因果律只可用于物质科学,而人生观则因其“顷刻万变”,由良心所命而起,“决不为科学所支配”,科学上之因果律对人生观实无能为力。既然“科学决不能支配人生,乃不能不舍科学而别求一种解释于哲学或玄学中(或曰形上学)”⑯。他十分看重19世纪末叶以来西方柏格森、倭伊铿、詹姆士等人为代表的“新玄学”,说:“此新玄学之特点,曰人生之自由自在,不受机械律之支配,曰自由意志说之阐发,曰人类行为可以参加宇宙实在。盖振拔人群于机械主义之苦海中,而鼓其努力前进之气,莫逾于此。”⑰他一再引用康德的“断言命令”、倭伊铿的“精神生活”、柏格森的“生命力”、詹姆士的“经验”、欧立克的“生活冲动”和“精神元素”以及直觉、自由意志等概念,为精神领域的自主性创造理论基础。并且,他又反省中国传统的儒家人生观,尤其是宋明儒的心性之学,“所谓明明德,吾日三省,克己复礼之省修功夫,皆有至理存乎其中,不得以空谈目之”⑱。他认为以“国家主义”“工商政策”“自然界之智识”三者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欧洲文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结果已宣告破产,“现代欧洲文明”那三大特征已成“三重网罗”,桎梏着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循欧洲之道而不变,必循欧洲败亡之覆辙;不循欧洲之道,而采所谓寡均平安政策,恐不特大势所不许,抑亦目眩于欧美物质文明之成功者所不甘。”⑲而“苟明人生之意义,此种急功之念自可消除”⑳,故其不仅“尤觉内生活修养之说不可不竭力提倡”㉑,而且更笔端含有深情地写道:
㊵ 这是张君劢对“科玄论战”的提法,引见上书第601页。
㊶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十六《淳安县儒学重修记》,第一册,第2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㊷㊹《篁墩文集》卷二十九《送汪承之序》,第一册,第5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㊸ 《篁墩文集》卷五十五《答汪佥宪书》,第二册,第2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㊱ 杨允元:《在印度讲学时的张君劢》,引见郑大华编《两栖奇才》第70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㊻ 从哲学方面看,朱、陆自有其分野,由此而形成道学内部的理学与心学两大系统。但在历史上,很多儒者把朱、陆之异简化为“道问学”与“尊德性”之别。这对数百年间形成的,被章学诚称为“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的“朱陆之辨”(《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第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㊽ 郑大华:《张君劢传》第127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㊾ 严搏非:《论新文化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引见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第211页,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㊿ 见《陆九渊集·附录一》,第547-54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51] 吕希晨、陈莹:《张君劢思想研究》第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除了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萧乾还在翻译时大幅删减认为与主旨关系不大的细节,注重文章的简洁,这是萧乾自译过程不同于译他的鲜明特点。
范峥峥知道,胡马强是不会再联系自己了,想下一步怎么办?该如何去面对丈夫?她的头脑中一片迷茫,想想自己还留在老家的儿子,她的心里掠过一阵难言的酸楚和苦痛。
[52] 《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中西印哲学文集》下册,第1000页。
[53] 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59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54] 《学术方法上之管见》,《中西印哲学文集》上册,第148页,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
[55] 《原子能时代之道德论》,《中西印哲学文集》上册,第329、330页,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
[56] 《国宪议》,黄克剑、吴小龙编《张君劢集》第102页,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57] 《世界文化之危机》,《中西印哲学文集》上册,第208页。
[58] 林安梧:《当代新儒家述评》。转引自罗义俊编著《评新儒家》第1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9][60]颜炳罡:《当代新儒学引论》第15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158-159页。
[62] 《儒家哲学在历史上之变迁》,《中西印哲学文集》上册,第462页。
[63] 《儒家哲学处于西方哲学环境中之觉悟》,上书第486页。
[64] 郑大华:《张君劢传》第127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65] 《胡适的日记》。《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265-266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
[66] 《李大钊选集》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式(2)~式(4)中:p为流体静压力,Pa;g为重力加速度,m/s2;μf为液相黏度,Pa·s;μs为固相剪切黏度,Pa·s。
[67] 《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译本第5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8]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第8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
基于网络药理学探讨白术-枳实药对治疗慢性传输型便秘的作用机制 ……………………………………… 宗 阳等(13):1798
[69] 钱穆:《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载《思想与时代》第32期。
[70] 方克立:《“援西学入儒”的现代新儒学》,引见《方克立集》第202-20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Controversy between Sciences and Metaphysics”and Zhang Junmai's Philosophy Style as a Modern Confucianism
CHEN Hanming
(The Management Cadre College of Tianjin Trade Union,Tianjin300380)
Abstract: Zhang Junmai,who has striven in academia and politics throughout the whole life,entered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s a Modern Confucian as the protagonist of“Yi Zao”in the“Controversy between Sciences and Metaphysics”in 1923.His appearance revealed to the world a modern New-Confucian style.He proposed that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n outlook on life relied on human being ourselves but not on science.This concept is as completely same as the earlier proposal by Liang Shuming in Western Culture and Philosophy.They both became the common stand of the later Modern Confucianism.Therefore,he and Liang Shuming jointly opened the historical prelude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nfucianism.
Key words: May Fourth and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s;“Controversy between sciences and metaphysics”;Zhang Junmai;Modern Confucianism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DOI] 10.15883/j.13-1277/c.20190300810
[收稿日期] 2019-03-15
[作者简介] 陈寒鸣(1960-),男,江苏镇江人,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董兴杰]
标签:五四新文化论文; “科玄论战”论文; 张君劢论文; 现代新儒家论文;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