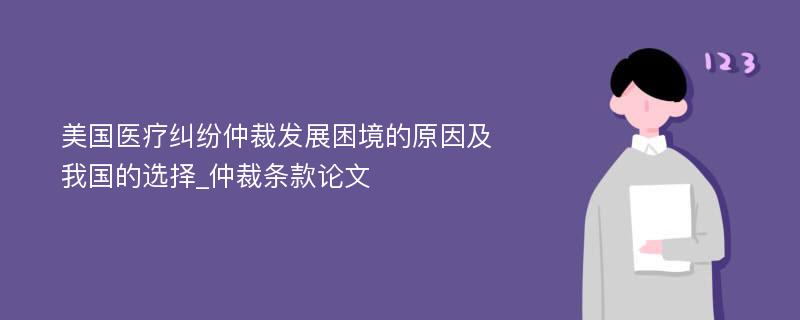
美国医疗纠纷仲裁发展困境的缘由与中国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医疗纠纷论文,美国论文,缘由论文,中国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397(2016)03-0146-14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3.13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法律界和医学界均倾向于采纳仲裁制度解决医疗纠纷,有学者甚至认为,“在现有法律制度下,通过仲裁委员会这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介入医疗纠纷的处理,无疑是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最好方式。”[1]除了论证医疗纠纷在我国《仲裁法》之下具有可仲裁性,这些研究均在探讨如何设计医疗纠纷仲裁制度,且泛泛地讨论医疗纠纷仲裁的好处,如成本低、专家参与裁判等①。在实务界,各地仲裁委员会热衷于建立医疗仲裁机构,如深圳市仲裁委员会和长春市仲裁委员会分别于2010年10月和2014年12月,成立“医患纠纷仲裁院”和“医疗仲裁中心”。仲裁已然成为国人期待解决医疗纠纷的灵丹妙药。但医疗纠纷仲裁中心或仲裁院迄今并未作出过真正的仲裁裁决,接手案件均以调解结案②。但这丝毫未影响当下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医疗纠纷仲裁功效的热切期盼,甚至有人期待其有解决“医闹”问题之功能。 1975年,为了缓解当时的医疗保险危机,美国密歇根州颁布了《医疗事故仲裁法》(Medical Malpractice Arbitration Act),首次以立法特别法的形式规定了医疗纠纷仲裁,很多州也都随后制定了类似的医疗纠纷仲裁特别法。在随后40多年的发展中,立法机关和各法院都在为积极倡导医疗纠纷仲裁而努力,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典型案例表达了对医疗纠纷仲裁的支持,各州立法机关也在后期修改法律,试图将自愿性仲裁改为强制性仲裁。但医疗纠纷仲裁的发展仍然很缓慢,仲裁在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仍占很小比例。为了应付大幅增长的医疗纠纷,日本、韩国、法国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在医疗领域试图以仲裁方式解决医疗纠纷③,这些国家的实践值得研究,但多数国家医疗仲裁要么时间短,要么比例少,多数沦为调解的配角,无论运行时间、运行深度还是对医疗仲裁理论和效果实证的探讨,都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美国医疗纠纷仲裁几十年的“惨淡经营”,固然与美国特殊的法律体制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探究阻碍医疗纠纷仲裁的缘由和根源,或许会给中国当下是否应该采纳医疗纠纷仲裁制度提供最可靠的范本和依据。 二、美国医疗纠纷仲裁的动力之源及发展瓶颈 美国医疗纠纷仲裁的产生并非理性发展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医疗事故危机④导致医疗保险费暴涨、医疗服务价格攀升、医生行业受到重创,仲裁成为化解危机的救命稻草。尽管一般仲裁法完全可以解决医疗纠纷的仲裁问题,但各州立法机关仍然制定了医疗纠纷仲裁特别法,倡导医疗纠纷仲裁;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联邦仲裁法》(FAA)的解释屡次表明对仲裁的支持态度。 (一)建立并推动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动力之源 与侵权法中的很多争议性制度不同,医疗纠纷仲裁制度得到了联邦层面和州层面双方的支持,他们在建立并推动医疗纠纷仲裁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成为该制度在美国建立并得以发展的动力之源。州立法机关与联邦法院的做法最为明显。 1.各州立法机关的努力 第一,制定医疗纠纷仲裁特别法。将仲裁作为解决医疗事故危机的手段是早期侵权法改革的项目之一。20世纪70年代,有19个州制定了特别立法支持并创造对仲裁的激励[2],以作为它们对日益增长的医疗事故危机的反应。密歇根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最为典型。1975年的密歇根州《医疗事故仲裁法》是美国最早的医疗纠纷仲裁立法,它采纳了自愿性仲裁模式,当事人可以决定是否选择仲裁。“尽管仲裁体系面临着宪法和合同上的挑战,密歇根州最高法院认同了立法机关的仲裁体系。”[3]305与密歇根州不同,加利福尼亚州于同年通过了《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作为其重要部分的《加利福尼亚州民事程序法》第1295节在医疗纠纷领域采纳了强制性仲裁模式,确认医疗服务合同中的强制性仲裁合意。该节还详细规定了有效的合同仲裁条款的标准,例如:“仲裁条款必须出现在合同的第一条,必须使用特定的语言,明确表明当事人将放弃诉诸诉讼的宪法权利并同意将争议交予仲裁。”[4]15鉴于强制性仲裁引起的合宪性和格式合同问题更严重,加州患者对医疗纠纷仲裁条款或协议有效性的挑战,更加明显和激烈。除了制定医疗纠纷仲裁特别法,近些年,各州立法机关还通过立法确认医疗事故仲裁条款的有效性,试图在原告挑战仲裁条款有效性时,增加仲裁条款被确认为有效的比例。这些州包括亚拉巴马州、阿拉斯加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伊利诺伊州、路易斯安那州、密歇根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南达科他州、犹他州、弗吉尼亚州、佛蒙特州、佛罗里达州。经过这些年立法机关的不断努力,州法院已经显现了更多的意愿来确认仲裁条款的有效性。 第二,由自愿性仲裁向强制性仲裁的转变。前期医疗纠纷仲裁特别法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美国全国总审计局经过调查认为,这由自愿性仲裁所致,并建议采纳强制性仲裁。有不少州修订立法以采纳强制性仲裁。1992年,佛蒙特州立法机关制定了《佛蒙特州医疗保健改革法》,取代了1975年规定自愿性仲裁的立法。改革规定,所有医疗责任纠纷必须先经过仲裁委员会审查⑤,但该委员会的裁决不具有约束力⑥。犹他州法律的修订体现了各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妥协。2003年,犹他州医学委员会施加压力,州立法机关提出《138参议院议案》(Senate Bill)并规定,医疗服务提供者有权拒绝给不将医疗事故纠纷交予强制性仲裁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虽然规定了30天的撤销期,但未规定急诊不能拒绝服务。医学界接受了强制性仲裁,但却导致众怒,患者担心给医疗服务提供者太多的权利,会带来很多不利影响。这种安排强迫患者放弃他们的宪法基本权利——由陪审团审判和诉诸法院的权利。犹他州最大的医疗服务机构山间医疗保健公司(Intermountain Health Care)采纳了强制性仲裁[5],使得愤怒有增无减,但患者的反应起了功效。最后,医疗服务提供者、患者、律师和政客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和妥协,立法机关通过了《245参议院议案》[6]。“该法第17节规定,医疗服务提供者同意以自愿性仲裁代替条件性提供服务的仲裁,患者可以在交予仲裁前请求调解。”⑦犹他州规定强制性仲裁的努力失败了,但仍有不少州的立法机关在为采纳强制性仲裁而努力。 2.联邦最高法院的努力 早在20世纪20年代,仲裁在美国已被广泛认定为解决各种纠纷的有效工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向来支持有利于仲裁协议执行的联邦政策[7]396,其态度对仲裁的发展至关重要,多次在判决中审查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合法性⑧,这在医疗纠纷仲裁领域同样如此。 鉴于各州立法对仲裁条款有效性规定了具体的条件,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种具体性规定不利于仲裁有效性的认定,若此种规定违反联邦政策,则优先适用《联邦仲裁法》。20世纪8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通过“Moses H.Cone Memorial Hospital v.Mercury Construction Corp.案”⑨、“Southland Corp.v.Keating案”⑩和“Dean Witter Reynolds v.Byrd案”(11)屡次阐明其支持医疗纠纷仲裁的意图,并重申联邦仲裁法优先于州法。它又通过1996年的“Doctor's Associates v.Casarotto案”(12)进一步明确此观点,明确了《联邦仲裁法》的目的和优先性的管辖范围:不管州法是来源于立法还是司法,若其调整一般合同的有效性、可撤销性和可执行性,可以适用,也可以依据“任何合同的无效所依据的法律基础或衡平”而认定仲裁条款无效;但因为医疗卫生影响州际商业,干扰医疗保健行业仲裁协议的州法,被联邦法优先;不能因为仲裁协议违反只适用于仲裁条款的州法而宣告其无效。 各州立法机关对仲裁条款有效性的限制,均因联邦法优先而失败;因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典型判例及其支持医疗仲裁的明显意图,对抗仲裁有效性的公共政策越来越少地被适用,原本是为了倡导医疗纠纷仲裁的州立法,反而成为阻碍医疗纠纷仲裁的绊脚石,却成功地被联邦最高法院移除了。 (二)医疗纠纷仲裁发展的瓶颈 为了在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更多适用仲裁,州立法机关、州各级法院以及联邦最高法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国会也曾试图立法建立一个与早期密歇根州相类似的医疗纠纷仲裁体系,为此,美国国家总审计局研究了密歇根州医疗纠纷仲裁适用的情况。总审计局评估的内容包括:医院、医疗服务提供者和病人参与的程度;对医疗过失纠纷解决的影响;医疗过失保险成本是否降低。依据这些评估内容得出的结论应该是相对可靠且具有可预见性的。但总审计局的研究结论却出乎意料:比例很少的医院、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患者参与了医疗纠纷的自愿性仲裁。从1975年制定立法截止至1991年3月研究时,20000个医疗事故纠纷中,只有882件是通过仲裁解决的。因此,总审计局很难确定自愿性仲裁对医疗事故纠纷解决过程的整体影响,也无法向国会提出行之有效的医疗纠纷仲裁项目的方案。这一调查表明,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医疗过错改革措施第一次浪潮的医疗事故仲裁立法,实际上对促进使用仲裁并无多大作用[8]212。总审计局最后认为,只有将自愿性仲裁改为强制性仲裁,才有可能增加采纳仲裁的比例。 其他对医生和医院的调查显示,医生和医院在采纳仲裁作为解决医疗事故纠纷的手段上动作特别缓慢,由此导致很少比例的医疗纠纷通过仲裁解决。20世纪90年代后期,兰德(RAND)公司(13)研究了医疗合同中仲裁条款的发生率并发现,尽管那时有很多流行的误解,认为只有9%的医生和医院在医疗合同中采纳了仲裁[9]174。同一时间的医院委员会的调查也表明人们很少使用也缺乏兴趣使用仲裁。几年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表明,医疗领域仲裁的接受度并无进展。 以上各种调查及数据都在表明医疗纠纷仲裁并不像倡导者所期待那般受到青睐,而笔者认为美国医疗纠纷仲裁发展的瓶颈更在于患者对仲裁的抵触。医疗纠纷仲裁协议或条款的出现,带来了大量的主张仲裁条款或协议无效的诉讼。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各法院受理的医疗纠纷仲裁协议或条款有效性的案例具有典型性,也是各方利益之间斗争最为激烈的州。加州最高法院在“Madden v.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案”(14)中认定,当医疗服务的代理或信托合同代表了受益人,代理人或信托人有权签订将医疗事故纠纷交予仲裁的协议。该种情况下,即使受益人并不知道仲裁条款的存在,仲裁条款也是可执行的。当仲裁协议的一方属医疗服务计划时,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坚持医疗服务仲裁协议的合法性,并适用于非签字人。但当当事人一方不是医疗服务计划团体时,法院倾向于仲裁协议的非签字人不受签字人签订的仲裁条款的约束,如“Baker v.Birnbaum案”(15),但同一法院却在3个月后的“Gross v.Recabaren案”(16)中认定丈夫签订的仲裁条款对主张失去配偶损失的妻子同样具有约束力。此外,加州各上诉法院还对不当死亡诉讼中仲裁条款是否对继承人有约束力、对未出生的孩子、对未签字的医生是否有约束力表达过看法。患者还依据违宪审查、格式合同、缺乏双方合意、违反公共政策以及合同条款妨碍仲裁的终局性等,挑战已经签订的医疗纠纷仲裁协议或条款的有效性。 综上,自愿性仲裁下医疗纠纷仲裁的采纳率确实不容乐观,相关的数据调查也显示了医疗纠纷仲裁发展缓慢,而笔者认为,医疗纠纷仲裁在美国的发展中,最大的败笔在于其并未得到患者的支持,为减少诉讼、降低当事人时间和金钱成本、提高受害人赔偿而产生的仲裁,却引起了更多的讨论其有效性的纠纷。强制性仲裁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医疗纠纷仲裁的采纳率,但必然会增加原告挑战仲裁条款有效性纠纷的可能性。为什么为了患者好的医疗纠纷仲裁却引起患者如此强烈的反感,为什么立法机关、法院和各利益集团40年的努力,并未换来医疗纠纷仲裁欣欣向荣的发展?难道答案仅仅是有些学者坦言的“患者误以为诉讼会带来更多赔偿”?这都是患者不买账惹的祸?原因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三、美国医疗纠纷仲裁发展困境的缘由 美国各州立法机关、联邦法院、州法院及其他力量纵使经过40年的努力,医疗纠纷仲裁的采纳率和患者支持率仍不尽人意,这确实不得不让我们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导致这一困境的缘由和根源到底在哪里? (一)质疑医疗纠纷仲裁的优势 1.仲裁是否必然比诉讼节约时间和金钱成本 美国法院审判医疗纠纷的一大弱点是由外行的陪审团决定复杂的医疗事故纠纷。有人认为,因为绝大多数案件都涉及复杂的医疗过失事项,包含医疗专业人员的仲裁庭会作出更有效、更公平的决定。而仲裁庭医疗专业人员的存在,可以省去培训陪审团为处理纠纷所需要的复杂医学事实的几个周时间[8]208。仲裁的程序也比诉讼简单,也会节省不少时间。“曾有一项研究考察了1500个针对医疗保健服务机构的过失纠纷后发现,2003年至2011年间,通过有效仲裁协议解决的纠纷比其他纠纷成本少21%。”[10]674 “但那些通常意义的好处是否真的降低了解决医疗事故纠纷的全部成本至今未得到准确实证研究的证实。”[11]1821除了启动仲裁实质性的受理费,仲裁当事人必须支付仲裁员的费用,医疗纠纷仲裁由3个人组成的仲裁委员会的费用会增加不少[12]370-371。标的为75000美元~15000美元的受理费是2250美元,标的为15万美元~30万美元的受理费是4000美元,仲裁员的费用通常是200美元~600美元每小时或者更高。复杂纠纷的仲裁通常不会很快做出裁决,复杂纠纷的裁决也不会很节约钱。 实际上,希望策略性地延迟医疗事故纠纷时间的被告律师,可以延长至比诉讼还长的时间。如在1997年加州最高法院判决的“Engalla v.Permanente案”(17)中,受害人几年都有呼吸道和其他肺部问题,但医生并未做进一步的诊断检查,至最后做X光显示是肺癌时,已经是晚期。5月底,当事人遵守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且特别提到请求人的身体状况,希望尽快解决。直至10月份,双方才对3个仲裁员的选择达成一致。在此过程中,被告使用了一系列拖延技巧,包括选择他们知道不能被接受的仲裁员。仲裁员选好后一天,请求人死亡。亲属随后提起诉讼,认为仲裁协议不可执行,主张欺诈、胁迫等。法院认定,被告滥用程序导致仲裁条款不能适用。被告遵守该判决,组成顾问委员会来评估原有仲裁程序并提出改进意见。该委员会“质疑了仲裁的总成本比诉讼的成本低,提到他们设计的仲裁程序越来越像法院程序,与诉讼的对抗性并无二致,也不必然就快。但仲裁与法院成本高低的证据不足,据很多证据显示,成本大体相当。”[11]1830-1831故医疗纠纷仲裁倡导者所津津乐道的成本低,并未得到确切实证数据的支持,处于优势地位的被告经常会拖延时间、增加成本,以促使受害人不战而退。 2.仲裁员的专业性优势是否会被扭曲 医疗纠纷仲裁支持者提出,专业仲裁员参与审判和裁决,比没有医学知识的法官及没有医学和法学知识的陪审团更能作出公平的决定。比起法官和陪审团,专业仲裁员更不可能被感情所左右,更可能理解纠纷中的复杂争点[11]1823。专业仲裁员在理解医疗专业的准确性上比法官和陪审团存有优势,但正是这一优势,恰恰可能成为其劣势,因为仲裁程序的特征使其容易产生有利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偏见。 仲裁员与被告“本是同根生”才带来的专业性,与仲裁的特性和医疗纠纷被告为“重复玩家”(repeat player)的现实,合谋使得仲裁对被告的倾向性无以复加。“医疗过错以外研究仲裁的学者已经提出,仲裁有利于会在多个案件中使用仲裁的当事人,如通过仲裁解决所有与雇员有关纠纷的雇主。”[13]685这些重复玩家在仲裁程序中有两个优势:重复玩家可以更好地驾驭仲裁程序并选择赞同他们立场的仲裁员[14]195;仲裁员更可能做出取悦重复玩家的裁决,他们依赖于将来再被选中[15]927-928。这在医疗服务领域同样适用。医疗服务提供者在医疗过错仲裁中有重复经验,而绝大多数病人却是一次性的。“当事人给仲裁员提供多次机会时,就会产生倾向性的问题。没有仲裁员会用惩罚性赔偿惩罚恺撒医疗集团,因为那将是他为恺撒做的最后的仲裁。”[16]11加利福尼亚研究局(州支持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2000年的报告指出,“1999年4月至2000年5月间,裁决给原告超过100万美元的仲裁员,这段时间没有再被医疗服务机构选择做仲裁员。” 有医学背景的仲裁员原本就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同根生”,而重复玩家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更是让医学专业这一原本的优势雪上加霜,这是导致受害人宁愿选择舍弃他的专业知识的优势,而将判定是非的权利交予外行的重要原因。 (二)医生对医疗纠纷仲裁的抵制 通常而言,医学界是支持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医院和医生不仅可以利用重复玩家的优势,而且将命运交予同行显然比交予外行稳妥。但50%的使用仲裁的被调查医生和医院承认,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保险公司让他们这么做。接近三分之一的医生这么做是因为这是他们医疗小组的政策。三分之一多的是因为他们相信使用仲裁解决纠纷便宜些[9]174。为何很多医疗服务提供者不愿意在医疗合同中包含更多和更宽泛的仲裁条款?因为仲裁带给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不尽是好处。 首先,失去实体法对其保护的权利。在《联邦仲裁法》之下裁决,没有任何条款或要求使仲裁员负有与实体法相一致的义务,仲裁员可能会无视其他法律对医疗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保护,包括对专家报告的时间限制、专家证据的条件和披露等。另外,医疗服务专业领域的法律及法规,有对医疗服务人员的专门保护的规定,仲裁员没有义务考虑这些实体法规定。 其次,更难达到澄清名誉的目的。仲裁员经常对当事人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作出不会完全免除当事人责任的妥协之裁决。“除了较低的辩护成本、更客观的裁决以及有吸引力的隐私性,有利的陪审团裁决可能是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声誉和自信更好的解决方案。”[17]639“很多医疗纠纷争议很大主要是因为医生寻求‘澄清名誉’的兴趣在起作用,这意味着很多医生拒绝调解。很流行的观点是,大多数医生倾向于诉讼以保护他们的名誉并避免医疗纪律部门的任何不利后果的影响。”[18]1172-173《健康质量保健法》规定:“不管多少额度以及何种原因带来的任何支付,都要向国家从业者数据库和州许可委员会报告。”[19]309医生只有胜诉而非任何形式的妥协和调解,才能达到澄清名誉、保证其竞争力的目的。 再次,失去上诉权及诉讼程序可以利用的优势。仲裁裁决的效力依据仲裁协议产生的方式分为两种:强制性仲裁因剥夺了当事人的自愿选择权,仲裁裁决并不当然具有约束力,当事人不满意可以向法院就争议事项提起诉讼;自愿性仲裁尊重了当事人的自愿选择权,除了法律规定仲裁裁决可撤销的情形,仲裁裁决具有约束力,当事人既不能上诉,也不能去法院起诉。在自愿选择仲裁时,放弃上诉权的不仅是受害人,医疗服务提供者同样如此,且《联邦仲裁法》规定法院只有在立法规定的很有限的情况下才能撤销仲裁裁决,即当事人一旦选择仲裁,就很难推翻仲裁员的裁决。法院系统很多可以利用的程序工具提供了很多策略上的优势。“如通过法院审理案件的好处之一是法官可以利用证据动议或者简易判决动议。这些动议在医疗纠纷案件中很普遍,在限定争点或给被告带来完全的胜利上,通常是成功的。”[8]213当事人对案件中的主要事实不存在实质性争议或案件仅涉及法律问题时,法院可不经开庭审理而作出判决,认为自己在法律上应当胜诉的一方当事人可随时申请法院作出简易判决。 因此,某种程度上,当下诉讼体系为很多医生获得他们期待的洗冤,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基于同样原因,很明显,至少在很多情况下,医疗过错保险人比病人更会利用与当下诉讼系统有关的固有成本,来创造以让患者放弃诉讼或以较低价格和解的动力[8]212-213。基于以上原因,医生和医院并不必然毫不犹豫地支持仲裁,况且,调查数据显示,医疗纠纷诉讼中的陪审团比其他领域的陪审团更加理性,对被告更加友好,医疗纠纷的原告胜诉率通常要低于一般民事纠纷胜诉率。 (三)原告对医疗纠纷仲裁的强烈抵触和挑战 限制原告获得赔偿,是侵权法改革的目标之一,作为侵权法改革措施之一的仲裁,自然不会获得患者的信赖。甚至有人认为:“在侵权法改革的争论中,患者支持者反对它是因为医生支持它。”[20]1169自从仲裁被倡导成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手段,原告及其律师就为获得陪审团审判,并质疑仲裁条款而努力。原告挑战仲裁条款有效性所作出的努力,会让人质疑仲裁真的有那么好吗?到底是谁从中受益了?原告主要从仲裁条款的违宪性及格式合同两方面,来挑战仲裁条款的有效性。 1.基于违宪对仲裁条款及相关立法的挑战 医疗纠纷仲裁首先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14条的正当程序条款。“依据实体正当程序,与其他当事人相比,医疗过错当事人因为仲裁条款而被区别对待;依据程序性正当程序,当事人被要求进行仲裁,却缺失诉讼程序中存在的程序保护。”[21]53涉及仲裁时效,要求任何人都应该在合理时间以合理方式被审理的正当程序的程序性保护,应该与其他限制纠纷解决时间的社会利益相平衡。法院通常认定原告都还未有机会发现损害、仲裁时效就过期是违反宪法的(18)。 其次,仲裁立法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14条的平等保护原则。它规定,任何州都不得拒绝任何人受法律平等保护。违反平等保护原则最典型的是对于仲裁时效的规定:“每一个州都有特别的仲裁时效适用于医疗事故纠纷。”[22]460“关于医疗事故仲裁时效平等保护条款有两项质疑:医疗过失中的原告与其他过失纠纷中的原告区别对待;基于立法对‘连续性治疗或者欺骗性隐瞒’情形设有例外时,不同医疗事故受害人被区别对待。法院认为,当立法基于这些例外对医疗事故原告区别对待时,该立法就违反平等保护原则,因为立法与涉及的合法的州利益并不相关。”[22]62认定该种特别仲裁时效违宪的州有新罕布什尔州、新墨西哥州、俄亥俄州、俄克拉荷马州以及俄勒冈州,德克萨斯州也可能这样做。 再次,仲裁条款违反了当事人由陪审团审判、诉诸法院的权利。特别是有些州强迫当事人在起诉前进行医疗纠纷仲裁,这是违反宪法的。有些州对赔偿具体内容作出规定,也干涉了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如1999年,俄亥俄州最高法院终结了《俄亥俄州综合侵权改革法》,认定其违宪(19)。法院认定该法违反了州宪法一个对象条款(one subject provision),该条款要求立法必须集中于一个主题。并且,1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的上限,或者对小公司三倍、对大公司25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的限额,违反了接受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权利,陪审团应有权确定赔偿数额。 2.基于合同对仲裁条款的挑战 格式合同是一种对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所提供的合同,以“接受或不接受”为基础,消费者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不接受即不能获得商品或服务。它是由缔约方中的强势一方拟定合同条款,弱势方对合同条款并无谈判或选择的余地。“医疗过错仲裁合同已经因其是不合理的格式合同而被批判。”[23]142原告经常利用此依据挑战格式条款的有效性,有不少法院也据此认定仲裁条款无效。如内华达州最高法院认定某医疗事故仲裁合同为不可执行的格式合同,因为弱势方并未注意到仲裁条款或后果(20)。亚利桑麻州的“Broemmer v.Abortion Services of Pheonix案”(21)涉及21岁要堕胎的女孩,在堕胎前,她被要求签署三样东西,包括仲裁协议。但护理人员并未与她讨论仲裁条款。她的子宫因流产破裂。法院认为,同意以及合理的期待对有效合同是根本性的。仲裁条款已经超出了原告合理的期待,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她知道她已经放弃了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事实是当事人并不能选择条款也不能在其他地方获得服务,仲裁条款不能实施。 但在“Buraczynski v.Eyring案”(22)中,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审查了两个医疗事故仲裁条款后,支持了仲裁条款,认定条款是可执行的,因为它们是经过考虑,不是被迫或者不公平的。没有迹象表明患者不可以质疑仲裁条款,患者也不必须在医疗服务和接受陪审团审判权之间进行选择,仲裁程序本身也未表明不公平。 但若仲裁条款规定妨碍了仲裁裁决的终局性,法院通常会认定为无效。在“Beynon v.Garden Grove Medical Group案”(23)中,仲裁条款允许医疗服务提供者拒绝仲裁裁决,并向由3位医生组成的另一仲裁小组重新提交仲裁。法院认定该仲裁条款无效,因为该条款未获得原告的同意,也违反公共政策,初始仲裁员的裁决具有终局性。 只要仲裁条款存在,可能原告就会继续试图在《联邦仲裁法》之下,寻求各种依据,避免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有关的强制性仲裁。毫不夸张地讲,患者的抵触以及原告对仲裁条款有效性的挑战是医疗纠纷仲裁无法普遍推广的重要原因。 (四)仲裁并未有效克服诉讼的缺陷 “医患关系以信任为基础,这最终被法院审判所侵蚀。仲裁会提供解决纠纷的更合作的氛围,这与先前存在的医患关系相协调。”[24]423但医疗纠纷仲裁的优势并未得到有效实证研究的支持,原因之一是实际交予仲裁的案件很少,甚至侵权法改革的相关实证分析都揭示,医疗纠纷仲裁立法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但更关键的是,仲裁本身可能也无法有效解决医患纠纷,也无法有效克服医疗纠纷领域所显现的诉讼及其程序的缺陷。 除了作出裁决者的身份发生变化,仲裁本身并未对纠纷解决有根本性的改变。可能证据及其披露会受到限制,审理本身也有希望耗时更短,但这些小修小补并不会在根本上改变纠纷的解决结果。“仲裁制度将决定作出者从陪审团小组转到了仲裁员或仲裁委员会,但在适用的实体法未有另外改变的情况下,仲裁员对非经济性损害的价值必然作出与陪审团同样主观的决定。”[8]215对于确定痛苦和损害的不确定性上,仲裁员不必然比陪审团高明多少,甚至作为高收入群体的仲裁员对精神痛苦的裁决额很可能比陪审团的裁决额还高。 另一方面,医疗事故纠纷是最为复杂的纠纷。“没有任何一个诉讼领域能够长时间作为医疗过失改革的兴趣点。”[8]207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起,各州、各群体都使出浑身解数,但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医疗事故危机总是周期性地阴魂不散。实际上,诉讼解决医疗纠纷所显现的瑕疵,可能与诉讼无关,而与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关。鉴于此,很多评论人依据与诉讼有关的实证数据下结论,当下诉讼体系尽管有缺陷,但总体运行良好。“整个体系中所有成员都在尽力去做,传统体系看起来也合理地解决了大多数纠纷。事实是很多人盯住了该体系的长期诟病,这或许说明分配给这一体系的任务难度很大,因为确定很多复杂医疗纠纷的过失与非过失本质上是极其困难的过程。”[8]207 面对这样棘手的难题,仲裁制度没有、不会、也不可能解决诉讼体系无法解决的内在问题,而只是用仲裁员代替了法官和陪审团而已。若原告只是误解陪审团会判决更多赔偿,这40年的经验和教训,不可能不让其醒悟,而若当下的医疗纠纷仲裁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必然会有现在被排除出体系的更多的原告来主张权利。 (五)撤销期间的规定及医疗纠纷仲裁的模式 1.撤销期间的规定 虽然各州的医疗纠纷仲裁立法选择的仲裁模式不同,但不少都规定了仲裁条款的撤销期间。如加州医疗纠纷仲裁条款规定了30天的撤销期,且这已得到加州上诉法院的支持,30天之内未撤销署名,仲裁条款适用于随后的医疗服务(24)。科拉罗多州规定了90天的撤销期间(25)。路易斯安那州和纽约州规定,未实施医疗服务前可以撤销仲裁条款(26)。亚拉巴马州《医疗责任法》则要求,在医疗服务结束、纠纷产生后,才可达成仲裁医疗责任的合意(27)。 规定可撤销期间原本是给当事人充分自由的空间,来决定是否将纠纷交予仲裁庭裁决,放弃陪审团和法院审判的宪法权利,特别是在规定强制性仲裁的州尤其如此,这也是仲裁精髓之所在。各州医疗纠纷仲裁立法原本也是为了鼓励医疗纠纷仲裁、缓解医疗事故危机而产生,但这些立法规定的仲裁撤销期间,在给当事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时,却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仲裁协议签署后,撤销期间给了当事人更多撤销已签署仲裁协议的机会,更减少了使用仲裁解决医疗纠纷的机会。“撤销期间允许病人在治疗前签订了协议,在治疗后终止协议。它们一点都不鼓励医疗事故纠纷仲裁。可撤销的仲裁协议挫败了州和联邦为取得持续、有力的纠纷解决方式而付出的努力。”[25] 2.医疗纠纷仲裁的模式 规定医疗纠纷仲裁的撤销期间,是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体现,而自愿性仲裁这一体现仲裁价值的模式,如同撤销期间,对医疗纠纷仲裁的发展起到了某种程度的阻碍作用。 毫无疑问,自愿性仲裁模式在医疗领域的正当性比在任何领域都要明显。仲裁最初产生于商事领域,至今也是解决商事纠纷的重要手段。虽然仲裁制度的发展史即是仲裁不断扩张的历史,但近些年仲裁在消费、医疗领域的争议说明,仲裁特别是强制性仲裁在这些领域是否真的合适值得怀疑。在医疗事故纠纷中,受害人的损失是身体伤害或者死亡,并无其他选项,虽然这些损害最终还是可以通过量化的形式,转化为财产性利益,但与商事纠纷中“财产性利益”存在区别的不是别的,正是该利益所承载的对于生命和健康的尊重。在该种意义上,没有人有权利剥夺受害人处置生命和健康的权利。因此,自愿性仲裁模式本是最合适的。但同样是这一规定却带来了阻碍医疗纠纷仲裁发展的后果。 密歇根州立法规定,患者在治疗前被告知可选择仲裁解决医疗事故纠纷,即采纳自愿性仲裁模式,但“仲裁委员会的决定是终局性的且有拘束力”(28)。美国总审计局考察了密歇根州医疗纠纷仲裁的适用情况,结论是:自愿仲裁立法对医疗事故体系未产生影响,因为绝大多数人并不选择仲裁(29),并且倡导各州采纳强制性仲裁模式。其他州的自愿仲裁模式也被证明并无效果,任何医疗过失改革法案都应该强制利用仲裁解决纠纷。“在实践中,几乎没有原告会跳过外行的陪审团,而选择有经验的医疗服务专家组,因为原告认为他们更有可能在陪审团诉讼中获胜。”[26]995 近些年,一些州确实通过立法将自愿性仲裁模式改为强制性仲裁模式,但笔者认为,这一模式上的转变并不会带来实质性改观。首先强制性仲裁更有可能受到违宪审查的挑战。其次,因强制性仲裁产生的裁决不具有约束力,当事人仍然可就同一事项向法院起诉,就会陷入“强制仲裁、获得裁决、双方不满意、提起诉讼、获得陪审团裁决、双方又不满意、上诉”的怪圈。“这种过程只会增加成本并延误医疗事故纠纷的解决。”[27]832 四、中国不宜选择医疗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理由 美国医疗纠纷仲裁制度40年的坎坷发展,与美国特殊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毋庸置疑,关于仲裁条款有效性的违宪审查及是否具有合同上可执行性的争点,关于医疗纠纷仲裁制度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关于患者及其律师团将来会如何对抗立法和司法扩大仲裁的趋势,这些问题至今无法确定也不得而知。但笔者认为,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原告总是通过个案不断挑战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实际上就否认了仲裁的预期优势。在全球都在倡导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背景下,中国到底是否应该选择仲裁作为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很显然,中国不应该也没有必要采纳医疗纠纷仲裁制度,医疗纠纷仲裁制度在中国的运行不会比美国更好,最后可能沦落为噱头,或者最多是变相的调解。 (一)受害人的抵触和反感同样存在 美国医疗纠纷仲裁制度始终未得到患者的信任和支持,中国患者的不信任感只会有增无减。中国医疗纠纷诉讼采纳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医疗纠纷鉴定制度,由法院决定是否提交鉴定以及由哪些机构鉴定,鉴定人对双方当事人必须保持中立。但目前中国医疗损害鉴定缺乏足够的公信力,主要是因为:患者担心医学会鉴定人员的身份无法保证鉴定结果的中立性,鉴定专家来自于各地医院的医生或高校医学科研专家,而诉讼中的被告却是医院和医生;医疗损害鉴定并非临床会诊,其虽涉及复杂的医学知识,但也涉及过错与损害是否有因果关系等实质性法律问题,单纯的医学专家未必能够胜任;鉴定专家不能出庭接受质询,为鉴定意见负责的是医学会而非专家个人,这更增加了人们“暗箱操作”的臆测。鉴于医疗事故鉴定的诟病,很多学者提出不少建议,但至今在实践中也未见明显起色,主要还是因为无论如何都无法消除患者对鉴定人员不能保持中立性的担心。鉴于此,受害人在诉讼中宁可主张缺乏临床经验的法医进行的司法鉴定,因为法医与被告并无瓜葛,这才是关键。 依据中国多年依赖医疗鉴定解决纠纷的惯性,医疗纠纷仲裁恐怕仍然离不开医疗事故鉴定来确定损害责任。提倡医疗纠纷仲裁的依据之一是可选择具有医学背景的仲裁员,避免了法官只能依据医疗损害鉴定才能断案的尴尬,且受害人至少可选择一位仲裁员,这既保证了裁判者的专业性,也保证了裁判者不会倾向于医疗服务提供者。但若舍弃医疗损害鉴定,意味着将命运交予未必是纠纷领域最权威、最相关的专家,他们医学知识的可靠性是相对的,这怎么就能够保证采纳多数意见的仲裁裁决,就必然比法官依据集体作出的医疗鉴定作出的判决更合理和公平?但若继续采纳医疗损害鉴定,又会无端增加当事人的经济成本,当事人不仅要支付仲裁员的仲裁费用,还要支付鉴定费用。而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医疗纠纷的解决短期内不可能抛弃医疗损害鉴定,仲裁员的所谓专业性和中立性,并不能说服受害人放弃诉诸法院的权利。 (二)医疗过错认定的悖论和医疗行为的内在特性决定了医疗纠纷解决的难度 医疗纠纷可能比绝大多数纠纷的解决难度都要大,其影响可能比任何纠纷都要大,它不仅关系着医患关系本身,还关系着社会公共利益。但医疗纠纷难以解决,问题不在于诉讼或仲裁孰优孰劣,而在于医疗过错认定的悖论和医疗行为的内在特性。 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的认定,离不开医疗专业人员的帮助,专业医疗人员的参与就不能保证中立性,因为实施鉴定的专业医疗人员与被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是患者的主观臆断。有专家曾坦言,手中的笔很沉重,甚至比操作手术刀还难。尽管依医疗事故的定义,有些医院存在违法违规的过失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案例鉴定为医疗事故应该没问题,但专家们往往顾虑重重很难下笔,只因医方中难免有认识的老同事、老同学和各种关系。有学者设想了一些制度加强医疗鉴定的中立性,但鉴定专家客观上也很难保持中立性,同行的同病相怜所引发出来的情感对鉴定结论的左右,是法律所无能为力的。将认定过错的权利交予医疗专家对患者来讲实属无奈之举。 医疗行为的内在特性决定了医疗纠纷事故或过错难以认定。医疗行为无法用准确来形容,同样的手术或药剂用在不同的患者身上会有不同的反应,会出现预想不到的损害结果。对于一个损害结果,有时很难判断到底是哪一因素导致了那一损害,到底是哪一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科学上缺乏绝对的确定性是复杂诉讼争论的主要原因。法律界似乎并不理解科学是在寻求真相,而不是确定真相。”[28]526-527‘‘科学和法律之间最重要的窘境之一是,法律要求绝对的真相,而科学不能提供毋庸置疑的答案。”[29]1098在确定损害和责任时,法律要求明确是与非,要求确定是否有过错、有多大程度的过错,但损害在医学上很难确定因果,有时不同鉴定机构鉴定意见相左,并不意味着鉴定人徇私舞弊。我们通过各种标准、各种手段所鉴定出来的“事实”,又真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还原事实真相?医疗行为的特性和医疗过错认定的悖论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圆满解决和患者的绝对信任,是一个永无答案却又会继续争论下去的问题。 (三)自愿性仲裁与强制性仲裁均无法克服自身缺陷 医疗纠纷仲裁有两种模式:自愿性仲裁和强制性仲裁。就美国医疗纠纷仲裁发展来看,自愿性仲裁并不会推动医疗纠纷仲裁的发展,这也是很多州近些年转而采纳强制性仲裁的原因。我国学者对于我国医疗纠纷仲裁应该采纳的模式并未达成一致,有学者倡导自愿性仲裁,即允许医患双方通过签订仲裁协议处理日后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裁决一旦作出即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30]。有学者倡导强制性仲裁,现阶段强制性仲裁模式更适合我国医患纠纷处理的实情,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满意,可以就同一事项向法院提起诉讼。“现在就让医患纠纷仲裁完全脱离司法诉讼环节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31] 倡导自愿性仲裁的依据是仲裁的契约性,依当事人的意愿和合意而创设仲裁是仲裁的本质所在。且自愿性仲裁的终局性特征也更有利,当事人选择裁决解决纠纷就是为了有效率地获得终局性裁决,耗时冗长的诉讼程序并非当事人的明智之举。有学者提出,采纳强制性仲裁,“强制仲裁结果的可诉讼性则可强化当事人对医疗纠纷结果的信心,可以促使当事人积极采取仲裁模式解决医疗纠纷。医疗纠纷事关当事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到侵害的问题,一裁终局的任意仲裁一旦产生错误却无法通过司法方式予以救济,则将对医疗纠纷弱势一方造成新的伤害。”[32] 笔者认为,医疗纠纷不是选择哪种仲裁模式的问题,而是患者多大程度上会去选择仲裁解决自己受到的人身或健康损害的救济问题。无论在医疗行为前还是纠纷发生后,如同美国患者对待自愿性仲裁一样,他们并不情愿选择仲裁,并不情愿放弃因人身伤害或死亡诉诸法院的权利。而强迫患者在获得医疗服务前就签订仲裁条款,已经失去了仲裁原本的意义,是强迫患者处分自己因人身伤害或死亡诉诸法院的优先权,否则患者将不能得到医疗服务,即便在仲裁后,患者仍然可以去法院起诉,还可以上诉,还可以申请再审,那么仲裁在医疗纠纷领域存在的意义何在?仅仅决策制定者认为仲裁才是解决医患矛盾、解决“医闹”问题的良策,就去强迫患者接受并认可仲裁吗? 另外,医疗纠纷仲裁在中国同样无法克服“重复玩家”的缺陷,这只会增加患者的反感和不信任感。美国40年前倡导仲裁来解决医疗纠纷,实在是应对无法控制的医疗事故危机的无奈之举,40年的努力也无法换来患者的信任感,这是不是更应该让我们反思仲裁在医疗纠纷领域的适当性?我国医患矛盾近些年确实比较紧张,但医疗纠纷仲裁真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吗?在美国不能良好运行的制度,就果真会缓解中国的医患矛盾、消除“医闹”吗?强迫患者接受仲裁难道不会使医患矛盾日趋紧张吗?仲裁难道真的能解决医疗纠纷“谁最适合鉴定事实真相”这一根本性问题吗?无论如何,医疗纠纷仲裁恐难担此重任,很可能沦落为变相的调解。 ①在中国期刊网,以“医疗”和“仲裁”作为篇名关键词搜索,有83篇论文及报道,从第一篇杨平的论文开始。(参见:杨平.设立医疗纠纷仲裁机构的设想[J].中国卫生法制,1998(1):24-25.)它们无一不是提倡医疗纠纷仲裁制度,且均试图为中国构造最合理的医疗纠纷仲裁制度。引频率较高的论文有:方兴,医患纠纷强制性仲裁机制构建探索[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11-214;郭玉军,杜立.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若干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2010(2):153-160;马占军.我国医疗纠纷仲裁解决机制构建研究[J].河北法学,2011(8):2-11;余承文,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研究[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6-29. ②如2011年2月,深圳医疗纠纷仲裁院的首例医疗纠纷仲裁便以调解结案。(参见:吴涛.深圳首例医疗纠纷仲裁案办结[N].深圳特区报,2011-03-01(A16).) ③2004年12月,日本颁布《促进利用诉讼外解决纷争手续的法律》,简称“ADR法”。主张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尊重纷争当事方自主解决纷争的努力,不通过诉讼,而采用通过公正的仲裁人或调解人介入的方式使各方达成和解的解决方式。2011年,韩国国会通过了《医疗事故被害救助和医疗纷争调解相关法律》。2012年4月,依据该法成立的韩国医疗仲裁院正式运行,该仲裁院以特殊法人的方式成立,具备准司法机构的调解功能和鉴定功能。2002年,法国根据《关于患者的权利及保险卫生制度之质量的法律》于各地成立了“地方医疗事故损害仲裁委员会”。地方仲裁委员会以仲裁为目的解决患者和医师及医院之间的纠纷。(参见:张超.日本:“ADR法”促医疗纠纷调解[N].法制日报,2014-05-20(009);王刚.韩医疗纠纷调解起步虽晚成效大[N].法制日报,2014-05-27(009).) ④20世纪70年代的医疗事故危机是侵权法危机的组成部分。很多保险公司倒闭,仅剩的几家商业保险公司在医疗事故保险领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试图规范医疗保险、通过限制赔偿额等措施改革医疗事故诉讼,以降低保险费,让医疗服务提供者可以承受。20世纪80年代以及21世纪初期又发生过两次医疗事故危机。 ⑤参见:VT.STAT.ANN.tit.12,§7002(1991). ⑥参见:VT.STAT.ANN.tit.18,§9403(1993). ⑦参见:Utah Code Ann.78-14-17(1)(a)(iv),(viii)(2002 & Supp.2004). ⑧参见:United Steelworkers of America v.American Mfg.Corp.,363 U.S.564(1960); United Steelworkers of America v.Warrior and Gulf Navigation Co.,363 U.S.574(1960); United Steelworkers of America v.Enterprise Wheel and Car Corp.,363 U.S.593(1960). ⑨参见:Moses H.Cone Mem'l Hosp.v.Mercury Constr.Corp.,460 U.S.1(1983). ⑩参见:Southland Corp.v.Keating,465 U.S.1(1984). (11)参见:Dean Witter Reynolds v.Byrd,470 U.S.213(1985). (12)参见:Doctor's Assoc.,Inc.v.Casarotto,571 U.S.681,687(1996). (13)RAND(兰德)是英语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缩写。兰德公司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性研究组织,主要对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方面的各种问题进行系统的跨学科的分析研究。 (14)参见:Madden v.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552 P.2d1178(Cal.1976). (15)参见:Baker v.Birnbaum,248 Cal.Rptr.336(Ct.App.1988). (16)参见:Gross v.Recabaren,253 Cal.Rptr.820(Ct.App.1988). (17)参见:Engalla v.Permanente Med.Group,Inc.,938 P.2d903(Cal.1997). (18)参见:Coon v.Nicola,21 Cal.Rptr.2d 846,849(Cal.Ct.App.1993). (19)参见:State ex rel.Ohio Academy of Trial Lawyers v.Sheward,715 N.E.2d 1062(1999). (20)参见:Obstetrics and Gynecologists William G.Wixted,M.D.,Patrick M.Flanagan,M.D.,William F.Robinson,M.D.Ltd.V.Pepper,693 P.2d 1259(Nev.1985). (21)参见:Broemmer v.Abortion Services of Pheonix,Ltd.,840P.2d 1014(Ariz.1992). (22)参见:Buraczynski v.Eyring,919 S.W.2d 314(Tenn.1996). (23)参见:Beynon v.Garden Grove Medical Group,161 Cal.Rptr.146(Cal.Ct.App.1980). (24)参见:Gross v.Recabaren,253 Cal.Rptr.820(Cal.Ct.App.1988). (25)参见:Colo.Rev.Stat.Ann.§ 13-64-403(Supp.1994). (26)参见:La.Rev.Stat.Ann.§ 9:4235(West 1997); N.Y.Civ.Prac.L.& R.§ 7550(McKinney 1998). (27)参见:Alabama Medical Liability Act § 6-5-485(1975). (28)参见:MICH.COMP.LAWS ANN.~600.5040(West 1993). (29)参见: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Medical Malpractice:Few Claims Resolution through Michigan's Voluntary Arbitration Program,GAO/HRD-91-38(Dec.1990).标签:仲裁条款论文; 医疗纠纷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法律论文; 医疗事故论文; 医疗论文; 仲裁协议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