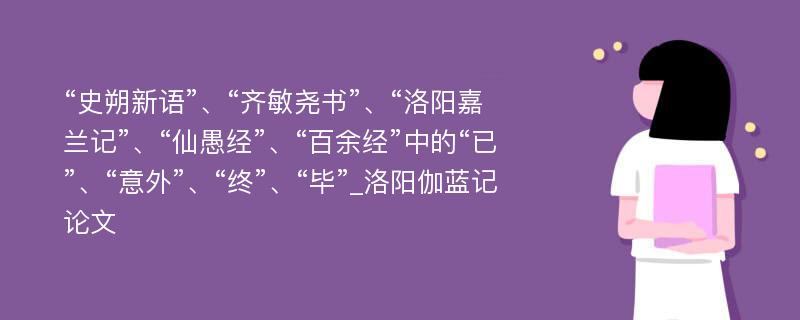
《世说新语》、《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贤愚经》、《百喻经》中的“已”、“竟”、“讫”、“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贤愚论文,伽蓝论文,洛阳论文,世说新语论文,百喻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1263 (2001)01—0073—06
在谈到动词语缀“了”的来源时,人们常常说到“已”、“竟”、“讫”、“毕”,认为它们都是完成动词,可以构成V+(O)+CV(完成动词)的格式,后来被“了”代替,成为“V+(O)+了”。但是,“已”、“竟”、“讫”、“毕”的性质是否完全一样?本文根据《世说新语》、《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贤愚经》、《百喻经》五部书中的材料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已”、“竟”、“讫”、“毕”的不同
(1)出现频率的不同。在上述五部书中, 这四个词出现的频率很不一样。见下表:(只统计处在“V+(O)+X”格式中的次数)
已竟讫毕
世说新语 0 155 21
齐民要术 0 3 102
13
洛阳伽蓝记0 0 3 0
贤愚经296
70904
百喻经434 1 0
(《贤愚经》中的296次“已”包括“竟已”1次,“讫已”5次, “毕已”2次。70次“竟”包括“毕竟”2次,“讫竟”2次。90 次“讫”包括“毕讫”15次,“讫已”5次,“讫竟”2次。《百喻经》的统计方法同,数字不一一说明。)
显然,在汉译佛典中“已”用得很多,在中土文献中“已”用得很少。在我们调查过的三部中土文献中,《世说新语》这样比较接近口语的作品中没有“已”,《齐民要术》这样篇幅较大的作品中没有“已”,《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关于佛教的书,但不是佛典的翻译,而是中土人士的著作,其中也没有“已”。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别。
(2)更重要的是用法的差别。
(A)“竟”、“讫”、“毕”前面可以加时间副词, 这说明它们在句中是作谓语的动词。如:
1)尔乃水出,咸得洗手。洗手既竟,次当呪愿。 (贤二14)
2)作愿适竟,馀处悉断。唯雨宫里,七日七夜。(贤十三64)
3)行食与佛并僧遍讫,食乃还下,各在其前。(贤二14)
“已”前面一般不能加副词(“不已”是“不停止”的意思,不是这里讨论的“已”),如果有副词必须放在“已”前面的动词之前。这说明“已”的性质已经不是做谓语的动词。如:
4)既闻是已,复心念难。(贤十二57)
又如下面所引例23)、32)、33)、36)。(也有少数例外,见下文例48)。)
(B)“竟”、“讫”、“毕”可以用在一个句子的终了, 后面不再接另一小句。如:
一人观瓶,而作是言:“待我看讫。”如是渐冉,乃至日没,观瓶不已。(百50)
“已”或是用在一个小句之末,后面再接另一小句,或者用在句中,后面再跟一个动词词组。(例见下。)而未见用在一个句子的终了,后面不再接另一小句的用法。
(C)“竟”、“讫”、“毕”前面的动词必须是可持续的动词; 如果前面是一个动词词组,则是表示一个持续的动作。如:
5)言誓已竟,身即平复。(贤一7)
6)洗手既竟,次当呪愿。(贤二14)
7)众僧食讫,重为其蛇广为说法。(贤三18)
8)发言已讫,合境皆获自然之食。(贤八39)
9)到作礼毕,共白之言。(贤一1)
也有少数例外,详见下文例49)—56)。
“已”前面的动词也可以是可持续的动词(见下文例43)—48),但也有很多是不可持续的瞬间动词、状态动词。 用得最多的是“见(O)已”、“闻(O)已”。其他如:
10)夜叉得已,於高座上众会之中取而食之。(贤一1)
11)得王教已,忧愁愦愦,无复方计。(贤三15)
12)觉已惊怖,向王说之。(贤一2)
13)蒙佛可已,於时金财即剃须发,身著袈裟,便成沙弥。(贤二9)
14)其儿生已,家内自然天雨众毕,积满舍内。(贤二10)
15)其一山上,有柔软之草,肥瘦甘美,以俟畜生。须者往噉,饱已情欢。(贤二14)
16)散闍起已,泣泪而言。(贤三21)
17)我成佛已,自调其心,亦当调伏一切众生。(贤三21)
18)城南泉水,取用作墼。其墼成已,皆成黄金。(贤十一52)
19)城西泉水,取用作墼。墼成就已,变成为银。(贤十一52)
20)急疾还家,到已问婢大家所在。(贤四22)
21)到竹林已,问诸比丘。(贤四23)
22)至佛所已,即言:“瞿曇沙门及诸弟子,当受我请,明日舍食。”(贤四22)
23)既取肉已,合诸药草,煮以为腮,送疾比丘。(贤四22)
24)欲求善法,除佛法已,更无胜故。(贤四23)
25)舍此头已,檀便满具。(贤六31)
26)施七宝床,让之令坐。坐已具食,种种美味。(贤八40)
27)值一木工口衔斫斤,褰衣垂越。时檀腻羁问彼人曰:“何处可渡?”应声答处,其口开已,斫斤堕水。(贤十一53)
28)是王舍城王大健斗将。以猛勇故,身处前锋,或以刀剑矛矟伤剋物命,故受此报。於是死已,堕大地狱,受苦长久。(贤四23)
29)阿难灭已,此耶贳羁奉持佛法,游化世间。(贤十三67)
30)我灭度已,一百岁中,此婆罗门,而当深化。(贤十三67)
31)舍是身已,当生梵天,长受快乐。(百29)
32)驼既死已,即剥其皮。(百42)
33)彼既来已,忿其如是,复捉其人所按之脚,寻复打折。 (百53)
34)时树上人至天明已,见此群贼死在树下,诈以刀箭斫射死尸,收其鞍马,驱向彼国。(百65)
35)尔时远人既受敕已,坚强其意,向师子所。(百65)
36)既捉之已,老母即便舍熊而走。(百93)
“已”和“讫”、“竟”、“毕”的这种差别很值得注意。“讫”、“竟”、“毕”都是“完成动词”,表示一个动作过程的结束,它们前面必须是持续动词,这是由它们的语义特点所决定的:“V /讫/竟/毕”都可以翻译成现代汉语的“V完”。“已”本来和“讫”、 “竟”、“毕”一样,根据它的语义特点,前面也应该是持续动词。但是在上述例句中,我们看到有“死已”、“觉已”、“成已”、“至天明已”等说法,“已”前面不是持续动词,“死已”、“觉已”、“至天明已”不能读作为“死完”、“觉完”、“成完”、“至天明完”,这说明这种“已”的性质已经和“讫”、“竟”、“毕”不一样了,也和用在持续动词后的“已”不一样了。
(二)这样,我们必须考虑“已”的性质。
有的学者如张洪年(1977)早已说过,“V+O+了”中的“了”是受梵文的影响而产生的。何莫邪(1989)也说,“V+O+已”中的“已”是受梵文的影响而产生的。辛岛静志(2000)说得更清楚,他说:在汉译佛典里,在句末用“已”的例子十分常见。这种用法相当于现代汉语“看见了他就开始哭”的“了”,是一种时态助词。例如: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五百亿百千梵天…适见佛已,寻时即往”(大正藏第九卷90b16);“贤者阿难…心念此已,发愿乙密,即从座起, 稽首佛足。 ”(同97c29);“比丘尼见说此颂已,白世尊曰:‘唯然,大圣!’”(同106c13)等等不胜枚举。但在佛典文献以外的中土文献里这种“已”的用例极为罕见,这一事实就使人联想到与原典有直接关系。在梵汉对比时,我们就发现这种“已”大多数与梵语的绝对分词(或叫独立式;Absolutive,Gerund)相对应。 上面所举的“适见(佛)已”与梵语drstvā(H.Kern and B.Nanjio,Sanddharmapundarīka, St,Pertersburg 1908-12[Bibliotheca.-Budaahica X],第169页, 第3行)相对应;“念(此)已”与cintayitvā(同215.2)相对应;“说(此颂)已”与bhāsitvā(同270.5)相对应。 在梵语里绝对分词一般表示同一行为者所做的两个行为的第一个(“…了以后”),相当于汉译佛典的“已”。
这种看法用来解释“死已”、“觉已”、“成已”、“至天明已”的“已”很合适。既然这种“已”是用来翻译梵语的绝对分词的,而“绝对分词”是表示同一行为者所做的两个行为的第一个(“…了以后”),那么,用“死已”、“觉已”、“成已”、“至天明已”来表示“死了以后”、“醒了以后”、“成了以后”、“到天亮了以后”就很顺理成章;也就是说,这种“已”前面的动词可以是非持续动词。“已”的另两个特点也可以由此得到说明:这种“已”是用来翻译梵语的绝对分词的,所以后面必须再跟一个动词词组或一个小句;它不是汉语中原有的完成动词,所以前面不能加副词。只是辛岛说“已”是“一种时态助词”,似乎不妥。不过当时的佛典译者也不会用汉语中一个毫不相干的词来翻译梵文的“绝对分词”的。梅祖麟先生(1999)曾指出战国末期就有“V(O)已”,如《战国纵横家书》中的“攻齐已,魏为□国,重楚为□□□□重不在粱(梁)西矣。”是个完成动词。他还举出西汉的若干例子,如《史记·龟策列传》:“钻中已,又灼龟首。”钟兆华(1995)还举出《墨子·号令》中的一例:“开门已,辄复上籥。”我们检查这些例句,看到“已”前面的动词都是持续动词。关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完成动词,梅先生说,东汉多用“已”,用“讫、毕、竟”的不多,南北朝“已,讫、毕、竟”并用。文中都举了一些例子。我们看到,这些例子中的“已”前面绝大多数也是持续动词,这些“已”和“讫、毕、竟”是可以通用的。也有一些例子(东汉5例, 南北朝1例)中“已”前是非持续动词,但都是在佛典译文中。现将这6例抄录在下面:
37)是菩萨摩珂萨于梦中觉已,若见城郭火起时,便作是念。(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
38)成就作佛已,当度脱十方天下人。(同上)
39)既闻经已,无有狐疑大如毛发。(同上)
40)闻是言已,恍惚不知其处。(支娄迦谶译《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
41)佛饭去已,迦叶念曰…(竺昙果共康孟祥译《中本起经》)
42)诸比丘从如来闻已,便当受持。(僧迦菩提译《增壹阿含经》)
在本文所调查的《贤愚经》、《百喻经》中,也有一些“已”前面是持续动词,“已”可以和“讫、毕、竟”通用,如:
43)作是语已,寻时平复。(贤一1) 作是语竟, 飞还山中。(贤十一52)
44)佛说此已,诸在会者,信敬欢喜, 佛说法讫,举国男女得度
顶受奉行。(贤一6) 者众,不可称计。
(贤六34)
45)语已辞还所止。(贤四22) 导师语竟,气绝命终。(贤
九42)
46)供养已,即便过去。(贤六34) 供养毕讫,即时过去。
(贤六34)
47)食已,徐问所以来意。(贤八40) 食讫,谈叙行路恤耗。
(贤八40)
“已”前有副词的在《贤愚经》中仅有1例, 这一例的“已”前就是持续动词:
48)告下遍已,七日头到。(贤八40)
这种完成动词“已”是和战国末期、西汉的“已”一脉相承的,是汉语原有的。它和梵文的“绝对分词”有相似之处:汉语原有的“V(O)已”的“已”表示动作的完成,梵文的“绝对分词”表示做完一事再做另一事,或某一情况出现后再出现另一情况。所以佛典译者用这个“已”来翻译梵文的“绝对分词”。但两者毕竟不完全一样:“觉已”、“成已”、“死已”、“至天明已”等的“已”原来在汉语中是不会有的。证据是:“攻齐已”、“钻中已”的“已”完全可以换成“竟”、“讫”、“毕”,而“觉已”、“成已”、“死已”、“至天明已”等的“已”不能换成“竟”、“讫”、“毕”。所以,东汉魏晋南北朝的“V(O)已”的“已”应分为两部分:(A)一部分是“V1+(O)+已”中的“已1”(V1是持续动词), 这种“已”是在佛教传入前就已存在的、汉语中原有的“已”。(B)另一部分是“V2+(O)+已”中的“已2”(V2是非持续动词), 这种“已”是用来翻译梵文的“绝对分词”的。在佛典译文中,“已2”用得比“已1”多。 在《贤愚经》中296个“已”中有161个“已2”,占54.3%。在《百喻经》中,43个“已”中有40个“已2”,占93.0%。
这两种“已”在语法上应作不同的分析。从句子成分来说,两者都是补语,而且都是指动补语。从性质来说,“已1 ”是动词(完成动词),“已2”已高度虚化,只起语法作用,已经不能看作动词。 从作用来说,“已1”表示动作的完结;“已2”本是梵文的“绝对分词”的翻译,表示做了一事再做另一事,或某一情况出现后再出现另一情况,进入汉语后,也可以表示动作的完成。“完结”和“完成”仅一字之差,但在语法作用上是不一样的。“完结”表示一个过程的结束,所以前面必须是持续动词(吃完)。“完成”是一种体貌,表示动作或状态的实现,前面可以是非持续动词(死了),也可以是持续动词(吃了);在后一种情况下,正如梅祖麟先生(1994)所说,是“把这些动作动词的时间幅度压缩成一个点”。所以,“吃完”和“吃了”的“吃”不一样,“吃完”的“吃”表示一个时段,“吃了”的“吃”表示一个时点。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V+O+已”中的“已”,在佛典传入并且有了汉译以后,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种“已”原来是汉语固有的,它只能放在持续动词(或持续动词组成的词组)后面,表示动作的完结(即“已1”)。佛典传入后, 译经者用它来翻译梵文的“绝对分词”。“绝对分词”既可以放在持续动词后面(表示动作的完结),也可以放在非持续动词后面(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实现)。由于“完结”和“完成”相近,所以人们可以用汉语中固有的“已”(“已1 ”)来翻译梵文的绝对分词。但“完结”和“完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在佛典译文中用“已”(“已1”)来翻译梵文的绝对分词之后, “已”的性质就起了变化,它产生了一种新的语法功能: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实现)。换句话说,就是产生了“已2”。 这种功能是原来汉语所没有的,是受梵文的影响而产生的。但由于“已2”的频繁使用, 它逐渐地“汉化”了,不但在佛典译文中使用,而且在口语中也使用。“已2 ”在口语中使用的历史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据初步的印象,应该说初唐时期“已”已经是口语词了(见下)。
在《贤愚经》、《百喻经》中,“竟”、“讫”也有少数放在非持续动词后面(“毕”没有放在非持续动词后面的)。现将全部例句列在下面:
49)馀妇语曰:“汝不须言。汝夫状貌,正似株杌。若汝昼见,足使汝惊。”株杌妇闻,忆之在心。豫掩一灯,藏著屏处。伺夫卧讫,发灯来看。见其形体,甚用恐怖。(贤二14)
50)食饱已讫,便命令坐,为其说法。(贤七37)
51)王与夫人相可已讫,俱共来前。(贤九42)
52)时驳足王即许之,言:“当取诸王,令满一千,与汝曹辈,以为宴会。”许之已讫,一一往取,闭著深山。(贤十一52)
53)王博戏已,问诸臣言:“向者罪人。今何所在?我欲断决。”臣白王言:“随国法治,今已殺竟。”(贤五23)
54)自伺大家一切卧竟,密开其户,於户曲内,敷净草座。(贤五27)
55)尔时树神语太子言:“波婆伽梨是汝之贼,刺汝眼竟,持汝珠去。”(贤九42)
56)太子闻语,而答之言:“若有此事,我能为之。”共相可竟,即往为守。(贤九42)
《百喻经》中的“讫”、“竟”、“毕”没有用在非持续动词后面的。
上述八个例句,有几个例句单看“讫”前面的动词,应该说是非持续动词。但联系上下文看,说的还是一个持续的动作过程。如例49)例54)的“卧讫”、“卧竟”,相当于“睡着”,指一个入睡过程的完成。例51)、例56)的“相可已讫”、“共相可竟”,相当于“商量完毕”。例52)的“许之已讫”指答应他的一番话说完了。真正特殊的用法只有50)、53)、55)三例。即使把八例都算上,也只占《贤愚经》160 个“讫”、“竟”的5%。 这和《贤愚经》中用于非持续动词之后的“已”占50%以上是大不相同的。这些“讫”、竟”的特殊用法可以认为是受了“已”的影响。这不妨碍我们前面对“已”和“讫”、“竟”、“毕”的区别的论断。
(三)魏晋南北朝的“已”和后来的“了”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上述对“已”的看法,也会影响到对“了”的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竟”、“讫”、“毕”的分布大概持续到唐代。《游仙窟》中还是没有“已”,只有“竟”(1例)、 “讫”(3例)、“毕”(2例)。也没有“了”。而《六祖坛经》中的“已”有7次,其中前面是非持续动词的4次:“闻已”(2次)、“悔已”、“得教授已”。已有“VO了”和“V了”,其中1例是“闻了原自除迷”。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1)《六祖坛经》虽然是宣讲佛教教义的, 但不是佛典译文,而是惠能讲说的记录,可见其中的“已2 ”已经是口语中用的词。(《游仙窟》中没有“已”,可能和作者的个人风格有关。)(2)其中既有“闻已”,又有“闻了”。 “了”已经开始逐步代替“已”。
到晚唐,和佛教有关的文献中还有“已”,但更多的是被“了”代替。“V(O)了”中的“了”怎样分析?梅祖麟先生(1994)说:《敦煌变文集》中“V了”的“了”有两种。在下列句子中, “了”处在动作动词(偿、食、祭等)后面,是状态补语:
我是天女,见君行孝,天遣我借君偿债。今既偿了,不得久住。(变,887)
兵马既至江头,便须宴设兵士。官军食了,便即渡江。(变,20)
子胥祭了,发声大哭。(变,21)
在下列句子中,“了”处在成就动词(知、见、迷等)后面,是完成貌词尾:
王陵只是不知,若或王陵知了,星夜倍程入楚救其慈母。(变,44)
迷了,菩提多谏断。(变,521)
圣君才见了,流泪两三行。(变,772)
他说:动作动词是有时间幅度的,后面的“了”“意义上跟现代的状态补语‘完’相当”,所以是状态补语。“‘知’、‘见’、‘迷’是没有时间幅度的成就动词,后面的‘了’不能读作‘完’义的状态补语,只能读作表示完成貌的词尾。”
他的术语和本文不同,但应该说,这两种“了”的区分和性质与本文所说的“已1”和“已2”是一脉相承的。据此,也可以把“了”分为“了1”和“了2”。[注意:本文所说的“了1 ”是指持续动词后面的“了”,“了2”是指非持续动词后面的“了”, 和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中的“了1”(即完成貌词尾)和“了2”(即句末语气词)不是一回事。]
把“V了2”中的“了2”看作完成貌词尾毫无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了2”有时出现在宾语后面。 如《祖堂集》卷十:“又上大树望见江西了,云:‘奈是许你婆。’”如果说“圣君才见了”的“了”是完成貌词尾,那么“望见江西了”的“了”又如何分析呢?这种“了2”在性质上是和“已2”完全相同的。梅祖麟先生上述对“见了”的“了”的分析,完全可以用在“见已”的“已”上。那么,也就可以把“见已”的“已”看作完成貌词尾。但这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如果前面的动词带宾语,“已”永远是出现在宾语之后的。因此,尽管“已2 ”不能读作“完”义的状态补语,但不能说“已2 ”是表示完成貌的词尾。反过来说,在分析“了”的时候,似乎也不能仅仅根据它“不能读作‘完’义的状态补语”,就断定它是完成貌的词尾。
吴福祥(1998)把“食了”的“了”叫做“结果补语”,把“迷了”、“死了”的“了”叫做动相补语。他有他的术语。但这两种“了”都是指动的, 根据赵元任(1970 )的定义, 应该都属于动相补语(phase complement)。我认为动相补语可以分两种:(A)表示完结。 前面是持续动词。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已1”和“了1”。(B )表示完成。前面是非持续动词。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已2”和“了2”。
(B)类动相补语离完成貌词尾已经很近了, 但它要发展成完成貌词尾还必须再跨进一步:紧贴在动词后面,即使出现宾语,也不被宾语隔开。所以,“见了”的“了”,只有到《敦煌变文集·难陀出家缘起》:“见了师兄便入来”这样的句子里才是完成貌词尾。“迷了”、“死了”一般不带宾语(宋代才有“万秀娘死了丈夫”这样的例句),无法用这个方法检验。但语法发展是有规律性的,既然晚唐已出现了完成貌词尾“了”,我们可以认为,同时期和以后的“迷了”、“死了”的“了”也发展成了完成貌词尾,而在此以前的“死了”还是动相补语。“死了”在《贤愚经》中有一例:
57)王语彼人:“二俱不是。卿父已死,以檀腻羁与汝作公。”其人白王:“父已死了,我终不用此婆罗门以为父也。”(贤十一53,檀腻羁品第四十六)
这个“了”显然也是不能读作“完”义的状态补语,但如果据此就认为是完成貌词尾,说完成貌词尾在北魏时已经出现,那大概时间太早了吧。
在追溯完成貌词尾“了”的来源时,人们常常说,“了”的前身是“已”、“讫”、“竟”、“毕”。但是根据上面的分析,更准确地说,“了”的前身只是“已”。所谓“完成貌词尾”,第一是说它表完成貌,第二是说它紧贴在动词后面。表完成这种语法功能不是从“了”才开始有的,我们所说的“已2”就具备这种功能了(而“讫”、“竟”、 “毕”却不具备这种功能),梅祖麟先生(1999)所举的东汉支娄迦谶等译经中的例句,也许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最早的“已2”。
后来“了”兴起并逐渐取代“已”,“了2 ”也具备表完成貌的功能。但“V+O+已2”和“V+O+了2”中的“已2”和“了2”还都是被宾语隔开的,还不是词尾;只有到“了2”移到宾语前,出现了“V+了2+O”的格式后,汉语中才产生了完成貌词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