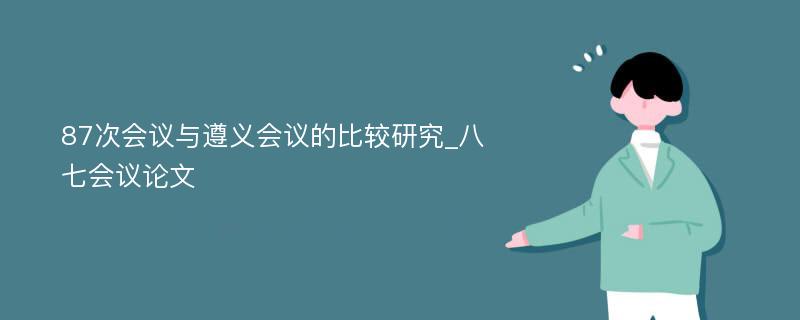
八七会议与遵义会议比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遵义会议论文,会议论文,八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 41 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70年后的今天, 我们研究八七会议,不妨将它与遵义会议试作比较,这不仅有利于深化对八七会议的探讨,也有利于加深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研究。
八七会议是在历经严重失败的险峻形势中召开的。1927年4月到7月,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公然抛弃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把反革命的屠刀对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国民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6万多党员的党, 在革命失败后的很短一段时间中竟只剩下1万多党员,出现了“非常崩坏的形势”(注: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3月1日。)。
遵义会议所面临的也是严重失败的形势。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放弃革命根据地,实行长征。长征初期,又继续遭受严重损失,致使中央红军在渡过湘江时,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
导致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主观原因,主要的都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错误。在国民革命时期,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理论基石,主要是“二次革命”论。这种理论,按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陈规,设计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远景,把国民革命的胜利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胜利。因此,虽然帮助改组国民党,却始终没有下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占主导地位的决心;在政权上,持“在野党”的态度;在北伐战争中,不注重发展自己的力量,而热衷于迎汪、扶唐、抑蒋,搞汪蒋平衡;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更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能够把汪精卫集团继续拉在统一战线营垒中。其间,虽然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的传达使认识一度有过变化,但未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沉疴,严重侵害了党的肌体。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错误,既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教条式指导有密切关系,也与党还比较幼稚有关。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到8年时间,连续3次“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在政治上,混淆革命性质,实行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完全违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注: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1961年8月21日;1963年4月17日,9月3日。)
这样,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所要完成的任务,便也是相同的,那就是纠正错误路线对党的统治。八七会议在政治上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决定在广大区域中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秋收暴动,表明已经开始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它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围绕新的政治方针,采取了加强组织建设的重要决策。
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提出的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这两个当务之急的问题,牵住了转变时局的牛鼻子。它虽然没有否定“左”倾政治路线,但“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注: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
由于坚决纠正了错误路线对党的统治,确立了新的行动方针,变换了党的领导,这就使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成为转换时局的、决定党的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它“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对于遵义会议,这个决议同时指出:它“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从作为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来说,八七会议与遵义会议并美齐辉于中共党史和中国人民革命史,千秋万世,永垂不朽。
但是八七会议毕竟是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又是遵义会议。时间、背景、主题、参加者的不同,必然带来其它一系列不同,从而使其各具特性。
遵义会议没有触及党在政治上的路线错误,反而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这里有一个策略问题。张闻天事后指出:“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让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注: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除了张闻天所说的争取犯过第三次“左”倾错误的领导同志这个因素以外,也应看到,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政治上的错误需要从思想上加以清理,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解决问题。摆在面前的现实是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后追前堵,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抓主要矛盾,首先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事实上,遵义会议后,新的路线取代了过去的路线。这样,遵义会议对“左”倾路线的纠正,分清轻重缓急,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办法,达到了目的。
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救出中国共产党于机会主义的破产之中”(注: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在政治上“使党有新的出路”(注: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3月1日。)。但是,它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又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政治上没有认识到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藉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积蓄革命力量,却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盲动主义的因素在新的中央领导中出现,并成为第一次“左”倾错误的先导。
对组织问题的解决,遵义会议表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会议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仍是代表党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进入常委会和最高军事决策圈,树立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样处理,涉及人事变动的范围小,但解决了根本问题,有利于在紧急关头实现战略转变。
八七会议对组织问题的解决有所不同。第一,它把长期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的陈独秀排斥在会议之外,“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1页。)。第二,它片面地强调了领导干部工人成分的意义,认为党发生机会主义错误,在组织上的原因就是各级指导机关中工农分子太少。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第三,对中共五大选举的政治局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八七会议增加政治局委员2名,候补委员3名。第五届政治局委员仅保留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则由候补升为正式委员,新选入罗亦农、向忠发、顾顺章、王荷波、彭湃、任弼时,占2/3。第五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保留周恩来、张太雷,新选入毛泽东、邓中夏、彭公达,张国焘、李立三则由正式委员降为候补。第五届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谭平山未保留,蔡和森也未保留,陈延年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未保留。这个大调整的主导方面,体现了八七会议在人事上与右倾投降主义的决裂。毛泽东被选入政治局为候补委员,周恩来保持政治局候补委员,对于开创新时期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于向忠发、顾顺章进入政治局,显然是机械地执行领导干部工农化政策的结果。
造成八七会议与遵义会议的上述不同,共产国际发挥作用的状况如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遵义会议乃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重要会议的举行,方针政策的调整,人事的变动,莫不必须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依据。1934年6月, 负责与共产国际保持电讯联络的上海中央局被警方破获,中国共产党断绝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倒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的机会。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失去了共产国际指令的依恃,坐上了被批判席。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所推行的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错误军事路线受到了批判。会议并且对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决议中给予指名批评。后来,毛泽东一再指出,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离开共产国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标志。遵义会议“才开始批评这些错误,改变路线,领导机构才独立考虑自己的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注: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1961年8月21日;1963年4月17日,9月3日。)。
八七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了主导性的作用。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指示“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紧急代表会议(最好不公开),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注:马贵凡译:《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史的档案文件》文件三,载《国外共党史中国革命研究译文集》(一),第402页。)。7月下旬,罗明纳兹到达武汉,即传达国际指示,作了批判陈独秀的报告。据李立三回忆:当时张国焘不同意陈独秀退出中央,而且以为没有办法召集会议,罗明纳兹两次三次催促,并声言如不召集会议,他便直接召集全国代表会议。后来,又派人到江西征求对国际的意见<%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3月1日。)。蔡和森也提到,罗明纳兹向张国焘等人声明:“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同时派人直接赴湖南宣布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和立即改组中央(注: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瞿秋白在中共六大的报告中讲到八七会议的召集时,也指出当时“中央经过一时的犹豫”(注:《八七会议》,第165页,第50、52、53页; 第10页,第125、126、128页,第161、172页,第54页,第57—88页。)。这些材料表明,八七会议的召开,罗明纳兹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起了重要作用。罗明纳兹还与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一起,筹备了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是罗明纳兹一手起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名单,先由罗明纳兹提出,讨论增补后,又经他认可方付表决。 八七会议3项议程,第一项就是罗明纳兹代表共产国际作报告,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这次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实行了总方针的根本转变,也与罗明纳兹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八七会议历史功绩的取得,共产国际和罗明纳兹自应有份,不可抹杀。
然而,由八七会议所开始的“左”倾错误,同样与共产国际和罗明纳兹分不开。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为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方针,是“一次革命”论的亦即所谓“不断革命”论的方针,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中他是革命的,现在已经反动了。”“我们应很坚决的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并且还应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打倒后帝国主义才能打倒”(注:《八七会议》,第165页,第50、52、53页;第10页,第125、126、128页,第161、172页,第54页,第57—88页。)。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脱离实际地宣扬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注:《八七会议》,第165页,第50、52、53页;第10页,第125、126、128页,第161、172页,第54页,第57—88页。)。8月21日, 中央常委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完结了他们的革命作用”,“成为反革命之最积极的动力之一”。中国的民族解放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只有工农的民权独裁与国际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直接斗争,——‘民族’资产阶级亦在其中——如此,方能履行这一任务”。决议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始终将要是一个无间断的过程”,“如果无产阶级及农民,怕超过资本主义式的关系,怕进入社会主义式的道路,那么,就是民权革命也不能得到胜利的完成”(注:《八七会议》,第125、126、128页。)。显然,这些论断与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的讲话一脉相承。甚至后项决议也出自罗明纳兹之手,亦不无可能。1927年底,罗明纳兹返国。12月,他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继续侈谈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他宣称:“如果革命不采取一些社会主义变革方面的决定性步骤,那么,任何一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是不能解决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已经过去了,它已属于完结了的历史时期。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第30、31页。)罗明纳兹的这些观点, 对于八七会议开始的“左”倾错误的形成,毫无疑义地具有某种灵魂的作用。
其实,罗明纳兹的这些思想,并不是他自己的原创,乃是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时的理论和政策提出来的, 他不过发挥到极端罢了。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革命问题》, 认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不久,斯大林又提出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第三阶段便是“苏维埃革命”。他断言:在这个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革命队伍中剩下的只是工人和农民。穷本溯源,这正是罗明纳兹超越中国实际的错误观点的源头。
中共六大指出八七会议对于左派国民党问题,“还保存了些幻想”。瞿秋白在会上承认:“我们的八七会议是错了这一着。群众先我们看见青天白日的旗帜,变成白色恐怖旗帜了。”(注:《八七会议》,第161、172页。)这个问题也是来源于共产国际的。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作出7项决定,第三项是:“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使国民党领导者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第532页。)。 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通过与国民党下层群众的联系,自下而上地改组其领导机关,并以此为基础召集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也强调:“现在不应退出国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要在国民革命成功社会革命时才能提出。”(注:《八七会议》,第54页。)不肯放弃国民党的旗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托洛茨基就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问题进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需要坚持这个政策试图挽回局面,以加重同托洛茨基斗争的砝码。
中共党人政治成熟水平的不同,是八七会议区别于遵义会议的内在根据。遵义会议的主心骨是毛泽东。毛泽东比较早地觉察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抵制和反对。他的正确主张曾被“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指责为右倾,并被排挤了对红军的领导。张闻天、王稼祥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层中毅然分化出来,对取得遵义会议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长征开始后,周恩来“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注: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至于红军将领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早就不满“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因此,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副报告,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及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注: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其内容是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研究的,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会后,他又起草了会议决议。在遵义会议上,对“左”倾错误形成了一种压倒的优势,是党成熟的表现和结果。
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批判,也是痛快淋漓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系统地批判了右倾错误,指出在国民党问题上,无在国民党中当主人的决心;在农民问题上,广大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而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在军事方面,不做军事运动而专做民众运动。蔡和森指出中央没有执行五大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党的指导没有建筑在群众方面。他提出党的家长制非打倒不可。罗亦农指出党的机会主义根本出发于无坚决夺取政权的决心,是革命的作客者,而不是革命的主人。任弼时指出党只做上层工作,未深入领导民众,甚至抑制群众;无土地革命的决心;怕群众。邓中夏指出机会主义早有由来,产业工人进入党的指导机关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注:《八七会议》,第165页,第50、52、53页;第10页,第125、126、128页,第161、172页,第54页,第57—88页。)。右倾投降主义给革命带来的惨重损失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对罗明纳兹的主题报告和会议要通过的文件没有争论,“一致反对过去机会主义,完全同意国际新的路线”(注: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3月1日。)。
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出现“左”的倾向,除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导以外,党内也有群众基础。李维汉认为:当时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属幼年,还很不成熟,还不能对陈独秀投降主义在理论上、思想上作系统的正确的分析和清算,也不能对新的方针和政策在理论上、思想上作系统的正确的分析和阐释。革命的失败,又使得党内比较普遍地产生出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拚命的精神。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167、168页。)。这种“左”比右好的思想,在国共合作实现之前就已产生。张国焘在中共三大上就说:“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注:马林档案,转引自《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76页。) 至于党的领导人的思想理论状况,瞿秋白最有代表性。他在五大以前对右倾投降主义作过系统批判,理论水平比较高,但思想中也存在着“左”的东西。1927年2月, 他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写道:“中国革命既以农地革命为中枢,又系反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军队,自然应当从国民革命生长而成社会变革——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可见中国现时的革命,既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的确是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虽产资产阶级性的,然而他与世界无产阶级联盟而反抗列强帝国主义;他的胜利的前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注:《六大以前》,第695、697页。)这些思想是他与罗明纳兹相一致的基础。正如罗明纳兹一样,瞿秋白的这些观点也是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理论和政策中得来的。不过,瞿秋白“一次革命”的观点似乎萌芽较早。他将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加上引号, 所引述的乃是1923年12月他在《新青年》第2期发表的一篇论文的观点。指导革命的理论,没有与中国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生吞活剥,还不善于吸收消化,这是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
八七会议与遵义会议存在着上述异同。通过这个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强化和加深这些认识:第一,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不到8 年时间,自建党以来,也不过14年时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转折。党的成长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然而, 1927 年和1934年的两次严重失败,并没有压跨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克服艰难险阻,吸取经验教训,党在革命实践的疾风暴雨中茁壮成长起来。第二,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基本保证。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中,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共产国际坚持用外国模式和经验来裁剪和规范中国革命,产生严重的教条主义,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事实已经证明:“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第116页。)第三,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任何时候都不能搞“本本主义”。如果以为有了什么“本本”,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可以无往而不胜,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第116页。)。第四,毛泽东是唯一的这两次历史性会议的正式参加者。遵义会议,他力挽狂澜。在八七会议上,他还不是主要人物,但他的发言总揽全局,高屋建瓴,紧紧抓住农民问题和枪杆子问题不放,切中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显示了领袖人物独具的素质和风采。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坚强核心,实乃由来有自,从这里不可以看到完全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吗!
标签:八七会议论文; 遵义会议论文; 陈独秀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毛泽东论文; 张闻天论文; 罗明论文; 纳兹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