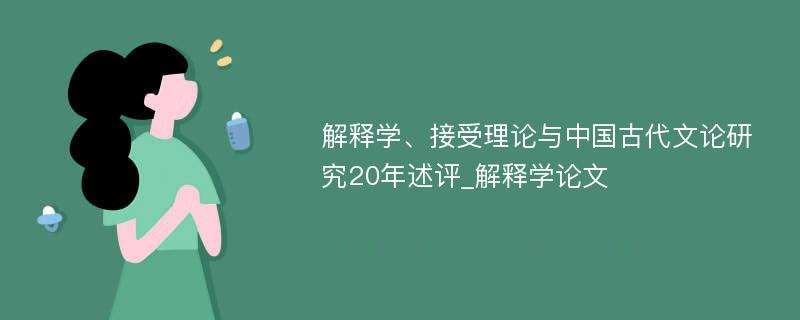
阐释学、接受理论与20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述评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年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6)01—0114 —07
在对《诗》、《骚》等古代文学经典的阐释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阐释思想和方法[1]。随着西方阐释学和接受理论的传入和引进,中国的文学阐释学研究开始出现突破性的变化。现今,尽管当年那些被同时引进来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已开始消退,但站在现代理论的高度,借鉴西方阐释学和接受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的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发掘和阐释的研究仍呈现出旺盛的态势,并正在孕育中国特色的文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
第一读者的尝试:比较诗学学者的实践
阐释学与接受美学是西方20世纪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研究的中心是作品和读者的关系,认为文学研究不能仅从作品入手,还应把读者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西方阐释学的核心是理解,理解如何成为可能是它要解决问题的关键,为此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阐释学提出了“偏见”、“前理解”、“视野融合”等重要概念。在阐释学哲学基础上,姚斯和伊瑟尔开创了接受美学理论,主张研究文学与文学史,必须侧重读者的接受过程。他们分别从宏观的关注读者审美经验的文学史研究和微观的文本召唤结构研究,确立了读者的本体地位。1991年,金惠敏等人在翻译完伊瑟尔的《阅读行为》后,在译序中曾预言“把这部晦涩的德国现象学著作译介给中国读书界,我们不敢奢望它会引起一场震动,颠覆根深蒂固的解读习俗,但相信它会给中国古典阐释学以一个冲击,至少会洞开一扇户牖,透进些新鲜空气。”[2] 正如译者所料,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很快就在中国文学阐释领域找到用武之地,这是因为中国文学阐释史中存在着大量可与它们互证、互识、互补的资料。当中国学者的古代文学阐释经验与之相遇,相见恨晚的情绪就会自然流露。
其实,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和实践,早在它被译介前就开始了。钱钟书以及深具西方背景的华人学者张隆溪、叶维廉、叶嘉莹,至迟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接触西方的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良好的外语基础和所处地带文化环境,让他们具备了成为“第一读者”的条件;而博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则让他们走在中国大陆大多数古代文论研究者的前头。他们从中西诗学比较的角度,对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研究的实践中积极垦拓,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引用西方解释学的阐释循环,互证乾嘉“朴学”的“知字、识句、通篇”方法:“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立本,而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 ‘所谓阐释之循环(Derhermeneatische Zirkel)者是矣’”[3](P171)。这种中西阐释学理论的互证互识方法,启发了后来的相关研究。
受钱钟书鼓励,时在美国哈佛的张隆溪80年代初连续于《读书》上介绍20世纪的西方文论,其中就有阐释学和接受美学。1983年《文艺研究》的第4 期发表了他的《诗无达诂》,该文第一次从比较诗学的角度,运用丰富的中国传统文论知识,较详细地对中西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思想进行互证、互释。中国的“诗无达诂”思想,经此文阐释,焕然一新,引起了大陆学者对中国阐释学思想的浓厚兴趣和极大关注。1984年3月《读书》又刊登了他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阐释学与接受美学》,粗线条勾勒了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及读者反应理论的主要观点和流派。
1984年,旅居美国的华裔学者叶维廉在台湾发表了《秘响旁通——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中外文学》十三卷二期1984年),其后又分别于1985、1986 年在《联合文学》上发表了《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与作品对话——传释学初探》。作者借这些文章,试图建立中国的传释学。 他认为不用西方的“诠释”(hermeneutics)而用“传释”,是因为“诠释”往往只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去了解一篇作品,而未兼顾到作者通过作品传意、读者通过作品释意(诠释)这两轴之间所存在的种种微妙的问题,他所要探讨的是作者传意、读者释意这种既合且分、既分且合的整体活动[4]。这样,叶维廉不仅从理论上发掘了中国古代阐释学的内在精神、思维形式、阐释路径,还进行了具体的批评实践,开辟了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道路。
1986年12月至1988年6月, 同在海外的著名词学家叶嘉莹在《光明日报》分别撰写《从现象学到境界说》、《“比兴”之说与诗可以兴》、《三种境界与接受美学》等系列论文,后由岳麓书社在1992年结集为《中国词学的现代观》。作者借用西方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来反观中国传统词学理论,认为两者有颇多暗合之处,并以此分析了“兴于微言”与“知人论世”、“比兴”说与“诗可以兴”等古老的中国阐释学问题。她分析张惠言与王国维对美学客体的不同解释,认为王氏说词是属于对美学客体的一种哲学诠释,而张氏则是一种政治、道德诠释。这种借用西方文论反思中国传统文论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上述4位名家在引用西方的阐释学、 接受美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古代文论,侧重的方向各不相同。具体来说,钱钟书侧重中西互证互释,以期达到中西融通的效果;张隆溪则从互证互补的角度,充分调用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资源,比较中西阐释理论的异同,以中补西;叶维廉在中西诗学比较的实践中,执着地设想建立中国传释学理论,融西于中;叶嘉莹则为我所用,借鉴西方理论发现中国特色的读者理论,借西释中。4位名家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对后来的研究深有启发。
接受的初期:理论的引入与视界的融合
80年代中期后,西方的接受美学、阐释学理论纷纷译介到中国,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空间也悄然开阔起来。与上述学者得天独厚的外语能力和西方经验相比,中国大陆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者,大多必须借助译介的西方理论文本,因此在借鉴和比较中,他们不可避免出现诸多的“隔”。
为“引起研究文艺理论和文学史方法论的同志注意外国当代文论的新动向”[5],1983年张黎发表了《关于“接受美学”笔记》,该文被认为是较早介绍接受美学理论的论文。1987年由周宁、金元浦翻译出我国第一本接受美学论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为我国学术界开始直接阅读接受美学著作,从宏观本体上把握接受美学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理论文本。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伽达默尔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因译文准确性的原因,少为学术界引用。但1986年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殷鼎的《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三联书店),都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阐释学理论的窗口。1992、199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出版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终于让学界较全面地了解到西方阐释学的理论。随着相关论文、著作的翻译,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很快就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找到生存空间,大大开拓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领域。
(一)中西接受理论的互证互识
与前面4位学者相比,初识这一理论的大陆学人,或许是对西方理论把握不深,或许是对中国文学接受理论的不自信,他们在质疑中,小心翼翼地进行中西互证、互识、互补,发现和整理中国古代接受理论。
1.中国特色接受美学术语的发现
国内较早借鉴西方阐释学、接受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大多是从中国古代文论的接受术语开始。较典型的如董运庭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玩味”说与西方接受美学》(《四川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邓新华的《“品味”论与接受美学异同观》(《江汉论坛》1990年第1期)、程地宇的《空纳万境,白多余韵——艺术空白论之一》(《探索》1990年第6期)、王志明的《“诗言志”、“以意逆志”说和接受理论》(《文学遗产》1992年6期)、樊宝英的《中国诗论“入出”说的审美接受意蕴》(《文史哲》1996年第5期)、周若金和樊宝英的《作者得于心 览者会以意——谈中国古典诗学的“自得”说》(《齐鲁学刊》1997年第2期)、 张胜冰的《接受美学与“道”》(《思想战线》1998年第1期)等等。通过比较,他们发现中国的读者接受理论不仅可与西方的接受美学相媲美,而且还在某些方面弥补了接受美学的不足。中国古代接受思想虽然不及西方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那样片面深刻,但却更为全面和辩证;中国美学的意味品鉴比西方美学的意义阐释更接近艺术的真谛。
2.中西接受理论的互证互识
在对古代文学阐释学的接受意蕴发掘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从宏观的读者接受角度比较中西读者理论的差异。如殷杰、樊宝英的《中国诗论的接受意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龙协涛的《中西读解理论的历史嬗变与特点》(《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紫地的《中国古代的文学鉴赏接受论》(《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唐德胜的《中国古代文论与接受美学》(《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樊宝英的《略论中西文论接受思想的异同》(《齐鲁学刊》1999年第4期)等等。这些论文通过考察中国古代文论重视读者接受过程中形成的接受和鉴赏术语发生、演变的过程,发现了中国古代诗论的特征:一是在中国古代诗论中,作者、作品、读者三者往往是三位一体的。诗论家从来不脱离诗作者和读者的接受关系来孤立地考察和研究诗作品,这与西方接受美学专志于读者中心,忽略文学作品的生成有所不同。二是中国诗论本身是一种泛美学接受,它自始至终蕴藏着强烈的读者意识。它既关乎诗歌的生成论,又关乎诗作的接受论,如“滋味”、“兴趣”、“神韵”等术语具有创作与接受的双重内涵。三是按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是先有创作,后有鉴赏,但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如“诗言志”等,最早并非是从创作中总结出来的,而是先从鉴赏中总结出来,以后才演变为指导创作实践,成为创作经验总结。
(二)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思想的整理
中国古代在对经典的解读中,产生了许多富有特色的文学阐释学思想。在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理论引进中国后,发现、整理古代经典的阐释思想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关注的热点问题。
1.“诗无达诂”诗学思想的再探讨
自张隆溪的《诗无达诂》发表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这一在古代文论中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1992年广东省古代文论研究年会曾以笔谈“《诗》无达诂”作为年会主题,要求着重探究阐释学、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等西方读解理论与“诗无达诂”的联系,以期有批判地借用西方的理论来整理、论析“诗无达诂”的诗学意义和创作欣赏的实践意义[6]。因为笔谈的学者大部分都是古代文论的研究者,且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理论还处于刚引入中国学界的状态,这种情况限制了他们深入探讨“诗无达诂”这一中国阐释学术语的可能性。他们的讨论仅限于借用西方理论之名,来发现中国“诗无达诂”阐释理论之实。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从分析的实践中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是所有的诗都不可达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实际上“有达诂”的诗,是比“无达诂”的要多。如孙立的《“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学术研究》1993年第1期),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诗无达诂”内涵在中国历代的演变及发展。邓新华的《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宁夏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通过讨论“诗无达诂”的释义特点和规律,指出它不仅高扬解释者在文学释义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赋予解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利,而且还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释义活动中解释者与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西方现代释义学无法解决的文学释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青年学者李凯更是认为“从阐释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诗学应该是了解和认识中国诗学,尤其是儒家诗学的必然选择。”[6] 他分析儒家元典在阐释形态中最有影响的几个命题,其中一个首推“诗无达诂”。
2.中国古代阐释理论初探
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释义特色的探讨,向来不为国外汉学家所重视,但从台湾学者李淑珍的论文《当代美国学界关于中国注疏传统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其实海外的汉学者较早就关注这一论题,“他们对文献的掌握或许不如中国学者周洽,但方法论上的反省大抵深刻犀利,对国人饶富启发。”[8] 如美国学者韩德森著有《典籍、正典与注疏:儒家与西方注疏传统的比较》[9],范佐仁著有《诗与人格:传统中国经解与诠释学》[10]。两位美国学者首开风气,分别从比较宗教及诠释学角度探讨中国阐释学传统。韩德森从宏观角度鸟瞰中西文化典籍及文化传统,揭露了我们习焉不察的儒者读经假定与解经策略。范佐仁则把焦点放在《诗经》的精读,认为《诗经》的重点在追溯诗人之志,藉以改变读者人格。
相比之下,大陆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的重视还要晚一些。1994年普慧发表《试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解释学思想》一文,较早认识到“如果结合西方现代解释学的理论,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就可以发现,在我们传统思想中,已经孕育着现代解释学的强烈胎动。”[11] 1998年汤一介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刊登了《辩名析理:郭象注〈庄子〉的方法》,文章对郭象注释《庄子》的两种方法“寄言出意”和“辩名析理”作了具体的分析,并在最后提出有关“创建中国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其后他又先后发表了《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学人》第13期,1998年3月),《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等文章,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 他认为这是“基于中国有长期而丰富的‘经典注释’的传统”,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理论应是在充分了解西方解释学,并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历史上注释经典的问题作系统的研究,在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丰富的注释经典的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之后,发现与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有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并自觉地把中国解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12] 此外,如周光宪、郜积意、李清良、杨乃乔等人,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的阐释学和解释学的理论研究,他们或从大处着眼,对中国古代解经方法进行梳理,或从小处着手,探讨中国阐释学特色的概念、术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3.哲学界的两次集中讨论
在中国解释学逐渐为学界所熟悉和认同后,中外学者开始对中国解释学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中国经典的阐释问题,首先引起了哲学界学者的关注。而对中国经典阐释的哲学研究,反过来又启示着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的研究。1999年台湾的《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发表了一辑专以中国经典阐释传统为主题的论文。如前面提到李淑珍的《当代美国学界关于中国注疏传统的研究》,集中介绍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注疏传统的研究,让人领略在外来文化观照下的西方学者的独特视角和观点。张隆溪的《经典在阐释学上的意义》,看到经典的超越历史性,认为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它不仅属于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而且能克服历史距离,对不同时代甚至不同地点的人说话。张鼎国的《“较好地”还是“不同地”?——从诠释学论争看经典注疏中的诠释定位与取向问题》,认为经典的权威除了自身外,还有一个历代注疏者随着时代的要求而建立的权威,所有诠释理解活动,必然包含着有传统经典的新生与传承,以及期望使其持续发挥实效及影响的努力。洪汉鼎的《从诠释学看中国传统哲学“理一而分殊”命题的意义变迁》,则从本体论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的哲学问题。两年后,中国大陆的《学术界》(2001年第4期) 开辟“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专栏,据编者按,其目的是“希望能对狭义‘解释学’(中国经典解释学)”,进而对广义‘解释学’(包括其他的解释学)的研究与批判,注入新的活力,从而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解释原则的创新。 ”其中汤一介的《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就是希望借鉴西方的解释理论与方法来讨论中国的“解释学”问题。他详细分析对经典著作解释产生的解释方法,认为《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可称为历史事件的解释;《系辞》对《易经》的解释,可称为整体性哲学解释;《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可称为实际(社会政治)动作型的解释。周光庆的《中国古典解释学方法论反思——兼与杨润根先生商榷》,反思中国古代解释学的解释方法论,认为在“述而不作”亦即“寓作于述”解释宗旨的作用下,中国文化经典解释的基本方法是语言解释方法、历史解释方法和心理解释方法,它们相互结合,不断发展,从一个角度成就了中国文化经典解释曾有过的辉煌。而王中江的《“原意”、“先见”及其解释的“客观性”——在“方法论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之间》,站在中西解释学的比较视野,考察中西解释学对“原意”、“先见”和“客观性”所持的基本立场,以缓解方法论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之间的紧张关系。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中国阐释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西方接受理论、阐释学传入并引发中国接受诗学研究大潮的驱动下,在哲学界建立中国阐释学倡导的感召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界出现了一个以读者研究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理论体系建构热潮。
较早借用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理论来分析古代文学的著作除前面提到叶嘉莹的《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外, 还有张思齐的《中国接受美学导论》(巴蜀出版社1989年)、龙协涛的《文学读解与美的创造》(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董洪利的《古籍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樊宝英与辛刚国合著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接受》(石油大学出版社1997年)、徐应佩的《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金元浦的《文学解释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这些著作,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文论中阐释学理论的特色,为后来古代文学接受史的撰写和中国接受诗学、中国文学阐释学理论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
1.文学接受史撰写的兴起
1998年陈文忠撰写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把接受史方法引入古典诗学研究,以作为接受史料的历代诗话为学术基础,考察经典作品的接受史及其诗学意义。这种新的研究范式的尝试,有力地回应了从读者角度撰写文学史的怀疑论。该著作既是具体作品接受史的微观研究,又是接受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总结概括,其中不乏精辟论点,如对接受美学“第一读者”的互识互补,对建立中国古代接受史架构的理论设想,都富有启发性。它通过对“单个作品”的微观接受史研究的实践,提出通过不同种类、不同性质作品接受史的考察,揭示接受史研究的多种方法、途径的可能性,并为古典文学具体作品的接受史写作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如果说陈文忠的著作仍是文学史撰写的理论建构和微观实践的话,那么尚学锋等人合著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则是首开撰写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的先例。它采用读者的视角,从历时性的角度探讨历代文学接受的历史文化情境,读者的接受方式和接受特点,总结古典文学接受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从共时性的角度则贯穿了历代对《诗》、《骚》、陶、杜等文学经典和名家的阐释和接受特征。
李剑锋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是一部单个作家的接受史。著作以西方为主要参照,兼用旧的方法搜集梳理资料,对元代以前陶渊明接受史的轨迹进行描述和探因。通过具体接受实践的分析,作者比较中西读者理论的差异,发现了中国接受理论三大特色:一是体现在理论的表现形式上,中国阐释学理论不注重理论体系的建构,但历代读者审美鉴赏经验的层积却为理论体系的形成不断添砖加瓦。二是体现在中国特色接受现象上,历代诗人学陶、仿陶成为陶渊明接受史普遍而重要的现象。三是体现在中国特色的理念术语上,在陶渊明的历代接受中,形成了真古、旷远、平淡、豪放、自然、闲雅、趣、味、韵等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理念术语,这些术语不像西方文论那样内涵精确、界说分明,却能较为传神地与批评对象相吻合。
2.中国接受诗学、中国阐释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自西方阐释学、接受理论逐步为中国学者熟悉以来,尽管不少学者提出建立中国解释学的设想,但从读者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理论的著作并不多见。青年学者邓新华首开其风,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就在全国各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以西方接受美学、阐释学作为理论启导和比较参照,发掘、整理、阐发中国古代富有民族特色的接受理论。他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出版社2000年),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首次系统地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进行清理、挖掘和阐发,并尝试建立起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国接受诗学体系。
另一青年学者李清良的《中国阐释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从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出发,系统清理了中国阐释学理论,全书分“导论”、“语境论”、“‘时’论”、“理解根据论”、“理解过程论”、“阐释论”六大部分。以西方阐释眼光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学思想,他发现中国特色的“中国时论”、“双重还原”法、“解喻结合”等阐释方式、方法,对中国古代阐释理论的建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2002年,周光庆在多年来从事中国古典解释学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中华书局2002年)。该书从宏观上对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历史存在和发展进行探寻,从微观上则对中国古典解释学进行个案研究,清晰地显现了中国古典解释学的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和效果。
2003年, 知名学者周裕锴出版了《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该书是他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题成果。 周氏在前言中认为阐释学并非西方的专利,尽管“阐释学”一词译自西文,阐释学作为一种理论主要是由德国传统发展而来,“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文化中同样存在着一套有关文本理解的阐释学思路”。著作中,他试图通过收集分析散见于各种典籍中有关言说和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的论述,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经学、玄学、佛学、禅学、理学、诗学中蕴藏着的丰富的阐释学理论内涵,并由此揭示出中国古代阐释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异于西方阐释学的独特价值。
李咏吟近年来连续出版了与解释学有关的系列著作,如《诗学解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创作解释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解释与真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这些著作虽侧重于哲学方面,但在对西方解释学理论的透彻理解基础上,李咏吟探讨中国古典解释学与诗学解释学的问题,指出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两条路向,一是儒家诗学解释体系,另一个则是诗骚解释体系。
有人曾感叹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文论一直是“负债经营”,从非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化中“借贷”数额巨大,赤字过高,认为文论必须在新世纪里通过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等的综合研究中提高质量,变“输血”为“造血”,改变现有局面。[13](P293) 回顾西方读者理论在20多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实践,正如乐黛云先生在为刘耘华的《诠释学与先秦儒家之意义生成——〈论语〉、〈孟子〉、〈荀子〉对古代传统的解释》一书作序所云,从选题到论证“都受到西方诠释学的‘照亮’和启发,借助他种文化的光亮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了新的、与现代文化接轨的解读,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同时又以中国的诠释实践以及从这种实践所产生的新的理论丰富和改造了西方诠释学的内容。”[14] 这一学术努力堪称是变“输血”为“造血”的成功尝试。
标签:解释学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接受美学论文; 张隆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