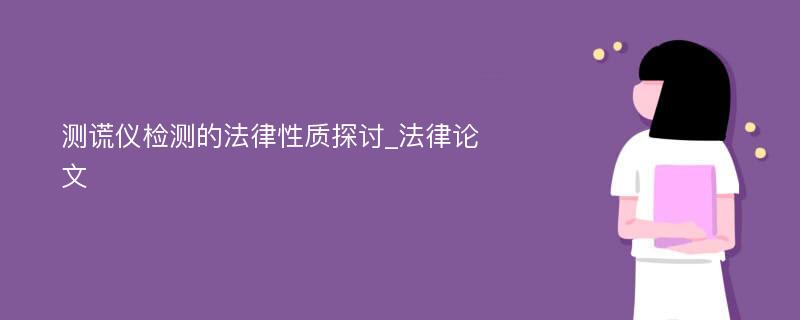
测谎的法律性质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质论文,测谎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测谎(Polygraph Test)①是指由具有测谎资质的人员运用专门仪器记录并分析被测人在接受特定刺激时的生理反应强度,并进一步判断其对相关问题是否知情或有关陈述是否真实的一种活动。测谎技术历经了100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当代,有50多个国家在使用测谎技术。测谎最初是在刑事诉讼领域发挥作用,被作为立案的前提条件、侦查的辅助手段、审判的证据,促进辩诉交易或刑事和解、在量刑时作为缓刑适用条件等。除了传统的诉讼领域外,测谎在国家安全、私人事务等方面的运用也逐渐增多,其人员筛查功能、人权保障功能、威慑功能都得到了充分发挥。然而,由于早期测谎原理存在的瑕疵以及诸多影响测谎准确性的因素的存在,使测谎的科学性受到一定质疑。此外,测谎系对被测人不愿为人所知的内心真意的揭示,可能侵犯被测人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反对自我归罪特权等权利。因此,各国基于对测谎科学性和正当性的不同考虑,对测谎的适用领域及测谎结论的证据地位各有不同做法。 在我国,测谎技术及其结论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其扩大运用的趋势非常明显。在北大法宝、北大法意和万律中国等数据库里,以“测谎”作为关键词,查询出的判决书数量逐年大幅提升。在审判中利用测谎技术的法院涵括了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这三个层级,在地域上遍及全国各省市。测谎技术不仅被用于刑事案件,还被扩展到了民事审判中,成为公检法机关都在积极利用的一种证据调查方式。某些办案部门对测谎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据媒体报道,我国东部某基层检察院在其推广的一种讯问方法中,要求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都必须佩戴一种仪器,在讯问时使用仪器同步观察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反应,以查明其回答是否撒谎。虽然该院在推广这种讯问方法时只字未提测谎,但根据其使用的仪器和技术方法来看,这种讯问方法无疑就是测谎,只是通过改头换面的处理来规避对测谎的科学性和正当性质疑而已。另据笔者了解,我国南方某市检察院要求其辖区内所有反贪部门,在每一个案件中都必须进行测谎测试,目的是用测谎来验证前期侦查结果、增强办案人员信心。随着测谎实务运用的普及,公安部于2005年颁布的《公安机关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均把测谎(心理测试)纳入其登记管理的鉴定业务范围。为了充分发挥测谎的作用,各地检察院纷纷出台规定促进测谎的发展。而与测谎有关的几起重大案件,更是把测谎推向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其中既有成功运用测谎破案的例子,如1998年杭州市萧山建设银行失窃案②;也有根据错误的测谎结论实施刑讯逼供导致重大冤案的,如1998年杜培武故意杀人案③;还有因被测人权利未能实现导致的对测谎程序规范的质疑,如2008年周正龙“伪造虎照”案④以及2010年山木集团前总裁宋山木强奸案⑤。 然而,我国迄今为止还没有直接规范测谎的具体法律规范,测谎技术的运用出现了一定的异化现象,如缺乏正确的功能定位,测谎沦为威胁、骗取被测人口供的工具;缺乏测试人员资质认定标准和测谎技术规范标准,影响了测谎结论的可靠性;缺乏严格的诉讼程序规范,被测人权利屡受侵犯。测谎技术的异化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测谎结论在诉讼实务中的运用极其混乱。各地法院对是否在裁判文书中评价测谎结论、是否将其作为裁判依据,做法各异。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与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即测谎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因为,诉讼法对不同的证据调查方法规定了不同的程序,测谎的性质不同,其程序规范亦不同;诉讼参与人可以享有的权利亦受诉讼行为性质所影响,如测谎是否具有言词性质决定了被测人能否主张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测谎的性质也决定了测谎结论的证据地位。因此,我国亟须对测谎的过程和测谎结论的运用予以规范,测谎的法律性质的确定将为从法律上规范测谎结论的生成和运用提供指引。由于我国测谎主要运用于诉讼领域,故本文的研究以诉讼中的测谎为基点。 二、测谎的法律性质之争 我国大陆学者鲜少探讨如何在诉讼法上给测谎定性,仅能从他们对测谎结论证据种属的论述中窥知他们对测谎属性的不同态度。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测谎的性质争论颇多,代表性的观点有侦讯说、勘验(人身检查)说、鉴定说。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测谎与讯问(询问)⑥、勘验、人身检查、鉴定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一)侦讯说 侦讯说认为,测谎属于讯问。如日本的田官裕认为,被测人对测谎问题的回答表现了其内心意思,测谎应视为供述的一种。⑦又如我国台湾地区的蔡墩铭认为,实施测谎检查并不是要以被测人的生理变化本身作为独立的证据,而是借由被测人之生理变化将质问与回答之间的对照关系体现出来,而成为证据,故仍具有供述证据的本质。⑧邱俊智、林故廷等人认为,测谎与讯问具有相似性,测谎过程具有发问与回答的意味,是侦讯取得供述的变形运用,所以测谎属于一种侦讯处分。⑨侦讯说看到了测谎与讯问的相似性,但没有看到测谎与讯问的实质性区别,不具有合理性。测谎不能定位于讯问。 讯问是侦查、检察或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就案件事实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发问。讯问是获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重要方式,获取口供是讯问的主要目的。测谎和讯问的相同之处表现在:(1)两者的进行方式相似。测谎的过程包括测试人员提问、被测人回答(在少数情况下可以不回答)、测谎仪同步记录生理反应、测试人员评判图谱并得出结论、作为证据或其他资料使用。讯问的方式是,有关人员提问、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回答、把回答予以记录、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这两个过程非常相似,都是通过提问与回答的方式进行的。(2)两者都具有交流的性质。信息的交流不以口头表达为限,只要行为人足以使他人了解、知悉其内心意思,就构成一种交流。讯问是采用问答方式直接进行的,其交流性质非常明显。测谎的交流性质则相对隐晦。虽然被测人也可以通过对测试问题的回答来传达其意思表示,但是,测试人员对被测人内心意思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分析生理反应图谱实现的,即通过分析图谱了解被测人接受测试时的“所思、所想或所信”。⑩被测人愿意接受测谎,同意把自己接受测试时的心理状态通过图谱的形式呈现出来,与此同时,测试人员通过仪器获取其接受刺激时的生理反应图谱并予以解读,双方就顺利实现了信息的沟通或交流。因此,测谎过程具有交流的性质,测谎具有供述的一些特征。 然而,测谎与讯问虽然具有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测谎不属于讯问。(1)目的不同。虽然测试人员在测谎过程中一般会向被测人提问,被测人一般也要进行回答,但是,测试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取被测人的回答,而在于获得被测人回答问题时的生理反应。测试人员对被测人是否回答、如何回答并不关注。在有些测谎方法中,问题也并非以言语方式呈现,而是以图片、视频等来进行,被测人也无须回答问题。但讯问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口供。(2)实施主体不同。测谎的实施人员必须是具有测谎专门资质的专门人员,为保障测谎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测试人员不能是侦查、检察或审判人员。而讯问的主体只能是法定侦查、检察或审判人员。(3)实施程序规范不同。诉讼法对讯问规定了专门的讯问程序,而测谎却有其完全不同的诉讼程序和技术操作程序。(4)对结果的利用方式不同。讯问结果体现为书面讯问笔录或录音录像资料,双方的交流内容可以直接被普通人感知、理解;但被测人对提问的回答体现在生理反应图谱上,生理反应图谱是其内心意思的真实表现,但生理反应图谱代表的含义不能直接被普通人理解和感知,必须借助测试人员的专门知识进行评判才能被揭示。 (二)勘验(人身检查)说 勘验(人身检查)说认为,测谎的主要目的是获取被测人在回答问题时的生理反应,与验血、验尿相同,都是对身体的检查。(11)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勘验是指在侦查中凭借五官对物的状态进行辨认。(12)这里的“物”包括人之身体、处所及一切有体物或无体物。(13)而人身检查则分为人身搜查、勘验中的人身检查和鉴定中的人身检查。因此,当勘验的对象是人的身体时,被称为人身检查。(14)勘验(人身检查)说认为测谎是对身体的检查,故属于勘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勘验中对身体的检查是对身体表征和伤害状况的检查,(15)但测谎并不是对身体表征进行检测,而主要是对人的心理状态的检测。 在我国大陆,测谎显然也不属于勘验的范畴。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6条的规定,勘验是指侦查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进行的勘查。勘验针对的对象是场所、物品和尸体,而测谎是针对人身进行的。同时,我国大陆的勘验与人身检查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勘验的对象是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等“死”的事物,检查的对象是与案件有关的“活人”的身体。 那么,同样针对“活人”的测谎是否属于人身检查呢?答案是否定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0条的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绝检查,侦查人员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强制检查。”因此,在人身检查过程中可以实施采集样本行为,在必要时可以强制采样。根据第130条的规定可以发现,测谎与人身检查不同。(1)目的不同。测谎的目的是通过采集生理反应图谱来推断被测人的心理反应。人身检查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这里的“某些特征”是指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体表特征,如相貌、皮肤颜色等;“伤害情况”是指伤害的位置、程度、形态等;“生理状态”是指有无生理缺陷,包括各种生理机能是否完善。采集样本的最终目的在于为鉴定提供检材。(2)检查对象不同。人身检查的对象是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测谎的对象不仅仅限于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还包括证人等知情人员。(3)检查指标不同。测谎所测的生理反应主要是呼吸、血压、皮电等生理指标。人身检查主要靠视觉来直接查看人的体表特征、伤害情况或生理状态,也可以通过采集生物样本来进行。采集样本一般针对人体自然组成部分,包括但不限于血液、唾液、精液、尿液、粪便及体内其他分泌物、毛发、指甲、牙齿印模、指印、掌印、足印及身体任何其他部位类似的标记。(16)(4)能否强制进行不同。在犯罪嫌疑人拒绝的情况下,可以强制采集样本。但测谎不能采取强制方式进行。被测人自愿同意测谎是测谎取得正当性的前提,测谎的顺利实施也需要取得被测人的配合。强制实施测谎不仅侵犯被测人基本权利,也会影响测谎的准确性。 (三)鉴定说 鉴定说认为测谎属于鉴定。(17)在日本,鉴定说的代表人物是松尾浩也和三井诚等人。“测谎的实质是一种委托鉴定。”(18)“测谎在性质上应属于心理检查或鉴定。”(19)我国台湾地区持鉴定说的代表人物是黄朝义、陈运财等。“测谎并非在于要求被测人对质问的回答,而是记录被测人对质问所产生生理之反应,并予以分析判定,而以之为证据资料提出于法院。但测谎鉴定之实施,并非单纯如DNA鉴定、指纹比对等身体检查(鉴定),而仅属心理检查或鉴定。”(20)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认为,“刑事程序上之测谎,系对于人之内心之检查,具有侵害个人内心自由及意思活动之心理检查性质。”(21)我国大陆认为测谎结论属于鉴定结论的观点认为测谎属于鉴定:测谎结论是鉴定人关于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意见,与精神病鉴定结论具有相同的性质;测谎在鉴定的对象与方法上与传统的鉴定有所不同,但测谎与鉴定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测谎结论应归于鉴定结论的范畴。(22)鉴定说立足于测谎的最终目的,以最终作为证据的材料究竟为何来判断测谎的性质。应当说,这种分析路径是正确的。由于我国大陆的证据法律规范与台湾地区差别较大,分析测谎的法律性质必须立足于大陆法律体系。但我国大陆的鉴定说只是在论述测谎结论的证据种属时顺带提及对测谎属性的态度,并无论证。 三、测谎的鉴定属性 (一)解析测谎法律性质的路径 测谎的法律性质之所以难以界定,主要是因为测谎的过程比较独特。测谎的过程包括测前准备、测前谈话、主测试、分析图谱等阶段,这一系列过程的总和共同构成测谎的过程,缺一不可。(23)测前准备需要完成的工作包括了解案情及被测人的情况、拟订测试方案等,可以通过与案件承办人交谈、查阅案卷材料、实地察看现场等方式进行,还可以询问被害人、证人。测前谈话采用问答的方式进行,确认被测人是否适合接受测谎及接受测谎的自愿性、与被测人讨论测试题目、调试被测人的情绪,并为主测试做准备。在主测试过程中也多采用提问与回答的方式进行,测试人员依据事先编排好的顺序,依次把测试题目读出来,被测人做出是或否的回答。(24)通过对被测人提出问题、呈现刺激,激发被测人的呼吸、皮电、血压脉搏等生理反应,并用测谎仪记录下来,最终显现为生理反应图谱。在主测试结束之后,测谎人员对采集的图谱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测前准备时察看现场使测谎具有了一定的勘验性质;测前谈话和主测试中的提问和回答使测谎竞合了讯问的一部分特征;通过测谎仪采集被测人的生理反应图谱,使测谎具有了一定的勘验、人身检查及采集样本的特征;测试人员利用其专门知识对测谎图谱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性意见又使测谎具有了鉴定的特征。 要把握测谎的性质,首先必须明确,在测谎的这一系列过程中,哪个阶段对测谎的定性具有关键意义,哪个阶段只是发挥补充或铺垫作用。测谎是为了获取被测人对案件事实的认知、记忆或信息,并进一步判断被测人陈述的真伪。但是被测人储存在大脑里的这些信息,办案人员无从得知,只能通过测谎仪采集生理反应图谱来识别这些信息。一般认为,主测试操作过程的优劣决定了采集到的测试图谱的质量;而测前谈话对测试题目的编制至关重要,甚至被认为是比主测试更关键的环节。但无论如何,从测谎各个阶段的目的和实施方式可以看出,测前准备、测前谈话、主测试这三个过程都是围绕准确采集测试图谱而进行的。但测谎仪记录的被测人的生理反应图谱并不能自行发挥证明作用,其证明价值需要通过测试人员的分析意见才能被揭露。单纯的测试图谱,对办案人员没有意义。测谎最根本的是测试人员凭借其专门知识和技能做出的结论性意见,能够作为证据使用的也只是测试人员的分析意见。只有到了分析图谱阶段,即把整个测试过程的结果从专业的、晦涩的图谱最终转化为普通人可以了解、知悉的内容,才最终实现了测试的目的,即得出被测人是否具有案件相关认知或是否撒谎的结论。 因此,可以把测谎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取得测试图谱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对测试图谱的分析认定过程。第一个阶段通过提问与回答的方式,激发并记录被测人的生理反应,但是,被测人的回答并不作为证据使用,测谎仪记录的图谱也不作为证据使用。在第二个阶段中,测试人员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通过分析测谎所取得的图谱,对被测人是否具有与案件有关的认知、是否说谎得出结论性意见。只有这种结论性意见才可以作为法院判决依据,也是整个测谎过程中所获得的唯一可以被作为证明依据的部分。因此,第二个阶段才是测谎的关键阶段。测谎的性质取决于图谱分析阶段的性质。 (二)测谎鉴定属性之证成 测谎是否属于鉴定取决于测谎图谱分析阶段是否具有鉴定的性质。 1.司法鉴定的科学性与法律性 鉴定是指鉴定人接受指派或者委托,利用科学技术方法,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或断定的一种活动。与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中的社会鉴定相对应,出现在诉讼过程中的鉴定被称为司法鉴定。(25)根据2005年颁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第1条:“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司法鉴定具有科学性和法律性的双重属性。司法鉴定是一种以科学性为基础,以法律性为保障的认识活动。(26)司法鉴定的科学性是指鉴定是由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运用科学知识、专门经验和技能,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判断的活动;鉴定结果直接涉及科学角度的推理、概括而非法律性的评价。鉴定的法律性是指鉴定是为了向法庭提供证据,是依照法定程序所作的检验、鉴别和判断。(27)鉴定的法律性要求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成立和产生必须遵循国家法律或法规;司法鉴定的启动和鉴定程序必须依法进行;鉴定项目采用新的鉴定方法、新的鉴定标准必须经过法律或法庭的认可或同意。 我国否认测谎结论属于鉴定结论的理由包括:测谎结论不属于鉴定结论,因为测谎只是运用机械手段对涉案人心态进行测试,并没有运用专门知识;专门性问题必须经过法律确认,测谎的对象未经法律认可,不属于专门性问题;测谎结论不可靠。(28)否定说认为测谎没有运用专门知识、测谎结论不可靠,测谎对象不属于专门性问题,从而否定了测谎的科学性和法律性。由于鉴定的基本属性正是科学性和法律性,因此可以推知,否定说认为测谎不属于鉴定。本文认为,测谎需要运用专门知识,测谎技术具有有效性和可靠性,具备科学性;测谎的对象属于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具有法律性。测谎属于鉴定。 2.对测谎科学性的证明 鉴定的科学性要求鉴定人具有专门知识、鉴定的过程需要运用科学知识、经验和技能,而且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的鉴别判断有助于查明案情。鉴定人的意见有助于查明案情是对鉴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要求。鉴定的可靠性是指鉴定所依据的理论、方法、数据等的可重复性,在相同条件下反复进行实践能产生相同的结果。鉴定的有效性要求鉴定能够实现鉴定的目的。 测谎技术在历经了100多年的发展后,已经发展出成熟的测试方法,如准绳问题测试法、紧张峰测试法、犯罪情景测试法等。正确运用这些方法需要掌握心理学、生理学、计算机学、侦查学等多门学科的专门知识。只有通过相关的培训,具备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人员才能取得测谎人员从业资格证。因此,测谎人员需要具备专门知识、测谎过程需要运用科学知识、经验和技能是不言自明的。使测谎屡受质疑的是其科学可靠性,包括测谎原理的可靠性和测谎结论的可靠性。 (1)测谎原理的可靠性 测谎的基本原理是,刺激会引发心理反应,心理反应必然引起生理反应;不同问题对同一个被测人引起的刺激程度是不同的;同一个问题对不同被测人产生的刺激程度也是不同的。通过比较被测人对不同问题的反应强度,就可以判断被测人是否撒谎或与案件的关联。历史上先后有一些理论对测谎原理进行了解释,如恐惧理论、惩罚理论、冲突理论、心理定势理论等,但它们都未能解决撒谎与情绪反应的一一对应问题,致使测谎原理的可靠性受到怀疑。但是,随着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朝向反应理论对测谎原理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使测谎原理的科学性得以确立。根据朝向反应理论,对有罪或知情的被测人而言,他们知道正在调查的事件,对相关问题有认知,也知道如果在相关问题上撒谎可能导致惩罚等后果,因此,相关问题对被测人形成一种新异刺激,这种刺激会产生强烈的生理反应;虽然被测人对准绳问题也会产生生理反应,但是,反应强度不如相关问题。同理,对于无辜或不知情被测人而言,准绳问题形成一个新异刺激,会产生强烈生理反应。比较被测人在相关问题和准绳问题上的反应强度就可以判断其是否有认知或者是否撒谎。 (2)测谎方法的可靠性 衡量测谎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最主要指标是信度和效度。对测谎信度的研究一般是通过内部一致性,即对不同相关问题的反应的一致性来进行的;也可能通过重测信度,即测试人员用相同方法对同一测试图谱进行二次评定。效度,也被称为有效性,是指测试在多大程度上测量到了想要测试的东西。它是表征测试控制误差的能力的数值,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用途而言的。(29)在对测谎科学性的评价中,主要关注校标效度,即一次测试结果的准确度。美国测谎协会在Polygraph杂志发表了《测谎的信度与效度》一文,公布了其对1980年以来发表于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以色列等国家的50多个科学杂志上的80篇研究报告的综合研究。这些研究报告包括对6380次测谎的研究。其中,11篇研究报告对1609组测谎图谱进行独立分析,并由独立证据验证结果,确定测谎的平均信度为92%;16篇研究报告独立分析实验室模拟测谎案件测谎图谱共计810组,得到的平均信度是81%。(30)测谎准确率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测谎准确率的综合评价,另一种是不同的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对不同的测试技术的分别研究。目前有关测谎准确性的最权威的一次评估是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于2003年作出的评估报告。该委员会在全面审查8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历时19个月,得出结论认为,测谎的综合准确率在81%~91%之间。(31)2011年年底,美国测谎协会(APA)完成了一次有关测谎效度的综合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针对具体事件调查的单一主题测谎总体准确率为89%(可靠区间为83%~95%),无结论率为11%。针对多主题测谎的总体准确率为85%(可靠区间为77%~93%),无结论率为13%。(32)日本、加拿大、罗马尼亚、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总体研究表明,测谎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足以满足作为证据的需要。 因此,测谎过程不仅运用到了专门的科学技术,而且这种技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能够得到保障,能够满足其作为鉴定的科学性要求。 3.对测谎法律性的认识 作为鉴定属性的法律性强调的是,鉴定作为一种在诉讼中进行的科学活动,与单纯的科学活动不同,其目的是为法庭提供证据,弥补法官知识之不足;鉴定的实施要遵守法定程序;鉴定的对象必须是某些专门性问题。其中,“鉴定对象必须是某些专门性问题”是对鉴定范围的限制。由于法律并未对“专门性问题”做进一步规定,理论界对如何理解“专门性问题”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有观点认为,司法鉴定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必须已经在相关的司法鉴定立法里有明确的规定。(33)专门性问题必须是经过法律确认的,对未经认可的专门性问题做出的意见不能作为证据。(34)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进一步认为,我国目前暂时采用部门确认的方式,即将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门规章中限定的鉴定范围,视为法律确认的鉴定对象。(35) 本文认为,鉴定对象的确立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待鉴定对象是否是解决案件所必需的事实。如果待鉴定对象与案件有关联,案件事实的查清以待鉴定对象的查明为前提,则进入第二步的判断。二是该对象是否必须依靠专门知识才能查明。如果该对象必须依靠法官并不具备的专门知识才能查清,该对象就属于鉴定对象。至于该对象是否必须是法律确认过的事实,本文认为,专门性问题无须法律确认,我国也并不存在对专门性问题的所谓的法律确认。 (1)从鉴定的起源和发展来看 “鉴定”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1887年由黄遵宪翻译的《日本国志》。在我国法律中正式使用“鉴定”一词的是1907年颁布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该章程第74条规定:“凡诉讼上有必须鉴定,始能得其事实之真相者,用鉴定人。”(36)该章程确立的是全面鉴定制,即只要需要“一定学识经验及技能”“始能得其事实之真相者”均必须进行鉴定,并未要求鉴定对象由法律规定。 (2)从鉴定的功能来说 鉴定主要是弥补法官能力之不足,揭示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的证据价值。诉讼中涉及大量的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法官无法凭其通常知识解决的问题,这些专门性问题只要与法官的常识、经验、知识相去甚远就属于需要鉴定的对象,法律不应当也不可能规定专门性问题的范围。据有关专家统计,司法鉴定至少包括28类,1000多个学科。(37)如果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问题才可以进行鉴定,就可能导致有些案件的专门性问题无法查明和证明。 4.从法律规定来看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2条规定,国家对从事四类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具体包括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该《决定》第9条规定,在诉讼中,对上述鉴定事项发生争议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列入鉴定人名册的鉴定人进行鉴定。从这两条规定的内容来看,法律并没有说只有属于四类鉴定业务的才可以进行鉴定,只是规定,如果属于这四类鉴定业务,就必须委托列入鉴定人名册的鉴定人进行鉴定。第2条只是规定了需要进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业务范围,虽然被列举的业务当然属于司法鉴定业务,但并不是说司法鉴定业务只有这四类。这也可以从作为《决定》的重要制定依据的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问题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得到证明。该报告指出,“作为司法鉴定进行管理的鉴定范围不宜太宽。相关法律已明确规定有关主管部门做出的技术鉴定,不应再列入司法鉴定的范围。司法鉴定主要是法医学鉴定、精神病学鉴定、司法化学鉴定、司法物理学鉴定等相关法律、法规未作规定,且与审判紧密联系的学科和与之相关联的边缘问题。相关法律、法规已经规范的内容,不应再列为司法鉴定的范围。”因此,作为鉴定对象的“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既包括《决定》所规定的四类专业,也包括由行业主管机关规范管理的专业。 此外,《决定》第2条第(4)项授权,“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根据诉讼需要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公安部于同年颁布了《公安机关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于2006年颁布了《人民检察院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二者都明确把测谎(心理测试)纳入必须登记管理的鉴定业务范围。虽然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都不属于《决定》第2条第(4)项授权“确定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的“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测谎鉴定被纳入司法鉴定登记管理业务只是时间问题。而且,测谎被纳入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登记管理的鉴定业务范围也使上述反对测谎属于“专门性问题”的理由不再成立,因为上述观点正是以是否被纳入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门规章的管理范围作为判断标准的。 测谎的目的是查明被测人是否具有与案件有关的认知或者是否撒谎,这个问题的解决对案件事实的查明至关重要。虽然一般情况下,被告人对案件的认知或者是否撒谎属于法官依据常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这些信息隐藏于被测人的内心,而且无法通过证据、通过观察等途径来解决的时候,如何把这些隐藏于被测人内心的信息,借助一定的仪器显现出来并加以分析判断,就需要依靠专门技术的帮助。因此,测谎的事项并非法官依靠常识和理性所能解决,测谎的对象属于专门性问题。 因此,测试人员对测谎图谱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是测试人员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的分析、判断,符合鉴定的科学性和法律性要求,属于鉴定。在评图之前的一系列测谎过程,包括测前谈话、编制测试题目、实施测试、采集图谱,都是为评图做准备的,可以看成是为鉴定做准备的工作,是为鉴定提供样本的行为,是鉴定的先前行为,可以被后面的鉴定所吸收。因此,测谎属于鉴定,要受鉴定规则的规制。 在测谎的整个过程中,测试人员对图谱的分析判断阶段对测谎目的的实现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可以依据该阶段的鉴定属性把测谎定性为鉴定。然而,测谎前面的几个阶段对测谎的定性并非毫无作为。测谎前面几个阶段的行为具有基本权干预性质,使测谎的鉴定属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测谎干预了被测人身体自由权。测试人员把与案件相关的问题编排成相关问题进行提问,强制被测人回忆其实施或经历过的案件,致使被测人出现显著生理反应,并呈现于测试图谱,干扰了被测人自由支配自己内在思维活动、使其免受骚扰的自由。其次,测谎侵犯了被测人的隐私权。测谎测试的问题属于隐私,而且测谎涉及的隐私在法律的保障范围之内,未经同意测谎而强行探测是对他内心隐私的公开揭示,侵犯了被测人的隐私权。最后,无论是测前谈话还是正式测试,测谎均具有交流性质。当测谎结论不利于被测人时,可能使被测人陷于自我归罪,测谎就构成了对反对自我归罪特权的干预。因此,测谎限制或剥夺被测人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和反对自我归罪特权,属于基本权干预行为。虽然测谎的干预性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予以正当化,但正是由于测谎的这种基本权干预性质,使测谎与传统的鉴定相比,有一定的独特性,需要经被测人同意才可以实施。只有经被测人同意实施的测谎才具有正当性,而且,也只有经被测人同意实施的测谎才能保障测试的准确性。由于测谎的这种干预性,要求我们在设置测谎程序规范时必须努力保障被测人的同意权。 ①“Polygraph Test”在传入我国之初被翻译为“测谎”,并获得了普遍的接受。时至今日,我国研究人员对这一技术的称谓出现了较大分歧,出现了“心理测试”(犯罪心理测试、心理生理测试、司法心理生理测试)、“犯罪记忆检测”、“测谎”并存的局面。2004年,“Polygraph Test”技术被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正式称为心理测试技术。本文认为,“测谎”称谓相比其他称谓更合适。“测谎”的称谓源于对“Polygraph Test”的翻译,从“Polygraph Test”的母语国对该词汇的解释以及“Polygraph Test”的起源和后来的运用情况来看,“Polygraph Test”最恰当的翻译应当是“测谎”;“测谎”这一称谓完全可以涵括测谎和测真的双重作用,能够正确描述该技术的功能;“测谎”称谓已被公众广泛接受。其他称谓或者犯了种属错误或者缺乏包容性,而且不为公众所熟悉,难以代替“测谎”称谓。故本文仍采用“测谎”称谓。 ②1998年2月20日,杭州市萧山建设银行31.5万元港币被盗。经勘查发现,本案没有确定的作案现场,没有确定的被盗时间,也没有很突出的重点嫌疑人。侦查人员按照接触该笔现金的可能性大小将该行所有人员分成三个层次,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地问话,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后经测谎,银行押运员潭浩被认定为有重大嫌疑。在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搜索测试之后,初步认定了赃款去向。然后根据测谎提供的线索,刑警从其家中搜出了该笔外币存折。在看到存折之后,他做了认罪供述。参见武伯欣、张泽民:《心证》,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页。 ③1998年4月20日晚,昆明市公安局民警王晓湘(女)与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民警王俊波(男)双双被人枪杀,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成为重大嫌疑人。经多次讯问,杜培武仍否认杀人。办案部门遂对其实施了测谎。测谎结论为杜培武否认杀人的供述是谎言。办案部门据此对其实施刑讯逼供并得到了有罪供述。杜培武一审被判死刑,后二审改为死缓。两年后,真凶被抓获,杜培武冤情才得以洗刷。 ④周正龙案件中,鉴于周正龙的口供与庭审表述前后矛盾,其辩护律师提出为周正龙测谎。法庭认为,目前在中国测谎结果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庭审中的其他证言证词能够相互印证,没有测谎的必要。程成:《周正龙案二审,辩护律师提出为周测谎被法庭拒绝》,载http://www.chinanews.com/sh/news/2008/11-17/1452565.shtml。 ⑤刘某于2009年12月底入职深圳山木培训,在工作近5个月后,提出辞职。2010年5月3日晚,宋山木将刘某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挽留刘某,但刘某不同意继续留下工作。当晚8时许,宋山木开车载着刘某来到罗湖区太白路北松泉公寓某房间,继续挽留刘某,并说自己很喜欢她,刘某再次拒绝。宋山木遂对刘某进行威胁、恐吓,强令其脱下衣服,随后强行与其发生了性关系。在该案中,宋山木一方曾向检察院提交测谎申请但被拒绝。检察院认为,测谎主要在侦查工作中使用。在进入审判阶段后,证据链已经完整,就无须再行测谎。在审判阶段,宋山木两次向法庭申请测谎,但都被拒绝。法庭认为,通过测谎得出的结论不能作为法定证据。然而,辩方及一些测谎专家都认为,宋山木不认罪,被害人的陈述是孤证,两者之间相互矛盾,案件的有罪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在没有其他法定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使用测谎的方法不失为审查、判断案件既有证据的必要选择。程伟:《宋山木测谎要求未被法院采纳》,载《羊城晚报》2011年7月1日;端子:《法院为什么拒绝宋山木的测谎申请》,载《大河报》2011年7月14日。 ⑥由于刑事诉讼中的讯问和鉴定与民事诉讼中的询问和鉴定具有同质性。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只讨论刑事诉讼中的讯问和鉴定。 ⑦[日]田宫裕:《刑事诉讼法》,有裴阁1996年版,第341页。 ⑧蔡墩铭:《测谎鉴定之实施》,载《月旦法学杂志》第49期。 ⑨邱俊智、林故廷:《测谎理论之应用及其限制》,载《刑事科学》第44期。 ⑩王兆鹏:《辩护权与诘问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页。 (11)林建中:《隐私权概念之再思考——关于概念范围、定义及权利形成方法》,台湾大学1999年硕士论文,第26页。 (12)[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张凌、于秀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13)蔡墩铭:《刑事诉讼法论》,五南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14)[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张凌、于秀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76页。 (15)同上,第76页。 (16)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保障——中国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 (17)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鉴定作为一种法定证据方法,包括对身体的鉴定和对心理的检查。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336页。 (18)[日]松尾浩也:《刑事诉讼法》(上卷),丁相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19)三井诚:《测谎检查》,载《法学教室》第209期。 (20)黄朝义:《论科学侦查中之鉴定及其证据问题》,载《法学丛刊》第170期。 (21)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6年度台上字第2254号判决。 (22)赞同测谎结论属于鉴定结论的观点参见宋英辉:《关于测谎证据有关问题的探讨》,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何家弘:《测谎结论与证据的“有限采用规则”》,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张泽涛:《美国测谎制度的发展过程对我国的启示》,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赵杰:《测谎结论的证据适用》,载《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许志:《测谎结论的证据法地位》,载《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3期;罗永红:《论测谎结论的证据价值》,载《理论与改革》2006年第1期。 (23)很多测试人员在主测试之后还会与被测人进行测后谈话。 (24)在偶尔进行的缄默测试中被测人无须回答问题。 (25)汪建成、吴江:《司法鉴定基本理论之再检讨》,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5期。 (26)卞建林、郭志媛:《鉴定机构性质辨析》,载《中国司法鉴定》2007年第4期。 (27)霍宪丹:《司法鉴定概念试析》,载《中国司法鉴定》2001年第8期。 (28)代表性的观点如向建国:《真实的谎言——测谎结果不宜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之思辨》,载《犯罪研究》2004年第2期。 (29)车文博主编:《当代西方心理学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页。 (30)陈鸿斌:《测谎证据能力之研究》,“司法院司法行政厅”1996年版,第9页。 (31)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The Polygraph and Lie Detection,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p.190,2003. (32)Meta-Analytic Survey of Criterion Accuracy of Validated Polygraph Techniques Report(2010-2011),http://www.polygraph.org/section/validated-polygraph-techniques/executive-summary-metaanalytic-survey-criterion-accuracy-val. (33)史杏娟、王晓红:《对司法鉴定概念的再思考》,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34)持这类观点的如张方、刘蕾:《试论鉴定对象之法律确认》,载《证据学论坛》(第7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页。邹明理:《论鉴定结论及其属性》,载《证据学论坛》(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35)陈力铭、余沁洋编著:《司法鉴定学》,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36)《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907年12月4日),载西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3辑),1985年版,第11~28页。 (37)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问题的调研报告》,载《中国人大》2002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