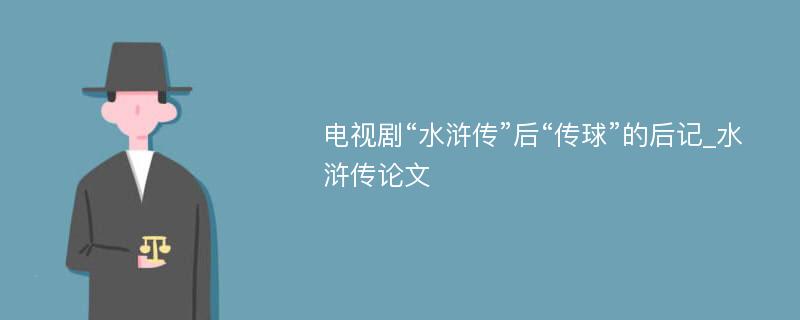
写在“通行证”上的附言——电视连续剧《水浒传》观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传论文,附言论文,电视连续剧论文,写在论文,通行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苦头,到头来还是吃力不讨好,甚至落得个千夫所指。我猜想,致力于把文学经典搬上银幕或荧屏的艺术家们,耳边会时常响起一个声音: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这声音未必会使他们止步不前,却无形中增加了他们工作的难度,因为他们的命运提在广大百姓的手里,而广大百姓对他们的提醒和苛求有着充分的道理,谁让他们去碰那些妇孺皆知并深入人心的经典呢?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算是过了这一关了,因为从媒体呈示的反馈看,该片的播映,受到了相当的欢迎,甚至在社会上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水浒热》;收视率的统计,主题歌的传唱,有关书籍的畅销,以及创作人员知名度的提高,都可作证。而且我想,无锡“水浒城”的门票一定较以往好卖,宋江故里及梁山旧址的游客激增,也未可知。这是题外话,打住。
我自己作为广大百姓的一员,与大多数观众的态度基本一致,也就是认为《水浒传》的改编总体上是成功的,否则我不会守在电视机旁一集一集地从头看到尾,就四大古典名著电视剧对我的吸引力而言,这还是头一回。这说明,此次改编,没有触动我那根捍卫经典的神经,而以我对古典名著的钟爱,这根神经是十分敏感的。但这也不是说,电视剧《水浒传》对经典的处理,就没有令人遗憾的地方。平心而论,如果我手里攥有一张对经典改编把关的通行证,我会愉快地把它发放给《水浒传》剧组的艺术家们,但也会在通行证上写下几句附言,说说我对这次改编经典之得失的感受。因为职业和爱好的关系,我大致还算得上一名经典的守望者,也想看到文学经典在“改头换面”后,仍保持甚至增强其原有的魅力。以下谈的,就算是写在“通行证”上的附言吧。
就从最显眼的地方说起。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影视是视觉艺术;把古典名著改编成电视剧,也就是把原来的文字形象转换成视觉形象。对《水浒传》来说,这意味着,梁山好汉们一个个从书中走出来,跳上荧屏,成为活脱脱的人。这种转换,需要编剧、导演、摄像、美工等一干人的力量,但最终要落在演员身上。也就是说,观众看到的,是演员和表演,而演员塑造的形象与书中的原型在多大程度上吻合,是观众判定改编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我在这里说“吻合”,决无贬低演员创造力的意思,这乃是改编经典的特性。如果完全是创作,演员的表演或许会有较大的空间,但既然是改编,就不能够任意发挥,否则何必挂靠经典而不自立门户呢?更何况经典的艺术形象在广大百姓心目中根深蒂固,轻易改动,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甚至导致改编的失败。所以说,演员的表演就是小说改编为电视剧后能否为广大观众接受的关键,而视觉形象与原有的文字形象能否吻合,又是演员表演成败与否的关键。我看到《水浒》播出后一次观众与演员的见面会上,主持人问观众某某演员象不象林冲,某某演员象不象李逵;这“象”与“不象”,就是经典的改编是否得到通过的标志之一。当然,这“象”与“不象”不能仅仅理解为长相或派头的相似或相差,而应该体现在气质、性格、神志等更为深刻的方面。用中国古典美学的标准看,“象”不仅仅是形似,而且应该是神似。这就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水浒传》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有具体的描写,在中国老百姓的脑子里也有大致的模样,又经历代画家的描绘,大致上有个“原型”,而演员的任务是把这个“原型”用形体、动作、言语、神情展现出来。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弄得不好,就会走样;即便不走样,也会苍白无力,让人觉得倒不如去看小说。这样的例子从前不是没有过,对于《水浒传》来说,这也是一个首先需要重视的问题。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在这一点上没有失望,甚至可以说有些振奋;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看到了一个活脱脱的宋江。
说老实话,在观剧之先,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宋江这个形象。一来因为他是这部英雄传奇中最不具备英雄本色的人物之一,二来因为他是这部连环式结构(故事接故事)的小说中唯一贯串全书的主人公;加之形貌平常,性格怯懦,在梁山众好汉的反衬下明显地缺乏力度,演起来会相当困难。然而剧中的宋江却活灵活现,神情毕肖(参照小说而言),着实令我惊喜。这不能不归功于李雪健的表演,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他把宋江这个人物吃透了。因而演起来从容自如,游刃有余,说得夸张一点,是精彩纷呈,大到慷慨陈词、装疯卖傻,细到举手投足、一招一式,无不让人心悦诚服,暗地里说:嘿,这就是宋江。我斗胆说一句,《水浒传》的戏,有一半是靠“宋江”撑住的。
俗话道,外行看热门,内行看门道。我对表演艺术是大大的外行,故不敢对演员的工作说三道四。以上谈的,大抵只是一个普通观众对于电视剧再现经典人物形象的基本要求,而我相信这种要求在大多数观众心理中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应当为电视剧艺术家尤其是直接演示经典人物形象的演员们所重视,不然的话,拍出来的戏给谁看呢?不用说,《水浒传》剧组在这个问题上,是下了大力气的。这不仅体现在演员的表演,也可以从许多有关拍摄的报导中看出,这种敬业精神,当是改编经典的成功之道;而以这样的敬业精神去塑造经典人物形象,也会得到老百姓的热情回报。
但在这里我要强调的不仅仅是敬业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整个《水浒传》的拍摄之中,是不用怀疑的。以演员而论,谁要是偷工减料甚至稍有懈怠,恐怕早就被开了出去。然而从剧中大大小小的人物形象看,虽然大都立了起来,但在艺术表现力上还是略有等差,有的甚至比原著中的形象有所倒退。这种艺术表现力的差距倒不一定是因为演员的演技不好,更重要的原因是艺术修养的高低和文化底蕴的厚薄。由此而来的问题在现代或创作题材剧里或许不太明显,但对古代剧尤其是经典改编剧来说,就十分打眼了。因为古代经典的美学蕴涵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作品;又由于时间的跨度,古代经典的艺术形象有着深广的历史积淀,渗透着特定时代的趣味、情调和精神。不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转换成视觉艺术的人物形象终究显得单薄、肤浅,最不成器者,还会流为一个被抽空了的符号或名字。而这些人物在小说中或虚或实地是被加以不同程度的描写的,按理说,成为视觉形象后应该更加光彩照人,但给人的感觉却是神气萧索。我仔细琢磨,问题应当出在演员的艺术修养和文化底蕴上;也就是说,没有或欠缺一定的修养和底蕴,是很难为人物形象传神写照的。究竟怎样去传神写照?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定律,但最起码细节是应该照顾到的。不妨举个正面的例子,即宋江的步伐。宋江出场时,是迈着小碎步,那时候他是郓城县的刀笔小吏,这种步伐很能体现他的身分和个性。待上梁山坐了头把交椅后,这种步子渐渐少了起来。以后受招安成了朝庭命官,宋江的步伐愈发舒缓了。小说里并没有特意去写宋江的步子,但成为视觉形象后,这类细节却不能不顾及到,因为观众们认识宋江,就是从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特征开始的。对这个名唤宋江的人物,人们凭什么断定他是宋江而不是晁盖或其他角色,是宋代的宋江而不是今天的宋江,是小说《水浒传》里的宋江而不是随便什么人臆造的宋江呢?除了剧情的交代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不经意的一招一式和举手投足了。“于细微处见精神”,这虽是一句套话,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却是至理名言;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没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文化底蕴,恐怕连想都想不到。李雪健饰宋江能有如此传神妙笔,一定得力于对中国古典艺术的谙熟(很可能深通中国古典戏曲艺术),以及对传统文化及风俗人情的深思熟虑。这恰恰是时下年轻一代演员所缺乏的。然而对待《水浒传》这样的古代经典,没有这方面的功力,要想把人物演活,是会遇到许多麻烦的。在电视剧《水浒传》里,就人物形象的表现而论,令人拍案叫绝之处在此;让我若有所失之处也每每在此。推开来看,其他几部古典小说改编的得失,也或多或少地与此相关。最典型的要数《红楼梦》。大观园里的少爷小姐,让一群在现代都市里长大的少男少女去演,实在是难为了他(她)们,尽管他(她)们为拍戏而认真读过几遍《红楼梦》,但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大家族里的人情世故和文化氛围,哪里是读几遍书就能弄明白的?因而创造出的角色大都成了剪纸。我也算看了二十余集,可十二金钗是什么模样,脑子里空空如也,更不要说其他的小姐、丫环了。当然,不能苛求所有的年轻演员熟识古典文化及艺术,但对于经典的改编来说,具备一些这方面的修养,是有必要的,因为毕竟我们面对的是文学经典,要为古代文学家和今天的观众负责。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把电视剧《水浒传》在人物形象上的特点,具体说是演员的艺术修养和文化底蕴带来的得失,当作改编经典的一条重要经验,以期今后同类工作有所借鉴。
再要说说改编的问题。这个“改编”,有着特定的涵义,不仅仅指把文学作品改成影视艺术而且指对原作情节、结构、人物、思想等等所做的改动。依我一贯的看法,是不赞成影视作品对原作作过多的改动的。原因有二,一是,经典自有其永恒的价值和魅力,改编者的任务应当是用另一种形式展示这种价值和魅力,而不是用另一种价值和魅力取而代之,更何况,又有哪一位改编者敢夸下海口,他的艺术眼光和表现手法超过了前辈大师呢?二是改动过多,势必要“冒犯”老百姓们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改得好则罢,改得不好,就难免画虎不成反类犬,惹得大批人士群起而攻之,担得个“犯众”的罪名。我个人自命为经典的守望者,头一个就会跳出来说“不”。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种担心,那就是使改编成为“改变”,即借经典之大名,贩一己之私货。说得好听一点,是再创造;说得难听一点,是拉大旗,作虎皮了。这样的改编自可以另起炉灶,又何必强与经典拉扯到一块呢?其结果是既埋没了改编者的才华(如果有的话),又落得个欺世盗名的坏口碑。说来说去,无非是要表明,改编经典,一定要小心从事,若非事出有因并胸有成竹,最好不要轻易在“太岁”头上动土。
但话又说回来,改编经典又不可能不对原作进行相当的改动。首先一条,从小说到影视作品的文学脚本,就必须经过全面的改写,因为文学与影视是不同类型的艺术,小说作品断断不可以直接用来拍戏,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除去这一条,改动经典还有其他的理由,比如原作的某些思想与当今意识形态相悖,某些文字描写无法用视觉形象表现,某些情节过于枝蔓而不利于“观”赏,某些人物的言行举止过于粗鄙而在今天看来有碍视听,等等。总之,改变经典,既要考虑到不同艺术类型的差异,又要顾及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改变者对原著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改动,当是情理中的事情。但问题在于,这种改动依据了怎样的美学原则,有没有损害经典原有的价值,还有,是否通过改动原作而真正发挥出了影视艺术的特长。以这些标准衡量,电视剧《水浒传》对小说的改动虽有一定的幅度,却基本上在情理之中;当然,不尽妥当的地方也有一些。
从结构上看,电视剧对小说改动最大的当在后五十回,除了保留讨方腊一段情节,其余破辽、征田虎、王庆等等统统删去。这是大手术,而这个手术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小说《水浒传》的后五十回是艺术性较差的一部分,除去翻来复去的冲锋陷阵,布兵斗法,几乎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而主要人物的事迹和性格待七十一回忠义堂排坐次后,也再没有什么发展。这种前后的不协调,很早就有人发现。想当年金人瑞腰斩《水浒》,将七十一回以后的部分一脚踢开,从艺术的角度看,是明智之举。而七十回本《水浒》的广泛流传也证明了这一点。电视剧主要取材于前半部分而改写后半部分,当有着原作艺术上的自身根据,也合乎自古以来文人及民众的欣赏口味。
值得探讨的是电视剧的通体设计,这关系到了整个作品的立意。电视剧在后半部分借讨方腊众将士阵亡以及佞臣陷害使梁山大业土崩瓦解而营造出一种悲剧气氛,从而使全剧有了一个凝重而严肃的主题,而且显示出一种关于人和生命的价值观。这应该说是对原作的思想意义作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较大的改动。从以当代人的思想意识以及电视剧应有的社会效益看,这种改动是可取的;而用马列文论的术语说,它体现出一种“历史和美学”的观念。道理在于,任何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因而不可能不融入当今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趣味。在中国古代,象《水浒传》这样的白话小说属于俗文学,它的前身是说书艺术。说书艺人为了满足市民(这是说书艺术的主要听众)的口味,难免往作品里掺杂一些今天看来是庸俗或落后的东西。就《水浒传》而言,它的核心思想当然是一个“义字”,但伴随这个“义”字出现的,是功名利禄、杀人放火等等不对头的思想意识。这些东西在古代尤其在市民阶层中常常是令人羡慕的,但在今天再去加以宣扬,显然不合时宜。即便是仍没有失去价值意义的“义”,如果不加以清理而简单地去美化,也与当今的伦理道德不容,稍不留神,就会成为封建余毒。电视剧是一种大众艺术,它不能不考虑到社会效果。退一步讲,即便为自身的思想性、艺术性着想,也应该对原著的立意及种种思想观念有所取舍;在这个基础上作一些加工、提炼,也是可行的。电视剧《水浒传》通过对小说的剪裁、深化,立定一种悲剧的基调;又通过前后对比强化全剧的悲剧效果,并把悲剧的原因归结到社会、历史以及人性,这样的改动当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但这种改动所产生的效应并不仅限于立意,而波及到了整个作品。对于改编经典来说,任何改动,哪怕是极其细微的动作,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电视剧《水浒传》将原著的立意升了一格,这就必然导致其他方面的变化,受影响最大的则是人物。从剧中人物形象塑造看,这种改动既有助益,也有闪失。
受益最大的无疑是宋江。宋江这个人物,向来不受人喜欢,有人称之为“假道学,真强盗”,(怀林《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这当是出于一种道德评价。但从艺术的角度看,宋江也不是《水浒》人物中写得最好的。历代评论家赞口不绝的,是对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个性鲜明,绘声绘色的描写,而宋江虽位居一百单八将之首,又是全书唯一贯穿始终的人物,但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他的位置也只能算是个中上,其美学内涵尚不能估价太高。可是当电视剧确定悲剧为基调后,这个人物形象发生了深刻变化,还是原来那些行为及经历,其内容眼见得就丰富得多了。尤其是后半部分,在小说里,宋江只是一个领军的统帅,性格和神情渐渐地平板、单调起来,几同于泥人木偶。而在电视剧里,这一部分却是宋江性格发展的高潮,他被推到了矛盾的中心,成了梁山英雄悲剧命运的焦点,从而有了十分复杂的内心冲突和微妙的情感变化。这时候,任何一个人物都不如宋江重要,而所有的重头戏几乎集于宋江一身,每一场戏都是沉甸甸的,都把宋江的性格深化一层。最终,电视剧《水浒传》的意义也就包蕴在宋江的性格和命运之中,而宋江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全剧最复杂、最富有审美意蕴的艺术形象了,尽管他的所做所为依然得不到大多数观众的同情。前面说过李雪健微妙微肖的表演,这有个前提,就是宋江这个人物要重新定位。如果李雪健饰演的只是小说中那个逢人便拜,见人便哭的宋江,他的本事再高,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有相当的局限;而当宋江因电视剧的悲剧基调有了更加复杂的性格之后,他对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和表现才有了更大的施展余地。由此可见,同是一个人物形象,电视剧里的宋江较之小说里的那个宋江在性格、思想及艺术表现上都扩充了许多。而且我有这种预感,李雪健演的宋江会和施耐庵写的宋江一样作为经典形象流传下去,进入电视剧艺术的名人堂。这种殊荣,不是电视剧《水浒传》里每个人物都享有的,虽然他们都以经典的文学形象为蓝本。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改编者对电视剧的立意做了较大的调整。当然也有的人物因这种调整而受损,凭我的感受,受损最大的是李逵。
李逵是梁山好汉中最受人喜爱的人物之一,在艺术描写上也出神入化,令人叫绝。他的性格的妙处,就在于一种几近于极致的单纯、爽直。金人瑞评价说:“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就说出了这位莽汉那极为可爱的风神,连他的杀人放火,做“恶”多端都丝毫不令人反感,反而凑成了他一片天真浪漫之情。象这样的人物,在电视剧中索性让他尽显本色,而不要强加一些观念性的东西,否则适得其反,象是往他那晶莹透亮的个性里掺了几粒沙了。然而电视剧里的李逵,其性格的张力远不如小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身“恶”的——也可以说是顽皮的——东西都被抹去了,而这些东西是极能体现他的个性的,甚至较那些善的——或者说是庄重的——东西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说他天性爱杀人,杀得兴起,连官军和百姓都不分,只顾抡起板斧剁瓜似地砍去。这种描写,让人看了并不觉得毛骨悚然,倒觉得忍俊不禁,心想李铁牛真跟个大孩子似的。而此类情节在电视剧里被删得一干二净。当然我指出这一点并不是想看李逵杀人取乐,也不是说电视剧就一定要把李逵滥杀无辜的描写具象化,而是觉着这种与人物性情深有关系的细节完全舍弃不免可惜,至少是可以虚写一笔的。看来改编者是抱着梁山好汉当善恶分明的念头,一心想使黑旋风“改邪归正”,孰知这样做反倒使人物呆板起来。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李逵闯进寿张县衙,当一回县官,升堂问讯那场戏。小说里是写李逵为过把判官瘾,硬让两个牢子假装诉讼,两个牢子被逼无奈,只好一个告被打,一个告挨骂,李逵偏偏把打人者当作好汉放走,把挨打者枷起来示众,理由是光会挨打,“没长进”。这是李逵的恶作剧,也是描写李逵性格出人意表而又妙趣横生的一笔。但在电视剧里,这场戏却被改成了李逵开堂公审,为百姓主持公道。这种改动,殊觉弄巧成拙。如此一改,李逵的思想境界是高了一分,而铁牛的性格魅力却又减了一分。类似的删改,在其他人物身上也能看到,比如武松智拿孙二娘,明明是说了许多“风话”,连擒拿的动作都有些不堪,可电视剧里的武松却始终堂堂正正,神情肃然。这也是为了体现英雄豪杰的大义凛然,却也同样是以减损性格描写的力度为代价的。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突出好汉的本色,而又把好汉与正义扣得太紧。若从电视剧的通体构思看,则又跟立意的改动有关。既然把故事变成悲剧,就得使各个环节都用来改化悲剧效果。以人物形象而论,愈是正义的性格,在毁灭时就愈显悲壮,悲剧不正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么?于是不知不觉地,人物性格描写便开始趋同,而那些熠熠发光的东西却因为与“恶”相关而渐渐暗淡了。这或许是“改编”的代价,但在我看来,这种代价值不值得付出,或者是不是非要付出,是可以斟酌的。
改编经典,是一个复杂并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这里不能说得很透,只是就电视剧《水浒传》在这方面的尝试发表些意见。无疑,这次尝试是富有成效的,从专家和社会两方面反馈回来的信息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我以为它给电视剧创作带来的积极影响还不止这些。从长处看,影视与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的联姻是一项方兴未艾的事业,而且有着美好的前景,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尝试及成就只是一个铺垫,未来的文学经典与影视经典的合璧,或者说真正把文学经典改编成影视经典,才是影视艺术家及批评家为之奋斗的目标。为此,象电视剧《水浒传》这样较为成功的改编出现后,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忙着庆功,而是冷静地寻找得失,总结出一些可以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的艺术经验,以利于整个电视剧艺术的发达。我之所以在为《水》剧通过民众检验而振奋之余,写上几句“附言”,用意盖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