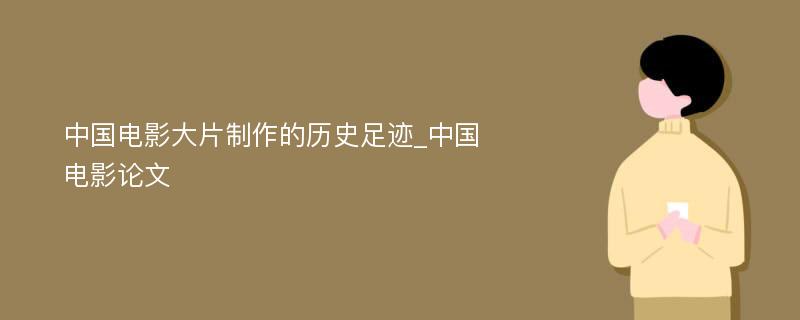
中国电影巨片生产的历史足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巨片论文,中国电影论文,足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0)01-0055-12
中国电影的巨片(或称“大片”)生产与制作,在新世纪的当下,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电影工业系统中最令人关注、最受人重视的核心与关键。它不仅满足了中国电影观众文化消费的需求,也满足了以捍卫、发展、重塑中国电影市场为基本任务使之能与国外电影大片进行竞争的需要;它不仅满足了中国电影观众文化鉴赏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也满足了以扩大再生产为目的、推动中国电影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它不仅满足了中国电影进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基本需要,也满足了以进入国际电影市场为目标、持续扩大中国电影在全球的影响力、塑造中国国家“新形象”的战略策略需要。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电影巨片的生产、提高和健康发展,就成为中国电影工业不可回避的重大任务和现实挑战,成为中国电影在未来不得不慎而待之,而又不得不决而断之的一个历史性选择。
“巨片”、“大片”的产生及相应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美国好莱坞20世纪7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的历史。《宾虚传》、《音乐之声》、《埃及艳后》等影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现,是好莱坞针对派拉蒙案判决之后电影环境的变化以及为实现与全民普及的电视进行竞争的策略性产物,并由此奠定了宽银幕、立体声、高投资、大场面和超级明星演绎的超级奇观的大片模式。至70年代中期,伴随着市场营销以及数字化技术在电影产业中的愈益重要,一种被贾斯汀·怀亚特称之为“高概念”的电影出现了。[1]从此,一种“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被明确确定下来,并在《大白鲨》、《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一系列“高概念”影片中被发扬光大。至21世纪,随着单片投资规模的大幅度攀升以及数字化技术手段的全面应用,模拟影像的传统形态已逐渐被一种奇观迭现、幻境层出不穷的虚拟新形态所代替。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大片新形态创造趋势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已成为各国电影工业无法回避的角逐市场空间的产销模式,自然,中国的电影工业也无法置身其外。
然而,近30年来,尽管世界各国的电影工业以不可避免之势被卷入了大片生产的时代,并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带来的文化全球化、文化市场的一体化而得到不断发展,但各国的电影工业在大片生产的形式、规模和文化特质上,还是有许多的不同。中国电影的大片生产毫无疑问地呈现出自身的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轨迹。因此,以交叉、并置和互文本为基本思路,回顾和梳理中国电影自身的大片生产历史足迹和民族文化叙事道路,对于进一步评估和展望中国未来的大片生产,乃至以积极姿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巨片生产,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电影大片生产的起步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工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为树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形象和建立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努力在电影作品中积极探索和尝试宏大叙事以及全景式史诗样式的书写方式,企图使中国电影以完全摆脱建国前的姿态呈现,以一种“宏大”、“阳刚”、“拨云见日”的新气魄、新形象,完成与新中国的同步建设。这一初衷,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电影工业在大片生产方面的萌芽初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大片制作的追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宏观的历史视野和民族豪情,叙述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战争的全局性进程,力图表现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前赴后继的斗争史和胜利史。
在这样的创作主旨下,出现了《南征北战》、《红日》、《万水千山》、《宋景诗》、《林则徐》等影片。无论是在规模上、视野上,还是在史诗品格、民族传统美学的应用上,这些影片都表现出了与建国前乃至同时期其他影片所迥异的特质。民族,特别是民族斗争的历史及其不屈的民族精神气质,成为这一时期这一类影片特意渲染的关键词。它有别于建国前那种个人或贫富斗争式的书写,而是着意于在敌我的框架内,滤去民族属性中的杂质,以单纯的斗争式方式,将民族的豪情尽情泼墨于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未来胜利必属于我们的民族自信之中。同时,这种对决,又往往重叠于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和历史斗争的经验法则,因此使得这种表述,具有远胜于以往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其规模的延伸、扩大与史诗品格的营造,便也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物质条件下,在其制作、创作和内容等方面,都达到了同时期乃至以往都难以达到的比较宏大的规模。
第二,塑造银幕上的杰出人物和普通平民的英雄形象以确立一个国家银幕的英雄形象,或是跨国界的全人类英雄形象,始终是大片生产中的一个中心任务。
在民族、历史的书写基础上,突出民族的群像,或者是个人,特别是个人中的杰出人物或英雄人物,成为此时期与民族书写同等重要的一种策略方式。《上甘岭》、《万水千山》、《董存瑞》、《林则徐》等等,都贯彻了在宏大叙事中突显历史英雄和当代英雄的主旨,以其历史的传承性和民族的感召力,激励着后来人,成为了深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银幕历史故事。新中国电影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一选择,既是新中国建立后区别于建国前银幕人物形象的一种必然性选择,也是世界各国以本民族的英雄人物来打造本民族的英雄电影史诗的一种普遍共识。不同的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欧美国家电影,更倾向于将本民族的英雄人物塑造成跨国界的全人类英雄人物,救世主的色彩极其鲜明,而对于中国而言,至今仍停留在民族英雄人物这一层次上。因此,尽管这一特点被延续了下来,但亟待提高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三,在20世纪中期全球冷战格局下,两大阵营的紧张对峙,成为全球性在政治、生活、文艺创作等各方面普遍存在的现象。而此时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其电影大片创作,也就不可避免地跟这种国际话语构成了一种互文本关系。一方面,这种紧张的对峙关系,加强了电影文本中的叙事对立关系和指涉隐喻关系;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电影当时面对的是与西方国家停止交流且文化对峙的冲突局面,所以主要吸收和借鉴了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创作经验。《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列宁在十月》、《宣誓》、《难忘的1919》等前苏联影片,成为了中国大片萌芽状态阶段的主要互文本对象。实际上,《攻克柏林》和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解放》所代表的两种叙事模式及其美学风格呈现,对于中国国产大片的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攻克柏林》所代表的“以人携史”的叙事方式,是将主人公的成长、磨难、生离死别放进历史的大环境中去描述,是战争史诗性表述与传统情节剧模式相结合的一种生成方式,新中国电影中的《万水千山》、《英雄儿女》等影片,就属于这一模式;而《解放》所代表的大型叙事系列剧及其“以史带人”的叙事方式,则是以历史铺展的恢弘性作为电影展现的主要目的,人物塑造仅作为叙事的一种辅助策略在历史或战争的推进中给予简略性展现。此时期的《南征北战》是如此,后来的《西安事变》也是如此。而集大成式的系列史诗片《解放》的叙事格局和历史语法、电影造型和俯视视点,更是直接影响到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史诗大片《大决战》的表现形式和书写模式,是电影互文本关系被实际运用的一个生动实例。
由上观之,无论是从20世纪70年代大片概念的产生来看,抑或是从世纪之交中国产生了进入国际电影市场的大片现状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述影片都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片,然而,从影片的历史意识、民族内涵、宏大视野的话语建构上来说,50至60年代的中国历史和当代题材所借鉴、开创的宏大叙事,具备了这一片种的文化、历史品格和基本要素形式,为其后中国国产大片的逐步发展,打下了初始的基础。
二、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历史大片全方位成长时期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民族历史大片得到充分发展的年代。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电影艺术创造力全面提升的年代,也是中国电影工业成规模化发展的年代。90年代整整十年民族历史大片全方位的生产,为21世纪初中国能够生产出进入国际主流市场、展开国际商业销售的大片,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历史大片的全面繁荣是以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一系列重要举措为前提的。1987年,国家设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设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专项基金;颁布了一系列推进大片制作的政策措施,从政策、资金、实践操作三个方面,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创作,给予了全方位支持。这些举措,直接促进了80年代民族历史大片的成功生产。80年代,中国先后生产、创作了《西安事变》、《南昌起义》、《血战台儿庄》、《孙中山》、《开国大典》等影片。这些民族历史大片,高屋建瓴,气势磅礴,以清醒、客观的历史主义观点,表现了20世纪中国现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尼克松说过:“必须是大国、重大历史事件、伟大历史人物,才能在历史上构成推动历史演变,产生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2]正是基于此,80年代的中国大片,一改以往不描写伟大革命领袖的做法,开始将笔触直接深入到伟人和伟大历史事件的宏伟描绘中,借鉴前苏联的创作经验,直接而又深情地开始重塑自己的现当代英雄史、伟人史、重大革命史。由此,80年代中国大片中所反映的孙中山、西安事变中的周恩来与张学良、血战台儿庄中的李宗仁等重大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不但对国内的观众产生了巨大感染力,而且对海外华人,尤其是台、港地区的华人观众群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华人观众不但从艺术欣赏上,更从历史评价上,产生了心悦诚服的民族认同感和历史怀旧意识,产生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捍卫独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
至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国际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歪曲性的描述,通过影视作品来展现更为宏大的国家和民族历史述说被推上了时代的前沿。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所反映出来的空前热情,使得几乎每一部重大影片的生产都是在国家、政府、军队的参与下共同完成的;上升为国家事件,大规模资助,协同作业,对伟人领袖和重大革命战役、革命事件的高度重视,对发行放映的全方位支持,这些显在因素的变化,大大改变了以往中国大片的史诗品质和美学品质,使得中国大片第一次以“国家代言人”的身份,对中国过往或现在的伟大人物、重大事件进行“国家定位、国家历史叙述式”的表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周恩来》、《鸦片战争》、《毛泽东的故事》、《开天辟地》、《重庆谈判》等影片,都以其极宏大的历史背景,将故事内容、影片人物上升至决定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人民生死的高度,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行了浓墨重彩的重书和历史再定位。而这一切,伴随着电影政策的进一步改革,政府资金、境外资金和社会资金的进一步交汇融合,“9550工程”的全面实施,在历史和现实诸层面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深化。
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历史大片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现代民族历史大片空前的规模化和宏观性。首先《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影片,皆以空前的规模和全景式的历史视野,展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重大历史转折以及历史洪流中历史人物的主体化形象。宏大的叙事架构,规模化的历史场面再现,纵横捭阖的镜像运动,皆成为这些大片的典型标志。在规模化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决战》,它的拍摄自始至终都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早在1984至1985年,中央领导就提出要创作反映“三大战役”的影片。1986年初,当时的中央领导明确指示“八一”电影制片厂组织各方面力量,尽快尽好地完成这一任务。摄制领导小组成立以后,为落实拍摄所需的经费、兵员和装备等,军委从十分紧张的国防经费中拨出数千万元的专款,并责成总后勤部全力支持拍摄;总参谋部特将有关部队的训练任务转换成参拍任务。该片拍摄地区涉及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50多个市、县、区,参拍人民群众达15万余人次。人民解放军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兰州五个军区和海、空军的一些部队,陆军、航空兵以及有关院校、武警部队共二十几个军级单位,三十几个独立师团单位、共约13万干部战士参加了拍摄,累计达330余万人次。同时,还动用了大量的坦克、火炮、飞机、舰艇、车辆等大型军事装备。这种大规模的摄制工作和复杂的组织指挥,如果没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的《大决战》影片摄制领导小组和顾问委员会的统一调度,鸿篇巨制如何能铸成![3]而在宏观性上,该片不再单纯着眼于双方的战略思想的高低,也不再单纯局限于双方的你争我斗,而是以历史的眼光,将战争的输赢归结为是否得到人民的支持这一历史性的又是自然性的关键点上。因此,它划开了单纯的输赢问题,将思考的深度引向了历史的深度。
其次,以《鸦片战争》为代表的另一类中国大片,则充满了民族的历史反思和批判精神,在涉及中、英两国历史性冲突的重大事件上,展开全景式叙事,与香港回归的现实进展密切呼应,成为公共话语空间在当下的一种历史性探讨。因此,当两段历史正在以极其巧合的方式重叠时,公共空间的历史性追问就成为一个民族最值得反思的时刻。在这方面,《鸦片战争》借助一个历史事件在公共空间的挪移,为历史性的宏观性展开和探讨提供了一个极其开放的文本。另外,以《兰陵王》为代表的影片又开创了另一类中国大片的形态。在这部影片中,其规模化和宏观性更多来自于一种接近于“好莱坞式”的“奇观化”表述,在被表现的内容上和镜像风格上,它游离于当时的中国大片的主流,开创了新的表现空间和影片形态。
第二,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和家国情怀成为召唤历史记忆和现实情感的双重表述。不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横空出世》;不论是《我的1919》,还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诸如此类的中国大片中,都流露出浓厚的民族主义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尽管这一双重表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基本确立,但在这一时期,显然被大大提升了。在这里,我们且不管它的社会背景和它的政治背景如何,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民族主义和家国情怀,不但成为叙事的直接推动力,而且亦被叙事推动成为跨越叙事层、思想层而直接变为意义符码的一种自动呈现和表述。在这一点上,它显然超越了前一时期的叙事设置而表现出一种更为宏大、更为久远、更为动情的历史内涵和现实哲思。
第三,人物奇观美学形态的确立,奠定了中国大片未来可以超越的基础。前苏联在史诗电影中所开创的“以人携史”和“以史带人”两种叙述方式,在这一时期,被中国大片彻底而又灵活地借用了过来。前者如《周恩来》、《毛泽东的故事》等。实际上,这类影片可视为中国大片的一种扩展形态。以《周恩来》为例,作为人民公仆的理想化形象,对他的塑造实际上内在地建构起了一种个人情怀、历史记忆、民族情感和国族认同的多重表述,达到了塑造领袖人物的一个高峰。而后者则如《大决战》、《大转折》等。同时,出于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宣传的需要,这两种表现人的方式,都从前一时期的单一和低徊上升为此时的“奇观”层次,并真正与娱乐片、艺术片迥异,从而真正创造了“人物奇观美学”的大片形态。由于叙事人物的成败以及影片是否引人入胜更是直接关系到一部大片的成败,因此,“人物奇观美学”形态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大片的基本成熟。而纵观国外的大片发展道路,除却绚丽的特技和恢弘的场景,奇观性人物的塑造其实一直是其不变的核心。所以,人物奇观美学形态的中国大片在这一时期的确立,尽管还显得单薄和不够丰富,但起码具备了未来可以超越的基础。
然而,尽管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历史大片获得了全方位的大发展,但与“高概念”意义上的好莱坞大片相比,还是存有着很大的差距。怀亚特认为,高概念是“一种高市场化的故事形式。这种可销售性的基础是明星、明星和人物形象之间的契合,以及时尚主题”。[4]而另有论者认为,所谓“高概念”电影,是以美国好莱坞为典型代表的一种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的“四大”商业电影模式,其核心是用营销决定制作,在制作过程中设置未来可以营销的“概念”,用大资本为大市场制造影片营销的“高概念”,以追求最大化的可营销性。“高概念”的“高”,往往来源于大导演、大明星、大场面、大事件,这些“大”给电影带来了“高概念”,使电影可以被识别、被关注、被期待、被炒作和被营销。因此,“高概念”往往意味着大制作、大投入、大营销,在数字化时代以后,也往往意味着高科技。正是这些“大”作为概念形成了影片的独特卖点。电影从创意、生产到走向市场的全部过程,都在利用这种“大”作为“概念”进行营销,以创造巨大的市场影响和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5]92以此来反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大片创作,尽管在大投入、大制作、大场面等方面,与“高概念”好莱坞大片有些接近,但其最核心的大营销、大市场和高科技却是严重缺失的,这注定了它的“高”与“高概念”的“高”,并不完全相同。而这,也恰是我们未来将要努力改变的重点。
三、新世纪:中国商业大片的国际化运作时期
自2002年《英雄》横空出世以来,中国大片以史无前例的加速度运动开始向好莱坞“高概念”大片迅速靠拢。由此掀开了中国电影史上真正的“大片”时代。随后的《十面埋伏》、《天下无贼》、《无极》、《霍元甲》、《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功夫》、《长江7号》、《功夫之王》等,都是这种“高概念”下的产物,它们一经甫出,立即成为中国电影票房的生力军,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从表面上看,中国“大片”呈现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一致性:高投入、大制作、国际组合、商业化运作等等,但实际上,中国“大片”并非是一种单一存在,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它已发展出五种主要形态并经过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以张艺谋为主的“功夫”阶段,周星驰、于仁泰是其补充,影片代表作是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周星驰的《功夫》,于仁泰的《霍元甲》等。其主要形态是以展现中华传统功夫为主的“功夫片”样式。在这一形态中,人物、故事情节、空间、摄影机运动等等,皆服从于展现中华功夫的“美”与“奇”,其背后所显示的,是一种“力”的象征,它间接指涉了以国内民间资本为主的经济力量在此时的一种强烈诉求和经营策略。第二阶段主要是以陈凯歌为主的“奇幻”阶段,刘镇伟等是其补充,代表影片是陈凯歌的《无极》和刘镇伟的《情癫大圣》,动画巨制《魔比斯环》也可归入此类。这一阶段的主要影片形态是以展现“东方奇幻”为主的“奇幻片”样式。在这一形态中,打斗、服装、人物造型、空间营造等等,都围绕一个“幻”字而展开,它所显示出来的,不仅仅是民间资本的活跃,而是国际混合资本对中国的一次“东方想像”。第三阶段主要是以冯小刚和张艺谋为主的“经典再造”阶段,张之亮、李安、吴宇森等是其补充,其代表影片是冯小刚的《夜宴》、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张之亮的《墨攻》、李安的《色戒》以及吴宇森的《赤壁》等。它们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皆致力于对“经典文本或经典人物”的现实性改造,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一种“主题的再生”,因此,此类影片可称之为“经改类”样式。在这一形态中,原先的文本意义大多被剥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另类读解,或称之为“现实化的重塑”。在这里,历史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再造;因此,如何讲述也就是讲述的方式,是这类影片的共同点。它背后显示的,是国内资本伴随着自信心的增长,以求对经典重新改造并使之上升为一种深具东方特色的世界主义的普适企图。第四个阶段是以冯小刚和陈可辛为主的“本土化”阶段,周星驰是其补充,其影片代表作是冯小刚的《集结号》、陈可辛的《投名状》和周星驰的《长江7号》等。第五阶段是以罗伯·民可夫为主的“神话重塑”阶段,其代表作就是罗伯·民可夫执导的《功夫之王》。本文之所以将它单独列为一个阶段和一种形态,主要原因是它和前面所提及的“经典改造”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合作方式(好莱坞编导,中国主演),也开创了一种新的文本写作方式,它使得中国的神话故事第一次真正变为“世界主义的”,从而实现了对“经典改造”的历史性跨越和现实性重写。在某种意义上,当本民族的神话传说不再单独为本民族所拥有时,它就已经获得了一种“世界认同”与“价值再生”。因此,无论从产业经济角度还是从文化发展角度来看,它都是值得认可的。它会迫使我们走出本民族的狭隘的文化观,而以一种更加开放和更加自由的心态,对其他民族的神话传说进行一种“中国式的世界主义重塑”,尽管这一重塑在现阶段还不可能,但却不能排除未来的可能性。①
上述五种形态的存在,显示出中国大片与其背后的投资主体所存在的复杂关系,但事实上,中国大片在此时期基本延续了三种制作模式:一是本土化制作模式;一是与香港的合力开发模式;一是国际化的合作模式。这三种模式虽各有特点,但国际化的市场运作模式和国际化的市场目标却是一致的,它显示出中国大片在“资本属性”上的真正渴望,从而以一种接近于“疯狂”的反弹方式开始了商业对艺术的彻底改造。21世纪初中国大片的这一次真正“勃兴”,显示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如下特征:
第一,彻底的消费主义奇观狂欢彻底取代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和家国情怀,在市场的诱导下,中国大片玩起了拼图游戏,各种思想与价值观的杂糅,未能给此时的中国大片带来主题鲜明的“高概念”,反而使中国大片落入清浊不分、含混不清的“平面化”荒漠。《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影片都是如此,场面的浩大与制作的精美,掩饰不住思想的贫乏与价值观的模糊。第二,单纯追求市场的最大化所导致的题材类型的单一化,成为中国大片发展中最严重的阻碍。看看好莱坞琳琅满目的类型大片,中国仅有的“宫廷武侠片”、“功夫片”实在令人难以满意。同时,这种靠单一博取市场的赢利方式,也必定会给中国大片的未来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带来严重危机。第三,由于核心价值观的缺失,中国大片在主题和价值观上的游移和拼凑,同样造成了叙事的割裂、悬空与混乱。这种情形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无极》、《十面埋伏》、《夜宴》等影片中,而最近的《南京!南京!》也是一种价值观的拼凑版,由此所带来的叙事上的混乱与割裂,尤为明显。第四,核心主人公的缺失、不“立”或“难产”,成为多数中国大片的一个最大损失。尽管传统的人物塑造,并非是大片创作的首要任务,但承载着核心价值观与核心思想的核心主人公,仍是广大观众充满期待、产生强烈认同的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一点,中国大片的发展将会陷入自身制造的窠臼。在这方面,前一阶段所确立起来的“人物奇观美学形态”,反而具备未来的可拓展性。
此外,尽管这一时期的中国大片在大营销、大市场方面较前一阶段获得了长足性的发展和突破,但数字技术、高科技的缺失,使得此时期的中国大片不仅与好莱坞的“高概念”大片仍有不小的差距,同时也是制约中国大片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当“创造影像”、“虚拟影像”替代“再现影像”越来越成为世界电影大片发展的主流时,我们似乎是除了固守“功夫武侠片”之外,只能向“文艺大片”突围,而灾难大片、科幻大片等多类型、多方向并展现中国科技未来、思想未来、人类未来的大片片种,却仍是我们心中的痛。
四、展望中国大片主流文化新高度时期
近几年来,电影界一直在为厘清“主旋律电影”、“主流电影”、“主流文化”等概念而努力。简单说,一种基本的倾向认为,“主旋律电影”所代表的文化应称之为“主导文化”,“主导文化”是由政府提倡、体现着当下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廉洁奉公、舍己为人等一切政府宣扬的主导品质,同时又得到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支撑的一种“箭头型”文化;而“主流电影”所代表的主流文化应再次与国际接轨,回归到“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行列,体现了一种植根于普通大众、着力表现普通大众的喜怒哀乐,同时又代表着人类基本情感、基本价值取向及基本未来方向的“柱尾型”文化。前者遵循的是先进和主导的原则,而后者遵循的是普世和大众的原则。②
尽管上述两种分类依然有其重叠和相互渗透,但可喜的是,我们能看到中国的一些大片正在不自觉地朝着“主流文化”的方向迈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生产出了《集结号》、《投名状》、《云水谣》、《赤壁》、《画皮》、《梅兰芳》、《南京!南京!》等大片,形成了与纯粹讲求市场与国际化运作的中国大片完全不同的特质,在“主流文化”、“主流电影”的新界定、新定位上,给出了自己的主动性表述。它们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尽量还原至“人”自身的尝试和努力,使这些大片开始回归到对人性所普遍存在的共同性的探讨上来,超越了“人物奇观美学”中对人物的“神性”表述和“超视觉奇观美学”中对人物的“魅性、妖性”表述,而逐渐退回至“人性”的表述。《集结号》中的谷子地,已不再是“主导文化”的代表,他既是服从组织、无怨无悔的英雄,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困惑、迷惘、坚韧、勇敢且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个人”,他吹响的,不是战争的集结号,而是人类最难能可贵的独立精神的集结号。而在《投名状》中,三兄弟的设置,特别是大哥和二哥的塑造,都突出了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望和反思,他们不再是铮铮铁骨、毫无瑕疵的汉子,而是更多地折射出了困惑了人类几千年的最基本的人性和兽性的矛盾。此外,《画皮》中对周迅所饰演的角色——尽量压抑妖性、增强人类共同的人性——的处理方式,也是主动向“主流文化”靠拢的一个生动的案例。
第二,大片意识开始被一种较为均衡的、非偏激的、多类型的、多元化的“质”所填充,而不再是一些徒具形式的杂糅和组合。在一个合理的框架和合理的条件下,寻求对中国大片的充分认知,是中国大片在走过最初的疯狂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最可贵的精神。受这些反思拉动,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大片开始处理人性的基本问题,开始处理历史问题,开始处理题材问题,开始处理文化问题,并尽力在多类型、多元化中尝试着突破与探索,譬如《集结号》、《云水谣》对战争类型的突破,《投名状》、《赤壁》、《南京!南京!》对历史题材的突破等等,都表现出一种拓展和对主流文化多种表述的认同。
第三,叙事人物开始摆脱不“立”的窘境,而逐渐走向“独立”和“丰满”,好莱坞大片所倡导的“人物弧线”原则,正在被新一批的中国大片所借鉴或参考。而与此同时,叙事人物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与转变,也开始显示出中国大片在与国际接轨中进一步的可能性。在这些大片中,除了谷子地、大哥、梅兰芳等人物的成长弧线有目共睹外,人物身上的“现代性”成长,也正突破着传统的书写方式。《投名状》中徐静蕾所饰演的二嫂,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贞形象,而是为了爱情而敢于争取的一个“现代女性”。
因此,尽管这一类中国大片,仍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在尝试对主流文化的回归和探索上,它们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达到了这一时期主流文化的新高度。
五、结语:一种不变的思索与探讨
中国电影巨片的生产与创作,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已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中国电影人的努力下,中国电影巨片的生产已经取得了较为辉煌的业绩,不仅扬名国内外,而且还打进了欧美主流电影市场;不仅确立并巩固了中国电影的主要传统类型和项目优势,而且还正在积极地寻求着各种创作突破的可能,为今天,也为将来中国电影的巨片生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当我们与美国好莱坞等电影大国进行横向比较时,我们又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而在这个差距的不断重复中,探讨如何缩小这个差距,应当是所有中国电影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结合前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电影巨片的生产,若想将来取得更大的辉煌,必须重视如下几点:
第一,必须重视、加强中国主流文化和人类共同性的建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认为,中国应“多讲共享价值,‘共享’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这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人本主义是中国各民族唯一能够共享的。即使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归根到底还是人本”。结合中国的历史经验以及国外的传统,这一观点值得我们参考。所以,加强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共享价值和人类共同性的建构,将不仅是中国电影巨片的任务,也是中国各文化艺术门类的任务。只有将此全面贯彻、推广下去,中国的对外宣传才会显得顺理成章,中国的艺术之花才会怒放,中国的大片创作才会蓬勃发展。
第二,必须重视、加强中国电影巨片创作的多元化、多类型建设。近几年来,中国电影大片只有一两种类型的说法,已成为中国电影人和普通民众心照不宣的常识性认知,而事情的悖论在于,当我们无奈地接受这一说法时,其实我们已经错失了寻求多元化、多类型开发的机会。中国当下的问题是,仅靠“武侠功夫片”或“战争史诗片”,是不能将中国电影推行到世界各国的影院中的,况且,中国的“战争史诗片”至今仍局限于民族主义和两党之争,而未上升到“世界反法西斯”等人类共同关注的高度。因此,加强中国电影巨片向文艺巨片、灾难巨片、科幻巨片等展现“中国人理想、信念和未来同时也是全人类理想、信念和未来”的类型大片的过渡和建设,将是中国电影巨片的当务之急。
第三,必须重视、加强中国大片发展的工业化体系建设。面对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业,再也没有人对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化的建设提出异议,在复杂而又庞大的工业化体系中,本文认为,中国目前最为急需发展的,当是数字化、高科技的研发、应用与提升。当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在惊叹《变形金刚》、《哈利·波特》、《魔戒三部曲》等大片中的数字化特技时,我们花巨资买进的高精尖的数字化设备,却静静地躺在厂房里无人来用。而这方面的缺失,却又成为我们搪塞不能拍摄其他大片的一个重要理由。现在的情形是,当我们的战舰编队已在爱琴海上对海盗船进行打击时,当我们的载人火箭已成功飞天时,当我们的国家形象正愈益变得强大时,我们的影像技术却未能跟上这一发展的步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电影的一大遗憾。
第四,必须重视、加强国际化、全球化市场运作人才的建设和市场开发。尹鸿教授在《“高概念”商业电影模式初探》一文中这样描述道:“高概念”电影作为商业项目的本质,促进了好莱坞电影产业的繁荣,也导致商业性在好莱坞电影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目前在好莱坞各公司内,商业业务人员越来越多,电影艺术创作人员越来越少,发行部门和市场管理部门的人员编制是电影制作部门的好几倍。现在好莱坞被称为是一个巨大的集金融、工业和商业为一体的经济实体,而不再是一个“艺术创作”实体。[5]93对于中国电影而言,这种趋势也是势在必行,而懂得国际化、全球化市场运作的商业性人才,将为此而变得愈加重要。
此外,伴随着国家形象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提升,伴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日益提升,如何让世界各国的人民充分认识中国,这不仅是一个国家外交部的事情,也是举国上下每个公民的事情,更是中国巨片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就此而言,中国大片的未来仍将任重而道远。
收稿日期:2009-11-09
注释:
①详见万传法博士论文《当代中国电影的工业和美学:1978-2008》,第237-238页。
②此方面的论点可参考赵卫防《中国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与发展策略——“全球视野下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及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等文章,载《当代电影》,2008年第1期。
